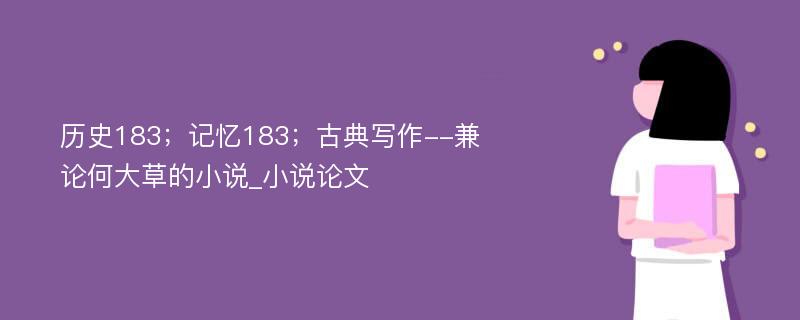
历史#183;记忆#183;经典化写作——何大草小说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记忆论文,经典论文,历史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记忆,经典化写作,当我写下这几个关键词的时候,心里有点儿发虚。我不知道这些词语离何大草的小说究竟有多远,能否真正抵达他所建构的那个象征世界。何况,从1994年那个最寒冷的日子写下中篇小说《衣冠似雪》的第一个字,如今,何大草已发表长篇小说《午门的暧昧》、《刀子和刀子》、《我的左脸:一个人的青春史》、《盲春秋》、《所有的乡愁》等中短篇小说近100万字。题材涉及历史和现实、革命和青春。各色人等轮番上演,内容之丰富令人咋舌。文体上不乏先锋实验、西学意味,又有宋元话本、明清小说的流风遗韵,还有唐诗宋词的意境。人物的言谈举止、情态心理,以及小说的叙述话语和叙述方式间,隐约地传达出华夏古老文化的鬼魅精魂,现代人生的倦怠、荒凉、颓废,甚至虚无和荒诞,由此将一扇扇隐匿的人性之门悄然打开,让我们得以窥见人存在的多种可能性。
何大草的小说写作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卡里斯玛型社会解体、文明分崩离析、价值处处挫败、华洋错杂、多元文化并存,一个主动汲取人类优秀文化传统,自觉追求“经典化写作”作家的全部努力。尽管这种努力的结果,可能是被不断地边缘化,情形正如米兰·昆德拉在谈到“人性危机”和“人的存在”不断被遗忘的境遇下“塞万提斯的遗产”所受到的诋毁一样①。这并非是要把何大草与塞万提斯相提并论,而是说,何大草做出的这种努力,虽然不被这个时代所重视,但依然而且更加可能会给我们的文学和小说写作带来新的经验,甚至有可能是弥足珍贵的经验。伊格尔顿在评述结构主义时突发奇想:最“真实”的东西并非就是我们经验到的东西,现实与我们对现实的经验互不相连②。这或许是我们看待何大草的小说和今天的文学的另一种颇具洞见的眼光。
历史
荆轲在千钧一发之际展现给秦始皇的并非见血封喉的匕首,而是秦始皇夜夜不离枕下的竹剑。历史系出身的何大草,第一次以作家身份亮相文坛,就对“历史”做出如此“篡改”,所隐藏的“机心”显然不同凡响。那时,苏童等一批“新历史小说”家刚刚度完他们的蜜月期,在极度的兴奋之后,疲惫地寻找着新的入口。何大草当然受到过他们的影响,但接下来荆轲对秦始皇说的那句话不仅使秦始皇目瞪口呆,也使我们看到何大草举意超越那批“新历史小说”作家的某种企图:“我来就是为了向陛下证明这件事的。”哪件事?就是我荆轲随时可以杀你却没有杀你这件事?这不仅有违刺客意志,不符“历史真实”,有悖生活常理,也与太史公对荆轲的悲壮叙写大异其趣,不过在这里却透露出何大草小说历史的某种抱负:主要还不是像新历史小说家前辈那样,通过文学的叙述拆解、颠覆主流的历史,寻找曾经被书写的历史与今天现实的某种深刻联系,或者说,这些留在纸上的过往记忆,如何进入今天的现实,如何化为血液在我们今天的生命中迁衍流淌,进而塑造我们的人性,牵绊、左右着我们的现实姿态,阻碍或者加速了我们走向未来的脚步,使我们成为今天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什么,并如此这般地生存着。
何大草的这类小说,在他的写作中占有相当大比重。除中篇小说《衣冠似雪》,还有《李将军》、《一日长于百年》、《天下洋马》、《春梦·女词人》、《天启皇帝和奶妈》,短篇《俺的春秋》、《千只猫》、《献给鲁迅先生一首安魂曲》、《带刀的素王》,长篇《午门的暧昧》和《盲春秋》等等。其中,中篇小说《如梦令》可谓其代表。
《如梦令》讲述南宋女词人遭遇战乱、丧夫,偏居江南后的故事。欲望的缺失是小说叙述的动力和叙述的起点,也是联结历史和现实的关键所在。小说把两个看似完全无关的故事,并置于同一个叙事时空,在延续与断裂中加以铺展:寡居江南的女词人,难以抑止生命本能的驱动,在无言的精神焦虑中过着白日梦一般的生活,最后与艄公的儿子寤生做起“摸鱼儿”的游戏;一对知青男女在动荡的政治生活中饥饿难耐,携手穿越江南迷宫般繁复的小巷和山丛,去一个小镇寻找稀饭馆,结果同样迷失在“剥青蛙”的游戏中。有趣的是,这对知青男女无意中还窥听了万大嫂与李会计苟且时发出的“猪吼”般的喘息,正像女词人夜间听到青梅把她的丈夫赵“置于驭下”所发出的呻吟和呐喊。这绝对是四个“偷情”的故事,只不过是两个大的“偷情”故事套两个小的“偷情”故事而已,其中有明有暗。“打通”或者说“缝合”这两个古今“偷情”传奇的“纽扣”,竟是一本据称是《粉红莲》的词集。小说的巧妙之处在于,当作者把这两个相隔千年的“偷情”故事,“后现代”地搬演于同一叙述时空时,就在“重复”中自动呈现出了“对比”。而“对比”却像一把神奇的钥匙,开启了小说多维阐释的空间,衍生出丰赡的意义。无论是多愁善感、才情横溢、名留青史的女词人,还是被意识形态所塑造的现代知识青年,甚或是懵懂无知粗鄙不堪的乡野男女;无论是出于战乱、动乱、骚乱等别的政治、社会的原因;也无论是江南是塞北是漂泊是自愿放逐是异乡客是土著民;也无论这朝代如何更替时代如何变迁时光如何流转,人类都有一个共同点——欲望的复合体。在此意义上,《如梦令》不仅告诉我们一切皆流,欲望恒在,人性的历史就是欲望的历史,探察欲望就是勘探人性,发现欲望就是发现人性,也就是发现历史;迁衍不息,永不枯竭的欲望之流或许正是历史发展绵延不绝的动力,一如西哲云,“欲望在其本质上是革命性的”。“作为一种革命力量,欲望试图颠覆一切社会形式”。③
从“欲望”进入历史,何大草的历史小说就找到了与现实的结合点,同时也找到了通达普遍人性的途径,并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意义上找到了人类再次还乡的道路。如果说,《如梦令》展示的是欲望缺失后人性和人存在的某种可能性,那么,长篇小说《午门的暧昧》描绘的则是一幅欲望溃败后的人性面相。小说讲述了大明帝国崩溃瞬间的历史。而这段历史的溃败被小说演绎为欲望的溃败,或者说肇因于欲望的极度匮乏。小说主要设置了两处互为映照的地理空间,一处是红墙碧瓦、古木苍然、深不可测的紫禁城,一处是桂木簇拥、青楼如云、醉生梦死的木樨地。前者位于京城的核心、帝国的心脏,后者居于京城的边缘、人性末端。前者是父权和极权的象征,后者是母亲和性爱的诱惑。中间还穿插了暴力的故事:冥王——快刀李可安沉溺于从无原则的杀戮中寻找某种人间平衡的快意,素王——名捕马梦园则依据信而有征的“理由”挥刀断头维持铁桶一般的秩序。这三个故事虽然作家用力各异,但在实际上成为三种欲望的象征:权力的欲望、性爱的欲望和暴力的欲望。三种欲望互为补充,互相生发,推波助澜,成就历史。可以想见,当这三种欲望到达巅峰的时候,也是大明帝国的太平盛世。但是,到了崇祯一代,这三种欲望不可避免地疾速走向衰竭。随着欲望的不断委弃,慵倦、孤独、绝望、虚无弥漫整个帝国,大明江山愈来愈失去前驱的动力,在李自成大军等外力的咄咄催逼下摇摇欲坠,直至在“人闲桂花落”的历史情景中轰然倒塌。欲望的溃败导致人性的全面萎缩,人的生命活力的极度枯竭,以及历史原动力的彻底丧失。
显然,欲望的溃败较之欲望的缺失对人类的打击和破坏更为巨大,是根本性的、决定性的和毁灭性的,而后者不过是人的一次离家出走与回归。缺失和溃败是人的欲望的两端,更多的时候是人的欲望的控制和升华。在弗洛伊德看来,恰恰是人的欲望的这种控制和升华,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历史。何大草的历史小说《衣冠似雪》和《盲春秋》正是这一点触及到了历史发展的“玄机”,而将早已沉入时间黑洞的过往引向未来,生发出智慧的熠熠光彩。历尽千辛万苦决意要刺杀秦始皇的荆轲,在壮志快酬的瞬间却突然改变主意,用一支对生命毫无威胁的竹剑代替了涂毒的匕首。他只是想证明自己有能力刺杀秦始皇,是一个真正的“壮士”,却不必让秦始皇丢失宝贵的生命。何大草对荆轲刺秦这一历史结局的如此改动,不仅完成了荆轲这一古代“壮士”向现代“士”的转变,而且也使这段历史富有了当代意义。著名导演张艺谋以几乎同样的方式处理影片《英雄》的结局时,《衣冠似雪》所隐含的当代意义被进一步确认,却没有人问:张艺谋是否在何大草的这篇小说中受到过启发?当然,你会说,残暴的秦始皇并没有因此放过荆轲,而是对荆轲的友善无动于衷,他的剑尖毫不犹豫地刺破了荆轲的白衣白袍,直至插进荆轲善良的胸膛。荆轲的行为并未能“以善抗暴”、“以爱抗恶”,这如何理解?我认为,一方面荆轲血染白袍可以唤醒人们再一次对暴政和极权之野蛮行径及其反人性、反人道、反文明的实质的体认;另一方面,多一个人示爱,多一个人行善,总比冤冤相报,杀戮相因,更符合人性的需要,更接近人类的文明。
相似的情形出现在长篇小说《盲春秋》中。李自成大兵压境,崇祯皇帝无计可施,大明江山已岌岌可危,帝国易主不出数日。但就在这时,李自成却快马传去手书一封,希望面见崇祯皇帝一次,共商“天下”大计。其真实目的是恳请崇祯皇帝效法古代明君,实行“禅让”,以不动一兵一刀实现政权平稳交替,免除京城百姓流血之灾。虽然商讨的结果是皇帝对“禅让”一事毫无兴趣,但这个超出历史“真实”的故事叙述本身,却蕴含了丰富的人性况味和现代意识:将暴力和战争的欲望放弃和升华到一个现代文明所指向的目标上来。《盲春秋》的故事发生在古代,何大草穿越历史的眼光却在当代。
记忆
哈罗德·布鲁姆把文学史看做巨人之士的英勇战斗,视为作家为自我独创进行斗争的强大“表现意志”。④每个后起的作家,都在前辈的巨大阴影之下进行创作,何大草也不例外。当他开始写作的时候,此前的“新历史小说”已经显赫一时,他在汲取它们的营养时,只有摆脱它们强大阴影的笼罩,抵挡来自它们的压倒性力量,才能为自己的想象独创性开辟新的阵地。凭着上述的创作实绩何大草做到了这一点。他把文本的历史转化为欲望的历史,并在欲望的缺失、溃败和升华中,重构被大历史掩埋和遗忘了的人性史。他以新的语法结构,擦去厚厚的尘埃,拭亮历史之镜的另一端,让我们一瞥久违了的被自然化的历史语码所深深隐匿的某种历史真相,同时也让历史重新带上体温,渗出血液,焕发生命的活力,进入了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实现了其意义的现代转换,为“历史如何文学”提供了新的经验,成为这个时期新历史小说汉语传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何大草写于2005年的《我的文学自传》里有这样一段话:
从《衣冠似雪》到《千只猫》,在我写出的100多万字的小说中,古代故事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其他所谓的当代题材,也都和记忆有关,与时代没什么关系。记忆这个词我不晓得是否用得准确,在这里我之所以使用它,也是有感于美国南方作家尤多拉·韦尔蒂的一段话:“回忆在血液中形成,它是一种遗产,包容了一个人出生前所发生的事情,就如同他自己曾亲身经历一样。”而小说家的劳动就是“通过回忆把生活变成艺术,使时间把它夺走的一切归还给人”。我觉得自己所有的小说,都是以记忆作为种子,以虚构的热情让它破土、发芽、拔节、生长。⑤
既然何大草所有的小说都与记忆有关,那么上述的历史小说同样逃不出记忆。可是在这里,我更感兴趣的是“其他所谓的当代题材,也都和记忆有关,与时代没什么关系”,重心又落在这句话的后半部分。何大草的“当代”如何“记忆”?“记忆”“当代”又如何可能与“时代”无关?我以为这其间隐藏着何大草一部分小说写作的秘密,隐藏着何大草对小说、对文学的特殊理解。
何大草与“当代”有关的小说,主要有长篇小说《刀子和刀子》、《我的左脸:一个人的青春史》和《所有的乡愁》,中篇《弟弟的枪》、《午时三刻的熊》、《急转弯》等,短篇《黑头》、《白胭脂》、《1979年的爱情》、《裸云两朵》等。这部分小说中,我以为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类:一类是关于“中学生”的;一类是关于“革命”的。对于后者,我将另文讨论。
成功地叙写中学生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并不多见。就我的阅读所及,有三部作品可以提及。一部是王蒙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一部是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据称是新时期“伤痕文学”的滥觞之作;一部是罗伟章的长篇小说《磨尖掐尖》。这三部小说从动笔到出版几乎跨越了新中国60年的历史,反映了几个主要历史时期中学生和中学教师的精神面貌,串联起来,则勾画了一幅新中国中学生的发展史和演变史,应该说对于我们理解和掌握当代中学生题材小说的特征颇具代表性。这三部小说几乎都是从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进入中学生的世界,凭借中学生故事的讲述和文学的话语权力,或者去证实民族、国家、政党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及其在塑造人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或者是对一个时期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和方法进行批判和反思,均具有政治性、政策性和当下性。这或许就是何大草之所谓与“时代”有关。
的确,何大草的中学生小说与此大相径庭。他指尖敲打出的中学生,不是我们日常所见,他们行动在井然有序、表面平静的校园生活后面,游走在一个看不见的甚至是畸变的成人世界的边缘。他们似乎与现行的教育体制,与常规的学生生活和学校管理,与常态的成长历程无关。他们仿佛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时代——一个被主流意识形态反复塑造,被主流媒体反复传播的那个社会、那个时代——很远很远。但又与我们的生活实际那么切近,以至于那个叫“双疤”、叫“熊思肥”、叫“包京生”的中学生就是我们自己的或身边同事、朋友的孩子。我一直认为,何大草通过文学想象发现了另一个中学生的世界,一个不同于王蒙、刘心武、罗伟章,甚至有别于王朔《动物凶猛》的中学生世界。王蒙的李春和呼玛丽,刘心武的谢惠敏和宋宝琦,罗伟章的郑胜和于文帆,更多的是属于时代的、社会的、学校的和老师的,而何大草的那群中学生,则是属于每一个家庭、每个父母、每个兄弟姐妹、每个中学生自己和每个人自己的。他们主要不是穿行在教室、操场、领奖台和考场,而是往返于街道、社区、网吧、家庭,骑着自行车,听着MP3,在烧烤摊驻足,在别的什么地方起哄或者打架的普通孩子。
到此,我们至少看到了两个中学生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对于文学来说都是需要的。只是何大草的世界有别于另一个世界而已。之所以这样,我认为这与何大草的“当代题材”都与“记忆”有关,而与“时代”无关的追求是分不开的。我没有理由去怀疑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但当且仅当生活化为作家记忆的时候,才能成为“文学”的源泉。当生活化为作家的记忆,就意味着它被作家的情感、心理、思想、精神、灵魂所拥抱、所渗透、所改造;就意味着它与作家的成长、经历、失败、成功、挫折、欢乐、痛苦、幸福和苦难联系在一起;就意味着它成为了作家的血液和胆汁、幻想和想象、希望和梦想、意识和无意识,最终成为作家精神史、人性史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说,任何真正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生命记忆和精神自传。就此而言,当何大草来讲述中学生的故事,而又自觉地践行这样的写作主张的时候,他就越过了时代、社会、制度、体制等与中学生的关系这一外在的层面,直接切入中学生也是作家自己曾经最为隐秘的内部世界——青春无助的世界。在那里,作为人的各种欲望正在全面苏醒、萌芽和生长,犹如一头初生的猛兽正在迅速成长,随时可能摧毁肉体的囚笼,狂奔而出,以极端叛逆的姿态,一头撞在冰冷无情的伦理道德和文明秩序的铁网上,直至头破血出,才能完成自己的成人仪式。
长篇小说《刀子和刀子》、《我的左脸:一个人的青春史》里的中学生就是在“刀”和“枪”的伴随下完成自己的成人仪式的。《我的左脸:一个人的青春史》讲述了2004年非典时期的三个月内“我”的成长经历。同学韩韩在“火药枪”的威逼下抢走了“我”的“金牌”,为了这块“金牌”的回归,“我”一步一步地陷入了两个女人的复杂关系中,一个是韩韩的妈妈,一个是熊思肥。这个并不等边的“三角恋”,又牵出了韩韩的妈妈与他的爸爸和另一个男人的“三角”关系。其间还充斥着阴谋、复仇、暴力、性爱与死亡的故事。“我”青春的欲望,就在这样一个阳光照射不到的阴森可怖的背面世界里被唤醒、被激发。小说透过“我”成长的冒险经历,展示了一个畸形、冷漠、血腥和荒诞的成人世界,而这个世界反过来又铸就了“我”最初的人生和人性。
《刀子和刀子》讲述的则是一个女生、两把刀子与性格各异的血性男女同学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恨情仇。故事是如此的触目惊心,使我们不得不怀疑是这个世界错了,还是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和记忆错了,或者我们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局外人”,关于我们的生活,关于发生在我们的孩子——中学生身上的事情,我们知道得如此之少,以至于一个中学生讲出来竟让我们瞠目结舌。《刀子和刀子》出版之初,葛红兵就感慨地说,这是他近年来看到的最好的青春小说,“青春的酷烈、无奈的伤痛被演绎得那么好:懵懂时期的爱情和友谊,叛逆时代的幻想和渴望,仿佛获得了文字的首肯,突然间露出了真相;血肉横飞的身体遭遇与黝暗无谓的灵魂处境是那么真切地遭遇到一起”,它召回了我们最隐秘的青春经验,有助于青少年的自我理解,也有助于成人世界在回味当中自我体认。⑥小说后来改编为电影《十三棵泡桐》,获2006年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大约与小说具有这样的特质不无关系。《刀子和刀子》、《我的左脸:一个人的青春史》可以说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原欲——暴力和性,如何推动人的成长,如何铺展和扭曲人的生命道路,使人成其所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这两部关于中学生的长篇都是关于人的“存在”的小说。⑦
阅读何大草的这类小说,总给我这样的感觉,我们每天都行走在生活的现场,却未必了解生活的真相本身。这也许就是何大草的“记忆”之于小说的好处:它总能穿越生活镜像的表面,直抵镜子的背后,将狰狞可怖的真相近乎荒诞地呈现出来。《刀子和刀子》、《我的左脸:一个人的青春史》尽管把故事置于中国西部的某个城市,放在泡洞树中学、文庙中学中来讲述,或者放在“非典”的特殊时期来展开,但事实上,这些时空背景与故事本身没有必然联系。换言之,把这些故事放在别的时间和地点可以照样讲述,而不会损失它的意义,因为它们是直接关于人的欲望、关于人性的故事,与任何人的成长有关,任何人与此都脱不了干系。
经典化写作
快十年了,我曾经在一篇谈论何大草历史小说的文章中说,“历史细部的精致清晰与整体的扑朔迷离,对比、重复、空缺和双重文本的叙述结构”,以及“‘神话/寓言’模式、诗意视景的运用”都一一印证了何大草“是一个‘形式’的骸骨迷恋者”。他不是那种诱惑语言走向思想,而是被语言诱惑产生表达的作家。“形式先于功能、方式优于内容的审美习惯,使何大草游戏于权威话语既定的审美规则,返回到源远流长的艺术传统自身。当别人沉浸于对‘现实’的模拟映射时,他却在对‘艺术自身’的模仿与创造中获得愉悦,并衍生出反叛传统的根源”。⑧几年前,我甚至有些偏激地说:“何大草的叙述技巧、虚构故事和操作语言的能力,即使在近十年的小说中,比谁也不逊色”。⑨我说的这些话,不仅被何大草后来的创作进一步证实,而且如果我转换一种方式来表达就是:何大草是一个“经典化写作”的作家。
所谓“经典化写作”,其实就是按照文学传统中经典作品的方式来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着命名焦急的文学史,曾将那一时期的文学划分为三类,即主流文学、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其中“精英文学”的实际所指是那些坚守所谓“纯文学”立场的作家写作。现在看来,这种命名并不准确,“精英”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思想史的概念,与“纯文学”的旨意相去甚远。何况搞“纯文学”的并非都是“精英”,是“精英”也并不都写“纯文学”作品,况且一部分“精英”可能跟文学没什么关系。再何况,“纯文学”究竟何指,是否存在,也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我以为“精英文学”和“纯文学”真正想说的是一种我称之为“经典化写作”的文学。按我目前的理解,要对“经典化写作”作出全面的诠释尚有不少困难,但我还是坚持认为,何大草的小说写作即属于“经典化写作”。
前面述及何大草历史小说时,我谈到《如梦令》将发生在南宋时期的女词人的故事与发生于“文革”时期的知青的故事并置于同一个叙述时空来讲述,谈到《衣冠似雪》对荆轲刺秦一个众所周知的结局的“篡改”,谈到《盲春秋》中一个明显与历史事实不符的情节,即李自成请求崇祯皇帝“禅让”;后来我在论及何大草的那些当代题材的小说时,又特别强调他的一个观点,这些小说与“记忆”有关,与“时代”无关。何大草为什么要这样来写小说?我认为,对于历史小说来说,他要通过这种“故意”叙述,造成一种“间离化”的效果,一方面提醒我们,那些已经被“自然化”、被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可能是特定时代特定意识形态的产物,是虚假的历史;另一方面又表明,在人性史的最深处,人类的历史总是在不断地重复和轮回;再一方面,也是我想着重强调的是,他想明确告诉我们:小说就是虚构。文学是在虚构中创造。对于那些当代题材的小说,他有意与“时代”疏离,将“记忆”和“回忆”提高到一个创作本体的位置,依然是想彰显小说的虚构本质。但虚构并非意味着不重要,对于小说而言,“回忆中的每一次邂逅,都在改变着生活”。⑩在小说中叙写记忆、保存记忆,就是在续写鲜活的生命史和人性史,就是在敞开人的存在,尤其在如今这样一个记忆危机的时代。
其实,坚守小说的虚构本质,就是小说“经典化写作”的一种立场。问题在于,多年以来,小说被生拉硬扯地拖向所谓“真实”,其结果使小说变得庸俗不堪。谁会相信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真会去大战风车?谁会相信但丁《神曲》中的炼狱、地狱和天堂会真实存在?谁会相信曹雪芹《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最后真被空空道人带走?谁又会相信卡夫卡《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尔的变成了甲壳虫?如此等等,举不胜举。但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常识,即小说是虚构,却不断被人们遗忘。翻翻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一点就会不证自明。在我看来,坚持小说的虚构本质,就是让小说回家。而何大草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借助“虚构”的无限可能性,并以欲望的发现和人性的勘探作为切入点,才使他自由出入于历史与现实、古代与当代、本土与西方,记忆与想象,努力地探寻着、实现着小说新的可能性。
注释:
①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一部分《受诋毁的塞万提斯遗产》,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页。
②④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第202页。
③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著:《后现代理论:批判性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
⑤何大草:《我的文学自传》,《十月》2005年第1期。
⑥何大草:《刀子和刀子》封二,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
⑦唐小林:《论新世纪四川长篇小说创作》,《小说评论》2008年第3期。
⑧唐小林:《绚丽的历史想象苍凉的人性悲歌——读〈午门的暧昧〉》,《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⑨唐小林:《没有乡愁却有记忆》,《十月》2005年第1期。
⑩何大草:《我的左脸:一个人的青春史》,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页。
标签: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历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如梦令论文; 人性论文; 读书论文; 中学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