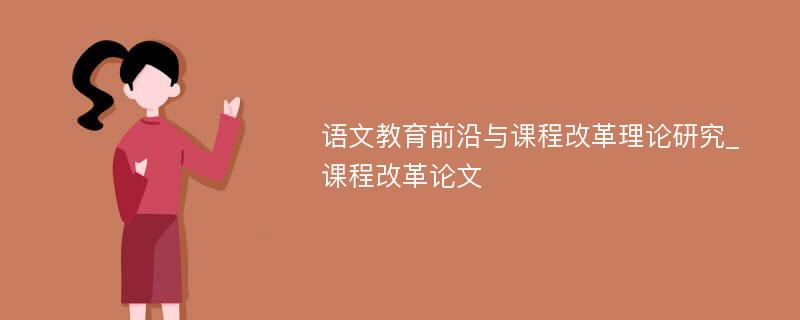
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理论前沿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课程改革论文,语文教育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怀着一种期待和冲动,走进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理论前沿——这里是思想的天地、智慧的原野、理性建构的领域。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理论前沿领域的研究,自然要立足于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的宏观视野和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与本质规律的探讨。我们在这种理论前沿领域的考察中,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点和层面出发,发现了几个全新的理论研究领域,即语文教学解释学与语文教学本体论研究、语文陶冶性教学与新课程教学论研究、语文教育观新构建与语文唤醒教育论研究。应该说,这几个理论研究领域组成了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理论前沿世界的绚丽风光。
一、语文教学解释学理论:基点的转移与意义的建构
语文教学解释学理论的研究,是一个开创性的新课题。它主要以哲学解释学理论为基点,打破过去的概念化阐释模式,建构全新的语文教学解释学的理论与方法,旨在为语文教学提供新思维、新视点、新思路和新方法。这是广大语文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早已触摸到的一个牵动语文教学生命的课题,它直接关系到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的功效和成败,因为语文课程与教学要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创新观和方法论,就离不开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按照解释学原理来说,解释学并非只是简单的认识论问题,而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语文教学文本解读活动的内在特征。以解释学为基本方法,对语文教学文本解读活动、文本阅读教学现象作出具有主体立场的解释,这是语文教学理论建构与创新的一个基本途径。所以有人说,解释学方法是语文课程教学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第一方法,语文教学解释学是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理论前沿领域中一个有着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
语文教学解释学主要是研究教学文本的理解与解释,所以,它借鉴和运用的主要是文学解释学的理论方法。在当代影响很大的文学解释学,与西方源远流长的哲学解释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近代以来,解释学经历了以施莱尔马赫为代表的认识论解释学、狄尔泰为代表的方法论解释学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本体论解释学的发展过程,即解释学从一种认识论、方法论迈进到本体论的层次。由于解释学经历了这种哲学层次的跨越,才拓展出了它的各个分支领域,也催生了富有交叉性、边缘性的文学解释学。语文教学解释学就是用这种文学解释学的理论方法,探讨语文教学文本解释的原理,把解释本体视为文本意义的审美生成过程,将读者的解读作为寻求理解和自我理解的活动,既建构文本的意义世界又建构自我世界。这种解释学理论方法,摒弃传统的解读研究只注重作家、作品的单向性模式,而把解读研究的基点转向文本、读者,即立足于探讨解读过程中读者与文本的双向交互作用,将解读作为一种读者与文本的对话,视读者的解读为作品的本体存在,把解读活动作为文本构成不可或缺的本体层次。也就是说,这种解释学理论的探讨是从作品本体到读者本体,是以文学本体论的两个重要维度——作品本体论和读者本体论作为理论基点进行研究,它建构在本体论现象学和读者反应理论的基础之上,是由重视研究作家、作品转向注重研究文本、读者的一个重大转移。
这种解释学理论方法,把文本、读者作为文学存在的本体层次,使之成为文学本体构成的重要部分,它显然不允许只专注于作家、作品的单一性阐释,而更加注重读者的解读活动。可见,语文教学解释学理论的这种前沿研究,特别是有关从作品本体到读者本体、读者解释与接受的主体性建立、解释形态与文本意义的多元理解,以及读者寻求理解与自我理解的活动、视野融合与阅读解释学原理等论题的探讨,会使这种新的解释学理论方法在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实践中获得深层的智慧启示,从而开辟语文教学文本解释与建构的全新领域。
二、语文教学本体论智慧:深层的醒悟与思维新秩序
语文教学本体论的研究,也是一个前沿性的新课题。对于“本体”与“本体论”,有很多阐释和讨论,在这里我们无意于考察形而上的概念性思辨,只是着眼于具体探讨语文教学的本体问题。我们认为,语文教学的本体,即语言本体或曰语文本体。毋庸置疑,语文本体的构成与存在原理——包括语文与世界、语文与文化、语文与主体、语文与生命、语文与存在、语文与意义等,是语文教学本体论要探索的基本问题。语文本体论是关于语文自身的学问,它要阐释和描述语文的构成与存在形态,可以说是语文教学的基础和根本。因此,深入研究语文教学本体论原理,建构语文教学本体论视点和思路,可以从根本上变革语文教学的思维与秩序,消除过去我们将语文与世界、语文与文化、语文与主体、语文与生命、语文与存在、语文与意义隔离的鸿沟,把语文作为主体生命的形式来把握,视一个语言形式为一个生命形式。显然,这是一个全新的语文本体观的建构,也是一个从根本上颠覆和重建语文教学思维和秩序的重大变革。
有不少专家指出,本体问题或存在问题是和语言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自柏拉图起,关于在语言中指陈非存在物的问题就一直困扰着西方哲学;从中世纪起,关于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就十分激烈,一直到当代也没有解决。安瑟伦关于上帝的本体论证明是从语言中使用某种谓词而推出实在的典型,直到康德才证明这种推论是荒谬的,而康德的关于‘存在’不是谓词的主张在当代语言哲学家那里有热烈争论。当代语言哲学家认为,利用现代语言分析手段,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本体问题,对古已有之的问题给出崭新的、确切的答案。”①语言哲学界的这种认识分歧与争论,引发了我们多方面的思考和深层的醒悟,使我们深刻认识到语言和本体原本就是“紧密交织”而同构于一体的,本体即语言,语言即存在,谈“本体”就不可能不谈“语言”。本体和语言的这种交织同构关系决定了近年来对语文教学本体的研究大都注重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语言的人文视界与本体论阐释,包括语言与人的意义世界的构成、语文本体世界的哲学透视等。这个方面重在探讨语言作为人之表征,是人的生命的呈现,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语言还是民族精神的外化,一个民族从诞生之日起所经历的漫漫历程都深刻在语言中。在语文教学本体论研究中,对语言与世界、语言与主体、语言与生命、语言与存在等所作的具体的探讨和哲学透视,多维化地揭示了语文本体构成的特征及其存在原理。语文教学的主体是人,人与世界不可分离。世界是人的生存居所,而语言是人与世界的本质关系。所以,语文教学一定要充分认识语言与人和世界的同构性。一个语言形式就是一个特定的生命形式,一个语言形式就是一个特定的存在世界。学习语言也就是拥抱生命、投身世界,而非单纯的、枯燥的知识灌输和技术操练。
第二,语文的文化性存在特质及其本体的文化阐释探讨,包括语文的文化性构成探究、“文化语文”论与“诗性语文”的分析等。这个方面重在探讨语言的文化性构成与存在的特性与规律,揭示语言的生成和发展与文化所具有的密不可分的联系,说明文化作为人类物质活动的产物和精神活动的结果从一开始就与语言结下了不解之缘。语文教学本体论研究对语言的文化性构成与存在原理的阐释,给语文课程改革与教学实践以多方面的启示。实际上,把握语文的文化性构成与存在特质,对语文进行文化阐释,是语文教学改革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诗性语文”“文化语文”“真语文”的回归与召唤。我们知道,语文新课程标准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语文作为一种文化的构成,揭示语文课程的文化特性和文化功能,强调语文教育不仅是“知识获得的过程”,而且是陶冶人性与情操、丰富学生的情感与精神世界、唤醒心智与灵魂、促进生命成长的文化过程。而在语文教学中要实现这一过程,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就是对语文的文化性构成与存在特质进行具体分析和透视,只有把握语文的文化性构成与存在特质,才有可能深入推进语文课程改革,并获得富有“语文味”的教学成果。
第三,汉语文本体构成美学与审美性存在的考察,包括汉字的美感特质透视、汉语文本体的审美特征分析等。这个方面重在从美学的角度揭示汉语文审美性存在的特质及其内在结构,以加强汉语文本体的审美性教学与研究。长期以来,我们的汉语文教学仅仅把汉文字作为听说读写的工具,仅仅注重形音以及表面的含义,使文字教学成为语文教学的细枝末节,而且走向枯燥化。这不仅使学生运用汉字表情达意的水平下降,而且造成语文教学的人文性缺失,不能很好地实现语文教学认知、审美的复合功能。因此,我们应当从中吸取教训,在教学中加强对汉字审美性存在特质的把握,重视引导学生去触摸和感悟汉字所蕴涵的审美因素,培养学生对汉字审美的特有感受力,即以汉字审美性存在为切入点,进行汉语文教学的审美设计,以从更高的美学层次上理解语文的内涵,优化语文教学效果。语文教学本体论研究中有不少这方面的探讨,能够启发我们汉语文教学的审美智慧。
三、语文教学陶冶性追求:生命的关怀与完整性建构
语文陶冶性教学研究,就是把语文训练的过程视为陶冶生命的过程,倡导在语文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完整性建构,即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说明:语文的世界是一个陶冶的世界,语文教学活动是对学生进行陶冶的完整性建构的活动。近年来,在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研究中,有不少专家、学者和语文教师对语文陶冶性教学作了多层面的探讨,包括语文陶冶性教学价值观及其基本理念、陶冶性读写教学的生态化建设、陶冶性教学状态的审美化追求、诗性语文的陶冶性教学设计、生命语文的陶冶性教学追问、审美语文的陶冶性教学建构、经典语文的陶冶性教学探究、绿色语文的陶冶性教学实验等。
在语文陶冶性教学研究的考察过程中,我们常常被有关的陶冶性教学论题感动,如关于生命语文的陶冶性教学追问,对语文教学活动中生命体验与生命互动过程的透视,对唤醒生命意识、关注生命情怀、提升生命质量、实现人生超越的教学价值取向的分析等。特别是关于“语文课堂生命陶冶场”的探讨,使我们在困顿中猛然窥见了语文教学的一片新天空。应该说,对这种生命语文陶冶性教学的呼吁,并非一种心血来潮,而是语文教学原本就具有这样的陶冶性意义。当我们认识到语文课堂教学是师生生命陶冶的一段重要过程,将对师生生命的成长产生深刻意义的时候,我们也必然产生另一种清醒的认识,那就是以往的语文教学也以它习惯的方式渗透在师生的思想观念中,长期影响着师生们的存在状态。它已经不只是在理念上枝繁叶茂,而且在实践中开花结果,成为师生习惯的生存方式。在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再也不希望面对那许多不健全的果实痛心疾首、追悔莫及了。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审视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真正以人为本,关怀生命,陶冶性灵,建构一个有利于生命成长的教学生存空间,这就是在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中倡导生命语文陶冶性教学的出发点。
注重陶冶性教学,是我国语文教育源远流长的一个传统。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开启了以“兴观群怨”为价值取向的诗教源头。与其他形式的教育相比,诗教更体现出潜移默化的效用,使学生在阅读的陶冶与感化中,实现心灵的净化和人格的升华。此后,这种诗教传统历经数代而不衰,滋润着一代代人的民族气质,涵养着一代代人的人生品味。但是,在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中,教育家多半将陶冶作为自发因素,很少有人把它上升为理论阐释,使其理智化和目的化。在当今建构和谐社会的新时代,我们应继承中华民族的语文教育传统,系统深入地研究陶冶性教学,充分发挥语文教学特有的陶冶功能,以促进学生的生命成长,实现对学生的完整性建构。
从小学语文教育到高中语文课程改革,有很多语文教师都把诠释诗意语文、构建诗意课堂当做自己追求的目标,在课程改革过程中充分发挥语文教学的熏陶感染作用,陶冶学生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如北京清华附中赵谦翔老师在“语文教育与人的发展”课题研究中,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以陶冶情感、启迪悟性为两条主线。山东青岛的苏静老师在“学生个个都是诗才”教学理念的指引下,在小学大胆尝试诗化教学,创立以古典文化为基点、以诗词诵读为特色、以构造诗化生活为目标的班本课程,引起了教育界的强烈反响。浙江杭州语文教师王崧舟,探索能够实现“价值引领、文化传承、精神诉求、生命唤醒、感性复活、个性高扬和智慧观照”的诗意语文教学,用诗意的语文来润泽学生的生命。从这些教学探索中,我们会发现一个重要的趋势,这就是语文教学正在回归传统、超越传统,追求一种真正的陶冶性教学。
四、语文新课程叩问:沟通理论与教学范式转型
对语文新课程教学的探讨,是一个众所关注的热点课题。语文新课程教学论也是一个正在重建的理论新结构,它包括新课程教学价值论、新课程教学功能论、新课程教学结构论、新课程知识教学论、新课程教材建构论、新课程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的变革等一系列重要论题。我们在考察中发现,其中有三个方面的理论探讨富有启示性和警醒意义。
第一,新课程教学与沟通理论的阐释。从沟通理论的角度来说,汉语文课程就是一种沟通课程,汉语文教学就是一种沟通教学。可以说,沟通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揭示了汉语文课程与教学特有的一种“沟通”新质。“沟通”与语言的问题,是近几年来在所有生活领域与科学领域日益拥有重要意义并受到特别关注的现象之一。钟启泉先生把它作为一种学科教学现象加以分析:“教学的重要本质就是一系列沟通”,“所有的学科教学都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性沟通现象,都是语言教学。没有沟通与语言的学科教学是不存在的”。②因此,我们必须从教学中的沟通与语言的视点重新审视语文课程与教学理论,以求得语文教学理论的范式转换。同时,这种教学沟通理论告诉我们:课程与教学的改革,从本质上说是一场“沟通”革命。所以,我们必须以教学的沟通与合作为基本事实,转变教学理论的范式。
第二,新课程学生观的建构与“为生命而为”的价值追求。语文新课程学生观的建构,表现出对学生生命成长的关怀和完整性发展的关注,这种新课程学生观体现了语文教学“为生命而为”的价值追求。具体来说,新课程学生观的重建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新的学生本质观,即从生命成长的角度来理解学生的本质,将学生视为不断走向完善的独立的生命存在、在语言中栖息和生成的生命存在、在文化中浸润和丰富的生命存在。正确的学生观是建立在对学生本质属性的正确认识之上的。新课程学生观对学生本质属性的这种认识,体现了新的教育理想和价值追求。二是新的学生发展观。语文教育是“人”的教育,新课程教学必须重视语文学习在学生生命成长中的基础作用,即强调要立足学生发展的终身性,为学生的完整性发展奠基。同时,要增强学生发展的自主性,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力求实现学生发展的个性化,促进每一位学生的发展。三是新的学生角色观。与传统教学把学生视为被动的知识接受者不同,语文新课程教学强调学生生命主体的能动性,将学生视为真正的语文学习的主体。同时,新课程还确立了学生作为课程评价主体的地位,以促进学生全面和谐的发展。这种新课程学生观不是把学生作为“一个需要填满的罐子”,而是把他们视为“一粒需要点燃的火种”。
第三,语文教学范式的转型与发展性教学理论。新课程学生观的建构,也促进了语文教学范式的转型和发展性教学的探索。应该说,整个语文教学都在面临着深刻的转型,即由传统的“授受”范式向“对话”范式转变。对话理念支持下的教学已成为新课程改革的一大亮点。没有教学范式就不会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积累和进步。为使语文教师更深入地认识教学范式的存在,建构语文课程与教学的新思维和新秩序,有不少专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研究从接受到对话这种语文教学范式的转型问题,通过对语文教学范式的深入探讨,揭示了语文教学对话范式的本质,对语文新课程教学实践富有深刻的启示性意义。此外,着眼于学生的完整性建构的发展性教学,从后现代课程观的视角透视语文教学活动,认为语文教学过程是一个自组织的过程。对我们来说,这种自组织的概念是非常新鲜的。因为长期以来语文教学似乎与自组织无关——我们的教学是明确的、确定的和有序的,我们尽量回避问题和干扰的出现,以使学生能够完全接受我们已经设定的对课文的单一、确定的解释。而且,我们的教学很难让语文课体现出多样性的、充满疑问性的、富有启发性的内容,更不能形成一种宽松的、促进探究的课堂氛围,何谈自组织的过程?为此,这个论题的探讨立足于语文教学实践,提出了语文新课程发展性教学和实施发展性教学的基本途径。这种发展性教学理论对语文新课程教学改革颇有思维与智慧的警醒性启迪意义。
五、语文教育观重建:文化过程论与唤醒教育观
随着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语文教育观在各种教育精神、课程理念和教学智慧的碰撞与融合中不断得到新建构。如钱理群的“以立人为中心”的语文教育观、王富仁的“大语文”与“小语文”论、童庆炳的“语文教学认识论与存在观”、潘新和的“语文教育:走向表现与存在”、韩军的“重建与反思:新语文教育论”等,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揭示了语文教育观建构的新内涵,我们从中可以获得语文教育观建构的真知灼见。此外,关于语文工具观的整合建构、语文生活观的思想发展、语文教育文化过程观的本质、语文课程唤醒教育观与文化建构观的内涵等方面的前沿性研究,也都给我们以深刻的思想启示。应该说,这些不同层面的探讨有助于语文教育观的多层建构。
在重建与反思中建构的新语文教育观,是秉承五四新文化精神,是建筑在“语言即人,即存在”的哲学观上的,以“说真实的、个性的话”为价值论,以“用语言立人的精神”为语文教育终极目的和本体论,以“举三反一”为语文教育的总体操作论的语文教育观。韩军老师用梁启超先生的话对这种新语文教育观的本质进行了揭示:欲新一国之国民,必新国民之精神,欲新国民之精神,必新国民之语言;新语文教育的原理是向着精神着意,向着语言着力,必从能力得益。韩军老师对这种新语文教育观的建构,能引导我们重新认识和深层把握语文教育的“新质”。
同样,在语文教育走向表现与存在的过程中,潘新和提出的“言语活动乃是人的一种精神建构,是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的思想,也透射出语文教育“新质”的光亮。他以此为立足点,以“言语生命”作为语文教育的核心概念而建立的“言语生命动力学”理论,开辟了语文教育观的新视界。他认为人本主义在语文教育中体现为言语与人的生命的血脉相连。人的言语要求,既外在于生命,又内在于生命,归根结底是内在于生命的。因此,应内(生命)外(生活、社会)兼顾,以内为本,以言语生命意识的培育为本。同时,他还强调语文教育应从重言语技能训练转向重言语动机和人格的养育,从重语文素养的培养转向重言语生命本性的养护,从重阅读转向重表现、重写作,发现并关注每一个个体的言语生命潜能、才情和天性、个性,扶助言语生命的成长,促进每一个言语生命的最大发展。这种语文教育观的建构,破天荒地揭出了发展学生言语生命意识的命题,使我们耳目一新。
为深化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曹明海在《语文教育文化过程研究》中提出了语文教育文化过程观的命题,认为语文教育不仅是一个单纯的语文技能训练过程,而且是一个陶冶性情、建构精神、促进生命成长的文化过程。语文教育文化过程观的建构,旨在打破长期以来仅视语文教育为“知识获得的过程”和“语言技能教育”的理论,以文化来整合工具与人文,开拓以人的发展和完整性建构为主体的理论新视点。具体些说,这种语文教育文化过程观的建构,包括两个层次的理论创新:一是语文教育不仅是语言训练的过程,也是文化传承的过程;二是语文教育是训练运用语文的技能,也是陶冶人性、涵养心灵、促进生命个体总体生成的过程。这种语文教育文化过程观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重新认识语文教育的本质与功能,而且有助于我们从实践上深化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
语文课程的唤醒教育观与文化建构观,也是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关注的重要课题。唤醒教育观重在强调语文教育之为教育,就在于它是一种生命、人格与心灵的“唤醒”,并认为这是语文教育的核心所在。语文教育的目的并不在于单纯传授某种外在的、具体的知识和技能,而在于从人的生命深处唤起沉睡的自我意识、生命意识,促使其价值观、生命感、创造力的觉醒,以实现自我生命意义的自由自觉的建构。这种唤醒教育观强调,语文教育的过程不仅要从外部解放成长者,而且要唤醒成长者的人格和心灵,解放成长者的内在创造力。就是说,语文教育的功能在于唤醒生命成长的觉悟,促进生命个体的总体生成。文化建构观则强调语文课程并不是作为技术性语言训练的工具而是作为文化主体而存在的,它承担着文化建构的使命,这就要求语文课程要以文化主体的自觉性建构一种生命形态的、过程性的、富有超越品质的运行模式,树立语文课程的文化建构观,即建构语文课程的生命形态——一种价值取向观、建构语文课程的过程模式——一种文化过程观、建构语文课程的超越品质——一种文化反思观。
注释:
①徐友渔、周国平等《语言与哲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4页。
②钟启泉《学科教学论基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页。
标签:课程改革论文; 本体论论文; 解释学论文; 教学理论论文; 语文教育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教育本质论文; 教学过程论文; 生命本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