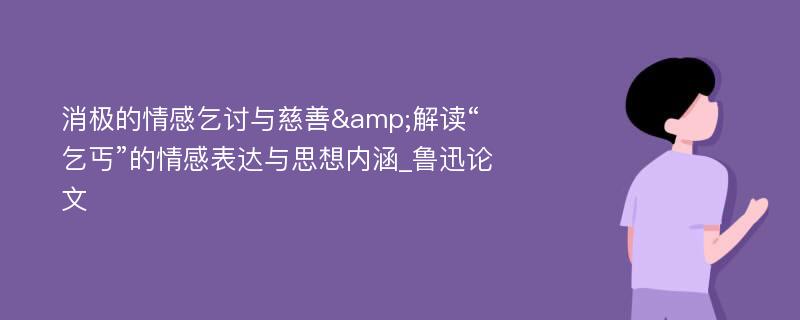
否定情感的求乞与施舍——解读《求乞者》的情感表现和思想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感论文,内涵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就有学者指出:“《野草》是鲁迅先生为自己写,写自己的书,是理解他的锁钥,是他的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枢纽。”[1] 这里的“为自己写,写自己”可以说已经提供了解读《野草》的钥匙。可是多年来人们总是习惯于政治思维模式的定势,或是对这钥匙视而不见,或是虽然拿着钥匙却找不到开锁的密码。所以对《野草》的解释真可谓牵强附会,歧义百出。其实,只要用“为自己写,写自己”这把钥匙,再找到解读每篇的合适的密码,即或从文化批判或从个人情感体验等不同的角度来解读,我们就能掌握《野草》每篇的内在逻辑,理解鲁迅所要表达的情感体验和思想内涵。比如《这样的战士》,过去人们习惯于从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解释,结果文中的“无物”、“无物之物”、“无物之阵”等处总解释得牵强附会,于理难通。如果我们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来理解,也就是说,把“战士”明确地定位在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上,那么不但能从逻辑上解释“无物”“无物之物”与“无物之阵”所表示或象征的意思,而且对全篇的把握也更通畅。既然战士的投枪的目标面对的是封建传统文化。当然作品中的“无物之物”就是指的几千年来形成的以封建礼教为基础的强大的封建专制文化了。而“无物之阵”,就是由这些被封建礼教文化浸润入骨的各式各样的人组成的社会。所以“无物之物”和“无物之阵”,就像鲁迅在杂文中把“所谓中国文明”概括为“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在《狂人日记》中把封建礼教的实质概括为“吃人”是一样,都是一种象征性的写法。同样,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即从《野草》的文体特点来考虑问题,用个人情感体验的方式来解读《求乞者》。
2 传统文论的“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实际上是指明了“文”与“诗”的两种不同文体的特点和功能。“文”最适于理性的逻辑思维,是说理或记事的工具,因此它最宜于“载”思想之“道”。“诗”最适于感性的形象思维,它表达的是难以说明或不便明说的内心体验或灵魂的秘语,因此它最宜于“言”个体的情感之“志”。“文”的“载道”或说理是要教化大众或说服他人,因此它“载”的“道”要清楚,说的“理”要明白。诗则不然,诗是最具“私人化”的艺术,它是诗人内心深处最原始最本真的情感的流露或宣泄。按照精神分析学的观点,艺术家正是被无意识中的本能欲望所驱迫的人,因这种欲望不能见容于文明社会,它就不得不通过曲折的方式来谋求满足,文学正是满足欲望的一种替代物。文学创作活动使被压抑的情感、欲望得到表现,从而得到升华。缪塞说:“最美丽的诗歌就是最绝望的,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五月之夜》)穆木天说:“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诗是要有大的暗示能。诗的世界固在平常的生活中,但在平常生活的深处。诗是要暗示出人的内生命的深秘。”[2] 诗不必承担说服他人或教化大众的责任,所以“诗”不必像“文”那样清楚明白,相反,“朦胧”倒是诗的一种审美要求。现代派诗人主张诗是“一个人在梦里泄露自己的潜意识,在诗作里泄露隐秘的灵魂,然而也只是像梦一般的朦胧的。”“诗的动机在于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马拉美说“指出对象无疑是把诗的乐趣四去其三”。“文”主要是作者出于社会责任感来启发民众,指陈时弊,表达理想。而“诗”则不必承担这么沉重而严肃的社会责任,它的本质职责是对诗人个人情感的承担,是诗人情感的止痛药和安神剂。把诗人胸中郁积的欲歌欲哭欲叫欲跳的满腹不平之气抒发出来。即福楼拜所说的,珠子是牡蛎生病所结成,作者的文笔却是更深沉的痛苦的流露。诗的语言不必是公众话语,它可以是某个“小圈子”里的“行话”或“黑话”,也可以是两个人之间的“悄悄话”,甚或是诗人个人的自言自语式的“独语”“宣泄”。了解了“文”与“诗”的两种不同文体的不同的特点和职能,我们也就知道了在解读或评价这两种不同文体时所应采取的不同的方法和态度。也就是说,对于“文”,我们可以用社会分析和理性思辨的方法去分析它的社会意义或思想价值,而对于“诗”,我们则要用个人情感体验的方式去感受诗人生命的颤动和灵魂的私语。
3 在《自选集·自序》中鲁迅自己把《野草》的文体定位为散文诗,这种定位也得到了研究者和读者们的认同。确实,《野草》中的作品,除有个别的嘲讽游戏之作外,绝大部分都是表现作者自己的孤寂苦闷的抒情之作。就抒发情感和创作过程来讲,《野草》中的大部分诗篇是典型的“蚌病成珠”之作。我们且不谈鲁迅当时在荒凉如沙漠的无边无际的旧战场上“呐喊”得不到回应,听不到战叫,只能“荷戟独彷徨”的无奈、孤独与苦闷,单就个人的情感生活上来讲,鲁迅所忍受的郁闷和孤寂、矛盾和痛苦也是超出一般人的想象的。1906年26岁时接受了母亲送给的“礼物”——与朱安女士结婚,婚后第二天就从新房搬出,第三天就又远走日本。20年来,鲁迅就是维持着这样一种无爱无恨,有名无实的夫妻生活。他自己说:“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鲁迅有着比常人更敏感的神经和更热烈的感情,然而,正值壮年的鲁迅却20年来没有拥有过男女间正常的感情交流和夫妻生活,这种人性生活的缺失造成鲁迅的难以排遣的孤寂和苦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校对古书,抄写碑文诗帖和大量的饮酒吸烟就是试图转移或麻醉这种无法排遣的情感的努力。难怪郁达夫在回忆鲁迅时借用一个学生的话,调侃鲁迅在北京寒冷的冬季不穿棉裤是为了克服性欲。鲁迅从传统的孝道和现代的人道主义的道德立场出发,一直抱着牺牲自我承受现实的态度:“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直到许广平这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女性闯进鲁迅的情感世界之后,许广平大胆的追求和火热的爱,使鲁迅那一团几乎被冻灭的爱情的“死火”又得以死灰复燃。然而,鲁迅既敏感而又自卑自傲的个性,使他陷于对这份爱的真实性和自己是否有条件和资格得到这份爱的疑虑之中,并且名誉、良心、道德、责任与爱情的选择的两难又使他处于极端的矛盾痛苦之中。所以《野草》中的部分篇章,就是他的这种兴奋疑虑而又郁闷痛苦的情感的表白和发泄。另外,从表现艺术上讲,《野草》是鲁迅作品中最隐晦难解的,这是大家公认的。这种隐晦难解对读者来说是一种困难,同时也是一种美和诱惑。作者自己在《〈野草〉英译本序》中说:“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究竟什么使得鲁迅这样一个“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的猛士“难于直说”呢?敢于面对北洋军阀的屠刀而宣称“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指斥当局的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直陈“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的鲁迅,究竟害怕和顾虑什么不能明说呢?笔者认为,从鲁迅被压抑的情感生活的角度来解释不失为通向《野草》隐秘世界的一条蹊径。作为当时的鲁迅,他的难以隐忍的强烈的感情需要表白和宣泄,他内心的感受,他的困境和苦衷需要向爱他者而他也爱的人去解释和说明,但是,作为社会名流的鲁迅,既受到来自自我良心和家庭责任与义务的道德的压力,也有来自社会公众舆论的压力,再加上他和许广平的爱还处于萌芽阶段的试探和疑虑,又使得他不能公开地表达他的心扉和情感,这就是“那时难于直说”的隐情。鲁迅在厦门写信给许广平说:“看见我有女生在座,他们便造流言。这些流言,无论事之有无,他们是在所必造的,除非我和女人不见面。他们貌作新思想,其实都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倘使顾忌他们,他们更要得步进步。我蔑视他们了。我有时自己惭愧,怕不配爱那一个人;但看看他们的言行思想,便觉得我也并不算坏人,我可以爱。那流言,最初是韦漱园通知我的,说是沉钟社人所说,《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月是她。今天打听川岛,才知此种流言早已有之,传播的是品青,伏园,衣萍,小峰,二太太……。他们又说我将她带在厦门了,……黄坚从北京接家眷来此,又将这流言带到厦门,为攻击我起见,广布于人,说我之不肯留,乃为月亮不在之故。……况且如果是‘夜’,当然要有月亮,倘以此为错,是逆天而行也。”[3] 从此信可以推知当时环境的压力和鲁迅的心情。当时他们的爱情还不成熟,鲁迅还没有后来的“我想同在一校无妨,偏要同在一校,管他妈的”那样不顾一切的坚决的态度。所以当时鲁迅只能是“在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只能是“像梦一般的朦胧的”泄露自己的隐秘的灵魂。再者,从语言上来讲,《野草》使用的是最具个性化的语言,它不带有启蒙或教化的色彩,而是带有个人的自言自语式的“独语”、“宣泄”的特点。诸如“影的告别”、“彷徨于无地”、“明暗之间”、“黑暗和虚空”、“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死火”、“死后”、“无物”、“无物之物”、“无物之阵”、“于浩歌狂舞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等等,都是个性化极强的“悄悄话”或“私人话语”。也就是说,《野草》里面的一些篇章,无论是从创作心态和抒情形式上,还是从表现艺术和语言运用上,都具有诗的特质,所以我们应该以感受或谛听诗人生命的颤动和灵魂的私语的个人情感体验的方式去解读或研究。下面我们就以这种方式来试着解读《求乞者》。
4 《求乞者》只有400多字。全文如下:
我顺着剥落的高墙走路,踏着松的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露在墙头的高树的枝条带着还未干枯的叶子在我头上摇动。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而拦着磕头,追着哀呼。
我厌恶他的声调,态度。我憎恶他并不悲哀,近于儿戏;我烦厌他这追着哀呼。
我走路。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
我就憎恶他这手势。而且,他或者并不哑,这不过是一种求乞的法子。
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予烦腻,疑心,憎恶。
我顺着倒败的泥墙走路,断砖迭在墙缺口,墙里面没有什么。微风起来,送秋寒穿透我的夹衣;四面都是灰土。
我想着我将用什么方法求乞:发声,用怎样声调?装哑,用怎样手势?……
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
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
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
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
灰土,灰土,……
……
灰土……
以往的研究者多从社会政治或道德实用的层面对《求乞者》进行解读和研究。如李何林先生认为作品表现的是作者反对向旧社会求乞的不妥协的精神:“《求乞者》中的‘我’,对着‘四面都是灰土’的灰色荒凉而又冷酷的现实,别人都在屈服地乞求,他是不妥协的:‘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至多’呢?他得到的是不对现实屈服求乞。”[4] “这一篇和《影的告别》写于同一天,同样弥漫着灰色暗淡的调子:四次描写了‘四面都是灰土’,并且‘灰土,灰土,……灰土……’,无穷尽的灰土。……这是旧中国现实的概括或写照,也是作者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感受。……‘我’对于孩子们的屈服投降,向旧社会求乞,是痛心的,他憎恶旧社会把孩子们毁坏了,对于求乞的孩子他也并不同情。”冯雪峰先生则认为:“《求乞者》写的是在灰色的社会生活和作者在灰色的社会中所引起的空虚和灰暗的情绪。”[5] 闵抗生先生基本上沿袭了李何林先生的观点,把不妥协的精神明确为“抗争”和“战斗”:“《影的告别》写了‘影’对黑暗的抗战,《求乞者》否定求乞,主旨仍是抗争。剥落和倒败的高墙,四面蒙蒙的灰土,凛冽的秋寒,各自走路的人,求乞的孩子——这就是当时北京的缩影。……在鲁迅先生看来‘各自走路的人’、‘求乞的孩子’表现了我们相当一部分民众的风气。而这,又都是统治阶级教育的结果,是他们的‘治绩’:……‘求乞’现象是‘灰土’世界的一部分,对求乞的否定,是与鲁迅先生改造旧社会的思想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对求乞的彻底否定,最后必然要导致否定私有制的战斗结论。”[6] 孙玉石先生感到了作者一向的人民立场与此文说的“无布施心”之间的矛盾,所以解释为是鲁迅“怒其不争”的愤激情绪的一种诗意的流露:“《求乞者》和《秋夜》可以说是表现了鲁迅战斗的美学观念相得益彰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歌颂枣树所象征的坚忍不拔的反抗斗争精神,一方面,憎恶求乞者所概括的安于命运的乞怜哀呼的态度。……鲁迅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灰暗颓败的社会景象。……我们说,这是写实,因为在当时地狱一般的社会里,像这样求乞的孩子伸手哀呼的悲怆画面,真是遍地皆是。但是,一向倾听被压迫的弱者呼号的鲁迅,这时为什么却无动于衷,而给与求乞者以‘烦腻、疑心、憎恶’呢?这又是因为诗里的描写是一种艺术的象征。鲁迅以孩子的求乞作为屈服于奴隶命运而向黑暗社会乞怜哀呼的人生态度的象征。他渴望人民的觉醒与反抗,而憎恶这种乞怜和哀呼。因此‘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予烦腻,疑心,憎恶’一段话,就是鲁迅‘怒其不争’的愤激情绪的一种诗意的流露,而不能看成是他对劳苦人民命运的冷漠和无情。”[7]
以上的解读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社会、政治和道德实用的角度来理解和分析作品,读起来总给人以研究者在借题发挥的感觉。此外,有的研究者把此篇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来研究:“诗人探讨人类的本质和人际关系。人并非单独地存在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人的本质也相应地体现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作为人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于他人实施道德和责任的能力。然而在散文诗中,‘我’、乞丐、和其他路人都显得冷漠和自私,如艾伯所说,‘于是社会成了不能沟通的残废个体的集合’。而那颓败的墙则是‘人们之间情感障碍的象征’。……在《求乞者》中,鲁迅寓言化地告诉我们,一个自我或一个作为自我的人,总是在不断选择的过程之中。但是这不是自由地选择,而是被与他人关系所制约的选择。主人公对他人拒绝和自身的犹疑都是这种制约的具体表现。出于感情上的厌恶他拒绝施舍,出于理性的疑虑他又畏惧求乞。这种感情与理性的两难是《野草》散文诗主要哲学命题之一,它向众多的主人公挑战,在《过客》、《墓碣文》诸篇中更触目惊心地表现出来。”[8] 笔者认为,尽管鲁迅曾自己表示“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但是,我们只能说鲁迅在这些散文诗里表现了他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即表现了他的人生哲学,而不能说在这些散文诗里鲁迅要刻意探讨和研究什么哲学命题。他所做的哲学的思考也是服从于他的情感的需要的。“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的意象让人联想到被称为现代雕塑史上“男子新殉的创始人”的瑞士雕塑家阿尔贝托·贾科梅蒂的著名雕塑《三个行走的人》。“他们如埃及神明那样谁也看不见谁一般地僵直行走,带着自信与无奈并存、敏感与孤独混杂的气质;带着难以觉察的隐忍、内敛的精神和不事张扬的痛苦;有离世的清高,亦有承担拥挤而又飘摇的人生的耐性。……在不确定的无限空间里,他们谨慎而又不由分说地让你体味到生活内部和人的内部某种吓人的高度浓缩的明确性。在这个意义上,贾科梅蒂比罗丹、马约尔更贴近现代人的心绪。由此你看到了痛苦里的痛苦,真实里的真实……贾科梅蒂手下的孤寂、徒劳而又不屈地行走着的人们,让我不禁想起中国一位老作家的话:‘人是孤儿’。而人们与人们何时才能相遇?”[9] 所以,鲁迅在《求乞者》中所作的微风、秋寒、灰土、颓败的墙、几个人各自走路的环境意象的描写,当然有鲁迅对世事人生的哲理认识,但主要是为了衬托自己孤独无助而又倔强的情感。这里的求乞与施舍不应从物质或社会道德的层面去理解,而应该从情感的层面去理解。即鲁迅要表达的是情感或说爱情的求乞与施舍是无助的。对情感的求乞他不布施,无布施心,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予烦腻,疑心,憎恶。同样,他认为自己如果去求乞情感或爱情也同样得不到布施,对方也会像自己一样不布施,无布施心,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予烦腻,疑心,憎恶。这就是当时鲁迅在朱安与许广平两个女人之间尴尬的情感波动的象征的诗意化的表达。对朱安这个名誉上的妻子,鲁迅表示:“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10] 而朱安则是默默地忍受着鲁迅对她的情感的冷淡,希望用行动来对他进行感化。就像她说的:“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11] 朱安的“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的感化行为确实带有求乞情感的性质。而在鲁迅看来,其他的可以布施,但爱情是不可布施的,过分的乞求反倒使人烦腻和憎恶。另一方面,鲁迅推己及人,想着自己如果向别人乞求爱情可能同样得不到布施,别人也会无布施心,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予烦腻,疑心,憎恶。当时许广平虽然已经闯进了鲁迅的生活,但是由于年龄的差距和鲁迅自己家庭的状况,他的自卑心理使他对能否得到这份爱尚持怀疑态度。鲁迅曾对许广平坦言“我有时自己惭愧,怕不配爱那一个人。”这可能就是当时的真实的心理。直到两年后他们的爱情已经瓜熟蒂落的时候,鲁迅才自信地说出:“我可以爱。”但在当时鲁迅确实担心自己的求爱如果受到拒绝后的尴尬和难堪,他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绝不愿因此而使自己的自尊蒙受羞辱。所以对许广平在信中热烈而急切的表白:“苦闷则总比爱人还来得亲切,总时刻地不招即来,挥而不去,先生!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分?有糖分是否就绝对不苦?先生!你能否……给我一个真切的明白的引导?……能够拯拔得一个灵魂就先拯拔一个!先生呀!他(按:指自己)是如何的‘惶急待命之至’!”[12] “学生是仰望于先生,尤其愿得作一个‘马前卒’以冲锋陷阵,小喽啰虽然没有大用,也不妨令他(按:指自己)摇几下旗子,先生能见谅他么?不胜急切之至!”对此鲁迅采取了试探虚实的以退为进的审慎态度。所以《求乞者》中的“我想着我将用什么方法求乞:发声,用怎样声调?装哑,用怎样手势?……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这一段话,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作者想着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求爱,但又意识到自己苦闷孤寂的情感是无人理解的,无法与人沟通的。并且,因为爱的情感是不可求乞和施舍的,所以担心自己的求爱也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因此决定采用静观的方式:“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这样我至少将在心中得到那份甜蜜的情感。即“我至少将得到虚无。”因为在鲁迅看来,“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另外,我们知道,《求乞者》与《影的告别》写于同一天,已经有研究者认为把《影的告别》“解释为鲁迅潜意识里对妻子的告别。结婚十八年以来,他最终希望付诸行动来结束不明不白的夫妻名分。”从情感体验的角度来分析,这种看法是合于情理的。也就是说,两篇诗作,是在同一天在同一种感情焦虑的推动下写出来的,表现了大体相同的情感。即《求乞者》表现了夫妻情感不可用求乞来获得弥合或补救以及自己对爱情追求的犹疑;《影的告别》则表现了告别无爱的妻子的意向。尽管作者此时的感情寄托之所还未确定,但他已经决定“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宁愿“彷徨于无地”了。
以上笔者从诗的抒情特点和艺术表现特点的角度,以个人情感体验的方式来分析了《野草》的表现艺术及《求乞者》所表现的情感和思想内涵。认为:《野草》中的部分诗篇是典型的“蚌病成珠”之作。《求乞者》表达的是情感的求乞与施舍是无助的。对情感的求乞鲁迅不布施并给予烦腻,疑心,憎恶。同样,他认为自己如果去求乞情感或爱情也同样得不到布施,对方也会像自己一样给予烦腻,疑心,憎恶。这就是当时鲁迅在朱安与许广平两个女人之间尴尬的情感波动的象征的诗意化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