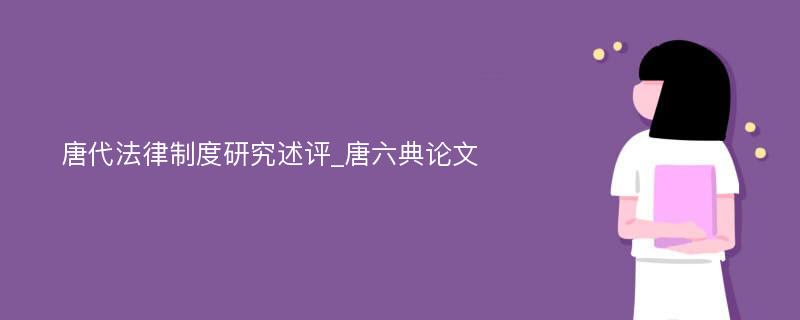
关于唐代法律体系研究的述评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唐代论文,法律体系论文,及其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代法制不仅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在东亚法制史上有着广泛的影响,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对于唐代法制,中外学者一直抱有极大的研究兴趣,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对于唐代法制的某些基本问题,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唐代法律体系的性质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对此,诚如学者所谓:“律、令、格、式的性质及与之有关的问题,已成了唐代法律乃至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一个分歧最大,矛盾最尖锐的问题。”(注:钱大群《论唐代法律体系与唐律的性质》,《法学研究》1995年第6期;也见钱氏:《唐律与唐代法律体系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8页。)笔者认为,对此问题的廓清,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唐代的立法技术,而且有助于准确把握唐代法制的基本特点。
鉴于有关唐代法律体系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所以笔者为本文设定的基本任务是:其一,综述学者对于唐代法律体系的主要研究成果(注:这里所谓“主要研究成果”是指一些专门的研究论文,以及一些涉及唐代法律体系性质问题的影响比较广泛的专著。)及提出笔者的评议意见;其二,顺便讨论《唐六典》的性质及行用问题;其三,在结论部分,笔者主张重新思考研究唐代法律体系的方法问题,包括研究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方法问题。
一、律、令、格、式的性质及其关系
关于唐代法律体系,《唐六典·刑部》说:“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新唐书·刑法志》也说:“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可见,这是唐宋以来人们对于唐代法律体系的基本看法,也是我们据以讨论的基础(当然,这也涉及到对《唐六典》性质的判别,下详)。
1.律的性质问题。关于律的性质问题的看法,学者的看法大致可能分为两种,并且均有广泛的影响。第一种观点认为律是一部包括民事、婚姻、诉讼等制度性内容的综合性刑法典,亦即所谓“以刑为主,诸法合体”。持此说者的基本理由是:认为律虽然是一部刑法典,但是其中包含有关民事、婚姻、诉讼等方面的某些制度性内容,所以是“诸法合体”。原因在于:一是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二是立法技术、立法经验不发达。(注:参见乔伟:《唐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5页;各类教科书均持此说,例如,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此章也系乔伟所写),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第205页;其他各书不具引。)第二种观点认为律是一部纯粹的刑法典,从而否定“诸法合体”的看法。持此说者的主要根据是:首先,认为《唐六典·刑部》明确指出:“律以正刑定罪”,表明律是关于定罪量刑的法律规则。这是外证。其次,认为律除了一些原则性和制度性规定以外,通篇均由犯罪构成和刑罚制裁两个部分组成。这是内证。最后,认为即使律规定了某些制度性内容,但是,目的不在正面的制度规范,而是描述犯罪构成的要件。所以律包含的民事、婚姻、诉讼等方面的制度性内容无法改变律的基本性质,从而不具有“诸法合体”的性质。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与战争的密切关系以及专制权力对于臣民的全面的“督责”,(注:因为篇幅以及行文方便,笔者正文没有详细开列各家的具体观点和理由,而是采取综合概括的方法表面出之。参见王立民:《论唐律令格式都是刑法》,《法学研究》1989年第4期,也见王氏《唐律新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46-60页;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页;前揭钱大群:《唐律与唐代法律体系研究》;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陈寅恪:《隋唐制度源流略论稿·刑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0-115页。)这样,中国古代每每将法律与暴力、惩戒相连也是势所必然。
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笔者的意见是:两说相较,以第二种观点为妥。基本理由是:首先,此说充分考虑到了中国古代法制传统的“刑法中心主义”(或者说“泛刑主义”)特色及其原因:相反,第一种观点以小农经济解释则缺乏充分解释力。其次,这一观点较好地分析说明了律的某些制度性规定的宗旨所在——构成刑法结构中的假定和处理部分,而非制度规范本身,因为唐代的制度规定另有其他规范——令、格、式等(其与刑法关系,下详),从而对律本身的把握显得更加准确,也更加具有说服力。
但是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没有很好处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律文与疏议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辨析《唐律疏议》,可以发现,其中所谓的制度性内容主要是由于疏议的存在而凸现出来的;而就律文本身考察,则所谓的制度性内容根本不能单独成立,或者至少是极不完整的。第二,律文与现代刑法典的基本差异。学者往往以现代刑法典的基本理念为标准来考量、来评析律文,结论也是从中得出的,所以比较两者之间的区别,乃题中应有之义。笔者认为,律文本身在表述方面与现代刑法典是有所不同的,主要表现在律文有关假定和处理部分内容要比现代刑法典规定得详尽具体,亦即律文规定的抽象程度不如现代刑法典,而所谓律文中的制度性内容也是由此而起的。这一特点恐怕与唐代立法技术的发展水平有关,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更与中国古代抽象思维的发展程度有关。当然,笔者在此并不否认视律为刑法典的基本判断。
顺便指出,现代刑法典尽管表述得十分抽象,但是如果考虑一下大量法律解释的存在,以及这些法律解释包含的制度性内容;如果再考虑一下在我国现今的司法实践中仅仅依靠刑法典的抽象规定无法定罪量刑的情况,那么律文和疏议包含着某些制度性内容也是毫不奇怪的,对司法实践更为有利。
2.令、格、式的性质问题。对于唐代法律体系的基本分野,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有一总体的论述。他认为:中国古代所谓的法律,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则是官僚统治机构的组织法——由行政规则及其处罚规则构成。(注:〔日〕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比较法研究》1988年第3期。)笔者认为,这一官僚机构的组织法,在唐代显然与令、格、式有关。但是,它们的性质如何呢?滋贺秀三没有予以讨论。无论如何,这似乎暗含着一种基本看法: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存在着刑法与行政法两大系统的分野。
那么,我国学者是的看法如何呢?为了讨论方便,先请引述两条基本史料。
《唐六典·刑部》说:“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规物程事。”《新唐书·刑法志》则说:“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这是唐宋典籍和史书的比较原则性的解释。怎样理解这两条史料,学者的看法差异甚大,大致也可分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令、格、式属于行政法规,这是主流观点。持此说者的根本依据是:它们是有关国家组织制度以及公文程式和行政细则方面的法律。(注:有关乔伟的看法,可以参见前揭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第205页;张晋藩:《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96-397页;必须指出的是,乔伟和张晋藩两位先生对于“格”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没有具体解释。)
关于唐代令、格、式的性质问题,新近的研究以钱大群先生用力最勤,分析也极为仔细。他的基本看法是:其一,认为“作为一般施政根据的令、格、式又是三种形式不同、性质不同的法律”。其二,认为它们之间的区分“是依其位阶及作用效力的不同来划分”。其三,认为令全部不是刑法规定;格大部不是刑法,只有少部分(刑部格)是刑法;式基本不是刑法。钱大群的论文旨在否定《唐律》是“诸法合体”与“律、令、格、式都是刑法”的观点,从而提出:律是刑法典,而令、格、式则主要是正面的典章制度法规,属于行政法规范。(注:参见前揭钱大群:《唐律与唐代法律体系研究》,第98-127页。)钱大群的结论虽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是,他的研究贡献主要是比较仔细地从唐代法律体系内部进行辩析,从而对于我们理解唐代法律性质依然有所帮助。
第二种观点认为“唐律、令、格、式都是刑法”,持此说的代表是王立民。他认为:律、令、格、式虽然各有特点,但是它们均是刑法则一。主要理由在于:其一,《新唐书·刑法志》:“唐之刑书有四:律、令、格、式。”其二,判断一部法典性质的标准在于制裁方式,认为“刑罚是刑法唯一拥有的制裁方式”;然而“唐令、格和式则仅有假定和处理两部分,大多没有制裁。这样,违犯了令、格和式就要到律去寻找相应的制裁部分内容。”诚如《新唐书·刑法志》所谓:“其有所违及人为之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总之,它们是不同形式刑法的并存,而非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并存;其原因则是它们比律规定来得详细、具体,具有补充律的作用,从而达到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目的。(注:参见前揭王立民:《唐律新探》,第46-60页。)
对于令、格、式性质问题,第三种观点比较有特色。张中秋认为它们不是行政法,但是也不是刑法。原因在于:一方面它们不是直接规定犯罪和刑罚的法律,而是关于国家机构组织及其行政方面的法律,所以它们不是刑法;另一方面违反这些规定,又要依据律予以处罚,因此它们不是行政法。结论则是“令、格、式是刑法化的封建官僚机构组织与行政执行法(典)”。(注:参见前揭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第82页。)张中秋的这一看法,显然受到滋贺秀三上述观点的启发,当然又有自己的体悟和阐发。
对于令、格、式性质的专门研究,学者也有所论析。霍存福对于令、式的辨析就非常仔细、具体。他认为:其一,唐人将律与令对举,反映了古代法律的法制和分化,体现了刑法与非刑法之间的差异。其二,在唐代,令与式属于非刑法规范;然而,两者之间又有着亲缘关系,从而难以作出通体的分别:原因在于“式出于令”。其三,关于格,霍存福没有具体的讨论,只是指出:“格对于律、令、式的‘补充修正法’性质。”(注:霍存福关于“唐代”问题写有多篇论文,参见霍氏:《唐式性质考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6期;《令式分辨与唐令的复原》,《当代法学》1990年第3期;《唐式逸文的遗存及搜集情况》,《中国法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唐式与日本式的比较研究》,《中外法律史新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而其他学者多有讨论。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唐代的格所调整的对象,几乎涉及国家行政机关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格是唐代与律并行的比较典型的行政法规”;并且认为:“格的体例结构同样以行政律为主而诸法合体的形式”。(注:胡留元:《从几件敦煌法制文书看唐代的法律形式——格》,《法律科学》1993年第5期;也见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律的传统与现代化——'93中国法律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304-317页。)有的学者认为:格既是匡臣的行政法规,又是惩民的刑法细则。(注:钱元凯:《唐格探索初稿》,西北政法学院科研处编:《法史研究文集》(上册),第265-271页。)有的学者则从比较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和把握格的性质。(注:具体的讨论,参见马小红:《“格”的演变及其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
必须承认,近年来学者对于唐代令、格、式法律性质的讨论,成绩是非常显著的,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唐代法律体系的性质具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依然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值得我们继续对此问题加以思考。
首先,唐代令、格、式虽然在法律规范的内容上与律有明显的差异,并且主要是对于官僚体制和行政运作的规范;但是,其宗旨在于督责臣民,因而完全站在现代的立场上来判断其属于行政法,显然无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唐代法律的“本来面目”(当然,就历史研究方法论而言,这是不可能的)。其次,简单地认为违反令、格、式要依律来定罪量刑就断定它们属于刑法,理据也是不够充分的。因为令、格、式作为独立的法律形式,是不争的事实;通过它们建立起来的各项规章制度和行政运作秩序要比刑罚制裁更为重要,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另外《新唐书·刑法志》的说法毕竟失之笼统,而且违反令、格、式是否以刑罚为主要制裁方式也是有疑问的。复次,从方法论角度讲,把令、格、式视为行政法或刑法,均有方法论本质主义之嫌。换言之,过分脱离中国历史语境,一唯地以现代法律标准来衡量古法律体系;或者一唯地使古代法律适应现代法律分类模式,结果难免削足适履。再次,笔者认为,唐代法律体系似乎立足于一种系统性的思维方式。例如,晋代的著名律学家张斐对于《晋律》的结构安排阐释很能说明这一点。他说:“律始于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终于诸修者,所以毕其政也。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故有三才之义焉,其相须而成,若一体焉。”又说:“自始及终,往而不穷,变动无常,周流四极,上下无方,不离于法律之中也。”(注:《晋书·刑法志》。)这一说法虽然不是直接针对唐代令、格、式等法律形式和体系结构的,但是,如果我们以此视角进行分析,那么,可以发现,《唐律》的体系结构以及律、令、格、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均可视为这一系统思维方式的反映。最后,中国古代皇帝专制与官僚政治体制的金字塔结构也是导致唐代法律体系独特性质的一个重要原因。《唐律》十二篇的结构告诉我们,除首篇《名例》的原则规定外,首重皇权,故有《卫禁》;次重官僚(皇帝治官不治民),故有《职制》;皇权和官僚体制赖以维持的基础则在社会和经济,故有《户婚》……归根到底,法律必须适用,故有《捕亡》和《断狱》两篇。律、令、格、式大致也然。律是国家的基本法典,但是一部《唐律》五百条不可能规范庞大复杂的官僚体制,故有令、式为之规范;又有不足,皇帝的敕、格为之补充。在笔者看来,唐代法律形式的区分固然不应否认,但不是绝对的;它们之间内在的一体性同样不可忽视。如果这样来理解,那么,律中的某些制度性规定的存在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而令、格、式的强制力根植于律也是必然的。
二、《唐六典》的性质及其行用
研究唐代政治史、法制史等的学者莫不称引《唐六典》,可见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但是,《唐六典》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典籍?这就涉及到《唐六典》的性质问题。另外,《唐六典》在唐代社会政治和法制生活中曾经起过什么样的作用?这又涉及到《唐六典》的行用问题。对此,古今学者颇有争议。在此,笔者首先综述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且提出自己的评论意见,以期对《唐六典》的研究有所帮助。
1.《唐六典》的性质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学者主要有两种说法:行政法典说和非行政法典说。行政法典说可以说是中国法制史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唐朝六典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古老的行政法典……自唐六典编纂以来,行政法从刑律中分离而自成一个法律部门,因而中国古代即有两大法典,一为刑法典,一为行政法典。”(注:前揭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第204页,此章文字系乔伟执笔;张晋藩先生也持这一看法,参见前揭张氏:《中国古代法制史》,第400-401页;论述最为详尽的是王超先生,参见王氏:《我国古代的行政法典——〈大唐六典〉》,《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洋洋四万言,考论甚详。)关于《唐六典》的行政法典性质的论证主要是由王超来完成的。他的主要理由是:其一,从制定的历史背景看,《唐六典》的制定使《周礼》的理想制度变为现实;唐代中央三省六部制度的现实则是《唐六典》制定的政治基础。其二,从体系内容看,《唐六典》包括了国家行政组织法与官吏任用法,因而“是一部典型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行政法典”。其三,从法律渊源看,《唐六典》“是以国家立法活动的形式产生,又以编制法典的方式制定”;其中入选的令、格、式则是唐代现行的行政法规。其四,从法律效力看,“《唐六典》不仅在开元年间成书时有充分的法律效力,就是在中唐以后,藩镇割据和朝政腐败严重影响国家行政管理效能的情况下,国家机关各部门在调整相互关系时,仍然是有法可依的,而这个法,就是《唐六典》。”(注:参见前揭王超:《我国古代的行政法典〈大唐六典〉》。)
在持《唐六典》的行政法典说的学得中,宁志新的观点比较特殊。他认为:《唐六典》“应是一部存在严重缺陷的不完备的行政法典,或更准确地称之为准行政法则。”(注:详细的分析,参见宁志新:《〈唐六典〉仅仅是一般的官修典籍吗?》,《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细辨宁志新的论文,可以看出,这是一种调和的观点。例如,首先认定《唐六典》是一部行政法典,因为法典的内容是唐代中央官僚体制和任用规范,渊源则是唐代现行的令、格、式行政规范,实践中又被引用;但是,法典的内容毕竟残缺不全,对于地方职官和各类使职不予规定,收入的令、格、式既不全面又不完整,制定以后也没有明诏施行等无法调和的矛盾,所以只得视为“准行政法典”。
持非行政法典说的学者在如何看待《唐六典》的性质问题上分歧比较大,根据笔者掌握的我国学者的研究情况,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典籍说。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指出:“开元时所修六典乃排比当时施行令式以合古书体裁,本为粉饰太平制礼作乐之一端,故其书在唐代行政上遂成为一种便于征引之类书,并非依其所托之周官体裁,以设官分职实施政事也。”(注:前揭陈寅恪:《隋唐制度源渊略论稿》,第82页。)严耕望先生认为:“六典一书之编撰,以开元时代现行官制为纲领,以现行令式为材料,其沿革则入注中,故其性质即为一部开元时代现行职官志。”(注:严耕望:《略论唐六典之性质与施行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4本,第74页。)陈仲夫则认为:“《六典》是一部以开元年间现行的职官制度为本,追溯其历史没革源流,以明设官分职之义的考典之书。”(注:参见陈仲夫:《〈唐六典〉简介》,收入《唐六典》(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钱大群先生认为:“《唐六典》是以《周礼》为体例,以国家机构与职官为纲目,以抄摘《令》、《式》中有关国家机关组织编制的内容为基本内容,以显示有唐一代制度盛况为目的一部官修典籍。”他的立论依据主要是:(1)《唐六典》只说唐代法律有四:律、令、格、式;(2)《唐六典》所收令、式残缺不全,无法独立运作;(3)没有“明诏施行”;(4)编撰者非专门立法机构,则是让“书院”去“撰集”,与唐代一般立法程序不同等。(注:钱大群等:《〈唐六典〉性质论》,《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钱大群:《〈唐六典〉不是行政法典》,《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也见前揭钱大群:《唐律与唐代法律体系研究》,第128-170页。)
第二政制官文书说。韩长耕认为:“除《周礼》而外,《唐六典》是现存的一部最古最完整的政制官文书。”还说:“《唐六典》应是初唐以迄中唐的一部社会制度史。”此说表述甚为含混。因为“政制官文书”应有法律效力,韩长耕自己也承认:“无疑是带有国家法典的性质,是有法律的约束力的。”但是“社会制度史”则否,仅仅表明《唐六典》是一部政制资料书,亦即所谓“政制类书”。(注:韩长耕:《关于大唐六典行用问题》,《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张弓也认为:“《唐六典》在‘官领其属,事归于职’的体例下,系统而详尽地介绍了唐代职官制度以及有关的政令、史事,不啻是一部唐前期职官全书。”(注:张弓:《〈唐六典〉的编撰刊行和其他》,《史学月刊》1983年第3期。)
第三官制法说。梁治平认为,行政法是一个近代的法律观念,宗旨在于保障公民权利,要求政府守法;它的法律基础在于宪法,而行政法本身只是宪法的实施细则。但是,在中国古代,既无所谓公民权利保障,也无所谓宪法政治,甚至没有独立的政府部门和纯粹的行政活动。结论是:“《唐六典》也好,明、清会典也好,都不过是古代官制法而绝非什么行政法。”官制法的出现“正好表明了中国古代国家的完备程度,以及立法者对于官吏问题的高度重视。”(注:梁治平等:《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66页。)
如何判定一部法典的性质?标准何在?这是我们讨论《唐六典》性质问题首先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而就《唐六典》来说,首先必须确定是否具有法典性质,其次才是什么性质的法典,尽管两者的关系极为密切。因为如果连法典也不是,那么,《唐六典》的所谓行政法典性质也就根本无法判定。学者的讨论没有予以充分的注意,这是非常令人感到遗憾的方法论缺失。
那么,判定一部法典的基本标准又是什么呢?在中国古代,以下几点可以作为基本的标准。其中,立法的一般程序。在中国古代往往先由皇帝谕令组织一个专门的立法机构,或委托专门人员从事法典的起草;而《唐六典》不具备这一特点,因为它是由图书编撰机构“书院”起草的,这是闻所未闻的。其二,内容是否反映社会实际。《唐六典》虽然本着“官领其属,事归于职”的原则详列现行职官制度;但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唐六典》详于中央官制而略于地方官制;对于某些已经弃而不用的职官和制度收而录之,而对于当时现行的职官与制度则不予规范。当然,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法典编撰史上也不乏例证;所以,千万不可单独作为一个评判标准。还有,所收令、式残缺不全,注释几占正文的一半,凡此均不符合法典的基本体例。其三,是否明诏施行。在中国古代,法典起草完毕以后,都由皇帝明诏颁行,方才正式生效。《唐六典》否是。这,不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吗?据此,笔者认为,《唐六典》不是一部法典;而陈寅恪先生的“类书”的看法信而不诬也。
事实上,那些认为《唐六典》是行政法典的学者,他们的主要理由是:(1)《唐六典》规定了唐代的现行官制和执行规范;(2)它的规范渊源主要来自唐代的行政法令、式;(3)虽然没有明诏施行,但是却被实际遵循和引用(关于引用问题下文再谈)。这样的论证过于形式化,因而无法服从。至于认为《唐六典》是一部“官制法”的看法,也有可商之处。笔者认为,说中国古代没有公民权利,没有宪法制度,这些都是信而有证的。但是,如果说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政府,没有纯粹的行政活动,虽然不能讲错,然而终究使人觉着“别扭”。笔者不禁要问:什么是“纯粹的行政活动”呢?中国古代国家机构运作过程又是什么呢?因此,指出古今之间的差异是必要的,而且比指出相同更为重要;但是,一唯以现代标准去裁量古代的事物,恐怕不妥,也无必要。所以,梁治平的上述看法没有多大的道理。
2.《唐六典》的行用问题。对此问题,唐代学者就有不同的说法,后世学者的争论大抵踪此,所以有必要稍事引述。今存唐代史料有三:韦述:《六典》完成之后于开元26年“奏草上,至今在书院,亦不行。”(注:〔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唐六典》引韦述《集贤记注》。)吕温:《六典》“草奏三复,只令宣示中外,星周六纪,未有明诏施行;”所以“郁而未用”。(注:〔唐〕吕温:《吕叔和文集》卷五《代郑相公请删定〈六典〉〈开元礼〉状》,也见《全唐文》卷六二七。)刘肃:《六典》撰成“奏上,百僚陈贺,迄今行之。”(注:〔唐〕刘肃:《大唐新语》卷九《著述》。)如此,则“行”与“不行”遂成千年历史“公案”,宋代以来争议不少,此不具引。
现在我们来看看现代学者的看法。日本学者玉井是博认为《唐六典》在天宝年间并没颁行,但是及至建中二年已经颁行。(注:〔日〕玉井是博:《大唐六典施行》,《支那学》第7卷第3号。)日本著名中国法制史家仁井田升也说:“虽《唐六典》成书时,似未被行用,但贞元、元和以后,则广为使用,五代宋代亦然。”(注:〔日〕仁井田升:《〈唐令拾遗〉序论》,参见仁井田升原著,栗劲等编译:《唐令拾遗》,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854页。)国内学者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两种:其一,肯定说。韩长耕在前揭文章中认为《唐六典》虽没有“明诏施行”,但实际上是“行用”的,并引例10条为证;结论:“《唐六典》在唐代不曾颁用,却又曾行用。”王超在评论诸家观点之后说:“《唐六典》产生于安史之乱前夕的唐朝鼎盛时期,不幸的是在它成书之后第十六年,即发生了祸国殃民的安史之乱,这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划时代历史事件。……可知韦述所说的《唐六典》,‘不曾行用’,正是指安史之乱前天宝年间玄宗倦于政事,昏庸享乐,李林甫、杨国忠乱政于朝和安史之乱使国家法制遭到破坏之时,当然是对的,是符合当时的实情的。”但是,到宪宗初年国势恢复,法制得到恢复,因此刘肃《大唐新语》认为《唐六典》“行用”是符合实情的,也是有史可证的。(注:前揭王超:《我国古代的行政法典——〈大唐六典〉》。)宁志新同意韩长耕的说法,认为“虽不曾颁行,但却曾行用,结论是令人信服的。”并且收罗35条例证(没有具体引出,时间自唐德宗即位到五代南唐二百余年)以后指出:“最晚自唐德宗时开始,朝廷大臣和政府机关已将《唐六唐》与《律》、《令》、《格》、《式》等法律形式同等视之。”(注:前揭宁志新:《〈唐六典〉性质刍议》。)
其二,否定说。一般来说,持《唐六典》不是一部法典或行政法典的观点的学者,往往对其“行用”也持否定态度。刘逖认为《唐六典》的制定是为了“装点盛世气象”,因此对“行用”提出质疑。理由有二:首先,唐代所有法律包括疏议都要明诏颁行,而《唐六典》则否,可见不合常规。其次,所谓援引《唐六典》,只是作为传统或先例加以援引,而非作为法律。(注:刘逖:《试说〈唐六典〉的施行问题》,《北京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钱大群针对刘肃《大唐新语》关于《唐六典》“迄今行之”的断案进行仔细的辨析,指出“原来,唐代的图书是否能藏于秘书省供官方阅读,是要经审查批准的,此即所谓‘行废’制度,或称‘行停’制度。”所谓“行之”则是指《唐六典》“被允许列在秘书省国家图书馆作为官方图书阅读。而根本不是说《唐六典》直到元和年间都作为法律被执行。”从而认为“作为唐代一部重要典籍,陈寅恪关于《唐六典》只是开元时制订的‘行政上认为便于征引的类书’的论断,可以看作是《唐六典》所起实际作用的概括。”(注:前揭钱大群:《唐律与唐代法律体系研究》,第153-155页。)这一结论,可以看作是《唐六典》“行用”问题的“信谳”。钱大群关于《唐六典》的“行用”尚有其它考辨,文繁不引。
笔者认为,关于《唐六典》是否“行用”问题的判定,关键在于:一方面,如果一部法典或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政书没有正式颁布实施,那么,不管其体例如何的完善,内容怎样的完备,都不宜视为法典或法规,而只看作法律草案。后世学者以之作为史料研究时的社会、政治乃至法律制度,均无不可。而上引韦述、吕温奏书中都用了一个“草”字,可见是作为“草案”上奏玄宗的;皇帝没“明诏施行”,则表明没有实施,道理至为明显。另一方面,如果《唐六典》在实际法律活动中被援引,则不能证明它就是一部现行法典或法规;因为在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中,援引传统、先例和故事(即便是前朝的)现象,史书不乏其证。(注:有关传统或故事的法律性援引的讨论,参见黄敏兰:《论中国古代故事制度的不成文法特征和功能》,《人文杂志》1992年第3期。)所以刘逖关于《唐六典》被援引史事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三 简短的结论及其他
通过上文的讨论,在此提出笔者对于唐代法律体系的几点基本看法:
首先,唐代的基本法律规范有律、令、格、式四种,唐人自己对此的概括是可以信据的。律属于刑法典应无疑问。但是律典的表达方式与现代刑法典有所不同,表现在对行为模式(假定和处理)比较详尽具体,涉及某些制度性内容。令、格、式的主要作用在于规范国家机构及其运用,从而与律在法律性质上可以划出一条界限。然而,由于违反令、格、式的处罚往往依据于律,所以有刑法化的特点而与行政法不同;因为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虽然也有可能求助刑法(刑罚制裁),但是基本的强制手段则是行政制裁。再者,我们也不能将令、格、式视为现代的“刑事附属法”(注:有关的讨论,参见储槐植主编:《附属刑法规范集解》,中国检察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页。)虽然“刑事附属法”的行为模式依据其他法律的性质而定,因为对于其他性质的法律规范予以刑罚制裁不具有主导意义。导致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这一特点,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古代法律“刑起于兵”的特殊传统,国家整合社会的组织结构,专制皇权对于臣民的严厉“督责”,古人注重系统的思维模式和立法技术,以及令、格、式本身与刑法的历史亲缘关系等等。(注:在汉代,律、令之间的原则性界限基本上是存在的;《史记·杜周列传》所谓“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可以为证。及至晋代,律、令的界限开始明朗,《太平御览》卷六三八《刑法》著录晋杜预《律序》“律以定罪名,令以存事制”即其例证,也是《唐六典》“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渊源所自。如以现存晋令逸文(参见张鹏一编,徐清廉校补:《晋令辑存》,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与唐令逸文对比,虽然在内容和篇目等方面有差异,但是两者的立法方法和调整对象则有相同之处;所以仁井田升认为“从晋令逸文中,可以看到唐令的前身。”(前揭《唐令拾遗》,第805页)格,最初也导源于科,亦即“后魏以格代科”(《唐六典·刑部》);而科,在汉代就是刑法,用于辅律补律的。后魏孝静帝《麟趾格》也是刑法典。(参见前揭马小红:《“格”的演变及其意义》和钱元凯:《唐格探索初稿》)到了唐代,《刑部格》还是刑法规范。式,如果从西魏年间的《大统式》算起(有的学者追溯到战国时期秦的“廷行事”,参见刘海年、杨一凡:《中国古代法律史知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9页),则也与刑法相关。这一简要考述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律与令、格、式之间的不解之缘,以及它们之间分化过程,一种非刑法化的变迁。)
令、格、式虽然均为非刑法规范,并且在总体上可以作出一些区别,但是它们之间的界限则是相对模糊的。应该说,令是最为基本的;式是令的发展,所谓“式出于令”是也,所以一般地说式的规范要比令具体(但并不绝对);格则是对令、式(包括律)的追加和补充,因此涉及面比较广泛,区分也就更为不易。(注:参见前揭霍存福:《唐式性质考论》和《令式分辨与唐令的复原》。笔者尝读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所收唐代令、格、式逸文,初读之下,也觉得颇难作出原则性的区别,也许可以聊备一证。)
其次,在笔者看来,《唐六典》只量部“类书”,既非法典,更非一部行政法典。这主要表现在:编撰程序不符唐代一般规则;内容与唐代现行体制出入甚大,收录的令式不能满足现行官僚机构的正常运作(尽管编撰者力求完备、严整);现实政治、法律生活中的“援引”无法证明它就是一部法典。
最后,关于唐代法律体系研究的方法问题。有的学者在判定唐代法律体系的性质时的基本方法是,以现代法律分类标准去衡量唐代法律(这固然无法绝对避免,因为历史学作为一门解释学科,“前见”可以说是合理的存在;但是,过于强调现代法律的分类标准,往往会无意之中歪曲历史,或者导致历史的虚无主义,或者无助于更好地理解历史。),结果,对于符合现代标准的,则予以肯定,对于不合现代标准的,则予以否定。例如,认为“律、令、格、式都是刑法”的观点,它的根本依据就是违反令、格、式要依律处罚,而全不考虑令、格、式作为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又如,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政府部门和纯粹的行政活动”,从而没有行政法。这种现代式的、西方化的标准的运用,尽管是为了揭示中国古代法律的特殊性,用意未尝不好;但是,刻意的强调,那么中国法律又是什么呢?因为中国古代“家天下”的王朝政权,如以现代标准衡量那简直不可以称之为“国家”,中国古代也没有“政治”,如此等等。结论不是非常奇异可怪吗?再如,有的学者看到令、格、式、典,就认为是行政法(或行政法典),则又简单地以古代比附现代,而不深入考虑唐代法律的独特样式。
笔者浅见以为,在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时,是否可在照顾古今的同时,确立一个比较可行的标准,这一标准可以稍微抽象一些,使其能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具有更大的解释效益。当然,这很难,但是值得我们共同努力。学界提倡“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学术命题,(注:有关的讨论,参见《中国书评》,文章很多,不拟详列。)非常有意义;尽管“本土化”不是拒斥学术的现代化,也无法避免现代(基本上是西方的)学术“话语”影响。但是,在中国历史中发现学术“话语”,同时关注其现代性的创造性转换,这将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极具挑战性的学术工作。
总之,对于唐代法律体系性质的研究,很有必要在新的认识前提或方法视角下重新予以思考。笔者以为,现在的基本任务是:我们可以在现有史料基础上(现有学者的讨论已经将此史料网罗殆尽)进行分析,首先,给出关于唐代法律体系性质的描述定义,以期揭示它们自身的固有特点;然后,再与现代部门法律的划分标准进行比较,以期作出一个恰当的批评。笔者上文的讨论思路,大致就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