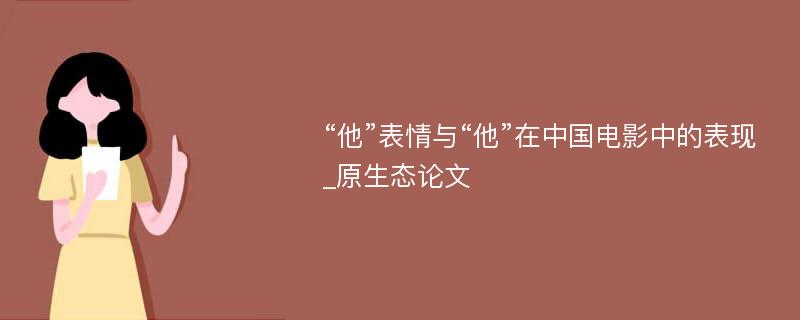
中国电影的“他”表情和“他”表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电影论文,表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一个国家的认知,它大多包含有国家表情的成分。所谓国家表情,也就是一个国家形象及其气质的一种人格化的表情意味,人们提及或者联想到一个国家,也就会自然浮现该国家一种典型性、标识性和符号性的人物表情及其与该国家特有的风土人情相互配合而成的视觉意象。它是根据经验以及想象而形成的,在一种准确和误读之间不断摇摆或者修正,并怀有不同的认同情绪。
在如此国家表情中,电影表演有着特殊的功能意义。在国际交往不多以及入境游客稀少的国家之中,除了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表演之外,电影表演也就基本上成为了外界认知的主要通道,电影中的演员表演成为了该国家普通民众以及人文风情的形象代言人,演员表情以及表演成为人们辨别和体认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即使在国际交往密切的发达国家,也会有意识或者潜意识地培育电影表演的国家表情作用,并通过它实现一种文化领域的软实力以及扩展到经济领域的宏观利益。它包含着深刻而微妙的政治、文化以及经济动机。
在新时期电影表演美学发展过程中,演员表演也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中国国家表情的角色,尽管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国际交往的迅猛发展,它只是其中的一个角色,而且,它的分量越来越弱。从八十年代“第五代”“寻根电影”阴郁而焦虑的表演神情,到九十年代“第六代”“状态电影”茫然而放肆的表演神态,到新世纪“冲奥电影”人偶尔华丽的表演奇观,它都与当时的其他各种国家表演元素共同作用而形成了中国表情。毫无疑问,这些电影表演以及表情大多是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体现的是“汉文化”的故事以及生活形态,它自然也是中国国家表情的主体部分。需要关注的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演员表演,在新时期电影表演的国家表情传播过程中,也有着特殊的功能作用。尽管学术界对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还有着不同的认识,如同饶曙光所称:
我们有关少数民族电影的很多争论,主要是围绕两个层面:一个是创作身份,到底是不是一定是少数民族省份的导演拍的?我觉得不应该以这个衡量,另外很多理论家提出的一个标准,就是少数民族电影一定是表现少数民族文化的,这也很难界定,因为对文化本身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变化,文化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最近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在面临着一个现代环境下的裂变,这种裂变当然也产生了很多困惑,尤其是当艺术家来审视这些事,它也会有一些审美。①
少数民族电影的演员表演以它特有的文化气质,使中国电影打破了“汉文化”的国家表情,在中国版图内展示了一种“异域”、“异族”的表演风貌,是一种中国电影的“他”表演和“他”表情。它使国外观众对于中国电影以及中国的认知中,了解到中国国土的辽阔、民族的众多以及中国文化的必然性,除了“汉文化”所演义出来的国家表情,还有少数民族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国家风情。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演员表演,成为了体现中国国家表情丰富多样的一种形象代言人。陈墨如此评述近年拍摄的少数民族电影《碧罗雪山》:
在我们这个时代,《碧罗雪山》难得的是它真的去凝视一个民族的生活,而且沉思。这部电影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看。第一个维度是可当民族志看,也就是民族学的观点。因为它是讲傈僳族的故事。其次,也可以从人类学的观点去看它,因为它实际上用人类学的眼光看人物、讲故事。它并非真要为傈僳族写志,故事中的人只不过是傈僳族中的一个部落,一个很封闭的部落,作者是在研究这个“民族/部落”的生存状况、生态状况,去凝视、沉思和表现原生态。非常了不起的是,作者的心态非常沉静,以至于我们能够看到政治人类学的生动内容,那就是其中错综复杂的权利线索及权利博弈:老祖宗的权利、年轻人迪阿鲁的权利、有钱人暴发户的权利、政府的权力、有漂亮女儿人家的权利,当然还有普通村民的生存权利等,各种权利都在展开博弈,呈现出生存斗争的真实状貌,但遗憾的是,都没有深入进行下去。再次,影片的重点,当然是生态人类学,即对生态和人类之间关系的考察。生态片的真正意义是考虑傈僳族会按照原生态那样去做。人杀熊,熊也杀人,共有同一个家园。熊被人杀了,人又被熊抓了、吃了。在那样一些部落里实际上被认为是正常的现象。这个部落有多少的历险都是不奇怪的,生存如同悲壮的史诗。②
这部“讲傈僳族的故事”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涉及了“民族志”、“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生态人类学”,“这个部落有多少的历险都是不奇怪的,生存如同悲壮的史诗。”显然,它与表现“汉文化”的电影及其表演有着显著的不同,“它真的去凝视一个民族的生活,而且沉思”,展现了另外一种的中国表情。这里,只要是一种平实的表演形态,它就会被观众认为是真实的少数民族生活面貌,这样就具有一种真实的感染力以及冲击力。它是基于陌生化或者遥远化的“他”表演和“他”表情,演员只要表现出一种质朴的状态,也就构成了真实化效果。如同中国观众原来对于伊朗电影的认知,郑洞天称道:“以前我们诧异于伊朗电影中大量非职业演员那么出彩,我后来去了伊朗才了解到,包括阿巴斯在内,他们的影片里并不都是非职业演员,他们有许多优秀的专业演员,只是我们看看他们像非职业演员而已。”③在此,一方面是由于伊朗电影的朴素表演风格以及“有许多优秀的专业演员”,另一方面也是陌生效应所出现的误读,而在普通电影观众的心目中,它更会被误读为它们就是伊朗人的真实生活。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也会产生如此的“想象”甚至“虚幻”,从而使演员表演也具有了“民族志”、“人类学”的意味。它的国际传播效应,除了说明中国有着众多民族的缤纷表情,也暗示了在中国广阔的疆域之中,其实“汉文化”也有着多样表情:
汉族其实又可以分成无数个部落,比如山西、陕西、湖北、安徽等地域的汉族,生活状貌并不相同。“中国人”这一个概念概括了十几亿人,其实哪儿的汉族都不一样。在汉民族当中有保留了数千年甚至上万年的生活方式,比如烧香、叫魂、婚丧习俗等。每个村庄和部落固然有相互交融的东西,但也有其特别之处。④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他”表演和“他”表情,使国外观众对于中国的认知需要具有一种复杂而开放的态度。
在新世纪的“冲奥电影”中,电影表演呈现出了卡通化以及奇观化的倾向。“华语大片敢于跨界而与好莱坞搏弈,这才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势崛起。不妨说,中国电影由此而迈出了走向海外,并在拓展国际传播空间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华语大片的优势在于,为中国电影产业化领航,扛起了商业大片之旗而抗衡好莱坞,提升了我们民族电影在全球主流市场里的竞争力,扭转了中国电影产业命运的颓势”,虽然“转瞬十年过去,华语大片竟陷于与自身初衷相背离的处境”,但是。“其历史成绩是不容低估的。”⑤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也以自己的各种通道“走向海外”,它的表演形态其实也有着奇观化的倾向,尽管它可能是极其原生态或者朴素性的表演方式。它构成了一种双重的表演奇观效应,第一圈是对于中国人的表演奇观,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熏染,诸如政府产业开发、旅游热、外出打工、求学以及广播电视信息输入的介入因素,使少数民族地区也发生了显著或者悄然的变化,这种表演奇观意识有所削弱;第二圈是对于外国人的表演奇观,缘之于地理的空间远隔以及历史文化的生疏,它的奇观效果会强于中国人的接受体验。因此,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表演文化,在双重的观众圈中有着不同的接受美学效应。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走向海外”,也会借助于人类学影视片颇受青睐的优势。《碧罗雪山》就是一部与日本经典电影《山节考》颇为类似的影片,它涉及到了图腾崇拜及其它在当代的悖论关系,“虽然故事是一个偏远山区所发生的,但是人跟熊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又是极具现代化的。现在全人类都面临着怎样和自然共生的大问题。影片一下子把一个极个性化的一件地域小事和整个人类联系起来。”⑥这一“偏远山区”,却又村村都有教堂和篮球场。影片的导演不是站在一种庸俗的知识分子立场,去怜悯和同情少数民族,而是怀抱着一种平等或者平视的情怀,演员的表演也不是去表现苦难,而是在平实的表演中将观众引入一种真实的环境之中。它不是一种伤感的表演形态,而是一种对于人类文明的新表情、新描述和新追踪,甚至有着后现代和前现代的重构意味,包含着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的意义,也就颇为可能受到国外电影界以及普通观众的关注。因此,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表演,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中国国家表情,以一种“凝视、沉思和表现原生态”的表演气质,展现了中国国家表情的“他”形态和“他”效果。
在中国经济与政治实力在国际格局中微妙变化的过程中,国外对于原来陌生以及有点隔阂的中国,逐渐视若“庞然大物”,却又不知“脾气”如何。国家表情重要代言人的电影表演,可以成为让国外观众了解中国“脾气”的一个有效途径,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表演也以自己的方式成为其中一条小径,以自身的表演“脾气”使国外观众了解中国的文化“脾气”,从而认识中国的国家“脾气”。
在新世纪的电影表演美学中,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表演“脾气”发生了一定的形态变化。由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特殊性质,它属于一种敏感的作品范畴,二十世纪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基本上属于“《五朵金花》模式”,《碧罗雪山》导演刘杰称道:
咱们国家的民族电影创作在以前都被洗了脑,做了强烈的心理暗示,心里都有个《五朵金花》,再加上献礼片,我有时就会不自觉地想找补点什么,总想掺掺“沙子”,不自觉地给自己修正、矫视。总是很怕碰民族问题的地雷。我觉得真实其实才是最大的尊重。⑦
因此,“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特别容易被政策化,被宣扬某种现行政策。”⑧它在电影表演上也容易“被政策化”以及被“格式化”,也是一种“《五朵金花》模式”,少数民族青年演员多为俊男靓女,朴实而又充满朝气,表演风格细腻却又有一点戏剧化的痕迹。但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国家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变化以及电影艺术家“真实其实才是最大的尊重”的观念发展,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表演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嬗变。由于这些电影的生产动机以及目标受众的不同,它们的表演形态也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及其呈现方式。
一是零度表演风格。它一般与导演的零度叙事原则有关,由于导演尽力将自己的主观情绪压制到最低点,拒绝煽情以及戏剧化的叙述,演员表演也必须保持一种冷静而自然的体现方式。在影片《可可西里》的开头,北京来的藏族记者见到巡山队长日泰,日泰并没有表现出惯常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主人公的好客和热情,而是冷冰冰地见了一面,颇有不近情理之状,基本上确立了影片如同故事内容一样真实而冷酷的表演基调。其实,序幕部分的巡山队员被杀,已经展现了零度表演风格的端倪,盗猎分子将一名巡山队员抓了,问他是否是日泰的手下,等到肯定的答复以后,盗猎分子下令团伙成员将他松绑放了,而当团伙成员准备松绑时,盗猎分子却没有任何前奏地枪杀了巡山队员,鲜血溅到团伙成员的脸上,使其惊愕万分。从下令松绑放人到突然抬枪杀人,转瞬之间盗猎分子并没有戏剧性的表情和表演,只是一种冷漠而下意识的表演动作。到最后日泰被枪杀时,也是如此冷漠而下意识的表演桥段,双方肃然对峙,几声枪响之后,巡山队长日泰死了,没有表现他死时或者死后的表情,也没有悲伤的音乐衬托他的牺牲,只是大自然飘动的落雪,烘托了此时的氛围。后面的镜头是几位喇嘛用清水洗净日泰的尸体,慢慢响起了六字大明咒的唱诵声,一切都是波澜不惊。显然,这种零度表演风格,比戏剧性的台词和动作表演更具有心灵的震憾力,在不动声色的表演之中,潜伏着强烈的心理和情感动作。
与“《五朵金花》模式”的正面主人公表演不同,零度表演的方式不再是阳光和热情,甚至是一种反“英雄主义”的表演方法,日泰冷漠地被枪杀,演员的表演没有高潮地加以表现,只是在看似偶然却是必然的境遇中遭遇杀身之祸,演员在前面的表演中虽然有所铺垫或者暗示,也没有特别强调和突出,只是在一种偶然和必然的交织中发生了。自然,作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零度表演风格,《可可西里》有着它题材的需求性和适应性,它是一个发生在人类生存极限地区的故事,它由真实事件改编而来,呈现出如同真实的电视纪录片一般的冷峻气质,可可西里的神秘和荒蛮,关于它的影片需要一种朴实而残酷的表演风格,影片中藏羚羊被枪杀,在火葬547具藏羚羊尸骨时,巡山队员按照藏俗绕圈行礼以及将被毁的汽车熊熊烧掉,可可西里充满着一种如同丛林法则一样的残酷,演员的表演自然也需要一种残酷表演方法。为了配合这种零度表演方法,《可可西里》中的角色台词很少,而是运用画外音交代故事的起承转合情节关系,以使演员在表演中保持一种统一的冷峻格局。如此零度表演风格,成为特定题材电影的表演样式追求,也成为了新世纪少数民族电影表演美学的呈现方式之一。
二是神秘主义的表演形态。它属于一种戏剧化的表演方法。新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戏剧化表演,可以分为两种形式:第一,是“《五朵金花》模式”的戏剧化表演方式,它是常规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表演方法,有着意识形态整体的规定性以及表演历史的惯性,“有时就会不自觉地想找补点什么,总想掺掺‘沙子’,不自觉地给自己修正、矫视”,在新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表演中仍然存在,甚至还应该是主流的表演形式,例如近年拍摄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额吉》和《骆驼客》;第二,是一种象征格式的表演方法,由于故事具有一种寓言叙事框架,虽然也是充满戏剧性的,但是,它有着哲学和宗教的“灵异”情节系统,产生了一种神秘主义意味的表演方法。根据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改编的藏族题材影片《喜马拉雅王子》,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导演胡雪桦称道:
它实际上在根脉上和《兰陵王》有一个延续,因为电影毕竟都是我拍的。但同《兰陵王》不尽相同,《喜马拉雅王子》不是寓言式的,而是带神秘主义色彩的史诗电影(Surrealism epic)……
因为汉文化,大家从各种艺术角度,各种艺术形式,已经做了很多的艺术探索。《兰陵王》是在我当博士的时候,发现《兰陵王》的剧本在日本被很好地保存下来了。但这个戏中国失传了。这个戏很重要,在中国的戏剧上如果没有了《兰陵王》、没有了《踏摇娘》,中国的戏剧就没有了。我在做《兰陵王》的时候,是先做的舞台剧,然后做的电影。我把《兰陵王》的背景搁在一个“凤文化”的背景之下。我们不仅是龙的传人,同时我们还是凤的传人……
藏族文化是个非常辽阔的文化,我们一提到藏文化,首先就想到拉萨那一块,其实还有云南、甘肃、四川这么一大片,这实际上也是我们民族文化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些都不是我有意识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发现我第一个拍的是一个鸟语的,第二个拍的是个藏语,那么我第三个一定要拍一个母语的。⑨
这里,也说明了“汉文化”的复杂历史及其“表情”,“我们不仅是龙的传人,同时我们还是凤的传人”,“藏文化”也“还有云南、甘肃、四川这么一大片”。《兰陵王》讲“鸟语”的演员表演自然是一种寓言表演,它不必拘泥于生活真实,而是一种历史神话意义的虚拟表演,讲“藏语”的《喜马拉雅王子》表演则是“带神秘主义色彩的史诗电影”表演,它的表演形态是大开大阖,具有戏剧性表演的爆发力和冲击力,肢体动作、面部表情和眼神变化的幅度都非常大,甚至颇为夸张。为了揭示角色的内心世界,影片大量采用了特写镜头,演员必须具有充沛的情感内容,才能在表情和眼神中准确而充实地表现灼热的心理活动。扮演男主人公拉姆洛丹的蒲巴甲,尽管表演稍显稚嫩,例如表演的情感层次感还可以更加分明,但是,也较好地表现了角色在复杂处境下的复杂性格,敢爱敢恨,嬉笑怒骂,多场决斗戏、情感戏以及心理戏都是酣畅淋漓,尤其是在特写镜头的“拷问”下,眼神所表现出来的心里内涵是饱满的。这种戏剧性的表演形态,使《喜马拉雅王子》出现了“裸体骑马”、“水中决斗”以及“男女情爱”等非常煽情的表演处理方法。它的象征表演方式,则是更主要的表现在“亡父魂灵”和“狼婆”的表演之中。由于“亡父”乃是“魂灵”,“狼婆”也是亦人亦巫,演员的表演不能采取常规电影的生活化表演方法,而是需要在人与鬼、人与巫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结合点以及在不同情景中的着重点。
那个时代还是有巫的,她是能和鬼魂对话的。狼婆警告鬼魂:“你的复仇,是触犯天神的大祸”;她对拉姆洛丹讲过去的故事,其实也是让他了解真相;当拉姆洛丹重又准备折回时,狼婆又阻止他复仇。最后鬼魂问狼婆:“你教我儿子什么咒语?”狼婆说:“爱,真正的爱。”鬼魂对拉姆洛丹的昭示,是人对神的不可抗拒的接受,狼婆的设置就是在人与神之间有了一个通灵者,也是善良之魂和邪恶之魔的抗争者。这是电影的“灵界层面”。⑩
如此“灵界层面”,也就需要一种虚幻和真实的“灵界”表演,是一种“神秘主义色彩”的表演方法。在新世纪少数民族电影表演中,也有着独特的美学意义。
三是原生态表演。它与零度表演有所不同,零度表演乃是一种风格,原生态表演则是一种状态,零度表演可能是原生态表演的状态,也可能是戏剧化的表演形式。原生态表演,是将生活化和真实性的表演方法推向极致。例如影片《可可西里》高度强调了本色表演及其生活化,甚至是一种赤裸裸的原生态生活,例如记者尕玉吃肉时的方法不对的一场戏;布东温泉保护站巡山队员欢快地跳舞,由于姿势的不协调以及体形不佳,跳得毫无美感;第三天,巡山队在周奈湖抓捕犯人时脱下裤子过河;在茫茫大雪中,巡山队员“我走不出去了”的哭声;巡山队员刘栋被吃人的流沙慢慢吞噬的过程,都是属于一种真实表演的美学范畴,它有着强烈的表演冲击力及其魅力。这种真实表演,与《可可西里》的特定题材风格有着不同寻常的默契,是一种“天然去雕饰”的本色演出。演员的服装不是漂亮华丽,而是破破烂烂的,对白也不是标准的普通话,而是夹杂着藏语,体现出一种朴实自然的表演性格。导演陆川曾有如此表述:我选择的演员尽量接近实际生活中的巡山队员,有的甚至是有过这种真实经历的人,当然主人公队长需要选择具有表演经验的职业演员,扮演巡山队长日泰的藏族演员多布杰是西藏自治区话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他是一个有着鹰一样的眼睛、坚毅、粗犷的男子汉,在业余演员中间,有原来的巡山队员,也有原来的盗猎分子,他们在演出中体现出令人不容怀疑的真实感,有的人因为原先是盗猎分子,有过被打被关的经历,在拍摄中表演被殴打的情景时的那种状态,真实得让人忘了这是在演戏。这里,陆川基本上采用的是演员的本色表演,例如影片中与演员名字同名的角色马占林,一个剥藏铃羊皮的小老头,因为家庭贫穷,带着家人在这严酷之地冒险,而且,这位肮脏猥琐的小老头儿有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最后竟然活着走了出来,有着一种毋庸置疑的表演真实性,是影片给予观众印象深刻的人物表演记忆之一。
关于原生态表演和戏剧性叙事矛盾的问题,郑洞天在与导演刘杰对话《碧罗雪山》时称道:
以前我们所有追求纪录片风格的,或者手段上都用非职业演员、手持摄影机,用表面上看不修饰的美学造型,一直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一旦故事有戏剧性了会是什么样的?许多导演往往用生活流的纪实形态时,我们觉得那是他作品里最动人的、最有价值的部分。一旦开始要人物照编剧设定的命运走的时候,两个东西就打架了:非职业演员的能力以及导演驾驭非职业演员怎么表演,设计出来的镜头和原生态之间的分寸,这个时候就特别考导演的功力。……这次你的故事恰恰特别戏剧化,单独拿出来按经典戏剧的规律来套,这个故事完全符合。就像赵老师刚才分析的,所有的条件都够,这其实就是戏剧性达到了一个点,这个点才促使最后这个故事动人,但是所有的处理,特别是表演和镜头,仍然让我们感觉是真的,我个人认为这两者之间处理得这么和谐在中国电影中是前所未有的。(11)
导演刘杰阐述道:
我每天拍,但全剧组的人都没有剧本,工作人员没有剧本,他们说压力很大,因为每天到了现场后导演才说今天干什么,他们到现场才准备,担心自己做不好。我说你们有担心,我很开心,这说明你们有责任心,你们都做得很好。因为我之前只写了个提纲,到那儿之后我发现不能凭着提纲拍。第一,这个提纲是我臆想的,第二,必须让这些故事成为这些人自己的故事,你不能告诉他你今天说句什么台词演个什么,你一说这个就完蛋了。所以我就用这一个月的时间给这些人洗脑,我使他们相信他们的生活中会发生些什么,他们的生活中有熊,每天就是大家一起聊天,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人能演到什么程度,就试,所以每天都在拍。拍了半个月之后,我说那个老爷爷不行,得换一个,所有人都懵了,说“导演,咱们以前半个月拍的可就全废了”,我突然之间就冒了一句话说“头半个月本来就没有用啊”,大家一听又懵了。(笑)我就没认为之前拍的有用,就是这样试啊试啊,我才知道谁是谁,谁不能演,谁能演成什么样。(12)
应该说,如此也不失为化解戏剧性叙事对于原生态表演障碍的有效方法之一,尤其是对于非职业演员,“两个东西就打架了”的问题,通过“试啊试啊,我才知道谁是谁,谁不能演,谁能演成什么样”,原生态表演与人类学影视片的美学走向颇为一致,都是运用真实的美学力量,“真实其实才是最大的尊重”,也形成了新世纪少数民族电影表演的一种重要风格特征。
由于新世纪少数民族电影的“走向海外”策略,一些影片生产已经与国外影业机构开始合作。陆川曾经说道:《可可西里》开始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影片的海外投资方希望我能够将它拍成一部标准的美国“西部片”,所以,我在剧本里面设计了秘密警察、盗猎者和巡山队员,他们彼此之间形成各种矛盾冲突,有追杀、有枪战、有爱情,这样一个非常商业的剧本得到了认可。只是陆川率领摄制组到了可可西里拍摄地以后,又产生了新灵感,最后拍摄完成的影片已经和原剧本有了一定的差异,但是,它还是基本保留了雪域高原、人与自然、生命被扼杀、正义不得伸张这些商业性或者艺术性影片的卖点,还是一部可以获取好莱坞片商信任的电影作品。《喜马拉雅王子》虽然不是中外合拍影片,但是,它的视野是国际性的以及有着“走向海外”的制片路线。它也是一部反映藏族题材的作品,虽然从《哈姆雷特》改编而来,但是,导演胡雪桦的创作方向是莎士比亚式的、藏式的以及胡雪桦式的。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西藏题材一直是各种话语的争夺之地,好莱坞也制作过几部涉及西藏的电影。胡雪桦认为:“我始终觉得有些作品对西藏拍摄的角度是带功利色彩的。好莱坞拍西藏,它并不会尊重西藏,因为它有很强的商业目的。西藏能引起‘话题’,是个热点,好莱坞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我们以为它从政治角度上看西藏,但我觉得它首先是商业上的。”“现在世界上的战争大都是宗教的战争,复仇的战争。人类太需要‘爱’需要‘宽容’了。这些实际上是我这部电影的由头。为什么搁在西藏,因为,我觉得,西藏还是一个圣洁的地方。”(13)
正是这些国际元素的介入甚至核心作用,新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表演美学也就有着多种力量的博弈关系,在影像表演的现代化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零度表演、神秘主义的表演形态和原生态表演等各种表演形态,在它的背后也有着国际元素等多种动力的渗透和制约关系,它们或隐晦或显著,或有意识或无意识,使新世纪少数民族电影表演也成为了一种颇为意味深长的国家表情。它的电影表演处理,还体现在以下两层关系,一是从原来汉族演员与少数民族演员共同扮演少数民族角色,现在演变为基本上由少数民族演员扮演少数民族角色,而且,颇为注重由本族演员来出演;二是从原来职业演员与非职业演员共同扮演,发展到更多地倾向于由非职业演员出演。《碧罗雪山》采用了非职业演员的表演方法,女主人公吉妮的扮演者娜真叶甚至没有上过学,导演刘杰称道:“她就生活在高黎贡山上,往西下山就是缅甸,往东下山就是怒江,以山里人的脚力,从江边公路上她家要爬四个小时的山”,“她家没电,电视也没有。她没上过学,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山上放羊,她甚至没去过县城。我问她为什么不去看看,她没回答,我猜想她是羞涩和胆怯。”(14)她一开始不肯演,导演颇是用了一点“计谋”,让当地乡干部“吓唬”她家,才同意来拍戏。赵小青称道:“我认为这部戏在使用非职业演员、使用原生态演员这点上有突破。以前非职业演员的选择只局限于真实和质朴,很少考虑他们的相貌,是否耐看?是否让观众感到愉悦?是否在影像层面有审美价值。这部影片考虑到了有关影像层面的美感问题”,“也因为他们形象的美好,加大了影片的悲剧力度。”(15)《可可西里》也是多使用非职业演员,由部分专业演员与非专业演员混编而成,他们大多有着影片所需要的“血与泪”以及在人类禁区为生命而搏斗的“生命体验”,日常生活化的本色表演显得单纯而又朴素。显然,它们都与原生态表演的美学追求有关。
在上述零度表演、神秘主义的表演形态和原生态表演等各种表演形态分析中,也基本上可以总结出新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表演美学的两个基本文化态度。第一,是极致的真实表演,主要体现为原生态表演及其零度表演,产生一种真实再现少数民族表情的表演方法。作为一种艺术创造,这些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表演自然是经过演员、导演以及其他职能部门的美学处理,但是,它的文化目标是实现一种纪录片一般的民族志和人类学效果。毫无疑问,这里的真实表演概念,包含着一种首次性和唯一性的原则,余秋雨称道:“艺术家的这种表现具有首次性和唯一性。他不重复他人,也不应被别人重复。在他之前,人们虽然经常面对这种现象也会‘熟视无睹’;在他之后,世界对于人们,至少在一个角落上变得更加真实。是的,只是真实,但为了渐渐逼近它,几乎要绞尽人类最智慧的代表者们的脑汁,几乎要经历人类的全部发展史”,“因此,即使仅仅为了表现真实的艺术家,也需要有标新立异的胆识。”“大师成功的根本秘诀,在于他们是真实的发现者。”(16)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真实表演,也以这种“首次性和唯一性”为归结,追求一种“不重复他人,也不应被别人重复”的表演文化效应。在“首次性和唯一性”的陌生化基础上,成为中国观众的“他”表情和“他”表演以及进一步成为国外观众的“他”表情和“他”表演,并最终成为中国国家表情的一个组成内容,“在他之后,世界对于人们,至少在一个角落上变得更加真实”;第二,是极致的美感表演,它缘之于神秘主义的表演美学追求,表现一种浓彩重墨的表演效果以及它的强烈美感,如同如椽巨笔,演员的动作和表演纵横捭阖,大气而又浓烈,阳刚处宛如是“大江东去”,阴柔处又好像“小桥流水”。胡雪桦称道:“《喜马拉雅王子》是一个关注人的生存的电影,一个颠覆了原来的‘宫廷的阴谋篡权的复仇’的故事,探寻‘爱和宽恕’的电影。在表现上我们努力地要体现出电影声光色魅力的形式感,让影像充满神秘感并流露一种不经意的现代韵律。”(17)如此的“形式感”和“现代韵律”,也就要求演员表演具有一种与“声光色”和“神秘感”相适应的美感形态。“美,是对真与善的超越、包容和沟通”,“艺术创造的内驱力,可以以真为目标,可以以善为目标,但最终都应以美为皈依。”(18)
这种真实表演和美感表演,似乎是表演影像现代化的两极,在文化姿态上一低一高,在风格取向一实一虚,但又没有美学等级高低之分。它表明了新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表演美学在政治、文化和产业方面的矛盾、妥协和竞合关系,既有着本土的因素,也有经济全球一体化以及文化趋同化环境下的国际元素。新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走向海外”的过程中,这些表演形态也就承担了中国国家表情的代言作用,它的丰富多彩及其魅力,对于国外观众了解中国文化“脾气”以及中国“脾气”是有益的。
注释:
①康健民等:《“〈碧罗雪山〉观摩研讨会”综述》,《电影艺术》2010年第10期。
②刘杰、郑洞天、陈墨、赵小青:《碧罗雪山》,《当代电影》2010年第9期。
③刘杰、郑洞天、陈墨、赵小青:《碧罗雪山》,《当代电影》2010年第9期。
④刘杰、郑洞天、陈墨、赵小青:《碧罗雪山》,《当代电影》2010年第9期。
⑤黄式宪:《与世界对话:凸显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及其国际传播实力》,载黄会林主编:《从孙中山到乔布斯:中华文明的现代传播——“第三极文化”论丛(201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⑥刘杰、郑洞天、陈墨、赵小青:《碧罗雪山》,《当代电影》2010年第9期。
⑦刘杰、郑洞天、陈墨、赵小青:《碧罗雪山》,《当代电影》2010年第9期。
⑧康健民等:《“〈碧罗雪山〉观摩研讨会”综述》,《电影艺术》2010年第10期。
⑨胡雪桦、倪震、胡克、杨远婴:《喜马拉雅王子》,《当代电影》2006年第6期。
⑩胡雪桦、倪震、胡克、杨远婴:《喜马拉雅王子》,《当代电影》2006年第6期。
(11)刘杰、郑洞天、陈墨、赵小青:《碧罗雪山》,《当代电影》2010年第9期。
(12)刘杰、郑洞天、陈墨、赵小青:《碧罗雪山》,《当代电影》2010年第9期。
(13)胡雪桦、倪震、胡克、杨远婴:《喜马拉雅王子》,《当代电影》2006年第6期。
(14)刘杰、郑洞天、陈墨、赵小青:《碧罗雪山》,《当代电影》2010年第9期。
(15)刘杰、郑洞天、陈墨、赵小青:《碧罗雪山》,《当代电影》2010年第9期。
(16)余秋雨:《艺术创造工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第72页。
(17)胡雪桦、倪震、胡克、杨远婴:《喜马拉雅王子》,《当代电影》2006年第6期。
(18)余秋雨:《艺术创造工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