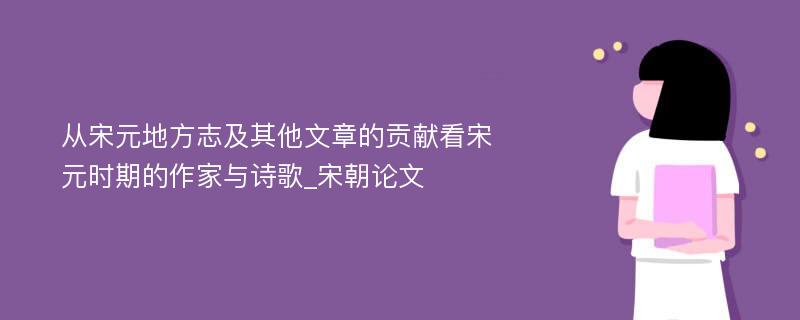
宋元筆記方志等文獻所見宋代作家及詩文輯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元论文,宋代论文,作家论文,詩文輯考论文,方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①,收録宋代詩人八千九百餘人,詩歌二十多萬首。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②,收録宋代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七萬餘篇。二者均爲宋代文獻整理研究的重要工程,惠益學界,厥功至偉。但因作家作品數量極大,相關文獻浩繁,疏漏在所難免,學界已發表出版了不少輯佚、補正及辨誤等成果。筆者也因研究所及,先後撰寫了系列相關論文。③近因課題研究閲覽大量宋元筆記方志等文獻,又陸續發現一些值得輯補考證的宋代作家及詩文作品。兹依所見予以輯考,以供研究者參考。 一、關中驛舍壁間無名氏詩一首 宋代趙溍《養疴漫筆》記載,“靖康之變,中原爲北地,當時高人勝士亡没者不少。紹興庚申辛酉,河南關陝暫復,有自關中驛舍壁間得詩二絶”。其第一首云: 鼙鼓轟轟聲徹天,中原廬井半蕭然。鶯花不管興亡事,妝點春光似去年。 第二首云: 渭平沙淺雁來棲,渭漲沙移雁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明月淚霑衣。④ 按,上録第一首詩作,《全宋詩》、《全宋詩訂補》⑤皆未收録。第二首詩作,《全宋詩》卷一七七收於黄孝先名下,題爲《詩一首》,並有序,詩歌字句略有差别,詩爲:“天寒霜落雁來棲,歲晚川空雁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明月我霑衣。”序云:“余嘗守官咸陽。縣廨之後臨渭河,汀嶼中,連歲秋有孤雁來棲於葭葦中,今歲冬深不復至矣。或已在繒弋,或去而之他,皆不可知也。感而爲詩題亭壁。”又據《全宋詩》小傳,黄孝先字子思,浦城(今屬福建)人,仁宗天聖二年(1024)進士,爲廣州尉,改宿州尉,改宿州司理,以善治獄遷大理寺丞,知咸陽縣,移綿竹,終太常博士、通判石州。所著詩二十卷,蘇軾爲之序,已佚,《全宋詩》録詩三首。上録見於《全宋詩》的詩一首,出自宋人趙令畤《侯鯖録》。⑥仔細辨析關中驛舍壁間所得二絶句的詩韻、内容及情感意藴,可以發現,二詩其實並無内在聯係,顯然非同題之作,也非出自一人之手,而只是南宋紹興中關陝暫時恢復之際有人自關中一併抄録在一起而已。據《侯鯖録》及《全宋詩》,第二首詩是北宋仁宗朝人黄孝先抒寫遊宦之際的人生感傷。而就第一首詩的内容來看,則可判斷其創作時間是在距仁宗朝約百年之後的宋室南渡之際,乃是抒寫金滅北宋、中原板蕩的時代變故。因此儘管抄録在一起的二首絶句中,第二首可以確定爲黄孝先所作,但第一首卻絶非出自黄孝先之手,而當是宋室南渡之際的詩作無疑,至於其作者姓名,由於缺乏記載,暫時還難以考知。綜上,上録第一首詩作,係《全宋詩》未收的佚詩,可予輯補。 二、京口旅邸中無名氏《雞鳴》詩一首 宋代周遵道《豹隱紀談》記載,“自來縣尉下鄉擾人,雖監司郡守亦不能禁止,邇來尤甚。京口旅邸中有戲效古風雅之體,作《雞鳴》詩。詩曰《雞鳴》,刺縣尉下鄉也”,“《雞鳴》三章,章四句”。其詩云: 雞鳴喈喈,鴨鳴呷呷。縣尉下鄉,有獻則納。 雞鳴於塒,鴨鳴于池。縣尉下鄉,靡有孑遺。 雞既鳴矣,鴨既羹矣。鑼皷鳴矣,縣尉行矣。⑦ 按,上録京口旅邸中無名氏《雞鳴》詩,《全宋詩》、《全宋詩訂補》皆未見收録。據周遵道《豹隱紀談》記載,此詩無疑是宋人所作,内容乃是諷刺宋代縣尉下鄉擾民。在宋代,國家規定縣級官吏若非公事,不許私自下鄉,以防瀆職和擾民。如太祖乾德二年(964)正月詔“應諸縣令、尉,無事不得下鄉……如有不因公事,輒下鄉村,及追領人户,節級衙參,並勘罪以聞”⑧。南宋《慶元條法事類》也規定“諸縣令佐非公事不得下鄉”⑨。可見,上録無名氏《雞鳴》詩,深刻反映了宋代社會現實,乃是一首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不僅可補《全宋詩》之闕,亦可詩史互證,具有特定文獻史料價值。 三、李少雲《病中作梅花詩》一首、另一句 宋代許顗《許彦周詩話》記載,“有李氏女者,字少雲。本士族,嘗適人,夫死無子,棄家着道士服,往來江淮間。僕頃年見之金陵”。並録其《病中作梅花詩》一首: 素豔明寒雪,清香任曉風。可憐渾似我,零落此山中。 另記其詩一句: 幾多柳絮風飜雪,無數桃花水浸霞。⑩ 按,上録李少雲《病中作梅花詩》一首及詩一句,《全宋詩》、《全宋詩訂補》皆未收録。據《許彦周詩話》,許顗曾親見李少雲,並與之有交往,因此其記載自然可信,所録李少雲詩一首及一句也可資補遺。 四、林希逸詩一首 宋代林希逸于度宗咸淳三年(1267)撰《行在仰山孚惠二王廟記》,記載孝宗淳熙年間臨安馬軍司李統領運木于西江,途中遇風潮,因此拜仰山二龍王,得神護佑,歸臨安後遂爲仰山二龍王建行廟於軍營。林希逸有感于二王顯異遍佈東南,“一念忠君,神人同也”,故爲之撰祀神詩一首: 王初化兮,二龍其始事矣,亦以語諸篙翁。食于袁數百載矣耽耽其宫,蘭蒸桂奠矣祀彌恭。湖南北兮江西東,瓜華之奉兮與物同。王知我宋萬斯年兮,心乎朝宗。宜帝所之入衛兮,實冥冥之孤忠。欲寄靈於一將兮,乃變幻江濤之中。今祠宇日辟兮象貌崇,若時雨兮收融風,掃疫癘兮慶屢豐。福吾民矣鞏吾國,期世世以祀兮,報王德於無窮。(11) 按,林希逸(1193—?)字肅翁,號鬳齋,又號竹溪,福清(今屬福建)人,理宗端平二年(1235)進士,淳祐六年(1246)召爲秘書省正字,遷樞密院編修官,尋出知饒州,景定中官至中書舍人,著有《竹溪十一稿》九十卷,已佚,今存《竹溪十一稿詩選》一卷、《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三十卷。《全宋詩》録其詩九卷,新輯集外詩附於卷末。(12)上録林希逸爲仰山孚惠二龍王所撰祀神詩一首,《全宋詩》、《全宋詩訂補》皆未收録,故輯録於此。 五、李兑詩一首 宋代沈作賓修,施宿等纂《嘉泰會稽志》記載,會稽有裘氏,自齊梁以來七百餘年無異爨,子弟或爲士,或爲農,鄉黨稱其行,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州縣奏旌表其門閭,是時裘氏義居已十九世,闔門三百口,至南宋寧宗嘉泰初,又五六世,蓋二十四五世以來,依然如故聚族,傳爲美談。並記載,北宋仁宗至和中,待制李兑爲之題詩云: 夫何于會稽,卓然有裘氏。同居六百年,相聚三千指。昔賢欽義方,列奏聞天子。詔恩表門閭,光華映閭里。(13) 按,李兑(995?—1070?)字子西,許州臨潁(今屬河南)人,進士,仁宗朝爲殿中侍御史,改同知諫院,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歷知杭、越,英宗時爲集賢院學士,判西京御史臺,以工部尚書致仕,約神宗熙寧三年卒,年七十六,《宋史》卷三三三有傳。《全宋詩》卷一七八僅收録李兑六斷句,未見收録此詩。(14)不過,檢《全宋詩》卷一四二八,李光名下收録此詩,題作《裘氏義門》,注明出自《兩宋名賢小集》卷一五八《椒亭小集》。(15)李光(1078-1159)字泰發,越州上虞人,徽宗崇寧五年(1106)進士,調知開化縣,移知常熟縣,欽宗即位,擢右司諫,遷侍御史,高宗建炎元年(1127)擢秘書少監,歷知臨安府、知婺州、吏部侍郎、淮西招撫使、知建康府、知湖州等,拜參知政事,有文集三十卷,已佚,《兩宋名賢小集》卷一五八存《椒亭小集》一卷,清四庫館臣據《永樂大典》輯有《莊簡集》十八卷,《宋史》卷三六三有傳。《全宋詩》收録李光詩,即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莊簡集》爲底本,參校《椒亭小集》等,新輯集外詩編爲第八卷。上述《全宋詩》收于李光名下的《裘氏義門》詩,就在新輯集外詩中。 據《嘉泰會稽志》記載,上録題爲《裘氏義門》的詩作,實當爲北宋李兑所作。李兑作此詩,係出於讚頌裘氏義門事蹟,時間明確,事由確鑿。《嘉泰會稽志》在收録此詩之後進一步記載,“其後又有族老季光,以所藏今昔留題詩刻石,傅惇作序”(16)。可見李兑此詩被李氏家族中一位稱之爲“季光”的族老刻石流傳,這位“季光”或者就是李光,或者並非李光,但因“季”與“李”字體相近而被誤作李光,後世遂將此詩誤收于李光名下。 六、劉次高詩一首 宋代胡榘修,方萬里、羅浚纂《寶慶四明志》記載,四明西南四十里有蓬島山,重岡復嶺,繚繞綿亘,“肥厚雄壯,不露峰角,兀然獨冠諸山。北爲安岩之翠峰,南爲石樓之赤巖,過松木嶺,入於天台……臨其巔,俯視數百里之外,滄海微茫,煙林縈帶,城邑聚落,了然在目。崇寧間,有尼結廬於其肩,號曰‘師姑坪’。今其故階遺井、瓦礫磚石猶存”。繼這段文字之後,又記載閬風劉次高登臨遊山詩一首: 軋軋肩輿過翠微,路經蓬島鎖煙霏。雨從半嶺岩窩出,雲在行人腳下飛。(17) 按,筆者檢閲《全宋詩》及《全宋詩訂補》,均未見收録劉次高其人及此詩,可輯補。 七、李丑父詩一首 元代脱因修,俞希魯纂《至順鎮江志》記載,鎮江竪士山東有天妃廟,舊在潮閘之西,宋理宗淳祐間貢士翁戴翼遷創於此,太學博士李丑父爲之撰記,記文之末“既書歲月,又系以詩,俾歌以侑食焉”。其詩曰: 峨峨兮新宫,神宴娱兮婆娑。翠旗兮蒙茸,弭節兮山之阿。渺湄洲兮閩中,食兹土兮維何?於赫兮威風,記兩淮兮戰多。紫金山兮摧戎,花靨陣兮揮戈。合肥城兮釋攻,若有神兮撝訶。驅厲鬼兮先峰,殿南嶽兮群魔。駭雲閑兮幟紅,非風鶴兮傳訛。望海門兮浮空,想護使兮韓倭。洶百兮魚龍,獨安流兮靡他。偭新廟兮淮東,瓊花時兮來過。配富媪兮民庸,江與淮兮無波。彼佐禹兮巫峰,眎功載兮同科。繄菊英兮蘭崇,薦芳馨兮九歌。繪長鯨兮來供,鼓犀渚兮鳴鼉。舞漢女兮豐容,邀游湘兮英娥。食兹上兮以功,羌如山兮如河。嘉士女兮敬恭,消疵癘兮淳和。俾邊民兮樂農,有年書兮麥禾。閲長江兮無窮,與牲碑兮不磨。(18) 按,李丑父(1194-1267)初名鋼,字汝礪,更字艮翁,號亭山,莆田(今屬福建)人,理宗端平二年(1235)進士,次年調邵武軍司户,歷通判福州、建寧府,除太學博士兼沂王府教授,開慶元年(1259)爲太府寺丞,累遷著作郎,權禮部郎官,景定五年(1264)出爲湖南提舉,咸淳三年卒,年七十四,有《亭山集》,已佚。《全宋詩》卷三一二八録其詩一首、一斷句。(19)檢《全宋文》卷七七六〇,録其《天妃廟記》。(20)但上録李丑父詩,《全宋詩》、《全宋詩訂補》皆未收録,可輯佚。 八、蔣重珍生卒年及《全宋文》佚文二篇 蔣重珍字良貴,號實齋先生,常州無錫(今江蘇無錫)人,宋寧宗嘉定十六年(1223)進士第一,擢承事郎,除僉書昭慶軍,改僉書奉國軍,理宗朝遷秘書省正字、校書郎,添差通判鎮江府,授寶章閣,兼崇政殿説書,遷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以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守刑部侍郎致仕,卒謚“忠文”,《宋史》有傳。(21)蔣重珍以狀元及第,並以直言正論爲世所重,乃寧宗、理宗時期名臣,詩文亦有記載流傳,今《全宋詩》録其詩6首。(22)不過就相關文獻及研究資料來看,關於蔣重珍生平及其詩文,還存在二個重要問題:其一,《宋史》本傳、《宋人傳記資料索引》(23)、《全宋詩》小傳等均不詳其生卒年。《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補編》稱“蔣重珍(1183-1236),端平三年十一月卒,年五十四”(24)。然又有學者認爲蔣重珍生於淳熙十六年(1189)。(25)有關蔣重珍生卒年問題,學界一些文史載籍或語焉不詳,或所載抵牾,還需考證論實。其二,今《全宋文》不録蔣重珍之名,其見於史志記載且非常具有文獻史料價值的二篇文章亦付之闕如。兹就蔣重珍生卒年予以考證,並輯録《全宋文》佚文二篇。 1.蔣重珍生卒年 關於蔣重珍生卒年,《宋史》本傳未載,後世載籍或不明其詳,或存在分歧。今考,蔣重珍卒後,南宋尤焴有《宋故刑部侍郎蔣公壙志》云:“公諱重珍,字良貴,常州無錫人……公生於淳熙癸卯三月己巳,殁于端平丙申十一月乙丑。次年二月壬寅,葬于當縣謝堰先塋之右”(26)。這當是有關蔣重珍生卒年最早的直接記載。尤焴亦爲無錫人,乃著名南宋中興詩人尤袤之孫,尤概之子。尤袤爲高宗紹興十八年(1148)進士,尤概爲孝宗淳熙二年(1175)進士,尤焴爲寧宗嘉定元年(1208)進士。(27)尤氏祖孫三世相繼,並登科第,乃無錫望族。特别是尤袤,爲程頤三傳弟子,理學精深,而蔣重珍“少從尤袤學”(28)。可見,蔣重珍不僅與尤焴爲同鄉,而且與尤焴父祖深有學術淵源。因此,尤焴爲蔣重珍撰寫壙志乃在情理之中,其可信度也非常高,無疑是記載蔣重珍生平的第一手資料。壙志明確記載了蔣重珍的生卒年,而且月日、墓葬俱明,據此知蔣重珍生於孝宗淳熙十年(1183)三月四日,卒于理宗端平三年(1236)十一月十二日,享年五十四歲。 對尤焴所記蔣重珍生卒年,還可通過其他史料來進行印證。經考,蔣重珍母顧夫人卒後,魏了翁有《顧夫人墓誌銘》稱“嘉定十有六年夏五月戊申,蔣重珍舉進士第一”,又載蔣重珍自述云:“重珍年四十餘,始獲齒名于進士籍。”(29)按,蔣重珍嘉定十六年進士登第,舉爲狀元,時“年四十餘”,若就此前推四十年,則蔣重珍生年恰爲淳熙十年,與尤焴所撰壙志的記載完全吻合。魏了翁在墓誌銘中又記蔣重珍自述:“惟昔試禮部,嘗以文字受知於先生(魏了翁),由是幸有録於門,心授神予,非他人面交勢合比也。”(30)《宋元學案》魏了翁鶴山學案也載《忠文蔣先生重珍》之目,稱蔣重珍“本鶴山校試禮部門下士也,其後遂問業”(31)。可見蔣重珍試禮部,受魏了翁知遇,後登其門就學,二人關係非同一般,元修《無錫志》即稱蔣重珍“與魏了翁、真德秀深相友愛”(32)。因此,魏了翁《顧夫人墓誌銘》的記述值得相信,據此也可斷蔣重珍生於淳熙十年不誤。 2.蔣重珍《全宋文》佚文二篇 《無錫志》稱蔣重珍“幼穎悟,讀書一覽輒記。嘉定十六年魁進士,擢承事郎,累遷至僉書奉國軍。召除秘書正字,入對,上七箴、三疏,奏語剴切,忤丞相史彌遠意,遂謁告還家。端平初,上勵精更化,召爲秘書郎,累遷至集英修撰,皆不就。嘗築一梅堂、萬竹亭,聚書自娱,天下高之”(33)。可見蔣重珍一生,在政治上積極建言,致君行道,在生活中也堪稱雅士,在家鄉無錫先後築一梅堂、萬竹亭,聚書自娱,其勵志進取與淡泊守志的出處進退之節爲天下所重。 蔣重珍築一梅堂、萬竹亭後,均曾撰有記文,分别題爲《一梅堂記》、《萬竹亭記》。蔣重珍今無文集傳世,二篇記文幸保存於《無錫志》中,且都有明確署名。然而,這二篇記文都未爲《全宋文》收録。現據《無錫志》標點迻録於下: 一梅堂記 寶慶丁亥,皇上即位之四年也,重珍試吏苕幕,以病易鄞幕,待次歸,治藥石,無宏榻之地,解脱閫中簪珥,得敗屋一區,掃灑扶持而居之。癸巳春,奉祠杜門,痼疾弗瘳,目昏耳聵,老態具見,乃於室之東南隅,撤舊而新,爲堂一間,兩挾置藥爐丹灶、蒲團紙帳於其中,將靜坐養疴,以苟旦暮之命。屋卑地狹,月餘落成。故舊有誚予者曰:“子其掃除一室之小者,丈夫歟?吾視子幼孤,繩樞甕牖,所居不能容膝,遷徙彷徨,將母而行,傍人籬落,竊一椽之芘,輒以爲幸。今破屋視昔已過分矣,而奚以堂爲?”余竦然而悲曰:“是予之過也。雖然,吾豈以堂爲樂哉?獨念吾家凋弊五十餘年,生意幾絶,其不肖誤蒙寧廟親擢,未幾,叨被皇上召對,名列班簿,幺微此身,病廢退休,足矣足矣。雖然,此身父母之遺體也,可不敬乎?築斯室也,敬斯體也,乃所以報親也。不然,則安宅何在,廣居何在,而顧區區於此堂哉?自斯堂而成,而可以求師也,凡齒德俱尊者,孝可及人者,義理精熟者,克忠克孝者,博通經史者,深識時務者,吾於此下一風而問焉,則身雖病而心不病矣。自斯堂而成,而可以合族也,凡姿禀可教者,好禮知恥者,遷善遠罪者,小廉曲謹者,貴不簡傲者,貧不卑屈者,文藝自將者,多識事物者,吾於此因材而篤焉,則身雖病而家不病矣。自斯堂而成,而可取友也,凡能修而通者,能言而踐者,卓犖之重者,淳靜而立者,已知大體者,能勤小物者,虚心無我者,善如己出者,惡如無隱者,相觀爲善者,吾於此久交而敬焉,則身雖病而道不病矣。夫心不病則不敝,家不病則不替,道不病則不孤,貧無憾也,賤無憾也,存順事而没寧。嗚呼,此豈忘其親而事身哉?”堂之前,有梅一株,清圓茂密,因以名堂,無所取義,示不改其舊也。(34) 萬竹亭記 余已記一梅堂,復爲後圃,開林爲徑,縛亭東偏,扁曰萬竹亭。有池,池上有梅。梅之外,琅玕森然,向亭而立,如衆賢盍簪,挺挺其清也;如三軍成列,懔懔其嚴也。風清月明,發揮高爽,雨陰霧暗,韜晦蒙密,景物常變,皆啓人意。余時命蒼頭,扶掖病足,自徑而亭焉,非日涉成趣之謂也,非起居適安之謂也,其所感慨深矣。余生於淳熙末年,時和歲豐,田里安樂,先君與諸父實居鳳山,貧不聊生,故廬已屬有力者。然茅齋方池,飽足幽趣,前植古梅,後列修竹,藜杖野服,日引兒姪,從容其間。故余平時清夢,皆此時事,嘗刻之家傳,以寫罔極之思矣。今是亭之營,本非求合,而梅老竹茂,渾然天成,時異事殊,心感情愴,見先訓遺風,使余一刻之不能忘也。是余之一遊一息,洞洞屬屬然如將見之也,可不謹哉。雖然,園林之樂一也,而其所以樂此者,則有間焉。蓋先君諸公之樂此也,安於貧,而予之樂此也,厄於病,貧者循其理分之當然,病者出於形體之偶然,律之以原憲之言,則大有愧矣。先儒亦曰,人多言安於貧賤,皆是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余之病廢,抑近是歟。書置壁間,因以自警。(35) 按,《無錫志》嘗記蔣重珍築一梅堂、萬竹亭之事,而上録《一梅堂記》、《萬竹亭記》二篇記文可與其事互相印證。據二篇記文,一梅堂、萬竹亭乃是蔣重珍于理宗紹定六年(1233)奉祠歸里後所建。這二篇記文記述了蔣重珍在理宗朝的重要仕履、生活經歷和思想心態,成爲了解蔣重珍生平事蹟、思想個性及文學創作的重要文獻,甚至可以窺見理宗朝士大夫的文風之變。元代陸文圭即有《跋蔣良貴梅堂竹亭二記》稱:“梅堂、竹亭二記,與鶴山書院拱極堂、矩堂相表裏,皆端、嘉一時崇尚理學之文,前乎曾、蘇,無是也,又前乎韓、柳,亦無是也,非無是文也,無是識也。嗚呼美哉!文靖之辭精贍,文忠之辭明暢,忠文之辭簡質,一以世教民彝爲主,藹然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又豈可以文論哉?”(36)陸文圭跋蔣重珍梅堂、竹亭二記,不僅可從文獻層面進一步證實蔣重珍二篇記文的可靠性,還可從文論角度看到後世對其記文崇尚理學、文辭簡質的風格的體認,道出了其記文的文學價值與時代特色。 注释: ①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9年。 ②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③如拙文《洪邁〈野處類稿〉辨僞》(《文獻》,2006年第3期)、《宋孝宗佚詩二首考録》(《社科縱横》,2008年第11期)、《〈全宋詩〉虞儔佚詩二首考録》(《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全宋文〉張鎡殘文一篇補正》(《文獻》,2009年第1期)、《史浩詩輯佚四首》(《江海學刊》,2012年第3期)、《王欽若詩輯補一首》(《江海學刊》,2012年第5期)、《吴芾、王十朋詩輯佚二首》(《江海學刊》,2013年第3期)等。 ④趙溍:《養疴漫筆》,陶宗儀等編:《説郛三種》卷四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174頁。 ⑤陳新等補正:《全宋詩訂補》,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 ⑥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3册,第2031頁。 ⑦周遵道:《豹隱紀談》,陶宗儀等編:《説郛三種》卷二〇,第984頁。 ⑧宋太祖:《禁令簿尉無事下鄉詔》,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1册,第59頁。 ⑨《慶元條法事類》卷四,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第24頁。 ⑩許顗:《許彦周詩話》,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第3頁。 (11)林希逸:《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卷一〇,《宋集珍本叢刊》第83册,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第465頁。 (12)參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59册,第37228頁。 (13)沈作賓修,施宿等纂:《嘉泰會稽志》卷一三,《宋元方志叢刊》第7册,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6951-6952頁。 (14)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3册,第2048頁。 (15)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25册,第16465頁。 (16)沈作賓修,施宿等纂:《嘉泰會稽志》卷一三,《宋元方志叢刊》第7册,第6952頁。 (17)胡榘修,方萬里、羅浚纂:《寶慶四明志》卷一四,《宋元方志叢刊》第5册,第5182頁。 (18)脱因修,俞希魯纂:《至順鎮江志》卷八,《宋元方志叢刊》第3册,第2730頁。 (19)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59册,第37386頁。 (20)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336册,第398-399頁。 (21)脱脱等:《宋史》卷四一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2352-12354頁。 (22)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59册,第37379-37380頁。 (23)昌彼得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第5册,臺北:鼎文書局,1988年,第3778頁。 (24)李國玲編纂:《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補編》第3册,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774頁。 (25)戈春源:《弘治〈無錫縣志·蔣重珍傳〉糾誤》,《史學月刊》,1997年第2期。 (26)佚名纂修:《無錫志》卷四下,《宋元方志叢刊》第三册,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2298-2299頁。 (27)佚名纂修:《無錫志》卷三下,《宋元方志叢刊》第三册,第2240頁。 (28)趙弘恩等監修,黄之雋等編纂:《江南通志》卷一四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11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45頁。 (29)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三,《四部叢刊初編》本。 (30)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三。 (31)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卷八〇,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685頁。 (32)佚名纂修:《無錫志》卷三上,《宋元方志叢刊》第三册,第2231頁。 (33)佚名纂修:《無錫志》卷三上,《宋元方志叢刊》第3册,第2231頁。 (34)佚名纂修:《無錫志》卷四中,《宋元方志叢刊》第3册,第2294-2295頁。 (35)佚名纂修:《無錫志》卷四中,《宋元方志叢刊》第3册,第2295頁。 (36)陸文圭:《牆東類稿》卷一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4册,第6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