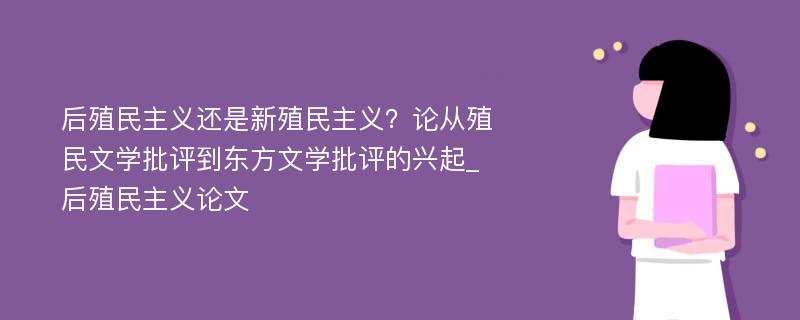
后殖民主义还是新殖民主义?——兼论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到东方主义的崛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殖民主义论文,新殖民主义论文,文学批评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下西方学界,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已经开始退出以怀疑表现出解构式激进的主流理论,走向了寂落;但西方理论界并没有在沉默中保持自己以往的学术尊严,另一脉具有前卫性的学术思潮也以解构式的批判从边缘逼向中心,使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西方学术界充斥着躁动,这就是以东方主义为思想核心的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思潮的崛起。
可以说,后殖民主义这个概念及在这一脉思潮下所操用的一套话语,在东方大陆理论界并不陌生。近几年来,当后殖民主义话语被有限地引渡到东方大陆之后,国内学术界已在一知半解中以某种变体的形式操用着这个概念及某些话语,并指向了当下大陆的文化及文学批评。那么,西方学者又究竟怎样评价它的崛起及其理论品质呢?我们从英国学者B.M.-吉尔伯特(Bart Moore-Gilbert)在《后殖民批评》(PostcolonialCriticism)一书《导论》中对后殖民主义思潮的描述中可以略知一二,即后殖民主义是在当下西方学术界正在膨胀的一脉学术思潮,并且其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后殖民主义及其肇事者的身份有着重要的文化性、政治性和地理意义;关键的启悟更在于,当东方大陆学者不自觉地跌入霍米·巴巴对原创后殖民理论进行模拟性(mimicry)的操用中,以变体的后殖民理论话语进行文化及文学批评时,西方学者却以后殖民主义的跨学科性与多元性,而声称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最终把后殖民主义交给了适应于任何一方文化语境下的自我定义(self-definition)中。
其实,我们从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和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一系列读本中,也很难找出这三位后殖民理论原创者关于这一概念的确切定义。但是由于这一理论在东西方文化及文学批评空间呈现出当下性,且有着重要的操用价值,所以我们应该对这一思潮崛起的理论背景投入准确的读解,以便恰如其分地选择以怎样的文化身份参预东方汉语语境下的后殖民理论批评,或走向西方,在拼音语境下与西方学者或东方主义研究者就后殖民问题进行对话。在东方大陆关于后殖民理论为数不多的读本中,王宁关于这一理论崛起的背景有着翔实的综述:“综观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的理论背景,我们并不难看出这样几个来源:他们从斯本格勒的断言‘西方的衰落’那里获取一些灵感,继续了这种从帝国内部进行的解构;此外他们从德里达那里获取了解构主义的理论与阅读策略,对一些描写殖民地题材的文学作品进行重新阅读和评价,从而对以往既定的经典文学进行重构;他们还从巴赫金那里获取对话诗学,并以音乐中的对位方式在第一世界内部奏起一种不和谐音,从而充当了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少数人’的话语发出者;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批判锋芒则在于从葛兰西那里获取了霸权的概念,从富科那里提取了基于权力和知识的写作,以后殖民地批评家或第三世界批评家的身份对帝国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进行评击。”(注:王宁:《后现代主义之后》,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从上述关于这一理论崛起背景的综述及对于后殖民理论三位原创者文化身份的了解,我们不难看出,从后现代主义到后殖民主义,这两脉理论思潮在文化策略上是延续的,两者都带着德里达解构理论对中心的颠覆性,以一种强烈的批判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对话语——权力进行挑战;所不同的是这两脉理论思潮的肇事主体在文化身份上则是断裂的,也就是说,从后现代主义到后殖民主义虽然都是在西方拼音语境下延伸的主潮理论,但是肇事主体的文化身份及其理论内涵却截然迥异。
后现代主义在本质上是西方本土学者操用解构策略对西方文化传统自身的逻格斯中心主义进行挑战,而后殖民主义的三位肇事者赛义德、斯皮瓦克与巴巴却是来自中东的巴勒斯坦地区和印度,他们的文化身份是地道的东方学者。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都是发生在西方语境下的文化思潮,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肇事主体则以西方的解构策略作为自己从世界文化的边缘——东方,向当下世界文化的中心——西方挑战的武器,把西方文化视为文化全球化的帝国霸权主义。从上述我们不难看出,在东西方文化的对话中,来自于中东的三位原创后殖民主义理论肇事者是秉有一种怎样的野心,从边缘向西方文化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挑战的。
这就是后殖民理论崛起的基本文化背景。(注:按:关于后殖民理论的基本文化品质,请参见王宁著《后现代主义之后》一书的第二编《后殖民主义》,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147页。)
但是问题远非我们所想象的这么简单。倘若我们在这里问:在翻译和介绍中被引渡到东方大陆汉语语境下的后殖民主义批评话语,在文化身份上究竟隶属于西方理论话语还是东方理论话语?这个问题显然被当下中国大陆汉语语境下急切操用后殖民话语指向文化与文学批评的学者们忽视了。毫无疑问,在普泛的意义上,一般东方大陆学者均在思考的缺憾中把后殖民主义默认为纯正的西方理论。关于这样一种误读性默认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在东方大陆所能够读到的原创后殖民理论读本全都是用纯正的英语撰写,是在西方拼音语境下出版的。并且这三位原创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肇事者,目前也都以国际精英学者的身份频繁地活动在欧美学术界,与那些西方学者平起平坐。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中,东方与第三世界被定位在“他者”(other)的文化地位上,这种文化定位旨在申明第一世界发达国家对东方或第三世界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歧视。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三位后殖民理论原创者却潜在地更情愿标明自己的后殖民地“他者”身份而步入西方学术界,以此代表东方或第三世界向西方挑战。其实,在东西方文化频繁对话以及西方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下,“东方”这一“他者”文化身份大有利可图,再加上后殖民理论取道西方被介绍和翻译到大陆后,一切就更加复杂化了。
那么,后殖民话语究竟是西方理论话语还是东方理论话语呢?让我们的思考在一种迂回中来回答这个设问。
我们知道,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原创后殖民理论在西方后现代语境下表现为一种解构式的激进主义,我们说在东西方文化的对话中,“东方”这一“他者”文化身份大有利可图,就在于赛义德等人对西方文化传统的挑战是从边缘逼向中心的,这样一种“他者”的身份突显出少数人边缘性话语的批判性格。注意:在西方后现代怎么都行的多元语境下,这种少数人的边缘性话语往往有着重要意义,也使自己对西文文化的挑战与那些操用解构策略的西方本土后现代主义者区别开来了。其实,西方语境下的本土后现代理论与他性后殖民理论都表现为解构式的激进主义,“两者是一里一外地对西方传统文化进行解构式的夹击”。(注:此观点拙作《后现代性、后殖民性与民族性——在世纪之交,艺术创作与批评应该追录一种比较的视野》,《东方丛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期,第12页。)但是不同于西方本土语境下的后现代主义者,后殖民理论的肇事者从边缘向西方文化中心的挑战,不仅仅是为了鸣响“对帝国主义文化霸权批判”的话语,也更是为了进入西方在主流文化中寻找立足之地,最终企获西方学术界的承认。
我们应该对后殖民主义思潮崛起的背景做一次编年意义上的反思,以便我们知道定位于怎样的文化阿基米德点上来读解、操用这套话语。
毫无疑问,“后殖民主义”这一话语的当下特色正是表征在“后”(post)这一书写符号上,逻辑地讲,后殖民主义思潮崛起的前奏必然是从殖民主义思潮的话语背景那里沿伸过来的。不错,当下西方理论界在编年史的意义上汇总与讨论后殖民思潮时,已在体系和学脉的追踪上,把后殖民主义话语与殖民主义(colonialism)话语维系起来,这正如我们在讨论后现代主义时,不能不反思现代主义。B.M.-吉尔伯特在1997年编撰、出版《后殖民批评》一书时,正是如此把自己的学术视野从殖民主义话语透向对后殖民主义话语的反思,B.M-吉尔伯特在本书的第一章即介绍了早期反殖民急先锋——诗人艾梅·塞萨尔(Aime Cesaire),并集入了他的重要文章《殖民主义话语》(Discourse on Colonialism)。必须提及的是,殖民主义批评话语在理论、政治及意识形态上的铺设、展开,与70年代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成立当下后殖民理论文化身份的“东方”,没有任何地域和政治的关系。我们避开从纯粹军事、政治和经济层面上讨论的殖民主义理论,作为对文化与文学批评的殖民主义话语更主要是在第三世界的另一个地域文化语境下展开的,即被欧洲殖民主义者殖民以久的非洲世界。一如B.M-吉尔伯特所言:“塞萨尔努力要解放的正是这个世界,正是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以及对这个世界与殖民主义的密切关系的理解开拓了他诗人视野,而不是什么‘纯’非洲的景象。但是塞萨尔的诗学是以对殖民主义进行精确分析为基础的,在《殖民主义话语》中最为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殖民主义话语》应被看作后殖民批评的奠基之作。”(注:艾梅·赛萨尔:《殖民主义话语》(Aime Cesaire,Discourseon Colonialism),《后殖民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 longman 1997.London and New York.p.73.)的确,当我们的学术视野在编年的反思追踪上,超越了当下的后殖民主义话语时,我们不难发现,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聚揽于“东方”这一地域概念之下的后殖民理论激情与理论思考,早在殖民主义文化与文学批评者那里储备已尽。可以说,对后殖民理论及其成因的讨论,如果我们不在学理与学脉上追踪到殖民主义理论及艾梅·塞萨尔,这将是最大的遗憾。
需要指出的是,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不同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其更主要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欧洲及其殖民统治者的,维护本土文化的尊严。如果我们在五、六十年代的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与当下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之间给出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殖民主义文化批判更少禀有个人获取的功利性,其的确是在“二战”之后世界两大阵营对立时,左翼阵营政治话语在殖民主义理论肇事者发言中的传声。正是出于这一意识形态的过滤,所以殖民主义理论肇事者的批判性是极为纯真的,也是极有挑战力量的。严格地讲,从事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学者,倘若对殖民主义理论缺乏编年史意义上的细读,那么,他在东方大陆当下的文化批判行动中所投入的后殖民思考,只能是在一种望文生义中完成的误操作。正如B.M-吉尔伯特所言艾梅·塞萨尔的《殖民主义话语》的确应该被看作后殖民批评的奠基之作。
写到这里,我们于此必须纠谬一个正在被当下东方大陆学术传递的误读。大陆学术界在介绍后殖民理论时,总是要提及康拉德(Joseph Conrad)及其《黑暗的心》,似乎康拉德及其《黑暗的心》被当下大陆学术界彻头彻尾地打入了后殖民文学理论讨论的领地中。其实从理论思潮的价值归向上和编年意义上来划分,康拉德及其《黑暗的心》应该首先归属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英国文学批评家E·R·列维斯(E R Leav-is)曾把《黑暗的心》言称为代表英国文学的顶峰之作,而实际上《黑暗的心》在非洲殖民语境下充斥着浓烈的种族主义(racism)情绪。出身在非洲西部尼日利亚的黑人作家及批评家切诺瓦·阿切比(Chinua Ach-ebe)正是就《黑暗的心》的英国文学经典性而给反击。在阿切比看来,康拉德的错误与西方人心中的愿望是紧密维系的,即把非洲看视为欧洲的陪衬物,一个遥远而又似曾相识的对立面,也正是在非洲的参照下,欧洲本身的优越性才能够呈现出来。所以阿切比认为:“康拉德在这部不长的作品中扮演了令人欣慰的神话传播者的角色。”(注:切诺瓦·阿切比:《非洲的一种形象——谈康拉德〈黑暗的心〉中的种族主义》(Chinua Achebe,An Image of Africa:Racism in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后殖民批判》(Postcolonial Criticism longman 1997.London and New york.p.112.)赛义德在他的论述中始终重复的一个观点“东方神话是在西方人的视界中虚构的”,其实在殖民主义文化及文学批评理论中已是司空见惯的潜在表述了。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讨论后殖民理论时可以谈康拉德及其《黑暗的心》,但在思潮的渊源上则要把其追溯到殖民主义批评话语那里去,并且虽然殖民主义文学批评不是解构主义的,但其仍充溢着批判的人格力量。
在《后现代主义之后》一书,王宁曾把欧美语境下的原创后殖民话语在东方大陆下的操用称之为“变体”,西方后殖民理论的东方大陆变体最多的是指向张艺谋及陈凯歌反映华夏旧日风情的电影作品。就我看来,有趣的是张艺谋及陈凯歌在西方电影节上大获成功的创作意识,似乎是步康拉德《黑暗的心》在创作意识上成功的后尘。在现代文化或后现代文化遮蔽的文坛上,越是种族主义的描写,越有可能成功。大概文明人不仅需要猎奇野蛮,也更依赖于第三世界的野蛮、落后和贫困来平衡西方文明的不稳定性。如果我们从文学艺术这一透镜,去看视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的全球文化蜕变,当欧美文化从现代向后现代高科技工业文明摆渡时,而第三世界文化却在史前文明与现代、后现代文明之间拉开一种审美反差的张力,拉丁美洲大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非洲大陆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亚洲大陆张艺谋的《红高粱》及当代文学创作留恋旧日风情的作品,在一个共性上,这些作品均力图把其所涉猎的题材置放在史前的审美意识及心理结构中转换为一种神话与梦幻。现代或后现代语境下的史前(prehistory)审美意识是殖民主义文学与后殖民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色,但是就殖民主义学批判与后殖民主义文学批判来看,这种史前的审美意识实际上是把荒蛮与丑陋展览给现代与后现代文明人来猎奇。阿切比在批判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时,曾给出这样一句表达:“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持续多年的观点助长并且还将助长非洲人非人化(dehumanization)的做法。一部宣扬这种非人化的小说,一部把人类的一个种族非人格化(depersonalize)的小说,能被称之为伟大的艺术作品吗?(注:切诺瓦·阿切比:《非洲的一种形象——谈康拉德〈黑暗的心〉中的种族主义》(Chinua Achebe,An Image of Africa:Racism in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后殖民批判》(Postcolonial Criticism longman 1997.London and New york.p.120.)的确如此,如果我们从现代或后现代文明的层面来划归或界定人的本质,殖民主义文学艺术与后殖民主义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取向,就是要逼使处在落后向文明过渡的第三世界芸芸众生在生存上再度回到野蛮去,以自己的非人化及非人格化与欧美文明人共享在这个地球生存的权力。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理解了阿切比对康拉德激烈的批判:“那个黑人向白人主子争取自己的权力几乎是无法容忍的。正是这种对权力和呼唤吓坏了康拉德,同时,也正是这一点吸引了他:‘他们也有人性——像你#
样有人性……丑陋。’”(注:切诺瓦·阿切比:《非洲的一种形象——谈康拉德〈黑暗的心〉中的种族主义》(ChinuaAchebe,An Image of Africa:Racism in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后殖民批判》(Postcolonial Criticism longman 1997.Londonand New york.p.120.)当然,《黑暗的心》其语言是极为优美的,意境是极其幽深的,成为英国文学的经典之作;无独有偶,张艺谋和陈凯歌之相应作品的电影语言也是极为优美,意境也是极其幽深的,也成为东方大陆现代电影史的经典之作。
这就是殖民主义文学艺术与后殖民主义文学艺术之间的血脉维系,把史前的荒蛮浸润在现代语言的优美之中,远古与现代就是这样遭遇了。(注:按:本句表述中的“现代”,不是指称界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两种思潮阶段标志的“现代”,而是统称“当下”的普泛概念。)
让我们把思路转向东方主义这一概念上来。殖民主义文化批判或殖民主义文学批评主要是在非洲大陆鸣响的。多少年来,黑人为了抹去欧美文化景观下种族歧视的阴影,曾投入了不懈的努力。这一努力所产生的效应足以启示第三世界东方的某些精英学者寻找怎样通向西方的途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赛义德就是这样蓄意推出了《东方主义》,且大大削弱了国际学术界对非洲殖民主义文化及文学艺术批评的关注,而把西方文化对自身反省的视点从非洲移开,聚焦于东方亚洲的中东地区。说的准确些,赛义德最初利用、亮出自己的东方学者身份,从边缘向西方中心挺进时,他所操用频度最高的话语是“东方主义”,而不是“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一书推出后,围绕着“东方主义”这一概念,的确在欧美语境下引发了大量的争论和使用,以至于赛义德不得不撰写《东方主义的反思》(Orientalism Reconsidered)一文就“东方主义”的滥用给予解释:“我首先应该就几个方面做出申明。第一,除了解答与我的书有关的问题之外,涉及到我的书,我将尽量少用‘东方主义’这个字眼……。第二,我不想使‘东方主义’这一字眼被认为处在一种自由无度的滥用中,并且这种滥用在当下是由我来承受,当然我对当下的状态还是很感激的。(注:爱德华·赛义德:《东方主义的反思》(Edward W.Said,Orientalism Reconsidered),《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 Criticism longman 1997.London and New york.p.127.)从另一个侧面看视,赛义德在骨子里对“东方主义”这一概念的“滥用”是极为自鸣得意的。对一位学者来说,他穷尽一生的思考能够推出一个概念被学术界广泛地操用或批判,这无疑昭示着他的幸运及成功。不是吗,此刻,赛义德正是假东方主义原创话语的提出者身份,而稳坐美国著名大学的教席。不同于已逝去的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中心在非洲,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策源中心而是在东方,其实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这里还潜在着第三世界内部关于批判话语权力的争夺和转移。
不同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是对非洲本土文化尊严的维护,赛义德为首的东方主义在西方后现代语境下表现为激进主义,许多迹象表明赛义德等高扬东方主义的大旗在客观上是为了维护巴勒斯坦地区及印度本土文化的尊严,在主观上却是为了自己从边缘进入西方文化的主流。值得关注的是,西方文化越是在世界上呈现出国际霸权的趋势,少数人那种代表第三世界文化的身份越是秉有可利用的价值。西方的民主往往对来自于少数人刺耳的尖叫声充满了兴趣,这一点不同于东方大陆的儒家文化。那么让我们来看视一下西方学者对《东方主义》和《东方主义》之后的赛义德是怎样进行评判的:“爱德华·赛义德对《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及前期关于《东方主义》的反馈性批评做了一系列重要的反思(另外对后来在1995年新出版的《东方主义》一书也奠定了的基础)。虽然赛义德在本文第二段所提到的那些批评者和很快就消声匿迹了,但从总体来看,赛义德认可了关于这本书的许多主要争论。像以往一样,赛义德仍然坚持东方主义的三个方面本质:一坚持西方知识和西方知识以意志与权力(will-to-power)控制世界其他地区这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注:按:编撰者在此句的表述中呈现出一种后殖民主义倾向,他把被西方知识的意志与权力所控制的地区称之为世界的“其余”(therest of the world),言下之意,西方是这个世界的主体,只有西方才能够称之为“世界”。),二坚持殖民主义话语(Colonial discourse)分析的本质必然秉有多学科的交叉性,三坚持东方主义的早期各种传统对当下中东政治有着持续性影响。这些争论在许多方面对当代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各种关系给予了实质性讨论,这使人想到《东方主义》是由《巴勒斯坦问题》(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及《论伊斯兰教》(Cov-ering Islam)构成的三部曲其中的一个基本部分。”(注:此段表述见于B.M.-吉尔伯特在《后殖民批评》一书中为赛义德《东方主义的反思》一文所写的评论,见于《后殖民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 lon-gman 1997.London and New york.p.126.)从这段表述中不难看出,赛义德在举倡东方主义时,即是从殖民主义批判话语那里承借了多学科的交叉性及其批判精神。所不同的是,东方主义这个在西方语境下秉有特殊地域色彩的话语成为赛义德步入西方主流社会的敲门砖。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大陆当下的后殖民理论传吵仅侈谈“后殖民主义”而不谈“东方主义”,这无疑是因为缺少对赛义德原典的阅读所导致的缺憾。赛义德的《东
方主义》正是从殖民主义开始起论的。
《东方主义》出笼后,用赛义德的话说,他遭遇了东西方学人大量的评论,甚至是敌意的辱骂,为此赛义德撰写了《东方主义的反思》这篇具有历史界标性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也表明了赛义德的思想在方法论与政治这两个层面上的重要发展,也为赛义德在《东方主义》和后来的研究《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之间时时呈现出差异性铺设了思考的路径。无疑,赛义德用地道的英语撰写的《东方主义》在西方语境下的推出,为后殖民理论的崛起而取代于后现代主义的先锋性铺设了背景。那么,《东方主义》的讨论究竟关涉怎样的内涵呢?我们不妨来细读一下赛义德在《东方主义的反思》中自己关于东方主义这一概念内涵讨论的总结:“作为思想与专业知识的一个部类,当然东方主义关涉几个交叉的领域:第一,关涉在欧洲与亚洲之间正在变化的历史与文化关系,即一种有着四千年古老历史的关系;第二,关涉西方学人把各种东方文化与传统研究作为一门专项的学科,这门学科早在十九世纪初叶就开始了;第三,关涉在意识形态方面,对称之为东方世界之当下某个具有重要性及政治性地区的各种猜想、印象和幻想。东方主义在这三个方面呈现出的相对共同标准是区分西方(Occident)与东方(Orient)的界线,我曾经申明东方这一概念本质的实际内涵比它作为人为概念的实际内涵要小得多,我曾把它称之为想象的地理。然而,这既不是说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界限是不可改变的,也不是说东方是一个简单的虚构,确切地说如同维柯(Vico)称之为多民族世界理论的几个方面,东方和西方是由人类制造出的各种事实。这个事实必须作为构成社会整体的各种成分来研究,而不是作为神学的或自然的世界来研究。因为作为社会的世界包括正在从事研究的人或主体,同时也包括正在被研究的客体或领域,把这两个方面同时涵容于任何关于东方主义的思考中是非常必要的。显然,从一个方面来讲,如果没有东方主义也就没有这些东方研究学者(Orientalists),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也就没有这些东方人(Orientals)。”(注:按:在赛义德此篇文章或关于他的后殖理论语境下,"Orientals"也可以翻译为“亚洲人”)从赛义德的综述中,我们应该收获一个启示:西方学人讨论后殖主义与东方学人讨论后殖民主义,应该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心理。这一点是非常微妙的。赛义德对后殖民主义文化进行批判,更多的是启用“东方主义”这一概念,而不是直截了当地使用“后殖民主义”。当然这里有一种地域文化感情的倾向性。(注:按:需#
指明的是,赛义德并非是在一个普泛的意义上认同所有地区、国家、民族及其思潮流派对“东方主义”这一概念给出的定义,他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把“日耳曼东方主义”(German Orien-talism)与自己设定的“东方主义”做了本质上的区别,申明他是拒斥日耳曼东方主义的,并认为所有对他的《东方主义》一书进行批评的学人都没有回答他之所以持这一观点的任何原因。从这一点我们应该注意,不能对“东方主义”仅有一种理解,那怕是赛义德的理解,也就是说,汉语语境下的中国学者对“东方主义”这一概念也应该可以给出自己的意义界定。)
关键问题在于,大陆学界的批评者在进入后殖民理论语境中后,是不是有着像赛义德那样的强烈的文化身份感?写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把思路调回前面所提出的问题那里去,后殖民话语究竟是西方理论,还是东方理论?在西方学人看来,原创东方主义话语隶属东方文化身份,但随着赛义德、斯皮瓦克与巴巴扯起东方主义的大旗在西方语境下的肇事,又因为全部的后殖民理论读本均是以地道的英文书写的,东方主义更被遮蔽在后殖民主义的招牌下取代后现代主义,成为西方语境下的主流话语。那么,这又对东方主义意味着什么?因为毕竟后殖民主义的核心理论是东方主义。(注:按: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启用“东方主义”这一概念时,并没有把他所定义的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为主体的“东方”视为一个内部相对稳定的地域,以使一个内部和协的东方在文化与文明上与西方对抗。就赛义德看来“东方”内部也因宗教信仰而充满了冲突,因此他把“二战”之后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为主体的“东方”称之“后二战”时期,认为:“当然毫无疑问,在我自己相当有限的生涯中,作为一个东方人的意识总是积淀在我的青少年时期,这一时期我生活在殖民的巴勒斯坦和埃及,这种东方人意识的冲动滋养在独立的“后二战”(post-World War Ⅱ)时期这种动荡的氛围中,这一时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1967年的战争,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的崛起,1973的战争,黎巴嫩内战,伊朗革命及其恐怖的余波,这些到处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既没有终结,也不允许我们对它那相当革命的冲击力有充分的理解。有趣的是在这里要企图理解这个世界的宗教是非常困难的,第一,这个世界总是处在不断的动荡中,第二,人们无法把握住这个世界,也没有人能够借助纯粹的意志行为或独立自主的理解,而站在动荡之外的阿基米德点上。为了在普泛的意义上理解东方和在特殊的意义上理解阿拉伯,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它首先要求战胜芸芸众生,迫切地祈求人们的关注,当然这种关注出自于经济、政治、文化和或宗教的原因,它其次也违背了(对东方和阿拉伯)中立的、公正的或稳定的界说。”(爱德华·赛义德:《东方主义的反思》(Edward W.Said,Orientalism Reconsider-ed),《后殖民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 longman 1997.Londonand New york,p.129.)赛义德等人在西方获取的国际精英学者的身份,也掩盖了后殖民理论的“他者”话语本质,也就是掩盖了东方话语的本质,因为赛义德等人东方学者的身份最终随着他们在西方获取终身教席已经西方#
了。这就是为什么东方大陆学人很少有人把赛义德、斯皮瓦克与巴巴认同为是巴勒斯坦或印度的学者,而是情愿把他们误读为是在欧美学界高唱凯歌的西方学人。毫无疑问,当下大陆学术界对后殖民理论的接受,是把其做为西方文化理论或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来承纳的。以东方主义为核心的后殖民理论其西方化的迹象说明了两点:第一,第三世界学者要获取国际学术界的显赫地位,必须要在西方学界占据一席地位,也因此必须向西方挑战,但是,向西方挑战实际上承认了西方文化中心论,其实西方文化绝对不会因为少数人的挑战而放弃业已获取世界文化中心的地位,而是挑战成全了这些东方学人在西方的生存。第二,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赛义德、斯皮瓦克与巴巴对他们的后殖民理论读本翻译为汉语或转让版权不感兴趣。因为远东大陆对他们这些功利性旨在西方的东方学者心目中,还是世界的边缘,他们的兴趣在于从边缘逼向中心,而不在于从一个边缘再度走向另一个边缘。
在东方汉语语境下,如果我们把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进行方法论上比较,后现代主义在东方大陆呈现为一种激进主义,它把西方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文化意识带入东方大陆,成为大陆学人解构华夏文化传统及权力话语的批判武器,而后殖民主义则是地道的文化保守主义,成为当下大陆学人抵御西方文化输入或东方旧日风情输出的理论武器。这样又有两种后殖民主义理论,一种是原创在西方拼音语境下展开的后殖民理论,其呈现为文化激进主义,一种是东方汉语语境下作为变体的后殖民理论,其呈现为文化保守主义。注意,这并不像某些无识者所说的,西方一切现代与后现代话语进入东方大陆后均转型为文化保守主义。有趣的是,在东方大陆语境下,作为变体的后现代主义与作为变体的后殖民主义自己对着自己干了起来,前者为东方大陆植入了西方后现代文明其及价值观,而后者却拒绝前者植入的一切。
让我们感到最为恐怖的是,当以东方主义为核心的原创后殖民理论取道于西方,假借西方话语的合法身份侵入东方大陆后,我们被来自于西方的原创后殖民理论遮蔽了,在这里我们可给出两个层面的理解,第一,当我们操用后殖民话语对华夏文化传统及当下文化的民族性进行维护时,我们已经被“后殖民”了,这就是我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当心!不要谈‘后殖民’,当你谈‘后殖民’时,你已经被‘后殖民’了!这真是一个悖论。”(注:拙作《后现代性、后殖民性与民族性——在世纪之交,艺术创作与批评应该追录一种比较的视野》,《东方丛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1998年第1期,第14页。)第二,在当下世界格局的重新分配中,远东大陆学人已经被中东学人借助于在西方所获得的学术权力征服了。说白了,对于东方华夏大陆的态度,赛义德、斯皮瓦克和巴巴比西方学人更为傲慢,当杰姆逊、佛克马等西方学人多次往来中国大陆讲学,宣讲自己的学术精神以引起中国学人的关注时,这三位中东学者却自恃在西方已获得的学术权力而对远东大陆不屑一顾。一言以蔽之,原创后殖民理论侵入大陆后在文化身份上已蜕变得非常复杂了,如果我们把肇事于西方拼音语境下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称之为原创后殖民主义理论,那么,进入东方汉语语境下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则是变体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说得透彻些,变体后殖民主义话语在本质上就是新殖民主义(newcolonialism)。所以,当我们在言说后殖民理论时,我们不仅受压迫于西方的话语权力之下,也更被压迫在那些于西方获取显赫学术地位并栖居于西方的第三世界东方学人的话语权力之下。在这个意义的层面上,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后殖民主义在东方汉语语境下的变体就是十足的新殖民主义,也理解了为什么在东方汉语语境下根本就没有原创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有的只能是新殖民主义,并且这种新殖民主义对东方汉语学术界的文化批评及文学批评有着既受西方又受东方的双重压迫,这就是东方学人借西方的话语权力压迫东方学人的诡计,只不过前者是中东学人,而后者是远东学人而已。新殖民主义不同于后殖民主义的本质就在于此。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怎样才能摆脱东方汉语语境下新殖民主义的压迫,走向国际学术界在原创的后殖主义语境下与西方学人及来自于中东的东方主义者,进行平等的对话?东方大陆一些学人的学术活动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乐黛云、王宁、张隆溪、张京媛、刘康、张旭东与王逢振等学者在欧美语境下的学术操作与发言,已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乐黛云作为亚裔曾任职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这一显赫的学术位置,她多年的学术活动为东方大陆学界与西方学界的各种学术交流与对话起到了重要的沟通作用。可以说,建国以来还没有其他学者能够做到这一点。青年学者王宁也以有效、频繁的国际学术活动及在多种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多篇文章,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对他的关注。而最为可贵的是乐黛云、王宁等又是栖居在东方大陆汉语语境下与西方学人直接对话的中国学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在欧美学术界发言的直接性使他们的学术活动绝然不是遮蔽在新殖民主义的阴影下完成的。他们也更没有利用对西方挑战的策略而最终企图获取在西方侨居的绿卡。可以说,缺乏比较文化视野或国了进术视野的学者,是无法理解他们及其学术活动的重要意义的。她(他)们的学术活动对那些睁着眼睛却拒绝看视世界的学者,对那些从海外留学国后动又无法在学术上与国际接轨的学者,无疑是一种启示。在多次的交谈中,王宁总是慎重地给出这样一句表达:“理论装备不一样,必然学术视野有差异。”此话的确言之有理。
标签:后殖民主义论文; 东方主义论文; 文学论文; 非洲大陆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大陆文化论文; 黑暗的心论文; 康拉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