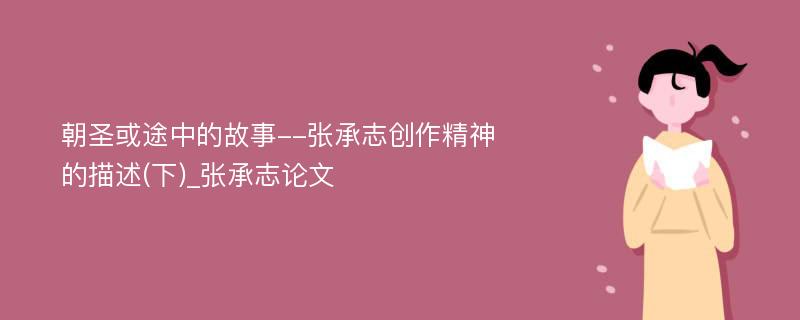
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张承志创作精神描述(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上论文,精神论文,故事论文,张承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下篇
作为人生态度的宗教、哲学,在人生长河中到处可以找到它的投影。它们所带来的人格心理结构上的种种沉淀与变异更证实了愿望对人主宰的可能性,这是人之为人的地方,人永远在这样的怪圈中受着甚至比生命更恒久的诱惑而深陷其中,这种幸福与灾难、超越与局限等相悖体验的难以交融又依依相连,在完成着一种什么样的证明呢?这种在重重选择中的为人的不能选择而又不得不选择,难道仅推之于命定便可解释得通?
是游移于两种现实之间,还是同时占有两种现实,即:是理性的择断,还是在梦与醒间无法摆脱纠缠,这是永恒困惑于人的东西,正象有限的人与终极理想之间的距离,除了作为生命行进形式的脚步,我们还拿什么去填充?
追寻的焦虑
然而,还是无法说清因、果,因了焦虑去追寻,还是因了追寻不断焦虑,继之又为摆脱它而不停追寻。人仿佛永远在一种命定的循环中无从解脱。
这种无从解脱之感在张承志已不单是时代的困惑而是灵魂的痛。存留与抛弃、焚毁与再生,人之有限与终极目的的无限,这之间,我们忍痛追寻着,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那种被撕裂似的焦虑的折磨。因此,追寻的过程就是跨越焦虑。但却无法摆脱永远的焦虑。
由现实而焦虑、由焦虑而追寻,追寻带来的是更形而上的生命意味的焦虑,无从摆脱又想要摆脱但终还是无法摆脱。“他”从《北方的河》走到《金牧场》,每一步追寻都笼罩着现实与生命双重的焦虑,这种寻求者的苦衷所包含的向内的刻骨铭心与向外的惊世骇俗把人对自由的渴慕和正因此对自由的逃避描摹得畅达淋漓。几年来,张承志作品不断重复深化着一个印象:他要达到一个地方,想捕捉一种东西,想肯定一些什么,而最终,他没有到达那个地方,他不可能捕捉到那种东西,最后的最后,连他真正想肯定的什么他也无法知道,或是在无止无休的路途(过程)中他已将它们忘记。
张承志小说的主人公是孤独的;叛逆现实,厌恶城市,背离群体,怀恋高原,创造并追寻心目中的“天国”。这种形象的孤独来自于精神深处的先驱、觉醒式的寂寞。
张承志是寂寞的,他的寂寞不是不为人理解的寂寞,因为众生的冷遇与讥嘲之外他还拥有理想,他的寂寞是更深的寂寞,因为他所拥有的理想连他自己都不能保证是不是一个虚空,为此这寂寞是与生俱来而永不能摆脱的。
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个虚空,而生命过程即是用理想的热情去填充这一个个虚空,假如连这理想的热情都是不能确定、不能把捉的虚空,那么我们还能剩有什么呢?!
我们追求、我们寻找、我们在路上、我们忍受焦灼与饥渴、我们把青春、爱情、生命都搭了进去,或许奋斗到底依然看不见可意的结局,可是生命毕竟燃烧过,粉碎过,奔涌过,升腾过,扪胸自问,承受了智者必会承受的寂寞,比较世俗的喧嚣之声,我们期望的怎能是后者?
苍凉的路的主题即是苍凉的人生的主题,追寻的焦虑与壮阔始终困扰着人而无法割舍,由“不甘”导出的奋进与热情已逐渐成为我们的生命方式与精神原则。
然而,焦虑更深了。
更深的焦虑逐渐加深着张承志的寂寞,而这寂寞的心理根源正是人格的不能完整实现——异化。物我的危机有三种,一是由对金钱的膜拜物化为臣服于金钱的经济人;二是由对工作的膜拜物化为臣服于工作的机械人;三是由对信仰的膜拜“物”化为臣服于原则的无心人。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造成无我的后果。前两种异化是外在的、“被迫”的,由外而内的带有某种不得为而为的色彩以至最终受污染、同化而——或无力自拔,或漠然地随遇而安,最终是对自我的不负责任。追求真理所伴有的理性、热情的态度、行为值得肯定,但若把它极端化,以信仰作为强权而扼杀自我,臣服于信仰。——正如真理再走一步就是谬误——也很可怕。这依然是不完善的自我,这种内在的、心甘情愿的、由内而内的从而带有知其不可而为的成份,以至深陷其中而无法拉开距离地对所信仰进行俯视乃至平视的批判,这种盲目依然是不健康的、是对自我的轻率,是另一种不负责任。
物我的存在造成无我,却比一般的“无我”更危险,以物代我既使“我”失去了无我情况下确立“我”的机会与选择,又使我还需克服、摧毁物才可通过对第一步的超越而达到第二步对真我的寻找。这是一种“假”,物我、无我都是与“真”相背的。难道“要认识自我,我们必须参与到自我之中。但我们的参与又改变了自我。”[①]难道为达到真我就必须要经历牺牲“真我”的程序,这种得失两难难道正是人永远无法走出的怪圈?问题是、还是,人生主宰理想还是反过来,理想主宰人。这种看不见的异化,是虽不同于物支配人(拜金主义)、权支配人,但实质也同样把人置于第二位,受外物(虽非物质而是精神)的绑架。问题还引发于是强制还是自愿,内化问题的复杂性总使得我迷惘于人的无能与伟大,这样的二重使得一些简单的事物因了人的参与而日趋复杂。如果不是出于血性、出于本能的追寻,那么这种内化无疑是一种更深的欺骗,它的不易认识与不好解决使得人蒙受至今仍分辨不出内心需求的真、假。有没有一种绝对的东西,任何时代、任何境况、任何条件,人都可以以之作为依存行动的根据,张承志千百次问、千百次出发、启程、找寻。人之精神支柱是不是始终不被时代、境况、条件打上印痕而衡量着任一时代的人。在张承志九死不悔的追寻与肯定中,上帝复活了。然而人又似乎失去了什么,人失去的是真自我还是假自我呢?为这失去,人是应当悲悼呢还是庆贺?理想与内在需求统一的问题是这样焦虑着每一个人。我们在得失之间或是无得无失之间问:是不是因为我们不能忍受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而不管这上帝是什么,或者,因不能忍受时代精神的空白与虚无;不能忍受由物欲熏染带来的充满污垢而独缺精神之氧的空气;不能忍受心灵单纯如纸同时苍白如纸或复杂如泥同时积尘如泥的世界而重建精神王国却也因重建的激情与热切而不问问建起的理想是不是现代梦幻,有梦还是好的,怕只怕因了盲目而再度使理想蒙上极权,把人引向一场无休无止的厄斗。
我们总在真、伪,正、负问题上纠缠不清而一再失去可贵的机会。理想被悬于至高无上、不容批判和怀疑的抽象层次,由此带来的理想本身的虚弱与抽搐使得我们追寻的焦虑层层加深。理想的正、负必然导致相应的两种牺牲观,负理想支配下的牺牲观或是顺从主义(无主体)、或是盲从主义(无思想),它所煽动起来的强力并不比正理想观所崇尚的牺牲小,法西斯主义运动、中国“文革”运动就是这种危害的例举。
困惑。
“人的血性中有多少种质,多少种色,多少分离化合,多少潜藏的可能性呢,它真的是高贵不凡的血性驱使么,或者是一场可悲的自杀自骗?”扪胸自问时,我们也同那个山海探险者一样,坚定又脆弱。
我们寻求皈依,但我们皈依什么?一统理想被一一粉碎后,我们面对的是确立目标的艰难(选择的艰难),“文革”“心灵大战”后的迷惘一代人的追寻,由茫然到坚定,由“荷戟独彷徨”到“向着自由的长旅”提步前行,由回顾过去的岁月到抬头对未来时日的前瞻,由少年到白头,这一步步的激昂慷慨与义无反顾,又何尝不包孕着孤独、寂寞、惆怅的难以排遣,不被理解、不被认同的冷落感与失重感,何尝不包孕着内心深处难以言喻、无法形容的苦涩,以至心灵一步一回头,在本就辛劳的路途平添几分摆脱不掉的艰苦。自由给了我们选择的空间,也给了我们选择的艰难,我们选择后要走上一条茫茫无止境、自己无法把握成败的路,它的目的的不确定与不能确保成功,使我们既刚勇又迷惘,既充满刺激又危险丛生,这种选择无疑被蒙上一层沦桑的色彩,辉煌在此,悲怆在此。过程哲学由此被推为生命至真的地位。
为了相信——
我怀疑着,只能向前
这使我们联想起布朗宁的诗:“我们借着不信而取获的/是一种因信仰而绚烂多姿的怀疑生命/而信仰的生命又因怀疑而绚烂多姿。”为相信而怀疑,因怀疑而向前探寻,也为相信。这因自由而获、由内而发的理想大大高于由外向内灌输强制的理想,怀疑地追寻真理比盲目顺从主义要高几个层次,从人出发,而非从物出发,即使这物本身就是真理。但也因此,人变得不能确定结局,对未知的惶惑又必然影响现实的心境,舍弃了最终结局而追寻过程的美丽,这是人的幸福,也是不得不承认的悲剧。正如为相信而怀疑,因怀疑而去相信,人在信与疑两极徘徊的沉重步履不时也响彻着人的结局与过程之间的矛盾心跳。舍一取一,本无谓得失,但舍的恰恰是确定的东西而所取并非如意;即便不如意,人因爱也决定去取,除了勇气,难道没有抛弃功利的纯粹信仰在内吗?假若没有这种甘于打碎一切、最终信念不移的精神——信仰,那么作为勇气的力量又自何而生、依何而存、随何而长?不能想象,智慧的人该忍受多大的苦痛而焚烧自己以为再生。或许正因此,至今没有哪一种生灵(除人外)能获得如此高的称谓——英雄。人造就历史,更造就自身。这二者恰是除人以外任何有生命、有呼吸的生物都不能完成的。
也正因为此,在对文化内核的清醒检视与对哲合忍耶教义、历史的狂热迷醉间,张承志作为人类心史的叙述者和作为个体人心灵的承受者所遭至的分裂,却很少有谁去问;以什么来平衡自身?张承志不断地寻找依托,母亲,父亲,在依托与寻找中,得以确立自身,但是这种灵魂寻找也使他耽于精神的另一种外界而不惶回于自身。这种寻找一方面使其脱离了俗界强加于我们的许多标准(去除焦虑),一方面也使他的自我处于更深层的漂浮状态(加深焦虑),依然未能彻底扎下根来,在幻想的存在与抽象的孤独中,自我越走越远。这种暗合于哲合忍耶早期隐居洞穴以修身的封闭心态也造成了一层人格保护层,障碍了真正成为自我涵义的再现,如若不把可能性召回必然性之中,而一味追逐可能性以脱离必然,其结果是再也不能回到自身。生活在现世中间,使我们渴慕理想的光辉,单纯禁锢于理想中也会使我们人格的另一面受损;超越自身并不是将自己连根拔起,张承志在“为人民”的不变的原则贯彻中不断深悟这一点,所以他寻一方水土、一方家园以存放和发扬他所向往的精神。但在融历史、宗教、文学于一炉的实践中,他也因之恰恰忽略了作为个体的自身,虽然他也一再强调自我的独立和文字所表现出的不屑于羁绊;真正成为自己或自我人格的完全独立,当然不是藏身于他人之间,安居于社会和文化的承诺与责任之中,也不是模仿别人,成为一个有限之物,一个数字符号,混迹于芸芸众生,我想也不该是生存于英雄或宗教之类的高层建筑下,以一种新的神话而在拔取自身中丧失本真。真正的道,是道成肉身,是灵肉统一,是“他一个人就平衡了我的世界”的默守气质与人格的坚韧;我们说,在现实层面,选择英雄与宗教比选择其他要好,但在理想层面,则不然;人根本的价值不等同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价值,同样不等同于宗教的价值。E·贝克尔的一段话让我们沉思:“正是人所需要用以维护自信和自尊的防御机制,变成了他终身的陷阱。为了超越自己,人必然粉碎他需要用以支持生活的东西。他必须像李尔王一样仍掉所有“借来的文化衣着”,赤身裸体地挺立于生活的风暴之中”(《反抗死亡》P140-141)。人追求超越的一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项自我的神化工程,而这神化过程同样抑制了自我中另一部分潜力的实现,也就是说,在达到更高人性同时也以人性的部分丧失为代价;被造感、移情、加上自恋情结的某种夸张,在皈依一教义以抨击历史作为对立面时也不可免地贬低其他人的生命价值,漠视其他人的生命感悟。投身于符咒之下,是无法达到超渡的,偶像崇拜,造成了一批追随者,其依赖性质反过来铸就了权威,而权威的催眠作用,在人类历史上是有深刻的心理印痕的。从更深的人学意义上讲,屈从权威,从而丧失所必有的批判精神,对于自我个人,是无法企及人性的全面张扬的。
A·卡缪曾讲:“……对于任何孤独者,没有上帝也没有主人,生活的重负将是可怕的。因而人必须选择一个主人,选择一个超越于形式之外的上帝。”C·莱维讲:“……无力达到自由的人们,由于不能承受显现在他们眼前的神圣的恐怖,他们必然要转入神秘主义,必然要掩盖……那……真理”,在张承志身上,这两种相悖的东西是如此密不可分地绞绕在一起,张承志选择了父亲形象,张承志在选择父亲形象同时不惜抵押上个人的精神自由,与真理。他的自我由此分裂为现想自我、现实自我、现实中理想的自我三种,换句话,张承志以三种身份存在于自己的著作里。《心灵史》如果算作1990年前的一个句号,那么他所写的一直都是“现实中的理想的他”,他把世俗文化作为庞大对立体系,以超越世俗王国而迈向天国之旅的起始,于抗争中,“现实的他”溶汇进去,然而,“理想的他”即越过世俗,亦越过任何形式对自我囿限的他,一直未有获得真正的表现与重视,我以为,这一点,恰恰是张承志不应为任何理想而丢掉的东西。
也就是说,《心灵史》固然达到了一个高度,但还未从历史的审判走向更明确的人类终极关怀,或正在走。在路上。人类学目光的一再遮折,使其张扬民族信仰理想同时,牺牲了鲁迅式鞭辟入里的理想批判,那份冷静与不自欺,与热狂一样重要。即便如此,《心灵史》所涵含的大于科学态度的人文精神,大于理性的价值,和于贫困、苦难中对“无权者的权力”的坚守都代表着人类于困厄中不屈从暴虐而坚持正道的可贵品质。
理想与宗教一样,大概都要有体内的支柱与体外的依托,《心灵史》很好地展示了这一点,哲合忍耶教义以及殉教的宗师(英雄)是他体内的支柱,而民众则是他体外的依托,二者缺一不可,代表着他精神的两面,他的神祗与人本。他游移于历史、人文、天道、人性间的内在冲突,正如贝克尔所分析的一切英雄主义的困惑:他“试图摆脱孤独,又想保持孤独。他不能领受分离的意义,然而他也不愿意完全窒息他的生命力。他希望与有力的超然之物相融合以便扩张自己,然而同时他又希望保持个性和距离……。”这种二元冲突决定了张承志的信奉,从一神教到泛神论,他所认同的前定和他特立于人的自然观,都可视作是他于神秘主义信仰与无神论间的踟蹰徘徊,“荷戟独彷徨”的心境谁说不源于“两间余一卒”的尴尬与自持。
“时常感到,在两个极端之间,在存在与空无之间,我们是徘徊于一种暧昧渺茫的中间地带。”[②]这种给不确定以确定的困惑,成了追寻中的主要体验。生命哲学、过程哲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置根的可能。从得失角度看,过程的美丽就在于既未得也未失,在得失之间未卜的美丽,未达到,所以就总抱有幻想、保有激情。理想如此。此意决非取消目的,没有目的也就没有了过程。目的是不存在的存在,仅此而已。张承志小说主人公追求本身就是过程的暗寓。生命是行进的过程。我们说张承志主人公及他本人的追求是极力要确立什么,天国也好、终极目的也好,但也绝不能排除他的追寻有逃避焦虑的因素。《北方的河》要逃避的是对世俗不公正的焦虑,《黑骏马》的回归是要逃避城市文明与少年忏悔的焦虑,《山之峰》是要逃避自父亲以来对汗腾格里的恐惧的焦虑,《黄泥小屋》、《九座宫殿》无不是在逃避一种外在而内射于心的焦虑。这对现实层次焦虑的逃避恰又陷入对生命层次焦虑的不可逃避,这更深层的焦虑的无法摆脱就使得不断追寻、无始无终成为张承志小说的母题。“他们以最高的速度将自己的生命往来奔波于不同的地点,这并不是由于他们喜欢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而是因为他们憎恶他们原来所在的地方,为此他们到处奔波飞行。”[③]比起这种绝望来,张承志值得庆幸的是他还未丧失一个目的,尽管这目的还不能为众人承认而只能推断,我把它称为终点渴望。有一点是相同的:“它发现它的目标还在更遥远的未来,它必得再次踏上它通往生命的艰苦旅程,而一次又一次的落入幻觉与醒悟的永恒循环。”并且,“从记忆的隐密的核心地带,我们精炼出来那充满绚丽色泽的景观;想象更把我们的记忆磨成希望。……因为它们从来不曾实现,所以才能保有它们纯朴的纯净。”[④]不是追求纯粹理想,也不是单纯逃避现实,而是寻找这二者之间的联系,而这一在此岸与彼岸间架桥的企图又时时潜隐在追寻纯粹理想的形式下,这就使得表现出的与实际藏匿于其下的有了出入与距离,这距离形成了对外——无止境(远的审美),对内——分裂感(深的焦躁)。这种憧憬的循环,正是因焦虑而追寻,追寻又带来更深的焦虑一样,是世俗的“惩罚”,也是永久的“苦役”。
我时常对着《心灵史》封面那个端坐于窑洞窗前,静默于功课的背影,想,也许正是在承受磨难的体验上,而不是如他所说的教义,张承志找到了可以将自我的自由作为抵押的相契相通。
“我放弃一切自由
放弃做为人的
——每一项天权
我要走进他要我走进的门坎
我要响应他向我发出的召唤”
分裂的苦痛
追寻的焦虑来自分裂的苦痛,更多的是自我分裂。在城市与草原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现有存在状态与应有生存方式之间,理想的正、负之间,追求目的与实现方式之间,自我与自己之间,身与心之间,张承志所承受的内心冲突和由这无法解脱的冲突带来的撕裂感,使得其创作表现出的风格始终沉郁、悲怆。
不同于时下一般小说所表现的人性与社会的冲突,张承志小说表现的多是人性与理想的冲突。在社会政治、现实层次之上他始终遵循着理想层次之内的个体内部冲突,这种个体、整体的分解力与离心力时时以两个方向的同等拉力主持着张承志的情感取向,这种自身内部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比起将自身作为一整体与外界冲突来,主人公所要承受的不可克服、无能为力之感更为巨大强烈,张承志曾表述过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有意回避。为什么,怕什么,怕读出自己灵魂分裂的痛苦,怕自己的精神面目在阅读中剥落,怕在现实承受外还要在阅读的想象中再承受一次,怕在陀翁的声音里听出自己沉默时的话语,怕读破,怕看透。正象《金牧场》中“他”怕真弓凛然的眼神、浓烈的语言一样,他需要又恐惧这种理解,“不仅仅是被剥开……他受不了被人一语道破将来。”他怕揭露、怕重去体验,究竟,在掀动历史、人心史、情感史时、张承志的手为什么这般沉重、胆怯,每一页纸仿佛都变成了压迫人的沉重石盘。那句话确是这么说的:“我不仅禁了《野草》,也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至今不读。”[⑤]
上篇提及的张承志模式,对现实的逃避与省略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另外的启示。历史——未来,张承志无论创作还是情感,都包容在这样的双向运动中:向前(精神上)一往如既(理性);向后(感情上)一如既往(感性)。前者因了理想主义的导引,相信历史的发展,明天必定比今日更好,是未来主义的。后者因了知青一代独具的责任感和他本人具备的专业习惯,这份重负使他在要超越历史时总沉溺于其中,脚步犹疑,正因此,向前、向后的双向运动,互相牵制、互相约束,才使得张承志的主人公包括张承志本人的每一步沉重异常、步履维艰,甚至在某些地方踟蹰犹疑、徘徊踌躇。他的每个主人公的形象都是那么冷峻、矛盾、顾虑重重、耽于沉思而缺乏行动,有时真让人想起哈姆莱特式的英雄。人物要挣脱过去,甩掉太长的青春太重的负担而将之汇入血脉,随之一同前奔,但又因原先总沉溺于过去历史的回顾、对过去的沉思多于对未来的前瞻,因此虽挣脱了过去,但对未来目标不明,只是向前,只能向前,而实际上这行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所以,在众生芸芸之中、在茫茫人海之中,他更感到孤独,这孤独仍然不单是置身不被理解人群中的孤独,而更是他本人在意志坚定时也掩盖不了、无法排除的对前途茫然的孤独。“这条道路通向什么地方/我至今不能知道/我知道的只是/它会有一个到达的地方。”历史已是过去,未来还未来临,现实近似空白,虽有追寻,更多是焦虑,打碎了旧的但还未找到新的,告别了往昔但还未看到前路,这是成熟的孤独。因此,他一直在找,想以此排遣困惑与焦躁,并将这种激荡不安视为对理想的背离和动摇。
张承志是历史主义的,所以他相信未来,相信历史的延续,所以他要寻找一种联系,创作也总是“寻找”的主题,在成熟与不成熟之间,在对历史的把捉、对人民的感情和对未知的怀疑、对理想前路目标的困惑之间,他以中年人的头脑对“十年动乱”有历史的认识,对自己有深沉的反省,而在这基础上又不失孩提般的天真与青年的热忱;问题在于思想理念与实践、现实的这一段距离中,他始终未找到联结点,这是症结所在,面对表象中庸实际走极端、非理性的国民性本质,过去政治极端造成极权统治(封建社会根深蒂固几千年),现实经济极端造成经济过热,那么未来面临三种选择,是感性人、理性人还是理性本身。张承志无从选择。他的创作矛盾正在于此,而且在颂扬人力量时却不自觉地转向操纵人的理性本身,这是不是一种极端呢?而且还是物,是异化。在这里,我可以说,宗教究其实正是一种异化。因为它已不是为人主宰的态度而演变为主宰人的锁链,依然是人的牺牲,是人对外物(不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主义)的屈服。
张承志又是反历史主义者,他在论文中直言:“当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真的可以对这些被埋没了的一切不屑一顾么?尤其是回忆一下最初使我们动心研究历史时的初衷,那时的发想难道仅仅是一种幼稚么?”“历史研究发展太盛且太久,浩繁的内容和分支有时使我们忘记了人类探究历史时朴素的出发点。”[⑥]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的话,那么张承志的创作脉络则愈来愈明显地表现着人挣脱冰冷历史的努力。历史具有强权性质,人之奋斗即是对历史这种性质的抗拒。人创历史,却反过来要受历史的限制与框缚,人内在、本能抗拒此命运,但面对客观必然的无情事实又完全使这一抗拒暴露了它的软弱、无力,更将人的不自信而求自信,自强而求自强的面貌显示无遗,人的生命就是很悲壮又很可笑的努力,在抗拒它自身创造的又抗拒不了的历史时,谁也摆脱不掉困惑与宿命,人对不公的抗拒这一过程也就构成人的历史(而非反人的历史——这也是张承志要反的历史)。这种努力是很可笑、很悲壮的,是很没意义又价值非常的。(功利上的结果与心灵上的拯救的冲突还会延续再延续直至宇宙有一天成为没有人的死寂。)
历史的与反历史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种种矛盾终归结于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太大的差异、过强的冲突。这是有人类以来无法克服的冲突,是现时代尤为强烈的比照反差的现实存在。张承志的敏感与机警又使他精神情感上承受着超乎常人的分裂——人格分裂,是退回过去,还是面向未来?是向后还是向前?不过有一点已明确了,横向以精神内部的异化反精神与物质关系的异化,纵向以古典热情反现实冷峻两条路都是走不通的。向过去寻找良药总不是长远的办法。也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些,张承志才不倦地寻找吧,或者是以寻找的热切来掩盖同样热切的怀疑。对于不可找到的找到,对于不再存在的存在,他深深感到自己被撕裂的疼痛,“……于是,我遵照启示,肉身置于闹市,灵魂却追逐自然。这样,只有我救活了一条灵魂,也只有我使这灵魂孤苦无伴”(《错开的花·题辞》)。一只脚留在过去,一只脚已踏上未来,一次次告别的宣言不过是一次次意识到的决心,宣言产生的本身就已表明了它实施的困难和不可能,因为告别过去就意味着告别自身、告别作为生命的一部分。有谁做得到只拖着半条腿跳着走路呢?“我总是顽固地盼着能找到一位医生。”“紧迫的事情是获得医药。”“究竟去不去找那个医生呢。”[⑦]这念头顽固地纠缠着他,这种疾病意识和急于获救的感觉已经被他熟识地称为“生命的过程”,“渡得过去与否,沉死或再生与否,都是不可能预料的事情。”然而,“治我的药只有我自己知道。”[⑧]创作的恢复可用清夜作为中介,而生命的追击该拿什么去兑换,比如分裂的苦痛,用什么去避免过于惨烈的体验,这是看不见的敌人,不是我们不承认面前的战场,不承认已经进入决战。同自己打仗多的只是一份顽强吗?或者一份挣扎?“自我治疗”可拿什么去换得终愈,或仅换得“疾病和健康的循环”,生命是涌动的一场什么?而终愈就是死亡呵。
关键的关键,在于忍耐了难以忍耐的分裂,承受了难以承受的苦痛,嘲笑、讥讽、打击、自残、牺牲,经历了人所经历的一切,也不能消除我们最终的困惑——吉诃德的长矛应指向哪里?
《心灵史》中,张承志干脆把对苦难的渴望发挥到了极致,然而在血气灼烫的文字后仍然有张承志不愿讲出的惶惑,宗教中的人性实质与殉难时的壮烈情怀间,他宁可寻求后者的浪漫、辉煌,而在历史的人性(宗教遭压制与屠戮)与宗教的人性(人必须承受苦难、血腥甚至自戕)之间,张承志的作为后来人的疑问,只能压在他烈火般的膜拜与文字的迷狂中,这种痛苦如果揭出是会动摇根基的,而不问是与非、对与错的信仰在这个实用功利与理性交揉的时代又是多么可贵;更有这样一种摒弃了事功的方法论,于对苏菲主义的神秘、出世、真挚、简捷的精神追随里,于从自己独行到架桥,从个人走向民众的行动里,于每一门都以大赞、祷词、颂诗结尾的形式里,于18世纪的黑暗至19世纪复兴的历史中立誓坚守皎洁本质的刚强里,凸现出来,是:“正确的方法存在于研究对象拥有的方式中”“正确的研究方法存在于被研究者的形式之中”。张承志自称是一个不愿描述当代的作家,更是一个以教徒的方式描写宗教的作家。“十三太爷马化龙为着换回多斯达尼,把自己一家人举意当了古尔邦的羊了”,张承志则为了内心的宗教的完整将自己的血肉之躯也放在了理想的祭台上,束海达依道路(殉教)是不同的,然而却是前定的,“这一切认识——我知道它们离人们习惯的中国文学实在是太远了。但是我相信这种文学的价值”。探求者思想追求的两极:天理与人性。就是这样在悲怆的信仰里融合为一。“在生死关头,人应当怎样做才不愧于人”的血写的历史、内里的事实以及底层民众为承担信仰所经受的考验的残酷性与舍命的追求,都足以对抗现代太多的纸糊彩绘的英雄和虚假塑造出的神明。宗教不是一个闲聊的话题,英雄同样不是,“正确的方法,存在于被研究者的方式之中”,“我选择了沙沟方式”,这种皈依不仅是“使历史变成情感,而且是将信仰化作生存,从乌珠穆沁到西海固,从草原额吉到沙沟马志文,让我们领悟到19世纪德国诺瓦里斯曾说过的一句话:“哲学是人们怀着无尽的乡愁,寻找人类心灵精神家园的冲动,”对于失却故乡、失却母语之后再不愿失却信仰的立誓坚守的哲合忍耶,对这句话的理解,会比只将它挂在口头引用的文化人要份量沉重,某些以中庸为思想土壤的知识分子,是很难贴近和理解这种异端的。
所以他孤独。“所谓‘知’——即真正代表时代的观点是挣不脱先锋命运的。当它独自出世孤独探索时,它不仅曲高和寡掷玉入泥,而且放弃了于通俗求弘扬的契机。而当他被结局证实以后,庸俗的聒噪声鼎沸而起,喊叫的是它昨天的见识。它又沉默了——这是一种学问和艺术向宗教皈依的过程,”所以他在求真的探索中将个体英雄汇入群体英雄,以找到更有力的信念支撑。神秘主义、叛逆性格、英雄本色所立于的那个雄厚的根基是独立不羁的人格与追求自由的人民的水浮交融,这命运,正如书中所引《哲罕耶道统史传》中船厂太爷的话:你已经有了知识了。——你千万不要把你的知识的光芒熄灭,而使你自己坠回黑暗!你不要熄了那光芒——以免来世降临,别的作者凭着他们的光芒奔行时,你却处于黑暗!“(《心灵史》,上同)所以有《天道立秋》、《重写一个金牧场》的沉著继续。所以有《清洁的精神》《以笔为旗》,有《无援的思想》《致先生书》《击筑的眉间尺》,有《神往》和《三舍之避》,有《大理孔雀》,凄美、刚烈、不屑与决绝就这样长在了一起。”“旅人一词的份量在于这旅途无止无尽,和命运一样短长。只要活着,我命定面临这跋涉的压力,在中国一次次地发现价值和美,并探求怎样活得美和战胜污脏。”[⑨]
在《穆罕麦斯》血流一样的声音里,远行人又一次上路。
“似乎火中含有水的湿润
那是由于悲哀
而水中却含有火的燃烧”
困惑的前卫
命中注定,困惑是前卫的侣伴。
“我无法面向前方,前方空无一人/我不想回顾身后,身后人群挤撞/过去已经逝去/泪水早已堵塞/象他们那样笑么,我不愿意。”小林一雄的歌唱出了张承志的深心感叹,思想精神若是走在时代的最前面(前面不再有人),设想信念并去付诸完成,孤旅独行,难免有孤苦的心境;环顾左右寥寥数人同行,回顾身后不见追随的身影,更为孤寂、凄凉;而前路不能保证,目的的明晰与真实无法确定,这才是最深的寂寞,寂寞中的寂寞。
这寂寞里深藏的反整体态度和由之衍生的骑士形象不同于当代其他作家笔下的反整体的“浪子形象”。后者以反文化小说为明显代表,“他们注重今生……似乎很少反物质的文化倾向……在现世中,他们会感到恐惧、迷惘、飘忽不定,这就意味着他们在潜意识中仍然把自己同他人联系在一起,他们缺乏一种我行我素的坚定感。他们的内心常常是软弱的,常常处在一种类似青春期的骚动不安中。……他们缺乏一种坚定的“自我放逐”的勇气,他们的放逐常常是被动的,因此就有一种被遗弃被冷落被窥视的感觉。”[⑩]张承志有他自己截然不同于众,也截然不同于以上新阶层的精神原则,他有他独立于世,又独立于所谓先锋派(伪现代派类)的困惑与苦痛。“象他们那样笑么,我不愿意。”他反对传统麻木与腐朽,更厌恶快乐主义的享受与嬉戏,而在这两股潮流之外他游弋在少水的现实之河里,精神所承受的寂寞是可以想见的,在洪水泛滥之外要寻求一理想的码头,在峰巅之上要找到那隐显的佛光,在喧哗中还要不顾湮没说出自己完全异于喧哗的主题。从这里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张承志并未达到彻悟,他是以庄子之形(出游)写孔子之心(救赎),(虽然在他的散文里不止一次地猛然抨击过孔孟之道,但我还是借用这一词语),他没有达到彻悟,甚至拒绝彻悟,他既要独善其身,又要兼济天下,虽然他背负重负、背负责任、背负使命并为之不惜人性牺牲,虽然我说他超越了肉体、超越了利益,但还未达到对人生的豁达、未达到象他的血性一般的回民族的超越苦难的洒脱,还未让生命在生活重负与挤压下显出它璀璨的光芒,但是我还是无法掩饰对这一精神原则的欣赏。即使这原则带给我们的是无尽的寂寞,我们也因对这寂寞的承受证明了我们曾生活过。
反文化现象在文学中的普遍存在说明了一个与张承志小说存在的现实中精神的反逆,二者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途。在外部与纯文学相峙的通俗文学之外,纯文学阵营中的审丑文学(反美学文学)正从内部分裂着“纯”字并正呈现出取代的趋势,张承志创作精神的可贵正在于在与外对峙之外还坚守对内划界后的阵地,这也许正是现时代最后的阵地?珍存这最后的最后,所背负责任使命之外还背负不被理解、不被体认的悲壮与寂寞,这一切谁能深知?我所理解的前卫是这样的前卫,是世人都背叛了一精神原则而自己不背叛精神原则的前卫,是不背叛自己的前卫,真正的先锋不应以形式、观念而应以精神、心态为准。
心肠应该成为一种界限,或说在一个熟知智识观念的文学时代里,最重要的界限就是心肠。
前卫的困惑是无法解脱的。张承志是我所说的真正的先锋,是思想的战士。他在“用一个现代人的歌喉向传统的梦道别”“但他强调他的“背叛”是代表着一个古老的大陆来向现代和世界提出挑战的。正是这使命感使他甘愿尝尽流浪的滋味。”(11)也许世界总是这么悖谬地存在吧,作为反历史主义的历史学者,作为迷狂的理性主义者,对于他这一切也是生存呵。
但是,张承志还是不甘,我已说过,他不仅要独善其身,还要兼济天下,而最深寂寞中荡溢的焦灼也使他变得急于辩解、急于剖白,于是,在一时期作品中,竟也调侃起来,带着嘲讽的微笔看众人,更看自己。《胡涂乱抹》就可看出端倪,无论是宣泄的情绪还是这作为情绪载体的形式,都如音乐节奏,代表着一种生命焦燥的律动。《黑山羊谣》的“复仇”镜头剪接式的模拟与重复更代表着深层的不安与愤懑,至《金牧场》这种文笔就无可掩饰,一切都简单、自然、无矫饰地流露,小林一雄的疯魔发狂Rock的大段描述所表达的情绪取向不谈,主人公“他”也一反冷峻、沉默而压不住时时的独躁。单就形式而言,一种单向的语言流已无法表达内心说也说不完的思想了,J(日本)、M(内蒙)即现实、怀想之外,还加上了议论、三种印刷体一同将一个丰富的内心推至读者面前。而《海骚》干脆就写人在海上的心灵波澜,依然是不安的急湍,即便是在自己无侮青春的人生正剧的作品里也阻挡不住这类情绪的生长,不安、惶惑、暴躁、无奈,还有些浮躁,这是更深层的叛逆,是不用宣言而已存在的叛逆。甚至在他对西省英雄的缅怀以在历史中、底层民众中寻找同道的时候,在对历史英烈的掩饰不住的颂扬里也掩不住对现实困境的心痛。“一种姿势不能保持顺畅之后,另一种姿势就如同排泄般产生了。”(12)过于激动与亢奋使得他不停地倾诉,这倾诉是表白而不再是交谈。这一倾诉的要求,同样焦急、焦躁,要求短期见效,小说形式已概括不了了,改为写散文、诗,这一形式不顾忌结构、人物、情节发展、时间脉络等,一气呵成,直抒胸臆,回忆、怀恋、自省、内视、纪实、议论。总之,张承志的创作在不断选择、扬弃着自己,此之孤军奋战、哑夜独语来,以俗抗俗或许来得痛快淋漓。反文化小说的泛滥正因此有一定存在道理。张承志小说的焦虑与躁动也有此滑向,但还只是有控制地,他时常把这种对物欲的不满、对平庸的不满包裹在对正面的描写与树立之下,将此作为出发点之一而最终是在打碎之后还谋取建立,这个原因使他不未与俗站在一地平线上诅咒、谩骂俗,而能站在高一层第轻蔑审视和冷眼观望俗世、观望一个与其追寻完全不同的喧哗时代。
前卫的困惑可能是“觉得自己浪迹在一幅广袤的白色的地图之中”时的那种对于迷路的恐惧与迟疑,可能是对新大陆追求中“只怕拼尽残生也走不到头”的热情、迷惘与犹豫,也许还是荷戟独彷徨的孤立、无依又不知未来的感受。但作为有叛逆血性的前卫,他的最深困惑更在于在叛逆现实、叛逆群体、叛逆自身之后,在承受追寻的焦虑与分裂的苦痛以及种种有关生的困惑之后,是否能够矢志不渝、能否在为理想背叛了一切之后还保有对这理想的最后不背叛。
路还是要走。
前卫依然是困惑的前卫。
所有、所有人都离去了
这条平常的旅程
寂寥岁月
踽踽独行
所有、所有的都放弃了
这个人总不肯舍下
那只手举的灯盏
那个憧憬
那份最初的忠诚
还会有后来人的
会有人乐于捡拾脚印
潮涌潮落问
海滩上总聚集着
贝壳收藏者的匆忙身影
还会有后来人么
苍苍茫茫
芸芸众生
哪里去找、去复制
再造
一个前卫
和他不可替代的
英勇
注释:
①P·蒂利希:《存在的勇气》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③④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上海文学杂志社1986年版
⑤⑦⑧张承志:《泛夜海记》/《作家》1988年第11期
⑥张承志:《历史与心史——读〈元朝秘史〉随想》/《读书》1985年第9期
⑨张承志:《重写一个金牧场——写在〈荒芜英雄路〉一书出版之前》/《光明日报》1993年2月8日
⑩蔡翔:《世俗的喧哗——当代小说中的精神文化现象之三》/《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6期
(11)李洋:《无边的漫旅——J·M世界与张承志的寻求》/《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5期
(12)张承志:《骑上水流——关于冈林信康的随笔》《外国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
标签:张承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