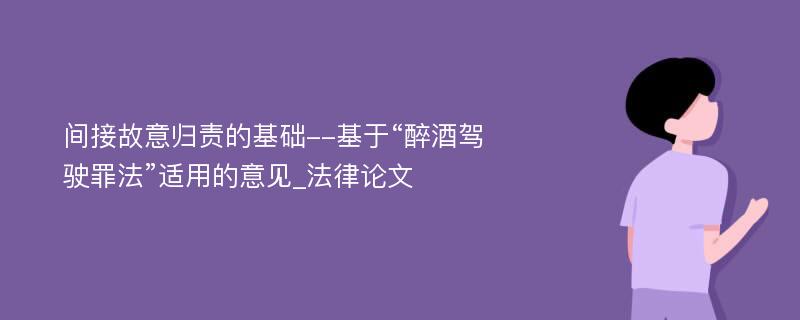
间接故意的归责基础——以《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为契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见论文,基础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为依法严肃处理醉酒驾车犯罪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8日发布了《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意见》)。《意见》在明确行为人明知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酒驾车,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的,应依法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的同时,强调指出,“一般情况下,醉酒驾车构成本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并不希望、也不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属于间接故意犯罪,行为的主观恶性与以制造事端为目的而恶意驾车撞人并造成重大伤亡后果的直接故意犯罪有所不同,因此,在决定刑罚时,也应当有所区别”。很明显,《意见》并非在一般意义上泛泛而谈间接故意与量刑的关系,而是赋予了间接故意与具体量刑之间的刚性联系。这不仅仅体现在文字表述上的差异,《意见》明确提出间接故意犯罪的量刑应当有别于直接故意犯罪,而对另一个量刑情节醉酒状态的表述则是“酌情考虑”,更需注意的是,《意见》的此项规定是在研究总结黎景全、孙伟铭两起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的恶性醉酒驾车犯罪案件的基础上作出的。黎、孙两案的共同特征是情节极为恶劣、后果极为严重、民愤极为强烈,一审均判处死刑。① 面对此类极端的刑事案件,间接故意在量刑中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如何?办案法官将面临刑事归责理论和职业理性的双重拷问。那么,黎、孙两案最终改判无期徒刑,申言之,对于间接故意(放任故意)、直接故意(希望故意)以及轻信过失这三种在认知方面并无根本不同的主观心态的刑事责任在实践中加以具体区分,其依据何在?本文的论述即拟为此寻找答案。
对于刑事责任依据的探讨,规范责任论的分析框架无疑是一个适恰并应予坚持的路径。规范责任论认为,责任不仅仅是心理学乃至生物学的事实本身,责任的本质是从规范的立场对事实进行非难可能性的评价,责任是作为心理要素的故意和过失与作为规范要素的期待可能性的结合。摒弃对于心理事实的单一分析传统,而是从心理事实和规范评价的二元维度对刑事责任概念进行阐释,是规范责任论最为鲜明的特点,也是该理论对于现代刑法理论的基本贡献。规范责任论对于事实和规范之间内在紧张关系的揭示,使得刑法诸多难题的解释变得豁然开朗。比如,同样是欺骗行为,却有民事欺诈和刑事犯罪之别。作为现代刑法的奠基理论,规范责任论获得了不同法系、不同学派的普遍认可。例如,英美法系国家一般将犯罪心理表述为行为人在实施社会危害行为时的应受社会谴责的心理状态。② 该定义明显具有规范和事实的双重蕴涵:1.规范内容——应受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谴责与否定;2.心理事实内容——具有知和意的心理要素,即认知行为性质以及行为与危害结果间的关系,并且表明对行为和结果的意向。对于规范要素和心理要素的关系问题,我国学者也有过精当论述,“主观恶性是心理事实与规范评价的统一,没有心理事实,主观恶性就是无源之水,同样,没有规范评价,主观恶性就是无本之木”。③ 基于此,本文将在规范责任的理论框架下,通过心理事实和规范评价两条主线对间接故意(放任故意)的非难基础进行深层次探讨,以此对间接故意与直接故意、轻信过失之间不同的责任分配之依据,作出阐释。
二、间接故意的心理归责基础
(一)心理责任的一般理论
作为犯罪心理的一种特殊形式之间接故意,首先从心理维度寻求阐释资源,在分析方法上具有其内在必然性,这不仅是近代责任主义刑法理论赋予犯罪行为道义非难的依据,更是由此衍生出来的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西方盛极一时的心理责任理论的基本思考特点。心理责任论认为,责任的实体存在于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心理关系之中,探讨责任的目的在于确定行为人对于行为的心理样态。并基于行为人心理关系之不同,将心理状态分为现实之认识和认识可能性两种,以区别故意和过失。在行为人虽曾认识自己行为之反社会性,而仍然实施行为的心理状态,称为故意;虽可能认识自己行为的反社会性,但由于不注意而未予认识以至造成危害结果的心理状态,称为过失。心理责任论主张在具备责任能力的前提下,如果存在故意或者过失,即可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否则,即无责任。该理论因认为故意和过失均为对于一定的意思与行为的结果关系的心理事实,其中并不包含非难的要素,故称为心理责任理论。④
尽管心理责任论自上世纪已降受到了诸多非议⑤,但行为人的主观心理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已成为当代责任理论的基本要素,构成了整个责任理论大厦根基(尽管刑法中存在着严格责任的例外规定),之后的责任理论无不是以心理责任理论为基础
(二)间接故意的心理阐释
间接故意所显现的是何种样态的“意思与行为的结果关系的心理事实”呢?诚如笔者一贯所坚持的:放任不属于意志因素,放任是一个人对有认识的可能(或者必然)发生的结果事实的非欲的(否定的或者模糊的)情感体验,放任在心理过程中归属于情感因素。而放任仅仅是一种情感因素而非其他,取决于放任心理对意志行为(主行为)的无效性(间接故意心理过程的不完整性),以及放任结果的他行为性。⑥ 而传统理论将放任因素作为故意的意志要素,与历来刑法上犯罪心理的知、意二分及“法不管情”的思维习惯是分不开的。
由该观点所引发的一个问题是:既然放任故意和有认识过失(轻信过失)均属于对危害结果的非欲态度,而放任故意和希望故意(直接故意)在意欲态度上却存在明显的分野,那么将意欲态度上截然不同的放任行为与希望行为归为一类,视为故意,将意欲态度表现颇为类似的放任行为与有认识过失行为在法律上划出一道鸿沟,就意思非难而言是否妥当呢?该问题不仅仅关涉到上述观点正谬之根本,也直接触及到了现代罪责分类模式的合理性问题。在回答该问题之前,有必要阐明笔者对希望行为、放任行为、轻信过失在心理上的特点所持之基本立场。笔者认为,希望故意和放任故意的区别在于意欲上的不同:希望故意对危害结果表现为一种积极的、刻意追求的态度,放任故意表现为对附属危害结果的一种消极的、非欲的态度。而放任故意与轻信过失在知、情、意三个方面均存在不同:在知方面,放任故意认识到了附属的危害结果发生的具体危险性,轻信过失认识到了危害结果发生的抽象可能性,但就现实而言,行为人认为危害结果不会发生⑦;在情(欲)的方面,放任故意表现为对危害结果的一种消极的非欲态度,轻信过失表现为对危害结果积极的否定态度;在意方面,放任故意缺失,轻信过失表现为对危害结果设法阻止的有意行为。需要指出的是,轻信过失和放任故意的心理构造在情感态度上是存在交叉的,放任故意的非欲态度在外延上对轻信过失的否定态度是一种包容关系,但放任故意中的非欲态度除了否定态度之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介于肯定与否定之间的难以言说的模糊态度。
根据上述粗线条的区分,我们可以对刑法之所以对这三种不同的心理形式规定为由重到轻的三种责任形态心理特征上作出一个大致的说明。希望故意表现出了积极的“恶意”,放任故意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消极的“恶意”,而轻信过失不存在“恶意”。在希望故意中惩罚的是行为人严重的主观“恶意”,在放任故意中惩罚的是对法律所保护利益的严重不负责任的态度,在轻信过失中惩罚的是一种不被容忍的错误。有必要强调的是,放任故意这种消极的“恶意”是以对附属的危害结果的认识为前提的,并经由目的行为的实施、附属结果的发生表现出来。放任故意的他行为性,决定了放任故意不存在未遂的责任形态。
我国有学者在论述希望故意和放任故意的区分问题时指出,“如果我们不去究明行为人的心理是希望还是放任,而根据行为人对结果发生的必然性的认识及他的行为是其意志支配、控制的结果就认定为确定性故意犯罪,不是更合理些吗?”⑧ 该论者是从刑事归责的角度提出这一设想的,立意颇为高远,但笔者认为其立论基础存在问题。将刑事归责的要素概括为责任能力、事实性认识、违法性认识、期待可能性四个方面,显然不够充分,尽管这种叙述角度的转换有可能为实务界带来极大的便利因而在操作上显示出其过人之处。我们知道,现在西方刑法责任理论一般都认为责任包括责任能力、责任心理、期待可能性三方面要素,尽管期待可能性问题的地位长期存在争议,但而责任心理远非事实性认识、违法性认识这么简单。笔者认为,仅从认识的角度来探讨希望故意和放任故意的区分,并不能得出正解。而主张将放任必然性结果理解为直接故意,甚至于以“确定性故意”来替代“直接故意(希望故意)”,即未能充分反映放任故意的客观心理特征,同时也忽视了放任故意与希望故意两者在主观恶性上的差别,殊不可取。⑨
三、间接故意的规范归责基础
(一)规范的一般含义⑩
传统上一般认为犯罪的本质在于违反法律,“罪恶非但是指违犯法律的事情,而且也包括对立法者的任何藐视。因为这种藐视是一举将他所有的法律破坏无余。这样说来,罪恶便不仅在于为法律之所禁为、言法令之所禁言,或不为法律之所令为。而且也在于犯法的意图或企图。”(11) 对此,宾丁提出了批评,认为它将犯人所违反的法规和据以评价犯人的刑罚法规视为同一了。指出犯人的行为,是对广义的法,即一定的法规的可罚性的违反,而不是对预告刑的规范即刑罚法规的违反。并鲜明地指出,犯罪的本质在于蔑视法规范的要求,即违反法规范性。(12) 在此基础上,梅耶进一步提出,法规范只是对于国家机关具有意义,而一般公民对其则完全不知。实际上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是“文化规范”,即宗教、道德、风俗、习惯、买卖规则、职业规则等决定人们行为的命令及禁止。故没有文化规范上的要求,例如没有业务上的义务时,行为人便不能被科处刑罚。并认为,法规范的这种规范机能并非基于法规范的法律性质,而是由于法规范自身与文化规范的相一致的缘故,构成要件符合性不过是作为违反文化规范的违法性的征表而已。
而规范理论在刑法中优势地位之确立,与梅兹格是分不开的。他指出,研究者们如果否定主观的决定规范在理论上有可能先行于法的客观评价,将不法理解为主观的违反义务规范的话,并不能理解其明确性而误解法的本质。即他会得出无责任能力者不能为不法行为的结论,并且将不法和责任当作不可分离的东西,肯定会得出责任是不法这样奇怪的命题。鉴于此,梅兹格将规范分为评价规范和决定规范。违反前者是违法的问题,违反后者便是责任的问题。并进一步指出,评价规范是对一定事态同法理念在客观上是否一致的评价,无须考虑行为人的个人情况;(13) 决定规范是对行为人作出的,其违反,必须在考虑包括行为人的个人能力在内的个别事情的之后才可以判断出来,即责任判断是个别的判断,是人格的非难可能性。梅兹格的评价规范与决定规范的二分思想直接为规范责任论(期待可能性理论)准备了理论依据。例如,格米德休密特就主张法律除要求个人外部遵守之法律规范外,还有必须采取遵守法律规范的意思决定,即不得为违法行为之意思决定的义务规范。休密特则直接借鉴了梅兹格的观点,将法律规范的机能分为两种:评价机能和命令决定机能。认为对于前者是有关客观的价值判断,对与后者是有关责任判断之规范,故只能依据命令规范而为意思决定之人,如违反其期待而决意实施违法行为时,才发生责任问题。(14) 对此,他进一步阐释到,只有在行为人具有社会性行为能力即具有责任能力而且不存在妨碍行为人在主观上履行“义务”的情况即不存在动机过程中使“义务”发生作用变得不可能的情况下,才能期待行为人作出合法行为的决意。所以,作为责任的要素,需要行为人在心理方面表象了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规范方面可以期待动机过程根据义务而展开,即能够期待行为人采取合法的态度以代替实际作出的违法态度。
需要指出的是,将规范分为评价规范(法律规范)和决定规范(命令规范、义务规范),并将之分别作为违法性和责任的判断依据,试图在不法与责任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其志可嘉,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正如大冢仁所指出的,“把法规范分为评价规范和命令规范,在相当程度上是妥当的,但是不能认为评价规范只关系到违法性,命令规范只关系到责任。”(15) 一方面,责任判断不外乎是刑法性评价,它当然应当根据法规范来进行,在该意义上,评价规范也制约着责任判断;另一方面,命令规范也必须在违法性论的领域加以考虑,正是在以一般人为对象的命令、禁止的前提下,才能够评价违反它的行为是违法的。因此,评价规范和命令规范都在违法性论和责任论中发挥着作用,只是他们在违法性论和责任论中发挥作用的方式有所不同。
(二)间接故意的规范阐释
对于罪过的规范阐释,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一般是从知、意两个方面展开的,具体表现为命令规范和决定规范的违反。对放任这一情感因素基本上没有予以独立评价,间接故意的非难依据通常是沿用希望故意的一套解释模式,即从行为人意欲决定(决定事物倚赖意欲作用)造成利益的冲突状况来赋予故意(包括放任)的非难品格,诸如表现较高的个人非难性、对实现非法事实的操纵、法敌对态度以及颠覆对法的忠诚等等。
这一点,在当下西方流行的客观归责理论表现得尤为突出,该理论论者从认知的层面来论述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在责任非难上的不同。或许认为,行为人认识到了风险而决意为之是一种个人的负面贡献,会颠覆对法的信赖与忠诚。这一观点和骆克信关于行为人作成了可能侵害法益的决定而表现了法敌对态度的思路基本上是相同的。被许乃曼称为归责基础上“完全的后现代客观化”的雅科布斯对此更是发展到了极致:他认为刑法的目的是为了确立一般市民学会对法律的忠诚,刑法的机能就是保障规范的同一性,保障规范能够证明自己在社会中是真实的。法律不能证明本身的正确性,亦即不能说明为什么必须有符合规范要求的意志,“法律所遭受到的这种可论证性的缺乏需要人们有意志地遵守规范。”(16) 责任刑法中的行为就是损害规范有效性的自我有责的活动。“对规范遵守的意志缺陷的负责就通常称为责任。”(17)“智力(认知——笔者注)的缺乏通常减轻责任,反之,意愿的缺乏只有当它完全不加重责任时才例外地减轻责任。”(18)
台湾学者黄荣坚先生秉承其德国导师雅科布斯功能主义刑法的衣钵,从可能性说的立场理解间接故意。他从法益保护和比例原则两个层面对排除意欲要素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论证:从法益保护的角度来看,对于故意的要素,除了“知”之外,再加上其他任何要素都是有害的。从比例原则的角度来看,对于故意的要素,除了“知”以外,再加上其他任何要素都是多余的。如果一个人已经预见构成犯罪事实发生的可能性,他就有避免这个事实发生的义务,而且也有避免这事实发生的高度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在他违反这个义务的时候,为什么不让他负这个高度的责任呢?事实上,行为人的意欲与否对于法益侵害的预防又有什么意义呢?既然行为人预见法益侵害的可能性,而且事情做也已经做了,行为人再怎么说他是无意的,也没有用了。何况就法益保护而言,如果他真无意侵害,他就不要做,既然已经做了,还能说是不要吗?所以就法益保护而言,在故意的观念里加上意的要素反而是侵害了被害人,也侵害了一般社会大众的基本人权,因为这种严格的定义降低了“故意”这个观念对于一般人生命、身体、自由和财产等法益的保障功能,而这种使故意贬值的做法并没有宪法上或刑法上的依据,行为人的意欲与否对法益侵害的预防并无意义。据此,他认为,没有理由在故意的观念里加上意欲要素,并认为这样的看法在今天我们这个人不尊重人的社会里尤为必要。(19) 我国学者冯军引用克莱因的话表达了类似主张,“决意实施法律禁止的行为,或者决意不履行法律命令的行为,就表示积极的恶的意志,就是故意。”把行为人针对结果的心理态度视为意志因素是不妥的。并因此认为故意与过失的区别在于认识上的不同,而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区别在于是否认识到危害结果发生的必然性。(20)
上述完全抛弃责任的心理事实,而纯粹地从规范决定的角度来解释责任的观点,显然是不全面的。不管是目的理性的刑罚观或目的行为论的刑罚观,都少不了“决定”。故意和过失都有行为决定,甚至不违反法秩序的行为也有行为决定,而所以不同行为决定受不同的评价,在于行为决定的先阶意思决定不同,欲望决定的有无。因为一定欲望的确定所导致的行为决定,不同于轻率的行为决定。不同于谨言慎行的行为决定,但不表示刑罚制裁的是欲望情绪,因为单纯的内在欲望没有表现于外,对法秩序没有产生可以掌握的威胁,因此受制裁的该是这种与法秩序冲突的欲望的外在表现。这种与法秩序冲突的欲望,对内显现的是人格,对外显现的是对法秩序的敌意,而故意、过失所以同时属于构成要件阶层和罪责阶层,正因为这种欲望具有对内和对外的意义。(21)
据此,笔者不赞成上述放任不要说的观点,并认为间接故意的放任要素具有单独评价的规范意义,尽管在某些场合,放任的判断并无必要,因为这在技术上可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认知中推断出来。“但是如果行为人意识到有产生该结果的危险,那他就足以要求他承担刑事责任。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他的犯罪意图没有调节他的举动,其犯罪意图也伴随着这种举动,或者,我们可以说,犯罪意图与举动是相符的,以致他在行为时认识到该结果可能从他的举动中产生”。(22) 该话揭示了放任的心理本质,即没有调节行为,但伴随着行为。然而不无遗憾,它没有对放任的心理品性及规范意义进行深层的说明,就此而言,它与放任不要说的观点并无两致。放任非难的规范基础在于对一定社会历史的生活伦理秩序的违反,对一定社会期待的违反。责任理论解决的不仅是可责性问题,还需解决可责程度问题。在放任的心理阐释的基础上进而对放任作出规范评价,在这两方面均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首先,可责性程度问题不能从认知层面的判断得出结论。犯意的多样性及放任内部所呈现出来的不同样态,尤其是后者,是我们一贯所忽视的。1.放任故意与希望故意不同,“放任”体现的是对法规范的消极的对抗,而希望体现的是对法规范的积极的敌视。这一点在可罚性程度上必须得到反映。尽管人们通常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一个人在采取行动时明知某种特定结果必将发生或者可能发生,这与一个人把这个特定结果作为采取行动的目的是同样可责的,但是,“按照‘双重结果’的道德学说,当一个人不希望他的行为产生某种结果时,尽管他明显地认识到这种结果必将发生,也比他寻求达到这种结果要少受责备”。(23) 2.放任本身具有两种不同的表现:一种是对附属结果持否定态度,一种是对附属结果持模糊态度。这两种不同的表现,在规范评价上也应该得到不同的体现。而对这些区别的忽视,势必导致间接故意的处罚加重。对于这两种不同态度的具体评价问题,我想布拉迪的见解不无参考意义:“在同一风险的情况下,行为人根本不关心的态度,反映了较高程度的漠视,而希望结果不要发生但这种关心未达到阻止其行为的程度的漠视,程度则相对地较低。希望结果不要发生的漠然较之于对结果是否发生根本就不关心的漠视,责任更轻。但对于风险不同的情形,希望结果不要发生就不是一个减轻情节。一个人不正当地实施风险性很高的冒险行为,即使他不希望结果发生,他的罪责将大于一个人去实施一个风险性不大但他根本就不关心的冒险行为。可以举一个更为直白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行为人行为时,明知有实际的必然性(practical certainty),但他希望发生奇迹而不要发生结果。较之于一个人认识到这种危害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而不关心,我们将会要求其承担更为严重的责任。前者,漠然性的程度较之于后者更高。……漠然性程度的另外一个例子:一个人认识到了不合理的冒险,但他没有停下来对之进行考虑,和一个人认识到了这种不合理的冒险,并想到这种危险,仍然决定实施行为。后者有更大的责任,表现出了更高程度的漠视。”(24)
其次,规范理论的核心在于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放任故意与轻信过失的区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对于某种行为的期望值的高低。“就一个行为而言,在认识到单纯的侵害可能性时,还必须有其他的非价要素的存在,如此才能表现出一个够强烈的意念要素。”(25) 这里所谓的其他非价要素即规范责任理论中所谓的“附随情状”,比如行为的最终目的是否非价(例如为抢劫后杀人灭口中的抢劫行为本身是被禁止的,而交通肇事中的道路交通行为是被许可而且有益的)、行为人是否准备自行承担风险(例如违章驾驶的交通肇事者其本人面临同样的风险,而驾驶不会伤害到自身的坦克车更有理由对其作出更为严厉的非难)、对被害人所拥有的行为支配程度、社会对风险的习惯程度、可能侵害的法益的种类,等等。这些客观情状如何,都将可能直接决定着放任故意抑或轻信过失的判断以及放任故意的可谴责程度。
四、结语
间接故意的责任基础既不是一个单纯的心理问题,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规范问题,而是这两者综合评价的结果,其中,前者是前提,后者是根本。刑法归责不仅仅是法律规则的逻辑演绎,刑罚的正当性及其限度,必须在刑法之外寻求。撇开心理事实必将重回以结果论责任的老路,不单刑事责任的制约机能无从发挥,雅科布斯所谓的训练民众法律忠诚之目的也将落空,因为刑罚的投入,只有在可能达到改变行为的效果时,才有意义且合乎理性。而仅从心理事实来探讨放任故意的责任问题,将是不全面的,心理现象作为一种事实而言,其本身并无价值蕴涵,放任故意的非难基础及其具体判断,主要仰赖于一定历史所形成的伦理的、道德的、文化的秩序以及当下社会的政策需要。对于规范评价的忽视,恰如对于心理事实的忽视,将同样导致间接故意和直接故意的刑事责任承担在理论上或者事实上的不加区分。
《意见》首次以规范性文件明确间接故意犯罪与直接故意犯罪在量刑上应当有所区别,特别是考虑到该意见是在两起造成重大伤亡后果、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的醉酒驾车死刑改判案件的基础上,在结果责任论仍对当下司法实践发挥着深厚影响的背景下作出的,尤其难能可贵。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仅仅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首先,该意见仅针对醉酒驾车案件,能否推及其他间接故意犯罪案件,尚有待检验,毕竟,实践中因间接故意杀人被判处死刑的案件并不鲜见;其次,《意见》主要是基于传统的责任理论即心理责任理论的角度提出区别对待这一原则的,因而带有先天局限性,为了增强黎、孙两案改判的正当性,《意见》不得不在间接故意之外,从醉酒状态、认罪态度、赔偿损失,被害方谅解等方面寻求支持。最后,刑事归责的理论研究在我国有待进一步深入。其中,如何在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基本前提下,将规范要素引入我国的刑法理论之中,将之作为我国罪责理论的建构基础并实现其具体化和司法化,尤为迫切。鉴于此,本文与其说在试图找寻问题的答案,倒不如说是提出了探讨问题的方向。
注释:
① 其中,黎景全醉酒驾车肇事后,不顾伤者及劝阻村民的安危继续驾车行驶,致2死1轻伤;孙伟铭长期无证驾驶,醉酒驾车与其他车辆追尾后,为逃逸继续驾车超限速行驶,先后与4辆正常行驶的轿车相撞,致4死1重伤。
② 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③ 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理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1页。
④ 参见洪福增:《刑事责任之理论》,台湾刑事法杂志社民国77年版,第24页。
⑤ 心理责任论受到的批评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无法对无认识过失的责任性作出说明;仅把责任作为心理现象来把握,没有完全摆脱通过外部现象决定责任的结果责任论的窠臼;仅有心理事实之存在,尚不能说明责任之全部,责任的内涵,除了心理的要素之外,尚需考虑规范的要素。
⑥ 详见尹东华、刘为波:《放任问题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我国学者储槐植教授也持类似观点,参见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8页。
⑦ 我国现在通行的教科书均认为,轻信过失的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认识有两种情况:包括抽象危险和具体危险,对此,笔者持反对意见。对有认识过失的认识因素作抽象风险意义上的理解,已经日益成为共识,当然笔者主张有认识过失的认识对象是抽象风险而非具体风险,有着更为深层的考虑,即试图在理论上廓清间接故意和轻信过失的界限,寻求一个间接故意和有认识过失责任分野的阐述支点,避免轻信过失的传统理解在对“认识到具体风险,而轻信其不会发生“解释上的被动——既然认识到风险发生是实际的,又何从谈起轻信其不会发生呢?即使这是一种轻信,那么它与放任在质上又有何种区别呢,更为直白地说,这又何尝不是放任呢?只不过放任的程度上有异罢了。毋庸讳疑的是,对抽象风险和具体风险的区分,在可操作性上存在很大不足,然而这并不能成为我们追求罪过理论的完美与纯化的障碍,更何况,下面将进行的从规范层面对期待可能性所作的阐释,可以有效地克服这一不足。
⑧ 冯军:《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另参见林亚刚:“对‘明知必然发生而放任发生’的再认识”,载《法学评论》1995年第2期。
⑨ 刘为波:“放任包括不希望的态度”,载《法学》1999年第11期。
⑩ 本文仅对规范概念作一粗线条的勾勒,规范概念的具体展开,参见刘为波:“规范主义刑法与刑法价值观”,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4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以下。
(11)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延弼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26页。
(12) 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
(13) 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3-54页。
(14) [日]大塚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15) [德]格吕思特·雅科布斯:《行为责任刑法》,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16) 同上注,第51页。
(17) 同注(15),第47页。
(18) 参见黄荣坚:“刑法解题——关于故意和过失”,载《辅仁法学》第8期。
(19) 冯军:《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166页。
(20) 许玉秀:“客观的故意概念——评德国的间接故意理论”,载《政大法学评论》第48期。
(21) [英]J·W·塞西尔·特纳:《肯尼刑法原理》,王国庆、李启家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4页。
(22) [英]鲁珀特·克罗斯、菲利普·A·琼斯:《英国刑法导论》,赵秉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2页。
(23) James B.Brady,Recklessness,Negligence,Indifference,and awareness,The Modem Law Review(Vol.43)381,p.388.
(24) [德]许乃曼:“刑法上故意与罪责之客观化”,载《政大法学评论》第50期。
标签:法律论文; 间接故意论文; 酒驾论文; 犯罪主观方面论文; 法律适用论文; 风险评价论文; 风险社会论文; 刑法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