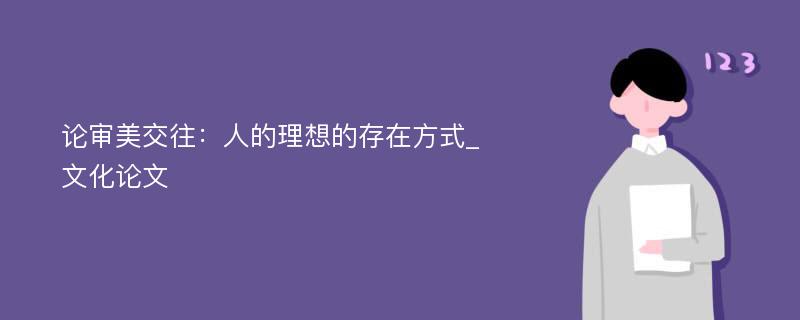
论审美交往:人理想的存在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想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交往是人与生俱来的命定。人不能脱离交往,就如不能离弃活动一样。一旦放弃了交往,人的活动在事实上就停止了,生命也就完结了。交往不仅是作为社会的人的本性,它简直就是人的本能需要。高尔基在他的一篇作品《伊则吉尔老婆子》中讲述了“鹰之子”的故事:
“鹰之子”腊拉是那么傲慢、任性,他被骄纵惯了,总是任意地追逐草原上的少女,又随手抛弃,并且他从来没有受到过少女的拒绝。一次,当一位少女因畏惧而推拒了他的拥抱,鹰之子竟残暴地踩死了她。草原上的人被激怒了,他们将鹰之子捆绑起来。但是,最终没处死他,而是给他另一种惩罚:给他自由。人们把他撵出部落,永远放逐了他,永远不许他与人接近,交往。
剥夺交往的权利,是对人最严厉的惩罚,这甚至比剥夺人的生命还要严酷。在死或禁止交往这两者之间,鹰之子宁肯选择死。然而,他不能,连死都不欢迎他。他只能永远孤独地活着,像个影子孤独地在草原上飘荡。他与生之欢悦永远分手了。他的名字“腊拉”意思就是“被抛弃”、“被放逐的”。人是生而自由的,自由是人的本性。但是,当鹰之子重新得到自由而失去交往时,自由反倒成为他所厌弃的该诅咒的东西。
自由最基本的含义即交往的自由。没有交往的自由不是人的自由,而是放逐,人非但厌弃它,甚至像逃避瘟疫,逃避魔鬼缠身般地躲避它——人不能没有交往;而现实的交往又限制了人的自由,总要给自由套上缰索笼辔。人永远处在这两难选择之中。
中国古代的隐士式生活或是一种调解方式。隐士生活是“隐”而不放弃交往,是一种有选择的交往。它逃脱了官场上更加不自由的异己的交往,选择了相对自由的山川林泉、江湖草野的交往。“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笑一声。”(李翱)自由自在地生活于大自然,与自然展开无拘束的交往,这是厌倦于官场生活的士大夫所向往的一种理想生活。借此可以逃避官场中四伏的险象,摆脱压抑、扭曲人性的繁缛虚伪的礼仪。然而,隐居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矛盾,只不过相对于官场那种极不自由的交往,相对于那种“居官一二载,则举止圆熟,言语低回,无复有山野之气”(注:《巽斋文集》卷一,《通荆溪吴运使书》)的异己的交往而言,隐居则稍稍让人暂时获得一种刚从重压下脱出的轻松感。其实,它只是重新进入了正常的而决非自由的现实交往罢了。
英国绅士的“豪猪式”交往也不失一种调解方式,即不是不交往,而是采取一种有距离的交往,欲求兼容交往和自身的独立。然而,“豪猪式”的交往只是一种外交礼节性的虚假的交往而非心心相印的交往,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交往。它没有心灵与心灵的撞击,更不能使交往双方两情欢洽。
在《沉思录》中,马克斯·奥瑞留写道:
人为自己寻求庇护之地,在田野、海边和高山上建造房屋……但这完全只是人类很平常的一种外在标志,而人在自己的权限之内,无论什么时候都选择退缩到自身之内寻求庇护,因为当他遇到挫折时,没有什么地方能比退回到自己的灵魂中去更感到宁静和自由了。(注:转引自夏洛特·布勒《人本主义心理学导论》,华夏出版社1990,P.58)
中止社会交往,退回内心,其结果只能是孤独。然而,即使在孤独中,人类也并不放弃一切交往。人不能忍受没有任何交往的彻底的孤独。孤独驱使人皈依上帝,人于是可以同心造的幻影相交往;孤独为人编织出白日梦,人于是有了一个可以自由生活于其中、自由地交往的虚幻世界,这正是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应该说,作家、艺术家的创作,首先是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可以自由交往的虚幻世界——作品,然后才以自己的作品与他人交往。
福楼拜在致路易莎·科拉的信中写道:
我过的是一种表面上失去任何欢乐、单调而乏味的生活。唯一支持我活下去的就是我内心那种永不平息但有时因无能为力而发出的呻吟声的长久激情。我用一种强烈的、变态的爱,爱着自己的工作就像一个苦行僧爱他那件刺身的粗毛衣似的。(注:转引自雅科布松《情感心理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P.213)
同自己心灵孕育的世界交往,这成为作家、艺术家极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精神慰藉。由于作家、艺术家从中体验到至深的愉悦,以至于他甘愿为此而舍弃现实交往。
同样,对读者、欣赏者来说,作品则成了他自己而非创作者的白日梦。他就生活于这梦的幻境中,与梦幻世界交往。无论创作者和欣赏者,作品中的世界不再是自在的世界,而是与我密切相关的世界,它同我一样享有人性、主体性:“溪水无情似有情,入山三日得同行。”(温飞卿)“雨中百草秋兰死,阶下决明颜色鲜,着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杜甫)原本没有生命的,在作品中被赋予了生命;原本没有人情的,在作品中被赋予了人情,于是,世界万物我都可以与它对话交往,同悲共喜,心心相印。“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
在审美天地里,我不占有对方,也不臣报于对方,一切存在之物都已转化为“你”,一切交往也都成为理想的自由交往。就如金圣叹在《鱼庭闻贯》中所说:“人看花,花看人。人看花,人到花里去;花看人,花到人里来。”(注:金圣叹《鱼庭闻贯》)这就是审美交往:人的理想的存在方式。在审美交往中,人既实现了他的交往的本性,又不必放弃自身的自由。审美交往是自由的交往,理想的交往。在审美交往中,人始终以自由的主体身份创造着,同时以自由的主体身份与所创造的审美对象相交往,由此充分地展开了自己的感性存在,发展了自己的感性存在。由于他所创造的审美对象原本是虚幻的世界,因此,当人投入其间时,他就不必再惴惴于因受他人的注视而沦为对象;也由于审美对象是虚幻的世界,人虽创造了它,却不据有它。人一无所持,却与对象处于关系之中。在审美世界,人始终以自由的方式创造着、交往着。正是这一自由的方式,使对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审美对象已不再作为“对象”而存在,它转而成为自由的主体。这是自由的主体与自由的主体间的自由交往,也即马丁·布伯所说的“我—你”关系。他们既是不同的两者,同时又是一体,在和谐的交往中,人充分地享受着真正的自由,体验到由衷的精神愉悦。
在《我与你》中,马丁·布伯对“我—你”关系作了精辟分析:
如果我作为我的“你”而面对人,并向他吐诉原初词“我—你”,此时他不再是物中之物,不再是由物构成的物。
他不是“他”或“她”,不是与其他的“他”或“她”相待的有限物,不是世界网络中的一点一瞬,不是可被经验、被描述的本质,不是一束有定名的属性,而是无待无垠、纯全无方之“你”,充溢穹苍之“你”。这并非意指:除他而外无物存在。这毋宁是说:万有皆栖居于他的灿烂光华中。(注:马丁·布伯《我与你》,三联书店1986,P.23)
“我—你”关系不同于“我—他”关系。在“我—他”关系中,他已沦为对象,沦为物。于是,我与他之间已壁立着主体与客体之鸿沟。“我—你”关系也不是“我”与“你”的关系。“我与你”实即“我—你”解体之后的机械组合,“我”已从“我—你”关系中分离出来,于是,“你”也就成为对象,成为物,成为它。唯有“我—你”关系中,“我”是我自己,“你”也是你自己,同时,我、你之间又构成了浑整不分的关系。这正是“不知我为蝴蝶,蝴蝶之为我”的审美至境。在这种以“我—你”方式展开的审美交往中,我凝神观照,醉心体验,而我又存在于被观照、体验的审美世界内,栖居于灿烂的光华中。我所观照、所体验的不是对象的形式或内容,字词或意义,而是不可分割的审美世界本身。这里,任何占有的欲念敛息了,任何阻障的中介坍塌崩毁了,我与审美世界直接相遇、照面。这里,我、你相互激发着,我敞开了我自身的全部丰富性,你也敞开了你自己的全部丰富性,我你间实现了全面的交往和交流。
杜卡斯说:“审美观照是对某一事情的出现采取全然的开放态度。”我的“注意力被凝聚在审美观照的对象之上,其内心世界早已清理出一块领地,随时准备接纳对象的情感价值。”(注:杜卡斯《艺术哲学新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P.112)我向对象全然开放,同时也使对象向我全然开放,使对象转化为“你”。当我的身心存在整个地投入于理想的交往之中,那震撼我、融化我的审美愉悦就悄然降临了。
审美交往是在人类交往活动发展演变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
在原始时期,人与自然浑融一体,人就蛰伏于自然母胎之中未经分娩,所以,庄子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注:《庄子·天地》)随着实践的发展,人逐渐将自己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人终于成为了人自己。然而,人与自然的这种区分还是初步的、不稳定的。对原始人来说,世界万物既渐趋清晰,又互渗互融,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存在着神秘的关联。这就是列维—布留尔所说的原始思维的“互渗律”:
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注: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P.69-70)
这是人类从混沌走向明晰,从蒙昧走向智慧的过渡性阶段。人通过自己的实践,特别是通过语言创造,终于让自己从自然中独立出来并超拔于动物界。就如刚刚脱胎而出,发出第一声啼哭的婴儿只能偎依于母亲怀抱,原始人也仍只能依附于自然,与自然、与万物相互感应,相互融合。人既与自然、万物相分离,又似乎连结为一体。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原始岩画、原始舞蹈尚未包含审美活动,而只是人与自然万物“互渗”的神秘关系的体现。人通过刻画狩猎的岩画、祈祷收获的舞蹈,企图为实际的狩猎、收获提供保障。
当人类实践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大,人与自然间的区分日渐明晰,人终于成为独立存在的时候,这才是真正体验到人自身的软弱无能,感受到脱离母胎之后的惊恐无援。人把自己的影象投射给自然万物,又震惊于自然万物的灵性,进而将万物视为神。自然界辽阔而神秘,令人深感自己的渺小;自然现象倏忽变幻,则令人深感敬畏。自然主宰着原始人类的命运,它或平和或震怒就决定了人的福和祸。人不得不匍匐于自然神之前,虔敬地加以礼拜。
这是人与自然间的不平等交往。人在他刚刚诞生之时,就折服于自然,与自然处于“人—神”关系之中。在这不平等关系中,还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的审美。
“人—神”关系在宗教活动中得到了强化。固然,艺术与宗教密切相关,并且常常借助宗教的力量,艺术才得以发展。但是,当人以审美的自由来欣赏神而不是以敬畏之心拜谒神时,他就已包含着对神灵的亵渎和对不平等关系的挑战,实际上把自己摆放到与神相对待的地位上了。虔诚的信徒永远跪拜于神灵之前,仰望那灵光笼罩着的神秘不可知的命运之神。神是他者,一位高高在上的主宰者,而人则只能温顺的默默承受主宰者的惩处之鞭。事实上,人只有摆脱了崇拜而逐渐成长为独立的人,他才具有独立的创造,才可能创造出“美的神”,艺术和宗教才会相互促进,尽管在这相互利用的背后隐含着根本的对立和冲突。可以说,当宗教艺术最为辉煌的时候,就表征着人类自身独立性的增长,表征着对神的地位的怀疑和动摇,也预示着宗教的衰落。
布克哈特在谈到宗教和文艺复兴精神的关系时说:
这些近代人,意大利文化的代表者,是生来就具有和其他中世纪欧洲人一样的宗教本能的。但是他们的强有力的个性使他们在宗教上完全流于主观,象在其他事物上一样,而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发现在他们身上发生的那种巨大魔力使他们特别趋向于世俗化。(注: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P.481)
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即秉承了前辈传袭下来的宗教本能,又有着强有力的个性、主观性和世俗化倾向。在他们身上明显看到宗教衰落时期的矛盾:偏于主观的个性是对宗教本能的反叛,而世俗化倾向则直接是对宗教崇高精神的挑战,这不仅在于追求自身生活的世俗化,同时也将信仰现实化,把天堂人间化,把高高在上的神拉回到平常人的位置。这种人神关系的变更,恰恰是促成一代文化伟人和他的艺术杰作诞生的重要原因。
宗教和艺术有密切的联系,乃至有许多共通点、共同点,但是,恰恰在审美精神上两者相互抵牾:
从表面上看,用于教堂服务中的音乐似乎是宗教的一种装饰,实则是对它的一种替代和批评。全体教徒的合唱,同时又是与宗教言词之意义的远离。在这儿言词决不具有最后的发言权和决定权,一种宗教如果遵守那种所谓“不要改动言词的意义”的箴言,就很可能把这种本是“解放的要素”转变成“压迫的工具”。因此,对宗教言词是需要批评的,而这种批评最终又是由音乐完成的。宗教教义的宣讲越是受音乐的强制,它就越具有人性味儿。(注:赫·曼纽什《怀疑论美学》,辽宁出版社1990,P.221)
审美是自由的精神交往,它抗拒任何权威、任何强制和不平等,呼唤一种新的主体间的关系。
生存作为人类第一需要,它迫使人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自身的生存而展开,教人以“势利”的眼光看待世界。当神的灵光渐次消褪,神不是降落到人间,成为与人平等的“另一类”,而是成为人的对象,成为物。“万物有灵”业已成为过去,自然神也早遭贬谪,自然转而成为人掠夺的对象,役使的工具。“人—物”关系、“人—工具”关系是“人—神”关系的倒转,人将自己册封为“神”,世界万物则成了任人占有、利用、改造、控制的对象,成为物和工具。这种关系同样弥漫了人类社会,人世间也唯有“神—人”关系或“人—工具(奴隶)”关系。于是,人竭力幻想自己成为凌驾于众生之上的神,而将旁人贬落为自己的奴隶和工具。在“人—物”或“人—工具”关系中,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审美。当世界沦为对象,沦为物,沦为工具时,它就对人锁闭了。除了“有用性”,世界万物和它的丰富内涵、意味都被遮蔽了,逃遁了。石头已变得不再是石头,而成了概念空壳。
无论人将自然视为神,将他者视为神,或把自己视为神,都是自由的失落。人与世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相互倾轧、征服、颠覆,人人都面临着被奴役的危险,人人都陷落到生存困境之中。于是,原始时期人与自然浑融一体的和谐,则成为在现实中无法寻觅的理想的生存境况,成为人魂牵梦萦的美好忆念。然而,一旦人呱呱堕地,他就已无法重返母胎。人于是为自己保留下一条虚幻的回忆之路,这就是审美交往。在审美交往中,人与自然、人与万物、人与人都处于马丁·布伯所说的“我—你”关系之中,我和你都是独立的主体,并在我你之间展开了自由的尽兴忘情的交往。自然、万物和人自身都在此交往中敞开了自己,共同迈进了物我两忘、浑融无间的大和谐。
马丁·布伯把“我—你”称作原初词,把“我—你”关系视为原初关系。他说:“泰初即有关系。它为存在之范畴,欣然之作为,领悟之形式,灵魂之原本;它乃关系之先验的根,它乃先天之‘你’”。(注:马丁·布伯《我与你》,三联书店1986,P.43)从客观上看,世界的本源即存在关系。但在人成为独立个体之前,这关系并不能被体验为“我—你”关系,甚至还不能作为关系被体验,因为人原本与自然浑然相融,无法区分。所以,审美交往中的“我—你”关系并非如马丁·布伯所说是重返原初关系,而是对浑融关系的追忆恋念。这是主体充分发展,成为独立的个体并因此体味到人的孤独、关系断裂所带来的痛楚之后,对原初关系的理想化和美化。作为脱离了自然怀抱而被抛入世界的孤独的人,他不能不为自己创造梦境,一个追索原初和谐的亘古之梦。
由于审美交往是在人类交往活动中分化而形成的,它的形态也必定是丰富多采的。
审美交往最典型地体现在关于美(优美)的审美活动中。美即和谐,这不仅表现在对象本身的和谐,同时也表现在人与对象间关系的和谐。在人与美的对象之间存在异己的对抗因素,不存在任何阻隔,两者相互吸引,相互交融,从而展现为一种理想的交往。悲剧也相似。悲剧重要的审美特征之一就是悲剧同情。没有同情,就没有悲剧。这也就要求欣赏者与对象建立平等的“我—你”关系,建立审美交往关系。
关于崇高的审美则不同。崇高首先是一种高于人的对象,它给人以震慑、威压,同时又激发了人,振奋了人,而只有当人具有把自己提升到与崇高相对待的位置,崇高才终于成为审美对象。实质上,关于崇高的审美过程展现为从“神—人”关系到“我—你”关系的转换,就如康德所说,崇高感是由压抑转到振奋,由痛感转为快感的。人类在相当漫长的时期里,与世界万物处在“神—人”关系之中,而只有当人具有了将“神—人”关系转化为“我—你”关系的心灵力量,崇高型审美才得以生产。正因为需要实现这一转化,所以,鲍桑葵把崇高称为“艰奥美”。因此,从发生学角度看,人对崇高的把握是在优美之后。在人与世界建立了和谐融洽的“我—你”关系之后,并且只有当这一关系培植起人的心灵力量之后,人才有能力实现这一转化。
对喜剧的体验则表现为从“人—物”关系到“我—你”关系的转换。喜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模仿比一般人差的人物,也就是说,人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喜剧的对象,这一关系究其实也即“人—物”关系的衍生。然而,如果不能将喜剧对象转化为“我—你”关系中的“你”,不能倾注以同情,喜剧对象也就不能成为审美对象。这也正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喜剧对象是“丑”而非“恶”的原因。因此,审美交往诸形态正是人类交往活动发展、分化,又相互渗透、转化的结果。
审美交往是一个既开放自我又免除了自我异化威胁的理想交往。就如弗洛姆所说:
人类存在的最本质问题在一种艺术和戏剧的形式中得以表现,观众——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消费者式的观众——参与了这种戏剧表演,他被带出了日常习惯性生活的范围,使自己与作为人的自己以及自己存在的本质联系起来。他的脚又站在坚实的基础上,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他被带回到了自我中,他又获得了力量。(注:弗洛姆《资本主义下的异化问题》,见《异化问题》下,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P60)
文学艺术是一个区别于日常习惯生活的虚构世界,它有自己的独立法则。在这里,现实的角色规范已成为没有约束力的虚设,欣赏者在同作品人物相交往时,不需要遵循任何角色规范。他始终是一个自由自主的主体,始终从自我出发,以自我的本性与对象相交往。在日常生活中摆脱不了的角色面具,如今已自然脱落,审美交往令他实现了“现象学的还原”,重新返归自我,同自己的本质相联系。这种从人的自我本性出发,既充分敞开自身又不舍弃自我的审美欣赏活动,正是抵御现实异化、维护人的本真存在的重要的生存维度。
在审美交往中,人物对象的每一生命经历,都将转化为欣赏者自己的体验。只要欣赏者洞悉人物每一细微的情感波动,或者稍纵即逝的潜意识闪现,他实际上也就更深入地发现了自我的内心世界,拓展了自我的内心世界。由于欣赏者在审美交往中的对象也就是欣赏者自己同创作者共同创造的,交往双方也就感觉不到而且也不需要任何外加的准则、规范。这是一种完全自由和平等的交往,它只发展人自身而不压抑人。它不断深化、开拓着人类本性而决不悖逆人类本性。阿格妮丝·赫勒指出:
艺术是人类的自我意识,艺术品总是“自为的”人类本质的承担者。这体现在多方面。艺术品总是内在的:它把世界描绘成人的世界,描绘成人所创造的世界。它的价值尺度反映了人类的价值发展,在艺术价值尺度的顶峰,我们发现了那些最充分地进入了人类本质繁盛过程的个体(个体的情感、个体的态度)。(注: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重庆出版社1990,P.114-115)
审美是个属于人的世界,它以人的价值抗拒着各种“实用价值”,以人的情感、人的态度、人的理想把受到种种角色分割的人的碎片重新凝聚为整体,以个体与个体间的平等自由的交往,将被异化社会异化的个体还原为人本身。
如果说,日常交往必须遵循的规范是社会律令的话,那末,审美交往则遵循美的律令。而美的律令是从人类本性出发的,它即人自身的内在尺度,人自身的生命节律,体现着人的自由和完美善。因此,审美交往也即遵照人自己的类本质,要求人返归自己的类本质,指示人沿袭自我本性而发展。当人复归于自己的类本质之中,当人依照自己的类本质展开交往活动,他所体验到的正是人的自由、完满和和谐。
当然,审美交往并不能替代现实社会的交往,而且审美交往所赋予个体的经验,由于它的虚幻性,在现实交往中往往显得毫无用处,并常常为现实所粉碎。但是,审美交往所涵养的人的天性和童心,恰恰是人抗御异化的力量。审美交往始终是从人的类本质出发、从个体自我出发的交往,它不断增强着个体的自我同一性。当人重返现实生活,就有可能使他在现实交往中既保持着独立性,又因广为接纳、同化外物而发展自我,因而,审美交往始终是人类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活动。
审美交往又是创造性的交往,缺乏想象力、创造力,就难以进入审美交往。可以说,人的心灵的深度决定着交往的深度,想象力、创造力的边界也就是与他相交往的审美世界的边界,只有不断拓展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才能使审美交往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
想象、创造是审美交往的出发点,而审美交往又进一步激发、发展了人的想象力、创造力,正是在审美交往中,人的创造潜能得到了充分发挥。鲍列夫说:
由于艺术文化能使人的精神始终具有创造力,它好像成了文化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动力来源。(注:鲍列夫《美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P.497)
当然,审美交往所培植的创造精神,不仅仅是人进行文化再生产的动力,更重要的是它开放了自我,推进了自我的发展,从而成为人类发展的巨大动力。审美交往是一个向无限开放的领地,人一旦进入审美交往,在它面前就打开了新的世界,它也就把自己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审美交往又具有超越性特点,它消解了现实交往的确定性和时空限制,使人摆脱了偶然性的束缚,无止境地拓宽了交往的时空疆域,使交往成为不受时空制约,可以自主选择的自由交往,成为向无比广阔的领域、无限多样的形式开放的交往。
在审美交往中现实恒定的物理时空已不复存在,对时间、空间的体验完全让位于对创造的体验,依据创造性交往活动的强度来衡量,因此,当人全身心投入到审美交往,沉溺于创造的欢娱中时,他也就体验到人的永恒和无限,存在的永恒和无限。如果说,审美交往的创造性特征使人体验到无限、永恒、完满的话,那么,对无限、永恒、完满的体验反过来又成为人追求无限、永恒、完满的创造性活动的动力,推动人永远向未来开放。
乔治·桑塔耶纳说:
我们能够解脱掉偶然穿上的尘世衣物越多,历万劫而长存的精神就越坦露而纯朴;它的优越性和同一性就越臻于美满,从而它的快乐就愈无可限量。那时在我们心中留下的尘念不多,只有那种纯理性的精华而已,有几位伟大的哲学家曾称之为永恒的与神性同一的本质。(注:乔治·桑塔耶纳《美感》,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P.161)
人没有一经获得就永世不变的确定形式,他处于不断的流动发展之中,并且永远地寻找自己。审美交往既为人提供了尘世自我的影象,又预示了人的未来的形象,并将“永恒的、与神性同一的本质”约许给人类。
交往需要与爱欲紧密相连,可以说,爱欲是交往需要的根基。爱欲推动两性间的交往,使人类得以繁衍。正如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由爱欲所推动的两性交往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社会交往的基础。然而一旦性交往扩张为社会交往,后者也就超越了前者而具有独立的品格和意义,这就造成交往需要与爱欲之间质的区别:爱欲乃属于生物本能,交往则成为社会“本能”;爱欲的满足所获得的是生理快感,而交往需要的满足所获得的是精神愉悦。由于审美愉悦来源于审美交往,因而它也就必定是精神性、社会性的。
可是,在弗洛伊德看来,艺术创作是创作者的“白日梦”,是由于人的性本能受到压抑,不能得到释放,于是,不得不以白日梦这种变形的方式加以伪装,并由此解除内心紧张,获得替代性满足,产生愉悦。欣赏者阅读作品的愉悦则是“由于作家使我们从作品中享受到我们自己的白日梦而不必自我责备或感到羞愧。”(注:《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知识出版社1987,P.37)总之,审美愉悦最终只能归结为爱欲,也即性本能的满足。
维戈茨基抛弃了弗洛伊德片面强调性本能的理论见解,把审美愉悦归因于神经能量的舒泄和消耗。他认为:“艺术在其直接作用上是违反节约力量原则的,在艺术形式的构成上正好服从相反的原则的。我们的审美反应,首先是作为破坏而非保存我们的神经能量的反应向我们显示出来的,它像爆炸,而不像斤斤计较的节约。”神经能量的舒泄和消耗越多,“艺术就越使人感到惊心动魄”,审美愉悦也就越强烈。(注:维戈茨基《艺术心理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P.268)尽管维戈茨基不赞同弗洛伊德的观点,但他同样是从生理方面探讨审美愉悦的根源,这就势必将审美精神愉悦降格为一种生理快感。
审美愉悦是复杂的多层次的体验,自然包含着生理快感,但它首要的是一种对理想的审美交往的体验,是由这种体验所生的精神愉悦。生理快感只是一种低层次的体验,决不能替代审美愉悦。审美愉悦作为精神愉悦,只能是精神与精神相交往、相撞击的结果。即使同自然交往,也只有当自然为人的情感所浸染,为人的精神所渗透而成为精神性对象时,才能激起人的审美愉悦。
虽然审美交往与爱欲相关联,但从本质上看,它已超越了作为个体本能的爱欲而成为一种特殊的人类社会性活动,是体现于人身上的社会性需求。因而,审美交往就不仅是个体的,而且具有社会性。审美交往的个体特征中就积淀着和包含着社会特征。个体与个体间审美趣味的共通性,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社会审美判断的共同准则,正是审美交往衍生的产物。不仅如此,即使审美趣味的历史演变,审美风尚的出现,也只有在审美交往中寻得解释。这不仅是因为人对精神交往的需求总是同社会历史状况密切相关,而且在于正是通过审美交往,才使审美趣味不断变更、分化、融合、冲突、发展。如果局限于生理层次考察审美活动,一系列问题都将坠入五里云雾。
埃斯卡皮说:
阅读一本作为独创性作品,而不作为旨在满足某一需要的实用工具的书籍时,要求读者到另一个人的家里去,求助于另一个人,于是得从自己家里走出去。(注: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P90)
读者走出“自己的家”而进入“另一个人的家”,其实就是进行审美交往。交往使人的审美趣味、审美能力得以融汇、整合,使个体抛弃了自己的狭隘性和片面性,进入到一个更高层次的精神交往之中,所以,“当我们‘欣赏’艺术品时,我们同它的作家一样被提升到类本质水平。”(注: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重庆出版社1990,P.115)作品世界是欣赏者与创作者精神交往的中介。当创作者为自己创造一个可以厕身其中并与之交往的世界时,他就已经摆脱了自身的局限,摆脱了各种欲望的束缚,以审美创造把自己提升到类本质水平,并把类本质注入于作品之中;欣赏者要欣赏作品,充分地享受作品,也必须把自己提升到一个能与作品交往、对话的境界,并通过交往更为深化了自己的类本质。这也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视界融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灵魂的融合”。无论是意识还是潜意识、理智和情感,在审美交往中都得到了重塑。审美愉悦也正是在这审美交往中,在这灵魂的交融、提升的过程,人类所获取的弥足珍重的馈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