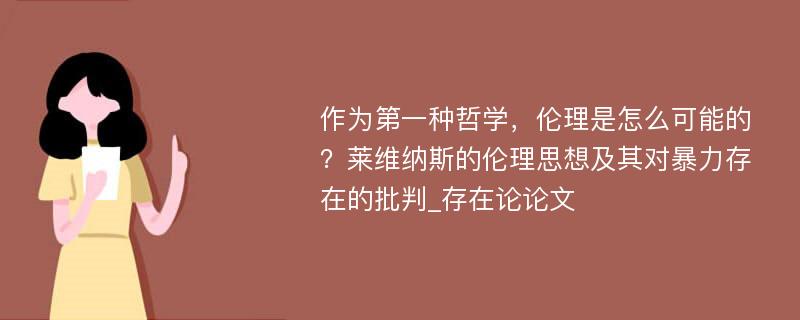
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如何可能?——试析勒维纳斯的伦理思想及其对存在暴力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纳斯论文,伦理学论文,其对论文,伦理论文,暴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6)06-0024-09
这是一个“他者”成为问题的时代。更准确地说,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日益成为问题的时代。这个问题绝不只是一个纯粹理论思辨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在“自我”不得不面对一个个陌生的“他者”时,“自我”如何与这些“他者”相处?在这个伦理、政治、宗教等实践问题日益成为哲学焦点问题的时代,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欧陆哲学界,不仅现象学发生了“神学转向”,解构主义也发生了“伦理学转向”。勒维纳斯关于他人、伦理、责任等问题的一系列思想,因此仿佛被重新发现般一下子从边缘状态成为欧陆哲学讨论的热点。与此相应的是,在近年来的国内哲学界尤其是西方哲学的研究领域,与他人或他者有关的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也日益成为热点。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国内的西方哲学研究正呈现出某种向政治哲学、伦理学等实践哲学转向的趋势。在此背景下,勒维纳斯的相关思想也日渐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和研究:从他的哲学思想与现象学的关系,到他的伦理学与形而上学及其对存在论的批判,甚至他思想中的犹太性等问题,都已或多或少有所触及①。无疑,这些研究几乎都注意到了勒维纳斯关于伦理学是第一哲学的思想。但是,勒维纳斯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认为伦理学是第一哲学?换言之,在勒维纳斯那里,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如何可能?对此问题,国内现有的研究主要还是通过讨论他人的不可还原性和我对他人所负有的责任来谈。然而,从他人的不可还原性就能推导出我对他人必然负有责任吗?进而,即使我对他人负有责任,那么这又是何种性质的责任,以致伦理学必须被视为第一哲学?对于这些问题,国内的研究还缺乏进一步的探讨,而这正是本文的目的。具言之,本文试图通过与勒维纳斯一道思考我们对于他人的责任在存在论上的“无端性”,以及这种“无端的责任”的可能来源,从而初步回答伦理学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可以称为第一哲学,进而希望能促进对相关伦理问题,尤其是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讨论。
一、存在的暴力
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关于存在的知识(存在论),或用勒维纳斯的话说是“对存在的把握(compréhension)”或“[存在]这个动词的语义学”[1]67,就一直被视为第一哲学。何以会如此,这里不加详论。我们只能简要地说,主要是因为从那时开始,存在——而且是作为纯粹在场(ousia)的存在——就被视为哲学所追求的第一因或本原/原则/开端/根据(archie)。[2]248-252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质疑存在论的首要性或基础性,首先就要质疑存在的本原性:存在真的是毋庸置疑的本原/原则/开端/根据,从而有其无上的统治权力?它的王权是否无疆无界,以致不仅万物要从其法则,而且他人也要服从其权力?是否存在的法则就是最初和最终的法则,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自明之理(truisme)?我们来随勒维纳斯一道看看,当把存在的法则视为最初和最终的法则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问世以来,“存在”就成了一个高贵的语词。按海德格尔的说法,存在不是存在者,存在与存在者之间有一存在论差异。但是据海德格尔说,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这种差异被遗忘了,存在被当成了存在者(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是纯粹在场的、纯形式的神)。所以海德格尔的努力就是要重提存在问题,拯救被遗忘于存在者中的存在。但是这样一个在海德格尔那里还要被重提和拯救的“对象”,在勒维纳斯那里却被体验为一种中性的、匿名的、吞噬一切存在者的无所不在的统治者。勒维纳斯早期将它称为无人称的“有(il ya)”,亦即“没有存在者的存在”:“存在的这种无人称的、匿名的、却是不可泯灭的‘毁灭’……我们应该用‘有’这个词来规定它。‘有’,因其拒绝采用一种人称形式,就是‘存在一般’(êtreen général)”[3]93-94,是所有事物以及“我”消失后留下的那个不会消失的东西,就像黑夜、力场,像一个不属于任何人的普遍的沉重氛围。[3]95海德格尔要从存在者回到存在,勒维纳斯却要从存在一般(有)挣脱出来而返回到存在者。但是,我们必须要立刻注意到,勒维纳斯的“有”又并不就是海德格尔的“存在”的法国翻译:“在海德格尔那里,焦虑产生出‘向着死亡的存在’,这种存在是可以把握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而那种对‘没有出口’也‘没有回应’的夜的恐怖,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生存”[3]102。这样一种没有出口、不作回答、吞噬和毁灭一切存在者的中性的“有”,对于具体的存在者来说无疑是暴力性的。
在那时(1946年),勒维纳斯还没有完全走出海德格尔的思想,所以他虽然体验到了作为“存在一般”的“有”对于存在者所具有的暴力,但还是小心地把这种“有”与海德格尔的“存在”区分开。但很快他就认识到,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亦即整个西方哲学一直追问的存在,在其conatus essendi(生存的努力)中同样充溢着权力意志。而当这种追求其生存的努力和权力意志被施诸于他人时,也就对他人施以暴力并犯有“谋杀”之罪了。他说:“纯粹存在总是在存在中的一种持存。这是我首要的论题。一个存在物是某种依附于存在的东西,依附在它自己的存在中。”“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的一开始就说,‘此在’是一种领悟自身存在的存在。……存在的目的就是存在本身”。[4]202存在没有外在目的。存在就是去存在,为其存在而存在,为其存在而斗争。为了能持续地维持其存在,存在者必须在其存在中同化他物,消灭他物的他性,使之转变为“为我”的环节或元素,同一到“我”的存在中来。这种对于他物的同化和同一,在人类存在中就表现为对工具的使用、对他物的享受,以及劳动和战争。如此,世界中的其他生物或物就为我据有,被我同一。[5]216于是存在史,尤其是人的存在史,就是一部“自由,自主,将他者还原为同一”[6]166的历史,对他者(包括他人)进行统治的暴力史。这一点在现代人的存在中几乎登峰造极。“人们”利用最先进的技术、最完备的体制(政治的、经济的),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统治他者、消灭他者的运动。“在其存在中,现代人一直是只关心确保其统治权力的统治者。所有可能的都是被允许的。对自然与社会的经验将会逐渐克服——或可能正要克服——任何外在性。这种现代西方自由的奇迹不受任何记忆与内疚的束缚,它向一种‘光辉灿烂的未来’敞开,在那里一切都是可以补救的。”[1]74
这是一场以存在本身为目的的斗争。勒维纳斯将之称为“没有伦理的生命斗争”[4]202:“这涉及一种将自身接受为自然的生存……涉及一种异教徒的生存。……存在指挥着它,毫无伦理上的顾虑,如一种英雄般的自由,与所有关于他者的罪责无关。”[6]170但问题在于,这种“自然的生存”真的“与所有关于他者的罪责无关”吗?这正是勒维纳斯要质疑海德格尔以及传统存在论之处。姑且承认,对于他物,我们可以(pouvoir),或者说有权通过使用、劳动、享受而消灭它的他性,将之据为己有,将之同一化。但是对于他人、对于一个向我们发出吁告、恳求的面孔,我们也可以对之施加我们的权力意志和暴力,也可以像对待他物那样对之进行摧毁、围猎吗?也可以将之作为客体进而作为我的财产、战利品、猎物或牺牲品而整合进我的存在的同一性之中吗?如果这样,勒维纳斯说,那就是谋杀,就是犯罪。因为,在其外在性中的面孔恰恰是对我的同一化的努力的抵制,是对我的权力的反抗:“汝勿杀”。这是一种伦理的而非实在的抵抗。[5]217正是这种抵抗使得存在的强权一旦施诸他人就必然犯罪。在这个意义上,勒维纳斯将存在的法则称为“恶的法则”。[4]206
存在的法则为何会被这样施诸于他人?勒维纳斯说,其根源在于人们“断言存在优先于存在者”,在于“把与某人(它是一个存在者)的关系(这是一种伦理关系)隶属于与存在者之存在的关系,这种非个人的存在允许对存在者进行理解/把握和统治(这是一种认知关系)”,于是这就使正义隶属于自由,使自由优先于伦理。勒维纳斯认为,这正是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后果。②所以他在另一个地方说,“在我们时代最有声望的海德格尔哲学中似乎有机地保持着这种同一对他者的霸权。当海德格尔探寻经由存在……来到达通向每一个真实的独特性时,……当他看到人被自由拥有而非拥有自由时,便将一个照亮自由而非质疑自由的中立者加于人之上。于是,他并不是在摧毁而是在总结整个西方哲学的传统。”[6]169③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在他人面前主动抑制我们存在的权力意志,不把他人同一到我的存在之中来,不把存在的法则施诸于他人,是否我的存在就可以免除有罪控诉,就可以在天地间无忧无虑地享受存在的快乐?勒维纳斯说:否!只要你存在,就已经对他人犯有侵占、剥夺、杀戮之罪,仿佛这是存在的“原罪”。
在《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中,勒维纳斯写道:“我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或者我‘在阳光下的处所’,我的家园,这些难道不已经是对那些属于另一个人(我对这另一个人已经施以压迫或使之饥馑,已经将之驱赶到第三个世界中了)的位置的侵占吗?它们难道不已经是一种排斥、驱逐、流放、剥夺、杀戮?”所以,勒维纳斯认为,帕斯卡尔所说的“我在阳光下的处所”就已经是“对整个大地的侵占的开端和图像”;于是,“对于我的实存——尽管它在意向上和意识上是无辜的——所可能完成的暴力与谋杀的害怕”,就总是“从我的‘自我意识’背后重新升起,不管在存在中的纯粹坚持多少次回到心安理得(la bonne conscience,或译为良好意识)。[这是]对我的此在之此占据了某人的处所的害怕……”[1]93是的,尽管在意向上和意识上无辜,但毕竟我的此在已经占据了一个此,因此已经是对他人之处所、之家园的占据与剥夺,已经是对他人的暴力与谋杀。所以勒维纳斯在同一处说,我们必须要对我们存在的权利作出回应,不是参照某种匿名法律的抽象,也不是参照某种司法实体,而是出于对他人的害怕。正是这样一种害怕,使得存在从其洋洋自得的良好意识(la bonne conscience)中苏醒过来,而回到一种更为本源的或前本源的愧疚意识(la mauvaise conscience)。这是对存在之原罪或者说实存之原罪——对于他人的原罪——的意识,但这又是一种无罪之罪:无罪,因为“它在意向上和意识上是无辜的”;有罪,因为它已经是“排斥、驱逐、流放、剥夺、杀戮”。勒维纳斯也把它说成是一种对于他人的亏欠:没有欠债的或借贷之前的亏欠。[7]143所以这也是一种永远无法偿清的亏欠:它欠的本来就不是一种可还清的债务。因此存在就意味着负有责任:对于他人的责任,永远的责任,更多的责任。
二、面孔:不可还原的他人
存在为什么不能以其自身为目的?为什么就不能以此为基础来构建一种伦理学,亦即,以存在自身的持存、以存在之权力意志的实现和自由游戏为衡量价值的最终和最高尺度?为什么必须要对他人负有责任?为什么要背负那种沉重的愧疚意识?这种意识如何产生?为什么不可以摆脱它?
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做,而且我们事实上也经常这样做。我们在阳光下自由自在地生存,在大地上无忧无虑地游戏,于权力意志之永恒轮回中游戏,并将此视为最高的价值:凡是能有利于或促进这种价值的就是善,否则就是恶——如果我们没有遭遇到他人,如果我们没有听到来自他人的呼告,没有被他人的赤裸的面孔所控诉、所抵抗的话。而且即便遭遇到这些,我们依然可以这样做:我们完全能够把他人同一化,把他人的他异性消灭,把他人还原为我的构成物。我们总有“理由”——但我们下面将会看到,在勒维纳斯的眼中,真正的伦理行为恰恰是“不讲理”的——为我们之施诸于他人的暴力、剥夺、杀戮进行辩护。但问题恰恰在于,即使在我们有理由或有权利这么做时,我们,人,却依然可以出于某种“没来由的”或“无端的”(anarchique)“愧疚”而不这么做,或即使这么做了也总被这种无端的愧疚所纠缠。何以会如此?勒维纳斯说,是因为自我在它的“前史/前世”中,总已经成为他人的“人质”,因此总已经对他人负有责任了。
于是勒维纳斯对于存在之优先性和暴力的批判、对于自我同一性的批判(也就是对伦理之优先性、伦理学之为第一哲学的阐明),就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首先,确定他人是否不可还原,与他人的面对面是否因此是终极的实事;其次,对自我的前史进行考古学研究,揭示那被传统存在论视为“端由”(本原、原则、开端)的自我或主体早已是被构造的结果,早已“无端地”成了对他人的“替代”和“人质”,从而前世注定且无可逃避地对他人负有责任。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他人如何可能的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难题。胡塞尔在《笛卡儿式的沉思》中尝试通过“结对联想”来说明白我是如何逐步构造出他我(他人)。这个尝试究竟成功与否,现象学内部一直争议不断,这里不想展开这方面的讨论。仅想指出的是,他人在胡塞尔那里最终是自我的主动构造的成就,并因而最终又还原到自我那里去。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勒维纳斯与胡塞尔针锋相对:他人不是自我构造的产物,因此也是不可还原的。
为了表明这一点,勒维纳斯诉诸于一种源初经验:我与面孔相遇的经验,或更严格地说,自我的权力受到面孔的抵抗的经验。为了更真切地进入这种与面孔相遇的经验,勒维纳斯将他人对于我可能具有的关系分为三类:(1)屈从——“他袒露在我所有的权力之下,屈从于我所有的诡计、我所有的罪行”;(2)实在的抗拒——“以其全部的力量、自由及其资源来抗拒我”;(3)伦理的抵抗——“但他也能——在此他向我呈现出他的面孔——超越所有的尺度以其自身来与我对立,以其无遮掩的裸露的双眼、直接而绝对坦率的凝视来反对我。”[6]173在第一种关系中我已经将他完全统治、同一。第二种关系虽然是一种抗拒,但这是一种实在的抗拒,抗拒的力量与被抗拒的力量都是存在的力量,服从的也是同一种法则:存在的法则;因而双方已经被整合进存在整体中了。因此在这两种关系中他人都不是绝对的他者,都被同一化了。但在第三种关系即伦理的抵抗中事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抵抗超越了所有的尺度——当然是存在论范围内的所有尺度,它“以其无遮掩的裸露的双眼、直接而绝对坦率的凝视来反对我”。这是一种最无力、最柔弱的抵抗:人的身上还有比眼睛更柔弱的吗?他就用这最柔弱的双眼来凝视我;人身上还有比双眼更裸露、更无防护的吗?他就用这最裸露、最无遮掩和防护的双眼来凝视我,以这种直接而绝对坦率的凝视来反对我、抵抗我的权能。如果他用他的实在的力量来抵抗我,我倒还可以用比它更强大的力量去征服,但对于这样一双柔弱裸露的眼睛,对于这样一种最为无力的抵抗,我的权能性却受到了最为严重的挑战。何以会如此?因为“在此他向我呈现出他的面孔”。一切都是由于面孔的出现而发生了变化。然则何谓面孔?简言之,面孔并不是这个世界整体之内的一张物理的、实在的脸,而是“作为面孔而发生的临显(épiphanie)”——外在性的临显。是无限的“源始的表达,是第一句话:‘汝勿杀。’”[5]217因此它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基本事件”。[4]198因此勒维纳斯说,面孔拒绝被包含(contenu)。在这个意义上,它不被把握(compris),不被合并(englobé)。既不被看,也不被触——因为在这种视觉与触觉的感性中,自我的同一性含括(enveloppe)了对象的他异性,于是对象复又变成了内容。[5]211在这个意义上,“面孔抵制占有,抵制我的权力。在它的临显中,在表达中,可感者,仍可把握者,变成了对于把握的完全的抵抗。”而它所反抗的又并非“我的权力的虚弱,而是我对于权力的能够(或权力的权力)(mon pouvoir de pouvoir)”。[5]215它使我的权力瘫痪:“它的凝视禁止我去征服。并非我的权力太虚弱以至于不敷征服之需,而是我不再能够能够了:我们将进一步看到,我之自由的结构被彻底颠倒过来。在此建立的不是一种与顽强抵抗的关系,而是一种与绝对他者的关系,一种与没有抵抗的抵抗的关系,一种与伦理上抵抗的关系。是这种抵抗打开了无限的维度本身——那把同一与自我之不可抗拒的帝国主义中止了的东西的维度本身。”同时,“意识的唯我论的焦虑”和“自我迷恋”在此也走向了终结。[6]173
所以面孔是自我唯一遇到而不是构造的东西。自我的权能性在面孔的抵抗这里遇到了它的界限。构造到此止步:自我的“自由运动既无法把面孔据为己有,也无法去‘构造’它。面孔在被遇见或构造之前已经在那里了。”[6]173构造的权能性能够遇到抵抗,但却无法构造抵抗。在面孔中向我临显的是作为绝对他者的他人。面孔是他人的踪迹,面孔的不可构造性证明了他人的不可还原性;所以他人是真正的外在性,不可同化的外在性,不可还原为内在性的外在性;是对唯我论的同一性的入侵、打破,是对意向性的挫败,是对自我自由的质疑。就像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或门铃声,在我根本来不及对它有所意向和筹划时,就已打破了自我的同一和宁静。
三、“无端的”责任
他人在面孔中向我走来,我与他人面对面,在这种“面面相觑”中经常发生的是:他人的面孔控诉我、质疑我,更向我发出呼吁、哀告,要我回应、负责。然而这是一种怎样的责任/回应?勒维纳斯说:“对于他人的责任/回应,对那在其面孔之裸露性中的第一个到来者的责任/回应。超出我对他者或许已经做或者还没做的事情之外的责任,超出任何可能将是或不是我的业绩的东西之外的责任,仿佛我在奉献给我本人之前已经被奉献给了他人。或者更严格地说,仿佛我在不得不存在之前就不得不回应他者的死亡。无罪的责任,然而在这种责任中,我却被暴露于一种控诉之前,不在现场的证明(无论是空间的还是时间的)并不能消除这种控诉。”[1]97然而,我为什么非要承担起这份“无罪的责任”?为什么不在现场的证据也不能消除这种控诉?难道仅仅因为他人是不可还原的,他人总是对我的自发性、自由提出质疑?我难道不可以(甚至有权利——从存在论的层次上说)不作回应因而放弃对他人的责任吗?甚至对他人施以暴力吗?在勒维纳斯看来,我之所以不能这样,最终是因为:自我,我,在它的“前史/前世”中,已经受到他者的“迫害”,已经被选为“人质”,从而已经成为他人的“替代”并因此已经对他人负有责任了。于是这就需要对自我的前史做一番考古/溯源的(archéologique)工作。而这正是勒维纳斯以《别于存在或本质之外》为代表的后期思想的主要任务。④
从笛卡儿以来,近代哲学的主流一直以自我为最终的根据/本原/开端;到胡塞尔,这种趋势达到顶峰。胡塞尔还从中世纪传统那里借来“意向性”这一概念用以刻画自我之意识活动的本质特征。勒维纳斯对于自我的考古学追问正是从质疑意向性的本原性开始:是不是一切意识都具有意向性?有没有前意向性的意识?如果有,那又意味着什么?首先来看这样一个事实:在人类的意识中总是存在着一种前反思的和暗中伴随着意向意识的非反思的意识。勒维纳斯要追问的正是:“在这种人们只将其当作前反思的和暗中伴随着意向意识的非反思的意识中,究竟发生了什么?”[1]82它们还有其意向性吗?它们还是“知”吗?关于这一点胡塞尔怎么看,我们不作讨论。但显然,勒维纳斯对此持保留态度:“作为先于全部意向的模糊的意识、隐含的意识——或摆脱全部意向的绵延——,它并不是行为而是纯粹的被动性”;“这种绵延摆脱了自我的所有意愿,绝对外在于自我的主动性,完全像一种衰老过程,后者很可能是被动综合的典范本身。”而且这种“作为纯粹绵延的绵延,作为无所坚持的存在的非介入,……[它]没有坚持于自我的瞬间的恳请,它已经是时间的流逝,它在进来之际即已离开[或开始之际即已结束]。”[1]85-87换言之,它是自我的任何回忆(当前化)都无法将之重新唤回的过去,是绝对的过去,是不可记忆的过去:“前反思的、非意向的意识将永远无法回过头来意识到这种被动性的意识。”[1]89这样一种绝对的不可记忆的过去,绝对的被动性,对于自我来说,就是一个不可同化的他者,先于自我的、意向性达不到的他者。
而自我本身正是由这样一种绝对的过去和被动性构成,由他者构成:“自我本身不能自身构成,它已经是绝对被动性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迫害的牺牲品,这种迫害使得任何能够在它之中苏醒以便自为地设定它的假定瘫痪。这种被动性是作为不可恢复的、先于任何记忆和回忆的过去之已经结束了的附属物的被动性。”[7]132-133所以“我并不是我自己的本原,我在自己中并没有我的本原”。[8]201而对于他人的责任也正是来源于自我的这样一个前史,来源于那个前意向性的绝对的过去:“意向性总是有一个内容,总是按照它的范围思想着。[但]有一些思想超出了它们的界限,比如欲望、寻求、疑问、希望——这些思想想得比它们所想得要多,想得超出了思想所能包容的范围。对于其他人的伦理的责任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伦理发生在意向性之前:“成为责任者/回应者,就是在任何决定之前成为责任者/回应者。……就好像在开端之前还有某种东西:一种无端(an-archie)。”[8]201在意向性的、意愿的决定这个开端之前,我已经成为责任者/回应者。于是对于他人的责任就成了一种“无端的”责任:在存在论的层面上没有开端、没有根据、没有端由的责任。但在这种“之前”和“无端”中究竟发生了什么?竟使我不得不对他人负有责任?勒维纳斯说:在这里发生了一种“着魔”(obsession),一种“迫害”:“意识在形成一个关于来到它上面的东西的影像之前,就已经被击中了,……在这些步态中,我们认识到一种迫害。”[7]130所以,“这一无端是迫害;它是他者对自我的控制,使得后者没有话语。这种迫害并不是指一种疯狂意识的内容,而是指形式,自我在这一形式下受到触发。它说的是意识的倒错,是一种并不能根据意向性来定义的被动性。”[8]203所以对他人的责任最终来源于一种绝对的被动性:我在自我的前史中已经被他人构成、被他人迫害,被他据为己有(着魔)且扣为“人质”,从而成为对他人的“替代”。作为人质和替代,我在决定、选择之前就已经不由自主地对他人负有责任了。这是纯粹的被动性:无所选择,也无可逃避。所以,不是我选择了善,而是善挑选了我——在我于当前中的创始和选择之前。[8]207
四、不可理解的替代
需指出的是,对于他人的这种“无端的”责任,这种替代,以及像“难道他人关系到我”、“难道我有责任看护我的弟弟”这样一类问题在存在中是不可把握、无法理解的。因为这些事情在存在论上是“无端的”,亦即无根据的、无理由的,是一种“例外”。勒维纳斯说:“这一对他人的责任被构建为一人为另一人,甚至一人作为另一人的人质,……替代他人。必须理解,这是一种在存在中不可理解的关系,这同样也是在说,这一替代是本质的例外。”[8]202存在(本质)的法则是“自私的”法则,是“唯我”的法则。所以“存在(esse)间(inter)的关系”也就是“利益”(intéressement)。而对于他人的责任、替代则恰恰是对这种存在间的这种自私唯我的利益关系的“解除”(dés-),所以是“公正”(désintéressement)。它发生在存在论上的一切开端/根据/原则之前,所以它不可理解:完全是“没来由”的“无端”之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勒维纳斯说,人是不讲理由——存在论意义上的理由——的动物:“存在的目的就是存在本身。然而,随着人的出现——这是我的整个哲学——有某种东西比我的生命更重要,那就是他者的生命。这是没有理由的。人是一种不讲理由的动物。在大多数时间里我的生命对我是更亲近的,大多数时间人在照看他自己。但是,我们不能不仰慕神圣(saintliness),……即,一个人在他的存在中,其更多的是委身于他人的存在而非自己的存在。我相信正是在这种神圣性中诞生了人。”[4]202-203
然而,这样一种对于他人的替代和“无端的”责任,也并非勒维纳斯的单纯宗教信念或道德说教。只要我们敢于直面一些源初的伦理经验,它就昭如日月。比如伦理上被告发和被迫害的经验:“一切的告发和迫害,……都预设了自我的主体性/臣属性,预设了替代,预设了置自身于他者之位置的可能性……”[7]150⑤这种被告发、被迫害的经验在主观感受上的体现就是面对他人的愧疚感。作为对自我的迫害和告发,愧疚感完全不请自来,是一种绝对的被动性。在这里,有“先验统觉之整体的一种逃跑,一种溃败,一种背叛,有任何行为之本源的意向性的一种溃败”;[8]201有自我对其主权的放弃,有对存在意义的质疑,有对自我的厌弃与憎恶。然而,所有这些——迫害与告发、意向性与良好的自我意识的崩溃以及愧疚感——又如何可能?是否恰恰是因为——如勒维纳斯所说——已经预设了自我的主体性/臣属性,预设了替代,预设了置自身于他者之位置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先行的替代,没有对于他人的这种无端的责任,我们怎么可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愧疚意识?良知怎么可能会不安甚至崩溃?所以或许正如勒维纳斯一再说的,在自我的前史中,我们早已被他人所纠缠,在自我的一切开端之前,早已有无端的责任在说话。前世缘定,无可逃避,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伦理学是第一哲学?
五、自我与他人或人与人之间:一个成问题的地带
勒维纳斯的这种思想并非完全不可质疑。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一个具体生命比如一个Dasein的存在本身,究竟具不具有伦理学上的第一性价值?更直接地说,存在本身的要继续存在,具不具有合法性?难道仅仅因为一个存在者存在了,占有了一个Da,剥夺了一个他者的Da,就因此具有原罪?为什么这个存在者自身就没有权利占据一个Da,一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勒维纳斯自觉地把自己的哲学与传统哲学相对立:传统哲学以“存在论”为“第一哲学”,因此以自我的“存在”本身为最高的价值,从而导致自我对于他人的暴力;而他则以“伦理学”为“第一哲学”,从而以对他人的责任为最高的价值,这是否反过来又会导致他人对自我的暴力?诚然,我们不能立足于自我而去抹消他人,不能把他人还原、同化到自我上来。但这是否就必定意味着要使自我成为他人的人质?无条件地、无端地承担起对他人的责任?自我与他人,究竟谁才具有更高的价值?或者如此提问本身就已经是不合法的?
究其实质,这个问题最终涉及的是究竟该如何理解人之为人,以及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究竟该首先把人理解为一个“唯我”因而“为我”的存在者,一个必然具有Da、也必须(有权利)具有Da的Dasein,从而不可避免地对于他人具有暴力的唯我论者?还是首先应该把人理解为一个他人的人质,从而首先应当无限地朝向他人、对他人负有责任的替代者?显然,这里争论的双方实质上是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或希腊人与犹太人。因此,这个争论最终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用德里达的话说则是:“我们首先是犹太人还是首先是希腊人(这不是个历时性的提问而是前逻辑的提问)?”[9]274但是,当“我们”随德里达一道如此发问的时候,问题的更为复杂之处在于:“我们”可曾想起“我们自己”是谁?可曾想到,由德里达针对勒维纳斯所提的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自己”是否有效?换言之,德里达所说的“我们”,是否能包括作为既非希腊人也非犹太人的中国人的“我们”?还是说,“我们中国人”已经某种程度地“希腊化”了、“希伯来化”了,因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西方人”了?也许?!但无论如何,中国古人首先既不是希腊人,也不是犹太人,而是地道的中国人。这不仅是个物理事实,更是个思想事实:中国古人对于人之为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着既非希腊式的亦非犹太式的理解。而这一点意义重大,它要求“我们”作为“中国人”在思考勒维纳斯伦理思想的时候,不仅应当深入到由他所尖锐化了的自我与他人、希腊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思想张力中,更应该把他的思想,把既包含希腊思想也包含犹太思想因而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思想带到作为它的他者的中国古代思想面前,在这种更大的格局与张力中思考人之为人的问题,思考自我与他者的问题,或不如说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古代思想的视域中,究竟有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自我与他人,还是个有待思考的问题。而这我们显然还做得远远不够。
注释:
①可分别参阅王恒的《时间性:自身与他者——从胡塞尔、梅德格尔到列维纳斯》(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杜小真的《勒维纳斯》(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叶秀山的《从康德到列维纳斯——兼论列维纳斯在欧洲哲学史上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4期)、孙向晨的《莱维纳斯的“他者”思想及其对本体论的批判》(《复旦学报》2000年第5期)、《现象学抑或犹太哲学——对莱维纳斯哲学犹太性的探讨》(《哲学研究》2001年第1期)、杨大春的《超越现象学——列维纳斯与他人问题》(《哲学研究》2001年第7期)等等。
②在这里,勒维纳斯认为,正义就是伦理,而自由则“意指着在他者中间保持为同一者的方式”(Totalité et Infini,biblio essais,Kluwer academic,1992,p.36)。而在后期,勒维纳斯则明确地将伦理与正义进行区分,他在1986年曾对人说:“在Totalité et Infini中,我用词语‘正义’(justice)来说明伦理,来说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现在对我来说‘正义’这个词已经是某种计算,某种知识,或是意味着政治的东西;它确实与政治无法分离。它是我试图与伦理学相区分的东西,而伦理是原初的。然而,在Totalité et Infini中,‘伦理的’(ethical)一词和‘公正的’(just)一词是同一个词,同一个问题,同一种语言。”(勒维纳斯:《道德的悖论:与莱维纳斯的一次访谈》,《文化与诗学》第一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页)
③但是在这一点上,勒维纳斯一度遭到德里达的猛烈批判。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这里无法展开。
④罗朗(Jacques Rolland)在谈到勒维纳斯的两本代表作《整体与无限》和《别于存在或本质之外》时说:“第一本书探讨自我的现象学,这一自我在一个世界中遇到他人,而他人则要摇撼和质疑它首位的纯洁。第二本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从事的是对自我的考古学研究,以发现已经被他异性变异了的自我。”(勒维纳斯:《上帝·死亡与时间》,余中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1页注释6)事实上,这样一种通过对自我的考古学研究为对他人的责任寻找更为古老的前存在论的“端由”的努力,一直是勒维纳斯后期思想的主题,包括他1975、1976年的讲课稿《上帝、死亡与时间》以及80年代的《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等一系列重要作品。
⑤主体性(subjectivité,subjectivity),在勒维纳斯那里并不是近代哲学以来所说的作为“实体”的“主体”的“性”,而首先应当在subject to(臣属、从属)的意义上理解,因此,一个subject,在他这里首先就不是通常理解的作为实体的主体,而是意味着一个从属于甚至臣属于他人的“主体”,一个因此总已经刘他人有所亏欠,必须对他人负责的“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