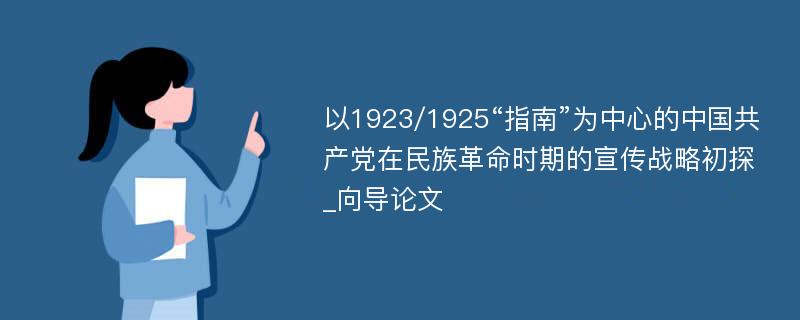
国民革命期间中共之宣传策略初探——以1923—1925年之《向导》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向导论文,中共论文,国民论文,策略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时期(也有称“大革命时期”),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长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前人的研究多偏重于运动过程的描述、政党组织与国共两党的合作与分歧方面,而对国民革命期间之宣传工作研究较少,或者说不够细致。关于国民革命史研究较为重要的著作,如黄修荣的《国民革命史》,对中共宣传工作的研究侧重于其对反帝反军阀等的宣传,忽视了中共对自身主义理论的宣传。近期,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一书,专门论述了国民革命中中共宣传话语的强势问题,精辟地分析了《向导》式话语的特点,以及“左派”、“右派”、“三大政策”等一些重要宣传口号的提出及意义,但对这一时期中共之宣传策略缺少动态的分析,且有一些重要问题没有涉及(注:请见黄修荣:《国民革命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版。)。
事实上,1923年至1925年,国共双方的关系及相对地位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而这一时期中共宣传策略的演变亦颇耐人寻味。本文试图以国民革命时期中共最重要的机关刊物《向导》为中心,结合国民革命的具体进程,对此时期中共的宣传工作进行初步考察。
一、早期中共关于国民革命之宣传
第一次国共合作很难说是“历史的必然”,国共双方所以能够合作,苏联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起了关键作用。
孙中山真正感兴趣的是苏联人的援助,允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只是获得苏联援助的“代价”,所以孙中山断然拒绝了共产国际提出的建立国共两党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建议,只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坚持自我主体,是孙中山接纳中共的前提。”(注:桑兵:《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356页。)
中共方面,在1922年8月举行的西湖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几乎是“强迫”中共领导层修改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而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事实上,中共党内对这一问题仍存在很大的争议(注:如蔡和森和张国焘等认为,“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会使中共在组织上和主义上丧失独立性,并对共产国际轻视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无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表示不满。(《张国焘回忆西湖会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42页。)这种意见在中共三大上依然有所表现。)。
共产国际要求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但“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目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同时积极开展群众运动,“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既要“对国民党施加影响”,支持其正确的政策,但“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的旗帜。”(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第436页。)中共三大基本上贯彻了这一精神,大会发表的宣言倡导,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号召“社会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肯定了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主体地位(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版,第165页。)。中共三大宣言称,“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这标志着中共的“工作中心从工人运动转变为国民革命”(注:黄修荣:《国民革命史》,第61页。)。三大通过的决议及其宣言,为中共早期的国民革命宣传工作奠定了基调。
与较为忽视宣传工作的国民党相比,深受俄国革命经验影响的中国共产党对宣传工作十分重视。西湖会议后,中共的政治机关报《向导》创刊,并成为中共宣传国民革命的主要阵地。早期的《向导》“印行6000-7000份,主要对象是学生与青年”(注:《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1922年11月底—12月初)》,《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第332页。)。为了便于销售,《向导》开始并没有用中共的名义发刊。发表于第一期的《本报宣言》,语气温和地提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使民众取得“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从《向导》早期的宣传内容看,中共采取了较低调的宣传姿态,没有强烈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色彩。
国民党一大之前《向导》所反映的中共对国民革命宣传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倡导国民革命。在《向导》第二期上,陈独秀提出了“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概念(注:独秀:《造国论》,《向导》第2期。)。中共并没有明确为国民革命定性,虽然中共提到“在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是要占个主要的地位”(注:独秀:《造国论》,《向导》第2期。),但中共的宣传家更努力于解释国民革命的全民性与超阶级性:革命或反革命的区分,“不应以一个阶级一个党派或个人之静的名称为标准,应该以那阶级党派个人之动的行为为标准”(注:独秀:《革命与反革命》。《向导》第16期。)。这为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
第二,承认国民党居于领导地位。中共早期对国共联合战线只是抱试试看的态度,有人断定国民党是一个“大而无当的破烂的”政党,“并不是什么可靠联合对象”(注:包惠僧:《回忆马林》,《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第259页。)。但为了贯彻西湖会议精神,中共改变原来对国民党的定性以及不屑一顾的态度,在宣传中统一口径,宣传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的政党”;“它的党纲所要求乃是国民的一般利益”(注:双眼:《国民党是什么》,《向导》第2期。),所以,“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65页。)。
第三,对国民党施加政治影响。虽然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但它还负有“矫正国民党的政治观念”(注:《国民运动计划决议案》(1923年11月),《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33页。),使其“革命化”,从而“完成在中国国民运动和国民党中建立左翼的任务”(注: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和东方部远东局——关于中国形势和1923年5月15日至31日期间的工作报告》(1923年5月3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第450页。)。中共希望利用《向导》的宣传,对国民党施加政治影响,完成以上任务。在将国民党塑造成革命的平民政党之外,中共还用劝诱式话语引导和推动其实行坚决的反帝路线、群众路线以及与苏俄结盟路线,即推动国民党左倾。如中共指出,国民党应该“一面与群众为亲切的结合,一面与苏俄为不二的同盟”(注:和森:《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向导》第1期。);“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外力及专用军事两个旧观念,十分注意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勿失去一两个宣传的机会”(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65页。)。中共认为,“国民党不仅是担负打倒军阀的使命,而且要变成推翻帝国主义的急先锋。”(注:仁静:《革命政府反抗帝国主义的第一声》,《向导》第48期。)除了从正面引导国民党外,中共还对国民党的许多政策和观念加以批评,以督促其向着中共希望的方向发展,防止其与军阀和帝国主义妥协。如中共批评国民党只知“与军阀周旋”,使得“民众难以发现国民党是代表民众利益奋斗的政党”(注:国焘:《革命党的“否认”病》,《向导》第15期;《中国革命与国际之关系》,《向导》第23期。)。对于临城案件发生时国民党企图“利用洋大人的势力来推倒曹吴”的态度,中共批评十分激烈,斥之为“卑劣而且懦弱”(注:独秀:《临城掳案中之中国现象》,《向导》第26期。)。
国民党一大之前中共对国民革命的宣传,配合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中国革命战略,与西湖会议的精神保持着高度一致性——各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和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是《向导》宣传的中心内容。虽然孙中山允许中共在国民党内宣传共产主义,但中共在宣传上总体上也表现得相当克制与低调(注:当然,《向导》仍有极少数的文章强调中共的地位与宣传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如《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第20期)中有,“惟有共产党是真正保护劳工为劳工阶级利益而奋斗的党,此外一切标榜保护劳工的党派和势力,都不过是为他们自身的利益或他们阶级的利益所施行的一种政策”;《两种革命的推究》(第45期)宣称,“共产主义可以绝灭人类一切底罪恶根株,使两种革命(革民众旧习性的命和革万恶军阀的命)根本解决”。)。
二、从国民党一大到商团事件
国民党一大召开后,中共在国民党内部的工作逐渐展开,其在国民革命中的自觉意识逐渐加强。在鲍罗廷的积极工作下,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做与共产主义几乎一致的解释”(注: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在革命策略方面,一大宣言称,“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国民党政纲承诺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并“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6页。)。孙中山本人在关于大会宣言的演说中表示,要“计划彻底的革命”,“以后应当把妥协调和的手段一概打消,并且要知道,妥协是我们作彻底革命的大错”(注:《对于国民党宣言旨趣之说明》,《孙中山选集》,第599页。)。
国民党与孙中山这种“左”的姿态使中共看到了希望。1924年初,中共在宣传中仍努力提高国民党的地位,瞿秋白更提出,国民党“始终是代表下层阶级的政党,是革命的政党,是代表大多数平民利益而奋斗的政党”。(注:屈维它:《国民党与下等阶级》,《向导》第55期。)中共在1924年2月的《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中指示,不可再对国民党“预存嫌恶藐视的心理”,而应“更加努力扶持他们”,在具体工作上要“采取种种策略化右为左,不可取狭隘的态度躯(驱)左为右”(注:《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45、51页。)。
但中共很快就发现,国民党一大之后,国民党及孙中山并未根本改变其政治观念和革命策略,国民党工作的重心仍是军事行动,而不是群众运动,且经常与军阀和帝国主义妥协。同时,国民党内一部分党员对中共的猜忌和排斥态度有增无减。这使中共进一步“认识”了国民党,并开始调整工作方法。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对2月的决议进行了修正。这一份颇具转折意义的议决案指出,国民党内存在有产阶级与劳动平民的利益分歧,不能“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阶级调和的政策”,而要“在国民运动的根本问题上指摘右派政策的错误”。中共自命为国民党内的“左派”,明确提出与右派斗争的口号(注:《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45、51页。)。两个月后,中共中央更是专门发出通告,指示对国民党右派斗争的问题(注:《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82页。)。不难看出,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工作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不愿再担当国民党辅助者的角色,要在组织上进行更富斗争性的工作,在宣传上采取更积极的政策。
与此转变相呼应,陈独秀1924年4月23日首次在《向导》上正式提出“国民党左右派”的概念——而在此前《向导》的文章中,国民党是作为一个“统一体”出现的。陈独秀认为,国民党内左右派的区别在于“采用革命方法的是左派”,“左派乃是真的国民主义者,右派乃是抛弃了国民主义,实际上可以说不算是国民党了”。国民党的“左右之分”“应该是以革命分子非革命分子为标准,不应该以相信社会主义与否为标准”(注:独秀:《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向导》第62期。)。“左派”和“右派”对应的不是“激进”与“保守”,也不是“革命”与“改良”,而是“革命”与“非革命”。在辛亥革命后中国整个政治话语体系里,“‘革命’具有无可置疑的绝对正当性和合法性”(注: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71页。),以“革命”的黄袍来定义“左派”,这就赋予了“左派”以“绝对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对推动国民党左倾十分必要。在陈独秀新提出的左右派划分标准中,“信仰”因素被淡化,也就意味着政党的区别并不重要,这为中共争取联合国民党左派,打击右派提供了理论平台。
虽然中共早期对国民党的批评引起了部分国民党人(包括孙中山本人)的不满,但中共从未放弃其宣传言论上的独立性,也没有停止过对国民党的批评,这种批评在商团事件后,变得更为激烈。蔡和森称,“广东商团事件,可谓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雇佣军阀以及国民党右派分子伙同宰割革命政府之奇观”,右派是帝国主义在革命党内部培养的“反革命的法西斯蒂”,他要求孙中山“澄清党内右派反革命的法西斯蒂”(注:和森:《商团事件的教训》,《向导》第81期。)。陈独秀亦指出,国民党右派分子“终必直接或间接断送党的生命”(注:独秀:《肃清内部》,《向导》第89期。)。此时,中共将“右派”与“反革命”完全划等号,意味着“剥夺其存在的合法性”(注: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71页。)。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共宣传话语的进攻性,以及将革命队伍“纯洁化”的要求。与此同时,中共对国民党内的“中派”也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认为胡汉民等“中派”在商团事件中“妄想执两端之术”,结果,“间接做了反革命与帝国主义的工具”(注:和森:《警告国民党中派诸领袖》,《向导》第85期。)。《向导》甚至怀疑,“国民党中派诸领袖不能负指导群众,组织群众的责任;并没有政治眼光,不能当得革命的领袖”(注:巨缘:《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的孙中山政府》,《向导》第85期。)。
此外,《向导》仍一如既往地批评国民党的一些具体政策,尤其是军事行动。如中共批评国民党在江浙战争中站在反直派一边,与军阀结盟,“不啻把改组后的一切宣言、党纲和政党的原则全部束之高阁”(注:述之:《江浙战争与国民党》,《向导》第84期;述之:《我们为什么反对国民党的军事行动》,《向导》第85期。),将国民党这种“牺牲己党的党纲政纲逢迎军阀”、“与帝国主义妥协”的政治态度,斥之为“下流的政治态度,不待言不能救中国,并要葬送国民党的生命!”(注:独秀:《国民党的政治态度》,《向导》第91期。)
这一时期中共宣传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积极确立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袖地位。在国民革命中保存阶级斗争,以自己的旗帜领导工人运动,由民族革命而至社会革命,可以说是中共一直未放弃的理想,因为这是共产党的根本使命所在(注:如瞿秋白早在1923年9月就指出,要“以劳工阶级的方法行国民革命”,“到国民革命的最高度,很可能与世界革命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屈维它:《自治主义与社会主义》,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版,第214页。))。虽然对这一理想的宣传在一段时期内策略性地受到压制,但随着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独立性和自觉性的增强,这种理想又似乎变得不太遥远。而对国民党态度和政策的不满,更使得中共感觉到采取主动政策的必要性。1924年5月的中共扩大执行委员会指示,将“劳动运动尤其是近代产业工人运动”——即阶级斗争工作——作为党的“根本工作”(注:《此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之意义》,《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50页。)。工人运动再次成为中共工作的中心。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上,更是将阶级斗争与国民运动的关系明确表述为,“阶级斗争足以促进国民运动,而国民运动亦足以增厉阶级斗争。”(注:《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26页。)两者并行不悖,且互相促进,在国民革命中推进阶级斗争具有完全的合法性。由于中国民族革命“在政治上是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而国民党只是民族运动中的一个“工具”,因此,中共进一步强调要防止国民党内存在的“阶级调和观念的危险”,中国无产阶级要“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国民革命,决不能“沉溺在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民主——引者注)运动中”,否则,将“遗无产阶级以不容易挽救的大害,并且足以减少民族运动的革命性”。而且,“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注:《对于民族革命运动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29页。)在此逻辑之下,在国民革命中施行阶级斗争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十分必要。至此,中共在意识上已经突破了“西湖会议”的精神,开始独立领导工人运动,其工作重心由国民革命再次回归工人运动。
中共在国民革命早期的宣传话语中,较少出现“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等带有较强自身理论色彩的词汇,《向导》所用的更多的是“群众”、“劳动平民”等较温和的词汇,也几乎没有特别强调过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问题,更遑论领袖地位。陈独秀在1923年底还认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但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注: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上),第209页。)“二七”罢工的失败和共产国际对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轻视都让中国共产党人感到沮丧。但1924年底,中共根据5月中执委扩大会议的精神,逐渐在宣传中强调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彻底性和不妥协性,并直接确立其国民革命领袖地位。蔡和森提出,反对“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闭着眼睛模仿一二世纪前的单纯对内的民主革命”(注:和森:《义和团与国民革命》,《向导》第81期。),即反对单纯的资产阶级革命。陈独秀主张,只有通过“实行横的国内阶级战争”(注:独秀:《欧战士周年纪念之感想》,《向导》第76期。),才能达到彻底革命的目的。“担负中国革命事业——由民族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注:述之:《二七斗争的意义与教训》,《向导》第101期。)。对工人阶级领袖地位如此浓重的宣传以及中共话语中“阶级”、“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斗争”等这些意识形态较浓的词汇的陆续出现,充分反映出中共试图将阶级斗争理论引入国民革命,并在此基础之上取得国民革命领导权的趋势——虽然中共还没有在宣传话语中对“阶级斗争”等概念作详细的阐释。
三、从孙中山逝世到五卅运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由于孙中山在国民党内崇高的权威地位以及在全国的巨大威望,使他的逝世对国民革命的进程和国共两党的关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海外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因孙中山的逝世感到机会来了,他们在孙中山在世时只能秘密而徒劳谋求的东西,现在可望得到了,这就是国民党和民族运动的领导权。”(注:(德)郭恒钰著、李逵六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版,第100页。)这一论断或许有猜测的成分,但三民主义的创立者的离世,的确为中共宣传工作赢得了更大的空间。
得知孙中山病重已无法救治后,中共中央在2月即部署他去世后的宣传工作。为了配合具体革命策略的需要,中共决定以如下方式来阐述孙中山的历史事业和思想遗产:第一,强调孙中山的反帝精神,宣传“中山自始即有反帝国主义之思想与行动”。第二,将孙中山与“左右之分”联系起来,一方面宣传“中山自始即根本反对封建制度……甚至反国民党中的右派——宋遁初、黄兴等”;另一方面,大力宣传孙中山“对海关问题和商团事件所发表之反帝国主义的宣言”以及“主张根本废除军阀制度之宣言”等孙中山晚期较左的言论,从而将孙中山塑造成坚定的“左派”形象。在宣传三民主义方面,中共中央指示“应以一九二四年一月民党大会的宣言、党纲、政纲为依据”,同时对于与阶级斗争理论冲突之民生主义,“不可多做解释”。中共还制定了“遵守中山先生遗言,继续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推翻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国民党统一,反对国民党分裂”、“以党的集权主义代理中山先生执行其总理职权”等宣传口号(注:《中共中央通告第五号——关于孙中山逝世后之宣传问题》(1925年2月5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91页。)。虽然孙中山生前并没有根本改变他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根本观念和具体策略(注:关于此论断,或许有学者持异议。但从孙中山最后北上与军阀协商、途中在日本大讲“大亚洲主义”等行为来看,他又回到从前对外国势力与军阀的看法上。),但鲍罗廷耐心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已经可以使孙中山“在口头上表示对左派的赞同”(注:(美)丹尼尔·雅各布斯:《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第130页。)。孙中山的逝世使得中共可以利用国民党一大宣言,以及他晚期表现出的某些激进姿态,将其塑造成一个“左派”,从而推动整个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向“左”转。中共在宣传中充分肯定孙中山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但同时表示,革命事业不会因为失去一位伟大的领袖而终结,“相信伟大的集合体指导革命比伟大的个人指导革命更有力量”(注:独秀:《悼中山先生!》,《向导》第106期。)。
“左、右”之分和“阶级斗争”仍然是这一时期中共宣传话语的重心。中共修正以前对国民党“左、中、右”三派的划分方法,转而提出“不左即右,没有中立余地”的二元划分,并将“左化的意义”定义为“真正同化于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中山主义”,督促一切国民党分子都要在“革命与反革命”(即左派和右派)之间作个选择(注:罗敬:《革命与反革命》,《向导》第110期。)。在此基础之上,中共进一步将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斗争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指出左右两派的斗争,“决不是一部份‘老党员’知识落伍的问题,乃是民族运动中阶级争斗的问题”。因为“国民党自始即是一个多阶级的党,所以自始即包含阶级利益的冲突”,右派代表的是买办阶级和封建的上层阶级(贵族、军阀、大地主)以及一部分海外华侨和留学生的利益,他们反革命的行为是“自觉或不自觉的阶级本能的表现”(注:和森:《冯自由派反革命运动的解剖——国民党淘汰反革命分子之必要》,《向导》第111期。)。而“民族革命的客观的趋势终于要超过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范围”,所以“全国革命”、“阶级调和”等口号都是带欺骗性的。中国的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应负两种责任:“一面应该为民族独立的共同利益奋斗,同时应为本阶级的特殊利益而奋斗。”两者缺一不可,才能完成彻底的国民革命的目标(注:和森:《今年五一之中国政治状况与工农阶级的责任》,《向导》第120期。)。阶级斗争不仅正式出现在中共宣传话语中,而且与左右派的斗争和国民革命建立了紧密地逻辑联系,从而达到了在宣传中确立阶级斗争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的目的。这种理论结构,虽然不能等同于共产主义革命理论,但却具有很浓的中共意识形态色彩和较强的现实解释能力。这种理论在五卅运动兴起后的宣传工作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五卅运动是国民革命中群众运动的高潮。运动初期,各阶级形成了反帝的联合战线,中共认为,五卅运动是“中国人民一致的从排日而进于排外,从阶级斗争而为民族斗争”(注:秋白:《帝国主义的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向导》第119期。)。因而号召“全国各被压迫阶级的群众”来维持并发展“长期的民族斗争”(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向导》第117期。)。但6月底,上海商会宣布停止罢市,统一战线出现分裂。以上海总商会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在运动中令人失望的表现,使中共获得了进一步宣传阶级斗争理论的绝佳机会。中共将这种分裂定义为“阶级分化”,称“此次民族运动……之阶级分化已非常明显”(注:《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言——告此次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向导》第121期。)。总商会的开市,“背叛了民众利益”,“完全表现出在民族争斗中的妥协的大资产阶级之阶级性。”(注:独秀:《我们如何应付这次运动的新局面》,《向导》第120期。)中共甚至断言:“北京政府的背后站着外国和中国的资产阶级。”(注:《为工会条例告中国工人》,《向导》第122期。)资产阶级不再是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的联合对象,而成了民族利益的背叛者,成了军阀政府的支持者,具有反动性,是国民革命理所当然的斗争对象。因此,“中国工人阶级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必然要以阶级斗争的理论做指导。”(注:秋白:《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向导》第128期。)瞿秋白总结道:“不但国民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中国被压迫剥削的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而且民族解放运动内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必不可少的,亦是事实上必不可免的。这种斗争里如果无产阶级胜利,便能使民族解放运动得着充分的发展;如果资产阶级得胜,那就中国民族的要求民权的要求都要被他们的妥协政策和私利手段所牺牲。”(注:秋白:《五卅运动中的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向导》第129期。)阶级斗争不仅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内容,而且无产阶级在这一斗争中的胜利也成了国民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
这一时期中共宣传中还出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中共开始积极宣传自身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从理论上讲,既然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阶级斗争亦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内容,那么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然要在国民革命中占据重要地位,甚至领导地位。五卅运动后,中共改变以往在宣传中极力提高国民党地位,而对自身地位问题较避讳的态度。五卅运动一起,中共即宣称其“不仅为工农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并且为全中国被压迫的民族而奋斗”(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向导》第117期。)。中共明显减少对国民党是国民革命中唯一领袖的宣传,转而提出,指导民众进行国民运动的责任“已经由孙中山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起来担负了”(注:唐兴奇:《五卅运动的意义》,《向导》第121期。),从而将中共与国民党并列为国民革命的领导者。8月,中共号召工人兵士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旗帜下,达到完全解放中国及工人阶级的目的”(注:《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告工人兵士学生》,《向导》第125期。)。不久又进一步提出“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旗帜底下”的口号,公开号召工人们“赶快加入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能领导你们的斗争达到最后的胜利”(注:《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旗帜底下联合起来呵!》,《向导》第126期。)。如此高调的自我宣传,说明中共主观上已经将自己定位成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了。对于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出现的“反赤化”、“反共产主义”等对中共不利的论调,中共亦利用国民党一大宣言、民族主义、孙中山等具有普遍认同性的概念,巧妙地予以回击(注:如中共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相联系,称反共产主义就是反对国民革命,反对孙中山;又如用“民族自由”的绝对目标来为其“激进”手段辩护。)。
至此,中共已经基本完成了其对国民革命与自身理论的融构,中共还在国民革命的宣传中获得了相对于国民党的话语强势。这种强势在很多方面体现出来:中共提出的一些最基本的普适性的口号,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行国民革命等,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并且深入人心。此外,中共的积极宣传也在一般青年中形成一种强烈的“左”比“右”好,“无”比“资”好的观念(注: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70、72页。)。这些观念甚至影响到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官员。如汪精卫当时的一句名言是“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向左去;不革命的不反帝国主义的向右去。”(注:转引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71页。)廖仲恺也写道:“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国民党中,必然发生革命派与反革命派。……那一派人替农工阶级打销压迫他们的力量便是革命派。”(注:廖仲恺:《革命派与反革命派》(1925年5月20日),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1924-1927)》第2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版,第47页。)不仅如此,中共对国民党的左右派划分的概念甚至出现在国民党正式会议的文件中,如国民党中执委称,“两年以来,……(党员)对于革命政策,亦意见亘殊,于是显分左右两派。惟右派人数极少,且皆属腐败懒惰分子,日惟升官发财为念,慑于积极革命之不利于升官发财,乃大反对”(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令严驳北京党员之违法会议》(1925年12月),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1924-1927)》第2册,第261页。)。国民党二大宣言中虽然没有使用“左右派”和“阶级斗争”,但二大宣言不仅比一大宣言带有更强的反帝色彩,而且将官僚阶级、买办阶级、土豪与军阀并列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亦在打倒之列,且宣言中“阶级”一词出现多次,明显受到中共宣传话语的影响。
小结
通过对1923—1925年国民革命中中共宣传策略的考察和分析,不难窥见中共宣传工作从被动到主动,以及利用一系列历史事件逐渐在国民革命的宣传中融构进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的过程。与其说中共发展了国民革命理论,毋宁说是中共利用“国民革命”这一概念的模糊性,将自身的主义和理念融入了国民革命理论。同时,这也是中共逐步引导国民革命话语激进化的过程。
中共成功的宣传策略与在宣传上的强势地位,固然对于引导国民革命的进展与扩大中共自己的实力方面,有着相当正面的意义。但宣传总是要建立在一定实力基础之上的,相对于宣传上的强势,此时的中共与国民党在实力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尤其是在组织与军事方面。这时,中共在宣传方面的强势,强调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打破了国民党一大后的平衡,引起国民党内一部分人的恐惧,从而激发出强烈的抵触情绪,使两党的矛盾激化。
戴季陶主义恰在此时出现。戴在致胡汉民的信中矛头直指《向导》,称“《向导》本期又对吾兄及精卫大加奚落,其故盖欲将国民党中稍能得青年信仰之人,均用打神鞭一律打尽,然后彼党乃可取得完全指导青年之地位,……将国民党领袖人物之信用,破坏干净。”戴认为,如不反击中共的宣传,“再听其若是荒唐,一年之后完全无可救药。弟与诸兄皆欲自存而不得,遑论救党,更遑云救国哉”(注:《戴季陶致胡汉民函》,《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2册,第14件,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为此,戴在上海奔走于各学校间演讲,“入夜则努力著作,常至通宵不寐。”(注:《戴季陶致胡汉民汪精卫函》,《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2册,第8件,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他连续完成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与《国民党员之义务》,并要求加印10万份。
戴季陶主义的出台,标志着国共两党主义与理论对垒的公开化。戴反对阶级斗争,提倡阶级调和,并试图重新确立“三民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独尊地位,以此与中共的宣传相对抗。国民党方面不可能轻易放弃其在国民革命中的主体地位,而中共由于其独立意识的增强及理论的逐渐系统化,必然会突破国民党关于国民革命的理念和设想。这种理论的对垒,表现在国民革命进程中,就是两党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此时,中共在组织上只有两种选择: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或者离开国民党。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及随后国民党通过《整理党务案》,宣告了中共在国民党内争夺领导权的失败。那么,两党的最终分道扬镳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标签:向导论文; 国民党左派论文; 革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右派分子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国民革命军论文;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论文; 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孙中山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