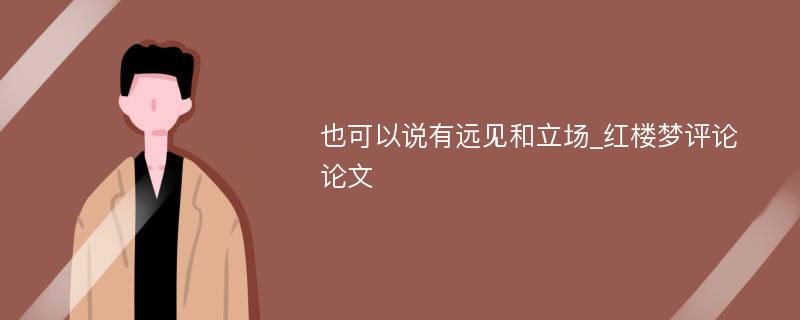
也说前见和立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也说论文,立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江先生: 拜读了你的第五封信,完全同意你关于对前见与立场问题的认识是一个阐释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的观点,我们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对阐释学理论的推进肯定大有裨益。同时,觉得你对问题的思考的确很严密,就你讨论的论域而言,也就是在你的概念体系中,认定前见与立场完全不同,这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但是,如果超越了你《强制阐释论》一文自成一体的概念体系,恐怕情况就会不一样了。 十分清楚,你对“前见”(包括“视域”)与“立场”作了独特而严格的区分:“前见”是无意识的,是理解者在所处的文化传统中形成的理解文本前的知识背景和认知模式;而“立场”,是主动的、自觉的、有意识的,在理解、阐释文本前已经预先操控、决定了阐释的结论,并不惜曲解和改变文本原有的意义和逻辑,使之适合于“立场”预定的结论。你根据这个区分得出“立场”乃是导致强制阐释的真正根源的结论,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然而,如果跳出你“强制阐释论”的独特的概念体系,从一般的语义学角度来理解“立场”的话,你对“立场”的个性化阐释,就不一定具有普适性了。首先在西文中恐怕不容易被普遍认同。我查了一下英文、德文辞典,与中文“立场”一词相对应的英文词有两个:(1)standpoint,含义为立场、观点、立足点(按:这与你说立场“表示阐释者的学术站位和姿态,或者说是阐释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倒是一致的)。同义词perspective(透视、前景、观点、看法)。例如a modern/political/theoretical standpoint。(2)position,有place(地方)、ways of sitting/standing(坐/立姿势)、situation(情势)等多种含义,其中opinion(看法)有立场义,position on sth.(观点、态度、立场),例如to declare/reconsider/shift/change your position,the party's position on education reforms,She has made her position very clear。①德文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对译“立场”一词的德文是der Standpunkt,其含义也是位置、立足点、立场、观点、见解、看法等。 这样看来,在西文中,立场与观点、见解、看法等词在含义上并无显著的区别。虽然前见在伽达默尔的阐释学中有特定的内涵,即你理解为理解活动前的某种知识准备或者认知模式,但无论如何它也还是属于见解、观点的范围,并没有与standpoint或者der Standpunkt有根本的区别。你文中所引用的伽达默尔的两句话:“即使见解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被理解”;“我们也不能盲目地坚持我们自己对于事情的前见解,假如我们想理解他人的见解的话”,也证明前见解与一般见解、观点或者立场在语义上没有根本区别。所以,你在强制阐释论的概念体系中对前见和立场所作的严格区分,我认为不容易为西方学者所理解和认同。在我看来,为了使你的“强制阐释论”在西方文论界产生影响,而不至于被误读、误解,建议“前置立场”的概念还是调换一下更好。 在中文语境中,这一点尤为重要。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立场”一词的基本含义在我国知识界和人民大众中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理解,其中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的含义无疑不可避免,所以,尽管你强调“我在《强制阐释论》中所使用的立场的含义,则的确与政治和阶级一类的概念无关”,但是并不能改变人们对立场一词含义的习惯性理解。当然,立场一词在具体使用中并不只限于政治性、阶级性的含义,还有许多其他含义。正如后期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词的意义即用法(或译‘在其使用中’)”,“立场”一词的种种具体含义也显示在其不同的使用中。不妨就拿我最近一个月间所读到的三篇文章对“立场”的使用为例,对此作简要的说明: “立场”这两个字真是久违了!一讲就容易让一些人联想到“左”。当今兴讲“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然而,“学术”就不涉及立场了吗?有一句话话糙理端,叫“屁股决定大脑”,这对学术就不适用了吗?衡量学术水平,跟立场、观点、方法无关了吗?苏东坡有一首七绝脍炙人口,题目是《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中就讲到了认识事物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求我们看问题要有更高的立足点,更开阔的视野,要选择最佳的视角。②显而易见,这篇文章是在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意义上使用“立场”一词的。而且,作者将立场、观点与视野、视角等词看成同义、近义词,混合、交替使用,不加区分,他还明确强调了立场与学术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中国学术界同仁对该文如此使用“立场”一词,绝对会接受和认同的。 批评家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宽容温厚的心胸,敏感细腻的感觉,以及坚定不妥协的人文立场,才能发现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艺术力量,与他们患难与共地去推动发展文学艺术。③该处对“立场”一词的使用没有突出政治性、阶级性,意识形态性也不明显,作者强调的人文立场,主要针对文艺创作和研究中众多受资本的、功利的逻辑所支配的负面现象而言的。对于文艺理论和批评来说,这种人文立场不但不会导致强制阐释,反而有利于对作品作出有创见的评论。 当张艺谋这代导演笃信世间只有物质时,当他们信奉现实主义为唯一的创作方法且把现实主义与写实主义等同起来时,当他们很少把镜头对准人性的幽微之境时,他们便拒绝了大多数高妙的存在。……事实上,在这样哗众取宠的时代,越是那些理想主义难以生存的时代,精英立场的坚持就显得弥足珍贵。众生下陷,只有其不断升高。但在中国,这样的理想主义者越来越少。电影界尤其如此。④该处“精英立场”的用法政治性也不明显,但突出了其理想主义的精神特质,用以批评中国第五代导演创作中世俗化、物质化的倾向和理想主义的失落,我以为是很恰当的。 以上三篇文章都属于文艺批评,它们虽然在不同意义(语义)上使用了“立场”一词,但共同之处在于:第一,就语义学角度而言,这些使用都是合适的、恰当的,能够在中国语境中为人们普遍接受或认可的;第二,就阐释学角度而言,在这些使用中,立场一词与观点、见解、看法、视域等等概念在含义上并不存在重要的区分;第三,对立场一词的上述使用,不带有任何强制阐释的内涵,同你的三个“前置”之一的“立场”,用法完全不同,语义也大相径庭。所以,你赋予“立场”以主动的、自觉的、有意识的、预先操控、决定了将阐释的文本的结论那种独特的含义,恐怕在中国语境中面对中国受众时,不容易被广泛接受。我因此而担心这容易导致对强制阐释论理解的歧义乃至误解,因为强制阐释论毕竟首先要为中国学界、中国读者所认可和接受。其实,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概念的使用或者用词问题,并不涉及你的基本观点、理路和推演逻辑,修改起来并不难。 下面,我想把话题拓展一点,谈谈红学研究中若干与强制阐释相关的问题。我不是红学家,只是对红学有点业余的兴趣,喜欢读一些相关的文章而已。但是,自从拜读了你的《强制阐释论》以后,再对照一下当下的红学研究,忽然发现,红学研究中存在着一些在我看来是相当典型的强制阐释现象。不揣冒昧,试举几个例子,可能会得罪某些专家、学者,敬请谅解。 比如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的红学研究。他在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上提出了独创的“秦学”来重新阐释《红楼梦》。虽然他文本读得很细致,但是由于预先设置了秦可卿的特殊身份作为阐释小说的关键和贯穿的地位,一切阐释都围绕这个先设的结论展开,因而这种细读不但是在有选择性地臆测,而且有时竟然罔顾历史事实。如他将林黛玉进贾府在荣禧堂看到的对联“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说成是隐射康熙太子胤礽,将秦可卿说成是胤礽的私生女儿,寄养在贾府,元春去世是因为秦可卿寄养贾府的秘密被发现了。⑤胤礽是历史人物,贾府和秦可卿是小说虚构的情景和人物,不能将二者等同起来。这种将文本与现实随意置换、等同的做法,固然显示出作为作家的刘心武先生的丰富想象力,但胤礽从来就没有女儿这一铁的历史事实却证明他的“秦学”难以成立。所以,我认为,总体上说,刘心武先生的红学研究属于强制阐释,它将《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的文学世界肢解了,目的只是要证明其“秦学”主张的合理性,实际上对普通读者理解《红楼梦》并没有带来什么好处。 又如著名文艺理论家刘再复先生,他学问渊博且富独创性。他的《红楼梦》研究,也很有成就,提出了不少精辟、独到的见解,颇给人启发,但也有一些看法有那么一点强制阐释之嫌。如他曾用李泽厚先生“自然的人化”论(其实来自马克思的《巴黎手稿》)解释绛珠仙草与林黛玉的关系,说绛珠仙草是“自然”,后来成为绛珠仙子、转世为人还泪是“人化”。⑥这种解释是先设定“自然的人化”为阐释的理论出发点,然后将人物命运与此机械地对应、类比,这既不符合《红楼梦》本身的叙事,也不符合李泽厚先生的原意。另外,刘再复在《红楼四书》中将《红楼梦》与中国的儒、释、道和西方的基督教、存在论等哲学美学思想结合在一起研究,将贾宝玉比作基督、释迦牟尼等;⑦又在《红楼梦悟》的批评集里提出《红楼梦》可视为与《伊利亚特》《奥德赛》一样的“史诗”的观点,认为《红楼梦》具有西方史诗的某些特点,尤其是《红楼梦》高超的叙事技巧和混沌的神话氛围与西方史诗比较接近,因而可以算是“中国的史诗”。⑧有学者批评这两种解释“很牵强,有生拉硬扯之嫌”。⑨这个批评在我看来是有道理的,因为,上述这种脱离了小说创作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预先设定基督教、佛教以及荷马史诗与《红楼梦》有内在相似性、可比附性,再从小说中寻找一些叙述或描写材料来论证这个预设的结论,这恐怕多少有些强制阐释的味道。 再如有的学者通过女性主义、荒诞性这样两个后现代主义经常使用的概念来解读《红楼梦》,认为《红楼梦》中林黛玉、晴雯、尤三姐等女子对自我命运的认识与抗争,与西方女性主义对女性的界定与评价比较类似,体现出后现代主义“消解中心性、秩序性、权威性”等特点;论者还把《红楼梦》中出现的神话描写和各种梦境、仙道的描写以及主人公的奇幻身世看作是“荒诞的”,与后现代主义讨论的荒诞性有一致之处。⑩可见其研究思路是以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某些思潮、概念生吞活剥地套用到《红楼梦》的阐释上,作生硬的比附性解读,得出二三百年前的中国小说《红楼梦》具有西方后现代特征的结论。这无疑也是一种强制阐释。 类似的例子在当代红学研究中不是个别的,而是多有发现。这不仅仅是我这个红学圈外人的感觉,红学界也有不少学者有此同感。由此,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强制阐释不仅仅是当代某些西方文论的缺陷,也是当前某些红学研究的弊病,而且其阐释的强制性和强制度并不亚于西方文论。看来,强制阐释论不仅仅适合于批评某些当代西方文论,而且适合于对红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领域)中的某些弊端进行有效的批评。就是说,它有覆盖中西的普遍阐释力,因而对于纠正当代中国文论批评中存在的某些不足和缺点,建设更加健康、丰富的文艺理论,也有着直接而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由此往前追溯,我还想到了鲁迅先生1927年写的关于《红楼梦》评论的一篇小文,其中有一段名言至今仍然给人以极大的启示:对《红楼梦》一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11)这里仅就与本文相关的话题,对鲁迅这段话谈几点我的粗浅体会:一是鲁迅实际上提出了现代阐释学关于不同理解者(此处指经学家、道学家、才子、革命家、流言家等等)对所要理解的文本必然有各自不同的“眼光”即“前见”“视域”,他们必然带着各自的前见(眼光)进入理解和阐释过程。二是这些理解者的前见(眼光)和立场是一致的,很难以是否主动、自觉来区分有无立场,而且似乎也不必要作这种区分。从经验角度看,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对人对事采取某种立场(广义的),不一定都是自觉的,相反,常常是不自觉的、身不由己的,这样就与前见(眼光)没有根本的区别。三是前见(眼光)和立场虽然不完全决定阐释的结果,但必定参与到整个理解、阐释过程中,对阐释过程和结果有一定的选择指向或导向作用,虽然在与文本视域发生矛盾时会不断修正、改变自身。鲁迅所说的这几种人,其前见(眼光)和立场对其阐释结果显然有直接的导向性影响。四是这几种人对《红楼梦》所作的阐释(即在《红楼梦》中所“看见”的),我认为都是强制阐释。鲁迅对这些阐释都是持批评和否定态度的,虽然他们多数不一定有自觉、明确的理论立场,而只是无意识的或直觉的。五是从鲁迅的这个批评我们可以看到,早在红学研究初创时期,强制阐释的情形已经出现,并且已经相当严重。所以,我们在批评某些当代西方文论存在强制阐释的毛病时,千万不要误以为我国当代文论中这方面的缺陷,完全来自西方文论的消极影响,实际上病根还在我们自己身上。 注释: ①参见《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北京: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②陈漱渝:《重提治学之道——从陆建德先生的两篇文章谈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1期。 ③陈思和:《再说说文艺批评——为第二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而作》,《文汇读书周报》2015年2月10日,第2版。 ④徐兆寿:《张艺谋与那一代导演的宿命》,《文学报》2015年2月12日。 ⑤刘心武:《红楼望月》,太原:书海出版社,2005年。 ⑥据刘再复2011年6月28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所做的“《红楼梦》与西方哲学”的演讲。 ⑦刘再复:《红楼四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⑧刘再复:《红楼梦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⑨刘永良:《对刘再复〈红楼梦悟〉的不同看法》,《红楼梦学刊》2014年第5辑。 ⑩孙波:《红楼梦的后现代特征》,《赤峰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11)鲁迅:《〈绛洞花主〉小引》,《集外集拾遗补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