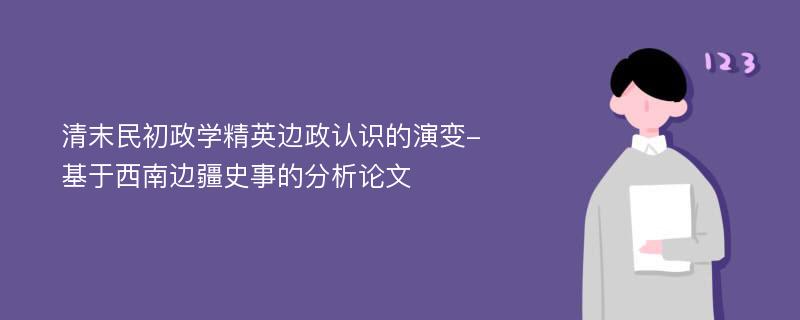
清末民初政学精英边政认识的演变
——基于西南边疆史事的分析
段金生
摘 要 :传统帝制时代的“天下观念”在晚清时期开始发生根本变化,国人的主权观念及对边疆民族问题重要性的认识,都有了新的发展。清末姚文栋关于滇缅界务问题的认知,反映出经过长期与欧美异型文化的接触,加以晚清以来对边疆民族地区事务的实践,近代国家主权观念已逐渐清晰,对边疆族群与近代国家建设互动关系的认识日益深入。但此时,传统帝制时代的“天下观念”并未完全破除,对近代主权国家疆域理念的认识尚在逐步形成中。民初川军援藏过程中地方实力派、北洋政府中央等各派政治人物对西藏问题相关认知的表述,表现出与清末相较,社会各界对边疆民族问题的认识,已经有了显著变化。但是,“五族共和”“民族平等”及“蛮夷”等词汇的普遍性交互使用及表述,说明仍未完全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主义取向的边疆民族认识理路,近代与传统认知的融合尚未完成。各派政治人物对西藏问题所持态度的差别与变化,不仅是各自利益或政治目标诉求的不同,也是北洋时期政治统一性缺失场景的突出表现。这些都说明,边疆民族问题不仅是边疆民族地区的事务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政治隐喻。晚清、北洋时期关于边疆民族问题的认知与实践,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边疆民族问题讨论热潮的重要基石。
关键词 :主权;滇缅界务;援藏;边疆民族
最近10多年来,中华民国边政研究的话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注] 例如,最近由张宪文与张玉法主编、两岸四地学者合著的18部《中华民国史专题》中,专门有《边疆与少数民族》专题,充分表现了近年学术界对边疆民族问题研究的重视。参见王 川等《中华民国史专题》之第13卷《边疆与少数民族》,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为行文方便,对文中提及的先贤前辈均免称先生而直呼其名,非为不敬,特此说明。 这一专题的研究主要在实践与认知两个层面展开。所谓实践层面,主要是指政策性、制度性的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呈现出“政治社会”的特点,[注] 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修订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第18页。 在政治史为主导的话语格局下,重视中华民国时期边疆民族地区政策性、制度性等实践性内容的研究,自然是应有之义。所谓认知层面,主要是指学术史或思想史的探讨。这是近年来学术界取得较为丰硕研究成果的领域。伴随近年来对边疆民族问题的关注,对近代尤其是中华民国时期学人及政治家对边疆民族问题思考的反思也日益成为学术界广泛讨论的话题。总体来看,目前学者们在讨论中华民国边政研究时,不论实践还是认知层面,关注的视野较为集中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华民国的成立,标示着传统帝制的解体,也意味着晚清改革的破产,但北洋时代中央权柄更迭频繁、地方实力割据称雄景象的突出与普遍,中华民国史领域的学者很长时期对北洋时代的重视有限。然而,历史的发展是延续的,在北洋时期(包括南京临时政府)共和政体的确立、反复与最终确立的过程中,晚清改革进程对其影响甚深,而其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能够初步确立党治政体的基础。探讨中华民国边政,不仅不能忽视北洋时代的边政实践与认知,更要了解近代中国内外变革大势下,晚清政府及士人的实践与认知。晚清政治、社会、思想、文化诸领域的发展与变化,是中华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基础。研究中华民国边政,不能忽略晚清这段由传统帝制向近代国家发展历程中多样形态的探讨。
总体而论,晚清、北洋时期,学术界对新疆、外蒙古等北部或西北边疆民族问题关注较多(当然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西藏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将选择清末民初时期发生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两个较突出的事件作为例子,通过对事件中相关人物认知或言行的分析,来审视晚清、北洋时期边政认识的发展脉络,侧重于梳理时人对边疆民族问题重要性认识的演变过程。首先,就晚清国际秩序与国家形态激烈变化形势下,关于边疆民族问题的讨论略作线索性梳理。其次,通过清末姚文栋所著《云南勘界筹边记》中所表现的晚清士人或知识精英关于滇缅界务涉及的族群、边疆政治等相关问题的思考,来分析清末主权国家观念的发展及其与边疆民族问题的互动关系,以更清晰地认识这一时期边疆民族问题在这一转型时代变化发展的面相。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对晚清社会群体分类的探讨,故在讨论时采取了宽泛化的方式处理,将士人与知识精英等同。再次,以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组织援藏西征军过程中,尹昌衡等相关政治人物的言论为题进行讨论。最后,综述清末、北洋时期的“边政”认识与实践对思考传统“天下”观念与近代国家建设,及其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疆民族研究热潮之间沿袭与变革的复杂关系。鉴于本文并非关于晚清、北洋政府时期边政认知与实践的全景式研究,仅是择西南边疆两个突出事例的重要关节点进行探讨;且并非直接从思想家或学者的相关思维认知表述入手,而是通过具体的边疆民族问题或事件中相关政治人物的实践思维或言论进行考察。因为,实践与认识彼此相辅相成不能割裂,政治人物实践过程中的认识更表现了当时社会认知层面的复杂内容。总之,应从多维的立体思维来观察历史发展的复杂演进脉络。中华民国边政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边政,虽然常被学术界视为边疆民族研究的第二次热潮,但此次热潮的出现并非突然,是晚清、北洋时期统治层及知识精英,包括社会大众对边疆民族问题思考与实践累积之结果。
一、“天下”观念的“动摇”:边疆民族问题在晚清视野中的渐变
近代中国在由传统“天下”国家向主权国家建设的形成过程中,边疆民族问题形态之演变一直是观察这一国家政体变革的重要因子。梁启超在1901年曾言,斯时之中国乃“过渡时代之中国也”。[注]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1901年6月),载梁启超著,吴 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第2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10页、第711页。 这一“过渡时代论”,广为学术界所引用,所论及的国家主权、民主政体等,一直是学术界讨论颇多的议题。萧公权在讨论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历程时也言:“自秦汉以来,专制天下之政治思想,一脉流传。千余年中,虽间受攻击,而根本未能动摇”;时至晚清,在外力因素下,“中国数千年闭关之局,遂不复能继续保持”,举国上下才“知旧章之不足用,思变法以图存”。[注]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507页、第663页。 梁氏、萧氏虽然在具体表述上各有侧重,但都强调了传统帝制向近代国家形态发展这一基本线索。这一激烈的变革时代,按学术界的主要叙事表述,包括了晚清与中华民国前后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的政治场景虽然表现有异,但政治思想的脉络却彼此联结,边疆民族问题在其中之表现尤为凸显。
文化主义是解读传统帝制时代社会政治形态的重要叙事方式与视角,其突出内容就是“天下”观念与“夷夏”思维。在传统“天下”观念中,“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注] 石 介:《中国论》,载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6页。 许纪霖认为,天下具有双重内涵,即理想的伦理秩序和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空间的想象,古代中国的天下空间经常处于弹性的变动之中。[注] 许纪霖:《多元脉络中的“中国”》,载葛兆光,徐文堪等《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0~31页。 不过,虽然自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事实上,中国历代正史中的《地理志》都有比较明确的疆域范围。虽然客观上,文化中心论在传统中国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但实际上,历代王朝均有相对稳定的控制范围,而且也认识到自身之外尚有其他不同文明形态的存在:内服、外服的使用,“并不意味着中国和邻邦或藩属之间没有疆界”。[注] 杨联陞:《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载[美]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8~19页。 不过,秦汉以来之政论,“皆以‘天下’为其讨论之对象。二千年中,未尝改移”。[注]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666页。 虽然事实上自清朝康熙时期已经有开始向主权国家转型的迹象或内容,[注] 李大龙的研究就认为:虽然鸦片战争之后,“近现代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理论严重影响到清王朝的内政和外交,”但“清王朝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并非始于这个时候,而是早在清军入关后不久即开始,开始于康熙皇帝时期的一系列边界条约的签订及其划界行动即是显著证据”。(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6~137页。)姚大力则认为:一方面,“中国”实际上并不可能把自身的边界真正延展到整个“天下”;但另一方面,“每个王朝又总是力图将本朝看作是更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的一个历时性共同体的延续。这个历时性共同体就叫做‘中国’”,“中国古代甚至已经出现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具体的王朝实体而带有抽象品格的国家观念”。(姚大力:《变化中的国家认同——读〈中国寻求民族国家的认同〉札记》,载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40~141页。) 但时至道光前期,“天朝”观念仍是朝野主要认识。
有日本学者统计了《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两部记载道光时期(1821~1850年)外交史料中,关于“天朝”与“中国”词汇使用频率的变化:前一书记载的道光朝最初十年使用的“天朝”次数达50余次,而“中国”不足10次。后一书主要收集了道光十六年(1836年)以后的外交史料,其卷一记载的时间范围是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至十七年(1837年)四月,使用了“天朝”6次,“中国”5次;卷二记载的时间范围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一月至五月,使用“天朝”仅1次,“中国”则14次,“中国”的使用频率超过了天朝。整体上,道光十年(1830年)至二十年(1840年)之间,“天朝”使用的次数逐渐减少,而“中国”的频率相对增多。而据《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和光绪年间的《清季外交史料》来观察,“天朝”的使用频率已经式微,而“大清朝”“中国”的自称则成为主要。不过,这一研究也强调,“‘天朝’在概念上不管如何,但是和疆域概念是并不矛盾的。在疆界问题谈判中,‘天朝地方’‘天朝版图’‘天朝土司地方’‘天朝疆界’‘天朝边界’等词语频繁出现”;当时的疆界概念和主权国家体系中的国境概念并不相同,“虽然在道路的管理、征税的管理、特产品商品作物的管理等问题上设有明确的疆界,但疆界内部的统治体系,和近代主权国家的一元化统治是明显不同”;认为“把天朝看作是在地理上具有无限延伸性,是不妥当的”。[注] [日]川岛真:《从天朝到中国——清末外交文书中“天朝”和“中国”的使用》,沈中琦译,载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70页、第273页。 道光、咸丰以后,“天朝”“中国”概念使用频率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传统文化中心主义的“天下”观念向近代主权国家形态的转变,“天下”观念下的弹性疆域思维也日益向主权国家的明晰疆域认知发展。萧公权就称道光、咸丰以后,“二千年之‘天下’观念,根本动摇,而现代国家之思想,遂有产生之可能”。[注]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666页。 在此形态下,传统的边疆民族问题形态也发生了变化。
晚清在向近代主权国家转型的过程中,边疆民族问题是内外冲突交织的重要领域。新疆、云南、西藏、外蒙古诸边疆民族地区先后都发生了内外交逼的严重问题,除了政府的政治实践外,晚清士人及知识精英也在深刻思考这一问题。“海防”“塞防”之争,实则就是统治者及知识精英在“天下”观念动摇的背景下,对边疆民族地区在国家疆域中的形势认知冲突的一次突出表现。双方观点的分歧,既是晚清王朝由传统帝制国家向近代主权国家转型过程中,对国家疆域形态的不同认知,也可以视为统治层对边疆民族问题认识的差异。[注] “海防”“塞防”之争,其实是一种观察问题视角与关注重心不同之论。关于此点,中华民国时期李寰就言:“清李合肥与左文襄曾有海防陆防之争。以当时情形论,老成谋国,各有卓见。迨甲午一役,海防失险,而国家大本,不致遽及摇扤者,说者以文襄经营新疆有备,陆防足恃之力亦多焉。今者倭寇掠华,沿海尽失。实现文忠筹海政策有待,似宜先继湘阴遗志,巩固陆防,以为重建海防之基础。”参见李 寰《新疆研究》,中国边政学会发行,1944年,第1页。 最终,清政府采纳“塞防”派之论,表现了清王朝重视王朝疆域的维护,也说明此时清王朝统治内部仍未具备近代主权国家的完全意识。当然,就客观形态而论,此时的边疆民族问题与清王朝面临的其他问题相比,尚非最突出与急迫的关键问题。金冲及就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来的刺激使中华民族真正产生了严格和自觉的整体感”,但直至甲午战争的刺激,“救亡”才成为了中国人民最沉重的议题。[注] 金冲及:《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载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页。 中国近代主权国家的建设进程与民族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金冲及所论的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正说明甲午战争之后的清朝,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主权国家思维日益彰显的形态下,边疆民族问题才受到政府及朝野人士的更多关注。王汎森关于清朝现代“国家”概念形成的分析,充分说明了近代主权国家形成的困难性。[注]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99~205页。 但反之,清朝“国家”思想的逐步形成,自然更使边疆民族问题受到关注。
Numerical simulations of urbanization impacts under hot weather conditions in Nanjing
1894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专门讨论“边防”,开篇即言“自古以来,皆有边患”,但今日“不料为边患者,乃更有海外诸邦也”;并称“外感纷乘,四肢不保,一举一动,皆蹈危机,腹心虽存,岂有生理?此边防措置所以不可疏也”。上述之认识,反映出边疆民族问题在晚清统治者与知识精英心目中日益受到重视,但仍是“四肢”与“腹心”的关系。甲午战争前后,边疆危机趋于更重,统治者与知识精英的呼吁更浓。郑观应言“防边于今日,盖亦戛戛乎难图之矣”。[注] 郑观应著,辛俊玲评注:《盛世危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422页、第451页。 孙中山称“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剂,实堪虑于目前”。[注]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9页。 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在近代主权国家观念日渐形成的场景下,边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愈加引人关注,清朝统治层及知识精英都进行了认真思考。
维新变法与清末新政,是晚清王朝加快建设近代主权国家以图生存的努力。在这个渐次展开的过程中,清王朝强化了对边疆民族地区统治的各项措施。日本学者茂木敏夫认为,19世纪70~80年代,清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统治实践方式的调整,是“放弃以往追认周边的版图统治方式,迈出了将其整个版图按文化一元主义的方向整合的一大步”,是通过“版图的整合、即边缘地区的中国化而引出的确立‘中国’疆域之问题”。晚清王朝的这一政治实践,“同该时期整个思想界的状况有着密切的联动关系”。[注] [日]茂木敏夫:《清末近代中国的形成与日本》,孙 江译,载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60页。 其时正是民族主义思想日益高涨的时期:中法、中日战争之后,“由于增加了主权观念,使中国民族主义,具备了族类、文化与主权三个要素”,并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官绅所广泛讨论;此后,“所谓‘国’的自我肯定,随之有迅速发展”,主权观念、民族主义思想更加充实。[注] 王尔敏:《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观念》,载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1~32页。
晚清在不断受到西力冲击的背景下,统治者及知识精英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传统“天下”观念的现实情境。近代主权国家的认知虽然缓慢,但围绕主权国家建设目标与途径方面的论战日趋激烈而复杂,清季、民初是这一论争最为激烈的时段之一。清末新政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及其反应,也深化了统治者及知识精英对边疆民族问题与主权国家建设关系的认识。当前学术界在探讨清末边疆民族问题时,多置于近代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进行,讨论多集中于近代民族主义问题,关于清末时期统治层或知识精英对边疆民族问题认知的复杂变动的研究则较弱。同时,既有研究关注的目光较集中关注于新疆、蒙古、西藏及东三省诸地,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探讨相对薄弱。但是,近代西南边疆民族问题是中国内外大势下的产物,认真观察时人对这一时期西南边疆民族相关问题的思考或认知,对理解近代中国主权国家建设、疆域形成应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教师教学分为课上和课下,课堂教学与课下教学的方式与构成都需要优化。课堂教学上,需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的教学设计不能只考虑课堂,课下教学也是教学的一个环节,应当将课堂与课下形成一个整体,课堂上吸引学生注意,使学生配合教师完成教学任务,课下通过教师的引导,顺利完成作业,减轻学生负担。
二、“非化外之民”与“非域外之地”:清末统治层或知识精英关于滇缅界务的认知
近代以降,在边疆民族地区的诸多内外问题当中,与邻国的界务问题是其中最突出者且涉及面广。在“天下”秩序正在解体、主权国家观念逐渐明晰的过程中,其时的士人、知识精英如何看待边疆各族群?对界务问题有什么样的思考?这些都是我们观察晚清王朝如何建设近代主权国家的重要维度。自1885年英国武力征服上缅甸后,中英关于滇缅问题的纠葛日多,边界问题尤为突出。1890年,薛福成接任驻英公使,专门派遣姚文栋考察印缅商情和滇缅界务,以图了解边界具体情形而不致在中英谈判中陷入被动。1891年4月,姚文栋到滇,时任云南总督的王文韶就向朝廷奏请,准许姚文栋留在云南差遣委用,以有益于边务。[注] 王文韶:《云贵总督片》,姚文栋:《云南勘界筹边记》,载马玉华《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西南边疆卷(四)》,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1页。以下所引《云南勘界筹边记》中相关内容,均引自马玉华《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西南边疆卷(四)》。 此后历经1年,姚氏根据查访云南边境情形,著成《云南勘界筹边记》,详细陈述了他对云南边疆族群与边界、边界与主权、滇缅界务具体情形等诸多问题的思考。其相关见解及与朝薛福成、王文韶等要员的往来函文,对理解清末统治层与知识精英关于边疆族群、国家主权、传统“天下”思维变革等的认知颇具价值。
传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周边邻国并非没有边界,但总处于不断盈缩变化之中。长期以来,中国中央王朝对中缅边境,在“天下”主义的思维下,多求边境相安、不喜多事,认为“内地”“外藩”都同属于“天下”,对“外藩”施之以“守在四夷”之策即可。但近代以后,这种传统的文化疆域思维与西方形态的明确主权思维日益冲突。[注] 参见朱昭华《中缅边界问题研究——以近代中英边界谈判为中心》,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9~27页。 在这个冲突过程中,中国统治者、知识精英对边疆族群、疆域的认识在不断改变,这一改变是与整个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的转变交织在一起的。
姚文栋也认识到边疆各族群对维护边界、稳定国家疆域的重要作用。在《野人山说》一篇中,姚氏通过考察,称野人山即腾越西境群山,“非域外之地也”,“山中野人,额设抚夷以治之,辖于诸土司,非化外之民也”;“诚不宜有疏失也”。在相关论述中,姚氏认识到云南边疆族群的多元化,虽然仍按照中国传统“夷夏”话语体系进行表述,但也看到土司这一西南边疆的特殊族群政治模式对维护近代主权国家疆域的重要性。同时,姚氏承认中国传统治边思维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形态下的开疆拓土意识的巨大差异,称西方越重洋万里而来,尚且对我国边境自然环境了若指掌,而“吾守边将吏在数百年里间,对之如望洋,查[杳]然不知其所及”,这些都折射了传统“天下“观念与近代主权国家在疆域、边界问题上的不同政治诉求。[注] 姚文栋:《云南勘界筹边记》,载马玉华《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西南边疆卷(四)》,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7~28页。
历经晚清的实践,中华民国时代的国人国家主权观念更加明确,边疆民族地区在国家疆域构成中的地位也更加明晰。中华民国已经具备了近代意义的领土主权观念,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以及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的相关内容,都已将边疆民族地区与传统内地行省一同视为国家疆域的重要构成。[注]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称:“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1912年1月1日),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页。 然而,边疆民族地区在清末就开始动荡的形势并未缓解,反而在中华民国初建、权威不显、统治根基不固的形态下,日益严重。西藏、外蒙古、新疆等地发生的问题,在民初边疆民族地区诸问题中均呈现出激烈的色彩。由于西藏地缘环境的特殊、政治及宗教形态的复杂等多维因素的影响,与其相邻的四川、云南在辛亥革命后都进行了援藏的政治行为。其中,四川的援藏西征活动,对川局及西藏局势都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注] 此次川军援藏,导致了四川都督的更迭,使初步稳定的四川政局再次动荡,此后川局日加复杂。川军西征,也使西藏局势面临变化,袁世凯中央政府、西藏、英国诸方就川军西征进行了复杂博弈。 审视川军援藏政治行为中相关人物的言行,既可以观察中华民国时期国家主权观念日益明确的发展历程,也能呈现出清末民初社会各界对边疆民族问题认识的延续与调整,又可窥视民初政局的脆弱与复杂,表现了边疆民族问题与近代主权国家建设的密切关联。
姚文栋对云南边境的勘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姚氏所著《云南勘界筹边记》,其中包括了其本人的一些认识,而其与薛福成、王文韶等官员的往来函件,则可从另一维度反映了清末朝廷要员关于边务问题一些看法。
对于四川地方政府之建议,北京政府回电称同意四川方面之见解,已“由院电请蔡都督迅派劲旅,与尊处协同镇抚”。[注] 《国务院复尹昌衡电》(1912年5月18日),载曾业英,周 斌《尹昌衡集》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1页。 从电文内容可以看出,滇、川地方政府都表达了援藏之认识,北京政府也意识到西藏问题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重要性。不过,政治人物的实际行动多受到政治利益的支配,四川、云南援藏之建议,虽然公开宣言都是为了保护西藏,维护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但事实上双方亦各有策划。在政治权衡之下,不仅川、滇地方政府态度如此,即使北洋政府中央对西藏问题的态度也常随政治时势而变,反映出边疆民族问题与全国政局的密切联系。
西伯利亚白刺叶中总生物碱的大孔树脂纯化工艺及抗氧化活性研究 …………………………… 其曼古丽·吐尔洪等(20):2763
总体上,姚氏关于界务问题上“人和”思想的阐述,事实上表现的是中、英双方不同的政治、文化思维,而其称边疆族群为“夷”,称列强为“洋”,既呈现了传统“夷夏”思维的继续,又表现了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对世界秩序认识发生的变化。他们的相关言论与认识,既有传统“天下”主义观念的延续,但又表现出向近代主权国家疆域思维转变的趋向,中华民国的成立,即是这一趋势的重要表现。
姚文栋在看到土司制度对保持或巩固近代中国主权国家疆域重要性的同时,也认识到变局社会形态下对土司制度进行调适的必要性。在《潞江下游以东皆中国属地考》中,通过对孟艮土指挥使、整欠土指挥使、猛勇土千总、整卖宣抚司、景线宣抚司、六本土守备、景海土守备、猛撒土千总、猛龙土指挥同知、补哈土千总等土司职官属地的文献考证,指出“此潞江下游以西之地十也”,但“皆有属中国者”。通过对木邦土司、蛮暮土司、大山土司、猛育土司的文献考证,得出“亦中国地也”的结论。这些“皆中国旧土司,至今犹守本朝印信。英、法两国觊觎不敢取,而滇中视若化外已久,此深可惜也!”[注] 姚文栋:《云南勘界筹边记》,载马玉华《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西南边疆卷(四)》,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5~39页、第43页。 历史梳理与实地考察的综合,让姚文栋认识到了土司这一边疆族群政治力量对维护国家疆域的重要作用,认为土司及其辖下的“夷民”对巩固中国西南边疆疆域稳固具有不可替代性,土司统属区域是中国国家疆域的重要组成。这样的认知,既有传统“天下”观念内服、外服思维的体现,也表现出中国传统帝制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模式的多元化,及其向近代主权国家发展进程中的调适形态。同时,姚氏对土司制度的调适问题也有思考。姚文栋在给云贵总督王文韶的说帖中称,自乾隆以后,“缅甸与中国多有未经清晰之界”,使英国侵缅后得以利用滇缅界址未定的形态,积极向外拓展。但在时代变革因素下,土司这一边疆族群政治体制与巩固主权国家疆域之间存在着内部的紧张关系。近代之前,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流土相间”办法,是因为“盖滇民之耕种于其地,贸易于其地者,是以万计,设流官以治之,与土司相错处而疆域定矣。文教日兴,则异俗自化,不难渐底于大同”。不过,在形势大变的情况下,“新疆、台湾皆改建行省”,而后外人不敢以兵再涉其地,其亦深得因时制宜之意。[注] 姚文栋:《云南勘界筹边记》,载马玉华《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西南边疆卷(四)》,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5~39页。 姚氏肯定了土司制度这一传统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模式,但改设行省之议,则表现了在变局下治理边疆民族地区模式变革的紧迫性,这事实上是近代主权国家思维日益明晰的表现。
姚文栋不断将他的这些认识与清朝地方大员及外交官员进行交流。《云南勘界筹边记》的下卷,主要内容就是姚氏向王文韶、薛福成等清朝要员报告关于滇缅界务问题的相关函文,反映了他们对边务相关问题的思考。
按照姚文栋在“自跋”中所言,上卷所论内容“专言地利,未及人和”,故撮其大旨而补为下卷,侧重从“人和”因素阐释他对边界、疆域、族群、边疆政治的认识。在中英关于滇缅边界的纠纷上,姚氏认为,英国初意是“滇之西欲与中国分大金沙江为界”,而滇之南则“欲分潞江下流为界”。但由于迁延数年,“中国迄无定论”,使英国“窥知我地学之蒙昧矣”。此语表明,与近代西方工业国家明确领土边界相较,中国传统“天下”疆域思维则显得“蒙昧”。姚氏之认识,说明了清朝在近代主权国家的建设中,逐步认识到自身的局限,但这个过程是缓慢的。这个缓慢的过程,也说明了其时清朝统治者及知识精英对主权国家疆域思维的认识,总体上尚不清晰。此前,中国与英国关于缅甸问题的交涉充分表明此点。此外,姚氏还阐述了自身对边务问题的认识,强调边地之要,关键在于兵力强、民气强、人才强:“新疆肃清之后,俄人拱手而还伊犁,畏兵力之强也。安南之役,法人扰闽而不敢扰粤,畏民气之强也。至于人才之强,不必远征也,观于黄正林、张天明而可知矣。令边地当时司阃者亦能如是也,守郡者亦能如是也,彼乌敢轻我边内无人而唯其所欲为哉?然则地利人和交相为资,盖不可缺一者矣。”[注] 姚文栋:《云南勘界筹边记》,载马玉华《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西南边疆卷(四)》,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40页、第42页。 边吏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界务问题认识尚且如此,其时社会大众的反应略可窥知,具有近代主权国家疆域理念、边疆族群认知的群体尚属少数。
在给清朝相关机构或官员的函文中,姚文栋再次说明了土司政治与国家疆域形成的复杂关系。在给王文韶的说帖中称:“明人筑关,未尝以关为界”,而边地险要皆在关外之地。并且,滇缅之间的界址无定,“乃以土司之去留向背为转移,而土司所有之分地,则皆随之未改”。[注] 姚文栋:《云南勘界筹边记》,载马玉华《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西南边疆卷(四)》,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51页。 在给薛福成的电文中,姚氏明确称,云南边地有三大要务,分别系滇西、滇南、滇北,“不可不于勘界之先,熟筹而审处之”,三个区域疆域的稳固都与土司关系密切。姚文栋同时向薛氏强调,若按国际公法“遇荒地不属邦国管辖者,无论何国皆得扰为己有”,如此当先以兵预占,则“可以先入为主”;故对于边地界址,应踏勘、询方周详而悉心筹划,才能“争先着而杜后患”,此为“巩数千里之边防,为亿万年之久计”。[注] 姚文栋:《云南勘界筹边记》,载马玉华《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西南边疆卷(四)》,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56~58页。 姚氏还向王文韶建议,要加强边境一线的控制,这一地带系险要所在,而“弃险即无异弃腾,弃腾即无异弃滇故耳”,弃险则“恐致如蚁穴之溃全堤”;强调其并非为这一小块区域而争,否则“区区关外数百里之地,去之亦何损于中国之大!”[注] 姚文栋:《云南勘界筹边记》,载马玉华《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西南边疆卷(四)》,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51页。 姚氏与王文韶、薛福成上述的文书往来,表现了此时清朝官员与知识精英在滇缅界务问题上的一些共性认知。
有效地教学应为孩子提供有价值的活动材料促使幼儿主动建构知识,现在我们的教学活动大多还是以主题活动为主的。主题背景下的晨间户外锻炼活动是以主题为背景,教师结合主题目标有目的地创设与主题相关联的各种形式、有侧重的投放材料开展体育锻炼活动,关注幼儿各种经验、能力的综合,让幼儿的户外体育活动有了更多的探索内容,其目的在于有效的提高户外体育活动的质量,培养体魄健康、乐观向上,积极勇敢,敢于挑战,个性发展的人,使幼儿的整体素质得以发展。
三、“西藏关系全国”:民初四川援藏行动中相关言行的政治隐喻
在近代世界格局重大转变之际,晚清疆域思维的发展变化十分复杂。在19世纪70~80年代边疆危机的冲击下,90年代以后,朝野各派的疆域、主权思维逐渐形成。1885年,英国占领上缅甸后,中英之间关于缅甸问题的争论日益突出。而在缅甸问题出现之前,中法关于越南的战争,使清朝与周边邻国传统的“宗藩”体制产生裂痕,不仅传统的藩属朝贡体制难以存续,而且,中国的西南边疆将失去屏障,与传统的国防观念发生冲突。[注] 朱昭华:《中缅边界问题研究——以近代中英边界谈判为中心》,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1页。 1885年,清朝中央政府在给驻英公使曾纪泽的电报中称:“前电英允共商善后,此时宜先照会外部云,缅无礼已甚,英伐之固当,但究系中国贡邦,此后英拟如何之处,全看其作何答复。至开谈,须以勿阻朝贡为第一义。”[注] 《使英曾纪泽致总署英俟印督到缅始决存灭办法电》(附旨),载王彦威、王 亮辑编,李育民、刘利民等点校整理《清季外交史料》,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76页。 可以看出,清政府虽然已经意识到缅甸存亡问题对中国疆域形态具有重要影响,但在外交实践中,却仍试图维持传统的“天下”思维,说明晚清政府的“国家”观念虽在不断调适,但传统观念仍然没有破除。
辛亥革命后,列强趁中国政局不稳,谋图分割在华利益,英国加快了策划分裂西藏的步伐。其时,达赖喇嘛虽在大吉岭,但听闻西藏扰乱且“华军自相残杀”,遂“意图乘时恢复”,于1912年9月回到拉萨,调集西藏本土军队进行驱汉活动,“阻断东西两道交通”,并谕告全国:“自今一概不许遵从汉人对藏之公文政令,其有汉人之处务须驱逐,无汉人之处亦须严防,务令全藏无一汉人足迹。”同时也要求川边藏传佛教区域“乘机独立”,川边各地纷纷响应,里化攻陷后知县被杀,盐井则降附,西康全境未被藏军攻陷者,南路惟有泸定、康定、巴安3县,北路则有道孚、瞻化、炉霍、甘孜、德格、邓科、石渠、昌都8县。[注] 尹扶一:《西藏纪要》,蒙藏委员会编译室印,1930年,第220页。 致使清季赵尔丰、傅嵩炑等人“自光绪三十年至宣统三年,七年中所辛苦手植之势力,遂告土崩瓦解”,[注] 华企云:《西藏问题》,上海:大东书局,1930年,第133页。 西藏情况万分危急。其时,西藏与内地交通断绝,相关信息无法电达内地中央政府,仅印度华商陆兴祺不断探查西藏信息,“随时将藏乱情形函电驰告北京、川、滇各处以图挽救”。是年11月,北京政府委任陆兴祺办理递信各事,关于达赖、班禅等应如何设法联络之处,“责成就近体察情形,随时呈报”。1913年1月,北京政府电告陆兴祺:“闻驻靖驻噶有名汪曲策忍及汪堆者,皆达赖心腹,该员可密为联络,示意噶札,告以达赖若能一意内向,中央必当予一美满希望。庶几藏事易于商办。此外班禅及著名各寺喇嘛等,应如何设法联络之处,即由该员妥筹速复”。陆兴祺不断与在印藏员频频接触,并“转大总统致达赖函电”,并“屡释共和真谛”。其后,陆兴祺被任命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注] 尹扶一:《西藏纪要》,蒙藏委员会编译室印,1930年,第193~194页。
在此危机时刻,邻近西藏的四川、云南地方政府都有援藏之行动。1912年5月11日,四川都督尹昌衡、张培爵致电袁世凯及国务院,言“前藏若失,边地势危”,后患不堪设想。需“赶紧筹援”,否则“英人借题代谋划,后悔何追?”建议准许四川地方政府筹拨陆军一支队,随同筹边宣慰使克期入藏。“西藏关系全国”,中央政府应“迅予统筹计划”。[注] 《致袁世凯及国务院电》(1912年5月11日),载曾业英,周 斌《尹昌衡集》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9页。 次日,再电袁世凯,明确强调“藏亡则边地不守,边失则全国皆危。民国初基,强邻环伺,莽之藏卫,即脱范围,内何以辑[缉]抚他族,外何以应付列强。”认为解决西藏之危局无非两端:一则为川、滇派军赴援,一则“收集驻藏陆军,背水一战”。[注] 《致袁世凯电》(1912年5月12日),载曾业英,周 斌《尹昌衡集》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0~131页。 上述电文表明,经过清末政治实践及民族主义思潮的浸润,政治人物已经认识到西藏与中华民国领土完整之间的有机关系,表现了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的明晰化,说明时人已经认识到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疆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地方政府对西藏问题持如此态度,北京政府的态度又如何呢?
《云南勘界筹边记》上卷主要考察了云南与缅甸边境地区的地缘环境、族群社会政治等内容。姚文栋详细论述了了滇、缅的地缘关系,认为“申画郊圻,慎固封守。内地且然,而况边徼乎?《易》不云乎:‘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未足,犹且设之,而况于自然之际险乎?”[注] 姚文栋:《云南勘界筹边记》,载马玉华《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西南边疆卷(四)》,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4~25页。 所论反映了传统“天下”观念“守在四夷”的思维与近代主权国家形态疆域认知之间的调适。姚文栋言自清初平滇之后,孟拱、孟养等地都首先内附,而后征缅之役,“孟拱、孟养皆抒诚效力”,今蛮暮、孟拱等土司犹有清朝所颁印信,故应向英国索还故地。建议与英国进行勘界时,如能收回瑞姑及两葫芦口,则龙川江一路可以无虞,此为上策;其次,亦须至大盈江入金沙江口而止,以保全南甸旧日之地。[注] 姚文栋:《云南勘界筹边记》,载马玉华《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西南边疆卷(四)》,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2~23页。 可见姚文栋在边界问题上,主张对边境地区积极经营,抛除了戒勤远略的历史传统,固守边界的近代主权国家思想已经较为明显。
辛亥革命后,四川局势本就动荡,成都、重庆先后成立了大汉军政府和蜀军军政府,彼此对峙,虽然双方最后统一,但内部局势一直未稳。“西藏为四川藩篱,藏固而后川固”,[注] 《致袁世凯电》(1912年5月11日),载曾业英,周 斌《尹昌衡集》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 西藏军队进攻川西,直接威胁四川的稳定:“藏失边危,河口、里塘相继告警,西藩一撤,全局皆危,势非大举,万难挽回。”[注] 《董修武等致袁世凯电》(1912年6月9日),载曾业英,周 斌《尹昌衡集》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9页。 在此情形下,“为巩固四川门户”,四川军政府组织西征军,由四川都督尹昌衡亲自率领,准备援藏。不过,四川军政府内部权势博弈激烈,尹昌衡离开,都督职务本应由副都督张培爵代理,但尹对张怀有戒心,为防其夺权,不以张氏代理,而任命其在四川武备学堂的老师、时任重庆镇抚长的胡景伊为代理都督。未料胡氏掌权后很快投靠袁世凯,一面排斥尹昌衡,一面打击张培爵,致使张氏辞职离川,而尹昌衡希望西征返川继续担任四川都督的愿望也最终落空。[注] 赖建侯:《胡景伊投靠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载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40页。 此后四川政局一直动荡,尹昌衡因失川督之职,曾回到成都,鼓动军队,“拒胡迎尹,威胁各界造成,几酿巨变”。[注] 《杨隽等控告尹昌衡之原呈》,《国民公报》1914年2月19日。 而尹昌衡主张西征,固有维护四川稳定、安定西藏局势之意图,但也不乏私心。在1914年就有川人指责其“窥边藏之富,倡为西征,张大其辞,蒙蔽中央,而祸边圉”。[注] 《邹稷光等具呈告发尹昌衡文》(1914年1月20日前后),载曾业英,周 斌《尹昌衡集》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81页。 此论是在尹氏受拘禁后向中央政府指呈尹氏之过失,虽有夸大或不实之处,也其实或也含有一些尹氏的真实意图。
本文作者赴欧洲考察,眼见当代高新科技与社会文化之于材料应用所带来的变化,以及对物我相互关系造成的巨大影响,有感而发,以综合材料艺术作为研究对象。希望在创作中改变主观性过强的表达方式,探索材料本身变化作为艺术语言的可能性。通过对陌生化创作原则的解析,介入艺术史上下文与当下文化语境中,得到不少体会,也摸索到一些具体做法。本文旨在强调物性对于综合材料艺术创作的重要性,同时也力图梳理自己在综合材料艺术创作中的思路,为今后从事相关艺术创作有更为清晰的定位。
我们以埃利斯的认知模型来分析一下蔡女士遇到的问题。在诱发事件A发生后,即两位时尚美女瞟了她一眼然后掩嘴而笑,她对A的解释是“她们发笑一定是觉得我的穿着太土了”,正是这一解释(B),才引发了她的C,即紧张情绪、生理反应(浑身发热、面红耳赤),以及后面行为(围上围巾,遮挡住半边脸并匆匆离去)。可以设想,如果蔡女士对同一情境做出另外的解释——她们可能在聊一件有趣的事情——她一定会继续享受与闺蜜的休闲时光。
在尹昌衡西征之前,云南重九起义后任迤西总司令的李根源对于四川与西藏政治关系,就如此评论道:“川乱以来秩序破坏,一切布置权行销灭,蛮烽复炽。而川军把持西藏,不许他省代谋,别具私心,不顾大局。但川边关系,乃川滇两省,祸不独在川。拟请中央,迅派大员为川滇边务将军,筹办一切。”[注] 《国务院电蔡锷请派兵会同蜀军进藏镇抚》(1912年5月18日),载吴丰培《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页。 云南如此指责四川,四川方面也并不放心云南。川军西征后,因滇军援川产生的疑虑,对云南援藏部队的路线也十分猜疑。尹昌衡就致电蔡锷,建议滇军由中甸线入藏,一方面此线入藏距离较近,另一方面也可避免川滇援藏部队彼此之间在军粮购买等方面产生掣肘。[注] 《致蔡锷电》(1912年7月3日),载曾业英,周 斌《尹昌衡集》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1页。 虽然最终蔡锷表示同意尹昌衡之意见,[注] 《蔡锷复尹昌衡张培爵电》(1912年7月123日),载曾业英,周 斌《尹昌衡集》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1页。 但双方之间的猜疑还是存在的。四川自为巩固川西门户起见,而云南不排除有借援藏而扩大地盘之图。1912年9月20日,北洋政府国务院发给云南的电文就称:“自前清设立川滇边务大臣以后,西之察木多等处,南之盐井等处,均已划归川边区域,先后派员设治,原电宁静以东属川,以西属藏等语,殊与近年事实不符”,“至川边抚剿,尹督既自任专办,筹兵筹款,皆由该督经营,滇自不必与争”。[注] 《国务院复蔡锷电》(1912年9月20日),载曾业英,周 斌《尹昌衡集》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16~217页。 北洋政府此语,表现了云南确有图谋川边之意。而北洋政府虽言要“保全领土主权”,但称“援藏一节,现饷款难筹,英人干涉,民国初建,岂容轻启外衅”。[注] 《国务院复蔡锷电》(1912年9月20日),载曾业英,周 斌《尹昌衡集》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17页。 因受英国之压力,北洋政府电令川军不得逾越江达以西,遵守清末西藏与四川的界限。[注] 《国务院电尹昌衡勿令川军轻进藏境》(1912年10月1日),载吴丰培《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3页。 在援藏行动中,滇、川地方实力派皆各有算计,表现了民初中央政府权威的脆弱,说明边疆民族问题的发生,与内地社会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北洋政府电令川军停止进藏行动,表现了边疆民族问题的产生与列强的侵逼存在直接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华民国政府虽然具备了近代主权国家意识,但其应对边疆民族问题的态度是以政治博弈为转移的。
中药制剂外用治疗斑秃疗效的Meta分析及选方用药规律探讨 …………………………………………… 雷 鸣等(6):828
人的认知是有延续性的。虽然进入了民主共和时代,但传统帝制时代的边疆民族认知或“夷夏”就随即发生变化了呢?显然并非如此。较之清末时人的主权观念,民初社会各界的国家主权意识已经更加明确,充分认识到边疆民族地区对维护或巩固国家疆域的特殊性与重要性,较之晚清塞防、海防之争时,对边疆民族问题的认知有了根本改变。然而,如同姚文栋在论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族群时,仍不时表现出传统“夷夏”观念,民初社会各界在呼吁保全西藏、强调西藏为中国领土的同时,“蛮人”等传统词汇仍不时充斥于相关文电中。当然,具体表述也呈现出民初兴起的“五族共和”观念。
1912年6月8日,四川军政要员在四川铁路公司开会,讨论西征问题。尹昌衡陈述了西藏问题对四川及中国之重要性:“西藏虽为中国之西藏,其实为四川之门户,对于中国为藩篱,对于四川有密切之关系。”并慷慨陈词,言“西藏不失于腐败之满清,而失于新建之民国,诚莫大之耻”,希望川军将士“刻刻以恢复西藏、巩固边疆、光荣祖国为念,俾去者有勇往直前之心,未去者[有]预备调遣之想,则西藏不难恢复,边疆不难巩固”。[注] 《在全体军官会议上的讲话》(1912年6月8日),载曾业英,周 斌《尹昌衡集》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1页。 6月上旬,在给川军发出西征令中称:“西藏为中国属土,屏藩吾蜀,素称恭顺。”[注] 《西征军令》(1912年6月上旬),载曾业英,周 斌《尹昌衡集》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1页。 其考虑虽多强调四川与西藏的地缘利益,但疆域主权意识却十分浓厚。不过,在民族观念、民族认识上的称呼却并不一致。6月16日,尹昌衡在成都各界欢送西征军先锋队出发大会上讲话称:“蛮人为我五大民族之一,现虽反抗,务使翻然改图。我军到时,对于蛮人,即一草一木,不得妄取,亦不得轻杀一人,临之以威,亦当感之以德。前此赵尔丰不德,我同胞不惮,以土枪土炮起而反对之。”尹氏此语就表现了互相歧异之处,一方面对西藏人民以蛮人视之,一方面也承认他们为五族之一、是为同胞。在同一地点与时间的会议上,四川军事参议院院长罗梓青先言:“中华民国成立,原合五大民族而成,所谓五大民族,即汉、满、蒙、回、藏是也,藏即为五大民族之一。今一旦反抗民国,则民族已缺其一也。我军此行宜示之以威,绥之以德,譬如兄弟五人,小兄弟不懂事,为兄长者约束之,教训之,否则鞭挞之,总期改过自新,联为一气而后已。”如果按此言之,罗氏之语虽有兄弟之分,但大致也表现了“五族平等”的观念,但他接着的话又明显的呈现出传统夷夏色彩,称:“军士此行,有如诸葛征蛮,五月渡泸,深入不将。然诸葛七擒七纵,总以攻心为上策。我军士既内顾无忧,尽可努力,并进使蛮夷率服,帖然归心,武乡侯不得专美于前矣。”[注] 《在武侯祠成都各界欢送西征军先锋队出发会上的讲话》(1912年6月16日),载曾业英,周 斌《尹昌衡集》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9~160页。
此次大会在成都武侯祠召开,“蛮夷率服”之语的使用,将此次西征视同诸葛亮南征,一方面隐喻出师顺利,一方面也隐喻着对西藏以蛮夷视之的思维。6月中旬,西征军发出的《告西藏番人文》,称“边藏藩服大汉,历有年所,……尔边藏诸族,含泪切齿,饮血枕戈,乘满祚之将终,奋螳臂而图报,亦有由也。”“本都督大兵在握,犹不忍不教而诛尔蛮族”。[注] 《告边藏番人文》(1912年6月上旬),载曾业英,周 斌《尹昌衡集》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1页。 在《安民告示》中,称:“照得你们西藏地方,久为四川保护,……今天你们辄敢抗拒官兵,蹂躏我汉民,实属目无法纪。”[注] 《安民告示》(1912年6月中旬),载曾业英,周 斌《尹昌衡集》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2页。 这种基于传统夷夏观念,来审视中华民国建立后西藏与中央地方关系的意识,显然与当时“五族共和”“民族平等”观念相悖离,于内于外都容易对西藏问题的解决产生消极影响。但这些词汇在政治人物中的使用,却从另一维度呈现了社会大众对边疆民族问题的普遍性认知。
综上所述,在援藏过程中,地方实力派、北洋政府中央都表现了国家主权意识,在这一视野下,都表现了对边疆民族问题的更加重视与关注。就政治人物的视野或思维而言,一方面,他们既受到社会舆论或社会普遍性认识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形态的制约。但他们的政治言行,却对社会各界具有象征或代表性意义。思想家或者学者的探索相对较为活跃,而政治人物的言论与实践一般较为审慎,但他们的实践对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问题的解决却至关重要。川军援藏是民初边疆民族问题的一个缩影,说明了边疆民族问题在近代主权国家建设过程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实力派与北洋政府中央不同的政治诉求,则反映了北洋时代政局的动荡与复杂。
四、结 论
中华民国边疆民族研究的兴起是在近代中西冲突与调适中发展的,其演进之进程十分复杂。这一进程的高峰场景出现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学术界多视这一时期为边疆民族研究的鼎盛或黄金时代。但任何事物的发展与成熟,均非简单的突起或显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疆民族研究的热潮,其间之发展自有其转承起伏之处,[注] 参见段金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及其发展趋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1期;《学术与时势:1930年代中国西部边疆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4期;《民国边疆研究的嬗变、学科构建与启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 而其源却不能不追溯晚清与北洋时代对边疆民族问题的认知与实践。清朝的“天下”主义与“夷夏”观念与前代相比,虽然在形式与表述诸方面发生了变化,但从根本而论,文化至上主义的本质并未发生变化,“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认知仍是主要内容。但晚清之后,这种认知开始发生了变化,发展至清末,经过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的实践与尝试,对欧美知识的日益接触与理解,尤其是甲午海战失败,导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国人的主权观念及对边疆民族的认识都逐渐有了新的发展。其间从东南到西北、西南,从陆疆到海疆,边疆民族危机日益升级,边疆民族问题在朝野中都受到了较之以往更为广泛的关注。梁启超论:“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注]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年),载梁启超著,吴 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第1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15页。 “精神”若无,“形质”难以有序成长;而“形质”若虚,则“精神”将终无依托或载体。晚清王朝尤其是清末时期应对边疆民族问题的实践,有利于深化国人对边疆民族问题认识与理解。
清末姚文栋关于滇缅界务问题的相关实地考察与认知,其与薛福成、王文韶等清朝要员的往来函文,透露出经过长期与欧美异型文化的接触,加以晚清以来对边疆民族地区事务的认识与实践,近代国家主权观念已逐渐清晰,对边疆族群与近代国家建设互动关系的认识日益深入。但此时,传统帝制时代的“天下观念”并未完全破除,总体上对近代主权国家疆域理念、边疆族群认知有所了解的群体仍居于少数。而诚如有学者所论,“在清季只是创意的起绪,也只代表文化学术一个新时代的曙光。一切重大的变动与发展,均集中在辛亥革命以后”;而清季的时代意义,“正足以符合醒觉二字,其重要性也正在这种先知先觉开创性的导向”。[注] 王尔敏:《清季知识分子的自觉》,载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29页。 时人对滇务界务问题的认知及其意义,与这一判断是一致的。中华民国创立,国人之主权观念更加明确,对边疆民族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更为深刻。民初西藏动荡,川军援藏过程中地方实力派、北洋政府中央等各种政治人物对西藏问题相关认知的表述,呈现出其时社会对边疆民族问题的认识与理解与清末相较,已经有了显著变化。但是,“五族共和”“民族平等”及“蛮夷”等词汇的普遍性同时交互使用及彼此歧异的表述,说明其时仍未完全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主义的族群或边疆民族认识,表现了传统影响至深且巨,近代与传统认知的融合尚未完成且任重道远。当然,这也是一个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民族在与异型文化接触后的自然表现,并且是一种持续性的过程。时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称边疆民族为“蛮夷”的现象仍然普遍,需要政府明令禁止,充分说明了此点。援藏过程中各派别、各政治人物对西藏问题所持态度的差别及变化,不仅是各自利益或政治目标诉求的不同,也是北洋时代政治统一性缺失场景的突出表现,表现了边疆民族问题不仅是边疆民族地区的事务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政治隐喻。总之,晚清、北洋时期关于边疆民族问题的认知与实践,是近代国家建设不断完善的重要过程,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边疆民族问题讨论及研究热潮的重要基石。
天馈线匹配网络工作在恶劣环境中,季节交替温差比较大,在高温高压下工作,功率大容易遭受雷击,因此,应尽量使用电气特性好、耐压高的器件,元件留有足够的冗余量。在电压比较高的节点上,采用多只电容串联、并联相结合的方式,如果空间允许,电感的直径越大越好。这样做能保证整个网络的稳定性。
孟子一到魏国,便受到梁惠王的接见。《孟子》开篇第一章即记录了二人相见的场景:“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由于涉及义利之辩,一开始便话不投机。除上面一章外,《梁惠王》还有四章记录了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都是劝导其推行仁政。几年后,梁惠王去世,梁襄王即位,孟子“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离开魏国前往齐国。
Evolution of the Political Elite ’s Understanding of Frontier Polic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 analysis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s at the southwest frontier
DUAN Jinsheng
Abstract :With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tianxia” or world in ancient imperial China undergoing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inese people gradually developed their concept of sovereignty and deepen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ethnic issues at the borders. YaoWendong’s understanding of Yunnan-Myanmar boundary affairs based on his fieldwork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hows that as a result of the long-term contact with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ractice of frontier ethnic affairs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modern concept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was gradually clarified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ontier ethnic groups and modern national construction was gradually strengthened. But,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tianxia"in the imperial era did not completely dissolved and the concept of modern sovereign state territory was still being formed.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en Sichuan army was “assisting Tibet”, politicians from the local power groups and Beiyang Government all voiced their views on Tibet.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ibet issues shows that, compared with peopl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people from all sectors of the society had greatly chang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ethnic issues in the border areas. However, the popular use of such expressions as “five races under one union” ,“national equality”and “barbarian”indicates that the old thinking about frontier ethnic people based o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d not completely changed and that the fusion of modern and traditional cognition was yet to be completed.The fact that politicians from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had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Tibet issues not only reflects their different interests or political goals but also points up the lack of political unity in the period of the Beiyang Government. It suggests that frontier ethnic issues are not only routine problems with the frontier ethnic areas but also indispensable political metaphors for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to some extent. In a word, the cognition and practice of frontier ethnic issu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iyang period was a cornerstone of the upsurge in discussion on frontier ethnic issue in the 1930s and 1940s .
Keywords :sovereignty, boundary affairs between Yunnan and Burma, assisting Tibet,frontier nationalities
中图分类号 :K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78X(2019)01-0066-12
作者简介 :段金生,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 昆明,650500)。
(责任编辑 甘霆浩)
标签:主权论文; 滇缅界务论文; 援藏论文; 边疆民族论文;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