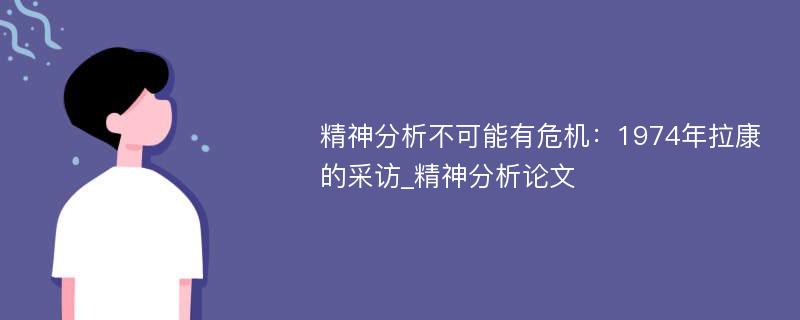
不可能有精神分析学的危机——1974年拉康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能有论文,访谈录论文,危机论文,精神分析论文,年拉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葛朗乍多(Emilio Granzotto,以下简称为“葛”):人们越来越多地谈到精神分析学的危机。有人说,S.弗洛伊德已经过时了。现代社会发现其作品既不足以理解人类,也不足以彻底地解释人类与世界的关系。
J.拉康(以下简称为“拉”):这全部是捏造。首先,危机不存在,不可能存在。精神分析学还完全没有到达其自身的界限。在实践与认识中,仍然有这么多的东西有待发现。在精神分析学中,没有即时的解决方法,而只有对于诸原因漫长且耐心的探索。其次,关于弗洛伊德。当我们没有完全理解他时,我们如何能判断他过时了呢?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他使我们认识了一些崭新的事物,而这些东西在他之前人们甚至想也不曾想到过。从无意识问题到性欲的重要性,从象征世界的人口到对语言法则的服从。
其学说把真理置于疑问之中。就个人而言,这是一个涉及到所有人和每个人的问题。这不是危机,而是另一种东西。我重复一下:我们离弗洛伊德还差得远呢。他的名声同样被用来掩盖了大量的事情。已经出现了一些偏离。后辈们并不总是忠实地追随原型,这就产生了混乱。1939年弗洛伊德逝世后,其部分弟子同样打算以别样的方式来从事那种把弗氏教导简化到某种平庸格式的精神分析学:仪式般的分析技术,限制在行为治疗中的实践和作为方法的个体与其社会环境的再适应。这是对弗洛伊德的否定。这是一种舒适的、沙龙式的精神分析学。
他本人已经预见到这一点。他曾说,有三种守卫不住的阵地,三种不可能的工作:控制、教育和训练精神分析。在我们的时代,由谁来负责控制,并没有什么大的关系。所有的人都自称是教育者。说到精神分析师,谢天谢地,他们兴旺发达了,就像术士和没有正式资格的医生一样。向人们提议帮助他们,就意味着一种确保的成功和拥有急于出门的顾客。精神分析学是另一回事。
葛:正确地讲是什么呢?
拉:我把它定义为症状——我们身临其境的文明之病的揭示。当然,这不是一种哲学。我厌恶哲学。在如此长的时间中,它已不再说一些令人注目的事情了。精神分析学也不是一种教条,我也不喜欢称之为一门科学。让我们说这是一种实践吧!它关心不会现身的东西。这门学科很难,因为它声称要在日常生活中引入不可能之物、想象之物。直到现在,它只获得了一些效果,但仍没有拥有规范。它听从所有种类的模棱两可。
不应该忘记,它涉及了某些崭新的东西,或根据医学,或根据心理学及其附属学科。它同样也太年轻。弗洛伊德离开我们才35年。他的第一本书《释梦》,1900年出版时很不成功。我相信,在几年中它只卖了300册。他弟子不多,人们把他们当作了疯子,甚至不同意他们贯彻与解释他们所学习到的东西的方式。
葛:在今天的人身上,什么是不会现身的东西?
拉:这是一种强烈的厌倦。生活就像前进中赛跑的结果。通过精神分析,人们料想可以揭露到这种程度,即通过忍受这种厌倦所能到达的程度。
葛:是什么东西促使人们去做分析的呢?
拉:恐惧。当某些东西——甚至是他所期望的——某些他没法理解的东西来临时,人就感到恐惧。他忍受着不理解的痛苦,渐渐地掉入了恐慌的状态。这就是神经症。在癔症神经症中,身体是由于恐惧得病而患病的,而实际上并没有得病。在强迫症神经症中,恐惧使头脑中充满了一些古怪的事物,一些人们无法控制的想法,一些在其形式和对象中具有多种多样涵义且令人害怕的恐怖之像。
葛:例如?
拉:在神经症患者身上,你能感觉到他被一种可怕的需求所控制,即数十次地去查看水龙头是否真的关上了,或者一件东西是否就在那里,可是明知水龙头就如其应所是,那件东西就处于其应所处。没有治愈它的药丸。你得找出为何它来到你身上,即它意味着什么。
葛:是治疗吗?
拉:神经症患者是一种靠言语来治疗的病人。首先是患者的言语。他必须说话,讲述,谈谈对自己的看法。就其由向他人言说之言语所构成而言,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学定义为对于有着自身历史的主体其中一部分的设定。精神分析学是言语的王国,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弗洛伊德已阐明:无意识并不是深到连意识的深度都到达不了。他曾说,在这无意识中,说话的是既在主体之中又超越了主体的一种主体。言语是精神分析学的巨大动力。
葛:谁的言语?患者的还是精神分析师的?
拉:在精神分析学中,术语如患者、医生和药物等,并不比我们通常在消极意义上所用的惯用语更准确。人们说:让人替自己分析。这是一个错误。真正做分析的是那个说话的人,即在做分析的主体。即使主体是由指示他如何前进的分析师所建议的方法来进行分析的,是通过分析师的干预来帮助他做分析的,分析者同样给出了一种解释。
乍一看,解释看起来是赋予分析者所说一种意义。事实上,解释变得更加难以捉摸了,它倾向于使主体所受痛苦的那些事物的意义变得难以辨认。(分析的)目标就是要穿过其叙说向他指出,症状(让我们说疾病)与无没有丝毫关系,它被剥夺了某种其应有的意义。即使表面上看起来它是真实的,然而它并不存在。
言语行为据以进行下去的方法需要大量的实践和一种无限的耐心。耐心和方法是精神分析学的工具。技术就在于能够衡量我们所给予分析者主体的帮助。因此,精神分析学是困难的。
葛:当人们说拉康时,人们不可避免地把这一名字与一句格言即“回到弗洛伊德去”联系起来。这意味着什么?
拉:准确地讲,这就是要说的东西。说到精神分析,就是指弗洛伊德。如果有人想做分析,他应该回到弗洛伊德,回到在字面意义上所读出的和所解释的其术语和其定义上去。正是为了这一目标,我在巴黎建立了一个弗洛伊德学派。我亮出我的观点已经20多年了:回到弗洛伊德仅仅是指,根据从其工作开始就已界定和列举的原则,重新阅读弗氏的教导,脱离那些偏离的场所和由存在主义现象学所带来的那些模棱两可的场所——就如精神分析协会制度性的形式主义所带来的东西。重新阅读弗洛伊德仅仅意味着重新阅读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中,如果谁不这样做,那就是一种滥用公式。
葛:然而弗洛伊德的东西是难懂的。有人说,拉康干脆使它成为不可理解之物。人们责怪您的说话方式,尤其是写作方式,说只有极少的信徒才能指望理解。
拉:我知道。人们认为我是晦涩的。这种晦涩在烟幕中遮蔽了思想。我问自己为什么。关于精神分析学,我在重复弗洛伊德,即这是“主体间的游戏,穿越它,真理进入实在。”这不清楚吗?
我的书被定义为不可理解。然而,这些书是给谁看的呢?我并非为所有人写这些东西。相反,我绝不会为了讨好某位读者而说这应该如此。我有一些事情要说,我把它们说出来了。对我来说,有读者就已经足够了。如果他们不理解,就要耐心一点。至于读者的数量,我的运气胜过弗洛伊德。我的书甚至有大量的人在读,这点我很吃惊。
我同样确信,在最多十年后,那些读我书的人就会发现我的观点是显而易见的,就如一只漂亮的啤酒杯。那时人们可能会说:“这个拉康,这么平庸”。
葛:拉康主义的特征是什么呢?
拉:当拉康主义尚未存在时,说这个问题为时稍早。我们才刚刚闻到它的气息,就像一种预感。无论怎样,我做了至少40年的精神分析实践和精神分析学研究工作。我信任结构主义和语言科学。在我的书中,我这样写到:“弗洛伊德的发现带给我们的是我们已进入其中的秩序的异乎寻常性。在其中,通过摆脱被正确地称之为小少爷(infans)的状态,无须言语,我们第二次诞生了。”
弗洛伊德以此为基础建立其发现的象征秩序,在既具体又一般的话语时刻,由语言所构成。是言语的世界创造了处于所有生成状态中的最初混乱的事物的世界。只有言语才把实现了的意义赋予事物的本质。没有言语,无物存在。没有言语的居间,快乐会成为什么呢?我的观点是,通过在其早期作品——《释梦》、《超越快乐原则》和《图腾与禁忌》——中对无意识法则的陈述,弗洛伊德作为一个先驱已经提出了几年之后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开启现代语言学之路时所用的理论。
葛:而纯粹的思维呢?
拉:像所有其它事物一样,思维服从语言的法则。只有言语才能产生语言,并赋予它连贯性。在思维的探索中,要是没有语言,人类不会前进一步。这是精神分析学的情况。不管我们归之于治愈代理、形成代理或测试代理的功能是什么,我们所能使用的只有一项:患者的言语。而所有的言语都需要回应。
葛:这么说,精神分析被当作对话。但有些人把精神分析学解释为忏悔的一种延续。
拉:然而是哪种忏悔呢?人们向分析师坦白一种十足的虚无。人们仅仅听凭自己向他述说所有脑海里发生的事情。正确地说,是那些言语。精神分析学发现的,就是作为说话动物的人类。整理他所听到的言语,赋予它们意义和涵义,这些都是分析师的责任。要想做一个好的分析,就应该在分析者与分析师之间达成协定或协议。
穿越一人的话语,另一人力图对他所涉及的东西形成一种观念,力图在显而易见的症状彼岸寻找真理的难解之结。分析师的另一功能是阐释言语的意义,以便使患者理解我们能够从精神分析中所期待的东西。
葛:这是一种极度自信的陈述。
拉:不如说是一种交换。在其中,重要的是一人在说,另一人在听。沉默同样重要。分析师不提问题,不出主意。他只会给出那些回应,即对于由其妒忌所激发的问题给出回应。然而到了最后,分析者总是走向分析师所引导的地方。
葛:您刚刚说到治疗。有治愈的可能性吗?人们能摆脱神经症吗?
拉:当它清除道路,摆脱症状时,精神分析就成功了。
葛:您能否用一种较少拉康式的方式来表述同样的概念?
拉:我称症状是所有来自实在的东西。实在,就是所有不会现身的东西,所有不发生作用的东西,所有与人类生活及其人格相对立的东西。实在总是回复到同一地方。你总是能在那里找到它,带着同样的面貌。科学家枉然声称实在中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为了要肯定这一种类的这些东西,必须要脸皮厚,或者说,就如我揣想它一样,必须完全不知道人们的所做与所说。
实在和不可能之物刚好相反。它们不可能走在一块。精神分析学把主体推向不可能之物。它建议主体把世界看作确实如其所是,换言之,是想象的,没有涵义。然而实在,就如一只贪婪的鸟,只沉浸于合理的事物中,沉浸于有意义的活动中。
我们听到有人不断地重复,应该赋予这意义,赋予那意义,赋予自身思维意义,赋予自身呼吸意义,赋予欲望意义,赋予性意义,赋予生活意义。然而,对于生活我们一无所知。学者们已经无法胜任向我们阐释这一问题了。
我的担忧是,由于他们的错误,实在这一并不存在的怪物终于就要做成了,就要赢了。科学取代了宗教。不同的是.它更专横,更迟钝,更蒙昧。有原子神、太空神等等。如果科学或宗教流行,那么,精神分析学就完了。
葛:在现今,科学与精神分析学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拉:对我来说,唯一真实的、严格的、可被遵循的科学,是科幻小说。另一种科学,正式的,拥有实验室工作台,摸索着前进,偏离了方向。它甚至开始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
对于科学家来说,看来恐慌的时刻来临了。在他们无菌的实验室中,那些忙活着陌生事物的大小孩们,裹在他们上了浆的工作服中,通过制造越来越复杂的仪器和杜撰越来越晦涩的公式,开始寻思明天可能发生的事情,寻思那些总是以新貌出现的研究最后带来的东西。要我说,得了!是否太晚了呢?现在生物学家在思忖它,要不然就是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对我来说,他们都是疯子。尽管他们正在改变宇宙的面目,然而,到如今他们还只是在思忖:这是否有可能并不危险。如果一切都爆炸了呢?如果在洁白的实验室中精心培育的细菌转化为不死的敌人了呢?如果,伴随着所有充斥在世界各地的粪土,世界被一群由实验室科学家所培育出来的这样的细菌所席卷了呢?
对于弗洛伊德所说的三种不可能的阵地,控制、教育和精神分析,我加上第四种,科学。撇开这一点,科学家们不知道他们的阵地是站不住脚的。
葛:在此,关于人们称之为进步的东西,有一种相当悲观的看法。
拉:不,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不是悲观主义者,永远不会。原因很简单,人类什么用处也没有,同样也不可能自我毁灭。就个人而言,我恐怕不可思议地发现了一种完全针对人类的枷锁。这怕是要证明,没有神的、自然的或其他的干预,人类用其双手和大脑终于做成了某种东西。
所有这些为了消遣而给予过度营养的大量细菌,就像圣经中的蝗虫一样散布在人间,恐怕意味着人类的胜利。然而这并没有来临。科学幸运地穿越了其责任的危机,就像人们所说,一切将回到事物的秩序中。我已预言:像往常一样,实在将占据优势。而我们,像往常一样,将变得无可救药。
葛:拉康的另一种悖论。除了语言的难懂和一些概念的晦涩,人们非难您的还有对字眼的玩弄,开语言玩笑,在法语中玩同音异义的游戏,确切地说,悖论。那些听您讲课或读您书的人有权感到不知所措。
拉:事实上我并没在开玩笑。我在说一些严肃的事情。就像那些我曾谈到过他们的蒸馏器和电路的科学家们一样,我只是在使用言语。我力图时刻参照精神分析的经验。
葛:您说:实在并不存在。然而一般的人知道实在就是世界,所有围绕他周围的东西,他肉眼看到的东西,他触摸到的东西。
拉:首先,让我们同样清除那个并不存在的一般人。这只是一种统计上的虚构。存在的是一些个体,这就是全部。当我听到谈论普通人、民意调查、大众现象和这一类事物时,我想到了40年倾听生涯中所有在长沙发上坐卧过的患者。依据某种标准,没有一位患者与另一位相似,没有人得同样的恐怖症,同样的焦虑,没有人运用同样的讲述方式,没有人会有让人无法理解的同样的恐惧。一般人,是谁啊?我,您,我的门房,还是共和国的总统?
葛:我们谈论的是实在,我们所看到的世界的全部。
拉:没错。实在(即不会现身的东西)、象征和想象之间的差别,就是真理。这便是,实在就是世界。为了确认世界不存在,或根本没有世界,想想所有这些平庸的想法即大量的傻瓜相信世界存在,这已经足够了。在指责我自相矛盾之前,我请我的《全景》杂志的朋友们好好思索一下他们刚刚读到的东西。
葛:人们说您总是更为悲观。
拉:这不正确。我既不属于制造人心慌慌者行列,也不属于焦虑者行列。没有超越焦虑期的分析师要倒霉了。在我们周围,有一些令人恼火的和折磨人的东西,如有规律地吞噬掉我们中大部分人的电视,这是真的。然而这都是因为,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听任自己被吞噬掉,他们针对自己所看到的东西甚至能自我编造出兴趣来。
此外,还有一些其它奇形怪状的或折磨人的技巧:将要登陆月球的火箭,海洋深处的探索等等。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折磨人的。然而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我确信,当我们厌倦了那些火箭、电视以及所有他们白白所做的研究时,我们就会发现吸引我们的另一种事物。这是一种宗教的复活吗?还是比宗教更折磨人的什么怪物?这是一种连续不断的节日,就像已经指出的那样,它长期受到嘲笑。
对于所有这些,我的回答是,人类总是能适应困难。我们对之可以设想的唯一的实在,我们靠近它的那个实在,确切地说,就在此。对此,真的应该迁就既成事实:如我们所说,赋予事物意义。否则,人类就不会得焦虑症,弗洛伊德也不会出名,而我也不会成为学派的倡导者。
葛:焦虑总是具行这种特征,还是存在着一些与某些社会条件、某种历史时期及某些地区相联系的焦虑?
拉:害怕其发现物的科学家们的焦虑看起来大概是最近才得的。然而,我们得了其它时期曾经来临过的症状了吗?其他探索者的一些悲剧?装配线上受到奴役的工人,就像古代战船上的一支桨,他们的焦虑就是当今的焦虑。或者,更简单地说,它与当今的定义和言语联系在一起。
葛:然而对于精神分析学来说,焦虑是什么呢?
拉:某种在我们躯体外表的东西,一种恐惧,一种可能由躯体(包括精神)引起的恐惧,然而并不要紧。总之,是关于恐惧的恐惧。大量的这种恐惧,大量的这种焦虑,在我们察觉它们的层面上,都与性有关联。弗洛伊德曾说过,就人类这个说话动物而言,性欲是不可救药的,没有希望的。分析师的一项任务就是要在患者的言语中找出焦虑与性之间的关系,这一重大的未知物。
葛:现在,人们把性布置在所有的拐角,在电影院和剧场,在电视和报纸上,在歌曲中和海滩上。我们听到有人说,与性领域相关的问题给人带来的焦虑会少一些。有人说,禁忌消退了,性不再使人害怕了。
拉:蔓延开来的性癖好只是一种公众现象。精神分析学是一种严肃的事物。我重复一下,它涉及到两个个体即主体和分析师之间一种纯属个人的关系。不存在集体性的精神分析学,就像不存在大众的焦虑症和神经症一样。
如把性置于阳光之下,在街角处曝光,被当作电视所放映的循环运输装置中的任何一种洗涤剂一样来处理,这样的性不容指望有某种益处。我并没有说这是不好的。要处理焦虑和特殊问题,这肯定是不够的。以所谓的悲观社会的名义来说,它是时尚的一部分,是这种充满了我们脑子的虚假的自由化的一部分,就像从天上下凡的一位迷人的准新娘。然而,在精神分析的层面上,这是没用的。
(Emilio Granzotto,"Il n'y a pas la crise de psychanalyse-Un entretien
avec Lacan en 19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