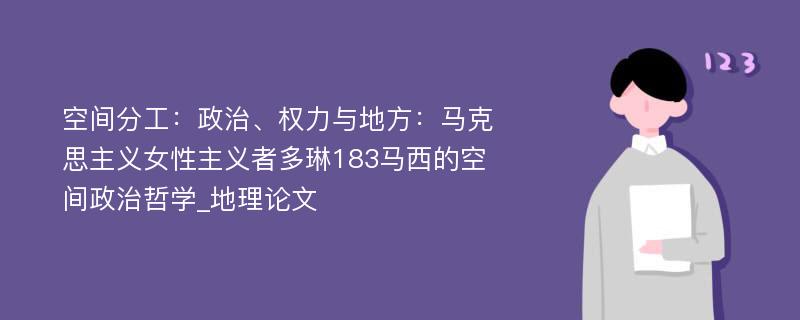
劳动的空间分工:政治、权力与地方——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多琳#183;马西的空间政治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空间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主义者论文,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空间政治哲学理论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政治哲学思想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学界对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尔、苏贾等人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英国著名的激进地理学家、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生于1944年)的别具一格的空间理论却一直没有受到重视,其著作已有两种译成中文①,但相关研究还很薄弱。本文拟从马西提出的“生产地理学”、“权力几何学”、“全球地方感”理论入手,对其空间政治哲学理论作一初步梳理与分析,以期推进相关研究。 一、劳动的空间分工与不平等的再生产 多琳·马西的职业生涯开始于英国环境研究中心(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简称CES),这是一个由英国政府和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建立的研究机构,该机构素以激进主义而闻名,但是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后,因削减经费,难以为继,CES随即不得不被关闭。而正是在CES工作时间,马西开始构思日后久负盛名的“工业区位”批判理论,为后来她的开创性著作《劳动的空间分工: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奠定了基础。离开CES后,马西来到了英国开放大学,逐渐成了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研究领域涉及空间理论与经济地理,阶级、性别、职业与不平等,“区域不平衡发展”,城市化、全球化及女性主义问题等,其思想较多地受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列斐伏尔的“都市马克思主义”及女性主义的影响,同时,她的研究反过来也进一步重新塑造了这四种“马克思主义”,总体上可划归为后马克思主义思潮。 与当代西方许多空间理论学者视角不一样,马西以空间为分析工具对资本主义生产问题进行了地理学的研究,建构起了“生产地理学”的基础理论与分析模型,为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运行与新变化提供了新的视野。早在1979年,马西就在《区域问题的意义何在》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劳动的空间分工”(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r)这个概念,试图从空间的角度来解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其1984年推出的代表作《劳动的空间分工: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中,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刻系统的阐释。该书具有浓厚的政治经济学色彩,但不同于哈维以资本积累的空间化逻辑为分析范式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马西是以劳动的空间分工及其组织结构作为分析焦点与中心线索的,从而彰显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另一重要方向、路径与特色。 马西在该书的一开始,就重新探讨了空间的内涵及空间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她认为,空间不是预先存在的盛装事物的容器,它具有关系属性,“实际上是由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建构而成的,是这些关系的产物。我们主动地在生命的组织和生活中创造空间(某个时间空间,多个时间空间)。而且,我们创造空间的方式,将反过来影响社会的结构化和我们生活的结构化”。②由此,马西特别强调了空间之于社会理论的重要性:“‘地理’应当从一开始就是具体说明的一部分。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是在空间中发生的,而这一点制约着其性质”③。因而,《劳动的空间分工》虽然关注的焦点是在传统上被称为“经济的”事物,但主要探索的则是产业区位(industrial location)的机制、城市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形态的变化,其总论点则是:“在一个国家内部种种支配性空间分工之间发生的重大变动背后是生产关系的空间组织的变化,是在此所说的生产空间结构(spatial structures of production)的发展和重组。空间结构的这种变动,是对经济的和政治的、本国的和国际的阶级关系变化的反应。它们的发展是一种社会过程和冲突过程。”④ 确实,劳动分工是亚当·斯密以来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重要主题,⑤但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关注的是劳动的技术与社会分工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忽视乃至忽略了劳动分工的地理空间内涵。与传统的经济学研究劳动分工不同,马西关注的是“劳动的空间分工”,它主要是指在空间维度上展开的多种类型的“产业”劳动分工。这里的“产业”不单纯是制造业,还包括电子信息行业、服装与鞋类行业、服务业、采矿业等;也不单纯是劳动力及其职业的地理分布,更包括技术、职位、部门、所有权、权属关系、行业、内部结构等要素的空间分布;它既包括一个国家内的“产业”的地理分布,更指的是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新的经济地理现象,例如,在生产全球化的今天,一个产品的制造并不一定局限于某个特定地区,各个生产环节很有可能会被分配到世界上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其分配方式是按照各地区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成本来设定的。马西指出,对“劳动的空间分工”的研究就是要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上述多种类型的空间分工现象,不仅要经验地、实证地分析国家内部及全球化中的劳动空间分工诸种现象,更要揭示其形成的原因与造成的结果。马西认为,劳动力在空间上进行分配的同时,等级关系的分配也在进行着,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她在论述工业变迁与空间变迁的问题时也指出,“宽泛地说,在职能上越靠近总部,社会地位就越高,而且既然等级体系拥有一种空间形式,社会分化和空间分化显然是相关的。”⑥ 将资本主义生产及其社会阶级分化的讨论与有关空间组织的讨论联系起来,努力阐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空间结构及其政治效应,这是马西空间理论的最大特色。马西指出,社会生产关系必定是在空间中发展的,并且以多种形式发展,而这些形式我们就称为生产的空间结构。马西原创性的贡献就集中体现为: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中三种不同空间结构的模式区分——部分流程空间结构、克隆型空间结构和区位集中的空间结构,这三种不同空间结构的分析模型与方法已被“产业地理学”后继者们奉为“经典”。据马西分析,在部分流程空间结构中,以电子业为例,技术上比较复杂的部件的研发,是与其生产分开的,而且这些与产品的最后组装也是分开的。在这里,不仅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占有者、管理者在不同的区位展开,而且生产内部技术上的分工或者说详细的分工也是如此。在克隆型空间结构中,生产过程本身在地理上仍是未分化的。情况可能是,在生产内部存在着某种分工,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各种部分被保持在同一场所;情况也可能是,在单一的资本所有权之下,在生产过程内部不存在很明显的技术分工。只有投资和对生产过程的监督和控制职能——生产资料所有和占有关系——在空间中展开。在区位集中的空间结构中,一种商品的整个生产过程集中在一个地理区域内。不管管理科层体系运行着什么样的财务和管理控制方面的职能,也不管生产过程中存在什么样的分工,都是位于一个地区之内。 通过上述分析,马西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这三种空间结构中的每一种都可以成为某个不同系列的地区间关系和某种地区间依赖形式的基础,并且每一种不同的空间结构,都意味着一种不同的地理分异形式和地理不平等形式。以英国产业的空间结构为例,其生产过程中占支配地位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逐渐向英国东南部集中,而在北部和西部的外围地区,则缺乏地位较高的白领管理职位,这种空间上的不平等不仅是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也是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在英国,有的行业寻求利用港口以便于进口原材料和出口产品,有的需要利用丰富的劳动力,有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寻求利用特定资源如煤炭资源。“由于这些方面具有在全国分布并不均衡的特征,所以演化出来的地理类型就是:每个这样的主要行业都将生产集中在一个或者少数几个地区”。⑦空间的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如今在英国,那些白领管理职位长期以来只占就业结构相对很小一部分的区域,承受高度的外部控制,实际上这些地区失去的并非一种职位和相关的人员,而是总体社会生产关系内部的一种功能。因此,“空间上的不平等,与其说是不同社会类型的职位(以及因此造成的某种地理上的‘机会均等’)的不均衡分布,不如说是生产控制权中权力更大的构思和战略层次被撤除出一些地区,并集中到另外一些地区。”⑧ 诚然,如人们熟知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于英国来说,以部门和行业之间的鲜明不同为基础的旧空间分工已经加速衰落,空间不平等的形式已经大为改观。马西强调,形式上大为改观并不意味着不平等的实际消除,而实际上则再生产出不平等的新形式。例如,实行生产科层制的企业在运行良好和不断增长的同时,既依赖于不平等,也再生产不平等;又如企业跨越空间的组织方式是通过一种与部门专业化、当地控制权及简单的分厂结构都不相同的方式来利用空间,这种利用实际上是以空间不平等为基础的,它既需要这种不平等,同时也必然再生产新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集中体现在产业上的不平等,进而引起劳动者收入和地位的不平等,区域间权力关系、生产能力的不平等,阶级、性别、种族在分工上的不平等。马西指出,在英国,生产管理越来越集权于英国的东部和南部,相应的英国的高层管理者、社会地位较高的人都比较倾向于留在伦敦这样的大都市,研究和开发人员则通常出现并居住于从布里斯托尔经过伦敦周围六郡到东英吉利的新月形地带,而劳动阶层则扩散至外围地区,甚至是其他国家。这样一种地理分布反映的正是空间的不平等,并且带来权力关系、职能、收入、地位的不平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生产绝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分工不平等导致的,它也是政治的问题,政治上的不平等也会导致空间形式的变化,进而带来不平等的再生产。地区政策制定的不平等,国家领导人政治战略的变化,都会造成空间的不平等再生产。例如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的那个时期,英国采用了多种很不相同的政治经济战略试图使某种更平等的地理前景能够出现,但是每一次都强化了导致旧空间分工衰落和新空间分工主导地位形成的不同特殊因素,带来了不同的不平衡发展模式,构成了不平衡发展过程的一部分。“以‘威尔逊主义的激情’为缩影的技术官僚改良型现代化战略,极大地复制了‘旧的地区问题’。外围地区的帝国旧产业基地的产业,特别是采煤区的就业,减少速度最快”。⑨这些战略,一时看上去确实像消除了不平等的形式:为各地区提供了工作职位,各地失业率出现趋同之势。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新的地理不平等形式的一个方面的体现。1979年的大选之后,玛格丽特·撒切尔开始任首相,随着她上台执政,各种过程之间的平衡又再次改变,她更加信奉市场意识形态,主张削减公共开支,不提供新的工作职位,导致旧“开发区”工作职位的损失再次加速,这种现象也发生在产业曾被分散化的地区。 当然,这些不同阶段采取的每一种战略都是在相当不同的经济环境下和相当不同的社会基础上提出的,表面上都是为了“拯救英国经济”,但同时这每一种战略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延续了地理不平衡,一些集团利用其社会权力,通过选址强化其权力,反过来加剧了不平衡发展的不均衡性,带来了不平等的再生产。而要想解决英国的地理不平等问题,“意味着解决国际资本——政治、经济和空间上的——支配地位,还意味着挑战英国社会某些阶层的社会权力,尤其是白领科层体系的上层,管理人员、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的上层,以及那些占据和维持最广泛意义上的英国权势集团拱形结构上部的人们”。⑩可以看出,英国的不平等问题不仅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有关,还与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之间有更密切的关系。因此,不平等的再生产不仅仅是一个有关分工的地理学问题,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问题,它和最广泛意义上的空间政治是不可分割的。 二、基于空间哲学的“权力几何学” 对“劳动的空间分工”的理解,更为基本的问题是“空间是什么”。 我们知道,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界针对空间问题进行了重新反思和探索,这其中有国内学界熟知的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他们对空间的社会性、政治性及其在“资本主义幸存”中所起的作用进行过颇有价值的分析;又如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卡斯特尔用一种共时性(synchrony)的分析方法来探索空间问题,以“再现”(representation)的方式来看待空间;后结构主义者尚塔尔·墨菲、恩斯特·拉克劳则试图让时间-空间的结构具有一定的动态效果,虽然他们的理论让时间性具有了开放性,但空间性可以说仍旧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空间依然是一种“再现”。 针对众说纷纭的空间理论,马西在2005年出版的《保卫空间》(For Space)一书中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空间哲学。她对空间的理解包括三个核心观点:第一,空间是相互关系的产物,“是由大如寰宇、小如尘埃的事物相互作用构成的”。(11)“关系”在这里指的就是事物间的一种互动关系,这样的关系也内在地包含了社会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与仅仅把空间视为原子化的物体类型和分布相比,从关系尤其是浸透了权力的社会关系方面形成空间(以及构成空间的现象)的概念,要更有帮助”(12)。第二,空间是多元“轨迹”(trajectory)共存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同时发生着各自不同且丰富多彩的“故事”(story),这就构成了多样性(multiplicity)的基础,而这样的多样性一定程度上又受到了空间差异性的影响,因此空间也是异质性(heterogeneity)共存的领域。在马西看来,多样性和空间缺一不可,失去了多样性,空间也就不成其为空间,两者同样是相互构造的关系。第三,空间是不断被建构的并且是开放的。换句话说,空间总是处于过程之中,随时都处于发展变动的状态,而空间的发展则是开放的,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马西以上述三个层次的空间观念为其基本立场,对当代西方各大流派的空间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其宏观目标是要“解放空间”、“保卫空间”,亦即“将空间从封闭、静态或科学、写作和再现的意义链中解放出来,这些意义链会让空间窒息而亡,我们可以将空间安置到其他的诸如开放性、异质性和活力的意义链中,在那里,空间可以获得新的、更具创造性的生命”。(13)马西要保卫的正是这种具有多样性、关系性、开放性和动态的建构性的“空间”。 马西认为,将“空间”从已有的静止、封闭、再现的概念“星丛”中连根拔起,将其置于另一组观念中(异质性、关联性、同时性及活力),“空间”概念将会绽放出一种更具挑战性的政治风景,激发当代左翼多样而全新的“政治想象”。马西指出,在最低限度上,她所持的三大核心观点与当代三大左翼“政治想象”将产生积极“共鸣”。 第一个核心观点将空间理解为相互关系的产物,正好与近年来所兴起的一种反本质主义的政治相契合。这种政治不是接受且与已经构造出的实体/认同协作,而是强调事物间相互关联的建构性。因此,它对基于不变的认同观念之上的本真性诉求抱有警惕的态度。取而代之的是,它提出了一种对世界的关联性理解及一种就世界的关联性作出回应的“关系政治”。 第二个核心观点将空间想象为存在多样性的可能性领域,这与近年来左翼政治话语对“差异”和异质性的强调产生了共鸣。这种“差异政治”最显明的形式,是坚持既不能将世界的“故事”讲述成单一的“西方”的“故事”,也不能将其讲述成譬如有关白人的、异性恋男性的古典形象的“故事”,而始终坚持这些“故事”只是许多“故事”中的特殊“故事”,而不是长期以来人们信奉的“普世”价值。 第三个核心观点将空间想象为总是处于过程之中的,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这与当代政治话语内部越来越直言不讳地坚持未来的真正开放性产生了共鸣。马西认为,今天许多人拒绝“历史终结论”的阐释,而赞成历史发展、人类未来发展的开放性,无论他们赞成这种开放性是通过“激进的民主”,还是通过“积极的实验”,抑或是通过“酷儿理论”(queer theory)中的一般方法论。她认为,“的确,特别像拉克劳所强烈主张的那样,只有我们将未来想象为开放的,我们才能认真地接受或致力于任何独特的政治观念。只有未来是开放的,才有制造差异的政治的存在地盘。”(14) 由上可见,马西自觉地将空间与政治内在勾连起来,试图构建起自己的“空间政治学”。这与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的政治哲学形成鲜明对照。拉克劳认为,空间和政治属于“二律背反”的关系,亦即空间和政治是同时存在的,但相互之间却呈现出一种相互排斥、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拉克劳甚至提出,当空间在我们面前逃遁时,政治学才能存在下去。换句话说,当我们在研究政治学的问题时,不需要考虑空间的问题,甚至要有意避开这个问题。马西的观点与之大相径庭,针对这个观点,马西在她的论文《政治与空间/时间》(1992)中继续强调了空间、时间、政治相互间的共生性,指出空间性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空间性之于政治学,正如时间性之于历史学,两者都是不可分割的。 马西“空间政治学”最核心的思想是以分析“空间权力”的形成演化、层级结构与运行规律为主干的“权力几何学”(power-geometry)理论。有学者指出,“权力几何学”“这一概念以马克思、柏格森、海德格尔等现当代重要哲学家的思想为基础”(15),它有力地“解释了不同类型的人群是怎样流动和相互作用,直至形成现今全球资本主义的丑恶不公的”。(16)总体地看,“权力几何学”涉及的问题有全球化、不平衡发展、差异性、性别、阶级、地方等,它主要阐述的是在全球化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背景下“空间权力”(space power)对不同地区人们的不同影响。这从现象上表现为,在全球化的今天,有人如鱼得水,大展宏图,有人则仰人鼻息,亦步亦趋,而这与权力的空间分布、区域差异有着直接的关系。这里涉及的问题是权力关系在空间维度上的不同分布,这样的差异性分布给不同的社会群体带来了不一样的影响。在空间中分布的这种“权力”更像是一种能力,掌握这个能力的“强者”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导和控制他们的生活并保卫他们自己的安全之所”。(17)不过,这里的“权力”层级与地位的高低,不完全由个人能力决定,而是由“先天的”空间差异性决定的。其实马西在《劳动的空间分工》中就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索。以产业劳动的空间分工为例,由于空间关系中存在着自然资源分布不均衡、新旧产业区域分布的不平衡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带来的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导致了不平衡的产业劳动分工和社会再生产,由此衍生出来的问题就有劳动者收入和地位的不平等,区域间权力关系、生产能力的不平等,阶级、性别、种族在分工上的不平等。据此可以推断,空间权力关系的两极分化,实际上是由空间差异性决定的。 “权力几何学”关注权力与空间的关联,而这样的关联性正是在全球流动的时间与空间似乎被压缩而变短、变小的过程中集中体现出来的。我们知道,伴随着资本、交通运输、旅游、贸易、新闻广播、网络传播、金融流动、电影或音乐的发行等在全球流动或展开,客观上呈现出所谓“时空压缩”的现象。而在这种呈现“时空压缩”特征的全球流动的过程中,有的群体居于主动,而另外一些群体则居于被动。马西把居于主动的群体定义为“发动了流动和移动”的群体,换句话说,他们掌控了“时空压缩”,并且利用这个过程增加了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这样的群体是“搭喷气式飞机旅行者,是收发传真和电子邮件、手里握着国际会议电话的人,是发行电影、控制新闻、组织投资和国际货币交易的人”。(18)另一些群体则是在被动接受“时空压缩”,这些人群包括很少外出的老年人、生活拮据的工人,或者那些四处漂泊的难民和非法移民劳工。对于这一问题,马西举过一个例子,她说在全球化的今天,住在里约热内卢贫民窟里的人们在禀赋上并不逊色,他们热爱足球,而且有些世界级的足球明星就出自那里。他们对世界音乐和舞蹈的发展也作出过卓越的贡献,比如桑巴舞和伦巴达舞都非常有名,他们似乎也以此为傲,但是他们却一生都被“囚禁在这里”。他们依然是强弱对比中的弱者,这或许就是空间动态分布的结果,这也就是“第三世界”的命运——“时空压缩”的被动接受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马西的“权力几何学”简单理解为“权力”在空间维度上的不同分布,这样的差异性分布对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群体与个人带来了不一样的影响,并且这个分布模式呈现出一种“拓扑结构”(19)。而这里所谓的“权力”指的主要就是掌控“时空压缩”的权力。马西的“权力几何学”的提出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委内瑞拉前总统雨果·查韦斯主政该国十四年,一直致力于社会公正和消除贫困,他受马西的影响,将其“权力几何学”作为委内瑞拉革命进程的驱动力之一。他宣称,“权力几何学”意味着把权力交给人民并赋予国家更多的自主权。实际上,查韦斯采纳“权力几何学”理念,正是为了让委内瑞拉在全球化进程中能够获得更多的主动权。 三、“全球地方感”理论的建构 马西的“权力几何学”在更宽广的意义上,实际上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权力”视域下的全球化理论,它主要关注的还是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地方的关系。 英国学者蒂姆·克瑞斯威尔在形容地方这个概念时做过一个绝佳的比喻:当你刚搬进学校里的宿舍时,你在墙上贴上海报,在桌上放一些书,然后这个空间就成为了你的“地方”。再比如说北纬40.46度、西经73.58度这个概念只是地理学中的一个定位方式,但如果我们仔细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就会发现这里是纽约曼哈顿曾经的世贸大楼所在地,顿时让我们回想起“9·11恐怖袭击事件”。这样一来,地方就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这是人文地理学为我们提供的一种视角,许多新马克思主义者对地方、空间问题的阐述,大多是从这个视角出发的,但是由于各自的研究对象不同,导致研究结果各不相同。在此我们不妨作一个简单的对比,例如哈维、马西这两位左翼学者都基于各自所生活的地区,对“地方感”(sense of place)这个概念作了不同的阐述,而两者的论述引发出一场关于全球化与地方、地方封闭性与开放性的著名争论。 哈维在他的论文《从空间到地方,然后回头》一文中,以自己的家乡巴尔的摩(Baltimore)为研究对象,阐述了“地方感”理论。在他的家乡有个小地方叫作基尔福特(Guilford),那里的社区安保工作表面上看做得很好,实行的是“门禁社区”制度,就是在居民区的四周修建围墙,有一条或两条道路用作出入口,门口设置保安。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护居民免遭娼妓、毒贩或暴徒的侵害,但这种办法却在客观上造成了族群分割,哈维指出:“在基尔福特的例子里,门禁社区的形成能有效地区隔白人社区(基尔福特之内)与黑人社区(基尔福特之外)”(20)。即便如此,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就在1994年8月的一天,一对八十多岁的白人夫妇在家中惨遭杀害,事后查明凶手并不是那些被隔绝在外面的所谓“黑人暴徒”,而是他们自己的孙子。哈维以这样的例子引出地方感的概念具有浓厚的负面色彩。在哈维眼中,地方更像是一座城堡,通过这个事例向我们表明“地方不只是存在,而且向来总是且不断为社会上强大的制度性势力所建构”。(21)与哈维观点相类似的段义孚曾经这样描述“地方”,“如果我们认为空间是允许移动的所在,那么地方就是暂停;每个移动中的暂停,都使区位得以转变为地方”。(22)在这样一种逻辑推导下,哈维建构起了保守的地方感理论:一方面,“地方”可以抵御资本全球流动所造成的冲击,具有“战斗性的特殊意义”;另一方面,这样的地方感有强烈的排他性,即地方内的人为了抵抗外部“威胁”的排他性,这其中也包括因全球化流动而带来的焦虑感。 与哈维的观点迥然相异的是,在《保卫空间》中,马西举了一个例子来极力说明“地方”具有的开放性。1999年,在德国汉堡周边的易北河河床上,人们发现了一块巨大的石头,媒体对这件事进行了广泛的报道,一时间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这块巨石引起了汉堡市民极大的兴趣,甚至于触发了德国人的哲思。原来,这块石头是在几千年前,被冰川从南边推过来的,冰川消退后就留在了这里。从地质学的角度看,这块巨石不属于这里,是一个外来“移民”,所以它不是汉堡的石头。可是换个角度看,假如在汉堡地区待了几千年都不能算是本地“居民”的话,那么今天的汉堡人恐怕都不具备成为本地人的资格。到底要在一个地方待上多久才能被当作“本土的”?德国人不断地思索着这个问题,最终这块石头所带来的“哲思”使得德国的移民政策有所放宽,并且2000年德国的公民权法中相关规定也略有松动,那些在德国长期生活的移民被赋予了公民权。汉堡作为德国最重要的港口,每年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劳工、资本、船只,这样的地理位置也使得它更容易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都市。汉堡的这个例子充分体现出了地方的开放性,并且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乐意接受这样的开放性,因为这里是“德国通往世界的大门”。这个事例充分体现出地方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其实,马西在阐述德国汉堡的例子之前,已经在《城市世界》一书中提出了开放性对于一个城市发展而言有多么重要,她指出:“城市的能量大部分来自对外部的开放性:来自那些抵达且加入了的混合体,并可能参与创造新文化的新移民;来自贸易连结及文化影响;来自货币流动。如果一个城市不处理其根本所在的交流,就有可能停滞不前,城市也将因此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23)。 这里,我们发现“地方”似乎在开放性与封闭性之间徘徊,学者们都是基于自身的研究对象(地区)来论述其特性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地方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并非简单对立的关系,两者是相互交织的。马西构建起的“全球地方感”的概念,就力图将地方的封闭性和开放性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在这里,开放性是绝对的,而封闭性是相对的。 地方的封闭性与开放性并非绝对对立的,马西基于“权力几何学”的立场,从方法论的高度确立起一种全新的地方观念——全球地方感(a global sense of place)。这个概念建立在空间权力关系的内在机制上,超越了时空二元对立的结构,将空间的开放性与封闭性有机整合到了一起。许多学者在论述地方(本土)与全球的关系时,往往把两者对立起来,突出地方的封闭性,强调地方成为了全球的牺牲品,声言要“保卫地方”,抵制全球化。然而马西在其著名的《全球地方感》一文中则转变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她以自己的居住地基尔本(Kilburun)为例阐述了这个概念。基尔本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地区,世界各地的人都带着自己不同的文化、习惯和记忆来到这里,同时用自己的方式改变着这个地方,这里所形成的地方感就不再是简单的社群感,没有明显的排他性。基尔本在包容各种文化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地方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中所包含的文化元素则是全球性的,全球文化汇聚一点,形成了一个新的地方,造就了“全球地方感”,这其中既有开放性,又有封闭性,绝对的开放性与相对的封闭性交织融合到了一起。正如马西所说的那样,“相较于以防御、反动的观点来看待地方,我实在没办法借由划出封闭的边界来界定基尔本,也不想这么做”。(24)马西的“全球地方感”理论力图在地方保护主义和丧失地方特色、无视地方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颇有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具体而言,城市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地方的实体化的体现,马西巧妙地用“全球地方感”的概念解释了当今人们所面临的新的城市问题。这其中就涉及城市的定居与移动如何协调的问题。有一些学者坚持封闭性与开放性简单二元对立的观点,认为人们所居住的并不是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而是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这种观点强调了空间的开放性,而忽视了封闭性的存在。对此,马西在《城市世界》(1999)中再一次强调了封闭性与开放性相互交织的关系,她指出:“国界在跨国公司的攻击之下已经倒塌,而‘地方文化’也越来越受到外地时尚与创新的入侵……有些移动和流动的障碍正在瓦解,然而在本书中我们发现,也有相反的发展趋势——许多新的障碍陆续建立起来。所以,‘流动空间’绝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某些障碍和界限瓦解了,新的障碍和界限又建立起来”。(25)说到底,马西的观点依然是“全球地方感”的基本立场,是用一种新的空间方法论来解决具体的城市问题的一次探索。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虽然“全球地方感”这个概念诞生于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但某些时候,英美所主导的全球化运动的认识逻辑却挑战着“全球地方感”的基本价值理念。英美发达国家凭借其对全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掌控,成为了全球化进程中的最大受益者,与此同时,这些国家还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和安排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并且以自己的标准来区分“发达”与“落后”,这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各国各地区的独立选择权和由此带来的多种可能性,对空间多样性造成了破坏。这是一种无视“他者”轨迹的空间观,在这种观点中,只存在单一的历史发展模式,单一的地方文化和千篇一律的城市面貌。而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并不是要消灭多样性,恰恰相反,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释放多样性并使其相互融合的过程,正如马西在《城市世界》中所说的:“城市是个多元的地方,很难将其理解为只有一种声音的单一实体。进一步讲,并非所有城市都被包含在一切网络里,也没有单纯被包含或被排除出去的‘整个’城市”。(26) 总之,马西经过几十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以其独特的空间哲学为理论基石,构建起了具有丰富内涵的空间政治哲学理论,并且在当代后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值得学界深入关注与研究。 ①多琳·马西的两本代表作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r: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与For Space已有中文版,她的另两本主要著作Space,Place and Gender(1994)与City Worlds(1999)尚未有中文版。值得一提的是,马西还于1995年发起创办了一份左翼政治杂志Soundings:A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Culture,该杂志发行至今,其宗旨就是要为英国政治、文化和经济论争赋予新的方向与深度,主要目标是探索社会主义传统的创新,催生当代左翼新议程。 ②③④⑦⑧⑨⑩(12)多琳·马西:《劳动的空间分工: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梁光严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1页;第55页;第7页;第123页;第107页;第302页;第304页;第3页。 ⑤对马克思主义的分工理论,西方有很多争论。弗里德曼就曾这样说过:“马克思对社会分工和制造业(技术)分工作了区分。在社会分工中,生产不同商品的不同就业集合被按不同生产者划分。在制造业分工中,生产某个单个商品的工作流程在不同的工人之间进行细分。”(A.Friedman,Industry and Labour:Class Struggle at Work and Monopoly Capitalism,Macmillam,1977,pp.92-93.)马西则引经据典,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段关于分工的精辟论述及其价值表示肯定,马克思说:“工厂手工业分工的前提是资本家对于只是作为他所拥有的总机构的各个肢体的人们享有绝对的权威;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正如动物界中一切反对一切的战争多少是一切物种的生存条件一样。因此,资产阶级意识一方面称颂工场手工业分工,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局部工人绝对服从资本,把这些说成是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劳动组织,同时又同样高声责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把这说成是侵犯资本家个人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工厂制度的热心的辩护士们在斥责社会劳动的任何一种普遍组织时,只会说这种组织将把整个社会转化为一座工厂,这一点是很能说明问题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12-413页。) ⑥多琳·马西:《空间的诸种新方向》,参见格利高里、厄里编《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谢礼圣、吕增奎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3页。 (11)(13)(17)Doreen Massey,For Space,SAGE Publications Ltd,2005,p.9,p.19,pp.177-178. (14)多琳·马西:《保卫空间》,瑷松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第16页。 (15)(16)Arun Saldanha,“Power-Geometry as Philosophy of Space”,in Spatial Politics:Essays for Doreen Massey,edited by David Featherstone and Joe Painter,John,Wiley & Sons Ltd.,2013,p.44,p.51. (18)(20)(21)(22)(24)蒂姆·克瑞斯威尔:《地方:记忆、想像与认同》,王志弘、徐苔玲译,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第107页;第91页;第93页;第94-95页;第113页。 (19)马西的“权力几何学”还以后结构主义的方式为人们呈现了空间权力的拓扑结构。在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发展过程中,波尔尼关于点线面的分析方式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因为这种方法使数学上更多更复杂的面积和空间的计算成为可能,彭加勒开创了一个数学分支——拓扑学。拓扑学广泛地应用于物理学和理论生物学。马西巧妙地借用了这个结构来分析网络、节点和维度的时空关系,她认为经济、文化、政治、地方以及个人之间都发生着不同的关联,都能构成一种拓扑结构,正是通过对空间权力的拓扑结构分析,马西向我们展示了空间的多样性及其与权力的错综复杂关系。 (23)(25)(26)Doreen Massey,City Worlds,Routledge,1999,p.122,p.167,p.125.标签:地理论文; 政治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权力论文; 空间分析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地理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 全球化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