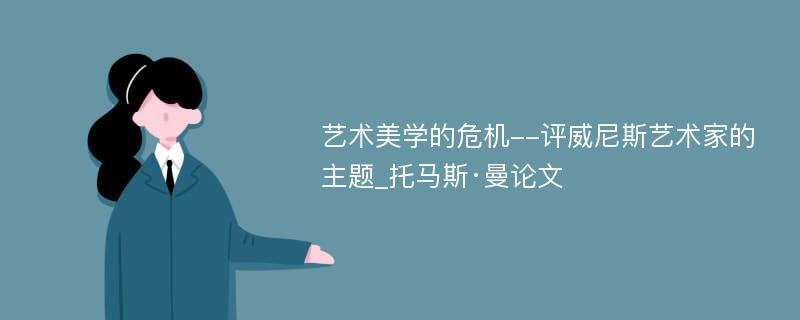
艺术审美的危机——评《死在威尼斯》的艺术家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死在论文,威尼斯论文,艺术家论文,危机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黑格尔宣布艺术已濒临死亡,尼采又号召用艺术克服宗教、道德、哲学及美学等人类“衰颓形式”之后,托马斯·曼在本世纪初上半叶创作的一系列以艺术家为主题的小说,又一次引起了西方世界对艺术问题的关注。不仅在德语国家,而且在非德语国家,这些作品都以它们充实的思想容量、隽永的哲理蕴涵、独特的文学技巧和凝重的文本风格而受到广泛的评论。其中,中篇小说《死在威尼斯》无疑是相当典型的。它1912年在《新评论》上发表时,引起了很大反响,并迅即被译介到法国和美国。二十多年后托马斯·曼在向英语国家的读者作介绍时,也特别强调这是他的重要作品。(注:Preface to Stories of Three Decades,1936。这部Stories of ThreeDecades(《三十年小说》)是英译托马斯·曼作品选集。)
但《死在威尼斯》意义蕴涵的错综程度也是相当突出的。汉斯·R·伐盖特认为,小说“有一个相对短暂和浅显的狭义上的发生史和一个复杂的、相对可以回溯得较远的史前史”。(注:Hans Rudolf Vaget,Thomas Mann-Kommentar zuSaemtlichenErzaehlungen,Muenchen:Winkler 1984,S.175.)托马斯·曼本人的比喻更是脍炙人口:《死在威尼斯》确实是名符其实的水晶多棱体;它是一个结构,一个映象,通过如此难以穷尽的回光返影的性质,从如此之多的切面放射出光芒,以致当它成形之时,创作者自己也会被它弄得目眩神迷。”(注:Preface to Stories of Three Decades,GesamtWerk,B.xiii.S.112-113,Fischer Verlag,1990。托马斯·曼很喜欢这个比喻,在1923年3月1日致费利克斯·贝尔陶克斯的信及另一封致保罗·阿曼的信中也有类似提法。)
所以毫不奇怪,批评家们对《死在威尼斯》的艺术家主题的理解,出现了种种歧见。他们或集中在社会制度对艺术家的压抑上,或偏重于叔本华与尼采的哲学思想的影响,或关注心理分析的运用和效果,或强调新教的伦理规范和本能的冲突……这些观点都不无根据,但在笔者看来,又多多少少忽略了艺术家主题小说的重要核心,即对艺术审美方式的考问。因此本文想从这一维度入手做些考察。
同构解码:从理性主义到审美精神
从《死在威尼斯》的“乐曲式组合起来的意义能指的令人惊异之处”(注:这是托马斯·曼在1930年发表的《生平传略》中谈到《死在威尼斯》众多情节成分时说的话。)中比较准确地剥离出艺术家主题的内涵,著名托马斯·曼研究专家H.威斯灵倡导的结构分析方法(Strukturanalysen)不失为一个启示。这意味着首先要对小说文本结构的特征有所洞察。这一点正是不少批评家所忽略的。
仔细研究小说叙述的展开,可以发现小说的中心情节即中年作家阿申巴赫和波兰男孩塔齐奥的关系,有一个类同性的细节与之相对应,二者形成双重的迭合。那就是故事进行到一半,出现于阿申巴赫幻觉里的年老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青年学者斐德罗之间的关系。这发生在阿申巴赫于威尼斯海滨浴场被波兰男孩塔齐奥的特殊的美牢牢吸引住以后。他曾试图离开,却终因阴差阳错又留了下来。在终日面对男孩的美色进行审美的静观的氛围里,阿申巴赫沉浸在自己的奇思遐想中,仿佛见到了柏拉图对话录记载的苏格拉底和斐德罗讨论美的场景。
这无疑是一个“同构”,或者说是同一主题的“变奏”:年长的智者和年轻的学子通过对话,在感情的基础上,探讨艺术和美的问题,寻求认识与把握美的本质可能性。(注:在苏格拉底和斐德罗之间有一层今天视为“同性恋”的爱慕关系。据文化史研究,这样的关系在古希腊不仅合法,还受到鼓励。从《裴德罗篇》的内容看,这样爱慕关系也有偏于精神和偏于欲望的不同。)区别在于,阿申巴赫与塔齐奥的对话还只限于无声的交流。但他不仅似乎亲眼目睹了千余年前雅典城外小溪边绿树荫下那一幕,而且自己仿佛已化身为苏格拉底,那个因钟爱自己的年轻学生而高谈阔论的诡辩家。在这里阿申巴赫的自我一分为二了。
这样的“自我分裂”又导出了小说前半部另一个更隐蔽的“同构”,即叙述阿申巴赫的文学创作道路的那部分内容。从作品的描写看,阿申巴赫的创作道路,很大程度上是托马斯·曼真实的文学历程的投射。(注:最明显的证据是,托马斯·曼完成《布登勃洛克一家》后曾计划写一部有关弗里德里希大帝的长篇,虽始终未能如愿,但小说中的阿申巴赫恰因这个长篇而大获成功。)作者仿佛在对着镜子写作,写着写着,笔锋转向了镜中形象的写作情况。即使接受有的研究者的考证结果,认为阿申巴赫是以另一位德国作家萨穆尔·卢勃林斯基(Samuel Lublinski)为模特的艺术虚构,(注:Hans Wysling,Aschenbachs Werks,Archivalische Untersuchungen oneinem Thomas Mann-Satz,in:Euphorion 59,1965。也有的研究者指出了阿申巴赫身上和歌德事迹的类同点。)也无法否认这样的写法体现了作者自我的分裂——他本人是作家,却从一种外在的视角来打量评说另一名作家。换个角度,它就是今天的批评理论称之为“元小说”的东西,通过小说形式来研究和表现小说如何诞生。当然在这一同构里,现实生活中的作者的创作道路潜在于文本背后,而阿申巴赫与塔齐奥的人物组合和苏格拉底与斐德罗的同构关系则清楚明白地存在于文本中。
弄清这两个隐性或显性的同构,对理解《死在威尼斯》的艺术家主题至关重要。回头来看前一个同构,它展示了阿申巴赫功成名就的秘诀和他从事创作的指导思想。这位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年作家,成功全凭借“在道德上是一个勇者”。有位观察家形象地把他的生活比喻成紧紧捏住的拳头,从来也不知松驰一下。他的小说就是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和紧张的“纪律”、“顽强意志与坚忍不拔的毅力”的产物。其中反复出现的人物形象,也是“智力发达”、“咬紧牙关”的“新型英雄”。尽管他们形态各异,但无非是故意隐瞒自身堕落的“高傲自制力”,或冒着毁容的危险把奄奄一息的情感纵火烧个精光,或用衰弱无能的躯干来掩饰内心的光和热等等。据说这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即小说里所说的“‘弱者’的英雄主义”,不难看出实际上就是从西方启蒙时期起就得到确立的理性主义。阿申巴赫本人就毫不含糊地“信奉绝对真理”,“崇奉理智”,并公开表示了对理性的信念,那是几乎所有伟大事物共有的标志,意味着“藐视”七情六欲、痛苦孤独、意志软弱。正是在传统的理性主义旗帜下,阿申巴赫完成了一系列有影响的作品,成了时代精神的代言人,登上了文学创作的颠峰。
在去威尼斯休养前,阿申巴赫就是这样一个以理性为最高准则的艺术家。虽然他隐约感到自己的创作已缺乏热情洋溢的特色,需要有一个欢乐的源泉,但他对理性的绝对真理坚信不渝,对情感的道德败坏深恶痛绝,不曾有过丝毫动摇。而一旦他从塔齐奥身上发现了稀有的希腊古典美后,一切全变了。在原先厌恶的阴沉或腥臭的景物中,突然绽放出明亮的奇妙的神奇色彩;从日常习见的太阳、海涛、霞光、云彩和习习微风里,涌现了古希腊众神的形象;而雅典的哲人们,也向他指点了通向美的奥秘的迷津——似乎阿申巴赫所在的不是意大利的威尼斯,而是古希腊的阿提卡。最终表明这一转变完成的,就是他和苏格拉底一而二、二而一的同构。
从第一个隐性同构过渡到第二个显性同构,无疑在明确地暗示,阿申巴赫这一次威尼斯之旅,也是人的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心灵之旅。它有如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他告别了西方的理性主义,转向希腊的审美精神。在这里,众多希腊意象的文化意味,要远远胜过其神话意味。当然,这一转向在阿申巴赫身上是不知不觉发生的,并充满了犹豫、徘徊和焦虑,但一旦发生,却影响深远。在塔齐奥难以抗拒的美的魅力面前,阿申巴赫觉悟到有关美的理性思考是如此苍白无力:“他对自然法则与个人之间所必然存在的关系沉思默想——人世间的美莫非就是由此产生的;他考察了形式和艺术方面的普遍性问题,最后觉得他的种种思考和发现只不过像睡梦中某些令人快慰的启示,一待头脑清醒过来,就显得淡而无味,不着边际。”从此以后阿申巴赫放弃了理智的思维,而一心一意体味着出现在他面前的感性美的化身。他以审美的态度,一刻不停地打量着心中偶像的面容身姿,谛听着对方的笑语欢声。他不讲节制,没有反思,根本不打算约束自己的情绪和冲动。他观赏着他以为是天工造物的神圣艺术品,认定是美的本质的再现的完美形体,如痴似醉,无休无止。以前不但贯穿于全部创作活动,而且作为人生最高目标的理性原则,此刻荡然无存。
这一转向,无疑是对理性主义的否定,最有力的否定恰恰来自现实生活本身。正是在活生生的美的对象面前,阿申巴赫坚持了大半辈子的理性信念分崩离析,溃不成军。同时否定也来自阿申巴赫的内心。他早先保持着但又始终潜伏着的一些原始想法苏醒爆发了。二者的合力,使他同古希腊的审美精神相沟通。他不再维护理智和逻辑,而推崇感官和形体。他明白了,无论上帝向人们显示灵性,还是爱神给人们传授纯形式的概念,都借助了美丽的形体与图形。而美,“是通过我们感官所能审察到、也是感官所能承受的唯一灵性形象”,因此,“美是感受者通向灵性的途径”。不仅如此,“思想和整个情感、情感和整个思想能完全融为一体”。把思想和情感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并且用思想来压制情感的做法,遭到了彻底的抛弃。
在这种状态下,阿申巴赫体验到了新的创作冲动。他不像以前投入写作有明确的目的或使命,或经过冷静的思索和准备,这一次是神来之笔,灵感之华。他被无法抗拒的力量所驱迫,也不明动机是什么,只觉激动万分而不能自己:“这是千载难逢的宝贵时刻,他觉得他写的语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温柔细腻,富于文采,也感到字里行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情意绵绵,闪耀着爱神的光辉。”理所当然地,他把这次写作称做“不平凡的时刻”和“不平凡的活动”。它象征着希腊审美精神挣破了西方理性主义枯僵的茧壳,阿申巴赫获得了文学创作的新动力。
审美超越:天堂之路还是地狱之门?
然而,如果小说的艺术家主题仅限于两个同构的转换所寓含的从理性主义到审美精神的蜕变,那么还不能说《死在威尼斯》提供了多少新东西,因为我们知道,歌德通过他的剧诗《浮士德》,就已试图要将理性主义和审美精神融为一体。席勒也充分地表达了这个希腊化的、将理性和审美合而为一的理想:“希腊人的本性把艺术的一切魅力和智慧的全部尊严结合在一起,不像我们的本性成了文化的牺牲品。……他们既有丰满的形式,又有丰富的内容;既能从事哲学思考,又有创作艺术;既温柔又充满力量。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想象的青年性和理性的成年性结合成的一种完美的人性。……在那时,在精神力量的那种美的觉醒中,感情和心智还没有严格地区别而成为相互敌对又界限分明的不同领域。”(注:《审美教育书简》之六。)
托马斯·曼无疑继承了这一传统,但他并没有简单地重复这一传统的信念。他是想通过《死在威尼斯》进一步展示出,艺术和美的觉醒,因人性本能的无可回避的弱点,很容易陷入危机。这才是小说的深刻之处。
平心而论,小说中阿申巴赫对波兰男孩塔齐奥的赞美和神往,一开始并无多少邪恶猥亵的东西,而是把他当成自己寻觅已久的美的本质的现身来欣赏的。他只是默默地静观,由衷地赞叹这一“精神美的化身”。吸引他的,不止是男孩子希腊原型的俊美面貌,更有透过不为人注意的细节而显露的幼稚而美好的情操——“对听天由命、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表示不满,而对神圣的、无法言表的超然意境则赋予了人情味”。他深信,“只有借助于某种形体,才能使人们的思考力上升到更高的境界”,“欣喜若狂地感到他这一眼已真正看到了美的本质——这一形象是神灵构思的产物,是寓于心灵之中唯一的纯洁的完美形象,这样完美的肖像和画像,有如神明,受到尊奉和崇拜”。
然而,危险潜伏着。心灵向感官和形体开放,虽然能够弥补理性思维的欠缺,体验情感的参与,也有助于性格的完美,但人类天性中固有的欲望和本能,却总是由官能的东西激起。就像小说指出的:“几乎每个艺术家天生都有一种任性而邪恶的倾向,那就是承认‘美’所引起的非正义性”。从理性的信条转向美的对象,在活生生的实际中,而不是在思辨中,审美精神能不能真正把持得住自己,会不会一失足从高贵的感性跌入卑下的欲念?对艺术家而言,这就成了严峻的考验。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会懂得,为什么在《死在威尼斯》有关的描写中,文本的织体既充盈着对感官形体的诗情般的赞美,又每每穿插着对它们的潜在威胁的沮丧和不安?小说的行文几乎处处都是这样光与影、明与暗的交织:把注意力从理智转到官能方面,固然能让思考力升华,但又使得灵魂“一味耽求快乐而忘乎所以”;美丽的图像与形体确实令人难以忘怀,但它燃起的不止是“希望之火”,也有“伤感之情”;对美的化身的赞美有如对神灵的尊崇,但无可否认,“这有一点痴,狂妄,甚至贪婪”……纵然是在美的激情的驱使下写就一段绝妙文章,也“似乎是不可告人的坏事”,要“受到良心的谴责”。
事实上,《斐德罗篇》里的苏格拉底已从不同角度指出了“美是难的”命题。不错,美超出于智慧与理智之外,是感官可见的激发灵性的最可爱形象;但对表征永恒之美的形象,却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邪恶的、渎神的,那意味着只关注肉体美的色欲,另一种是高尚的、虔敬的,这才体现了向往精神美的纯洁感情。此外苏格拉底还认为,美的本质或美的本身,只存在于天的顶端之外的最高境界。生命之灵犹如飞鸟,长着双翼,它飞升到上界,以观照美的存在。但一般的生命之灵到达不了如此高的境界,因为它的双翼就像驭车的两匹马,一匹驯良一匹顽劣,难以控制,丑恶罪孽也经常损伤它们。所以生命之灵尽管努力追随神灵,仍然容易失去羽翼的平衡,而沉沦不复。(注: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并参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第19章,人民出版社,1993年。)
小说未曾正面介绍以上这些观点,但它们潜在的意义指向是确定的。只要提到《斐德罗篇》,凡了解古希腊文化遗产的人,都不难回忆起有关的内容。在小说相应的描写里,遐想中的对话其实已透露出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的危险:品德高尚的人在表征永恒之美的形象面前虽虔诚崇拜,但爱之烈焰仍随时可能将他焚毁;而求爱的人比被爱的人更神圣的观念,本身就是七情六欲所有的狡黠和最隐秘的乐趣的来源。这里的种种微妙,也正是阿申巴赫从静观的审美不知不觉地陷入色欲迷茫和情感倒错的歧路的肇始。我们看到,在塔齐奥有意无意的迷人的微笑前,他不禁悄声吐出了那句表白爱情的陈辞滥调,并一反常态,花里胡哨地把自己打扮起来,完全忘掉了几天前他还多么讨厌别人这样虚假而不得体的装饰。与此同时,他心中的幻景也增加了象征着原始本能的潘神世界的神奇动物,终于在一次可怕而奇特的梦境中,亲身参与了“异教的神”——酒神淫猥放荡的祭祀仪式。
在这里,酒神的文化意味仍超过其神话意味。换言之,酒神的出现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审美精神陷入危机的一个表征。因此不能单独地考究酒神之梦的神话渊源,或对号入座地将酒神等同于作品中的人物。(注:如Hans-Joachim Sandberg就认为阿申巴赫是酒神的化身,塔齐奥则是信使神赫尔墨斯的化身。)只有将酒神之梦和苏格拉底与斐德罗的对话联系起来,才能准确把握《死在威尼斯》中酒神的象征属性和对于艺术审美的意义。
在德国文学传统上,酒神的出现同样不是第一次。作为西方理性主义和希腊审美精神融合为一体的努力的继续或补充,尼采是第一个(正如他自己宣布的)将酒神当作希腊灵魂的最精华部分引入进来的。在他看来,由于歌德的“希腊的”概念排除了孕育酒神艺术的根本要素,“歌德并不理解希腊人。因为只有在酒神秘仪中,在酒神状态的心理中,希腊人本能的根本事实——他们的‘生命意志’——才获得了表达。”尼采宣布:“一切生成和生长,一切未来的担保,都以痛苦为条件……以此而有永恒的创造喜悦,生命意志以此而永远肯定自己,也必须永远有‘产妇的阵痛’……这一切都蕴含在狄奥尼索斯这个词里:我不知道有比这希腊的酒神象征更深的象征意义。在其中可以宗教式地感觉到最深邃的生命本能,求生命之未来的本能,求生命之永恒的本能”。(注:《偶像的黄昏》(1888年)。中译文见《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三联书店,1986年,第333-334页。尼采的批评还涉及以研究希腊艺术著称的文克尔曼。)尼采在他“开始出发的地方”即《悲剧的诞生》中,就倡导酒神艺术和日神精神的对立,原因是一样的,即为了提倡“一种满溢的生命感和力量感”。
但在《死在威尼斯》中,这种生命感和力量感已过分涨满,以致溢出了正常的轨道,梦境里整个酒神祭充斥着淫乱、粗鄙、喧闹和堕落,显然已和尼采用以拯救人类衰颓的酒神艺术大异其趣。为什么会这样?有证据表明很早以前托马斯·曼对酒神艺术就有自己的看法。他于1895年发表了一篇书评,指出“新近在抒情诗人们中间有一部分人,他们喜欢让他们的情绪和感情‘彻底得到放纵’。人们称之为‘酒神的艺术’……这涉及在艺术的状态中把伸手不可及的迷雾‘诗化’得更浓密,不让它的迷误遭到粉碎;这涉及把虚假的夸大其辞以强有力的形式加以魔术化,不仅仅用酒神狂放的号叫来表明自身的无能为力。”(注:引自Thomas Mann und seine Quellen,Festschrift fuer Hans Wysling,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 1991,S.70。有的研究者如克劳斯·施略特认为,直到和《魔山》同时诞生的散文《歌德与托尔斯泰》中,尼采的艺术观的影响才被托马斯·曼抛弃(见所著《托马斯·曼》,中译本第120页,三联书店,1992年),这一评价显得过于保守了。)从中可见托马斯·曼对尼采的酒神艺术抱着不同见解。
那么能不能认为,托马斯·曼反过来落入了尼采批评的那种泥沼,是“按照德国习性,根据希腊哲学家来判断希腊人,例如把苏格拉底学派的庸俗特性当作理解希腊本质的启示”呢?(注:《偶像的黄昏》(1888年)。中译文见《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三联书店,1986年,第332页。尼采的批评还涉及以研究希腊艺术著称的文克尔曼。)这种看法又是另一种简单化。其实托马斯·曼上述的批评,主要针对一些二流的模仿者。即使在40年代态度更为严峻的《从我们的体验看尼采哲学》一文中,托马斯·曼一边揭示了尼采狂放不羁的审美醉意实质和野蛮主义相邻,一边也没有忘记肯定,这种把一切生活当作审美现象的存在的唯美主义是“反叛资产阶级时代全部道德的第一个形式”。毋宁说,小说是在不偏不倚地展露艺术审美的沉醉有可能达到何种危险的边沿和极限。这一点是和柏拉图对话录《斐德罗篇》有关美的追求易于堕入沉沦的宗旨相一致的。
至于这两方面都借助梦境来昭示,则反映了作者的独特用心。正如弗里德利克·J·霍夫曼所说,托马斯·曼这一由精神分析而来的表现手法,并非为了实施某种“疗效”。“曼怀疑……用艺术家生理和心理上的本性性质的术语,简单地解释艺术家的处境,对其人生和作品还只是一个不充分的证明。他依然首先对艺术家感兴趣,因为艺术家可以洞察到人类行为的非理性渊源。关于人类无意识的‘黑暗领域’的知识,加上对存在于人类意欲和试图控制它的力量之间的张力的理解……仍然是审美态度(aesthetic temperament)的明显标志。”(注:Frederick J.Hoffman,Freudianism and the Literary Mind,pp.215-216,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45.)
也正在这里,托马斯·曼超出了歌德。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代表着人类对外部世界的知识的需求,他不知疲倦地试图掌握所有的知识,靡非斯特就用关于人的自身、关于人所处的世界的绝对真理来引诱他。而这样的知识,如果没有魔鬼的诱惑和邪恶力量,人们既不可能生企盼之心,也不堪负担或承受。在靡非斯特的魔力的协助下,浮士德尝试了种种可能,包括和古希腊的美人海伦结合并生育了下一代,但一切努力,没有超出对外在世界各个方面的了解、把握、占有和征服,遵循的途径也是现实时代和古老传说的贯通,是基督教信仰和希腊风范的组合。但托马斯·曼不再停留于这一点,而是回溯得更远更深入,回溯到了既非基督又非希腊的心灵国度,无所遮掩的人的内在的国度,这里虽然一再努力要建立理性的永恒王国,但在根本上却是审美的本能的无底深渊。酒神的迷醉就是这一深渊的黑暗力量的形象表征。
完全不妨认为,在《死在威尼斯》中,神灵也在用美的真相或本身来引诱我们,但若失了神灵的帮助,单凭人的能力,也同样不堪负担或承受。为什么阿申巴赫面对活生生的美的化身,豁然醒悟于前,却又走火入魔于后?关键就在这一点。这恰恰也是艺术家们无可回避的宿命。一旦他们经过艰难的自我摸索,遵从内心突然苏醒的声音的指引,踏上审美创造的真正历程,并不意味着就顺利地超越了世俗的沉浮。离开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远不等于征服这一条道路。在艺术审美的漫漫长途中,继续有魔鬼与上帝的考验在等待着,稍有不慎,或者略微孱弱一点,都会把持不住自己,重新遁入罪孽的轮回。美的精神的觉醒驱动了感官的体验,冲决了冷冰冰的理智的囚笼,但也很可能同时开启了地狱之门,而不是一般人设想的天堂之路,根源就在人性的深处,赤裸裸的不加武装的灵魂所拥有的,远不止“善”、“恶”之类二元对立的抽象概念。
孤独死亡:召唤、感应和新生
托马斯·曼曾说过,他起意写《死在威尼斯》,起初是想表现“艺术家尊严的矛盾”和“文学大师的悲剧式的东西”。(注:转引自克劳斯·施略特《托马斯·曼》,中译本第84页,三联书店,1992年。)说到底,这一“矛盾”或“悲剧”,实质就是艺术家“把整个心灵都奉献给美的创造事业”之后面临的两难处境。
所以一旦选择了艺术和审美,也就不得不随时准备面对死亡,这不仅仅因为艺术是一种更高的生活方式,一种既“带来更深刻的欢乐”,也“更快地消耗着生命”的生活方式,同样也由于它必然要面对天堂与地狱间的临界抉择。在此意义上,小说标题寓含的死亡主题,不应孤立地视为叔本华哲学的痕迹,它本身就是作品艺术家主题的有机组成。从这里才能真正懂得,托马斯·曼在写作同为艺术家题材的《托尼奥·克列格尔》(1903)时,为什么会感叹“文学即死神”。(注:转引自克劳斯·施略特《托马斯·曼》,中译本第84页,三联书店,1992年。)
事实上,死神的影子不仅鲜明地体现于小说标题,也再三表现在具体描写中——死亡不仅是艺术家阿申巴赫的下场,而且在他踏上心灵之旅的起点前就向他招手了。那个改变了阿申巴赫生活的常轨,使他滋生出不可遏止的漫游远方的渴念的神秘流浪汉,就是在殡仪馆的门廊里,在一片坟场般的氛围里,向他发出无语的召唤的。这个流浪汉倏忽间就看不到踪影,他究竟是匆匆的过客,或者就是死神的使者?
同样的道理,威尼斯这个“过去有一段光荣历史,现在还很有魅力”的美丽城市,这个几个世纪来以它辉煌的绘画、音乐和瑰丽的建筑物向整个欧洲散发着无穷诱惑的艺术之都,在阿申巴赫印象中却是那样晦暗无光,阴沉丑恶。咸水湖蒸腾着腐臭,大街小巷充斥着恶浊的垃圾,海洋也萎缩成无精打采的黑压压一片……甚至威尼斯水城特有的平底小船贡多拉,在他心目中也和棺木一样,漆成特殊的黑色,让他联想到死亡、灵柩、葬礼和临终悼别,但又令人惊异地有一种舒适之感。当他坐着平底小船驶向海滨浴场时,有没有意识到,对他而言威尼斯之旅实际也是死亡之旅?
这一死亡之旅必定相当孤独,因为一般人只知道活着,却不明白生命的历程同时也是死亡的进程这样一个辩证道理。阿申巴赫未必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因沉溺在对美的偶像的迷醉中,他并不回避死亡的到来。大规模的瘟疫悄无声息但又无可置疑地逼近并降临了,他反以为是和塔齐奥有更多时机单独相处的好机会。他越来越感到死神的威胁,但宁可与瘟疫为伴,也不离开美的偶像。这样做看似违背常情常理,但对一心一意追求审美理想的艺术家却合乎逻辑。他在流逝的夜色中恍惚见到的故乡那只古老的计时沙漏,已经向他发出明确警告;沙漏上部不多的赭红色沙子,正在快速下泄,形成了一个小而急的漩涡。这无疑在预示,他的生命岌岌可危。但他身不由己,似乎心甘情愿看到自己生命的终结。
阿申巴赫死时同样十分孤寂。他最终死在塔齐奥一家即将离开威尼斯的那天早晨的海滨沙滩上,除了临死一刻他犹在瞻仰的偶像,四周几乎再没有其他人。上流社会尽管震惊于他的死讯,却不知道他真正的死因。虽然小说专门有一节文字,交代阿申巴赫“个性孤独,沉默寡言”,然而孤独不仅仅是个性的问题,而是所有将生命奉献给艺术审美事业的人必不可免的遭遇,这一事业也是一般人难以接近并能理解的。阿申巴赫在整个威尼斯逗留期间如此离群索居,极少与人交往,主要就因为他过着一种特殊的心灵的生活。所以,即使他仿佛性欲倒错地把自己打扮得像个风骚的老情人,也仍有别于他在赴威尼斯途中遇到的那个花里胡哨的老头,因为他并不和别人胡混在一起,而只是珍藏着并守护着内心独自的向往和企盼。
面对阿申巴赫衰朽的尸体,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托马斯·曼长篇小说《魔山》的这位主人公,具有类似的精神气质:体验一切,不惜冒险踏入各种禁区,甚至是同道德王国相对立的罪恶王国。这其实是艺术家共同禀有的特殊气质。差别在于,在《魔山》里,卡斯托普因意想不到的疾病栖身疗养院,从而中断了和世俗的中产阶级社会的联系,唤醒了他原先昏睡着的敏感和勇气,促使他对存在的内在本质进行内省,同时在这过程中始终有来自各个方面的不同信念和不同力量在影响着他,最后魔山上的年轻人在周围不同方向的合力作用下摸索到了未来的道路,重新回到了生活中。而《死在威尼斯》的阿申巴赫,因听从了富于象征性的流浪汉的暗示,打破了日常起居和从事写作的有规律生活,来到远方陌生的环境中,自由释放出平素理性禁锢下的冲动,一边独自品味内心的潮涌,一边又不知不觉地为其裹挟而去,迎来了孤独而死的结局。
但对阿申巴赫本人,这未尝不是最好的归宿。他数十年间辛辛苦苦铸就的理性信念,就仿佛是一袭铁衣,既包裹住他的心灵,也支撑着他的躯壳,现在他已经完全脱卸下来扔掉了它,只靠美的激情的燃烧供给他生活的光热。那么,当炽情之火和因之而起的审美对象不在以后,他又以什么东西作为自己生存的根据?难道还要他再度捡起业已破碎的铁衣重新披挂在身?因此阿申巴赫临死是幸福的。就在那一瞬,他似乎还看见塔齐奥的灵魂在对他微笑,为他指示着方向,而他自己也继续像往常一样跟着美的灵魂在神秘莫测的太空中神游。这不再是前些日子他在威尼斯城的无卿盯梢,而是一种质的超升和飞跃,因为在他生命行将结束的前几天,那个意义深长的同构又突然出现了。在神思恍惚中,苏格拉底又和斐德罗作了一次对话,更确切说是苏格拉底大彻大悟的独白。年长的智者已认识到,凭感觉而获得灵性是一条虽幸福而又冒险的道路:“美意味着纯朴、伟大、严谨、超脱及秀丽的外形。但……秀丽的外形和超脱会使人沉醉,并唤起人的情欲,同时还可能使高贵的人陷入可怕的情感狂澜里。”这一启示无疑是他以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
既然生命中寄寓着死亡,死亡也可以意味着新生。正如歌德一首小小的哲理诗《幸运的渴望》所写的,只要不曾像飞蛾那样一往情深地追求光明并最后在火焰里殉身,只要不曾有过“死和变的经验”,那么在这“灰色阴暗的尘寰”里,你就永远“只是个忧郁的过客”。也许,正是由于死亡,阿申巴赫才得以把自身的蜕变坚持到底,让自己的心灵之旅升华抵达它的终点。
结语
那么,《死在威尼斯》的艺术家主题有无积极意义呢?回答是肯定的。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小说展现的并不止于个别人的遭遇,而是着重在理性的或审美的艺术思维方式的选择过程,这是摆在所有艺术家面前的难题。但这一艺术审美的难题并非玄学思辨的产物,而是实际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的挑战。它表明了西方理性主义统治地位在世纪之交的动摇,又反映出审美精神自身的困境。正如卢卡契所说,托马斯·曼充分领会并把握着他那个时代高度发展的德国哲学传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透彻地了解那些哲学体系和时代基本问题的亲密联系,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完美地把人们痛苦地获得的哲学信念同艺术的创作结合在一起。(注:Georg Lukacs,In Search of the Bourgeois(1945),in The Stature ofThomas Mann,ed.by Charles Neider,New Directions,1948,p.472.)他的小说创作中的艺术家主题,既因其内在的美学哲学蕴涵而具有普遍价值,又没有脱离和时代的紧密联系。
同样作为艺术家,托马斯·曼毫无疑问也感受到了审美的危机。面对这一处境,他不可能无动于衷。尽管他和20世纪初多数作家一样,只从事展示而不是指引,尽管他倾全力而为之的,只是以精雕细琢的笔触,曲尽其致地写出艺术家进退维谷的各种体验与感受,但不应把他当作无倾向性的专以暴露为目的的反讽家,或单纯的审美困惑的鉴赏者。就像D.J.恩莱特说的:“对曼而言,在本质上艺术家永远是个意义多重而含糊的人物。但这必须立即加上一句,就像曼对疾病的不间断研究是为健康服务一样,他对艺术家创造活动和心灵的探究也是对生活的某些关节点的真正关注,在那些关节点上问题最为确实地被摆了出来,并且迫在眉睫。”(注:D.J.Enright,The Apothecary's Shop:Essays on Literature,Secker &Warburg,1957,p.136.)正是这一关注,体现出小说家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由此看来,不能简单地认为,托马斯·曼一系列规模和形式不同的艺术家小说,仅是为了宣泄自己病态的心绪,从中获取个人的疗救或“鞭策”。与此同时,轻率地斥责托马斯·曼小说的艺术家形象也显得过于浮浅。在他笔下,艺术家不只是一种职业或行当,就其本质而言,更是一种生存方式,不同于世俗的、功利的、利害关系的审美生存方式。它不一定是纯粹的静观,也未必是逃避尘世的怯懦,而更多是在对抗理性主义的抽象教条乃至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中的独立抗争。这样一来,艺术家面临的难题,实际也是人们至今仍在面对的难题,只不过艺术家更敏感、更强烈地向往着超越,也更深沉、更急剧地体验着痛苦。
从人类心灵历程的宏大视野来看,小说的艺术家主题的意义还要更为深远。托马斯·曼本人就曾从思想史的角度回顾和瞻望了西方“反对18、19世纪古典理性信仰的叛乱”,即以尼采为代表的“一场席卷全西方的运动”。这一反叛运动虽有所成却未能毕其功于一役,所以“它必然的续篇是在获得一个较之资产阶级时代自负浅薄的人道概念更具深度的人道概念这一新的基础上重建人类理性”。从这样的长期任务来看,“贬抑理性和意识以捍卫本能是一时的修正,而持之以恒的、永远必要的修正是以精神——或者以道德,听凭所愿——捍卫生活”。(注:《从我们的体验看尼采哲学》,中译文见《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版,第341页。)尽管托马斯·曼的艺术家小说未能明白告诉我们,究竟应如何“重建人类理性”,究竟应如何以精神来捍卫生活,但已经表明,仅仅为了实现第一步的修正,即贬抑和冲破那种古典的理性并尝试一种艺术审美的生活方式,人们需要何等的勇气,付出何种代价。他们彷徨逡巡的艰难步履,留下的沉重而难以磨灭的脚印,正是迈向未来的更具深度的“人道概念”的必不可少的一步。
伟大的席勒早就意识到了全部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他指出:“问题在于人怎样开辟一条道路,使他从一般的现实达到审美的观实,从单纯的生命感达到美感。”(注:《审美教育书简》之二十五。)今天人类仍面临着这一远未完成的任务。道路有待继续开辟,续篇有待接着撰写,无论在理论或实践的层面,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