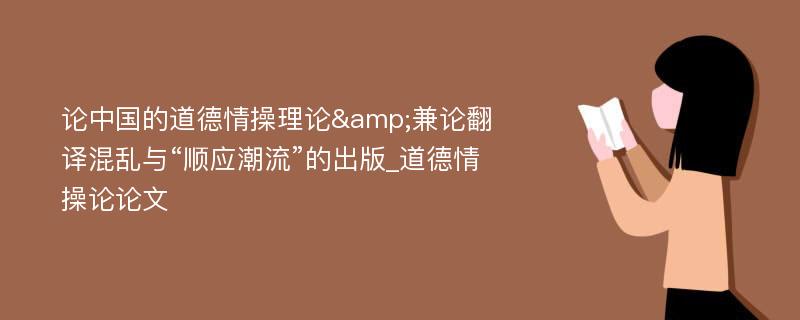
《道德情操论》在中国:略论翻译乱象与“跟风”出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操论文,中国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道德情操论》在中国的接受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此书是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主要著作之一。在过去的近10年间,斯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中译本可谓国外学术著作中版本最多的两本书。遍览图书市场,此书不同译本的封面、封底或腰封上大多印着“总理推荐”“作者五次修改”等广告语,甚至不加分辨将其好友大卫·休谟那段“主教到米勒书店购买此书”的戏谑之语(参见:欧内斯特·莫斯纳、伊恩·辛普森·罗斯编:《亚当·斯密通信集》,林国夫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65页)写上作为此书受欢迎的明证。的确,此书自1759年由伦敦的米勒书店首次出版以来,各方好评如潮,出版商更是欢欣鼓舞。休谟言及的宗教人士、文人贵族、政客书商的赞誉、喝彩之声,却有遮掩《道德情操论》真正价值的嫌疑。作为斯密好友,休谟勾勒欢迎者的身份与心态时似有“明珠暗投”的惆怅语气。在他看来,获得一帮有迷信观点的人的称赞,对一本杰作的作者来说实在不是件好事;如若大众真正理解而不迷信盲从,这倒真是此书之大幸。当然,《道德情操论》堪当赞美。它言辞优雅,乃英文写作之典范;而且,其理论博众家之长而有所发展创新,确实值得进行严肃的学术探讨。同时代其他严肃的学者如拉尔夫·格雷菲斯、埃德蒙·伯克以及法、德两国的知识界,也都提出了严谨的学术批评。因此,此书堪当经典,值得反复阅读。
然而,造化弄人。两百多年之后,《道德情操论》当年在不列颠的命运又在当代中国重演:“跟风”出版与草率的翻译比比皆是,一片推崇喝彩声下掩盖了真正严肃的阅读。1997年,《道德情操论》有了第一个中文译本,即由蒋自强先生等人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本。从1997年到2012年,《道德情操论》已经有将近30个译本出现。一时之间,不同版本的《道德情操论》充斥图书市场,令读者眼花缭乱。以学术出版著称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出版社,都将出版《道德情操论》视为一线商机。
这跟风而来的众多译本,凸显出中国翻译著作出版的种种乱象。不同译者几乎都很少说明各自译本与其他译本的不同之处,很少提到是否参考、借鉴了其他译本,或者指出各自译本的优点和不同理解。如此反复翻译、出版,是否是后来的译本就在前面译本的质量或理解上更胜一筹?对照几个译本即可看出,有不少译本只不过是在已有译本的基础上稍加改动、修饰罢了。比如,2008年北京出版社的译本、2010年华夏出版社的译本,与1997年商务版在很多地方都有雷同。也有译本对英文本进行了大胆编排,在章节内容上做了极大的改动,而这些改动有何理由却未告知读者。比如,2011年商务印书馆国际出版公司的译本、2012年华中师大出版社的译本,就对《道德情操论》的章节做了大胆的改编:或将某些章节提前,或将同一卷内容拆分,或直接砍掉第七卷的内容。如此翻译,是否真有新意还是故弄玄虚?若是因为这样重复翻译、出版,必须突出各自译本的特色,大可以写一段“告读者”,告诉读者译者心中的斯密和《道德情操论》是何种模样,该译本的理解角度和特色等。然在对此书一知半解的情形下随意翻译编排,无论是作为学术著作还是心灵鸡汤,都是极不严肃的。针对这种随意编排的现象,2008年,李华芳曾撰文《总理推荐书,人们就该读?》(参见http://book.douban.com/review/1419181/),详细评论过2008年中国城市出版社的译本,批评该译本对《道德情操论》第七卷的删砍,并指出翻译界存在的复译、抄译以及翻译态度等种种问题。
诚然,一个文本一经诞生,的确无法阻止读者以怎样的心态接受。读者若要砍头削足,取其脏腑,或手足鳞爪,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他人无权干涉。就像鲁迅先生谈到《红楼梦》的接受时所说的那样,“一部《红楼梦》,道学家看到淫,经济学家看到易,才子佳人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了排满,流言家看到了宫闱秘事”。一本书内容丰富方能“横看成岭侧成峰”,这也未见得就是坏事。中国读者中,有人将《道德情操论》理解为伦理道德经,有人用之作为处世箴言,或视之为严谨的学术总论,统领经济、政治、语言等各门学科之纲;这些不同读法本身无关紧要,只要读者能够从中获取正能量即可。但译者如此引导读者,则不知想要通过这一媒介传达怎样的信息了:是将此书视为道德说教呢,还是当作风雅谈资呢?在这个读图比读字多得多的时代,估计连“附庸风雅”都谈不上了。尽管现代的大众传媒如此发达兴盛,众多译本也让人们有各种选择的余地,但真正深度的阅读恐怕不多。或许,当年的英国读者还真正读过此书,没有将此书作为书柜、床头的装饰品,而现今中国如此众多译本的购买者,是否真正读过此书,则实在难料。
翻译作品的接受需要准确的翻译和学术研究的推动,需要研究型翻译。早在2005年,罗卫东先生就在《老调重弹:研究型翻译的重要》一文中谈到,对斯密经济学、伦理学思想渊源的理解影响译者对《道德情操论》文本中一些关键词的翻译(参见《博览群书》2005年第3期)。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merit、demerit的翻译,译为“优点”、“缺点”显然与斯密所谈的“正义论”不匹配。另外,sentiments、principle、sympathy、nature等词语都是需要译者审慎对待的。研究型翻译需要学术研究的推动。这些年来,伴随国际斯密研究的热潮,国内的斯密研究也有兴起之势,尤其是斯密的伦理学,不仅吸引了伦理学研究者的关注,同时也让经济学家得以重新思考斯密的整个思想体系。随着1997年《道德情操论》的出版,以及对“斯密问题”的追问,经济学家们也开始正视斯密研究中的某些问题。晏智杰先生就曾撰写《晏智杰讲亚当·斯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这样介绍性的著作,向广大读者介绍斯密的经济、伦理等思想。同类的著作在国内也有几部,而学术界内以斯密伦理学作硕士、博士论文主题的文章并不少见。但是,伴随着《道德情操论》出版而来的斯密伦理学研究,也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抬高斯密伦理学的地位,贬低经济思想的重要性,此种现象归根到底也还是因为我们对斯密的思想缺乏整体的认识和解读(参见罗卫东:《情感秩序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38页)。同时,对斯密思想缺乏整体认识这种现象也造成了译本众多却良莠不齐的后果。
研究型翻译,需要全面理解斯密的思想体系。既然中译本有广告打出此书是斯密生前五次修改的杰作,那么,翻译过程中参考一下这五次改动就显得很有必要。从1759年到1790年,六版《道德情操论》出版,而且每次都有或大或小的改动。这30多年的时间中,正是英国和欧美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每次再版,斯密一方面要回应这些批评,一方面也加入自己的思考。相比《国富论》的四版三次修改,斯密对《道德情操论》六版五次修改的呕心沥血非同一般。译者或读者从这五次修改中能获得些怎样的信息呢?
根据格拉斯哥版斯密全集第一卷编辑拉斐尔、迈克菲撰写的《格拉斯哥版〈道德情操论〉编者导言》第四部分的说明,此书版本及改动如下:1761年第二版除了篇章的调整,还有一些重要的修改,比如,斯密在第一卷第三篇第一章第九段的脚注中再次阐释同情的含义,作为对休谟的答复。在第三卷第二章增添了16段,尤其是无偏旁观者理论的修改,为良心论提供本源上的解释,作为对艾略特的答复。1767年第三版,斯密将《论语言的起源》作为本书的附录出版,此文1761年在《哲学杂录》第一期发表,在第四、五、六版中一直保留。笔者猜测斯密附上《论语言的起源》,或许是想以同情在语言起源上的作用来补充《道德情操论》中的同情理论。1774、1781年的第四、五两版,斯密做了一些细小的修改,包括词语书写的现代形式,例如将tho’改为though、compleat改为complete以及一些标点符号的改动。这也可以看出斯密对英语写作的严谨态度,以及对读者阅读的尊重。1790年第六版做了很大修改,增加了很多内容,包括第一卷第三篇第三章;改写第三卷第二、三章的内容,包括对良心、无偏旁观者理论以及自我控制的论述;增加整个第六卷;改写第七卷第一篇第一章;增加《告读者》,说明其改动的内容。另外,两位编辑还提到了《道德情操论》1792年第七版的来龙去脉,认为这一版是斯密没参与校对的。
我们知道,第二版中对休谟的回应,是斯密对自己同情理论的一次申明。在斯密之前,苏格兰启蒙时代其他思想家也提出过同情理论,比如哈奇森、休谟等,尤其是后者的同情理论,在其《人性论》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该理论也非常明确:同情是情感交流的媒介。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承袭了先前同情理论的某些观点,但也对同情的内涵提出了新看法。这个脚注正是对此的解释。在此,斯密赋予同情以认同(approbation)的含义,以此论证同情的愉悦,这一层“认同”的内涵对《道德情操论》中的正义论、良心论的论证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在斯密文本中,同情究竟有多少层内涵,分别起到什么作用,虽然已有沃哈恩指出(帕特里夏·沃哈恩:《亚当·斯密及其留给现代资本主义的遗产》,夏镇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34页),此观点还可进一步探讨。而在对艾略特的答复中,斯密则提出以不同层次的旁观者的同情共感论证良心和义务感的形成,比其他前辈们将良心寄托在宗教情感或无凭据的道德感上要更进一步。
第六版增加的内容应该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卷第三篇第三章,论述道德情感败坏的情感因素,第六卷对德性品质的分析指出了“经济人”和“政治人”应该具备的品质,以及斯密对斯多葛学派相关内容的调整修改,这些重要的修改足以反映斯密晚年对商业社会道德败坏的担忧,以及对商业社会个体品质的设想。商业社会的个体是“经济人”,也是“政治人”。“经济人”的提法在经济学界似已成定规,而“政治人”的提法却很少见,斯蒂格利茨认为斯密没有将“政治人”和“经济人”统一起来(参见唐纳德·温奇:《亚当·斯密的政治学》,褚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160页)。但笔者认为斯密将“政治人”和“经济人”的品性统一在第六卷《论德性的品质》之中,其对体系精神和公共精神这两种品质的论述不仅是对“政治人”的假设,也是对“经济人”的要求。笔者以为更重要的是,斯密设想了商业社会的“人”——不仅是经济人、同时也是政治人——这个原子化的“人”的各种品质。
斯密的五次修改至少可以反映出:一、篇章布局的严谨逻辑;二、对自己理论的充分论证;三、对英语写作的严肃认真;四、对其所处时代问题的密切关注;如果可以的话,还可以加上斯密对自己道德哲学体系的完整性、统一性的注重:因为自德国历史学派提出“斯密问题”以来,体系的统一性就是一个问题,而斯密研究中已有一类观点指出没有“两个斯密”,其依据便是对文本的阐释。随着研究的深入,斯密的语言论、修辞学以及天文、物理学史中的观点,或许都可以与《道德情操论》形成互文。以上五点提醒译者:第一,不应该随意改动篇章目录;第二,译者应该仔细揣摩斯密提出的理论,注意各种措辞的准确性;第三,应注意修辞标点的使用;第四,译本应注重斯密思想体系的整体性。对修改内容的理解,不仅有助于译者的翻译,同样影响读者对文本的接受。尽管翻译是一项创造性工作,译者有权根据自己语言的习惯进行翻译,但如此重要的修改,被大多数译本视而不见,那些不考虑作者意图、不理解作者用意的译本,恐怕再多也无益,反而造成资源的浪费。
18世纪的斯密撰写《道德情操论》面临的问题与当代中国的时代问题颇有相似之处。斯密通信集的编辑之一伊恩·罗斯撰写的《亚当·斯密传》中在不同章节讨论了这六版的修改与时代背景的关系,尤其是第六版修改的时代背景。此时,尽管英国已经远离光荣革命、刚刚结束美洲独立战争,法国革命一触即发,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转型并未彻底完成。斯密认为此时应为立法者提供道德上的、而非经济上的建议。同时,斯密意识到社会上新的财富以及那些拥有这些财富或拥有获得这些财富能力的新生代领导者们所树立的榜样,威胁到了传统道德的确定性,他似乎认识到了完全有必要重新敦促人们认识道德情感的重要性,同时阐明他所设计的分析美德本质的“体系”及我们所具备的能让我们感受美德的心灵力量(参见Ian Simpson Ross:The Life of Adam Smith,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斯密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时代。E.P.汤普森以“道德经济”概括了商业社会来临之前的经济社会形态,而到了18世纪,“市场经济”已经逐渐占据了整个社会,以斯密的话说,是一个“每个人都成为商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有交换自己劳动产品的自由,这与奴隶社会和中世纪的交换形式截然不同。一旦享有这种自由,人们追逐财富的欲望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贪婪、奢侈等以往被批判的品性开始获得一定的认可,但伴随而来的是财富与德性的矛盾日益激烈。富与德的矛盾古已有之,然在商业社会尤为突出。在这个人与人皆为“陌生人”的时代,会有怎样的社会秩序?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从人类的基本情感、欲望出发,论证道德情感和社会秩序的形成,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的回应。然而,他也看到追求权贵的激情所导致的道德腐败的后果,却无法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在第六版新增的第六卷中,他对“经济人”、“政治人”以及商业社会的“人”的品性的设想,以及其思想中自然神论的色彩,或许是他对这一问题的某些思考。当代中国正处于这样一种巨变之中,熟人社会逐渐瓦解,陌生人社会正在形成,面临这样的变化,对道德情感的吁求与公序良俗的建设如此迫切,《道德情操论》至少在某些方面能为人们提供一些启发。
相比斯密另一本著作《国富论》第一个中文译本的诞生,《道德情操论》的第一个中译本晚了近一个世纪。20世纪初,中国亟须富国强兵之道,作为一本讲述富国富民的英国著作,《国富论》很自然被译介到中国。直到现在,严复翻译的《原富》这第一个译本仍有其一定的价值。到20世纪末,中国经济已经获得一定发展之后,斯密这本论述“道德情感”(moral sentiments)的著作才逐渐受到国人的关注。这种与英国恰恰相反的接受过程,概因为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苦难历史,而一旦获得独立发展,道德情感的问题才重新提上日程。中国并不缺少这样的著作,先秦诸子百家的经典也曾提到人之情欲,但总体来说,中国古典哲学却是概论颇多,而少有像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这样对人类欲望、激情的条分缕析、细致剥离的论述。李泽厚先生则在《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和《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两书中再次强调“情本体”的意义。但“情本体”的“情”是何种“情”?又如何作为本体?这些是他没有展开的问题。李泽厚先生开启了对情感问题的思考,而苏格兰启蒙作家的道德情感论恰好回应了这样一种思考。
无论是中国当下日益兴盛的国学、儒学,还是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或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情感理论,它们所致力的是对人的激情的重新认识。这是一场新的启蒙,一种情感的启蒙,它真正认识人类的各种情感如何引导人们在经济政治活动中构成道德伦常的秩序以及应有的公序良俗。当代中国正需要这场情感启蒙。所以,我们期待更好的译本出现,也期待更严肃贴切的阐释产生,期待真正的阅读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