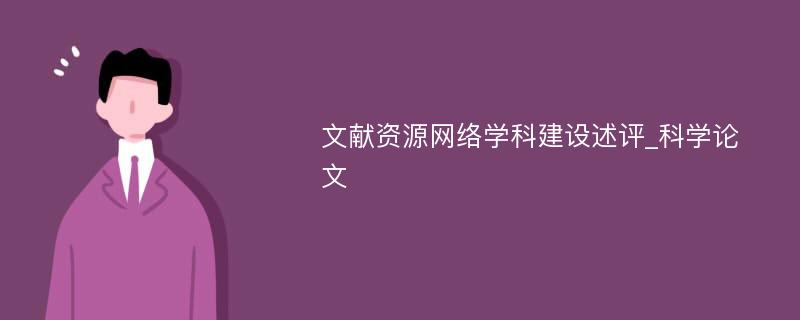
文献资源网络的学科建设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学科建设论文,文献论文,资源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献资源网络是指众多文献按某种形态相互联结的关系总和。它表现为由文献机构和通讯设施互相连接后所形成的纵横交织的组织结构。它是把文献资源和网络技术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研究其规律性,研究它与社会其它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迄今为止,尽管有关文献资源网络的研究文献不胜枚举,但遗憾的是,尚缺乏浓缩度极高的综述性述评。况且现有的文献资源建设概念自身仍有相当的模糊性和局限性,难以与网络在概念精确的前提下进行匹配和组合。因而,不管意识与否,最先产生的学科通常是位于整个物质序列链中间的界面,即藏书,然后再从这个中间界面向两端延伸,于是就分别有了微观的文献信息和宏观的资源网络。这样,除了固有的文献采集、选择、布局、规划、组织、传递和服务外,文献资源网络自身还包括网络协调、评价、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资源共享等。显然,它是涉及各相关因素的一门横断学科,并与其它学科相互作用。尤其是近年来,文献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学、档案学中的各自相关的概念和术语正在开始重新整合。文献资源网络建设研究经过长期的孕育,逐渐成为当今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中重要的学科前沿。在此前提下,笔者对原始文献中的大量数据、资料和主要观点进行归纳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从科学学的角度进行评述。这也许对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们不无裨益。
|1 准科学(Para-Science)
文献资源网络研究的第一阶段是准科学阶段。严格地说,20世纪90年代是比较明显的学科分界线。90年代之前,文献资源网络的学科理论严重滞后于产生这种理论的自觉实践。毫无疑问,属于厚积薄发性质的自觉实践不能不建立在与之相比更为雄厚的自发实践基础之上。它们共同经历了漫长的藏书访求——藏书补充/文献采集——藏书建设——文献资源建设等主要阶段。首先,网络研究建立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文献在科学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文献研究具有客观性、历时性、可用性、选择性和价值性等特点。其次,文献研究的理论与文献资源建设的实践互动后孕育了上述文献资源网络建设的产生。无论古今中外,都是如此。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与网络技术相互结合之前,文献资源建设则是网络科学理论的胚胎。为此,范并思认为,文献资源建设对中国图书馆学还有另一重要意义:如同“量子”概念对于物理学和“氧化”概念对于化学那样,它不仅带来了学科理论的新变化,而且还是中国图书馆学家首次用自己的概念创造新的领域,并且如此科学地包括了这一领域的实践问题[1]。在这一领域,中国站到了世界前沿。据文榕生统计,1872~1987年间,中国共发表有关文献资源方面的论文3030篇[2]。据李钟履在其《图书馆论文索引》的统计,1909年8月至1949年8月,有关文献资源建设研究的论文为173篇。据肖自力等统计,自1949年到1989年,中国发表有关文献资源建设(包括藏书建设)方面的论文总计2243篇(不含消息、报道和台港地区的论文),出版专著、教材共31种[3]。另据吴慰慈统计,1949年10月至1979年7月,有关文献资源建设研究的论文为325篇,出版专著、教材10余种;1979年8月至1988年5月,骤增至1972篇,年均208篇;出版专著、教材等约20种,其中属于综合性、概论性的15种,专论性的5种,剩下的则是论文集和译文集[4]。另据王惠翔统计,1979~1989年间,中国在这方面共发表有关文献资源共享的论文678篇,尤其是1987年之后,内容侧重于文献资源的合理布局,比重约占65.78%[5]。代根兴则认为,这一时期有关宏观性质的文献资源整体化建设论文535篇,在10大相关主题排序中居第二位[6]。尽管上述数字来源不一,但都为文献资源网络建设概念得以形成的背景和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肖自力等认为,伴随着国外先进经验和理论成果的相继引进和国内学术活动的日益频繁,中国在文献资源建设方面的课题研究具体体现在文献资源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及其技术方法的研究,藏书建设的原则,藏书发展的规划,藏书体系的结构,藏书复本和剔除,藏书数量和质量,藏书复审和评价,藏书的保护技术等。当然,文献资源建设的概念自身仍有待于拓展和深化[7]。正是在如此的基础上,构筑网络建设的理论必然显得比较稚嫩,其主题覆盖面较窄,整个体系若明若暗的成份较多。尽管这一时期不乏某些较好的论文,但因泥沙俱下的缘故,总体水平不高,故此呈“失重态”形式,其主要特征如下:
(1)概念的不确切性。所谓的网络建设研究似乎是从经验事实中所分离的思想片断的堆砌。虽然其中的有些思想是客观事实的正确描述,但还有不少是作者主观的推断。因此,不同的作者对文献资源网络建设的观点往往不同,甚至同一作者在不同时期的观点有时也会大相径庭。文献资源网络建设的概念究竟是什么,莫衷一是。
(2)学科结构不甚合理,科研成果难以检验和应用。基础研究形成过高的台阶,应用研究的水平却很低,而且,科研队伍的年龄、专业知识和岗位层次的结构也不够合理,导致科研的总体水平不高。知识商品化的机制尚未形成,严重影响文献资源网络的投入产出效益以及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3)智力常数不高。这里的智力常数是指单位科学成果中所包含的智能大小的量度。文献资源网络的描述有时停留在表面的演示阶段。论文作者的直觉和猜测较多,思辩和验证较少,或者仅是浮光掠影和空泛议论。由此也引起众多从事实际操作的图书馆人员介入研究的过程,并提出一些新观点和新概念,从而进一步为网络研究向中高层次的演化准备了丰富的思想营养。
(4)知识熵较大。上述智力常数低的直接后果则是知识熵的骤增。这里的智力常数与知识熵成反比。在充斥大量知识熵的过程中,经验事实掩盖了科学概念。研究者本人很难以整个社会信息系统作为背景或以共有的文献资源作为参照物,单个图书馆藏书的选择、采集、组织、复审和剔除等微观问题极易在表面上掩盖宏观文献资源网络研究的根本实质。
|2 前科学(Pre-Science)
文献资源网络研究的第二阶段是前科学阶段,时间是1990年至今。那些在准科学阶段后期逐渐稳定的概念,经过多次沉淀和整合后又形成新的知识单元,成为构建新知识体系的基本成份。比如,分别作为知识单元的文献资源建设理论和网络技术等合在一起构筑起文献资源网络的知识体系,其中的文献既是静态物化的信息、情报或知识,又可成为动态激活了的社会资源,而网络则是在文献、信息、情报和知识之间的有形或无形的纽带。在构建这种新的知识体系过程中,一方面文献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学、档案学等的学科界限通常各自有别,另一方面这些学科中各自的概念和术语有时又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集文献信息学说、宏观图书馆学说、知识/情报交流学说、信息资源学说、网络技术学说等林林总总的概念和术语之大成者当然首推文献资源网络的研究。唯有结合微观和宏观的学术问题,文献资源网络研究才能真正从“馆内科学”转化为“馆外科学”。程磊认为,如今随着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我们在先前藏书建设的基础上,还应包括“办公室藏书”、“出版社藏书”、“书店藏书”和“家庭藏书”等[8]。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已成为网络研究坚实基础的知识单元——文献资源建设(包括藏书发展)目前已是全球图书情报界最为活跃的研究课题之一。它在美国的博士论文中居第4位,而在我国的硕士论文中则居11位。我们知道,当一门学科进入教学领域,它已开始成熟并相应地形成完善的理论。毋庸置疑,文献资源建设已成为我国信息管理学的46门必修课之一,无论是学士课程还是硕士或博士课程,都不例外。1995年,中国科学院孟广均研究员招收“文献资源建设与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就是明显的例证。《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也已正式用“文献资源建设”取代先前的“藏书建设”概念,并将其作为新的学科分支。至于另一知识单元的网络技术理论,似乎也可以此类推。尽管如此,由于各个研究者分别从不同的侧面进行观察和研究,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推出多少个持之有故的观念,就能在此基础上相应地形成新的自圆其说的知识体系,在这段时间内似乎谁也不能取代谁。比如,美国学者戴维·斯塔墨认为,不管我们自身的规模如何,也不管大型研究图书馆如何冷漠,且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但所有的图书馆都联系在一个大的网络存取链里。在此前提下,每个图书馆的馆藏及其服务对于整个图书馆界和读者都是至关重要的。这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根据中国的国情,张玉礼指出,中国的藏书建设观念已转变和更新,其表现为:从“重藏轻用”转向“读者第一”;从“藏书为主”转向“藏刊为主”;从“封闭”转向“开放”;从“静态”转向“动态”;从“孤立”转向“协作”;从“单一载体”转向“多元载体”;从“无限增长”转向“零增长”;从“书库”转向“数据库”;从“盲目发展”转向“合理布局”[9]。代根兴则从端倪初露的文献现象中更为深刻地演绎出“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新概念[10]。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属于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有张欣毅的《文献资源建设和调查评估的理论研究》、杨沛超的《试论我国文献资源建设的发展趋势和研究特点》、吴晞、茆意宏的《文献资源建设理论综述》和代根兴的《中国文献资源建设理论展望》等。引文分析、书目核对、用户评议、加权赋值评级、文献复本数学模型、布拉德福离散定律、文献增长规律、文献老化规律和文献半衰期理论等相继成了文献资源网络研究中新的学术生长点,这一时期的总体研究呈“多重态”形式。被公认的文献资源网络理论研究建树者和这一领域的学术权威还没有出现。当然,一旦科学工作者内部都已达到了统一的认识,或者其中仅是两家共处的局面,则“多重态”随之消失,它意味着前科学时期的结束。
|3 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
文献资源网络研究的第三阶段是常规科学阶段。不过,非常遗憾的是,这一阶段尚未到来。位于常规科学阶段的两个知识单元——文献资源建设和网络技术已融合为稳定的知识体系,即文献资源网络研究不仅已成为高智力、低知熵和稳定的知识体系以及进入与之相应的常规教学领域。而且也是一种公认的科学规范和固定的社会建制。这里的科学规范也可称之为理论范式(Paradigm)。它需要哲理性的思考,并进行科学的发现,逻辑推理、观念形态、知识结构、价值系统的研究以及规则、标准和理论的评价等。因而,它致力于有关文献资源网络的起源、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的探究,并且能回答如下一系列问题,如网络的研究对象、研究性质和研究内容等是否完全明确,概念系统是否无懈可击,内在规律是否充分揭示,抽象理论是否能解释现实问题,网络理论的社会认可程度如何,网络的理论体系是否确立并可称之为学科,该学科与其相关学科的关系如何。总之,位于这个领域的知识总和是否已完全达到建树一个学科所需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这种理论范式的主要特点是:A.凭借公认的科学成就,足以把无数忠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使他们避免进行科学上相互的竞争;B.这种科学成就又足以为其他善于思考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C.形成权威的理论体系以及与此相应的一系列规程;D.应用这些规程所需要的各种心理素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科学共同体。至于网络的社会建制则包括固定的拨款制度、理论刊物、科研组织和知识商品化的运行机制等,它是科学规范或理论范式的依托和保证。尽管距此仍有相当长的过程,但与过于放任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宏观调控得当的中国在上述前科学领域的有关理论专著出版以及与之相关的博士专业课程定位等都已表明,如此文献资源网络的理论自身正在为其迅速进入常规科学做好准备。
|4 不同的学术观点
围绕着文献的合理内核逐渐展开和沿着学科自身进展的轨迹,人们对文献资源网络自身建设的认识也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经过无数认识上的自我扬弃之后,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7种观点:
(1)典籍(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论。所谓典籍无非是古代文书、档案、图书的统称。对于这些典籍,古人称之为“文献”,今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和资料。“人们的认识次序是先典籍、后文献。作为文献的早期说法,典籍论似乎早已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难以摆脱的思维定势,尤其是那些古籍专家,更是如此。这种典籍后来成了文献资源网络建设的基础。
(2)存贮(Storage)论。所谓存贮,是从文献积累的角度,人类借助于文献,使信息获得了人脑外的客观存贮。这里的存贮,具体表现为文献实体在空间意义上的物理量、信息量的叠加和时间意义上的延续。在文献存贮量的增长方面,普赖斯(Price)概括为指数定率表达式。在文献存贮密度方面,缩微制品和光盘的一般存贮密度大大高于纸张。在文献保存方面,磁盘记录寿命约3年,磁带和激光盘记录约10~20年,纸、唱片和胶片的寿命似乎更长,缩微片甚至可存贮500年之久。在文献保护方面,人们使用如下的方法:A.收藏非酸性的书籍;B.把馆藏书刊缩微成胶卷和平片;C.用化学方法处理酸性纸;D.使用烟熏法杀灭手稿本的飞蛾、蛀虫以及把电影胶卷储藏在冷藏箱内。E.书库环境的改善等。显然,存贮始终是文献资源网络建设的主要前提。
(3)利用(Usage)论。所谓利用,是从社会功利的角度,对于文献服务的新认识。我们知道,文献一旦得以形成并获得有效的开发和利用后,就不仅能为全人类所共享,而且也能成为用之不竭的财富。何善祥认为,凡是古今中外有成就的科学家,都在充分利用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研究[11]。为此,用户第一成了文献机构服务的宗旨。藏书储存的数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藏书利用的程度。欧美国家都力求100%地满足其用户的文献需求,藏书利用率高达400%以上。藏书利用与文献检索密切相关,比如,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120个远程终端,可检索国外文献约3亿篇,国内文献约300万篇。尽管文献的充分利用是件好事,但使用过于频繁也会损害书籍,反而影响了读者的进一步使用。此外,还有人对先前“炒得过热”的馆际互借持有异议,认为馆际互借任务的加重会导致馆内工作量的骤增、成本费用的上升和服务水平的降低等。在文献资源的网络建设中,这一切应引起我们的深思。
(4)资源(Resource)论。所谓资源,是从社会供需的角度,对人们赋于文献自身价值的思考。文献资源是指可用作参考或依据的一切文献信息。它不仅为人们提供其所必需的知识、经验和技能,而且使之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在这个前提下,肖自力等学者根据人类开发和利用文献资源的方式和方法,这样来进行历史时期的划分:A.社会成员个人收藏利用时期;B.社会专门机构分散收藏利用时期;C.文献资源整体保障时期[12]。杨挺认为,文献资源是种智力资源[13]。程磊也把办公室藏书、书店藏书和家庭藏书等都列入文献资源网络建设的范围。许多中国学者主张“资源论”。基于这种认识,人们对当前文献布局的不合理状况难免忧心忡忡,如文献富集和文献贫乏并存、资源配置不甚合理等。此外,名义上称之为文献信息资源中心的图书馆实际上仅拥有相当有限的信息资源。图书馆既不可能代替读者收集和加工所有的信息,也不可能参与读者利用信息资源的全过程。所有这些都表明,文献资源愈来愈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
(5)载体(Medium)论。所谓载体,是信息(包括知识)赖以存在的物质外壳,它也可狭义地专指文献载体,即记录信息的一切人工附属物。周文骏认为,文献是指以文字、图像、符号、声频、视频为主要手段的一切载体[14]。彭斐章认为,文献是指人们为了存贮和传递的目的而记录的社会情报的一切载体[15]。波兰的A·鲍梅卡尔斯基认为,文献是科学情报的物质载体。沈继武认为,文献泛指各种物质材料的知识载体[16]。张欣毅则认为,载体代表文献的“物”的方面,它为跨时空的文化信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往今来,文献载体可为龟甲、兽骨、玉石、泥版、纸草、金属材料、简帛、蜡板、羊皮、纸张、磁性材料和光电材料等。目前,这些载体中的大部分都似乎完成了其自身的历史使命,唯有纸张、磁性材料和光电材料一直在使用着[17]。虽然如此,它们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然而,不管怎样,载体自身体现了文献资源网络建设的轨迹。它不仅已为从事图书情报专业的人员所认可,而且也为更多的社会人士所接受。
(6)符号(Symbol)论。所谓符号,是指任何具有传统解释或主观解释的标记。人类文化是借助于符号才得以形成的。本世纪以来,人们开始赋予文献符号的新意义。情报学家贝尔金和罗伯逊认为,文献是信息工作者按一定的结构形式有意地汇集在一起的符号。戴彭斯也认为,文献是符号的物理载体。基于这种认识,记录符号是文献得以构成的基本要素之一。符号对于提高情报检索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它转换了新的角度,从而使人们对于文献资源网络建设的认识上了一个台阶。
(7)比较(Comparation)论。所谓比较,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的文献资源及其网络建设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比较,了解和掌握它们的共同点和差异点,并对其中差异点作出科学的解释。钟守真在比较图书馆学的领域颇有建树。仅就研究热点而论,据邱均平的统计,美国为A.图书情报管理;B.情报检索;C.数据库;中国则为A.情报科学;B.分类编目;C.图书情报事业[18]。此外,还有从其它方面进行比较。如窦平安从一般特性、成本、出版条件、市场和产业界和互补方式这几方面对CD—Rom、联机和缩微三者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无论采用何种情报技术,其最终决定者是情报用户,而不是情报提供者的结论[19]。这些比较丰富了文献资源网络建设的内容。
总之,上述各种观点虽然表面上各自不同,但其实质上却互有联系。我们若对这些观点进一步地分析和比较,则会发现符号论和载体论互为表里,典籍论和资源论辅车相依,存贮论和利用论相反相成等,由此还验证了文献资源网络的学科建设在完成从准科学向前科学过渡的基础上充分体现其应有的社会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