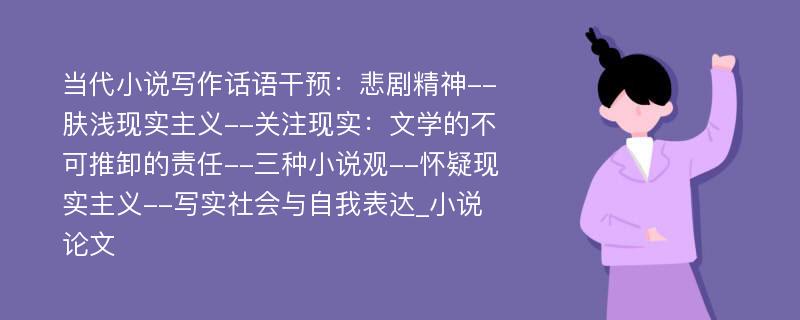
近期小说笔谈——介入当下:悲剧精神的阐扬——肤浅的现实主义——关注现实:文学义不容辞的责任——小说三看——可疑的现实主义——书写社会与表现自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笔谈论文,小说论文,义不容辞论文,可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十年代以降,小说发展呈两极形式:一是在反抗现实、反抗世俗的先锋轨道上滑行;一是在贴近媚俗的商业化炒作运动中悄悄解构了纯文学的意义。无疑,这些当下状态的小说创作给文学史上意义的小说打上了一个重重的问号。
近年来,由刘醒龙、何申、谈歌、关仁山、刘玉堂、刘庆邦、赵德发、王祥夫、谢志斌、张继、柳建伟、黄建国……等一大批关注基层生活,尤其是农村基层生活的作品以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姿态介入了当下社会的本相,深入到各色人等的生存本相之中,去寻觅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本质特征。有人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回归,有人却不以为然。我以为,从整个小说走向来看,这种对“新写实”和“今日先锋”的反动,是有其进步性的;但是,在这个运动的惯性中,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它所存在着的致命弊端。
我从来不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真正有过现实主义,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五四”时期,现实主义刚刚生根,就被引入了歧途,更不要说以后在各式各样的政治化的文艺运动中,它每露端倪就被扼杀。因此,现实主义,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在中国似乎永远是短命的,它根本就无家园,又何谈“回归”呢?如果须得真正倡扬一回现实主义精神(绝不再是那种假冒伪劣的“伪现实主义”),那么就得正儿八经地从创作实践到创作理论都来一回大检视,从中勾现出时代、社会、人三者之间的本相。
无疑,这一大批“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家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参差不齐地为这个时代、社会和人物画出了动人的映像和肖像,他们那种热诚的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关怀,为小说再次吁请“人的确定”和“打捞理性”作出了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刘醒龙们所作出的努力是代表着一个时代和整个社会进行对话。然而,我们亦不可不看到,在这一大批“现实主义”作家之中,更多的人尚未进入“有意后注意”的写作层面,也就是说,他们在有意为之的理念上尚缺乏批判现实主义的主体意识。因而,有人认为这些作家之中多数人的作品只是回归到“乔厂长”式的“现实主义”旗帜之下(如谈歌的“大厂”系列等),这也并不足怪。除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这个命题已在中国讨论了近一个世纪)外,为什么这些小说不能在人道主义和人性的人文旗帜下,使之更有人性的深度;使之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使之成为这个时代创作和精神的标高呢?!我以为,最最致命的弱点就是这批“现实主义”作家的主体意识中缺少批判现实主义的魂魄:悲剧精神!
我这里所说的“悲剧精神”并不啻是美学层面的,应该从更大的哲学层面加以现解。从诸多的作家作品来看,作者介入当下时,只把眼光停滞在对社会的本相和人的生存本相上,而未从更广阔的视界中将这种时代、社会和人的本相从形而下的描写中提升到形而上的哲学层面。也就是说,作家在描写中,还未超越“新写实”的写作框架,在中性的价值判断中徘徊,而放弃了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悲剧精神主体的介入,当然,这种介入并不是“十七年文学”中的那种虚伪的英雄情结的介入,而是老巴尔扎克、老托尔斯泰,甚至是雨果、左拉式的悲剧精神的自然植入。综观这批创作,包括刘醒龙在内,他们在描写现实的力度上已达到了“仿真”地步,亦给人以某种生活的启迪,但就其在发掘深度模式的人方面,在美学的悲剧力量的震撼上,却难以进入大家风范。
可以看出,这批作家除了少数是年轻者外,有许多是经历过“文革”的中年作家,他们并不缺乏生活,亦不缺乏对于时代社会的历史性思考,但为什么独独缺乏悲剧性的思考呢?是这个眼花缭乱的商品化时代耀眼的光晕遮蔽了作家透视的目力?抑或是害怕“三突出”的魔影纠缠?
当然,这些作品中亦不缺乏具有悲剧意识的力作,但这毕竟是极少的。如《山西文学》这几期组织的“中国乡村小说特辑”中有李秀峰的一篇《一夜村长》,在反讽的梦幻之中凸现出了作家强烈的悲剧意识,它不但是美学的,更多的还是对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本质性批判。为什么它不能成为我们作家的普遍认同呢?
在呼唤批判现实主义的同时,可千万不要忘记对它的灵魂家园——悲剧精神——的关注。
谈到现实主义,人们总要强调与时代、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但如果仅仅只说到这里,那还等于什么也没有说。现实是多层次的,文学应该把目光投射到哪种层次上?同时,人们可以站在种种不同的立场上关注现实,而作家应该把立足点放在哪里?——这些,是更应该追问的。并非所有以现实生活为描写对像的作品都堪称现实主义的作品,更并非所有以现实生活为描写对像的作品,都堪称优秀之作。在所谓的现实主义“再掀冲击波”时,应该避免这种倾向,即简单地以是否关注了现实为标准来衡量作品。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已不再对作家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评判了,而习惯于依据某种标签对一批作家作品进行整体性的褒贬,所有被认为能够戴上同一顶帽子的作家,便都是好的或不好的。最近,在谈到所谓现实主义回归时,也显示出这种倾向。仅仅只在某种层面上关注了现实,是一件容易不过的事,而现实主义,却意味着比这多得多的东西。
这一两年涌现出的那些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回归的小说,例如何申、谈歌、关仁山、刘醒龙等人的作品,不少都是以当代乡镇生活为审美对像的,主人公是乡镇长一类人物。这是这类作品引起喝彩的一种原因。当代乡镇,是充满活力的地方,作为城市与乡村的结合部,它不城不乡而又亦城亦乡。而乡镇干部这类人,则是官与民的混合体,往往不官不民却又亦官亦民。这样,便使得乡镇这种空间和乡镇干部这类人物,都很富有文学意味。同时,此类题材又少有人触及。于是,这两年触及了这类题材的作品,便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但题材领域的开拓,人物形像的新颖,对于小说来说,并非多么了不得的事情。写了什么,并不特别重要;写得如何,才是最关键的。既然这些作品被称为现实主义的,那么,就不仅要看它们写了些什么,更要看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具备了现实主义的品格。在谈到现实主义时,我常想到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夫子自道。他认为,许多人的现实主义都是肤浅的,而自己的现实主义则是纯粹的、深刻的,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因为“我描写一切人类灵魂的底蕴”。当然不必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作现实主义的唯一典范,但我以为尽可能深刻丰富地揭示出人类灵魂的底蕴,却是文学作品,尤其是现实主义作品所应该追求的。仅仅在一般意义上强调现实主义作品是关注现实的,还远远不够,还应该进一步说,现实主义作品关注的是现实中的人,是人的处境、人的灵魂。因此,是否关注了人的灵魂,以及把人的灵魂的底蕴揭示到怎样的程度,便是衡量现实主义作品肤浅还是深刻、拙劣还是优秀的一种标准。以这种标准来衡量这一两年出现的被称作现实主义的作品,应该说,总体上的成就还并不足以让人欢呼雀跃。关注现实时,把目光停留在社会学的层面,浓墨重彩地写各种各样的事件,而人物却淹没在事件之中,仍然是不少作品的通病。这方面,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和谈歌的《大厂》便具有代表性。《分享艰难》的主人公是一位镇党委书记,《大厂》的主人公是一位厂长。两篇小说都着力表现这书记和厂长当得怎样艰难,而难也就难在缺钱,到处都需要钱,拆了东墙补西墙,仍是照应不过来,至于人们心灵的冲突,灵魂的痛梦,却触及得并不够。这样,小说便仍然只能算是一种肤浅的现实主义。尤其对《分享艰难》这篇小说的题目,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究竟谁为谁分享艰难,弄不明白。
也许是受着这个时代精神气候的影响,也许是觉得钱的问题比什么都重要,我还注意到,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作品,不少都对道德评判、道义立场采取回避的姿态。对作品中人物的玩弄权术、跑官要官、贪污受贿等行为,作者并不表示出愤怒和谴责,倒是无奈、宽容和认可。这种倾向,在写到那类“能人”,那类所谓“农民企业家”时,表现得尤其明显。这类人往往无恶不作,但却对当地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一倒,便会导致当地经济崩溃,这样,即使他们恶贯满盈,也仍能受到种种保护,从而逍遥法外。面对这种现像,作家们常常缺乏最起码的道德义愤,甚至连一点困惑都不流露出来。在这些作品里,伦理已彻底被历史击溃,已不再与历史有对垒之力。一种肤浅的历史进步论在消蚀着作家的道德情怀、道义立场。
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不少作品,在看取现实时,仍有很大顾忌。对现实中的丑恶、污秽,揭示得是有节制和有分寸的,另一方面,还要有意无意地给现实涂抹上一层亮色。有的作品,则表现出一种廉价的乐观。这样,便仍难逃“瞒和骗”之嫌。
还有必要特意指出的是,不能一说现实主义,就回到那种浅白直露、老妪能解的阶段。把现实主义与通俗易懂划等号,认为现实主义就意味着“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这不仅是对现实主义的曲解,更是对现实主义的侮辱。而这种现像,在这一两年的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中,也是能让人感觉到的。
应该说,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大多数作品,充其量也还只是一种肤浅的现实主义。
文学要关注现实,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当我们赞扬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德莱塞的伟大与不朽时,不就是首先因为他们出色地担当了那个时代的“书记官”、并在其作品中深刻地反映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现实吗?这里要澄清的问题之一是,全面理解与正确看待文学关注现实和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两者有区别,却又有一定的联系。新时期伊始,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致词,明确地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广大文艺家为邓小平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指示发出欢呼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从根本上解除了政治对文艺的长期而严格的禁锢。根据这些指示,文艺可以不再像过去那样把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当成唯一的、唯此为大的任务。但是,这并不是说文艺从此可以完全与政治脱尽干系。在同一篇祝词中,邓小平也是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像,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毫无疑问,文学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就必须密切关注现实,把反映现实生活当成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决不是靠写清官秘史、影星轶闻、红尘少女、原始蛮荒等所能完成的。当文学真正关注现实时,也就自然地与政治发生了联系。我国当前的现实是,亿万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同心同德,建设四化,振兴中华,这是现实,也是最大的政治,文学不应漠视这个现实,这个政治。只要我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就该承认,这些年来,文学逐渐失去往日的荣耀,更别说轰动的效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不是人民群众不需要文学,而确实是文学远离了现实,远离了群众。文学不关心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生活,却又要求人民群众视文学为不可缺少的生活的一部分,难矣哉。
与文学关注现实这个话题密切相连的,还有一个正确看待现实主义的问题。近几年,现实主义在一些同志眼中几乎已经完全变成陈旧、落后的代名词,其实,即使在先锋派似乎一统文坛的时候,现实主义也并没有销声匿迹。这不仅因为现实主义在发挥自身固有优势的同时,也在努力改造自己、充实自己和丰富自己,以求适应时代,适应人民,也因为文坛在经历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实验之后,发现这些实验并没有获得想像中的成功。倒是《分享艰难》、《大厂》、《年前年后》等一批高举现实主义大旗的作品出现之后,人们却有一种久别重逢的喜悦。说实在的,我本人欢迎这些作品,但并不把这些作品就说成是现实主义的精品,也不简单地认为,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回归。对这些作品,我最为着重的,是它们关注现实的热情和努力丰富与发展现实主义的探索精神。在这些作品中,洋溢着现实生活的芳香,表现了作者直面现实、正视现实和敢于将当今现实中的矛盾不加粉饰地“记录”下来的勇气,这些作品还努力塑造我们这个变革时代的新人形像。因此,我愿将这些作品看成是一个可喜的信号。照我想,现实主义在总结了以往教训(简单化,拔高,粉饰现实,图解政治、政策等等)之后,同时,将现代派甚至后现代派的一些方法与技巧吸收、消化、改进后为我所用,那么,这样的现实主义,就不仅会以一种全新的面目出现,而且可能比其它文学流派、创作方法更适合也能更出色地承担起文学关注现实、反映现实的任务。
总之,我以为,即使作为一项探索,坚持与发扬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提倡关注现实,表现现实,也是文学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小说在文学公众的文学生活中已领衔有日,即便如今大众艺术消费已看好一位新贵“电视剧”,可其佼好者亦多出自小说门庭。其实不妨说,打从小说被指为“街谈巷说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就已经在小觑它的同时昭示了它拥有大众的趋势。
不介意读者的小说家恐怕历来很少,然而像拉美现代文学运动先驱人物鲁尔弗宣称的那样,把读者放到“合作者”位置上的,大概也算不得太多,只是拒绝“合作”的作者不一定十分自觉。我要说的“三看”似皆可入于此列。
“三看”亦即“三不……看”——我是说“不堪看”的自可不看,“不必看”的亦不妨不看,至于“不容看”的,看也枉然——就是受动于作者自觉不自觉的拒绝,并非自己前阅读的约法。
“不堪看”的其实也是毋须说的,作者带着很为纯粹的商业目的写给书摊摊主时,自然也着眼于某种“可读性”,然而那“可读性”带来的销路的可观性常常不足以改变我(们?)关于不堪看的立论,至少有些倒胃的趣味、败兴的妩媚、虚假的胸毛、莫名的怪力“游走”在朽拙的套套之中,绰绰有余地构成这一立论的支撑。
以为“不必看”的一类要复杂一点,既包括通常称做平庸的一类,更包括很不“一般”的一类——我指的是“私人性”、“个人性”强到臻于“纯粹”的一类。小说的个人性作为内倾性作者的一种执着原是无可厚非的,而且,由于“现实主义”的歧途呈现过它的极端,文学蒙受过大时代及其政治文化背景的大一统的制控,个体性在“公共性”、“集团性”的绑架劫持中遭遇过失落和泯灭,乃至“永远的认同”至今仍遗风流韵于我们的民族特性。如此,个人性的强调就不只在“返正”、“归宗”的意义上张扬文学的本体和特质,也足以在“出新”的意义上收获“刮目相看”。
问题只是发生在极端,发生在纯个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存在可能,亦即仅仅发生于个体性在指向“生命特点”的同时,是否也无可规避地包涵了它的“文化特点”?与其说这是把问题引向古老,不如说是让问题面对生命本身的坚硬现实。纯生命的个人性大概就存在于细嚼慢咽地抑或狼吞虎咽地“食”着的人,还得排除那个“卖大饼的”,到了“色”着的人,如果不是意淫不是性无能者,就会涉及到两个人,同性恋、异性亦皆然,而且这里也明显地动用了排除法,比如说排除了事实上并不鲜见的三角或多边。至于个人的思想驰驱和精神独语,不说其赖以对话的潜对像和实施扬、弃的思想材料上早已集结过许多“非个人”,旁边还潜隐着一个非个人创造出来的上帝,凑热闹似地搅合过来窃窃“发笑”。
一方面纯个人几近莫须有,一方面不纯的个人就并不很个人,生命意义上的个人性的表现难度就显得太大。若把个人性说成就是个性、独特性、“伊特性”等等,又分明怠慢了个人性一说的纯粹意味和新鲜程度。我不是挑剔一种名目,一种名目化的宣言,我是觉得我们恰恰在实际上有种决绝地、毫不通融地致力个人化、私人化的操作。这就不能不有些勉为其难,有些勉为其难而带来的左支右绌。这结果能够看到的就多了些乐此不疲的自我抚摸、多了些“癌变般的花哨词汇组织的增长”(纳博科夫语)”面对这类读品,私下冷不丁生出“不必读”一类的个人念头,不一定缘自“个人”跟“个人”之间的隔膜,“不必读”的念头,恕我明言,主要还缘自它与自己“不相干”这种个人情绪。你在你的房间里如何手淫如何跑马,你在你的镜子面前如何自恋如何自怜,你自个儿如何本能冲动如何自我沉浸,如何恋异性好同性如何男性说女性论,悉听尊便的事,跟我何相干涉?接受启蒙么?重温人之初么?投入圣战么?陪哥儿姐儿们自戕抑或自娱么?
列出“不容看”亦即“不让看”的一类,说起来也是应该有些惭愧的。人家未见得存心不让看,实乃自己看不懂,又不愿接受福克纳对他的读者忠告的那样,两三遍之后还是不懂就“读四遍”。只是想到鲁迅先生当年说过有些文章就是看不懂这样的话,又得着点安慰和逃路。
这中间排除自己智识无法企及的那类“最高分”,再排除作家自己也给自己搞浑得跟我一样不能懂的“最低分”,剩下的就有思考的余地。比如你是否可沿着媚俗性的一端看向另一端去,发现一种同样很为时兴很为执着的“高雅欲”或谓“高雅迷”?作者心存高雅是应该的事,尤其是当文艺泛滥了低俗、庸俗、恶俗。问题恐怕还是要回到“度”上,仅仅成为出示高雅的欲望且至于入迷,大概也就剩了做工,成了症候。
显在的例子就有小说热衷文学之外的觊觎和高蹈,常见有把哲学讲章奉为蓝本,把历史解释当做基础来构筑小说的嗜好。无奈哲学、史学那里自有甲乙丙丁,生活的真相在那里非独穷尽不了而且纷纭得很,真真伪伪虚虚实实盲流似地涌向小说,就有些其一其二的兼顾不得或兼收并蓄的缠杂不清。文坛上除了屈指可数的二、三子,通常是越把“小说”写成“大说”、越把小说写得很哲学、很人类了,就越是让读者在演绎的肆虐、阐释的艰涩中走出耐受力的限度,愣怔怔去感受拒人千里之外的“不容读”。况且,这现象本身也正昭示文学对于自体的越位和远逝。“每当文学才能减退时,哲学家们就占了上风了”。莫里亚克的这句话实在是很为逼真的。
以上便是包涵了个人好恶和偏见在内的“三看”。时下似乎又昭示着从“不耐看”的方位生出“四”来的可能性。我指的自然是一批直面现实而多流于“现像罗列”的作品的出现。这类作品的成败,包括其堆砌材料的恣意和总体思考的匮乏,包括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不达“标”和不到“位”,或者还可以包括其爆冷门似的得到读者和评家垂青的现像本身,都很可以启示我们对于小说生态和前景的多重反省,鉴于其属性跟上述“三看”不好并列,也鉴于其初露端倪、尚未构成新质和潮流,还是容当别议,而待以时日。
《钟山》拟搞一个有关目下小说现实主义回归的笔谈,我感到很茫然。主事者说知一些作品与我,主要是北方一位作家有关工厂生活的两三个中篇,便找来读了。但很抱歉,从中我并没有感到现实主义回了归,甚至对什么是现实主义倒有了可疑。
不错,这几篇小说是力图去反映工厂的改革生活。这是现实,但未必构成主义。不能说触及了现实就都是现实主义,否则这个世界上便没有不是现实主义的小说,因此这个概念的要义可能更在于作者所奉持的“主义”是什么。那几个反映工厂的中篇奉持的是什么主义呢?据我看至少是“煽情主义”,而且这种煽情又搞得很做作。你看,那些厂长们动不动就被包围起来,甚至有人对他动了拳脚,血任意往下流,他却一动不动,说些掏心掏肺的话,于是工人感动了、沉默了。凡是这类场景,俱是作者浓墨重彩之处。他似乎刻意要把那些厂头们塑造成“无奈的救主”和“受难的基督”。然而每每看到这里我却有说不出的别扭,因为它和现实的反差太大了,而读者也不再那么幼稚了。
但没想到的是,读者不幼稚,有些编辑和评论家却“幼稚”了起来,他们为那些场面所感动,便把这样的作品说成现实主义回归了,甚至给这种文学定了位,叫作“分享艰难”的文学。天呐,分享艰难?谁和谁分享艰难?作品糊弄了我们一次,莫非评论还要跟着再糊弄一次?写到这里,正好想起《钟山》那天晚上的招待,席上一位朋友说京都名气挺大的某作家,也是在宴席上,一边拣起一只大虾子,一边感叹地说:唉,不知农民能不能吃得上。莫非这就是分享艰难,然而又是多么伪善。那小说,作为一个搞评论的,难道真看不出里面的伪善乃至伪现实吗?
对小说,我实在不想多说什么,毕竟也还有些可取之处,而且作者他要怎么写也是他的自由。问题是评论,而“现实主义回归”正是一些编辑和评论的嚷嚷,《钟山》找我们来谈,是否想回应这股潮,倒也难说,发有关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我完全赞成,但刊物对这种口号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概念,要做仔细的审辨。刚才说过“分享艰难”,现在再不妨看一看与它相关的“社群文学”。社群明明是一个分离性的概念,可是作者却偏偏把它搞成一个“向心”之类的概念,所谓同心协力、达成共识、增加凝聚、分享艰难,大抵不出这些表意范围,它们在现实主义这个大概念的笼罩下,几乎达成了京海共识(当然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对此我个人表示无法赞同。我倒是赞同《上海文学》搞得有声有色的“新市民文学”。新市民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新近形成的“社群”,它的出现无疑对打破我们长期固存的政治经济文化一元化的格局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由此也可以见出“社群”概念本存的分离和趋异的属性。但一会儿张扬新市民,一会儿又呼唤那种分享艰难式的社群现实主义,却没想到在理论上他们并不兼容。看来口号频繁并不是好事,殊不知,这个口号与那个口号之间很可能是吊诡的。当然保持一致的也有。比如,置中国严重的前现代状况而不顾却大力张扬后现代的理论,然后又推出文化民族主义性质的“中华性”主张,再到现如今对分享艰难的社群文学的推崇,我们隐然已经看见从边缘向中心、从两侧向体制努力的话语倾向,在我看来,这倒是一种很切实的现实主义的文本策略。
我一直认为,所谓现实主义,乃是一个现实、多种主义。而目下我最欣赏也认为最需要的则是十九世纪形成巨大流派的那种“批判现实主义”。这种批判的现实主义我已经感到久违了,作家们不知干什么去了。不过我刚刚读到这样一篇很好的作品,那就是《上海文学》第10期上阙迪伟的中篇《新闻》,它被编在“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栏目内才是真正合适的,若是在这样一个立场上谈现实主义我举双手赞同。看看作品所揭示的内容,再体会一下作品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冷峻的批判精神(这和那种动不动就掏钱捐款的煽情描写正成对比)。因此,我认为《钟山》如有意为现实主义推波助澜,那么是否可以考虑一下像阙迪伟这样的作者、像《新闻》这样的作品呢?
最后,我还要重复上次我说过的话。今天,谁要撇开批判意识和精神却侈谈什么现实主义,打死我,我也不信。
每当社会转型期间,随着社会的改革与社会思潮的急剧变动,在文学的潮头上便往往会翻涌出新的景观。而每当文学新景观出现之际,紧跟着便有一些敏感的批评家和文学编辑撰文力图对之作出自己的描述、阐释、概括,甚至竞相给予新的命名。这恐怕也是文学新景观的组成部分,甚或也可说是另一种文学景观吧。
近两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和改革的深入。在文学创作界,当一些新生代作家呈现勃勃生机的同时,又出现了以刘醒龙、何申、谈歌、关仁山、刘玉堂等为代表的引人注目的文学新走向,他们的新作和近作又给了当前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某些新的活力,添增了某些新的内容。
显然,这种新的文学潮头,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些批评家的关注视线,并已给以新的命名。有人称之为“社群文学”,有人则称之为“现实主义新的冲击波”。
虽然,我们无需急于给这种新的文学现像立即就冠以“新××”的命名,但阅读了这些作家的部分近作之后,我们确实可以从其与前期文学思潮的简单对比中,发现一些明显的异同之点。
就作者与现实关系来说,我以为,给人印像较深的是,这些作者的近期作品大都体现了一种可贵的社会关怀精神和公众意识。一方面,这些作品对转型期间人们因经济利益关系而引起的种种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作了真实描述,另一方面,这些作品也表现了无论是干群之间,还是群众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分享艰难”式的气概(几篇作品都不约而同地这样写,又不免显得雷同)。应当说,这是作者对社会转型期间,社会状态、公众心理的一种新的发现与把握,也是新形势下对关注现实的文学传统的继续与发展。
显然,以刘醒龙为代表的这些作家的作品所表示的乃是一种社会写作和社会关怀的倾向。它与新生代作家注重个人写作表现自我的创作倾向有着鲜明的区别。在陈梁、徐坤、韩东、朱文、鲁羊等人的笔下的当代生活,其出发点和归结点几乎都是自我的生命形态以及作家个人的内心体验,写作带有鲜明的个人性与私人性,而在刘醒龙等人的作品中的当代生活则明显地充溢着群体的社会意识。一个偏重于个体与内心,一个侧重于社会与群体。前者表现了“对主流、世俗社会的自觉拒绝”(陈思和),后者则体现了作者对当下社会状态的某种认同与关怀。
文学的两极就这样鲜明地存在着、对峙着。
可以说,这些作品正是作者对社会转型期间的社会矛盾、生活状态的发现与把握的一种方式。而如果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则又可从以前的文学思潮与表现方式上找到一些渊源关系。
譬如与新时期初期的改革文学和社会问题相比,这种社会关怀小说自与之有着某种相似之外(如对现实的关注,对社会状态的关怀)——这种相似多少也表明了两者的承续关系——但这两者所呈现的不同之处也说明前者并不是后者的简单重复。
首先是切入点的不同:现阶段的社会关怀小说已由前阶段的政治切入转为经济切入,艺术上也摆脱了早期作品中改革与反改革的情节模式(几乎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一些新的情节模式)。
其次是,现阶段的社会关怀小说已减退了前期小说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而代之以生存艰难的具体描述。
譬如,与90年代初期的新写实主义小说相比,二者虽然在选材和开掘上有某种不同(新写实小说大都取材于普通人的生活琐事,社会关怀小说则落笔在社会群体与公共关系上),但二者在表现方法上也未尝没有相同之处:在对现实生活作原生形态的描写中,表现出社会转型期间社会生活的无奈与艰难。
从这个意义上,是否可以说,当前的社会关怀小说的文学新景观正是社会问题小说、改革文学与新写实文学的交汇与发展呢?
当然,眼下要想对这种文学新景观作出准确的描述、精当的评价,显然还为时过早(但作为一个文学编辑和文学评论工作者,给予及时的关注与重视,却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即使从目前的创作现状来看,这些作品在批判力量、思想深度与艺术创新等方面的不足,也表明着这种创作流向仍需要一个逐步完善、提高的过程。
也许,书写社会与表现自我正是当今文学创作的两个基本潮流与走向,它们也各自有着自己的上品、中品与下品。作为文学期刊的编辑和评论工作者,我们理当促进更多的上品、精品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