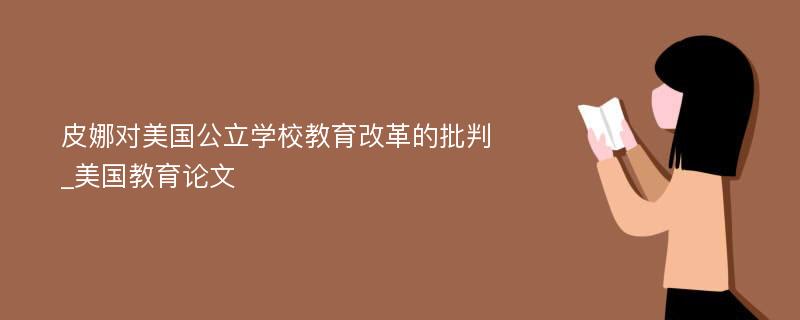
派纳对美国公立学校教育改革的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改革论文,美国论文,批评论文,学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来,我国教育理论界对美国的教育改革引介很多,特别是对2001年小布什政府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草案到2002年布什总统签署它成为法案所引致的改革更吸引了很多学者的注意,甚至有多篇硕博士论文也以此为主题。但这些介绍多以正面为主,忽视对美国国内反对之声音的注意。这样容易造成美国政府的改革较为成功的印象,甚至也许会成为以美国正在加强州一级统考等措施为例来论证我国各类统考之正确性。其实在美国国内,从一开始就有学者对这些改革的商业操作和政治转嫁性质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派纳就是其中一位。(注:威廉·F.·派纳(William F.Pinar)是当代美国最富有影响力的课程理论家之一。他是20世纪70年代“概念重建”主义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致力于从自传、种族和性别的角度理解课程,曾经到我国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做过多场演讲。)
一、当今美国的教育改革是“对公众进行错误的教育”[1]
《决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中规定了阅读改革、早期教育改革、教师质量行动、评价体系改革等。其中评价体系的改革最为牵动人心,引起的争议也最大。例如,法案规定:从2005—06学年度开始,全国3—8年级所有学生每年必须接受各州政府的数学和阅读统考,各州可以自行选择和设计统考试题,但其试题必须与该州的学术标准相符合;各州必须至少进行一次10—12年级学生的阅读和数学统考;2007—08学年度,在每个年级段3—5,6—9,10—12,各州必须测试其中一个年级的科学;测试必须包括残疾的学生和英语欠流利的学生;各州必须参加每两年一次的4年级和8年级的国家教育成就评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中对阅读和数学的评估;各州必须向公众提供考试成绩报告;向学生提供个人成绩报告;公布每个学校和学区基于性别、种族和少数民族、英语熟练程度、残疾、收入的测试结果,等等。[2]
颁布法案的初衷之一是美国的中小学据认为不太重视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和考核,以至于美国中小学生在国际性的基础知识竞赛中从没拿过名次。所以美国在这次教育改革中,决心提高其中小学生,甚至是学前儿童的学术水平。实行州统一考试是为了把联邦政府的资助与各个学校的教育质量联系起来,以期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学生的学术质量。
在这些改革者冠冕堂皇的修辞背后,派纳认为当今美国的公立教育是在对其公民进行错误的教育,正在进行的改革是“商业思维”式的改革,其中充满了商业词汇,如“底线”、“效益”等,它强调标准化考试中的成绩。它通过提高等级制的控制加强了那些破坏教和学的力量,因为教师和学生会通过限制他们自己的工作来反抗这些控制。美国教育的目标远离了教育的应然状态,成为怎样吸引年轻人学习学术科目的问题。学校即使偶尔也教授大众文化,但那也是为了能使学生产生学习兴趣,而不是为了通过课程使学生把自己当下活生生的经验和学术知识相联系,以培养学生的理智发展和批判思维能力。在派纳看来,学校课程的宗旨不是培养能在测验中取得高分的人,从而使美国的学生在标准化测试中获得比日本或德国学生更高的分数,而是必须吸引并拓展学生理智的、心理的、社会的兴趣,促使学生关切自己与他人,帮助学生成为在公共领域致力于建设民主社会的公民,在私人领域对他人负责任的个体,运用智力、敏感与勇气去思考和行动。[3] 公立教育,就是自我和社会的政治的、心理—社会的、基本理智的重构。[4] 教学的过程是使学生利用学术知识在社会和世界中理解他们自己的自我形成的过程。[5]
派纳认为尽管从19世纪末期开始美国就强调在普通学校里培养美德,但其实从总体上说来,学校谆谆教导的并非美德,而是中产阶级崇拜、竞争、工具性、欧洲中心的单一文化主义。[6] 过去,公立学校仿照的是工厂模式,学校课程以单元为单位进行设计和讲授。这样做,赢得的是社会控制,失去的是诸如问题解决、批判思维、和创造性等类型的智力。这种标准化的教育降低了学校所教和所学的东西的质量和数量。出类拔萃的往往是那些能忍受重复教学和记忆背诵的学生。在这种教育中,学校的所教和所学缺乏迁移性一直是一个为人所诟病的问题。后来学校演化为“公司模式”,其目标是学习基础知识。这个模式允许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使用多种策略,如小组和同伴教学、小队教学等,甚至允许学生和教师为了达到学习目标而对课程做细微的改变。这个模式宣称智力是多元的。教师被比喻为“教练”,其权威已经比工厂模式中的“工头”少了很多。
但问题的关键是即使在相当灵活的公司模式中,教育的目标,即培养在后工业社会中所必须的知识和技能,却没有被置疑。这种模式的认知方式是工具性的推论、计算和问题解决等。智力仍然被认为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是技能的掌握,是工作中能促进合作的知识和态度。这种智力观对当前的经济组织形式很有用,但是对探究人类经验的更基本性的问题却没有多大用处。派纳认为智力的自由应该包括认知的沉思冥想形式,应该允许探索那些没有立即的实际盈利、可能不被标准化考试所评价的学科。这些学科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研究。[7]
不管是工厂模式还是公司模式,制度化的教育实践是依赖惩罚生存的。派纳认为学校教育的意义不是要求学生在成年以前进行自我放弃,也不是延迟满足,不是变得更加负责任,不是被迫把自己置于优雅的服从的位置。教育的意义是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公民,学习与她/他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欢乐有关的学科,这些问题和欢乐也与这个国家、这个地球上另外每一个人的问题和欢乐有关。教育的意义还意味着把学术知识归还给个体自己,在教授知识的同时要联想到这些知识对学生个体自我形成的可能后果。教育应该是我们修正自己的最大希望,要为整个社会提出学术知识的意义。
派纳还批评了把学校作为医治社会疾病的良药的企图。他说今天还有太多的美国人仍然相信好学校能根除犯罪、消除贫困、培养忠诚的公民。派纳引用拉希(Lasch)的话说“自从赫拉斯·曼掌管马萨诸塞州的学校以来的150年间,如果有一个我们可能应该学习的教训,那就是学校并不能拯救社会。”[8] 派纳认为美国过去30年中教育改革的错误是把改革定位在如何使当前的教育系统起作用上。政治家们认为唯一的途径是用独裁主义强迫儿童完成他们不喜欢的任务,于是他们采用考试驱动的课程和教学,其本质目的是为了转移人们对深刻的政治动机和反教育的结果的注意力。
二、危机的政治转移:作为替罪羊的教师
派纳认为进行中的学校改革是政治事件,是南方的白人政治家们利用教师们在政治上的脆弱来转移其政治责任的伎俩。本来学习成绩不良的原因主要是反动的南方历史和它的种族歧视文化,是政治家们使公立学校在财政上匮乏的保守政策造成的。他们的“责任制”修辞的目的是把公众的注意力从更宽泛的美国文化,特别是南方文化中的反理智主义问题上转移开来。这是政治家们惯用的手段。[9] 派纳说,教师作为替罪羊的做法被伪装在对儿童的关注中:如“不让一个孩子掉队”。[10] 如果把美国近40 年的学校改革和教师教育改革置于文化和政治危机以及右翼势力的支配地位中来看的话,就会发现它们其实都是政治转移的手段。这些右翼改革是在理智上奴役教师。
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所规定的各项改革,特别是有关评价体系的改革中,联邦政府通过把在特定学年度参加州一级的统考以及统考成绩与联邦的数额庞大的经费资助挂钩的做法,收回了许多学校和教师一级的评价权。这意味着教师的学术自由减少了,他们丧失了很多藉以评价学生的学习和学术成就的手段,意味着要他们必须为学生的学习成绩负责任。但在派纳看来,“学生的成绩(或缺欠)不能完全归因于公立学校教师的水平,教师的失败也不能归罪于大学师范教育工作者。我们教师并不对学生如何变化负主要责任;教育的过程,与家庭、历史、文化相互交织,过于复杂,无法依据线性——因果方式归因于某一特定的群体。而且,如菲利普·韦克斯勒(Philip Wexler)所言,符号社会中的认同感形成主要发生在校外,不同于以印刷品为基础的学校,校外的大众文化是意象性的。如果韦克斯勒所言是正确的,即教育在真实的意义上发生在学校之外,只是偶尔发生在校内,那么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就进一步缩小了。”[11]
派纳建议教师们只有从课程理论的角度努力理解他们所处的历史时刻,他们才有可能从目前的被奴役状态中解脱出来,才有可能解放每个学生的力量,他们的形象才可能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象征。其中,教师们应该意识到他们处在优雅的服从的位置上。他认为教师们在政治上相对无权相对脆弱的地位,导致了他们不论是在与等级制的政治关系还是与研究者的理论关系上都处于“优雅的服从”的位置上。例如在此次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改革中,通过强调教师和学校的“责任制”以及学生成绩的“底线”之类的商业词汇,政客们加强了对教师本人以及教师们教给学生的内容的控制。“由于职业上的乐观和设计上的无知,我们教师拒绝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历史性的现在是一个受右翼反动分子和迷恋商业的政客们折磨的教育梦魇。”[12]
在专业内部,一般而言,教师们遵循着从理论到实践的线性关系。他们把自己放在一个幼稚化的位置上,要求知道“什么起作用”。教育研究者和教师的关系也是一种等级制的线性关系,是职业上的从属关系。这样做,教师们就不会集中精力于如何为学生提供生动的教育机会,以及鼓励学生以各种种族上和性别上合适的方式来鼓励学生利用这些机会。
为了抵制自己“优雅的服从”的命运,派纳的建议是坚持把商业的修辞限制在商业的范围内,不要把其强制施行到教育专业内部。教师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责任制的修辞中,他们实际上被降为技工,管理着学生的“生产力”。教师们应该从一些身体上受到奴役的人那里获得内在的勇气和社会团结来批判教育现状,为了迎接那个还没出生的世界,教师们应该“反驳”和“顶嘴”。这样做,意味着教师们应该珍视学术知识和学术认知,珍视自己的和学生的“心灵生活”,在教授基本技能和基本知识的时候,教师们必须与学生保持活生生的关系。
教师们除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外,还需要学习课程理论,以了解和理解他们的工作环境。派纳认为“这样的学习,和它所支持的复杂的会话,能够提供重建教育中的公共领域所需要的自我动员和集体行动的热情”。[13] 他们必须了解他们的处境与奴隶和妇女的处境很相似,因为种族歧视和厌恶女人的做法已经被延迟和移置到公共教育领域中。教师们和学生们的智力自由已经被“责任制”之类的修辞所制约。教师们除非领会到自己是政治转移的牺牲品,否则他们还是无法理解自己的工作处境。这需要教师把自己不仅看作是教育的学生,而且看作是自己的教育的学生。[14]
三、教师们应该培养自我反思的和跨学科的能力
派纳认为对教师的培养涉及到培养心灵独立性、自我反思和跨学科的学识。为了沟通社会、种族和政治之间的潜力,教师们应该理解他们自己的自我形成和他们所教的学科之间复杂和转换的关系,在自我和社会、地方和全球、学校科目和日常生活的交叉点上进行跨学科的研究。
从1970年代开始,派纳就开始论证主观领域是教师和学生把学术知识与他们的自我形成相联系的地方。他认为主观领域的这种联系是在历史时刻进行的,镶嵌在地区、国家和移民社群的文化中。为了能重新建构自己,他呼吁使用自传的研究方法进行身份研究。在他看来,没有私人领域的重建,公共领域的重建就不可能进行。
在当前的美国,教师的身份正在被从工头设想为经理。虽然这是一个提升,但却仍然是由别人所设想的身份。如果教师们毫不批判地接受学生及其家长、管理者、政策制订者和政客们对其身份的设想,那么他们自己的以及他们培养的学生的理智就会受到局限和破坏,他们的理想也会消失在日常教学工作的表层。通过学习课程理论所倡导的自我理解和跨学科的理解教育的思想,教师们可以用其它的方式看待教育,可以用非工具主义的方式对待师生关系。在课程理论家和教师们的共同努力下,教师也许可以拥有除社团主义所建构的身份之外的身份。[15] 派纳充满激情地倡导:“作为自由探索的知识和理智成为了我们的翅膀,我们藉之以飞行、访问其它世界、 回到这个世界来号召其他人, 特别是我们的孩子, 进入一个比我们现在所居住的世界更加肯定生活价值的未来世界。 当我们下沉, 淹没在由别人设想的角色里, 我们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可能性(aborted possibilities),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中认识到我们个人的和公民的身份政治、不可能认识到创造和生产的教育动力学。”[16]
为了避免教师们过多地淹没在日常的教学事务中,派纳建议他们要经常在大学注册学习,但是并非仅仅在教育系或他们所教的学科的系。教师们必须也学习他们当下的专业和兴趣以外的领域,特别是应该学习非裔美国人研究和妇女与性别研究。当教师们来到大学教授那里的时候,教授们必须向他们提供智力的挑战。对那些未来的和实习的教师而言,学习课程理论并不意味着学习一种起作用的怎样教的技术,不是学习设计能产生可预测其结果的社会工程,因为这样做意味着考试和测量。派纳引用已故的19世纪晚期黑人女性主义者安娜·朱丽亚·库柏(Anna Julia Cooper)的话“我们如此受考试和测量的支配,如此受百分比和延迟的局限和刺激,以至于机器随着大生产而失控,反过来又撞翻了开动机器的人。我认为发明机器人不是用来委派任务、进行目标考试、打分数和用来麻醉那些胆敢把原创性的思想带给学生们的特定问题和需要的教师们的。”[17]
派纳还警告说,一个潜在的危险是教师们适应了他们所讲的语言。如果教学只是一个实施别人的目标的过程,而不是为了培养创造性和独立性,那么教育的过程就被分解了。派纳引用加拿大著名的课程学者特德·欧克的提议说:“除了‘课程实施,’‘课程即席创作’怎么样?”[18] 欧克认为这样做能让教师们的整个身体敲打出新的和不同的节奏。当然课程即席创作的境界只有在教师们充分理解自我并具有跨学科的能力时才能达到。
四、课程研究者的责任
派纳对课程研究者的身份和他们与教师的关系以及他们对课程所持的态度都有发人深思的建议。他的这些学术思想极大地促进了美国课程研究的理解范式的发展。
首先,研究者应该意识到课程是“复杂的会话”。对许多在职教师而言,课程可能只意味着他们所教的学校科目,对接受职前教育的未来教师而言,课程可能只是他们被要求读的一系列书籍。但是派纳提出:“课程是一个高度符号化的概念”,是年长一代所选择要告诉年轻一代的东西。但不管学校科目是什么,课程都是历史的、政治的、种族的、性别的、现象学的、自传的、美学的、神学的和国际的。课程成为一代代人努力界定他们自己和界定世界的场所。”[19] 从“复杂的会话”的意义上来说,课程研究者应该努力从无数个向度来理解课程, 而不仅仅只是从传统的课程开发的维度。研究范式的转移意味着研究者与教师的关系的根本性转变。
其次,研究者与教师之间是顾问和合作者的关系。在课程开发范式中,研究者与教师的关系是专家—客户的关系,这是所谓理论应用于实践的线性关系,是一种等级制的不平等关系。实践证明这种关系已经失败了。教师对专家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教师的失败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归因为大学师范教育工作者的失败。派纳的建议是课程研究者应该做教师的朋友和同事,应教师的要求为他们提供专业知识,也可以向政策制订者提供专业知识,但是派纳指出,如果他们不采纳这些建议的话也不必伤心,因为他们的兴趣不一定是教育意义上的,而更多的是政治和经济意义上的。课程理论家必须坚持不对公立学校的弊端负责。[20] 在这个意义上,派纳的意思是课程理论家应该致力于探讨只有少数人才会理解的现象和观点,就是说进行先锋性的研究。派纳用物理学、舞蹈和绘画作为比喻:“设想一下如果学者的工作限于初学者能够理解的水平,物理学如何进步。设想如果舞蹈与绘画不突破多数人认可的形式,艺术如何发展。任何领域必须有一部分先锋性工作,否则便无法前进。”[21]
再次,课程研究者应该反对学术职业主义,做一个私人公共知识分子。派纳认为课程研究者应该是私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在尼采自我克服的意义上是“私人的”,同时又公然地拒绝把他们的智力劳动用在毫无质疑地为国家服务和与政治现状同谋上。他们从“内部”工作。课程理论在他们那里构成了公共的和政治的行为,需要自传地挖掘和自我反思地阐明他们在社会中的主体性。[22] 如果没有不断进行着的自传理解,课程理论家的理智实践往往会模仿时髦的和有利可图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