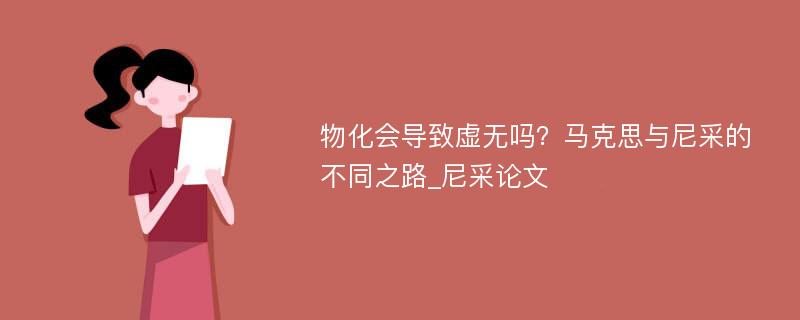
物化通向虚无吗?——马克思与尼采的不同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尼采论文,马克思论文,之路论文,虚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物化”(Verdinglichung与Versachlichung)是社会批判理论的常用术语,是理论左派现代性批判常常使用的范畴;而“虚无”(Nichts)、“虚无主义”(Nihilismus)往往是保守主义阵营现代性批判常用的语汇,是理论右派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采用的概念。问题在于,“左”、“右”两派的批评能够通过“物化”、“虚无”这两个范畴融通起来吗?左翼阵营的代表自然应该选择马克思,而右翼阵营的代表我们选择尼采。就他们各自的地位、影响而言,这种选择应该算恰当。虽然马克思与尼采分别对物化、虚无问题都有极为深刻的思考,但马克思不用“虚无主义”一词,尼采也不用“物化”一词。马克思对“物化”极为重视,按照卢卡奇、广松涉等人的看法,“物化”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一个范畴;而“虚无主义”显然是尼采理论中最核心的一个概念。那么,“物化”与“虚无”的关系如何?“物化”必然导致“虚无”吗?对于现代性批判理论来说,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在马克思、尼采、韦伯、屠格涅夫、卡夫卡等思想家或文学家那里不断被思考的时代重大问题。本文试图探讨马克思与尼采在此问题上的不同理解,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一、物化世界损伤“人”的三种情形 物化世界对人形成一种否定,这是一种很流行的意见。人们经常会把这种看法加诸马克思。但这是不妥当的,至少未能完整地反映出他关于物化与人的关系的基本观点。 实际上,物化世界否定的“人”,首先是个性之人,尔后是权利、尊严意义上的“人”,总之是人权、尊严、个性意义上的存在。这种意义上的“人”与物化世界可能产生尖锐的对立与冲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手稿中,马克思把劳动的对象化看作是“对象的丧失和为对象所奴役”,并招致劳动者的异化。他明确指出,劳动的对象化(Vergegenstandlichung)就是现实化(Verwirklichung),而“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所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①由于劳动的对象化直接表现为劳动者的异化,所以,劳动者创造的物的世界就与人的世界直接对立:“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②甚至“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③显然,劳动创造的物的世界与人本身的世界是对立的。物的世界的扩大和进步并非有利于人的世界的实现,却直接阻碍人的世界的实现。这自然不是指生产关系、生产力意义上的“人”没有进步和改善,而是指伴随着物的世界的增大,“人”的权利、尊严没有得到保障,个性更没有得到尊重和实现;相反,物的世界的增大是以牺牲劳动者的正当权利、尊严,贬抑人的个性为代价而实现的。 后来,卡夫卡说办公室在杀人,公务员“他们把活生生的、富于变化的人变成了死的、毫无变化能力的档案号”,“到处都是笼子”,“我身上始终背着铁栅栏”,以及“这是精确地计算好的生活,像在公事房里一样。没有奇迹,只有使用说明、表格和规章制度。人们害怕自由和责任,因此人们宁可在自己做的铁栅栏里窒息而死”④,他控诉的正是日益合理化的社会对人权、尊严、个性意义上的“个人”的胁迫、排挤、模式化、常规化,控诉有个性、有尊严的人被社会关系系统(即马克思后来说的社会关系之物)胁迫、忽视和否定。卡夫卡说:“财富意味着对占有物的依附,人们不得不通过新的占有物、通过新的依附关系保护他的占有物不致丧失。这只是一种物化的不安全感”⑤。这时,他是在财富之物与人之间作出明晰的区分,否定把人仅仅理解为物的所有者,仅仅以物来注释人。 卡夫卡认为物化体系压抑、窒息人,其意思与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手稿中的上述看法是基本一致的。这种一致表明,青年马克思与卡夫卡所谓与物的世界对立的“人”,不是抽取了个性、能够生产和交换的普遍的及一般的“劳动者”,不是现代社会中不得不以“物”表征自己的“人”,而是高于物的“人”。 在这里,物化世界对“人”的否定有两种情况:第一,“人”被界定为个性之人,物化世界否定的是人的个性;第二,“人”被确定为有人格之人,物化世界否定的是人的尊严、人格。资本的内在需要不考虑人的尊严与人格,却把它们纳入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系统之中。只有在利于利润更大化时,人的个性、尊严才有利用的价值,但这种价值是一种工具性、外在性价值,不是根本、内在的价值。物化体系没有把人的个性、人格、尊严视为人的内在价值,却根据物体系自我壮大的内在需要把“人”外在地设定为一种有效的工具。物体系的内在价值与人的“内在价值”发生了对立,出现了裂痕。这就是通常所谓人的“物化”,是物化世界伤害、否定人的实际情况。在本文第二部分,我们将讨论并指出,按照马克思的逻辑,这不能算物化导致了虚无,也不等于物化世界否定了人:因为“人”不只是个性、人格,也有其他维度的体现和存在,即可以是普遍的、一般的、社会性的“人”。而普遍的、一般的、社会性的“人”恰恰是在现代物化体系中获得实现的。更为重要的是,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种维度上得以实现的“人”,将为个性、人格维度上的“人”的进一步实现奠定基础和准备前提。但按照尼采的看法,物化世界是在压抑、否定富有创造性和个性的人,并通过这种压抑与否定成就一种平庸。这是本文第三部分的主题。 在进入第二、三部分之前,我们不能忘记,物化世界对“人”的否定还存在第三种情况:特定物化产品对人的基本权利构成威胁与否定。一些特殊的人造物开始严重地威胁与敌视人,如核武器、化学武器对人的威胁与残害。按照京特·安德斯的看法,核武器直接具有毁灭人的效应,所以,核武器的制造和威胁就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实行虚无主义的罪责。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我们最后的结论:手中握有原子弹的人是行动中的虚无主义分子”。⑥在他看来,尽管力图以这样的武器威慑他人的人甚至连“虚无主义”这样的词都没听过,甚至多数人都在私人生活中和蔼可亲、严肃正经,仍不能否认这些武器与虚无主义的内在联系。“因为不管他们知道与否、愿意与否,事实上他们信奉的是完全另一种哲学和遵循完全另一种伦理道德:物的哲学和物的伦理。因为在‘客观精神’的招牌下出现了一条公式:‘人人都要遵循他所拥有的物的原则’。”安德斯的意思是,“谁占有了物,他就拥有了这个物的准则,拥有原子弹的人也同样拥有它的准则。这与人是否情愿无关。”⑦看来,从物化通向虚无,还存有安德斯这里所说的这种路线:从人们所制造的“物”中产生出来了一种毁灭性力量,使得最有意义的生命存在可能瞬间变成虚无。而且,这还不是指“物”泯灭了人的尊严、人格与个性,而是直接对人的毁灭。也就是说,原先的虚无主义是把人的尊严、人格、个性、精神泯灭或虚无化,现在则是更实在的虚无主义力量把人的身体、物质生命虚无化!这比通常所谓以否定人的崇高价值为特点的“虚无主义”更严重的另一种“虚无主义”,即以否定人的基本生命、否定人的基本权利和价值为特点的“虚无主义”,是突破了更低底线的“虚无主义”。 二、物化不通向虚无,物化可以促进“人”的实现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没有核武器、化学武器,他不可能从这个角度思考物化与虚无的关系。而且,我们知道,虚无主义未能构成马克思理论的核心关注,或者说,虚无主义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并未构成非常严峻的根本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施蒂纳时认为那是小资产阶级空虚、无力的表现。而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剖析资本的逻辑时,马克思认定资本为了获取利润消解一切神圣和崇高,那是资本逻辑的必然产物。资本孕育出的虚无、空虚并不覆盖到一切阶级身上,却只体现在逐步丧失历史进步性的资产阶级身上,无产阶级不会受到它的浸染和困扰。对无产阶级来说,物化并不必然导致虚无,物化财富却为一个更理想、更崇高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充足的物质基础。物化并不一定导致虚无,其缘由首先还不是无产阶级不会像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那样摆脱不了虚无,⑧而是因为在马克思那里,“物化”并不是一个完全负面的概念,它还意味着促进效率的提高,促进一种“人”的实现,并为“个性人”、“尊严人”的进一步实现提供基础。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劳动的对象化得到肯定,被归于一般的商品社会中:在一般的商品生产中,“对象化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把活劳动变成再生产自己的手段,而起初交换价值只不过表现为劳动的产品”。⑨在资本主义特定条件下,物的价值则只能在交换中实现,只能在一种社会关系中实现,进言之,这种对象化的实现越来越依赖于一种严密、复杂、发达的社会关系系统,依赖于分工、交换体系,由此才导致物化(Verdinglichung)、物象化(Versachlichung)。物的实现取决于社会交换体系的认同,而社会交换体系越来越不是直接的物的交换,却体现为日益复杂的事务操作体系。这个体系越来越规范化、精确化、程序化、法制化、“对事不对人”,越来越不随意化、人情化、“对人不对事”,越来越不受人的个性、情感等主观品质的影响。这个事务操作体系的效率影响着物的实现,并且使得几乎所有的人事都与事物、事务纠缠在一起。人纠缠于物、事之中难以自拔,人被物化、事化了。于是,“人”不仅仅是个性存在,完全可以是甚至首先是一种一般的社会性存在。通过社会生产、交换体系得以实现的“人”是一种普遍性、共通性意义上的“人”。马克思特意申明,个性不参与商品的社会生产与交换过程。他指出,在现代交换体系中,交换者基于一种抽象的等价置换体系被视为价值相等的抽象人:“他们本身是价值相等的人,在交换行为中证明自己是价值相等的和彼此漠不关心的人。……他们只是彼此作为等价的主体而存在,所以他们是价值相等的人,同时是彼此漠不关心的人。他们的其他差别与他们无关。他们的个人的特殊性并不进入过程。”⑩显然,这种意义上的“人”之所以获得社会实现,得益于日益发达的物象化(Versachlichung)系统,得益于这一系统的规范化、精确化、程序化、法制化特质。由于这一系统日益发达的这一合理化特质才使得物的生产、交换的规模和质量不断提高,使得“人”在这种社会性的意义上不断获得实现。由此,不能仅仅在个性、特殊性的意义上界定“人”,“人”的内涵还通过社会性得以大大扩展,通过物化、物象化系统得以丰富和扩展。在社会交换体系日益复杂化、规范化,即越来越物象化的现代社会中,必须参与而且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交换的劳动者,作为支配一切的主体而从交换行为本身中返回到自身。因而就实现了主体的完全自由。显然,这里通过社会交换获得“自由”的“主体”是遵从和认同了物化、物象化社会交换体系的“人”。用马克思的话说,“作为这样的人,他们不仅相等,他们之间甚至不会产生任何差别。他们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占有者和需要交换的人,即作为同一的、一般的、无差别的社会劳动的代表互相对立。……每个主体所给出的和获得的是相等的东西……”(11)由此而言,对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来说,物化(Verdinglichung)与物象化(Versachlichung)不再仅仅是负面的东西,而是既具有历史进步性又具有负面性,既在普遍性和一般性维度上实现人、又在个性和特殊性意义上压抑人的一个历史性范畴。(12) 这意味着,社会关系之物与物理意义上的财富之物成全的是普遍的、一般的人,不是个性之人。众所周知,在《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看来,这种普遍的人恰恰是人的自我实现过程中必经的历史阶段,个性之人遭受压抑是难以避免的历史性现象,不能完全否定这种现象的历史进步意义。因为,物化的人也就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这样的人比“人的依赖关系”下的“人”更发达,并且与“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相适应。只有这样的社会形态才会为自由个性得以实现的未来理想社会奠定坚实基础。(13)这是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论的基本内涵。在第二大形态中,“物”的壮大和进步促进普遍维度的“人”的实现,并为个性之人的实现奠定基础。“物”并不敌视“人”,历史地看,它们是统一的。所谓“见物不见人”,仅仅是在个性、尊严、人格意义上注释“人”了;反之,则是“见物必见人”。 问题的关键是,不能仅仅在个性、尊严、人格意义上界定“人”,也应该或更应该在抽取了个性,能够生产和交换普遍的、一般的人类劳动的“劳动者”与“交换者”的意义上界定“人”。由此,“人”的实现不仅仅体现为个性的实现、人格与尊严得到尊重,还体现在自己的劳动通过社会交换获得实现,自己的法权在政治法律实践中获得实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人经历一个物化阶段是必然的、无法避免的。正如艾萨克·鲁宾所说:“马克思不是仅仅表明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更准确地说,是表明在商品经济中,社会生产关系不可避免地采取物的形式,并且除了通过物不可能有其他的表达。”(14)“以物表现人”在现代社会中无法避免,在历史上首先是“进步”现象,只有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这个意义上,它才是一个批判性概念。也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使用较多的Versachlichung(物象化、事化)一词,经过韦伯等社会理论家在20世纪的中转之后已经逐渐丧失了批判性含义,变成一个中性词了;倒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使用较少的 Verdinglichung(物化)一词,现今仍然是一个批判性概念。 众所周知,启蒙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对“人”的理解各不相同。他们分别从普遍性维度和个别性维度上界定“人”,但两者并非绝对对立,完全可以获得统一。马克思的人论显然就致力于这种统一。不能因为“物化”体系与个性、人格意义上的“人”有所抵触、冲突,就一概地判定物化体系具有敌视人的虚无主义性质。社会物(社会关系系统)的日益合理化带来的另一种“物化”,即马克思、韦伯所谓的Versachlichung,完全可以成就普遍性维度上的“人”以使其获得实现,从而“物化”导致“人”的实现,而不是相反。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物化导致虚无不仅是指物化体系贬抑个性、人格,而且还可以指核武器、化学武器对人的威胁与残害,可以指往牛奶里注入三聚氰胺、往食品里加入塑化剂、在蔬菜上使用剧毒农药,或者可以指为了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而置他人的生命这种最基本的价值于不顾、把物的价值置于人的基本价值之上;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说,之所以出现这类情况,恰恰是因为制度化的社会关系(社会物)系统合理化水平还不够高、不够发达所致。也就是说,制度化社会关系系统合理化水准的提高,这种意义上“物象化”(事化)水平的提高,恰是杜绝出现物化敌视“人”现象的正常渠道!这恰恰意味着,合理、全面地理解“物化”,把它包含的两种情形Verdinglichung与Versachlichung区分开来,明晰各自不同的内涵与功能以及其中的复杂性,才是避免“物化压抑人”、“物化导致虚无”等简单结论的关键所在。 三、物化通向虚无:尼采对现代文明本质与前景的认定 马克思看好现代文明的前景,认定它的潜力会随着无产阶级的解放得以进一步释放。尼采以及随后的马克斯·韦伯却开始放弃这种乐观主义信念,担忧日益物化、合理化的现代社会将陷入平庸化,使得富有创造力的精英人物越来越受到约束,失去自由的创造性空间,以至于深深忧虑现代文明会陷入虚无主义。 就我们的阅读所及,没有发现尼采使用“物化”(Verdinglichung与Versachlichung)概念,但在他对现代社会专门化、机器化、客观化、制度化、安全化的批评中,显而易见存在着一种对这种现代物化体系的不信任和批判,以及对更新和创生一种为创造、全面发展、风险、自由留有更大空间的新文化的强烈希冀。在尼采的眼里,物化体系明显体现为中下层人团结起来对高等人的统治与约束,体现为中下层人对安全、保险、按部就班、专门化技能、严格秩序、顺从、谦让、宽容等品质和价值的喜爱,同时也是对风险、实验、创新、反约束、除旧布新、痛苦、孤独等品质和价值的惧怕。一句话,在尼采的眼里,物化体现着一种体系或制度基于安全和保险的完善化,体现着一种中下层人价值与品质的甚嚣尘上,体现着传统西方文明自古代以来沿着柏拉图主义的方向不断深化、不断成功,因而最后功德圆满、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并被另一种新文化替代的时代变迁,体现着旧文化退出、新文化正在创生的“虚无主义”空间。这个空间既是旧文化和旧价值的逐渐泯灭的空间,更是新文化的不断孕育的空间。 在《敌基督者》中,尼采曾把人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是侧重精神的、创造性的高贵者;第二等是正义的守护者,秩序和安全的守护人,最具精神性的执行人,是第一等级的追求者;第三等则是平庸的大多数人。尼采并不认为平庸有什么不好,反而认为大多数人就是处在这样的层面上,是很自然的。尼采认为,处在越高级别上的人,就承担得越多,越需要负责任和抗风险的能力,越需要忍受痛苦与孤独,更多具有创造、个性张扬、不固执于日常意识形态偏见等的能力和品质。尼采说:“生命向高处攀登总是变得越来越艰难——寒冷在增加,责任在增加。一种高级的文化是一个金字塔:它只能奠基在一个宽大的地基上,它首先必须以某种强有力、健全稳固的平庸为前提。手工业、贸易、农业、科学、绝大部分艺术,一言以蔽之,全部职业活动的总和,都仅仅是与平庸者的能力和追求相适应;这样的职业活动似乎不适合与众不同的人”。大多数人就应该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职业,“掌握一门手艺、专业化是一种本能。一种更深刻的精神,完全不值得对平庸本身表示抗议。为了使与众不同者存在,首先需要平庸;平庸是高级文化的条件。当与众不同的人对待平庸者比对自己和同类更温和,这不仅仅是心灵的礼貌——这直接是他的义务”(15)。 显然,尼采并不像很多人理解的那样反感第三等级的人,反而认为这一等级的人是很自然的大多数,没有什么值得谴责和批评的;他反对和批评的只是把这一等级的品质和价值作为唯一和至高标准,并对更高的两个等级进行挖苦、讽刺、反对,特别采取一种美化自己的、很虚伪的意识形态形式,如明明出于怨恨、嫉妒,还想出一些美化自己的理由,把自己说成是善和美的、崇高和伟大的,而把自己达不到的更高等级的那些品质和价值说成是危险的、恶的。按照尼采的看法,第三等级顺从、支持更高等级是很自然的事,反对和反抗更高等级则是不自然和不合理的事。由此,尼采反对所有鼓吹平等的理论,认为它们颠倒了这个自然秩序和逻辑,把世界弄得不像本来的样子。“不正义从来不在于权利的不平等,而是在于对‘平等’权利的要求”。(16)平等是软弱者的嫉妒、复仇、怨恨、恐惧。无政府主义和基督教尤其如此。我们知道,物化体系不断致力于把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规范化、精确化、程序化、法制化、“对事不对人”,就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社会公平、社会平等的水准,使更多的人特别是底层民众享受到更多、更好的社会保障和服务,享受到更多的社会发展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是一个良好社会的基本标志。但在尼采看来,对平等的现代要求似乎过了头,特别是平等的意识形态成了敌视和否定最有能力的人创新的紧箍咒,这就是现代文化的内在弊端和需要调整之处。 尼采认为,日益凸显制度、机器的关键作用,让人按部就班、平平庸庸、抹杀个性、放弃创造、惧怕冒险的物化体系中,人,特别是富有个性和创新性的人会变得渺小,适应并被动地就范于专门化牢笼。为此,尼采强调,需要相反方向的运动,也就是“产生综合的、累加的、有充分理由的人,人类的机器化是这种人存在的前提,作为一种底架,这种人能够在它的上面为自己构筑更高的存在形式。”(17)正像尼采认定“虚无主义”意味着旧价值的失效和新文化、新价值的创造,因而这个概念可以喻示着积极功效一样,尼采也这样看待“物化”,认为“物化”可以是积极的“物化”:正是因为人都面临着物化的命运,才需要超人的塑造,需要超人来带领众人走出物化。“物化”、“物化的人”正是产生伟人的理由和契机所在。“超人”就是一种超善恶、不断超越自己、不断创造的人,因而也肯定是超越物化体系的人。 尼采强调,安全、保险、过早的知足,会造成一种退化并形成一种枷锁,阻碍创造性和伟大的创生。他指出:“这将成为一种可怕的精巧的枷锁:如果最后没有炸开枷锁,没有一下子粉碎所有爱与道德的束缚,那么,这种精神将会枯萎、缩小、女性化、客观化。”(18)物化体系会消灭生命的风险性特征,会逐渐走向衰落与毁灭。“舒适、安全、恐惧、胆怯,这些东西试图取消生命的危险特性,并想对一切进行‘组织’——经济科学的虚伪。如果存在巨大的危险,人这种植物在不安全的情况下生长得最茂盛:当然,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会走向毁灭。”(19)物化体系塑造了一种对大多数人日益安全的保护体系,使得人失去冒险和创造的勇气,变得更加懦弱、标准、按部就班。尼采认为,如果普遍规范抑制创造、扼杀战斗精神和生命力,那它就导向虚无:“把一种法律规范想象成绝对的和普遍的,不是把它当作权力联合体的战斗武器,而是把它当作反对所有战斗的武器……这是一种敌视生命的原则,是对人的败坏和瓦解,是对人类未来的谋杀;是一种疲惫的象征,一条通往虚无的秘密路径”。(20) 这样,在马克思认为物化不会造成虚无主义的地方,尼采认为会造成萎缩和衰落,是虚无主义:既是衰落的开始,也是需要和呼唤创造的开始,意味着双重的意义。 由此,塑造超人是时代的使命和要求。这势必造成痛苦、磨难、遭受蔑视、承担重估价值的风险。但这对于超越日益失去创造力的旧文化而言都是值得的。只要为了呼唤和塑造超人,经受痛苦,承担风险,历经磨难,都具有积极价值:“培养更好的人造成更加巨大的痛苦。在扎拉图斯特拉那里展示了这种过程作出必要牺牲的理想:离开家乡、家庭、祖国。在占支配地位的风俗的蔑视下生活。尝试与失误的折磨。摆脱陈旧的理想提供的一切享受(人们尝到了它们充满敌意、格格不入的滋味)”(21)。其实,早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就批评了追求神机妙算、廉价乐观主义,以及崇尚理性、知识的现代文化,认为这种文化始自苏格拉底,通行于亚历山大里亚。整个现代人都沉湎于这种文化:“我们整个现代世界被困在亚历山大里亚文化的网中,把具备最高知识能力、为科学效劳的理论家视为理想,其原型和始祖便是苏格拉底。”(22)尼采认为这种文化已经发育成熟,使整个社会直至底层都在追求神机妙算,向往廉价乐观主义,是一种有利于底层人而抑制甚至扼杀富有创造力的超人的文化。它的最大问题就是不断孕育出了虚无主义,把一切特别是低等的、低俗的都视为有价值的、有品行的,失去了对崇高精神的追求,日益诉诸例行化、稳固化、制度化的僵化体系,是一种逐渐衰落、枯萎、不敢冒险、害怕悲剧与痛苦的文化。 当然,对尼采来说,物化导致的虚无不见得是坏事,相反,虚无是通往创造的契机。旧文化的衰落和泯灭,是更富有创造力的新文化孕育和创生的温床。“无”既是原有价值的虚化,同时也是新价值、新文化摆脱羁绊获得生长的空间。 四、反思现代性的两种模式:马克思与尼采 马克思与尼采对“物化”和“虚无”的两种不同态度,象征着两种不同的现代性反思。可以说,马克思相信现代文明的进步性,相信现代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会约束、提升、改变人的一些自然本性和事实。他在这种约束、提升、改变中看到了理想社会到来的必然性和希望。而尼采则认为,需要进一步反思文明与自然的关系。文明、文化是在约束、提升、改变自然事实,但有自己的限度。当一种文明推崇的价值与自然本身的倾向相违背时,就表示这种文明陷入了颓废和虚无的境地,就需要调整和改进了。按尼采的看法,现代西方文明恰恰就陷入了这种境地。用来文饰、矫正自然本能和欲望的文明元素是一种弱者、失败者的素质,与大自然的进化倾向是相反的、对立的。于是,这种对自然的约束、提升、改变、矫正就具有了“敌视强大、健康、活力,以数量战胜质量,以平庸取代高贵,并培育软弱、渺小、颓废”的功能。当文明不是推崇健康、强壮、富裕、卓有成效、勇于进取之时,就陷入了所谓的虚无主义,表明这种文明迫切需要重建和改变了。马克思和尼采都相信资产阶级陷入了虚无主义,无可救药。但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不会重蹈资产阶级的虚无主义之路,而尼采则认为虚无主义是现代的宿命,甚至是整个西方文明自古至今发展的必然逻辑,浸染了现代文化的任何一个阶级都无法避免。尼采相信,只有在克服这种虚无主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得重生,也就是说,走出虚无主义是现代人的一项极为艰难的选择,没有必然成功的好命运伴随。与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在资产阶级现代世界中浴火重生一样,尼采也认为超越资本主义的超人也能在现代文化中孕育生成。超越资本主义世界是两人共同的判定和追求。不同的是,马克思相信:物化、物象化既是一种进步又是一种阻碍,是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所呈现出的特殊现象,既不能完全肯定,也不能完全否定,应该通过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完善与调整,释放其中蕴含的解放性潜力,把现代社会中蕴含的理想发掘出来,使之获得进一步的实现。现代社会没有穷尽在解放、自由等方面的巨大潜能,进一步的调整和变革所能释放出的能量足以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而尼采则认为,西方文明自苏格拉底开始,自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文化结合开始,发展到现代,已经步入到衰退的阶段,进入了虚无主义的时期,内部的潜力释放不足以建立一个更高贵的文化,所以,希望只能定位于迎接新文明的创生。 其实,在笔者看来,两人的角度从表面上看是不一样:马克思看重的是大多数人,特别是中下层的普通人;而尼采看重的是少数精英,或者富有创造性的超人。其实,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也是承担重担、具有创建未来能力的强者。马克思只是着重于让它为更多人担责,至于能力、素质和态度,与超人存在很多类似。尼采不把为更多人担责看得很重,不是因为他不重视这一点,而是因为在尼采看来,为更多人担责是超人的自然品质,是最自然不过的,是不言而喻的。由此来看,两人只是着重点不同而已。对尼采来说,物化体系窒息、压抑超人的存在,使得真正高贵的东西不再可能。而革除物化体系的虚无则是开启一种使高贵成为可能的局面。而对马克思来说,物化体系是保证大多数人自由的制度,应该做的不是推翻它,而是进一步释放其中蕴含的更大潜力,增加自由时间,使高贵得以可能;而虚无化是秩序的损害,从而使得普通人在竞争中重新回归强人奴役的可能性增加。 现当代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瓦蒂莫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遗忘就是存在被降低为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交换价值,所以,遗忘存在就是它即被主体置于他所确认的价值中,被主体纳入自己的权力体系之中。“虚无主义就是存在沦落为交换价值”,(23)就是交换价值成为唯一价值,从而导致最高价值的陨落。这样的解释不但把尼采的“上帝之死”与海德格尔的“存在遗忘”,而且也与马克思的物化理论统一起来了。于是,“虚无主义是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的消费。虚无主义并不意味着处于主体的权力之中;毋宁说,这意味着,存在被完全消解在价值的谈论之中,消解在普遍等价的无限转换之中。”(24)存在在价值里得以消费,就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必然完成式,也就是完成了的虚无主义。把交换价值的普遍化视为虚无主义的完成,进而整合尼采与海德格尔,并进一步断定“呈现给马克思的也是同样的事件”(25),甚至还把“既无狂暴也无同情的冷漠”、“完全被控制和管理的社会”两个意思都整合进尼采与海德格尔搭建起来的虚无主义解释框架中。瓦蒂莫的这种解释看到了尼采、马克思、海德格尔、韦伯、阿多诺与霍克海默之间的相通性,但不能由此遮蔽他们之间的差异与区别。把这些思想家都安插在瓦蒂莫所理解的后现代逻辑中,对于有明显差异的马克思和尼采来说,是蕴含着很大风险的。从根本上说,面对基督教世界的衰落,马克思与尼采都坦然接受,并无惋惜和忧虑,他们都积极地在这种衰落中探寻更好更高的新世界。而对资产阶级创造的世界,他们都很不满意,因而都把希望寄托在对这个世界的进一步改造和超越上。但在反思现代性问题上,马克思和尼采还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模式。一致掩盖不了相异,差别也上升不到完全对立。 注释: ①②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第52页;第51页;第52页。 ④⑤卡夫卡:《谈话录》,载于《卡夫卡全集》第4卷,洪天富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312、313、316页;第317页。 ⑥⑦京特·安德斯:《过时的人》第1卷,范捷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第267页;第267、272页。 ⑧相关分析参见刘森林:《马克思与虚无主义:从马克思对施蒂纳批判的角度看》、《资本与虚无:马克思论虚无主义的塑造与超越》,分别载于《哲学研究》2007年第7期和《吉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⑨(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20页;第107-108页。 ⑩(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359页;第358页。 (12)具体论述参见刘森林:《重思“物化”:从Verdinglichung与Versachlichung的区分入手》、《物象化与物化:物化逻辑的再思考》,分别载于《哲学动态》2012年第11期和《哲学研究》2013年第1期。 (14)转引自贾斯廷·罗森伯格:《市民社会的帝国》,洪邮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203页。 (15)(16)尼采:《敌基督者》,载于吴增定的《〈敌基督者〉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252页;第253页。 (17)(18)(19)(21)尼采:《重估一切价值》,林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967页;第969页;第70页;第969页。 (20)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周红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55页。 (22)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第76-77页。 (23)(24)(25)詹尼·瓦蒂莫:《现代性的终结》,李建盛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73页;第74页;第78页。标签:尼采论文; 交换价值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虚无空间论文; 历史虚无主义论文; 物化女性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政治论文; 资本论论文; 哲学家论文; 存在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