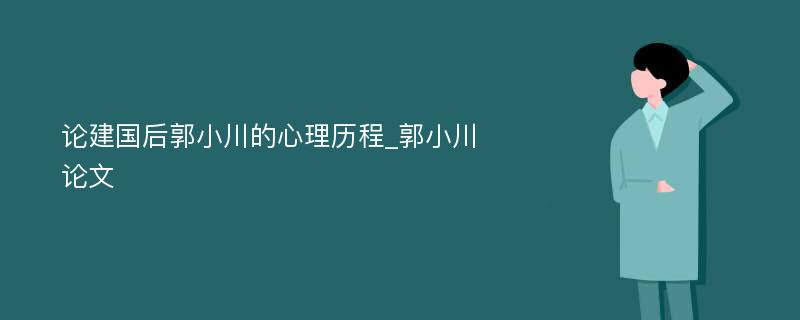
论郭小川建国后的心路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路历程论文,郭小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3)03-0112-07
郭小川是以“战士诗人”著称于中国当代诗坛的,但“战士”实际上不足以概括郭小川复杂的心灵世界与人生历程,正如其夫人杜惠女士及子女在《郭小川全集》的《后记》中所说:“郭小川的公众形象主要是一个战士诗人,他活着时抛给世间的多是昂扬与奋发,是他那个时代特有的激情与梦想。然而真实的他确是单纯如此吗?我们觉得不是 的。”“他很深入地介入历史,而这种介入在他而言又有某种特别的地方,那就是他不只是遵命式的介入,而是充满个性色彩的介入,在否定个性的时代里,他这种个性的坚持就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1](P393,394)
一、圣徒般的战士人格
与许多延安出身的诗人、作家不同,担任过丰宁县县长,亲率县武装支队与敌匪作战,领导穷苦百姓打地主、斗恶霸的郭小川,曾是手持武器的真正的战士。对于自己所投身的革命事业,郭小川的内心深处,是涌动着一种近乎圣徒般的感情的,并时常外化为一种刚勇无畏的战斗人格。参加八路军之后,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人活着,最可怕的事情不过一个死,/最大的风暴现在已经经历,/我没有眼泪,只有呼喊:‘来呀,/ 英勇的战士!’”(《让风暴更猛烈地吹吧》)在清算复仇大会上,他曾以县长的身份, 站在讲台上大声呐喊:“今天,我讲三个问题,第一是复仇!第二是复仇!第三还是复仇 !”[2](P28)建国后,郭小川身上时常散射出来的,仍是这样一种战士的情怀。到作协 工作后,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对于他认为够得上“右派”的人,是毫不留情的 。担任过中国作协副秘书长的黎辛曾经回忆说:“反右开始后,郭小川斗人是很厉害的 ……批冯雪峰的假材料不是他造的,但他大声跟着嚷嚷。”[3](P173)在批判刘绍棠的 会议上,他曾严辞厉色,指斥刘绍棠虽然还是个孩子,但“在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点 上,实在并不见得比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人差多少”,实在是一个浅薄、无知、狂 妄的反党“急先锋”[4](P495—496)。从郭小川这一时期的日记中,我们也可闻到一种 浓烈的火药味:
2月9日:九时,参加文艺报的汇报会,杨志一从上海、南京回来,侯敏泽从四川、武汉回来。成都流沙河、石天河一批人的情形实在令人担忧,他们的思想实在已经具有反动的倾向了。
6月21日:这次反右派一定要彻底。机关内划清界限,扫除右倾言论也一定要彻底。我想,一定要下决心,不把右倾错误打垮,决不收兵。
9月6日:翻到《中国青年报》,它批评了《人民文学》七月号,我找来一看,李国文的《改选》,的确坏透了,完全是敌对的。[5]
在郭小川心目中,共产党“是人类的希望”,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是世界上最为圣洁的事业,因此,他大声宣称:“党的一根毫发/也不能任人损伤!”当他真诚地相信有人是在反党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了,他要“保卫我们的党”(《发言集》)。后来,当他也遭到别人的批判审查的时候,他一直坚定地认为,自己对党是忠诚的。
1959年11月,他在因“右倾错误”而写下的一份“思想检查”中,虽承认自己存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同时又反复强调:“在反丁、陈斗争中,我是积极的。”“我反对埋怨中央或互相埋怨,我强调大跃进是无可争辩的,而且几次自觉地汇报机关的 情况。”“我历史上从来没有跟谁闹过不团结。”“我是一个能够为党冲锋陷阵的人。 ”[5]这些话,与其说是检查,倒不如说是自我辩护。实际上,对遭到的批判,郭小川 一直是耿耿于怀的,故而1962年5月26日,当作协召开甄别大会,为一些遭到错误批判 的人恢复名誉时,他曾拒绝与会,以示抗议。“文革”初期,当他被关进牛棚时,心中 想的仍然是:有些人是真正的黑线人物,而他自己对党并无异心,只不过是一时被误解 而已。有一次,他曾对前来送饭的儿子悄声说:“把我和某某某、某某某这样的人关在 一起!我怎么能和他们一样呢!”当他得知金敬迈、李英儒等人进入“文革”文艺组的时 候,也大不以为然,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左”派[3](P224)。
1974年,林彪专案组在审查叶群笔记时发现了“文艺问郭”字样。由于在延安时期,郭小川夫妇与叶群之间有过密切交往;解放后,郭小川也与林彪有过工作方面的接触,这“郭”自然就被怀疑为是郭小川了。郭小川1972年7月发表于《体育报》的《万里长 江横渡》一诗,也被怀疑是为歌颂林彪而作。本已被宣布“解放”的郭小川,又一次遭 到隔离审查。面对突如其来的更为致命的灾难,郭小川依然无所畏惧,迅疾写下了《我 与林彪反党集团的关系》、《关于<万里长江横渡>的交代》等材料,进行了坚决的辩解 。他反驳说:“是不是因为我在20年前与林彪有过一次(仅仅一次)工作关系,30年前和 叶群有过同学关系,十几年前与她见过一次面,就必须审查我呢?那么,在关键的时候 同他们有过比我亲切得多的关系的,大有人在,难道都审查吗?”[6](P266)由于郭小川 拚死抗争,此事终于不了了之。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与自信,在连续不断的打击与挫折面前,郭小川仍能不时表现出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乐观与豪迈。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改造”期间,人们经常见到的郭小川的形象是:赤裸上身,手握镰刀,大声地唱着歌,行进在上工的队伍中。在艰苦的劳动之余,他仍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们怎能不欢乐!——因为我们拼命劳动;我们怎能不欢乐啊!——因为我们拼命革命。”(《江南林区三唱》)。他在给妻子的信中,也曾这样表示:“早已下定决心,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永远在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工农兵结合中改造世界观,永远生活战斗在第一线”[7](P193)。当因林彪事件的牵连,被押送到天津团泊洼继续审查改造时,他仍刚健不屈。“有一天在食堂大庭广众下,他问华君武:‘君武,你说咱们是不是走资派?’这话带有极 强的否定‘文革’的挑衅性,众人皆一怔,华君武也不敢接言扭头走开,而郭小川神态 自若毫无惧色”[10]。如此逆境中的郭小川,甚至于暗中写下了致邓小平的“万言书” ,提出应改组文化部,反对文化专制主义等。他的那首洋溢着壮志豪情的诗歌名篇《团 泊洼的秋天》,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
1975年,与林彪集团的关系得以澄清之后,回到北京的郭小川,私下里拜望了老首长王震、老熟人纪登奎等,并受到了李先念、华国锋等人的接见。当他从高层领导人那儿得知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态度之后,兴奋异常,随即四处找人了解情况,向好友传达有关信息,用他女儿郭岭梅的话说:“有点组织队伍的感觉。”[3](P308)据有关迹象判断,郭小川很可能从高层领导那儿得到了某种暗示,并缘此而激起了他强烈的政治使命感。他要利用自己的影响,团结文艺界的力量,奋力投入到反抗倒行逆施的“四人帮”的斗争中。在他为此而再度受到追查,被有关领导安排到河南予以保护期间,仍对当时在河南林县体验生活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李保元等人大讲江青、张春桥的劣迹丑行,并在致李保元的一封信中宣称:“我相信,我拿起枪来绝不会比拿笔差!如果他们 上台的话,我们就上太行山。”[3](P313)为了自己所信仰的事业,不惜鱼死网破,献 出一切,这就是战士诗人郭小川。
二、渴望掌握自己的命运
郭小川对于诗歌的衷情,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开始了。参加革命后,炮火硝烟的战斗生活,进一步激起了他的诗情。我们从他当年写下的《女性的豪歌》、《草鞋》、《老雇工》、《晨歌》、《疯妇人》、《给一个瞎子》等作品中可以看出,郭小川诗歌的起点也是比较高的。特别是其中的《晨歌》、《疯妇人》、《给一个瞎子》等,至今读来,仍缘其情真意切、新颖独到而令人感动。但也许正是与他奉献革命的战士人格相关,建国后直到1954年,郭小川基本上停止了文学创作,而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新闻宣传等一些更为实际的工作之中。郭小川心中诗歌精灵的复活,是在1955年调往作协工作之后。
按照郭小川自己后来向党交心时的说法,促使他奋力于写诗的主要原因是:到作协工作后,“在作家们面前有自卑感,感到某些作家‘看不起我’,以为‘哪里来了个毛头小伙子,居然来领导我们’,甚至有人说:‘作家协会的工作,让非作家来领导,简直是笑话。’”为了证明自己有文学才能,所以奋力于创作了,把创作放在第一位,把工作放在第二位了[1](P25—26)。在写于1974年的一份思想检查中,郭小川再次重复了这 样的意思:“我一到旧作协,就对那些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老作家’以及来自解放区 的部分‘老作家’抱着厌恶的态度,觉得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这种情绪,部分地是由 于我由做党的宣传工作刚刚改做文艺工作,对文艺黑线的那一套还不熟悉,但更主要的 是一种自大狂,认为‘自己是解放区来的,是有革命经历和战争生活经验的’,这是属 于个人主义的东西。因此我想,‘你们都以为自己是老作家,那又有什么了不起,我也 能写,不信,写给你们看看’。所以,我的创作动机哪里是为了以文艺为武器进行阶级斗争!而只是为个人‘争一口气’,为了名利。”[14](P313—314)郭小川这儿坦陈的,无疑是自己当时的真实心态。现在看来,这也实在算不上什么错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倒正是他不甘平庸的战士人格的体现。
以实际情况来看,郭小川上述谈及的“自卑感”之类,只不过是激发他投身创作的原因之一,另有一些重要原因是:与以往的工作相比,作为作协秘书长,他要迎来送往、与人谈话、协调各种人事关系、处理各种琐事,不仅纷乱无绪,且缺乏实效,这实在不合于他为革命做出更大贡献的志向。所以,到作协不到两个月,他就感到“心中逐渐增多了委屈的情绪”[9](P380)。更为令他苦恼的是,在处理个别被认为有问题的作家时,作为具体负责人,他希望慎之又慎,实事求是,但却遇到了各种压力,如“张海曾来催我要快些讨论陈企霞的问题。四面八方都把我逼住,真是叫人烦恼”[5](P34)。他虽积极充当过批判丁玲的枪手,但当他奉命在为“丁陈”一案写结论时,发现不属实,便提出应向被批判者“道歉”,结果引火烧身,遭到了一些领导人的指责。在“反右”运动中,他虽积极参与,但反对扩大打击面,并力图保护艾青、秦兆阳、李清泉等人却又无能为力。郭小川终于痛切地感到“文艺界太黑暗,是非不分,好坏不分,好人坏人不分”[3](P223),并产生了“实在不想干下去了”、“实在不喜欢在作协工作了”之类念头。
1959年6月9日,忍无可忍的郭小川,亲笔致信作协副主席刘白羽:“我到作协工作已将4年,最近越来越觉难以工作下去。说句丧气话,再这样下去,有沦为‘政治上的庸人’的危险。一九五八年是搞运动的一年,不去说它了。一九五七年到现在,我只到国外三月(差几天不到),到江西参加会议七天。此外一天没有出北京。今年半年已快过去,对生活中发生的新问题、新事物,毫无直接的接触。一天到晚被事务纠缠着,弄得身体垮下去,不能读书,不能下去,也不能认真写作。老实说,这个时期,我忧虑得很, 常常为此心跳,夜不成眠。”[10](P200)1959年6月15日,郭小川又致信邵荃麟,再一 次申明:“我过去总算是个豁达的人,并不是那么狭窄的,不知道最近为什么这样怪? 一天到晚,在一种又兴奋,又疲倦,又急躁的状态中过日子。我当然是极力控制的,但 仍不能奏效。天天扎针、吃药,也无济于事。这种情况使我苦恼异常。我真有点害怕, 是不是精神分裂症初期的症状?”[10](P202)可见郭小川当时对作协工作已厌烦到极点 。
然而,令郭小川没有想到的是,他致信刘白羽,本是出于对领导的信任,结果竟自投罗网,授人以柄。事后不久,刘白羽公开了郭小川的信,以此作为“个人主义”的实证材料,组织发动了对郭小川的批判。在批判会上,许多人响应领导号召,纷纷指责郭小川“重业务,轻行政”,“工作不好,还要偷懒”,“严重的个人主义世界观,长期潜伏,而且异常顽强”,“丧失了斗志,对工作也丧失了热情,以至厌倦”,“一本书主义,是受了胡风思想的感染,要成名成家”,“向党伸手,闹独立性”,具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6](P27—36)。在反胡风运动中,郭小川曾经写过一首题为《某机关有这样一位青年》的诗,其中写道:“他急切地要出人头地,/让他的名字天下流传。 ”“他计划了很久才有了新的发现:/写文章,成名可比较方便,/只要它在报刊上登几次,/就能赢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于是他好像着了迷一般,/写呀,写呀,写个不完。/工作时间他在构思,/听报告、开会都心不在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时隔不久,郭小川对胡风分子的批判,竟全部落到了他自己的身上。
郭小川到底是一位顽强的战士,遭到如此严厉的批判之后,他不仅没有被批判者的声威所吓倒,没有被上纲上线的大帽子所压服,也没有因“委屈情绪”而消沉,更没有因此而窒息他的创作激情,相反,他内心的诗歌精灵更为亢奋了。此时的郭小川,心里想的也许是:既然容不得其它选择,为了避免“沦为政治上的庸人”,那就只好通过写诗以自救了。他铆足了劲,在尽力干好工作的同时,以更为旺盛的激情,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投入到了自己所钟情的诗歌创作之中。按郭小川自己的说法,从1955到1962年,他在作协工作的7年,是心情最不愉快的7年,但在诗歌创作领域,却恰恰是他大获丰收的7年。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重要地位的长篇叙事诗《白雪的赞歌》、《 一个和八个》、《将军三部曲》以及《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望星空 》等一大批抒情诗,就是在这7年之内完成的。郭小川是战士,但他实在又是一位并不 愿轻易为别人所驯从的工具,而是一位向往人格独立,力图以个性化的方式介入历史, 渴望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战士。也只有这样的战士,才有可能同时成为诗人。
三、同情“右派”的“左派”
郭小川钟情于诗,而且有着成为大诗人的梦想。
从中外文学史来看,那些卓尔不群的大诗人,往往有着超越性的文化眼光,有着对现实的个性判断与独立思考,有着体悟与把握更具普遍意义的人生况味与人性价值的能力。但就郭小川的实际情况来看,文学素养的偏狭(主要是苏联文学影响),文化结构的粗疏(主要是阶级斗争理论),以及身为国家体制内的干部等因素,不仅影响了他的诗歌眼界的提升,而且在某些方面,与真正诗的追求实际是对立的。在郭小川的诗歌道路上,我们时常看到的正是由于这类对立所导致的苦恼和摇摆不定、莫知所从的窘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郭小川的诗歌才华。
郭小川在体察现实、思考问题的时候,常常守住的一个重要基点是:坚信党与革命领袖的英明正确,总在努力设法跟上时代的脚步。1952年9月1日,他在致夫人杜惠的信中说:“也许在我们这一代,还要经历一次人类最后的战争,在很长的岁月里,我们将会遇到许多困难以至挫折,但是我们应当永远使自己感到幸福。这就需要一种伟大的意志力,永远随着时代前进。”[7](P9)作为一位诗人,有时是需要追踪时代的,但一味地 追踪时代,又很可能丧失自我,甚至有可能陷入愚昧可笑的迷信盲从而不自知。“文革 ”前夕及“文革”期间的郭小川,正是犯了这样一种已经远离了诗人的错误。1969年1 月8日,当时一直在遭到批斗的郭小川,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往日的罪过,将 成为我永生永世的教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将是我的强大武器。伟大领袖毛主席呵!下 半生我将永远忠于您!”[11](P360)在“文革”期间的检查材料中,他曾这样揭露过《 人民日报》的“走资派”胡绩伟、安岗等人的罪责:1965年,当他采写的长篇通讯《小 将们在挑战》送《人民日报》后,胡绩伟阅后不满,认为:现在有一种倾向,打球打赢 了,就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那么,打输了怎么办?并亲自动手改掉了一些相关的句 子。1965年夏天,他曾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提议大张旗鼓地宣传工农兵活学活 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结果被安岗以“不搞声势”为由予以拒绝。他还谈到:“大 约1966年3、4月间,在一次编委会上,我批评了《人民日报》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 以后,仍不紧跟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宣传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的群众运动,比《解放军报》晚了六年。”胡绩伟、安岗等人当时的见解本是高明的, 他们也许已多少敏感地意识到了中国社会发展中隐含的危机,试图予以力所能及的抵制 。而郭小川不仅了无所悟,反而将其视为是“走资派”对他的刁难。郭小川的结论是:“在这几年中,我基本上没有执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而是 “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1](P124—127)。郭小川在特定情况下写的这类 材料及表白,当然不无争取尽快解放的用意,但他所谈的自己有过的那些做法,则是事 实。可以想见,陷入这样一种时代误区的郭小川,要写出真正优秀的作品,是绝无可能 的了。他后期的那些诗作,之所以空洞乏味,根源正在于此。
即使在为不少人称道的《团泊洼的秋天》这样的名篇中,也因其中“毛主席的伟大号 召,在这里照样有最真挚的回答”、“这里的《水浒》,已经开始受到众人的唾骂;/ 反对投降主义的声浪,正惊退了贼头贼脑的鱼虾”这样一类空洞无味的叫喊与不良的时 代印记,而破坏了整体诗境的完美。
而当郭小川不自觉地从诗人的立场出发时,产生的又是另一些想法了。1956年,他在一份不为外人所知的笔记中思考了艺术与政治、艺术家与党的领导间的关系,大胆地提出了以下主张:文学艺术的方向应有利于鼓励作家的创造性,“而不是限制他们的创造性,关于艺术方面的各种问题则由他们自己去探讨,去考验,党不应该干涉”。“不要把政治与艺术做机械的理解”。要信任作家,不要把他们看做小孩,不要对作家“耳提面命”。认为党的领导中的缺点“最主要的是粗暴干涉,要管的没管,主观主义,脱离艺术实践和脱离艺术规律的妨碍创造性”。对于当时盛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中,忽视真实性,而将“革命发展”解释为“理想的”东西,强调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之类,也认为规定太死,“妨碍个性独创性”(《关于文学的思考》)[12](P262—2 63)。在1960年4月25日写下的一份笔记中,则对如下重大问题表示了怀疑:“历史观点与革命观点的统一,是否就是历史观点?”“人道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否还有共同的东西?”“古典文学中的某些思想感情为什么能感动我们?”(《对历史观点的思考》)[12](P445—446)
即使在“文革”后期,在仍然受到“四人帮”追查的状况下,郭小川仍于私下里写下过一份颇有个人见解的学习笔记。在这份笔记中,他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对中国文艺界的问题进行了严厉批判。其中写道:毛泽东在论述“双百方针”时,曾批评了“一棍子打死”的做法,但“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从领导上说,没有造成这样的条件,人们一提意见,常常不分青红皂白,说成是‘破坏’,‘一棍子打死’的现象,层出不穷”。“现在重申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一个进步,但是,仅仅提一下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大肆宣传,需要造成气氛,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做,现在还看不出认真执行的迹象”。“前些时,帽子满天飞,信口开河地骂人家是‘坏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捞取政治资本’;对于有些戏,不但不许批评,连提点建议都可能被骂为‘破坏’以至于‘夺权’、‘反扑’、‘文艺黑线回潮’等等。这是为什么呢?根据主席的教导,这是因为‘非常胆怯’。”[12](P660—661,664)郭小川虽然没有敢于直接批评毛泽东,但对于他所批评的这些问题,他 不可能不想到毛泽东是有责任的。
据郭小川女儿郭岭梅的切身体察,1976年“天安门事件”之后,隐身在河南的郭小川,对毛泽东的有些做法已表现出明显的怀疑了。原来,对于此类敏感问题,孩子们是不敢与他谈论的,“一说,他就烦燥:‘你们不懂。’毕竟是多少年党培养成的,看到违背理想的事情,他是没想到的,心里苦得不得了。一直没理清矛盾心理,说不出口。我们说到‘主席做法做得不对’,他听了不说话;说到‘江青当政’、《红都女皇》事件,他也不说话;说到整老干部,他也不说”。郭晓惠也证实,“毛主席去世时,父亲的悲痛程度确实不如周恩来那一次,他反显得有些冷静”。他甚至私下里谈论过对毛泽东某些做法的不满[3](P316—317,324)。可见,郭小川的晚年,是在力图找回自己独立 思考的个性。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这样一种独立个性,由于与政治要求的背离,又往往是犯禁的。郭小川的《望星空》、《一个和八个》等之所以遭到批判,就是因为前者被判定为表现了人生的空虚,表现了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幻灭感,是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后者则被定性为宣扬了反动的“人性论”。
郭小川内心世界中存在的矛盾冲突,也导致了他在一些政治问题上的窘迫。比如在当年的“反右”运动中,郭小川当然也积极参加过批判别人,但他实际上又不无疑虑,正如郭小林后来在谈及他的父亲时说过的:“郭小川50年代中后期曾担任过中国作协部分 领导职务,他不可避免地卷入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旋涡。但是,参与整人绝非郭小川的荣 耀,相反,我们今天可以从他留下的日记中看到,一方面,他的历史限定性决定了他曾 是相当‘左’的,用那时的流行话语批判起同志时也曾声色俱厉,并且由于真诚被某些 权谋者蒙蔽利用过;另一方面,由于他所受到的人道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他在内心里又 不无矛盾——每当极左的理论与现实生活发生冲突时,他总有某种不安甚至因良心受到 谴责而痛苦。所以他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法以‘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 的办法来解脱一些人。据他生前回忆,冯牧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尽管有些人并不知道。 ”[13]郭小川又正是为此而曾被视为“右倾主义”,遭到过严厉批判的。直至1999年, 郭小川当年的老同事、87岁的林默涵对郭小川的评价仍然是:“他在左派,但他同情‘ 右派’。有自由主义,党性一般般。”[3](P167)由此可见,郭小川是曾力图坚持独立 思考的人格精神的。可惜的是,由于个人及历史的局限,郭小川终生未能达到完整而独 立的人格境界。
四、陷入绝望的诗歌精灵
晚年的郭小川,私下里这样评价过自己的诗:“有人把我排在第一位,我看太高。我排在二三位是可以的。”“在运用韵脚上,我属第一,没人能超过我。”(周原《生命的孤独》)[6](P281—282)这话说得也许有点儿过分自负,但我们仅从“祖国是一座花 园,/北方就是园中的腊梅;/小兴安岭是一朵花,/森林就是花中的蕊”(《祝酒歌》) 这样一类诗句中,是不能不敬重郭小川的诗歌才华的。仅从《月下》(《将军三部曲》 之一)中,那个大战之前的将军与秘书河边赏月的意境中,就可知道郭小川的胸中活跃 着怎样的诗歌精灵。另如《向困难进军》、《乡村大道》、《甘蔗林—青纱帐》等作品 ,就其篇章的凝炼、情味的真切、韵律的圆熟、诗句的畅达而言,至今看来,仍可堪称 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出类拔萃之作。甚至叫人感到,仅凭这几首诗,郭小川即可傲然卓 立于中国当代诗坛了。郭小川也是一位勇于独立思考的诗人,他的《一个和八个》、《 望星空》等作品中之于人性的、人生的沉思,也为同时的许多人未能企及。
但当我们通读一遍郭小川的全部诗作,又不能不吃惊地发现,在这样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笔下,更大数量的则是枯燥、平庸、肤浅之作,或是赤裸裸的战斗的呐喊与嘶唳,如《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发言集》;或是将政治理念与自然意象进行了生硬的粘合,如《致大海》、《昆仑行》;或是以“毛主席的教导/永远记在胸”、“继续革命呵,/‘斗私批修’无止境”,“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毛泽东思想威力大无穷,/一切领域中作统帅”之类政治口号的罗列取代了个性化的诗情体验,如《煤都的回声》、《出钢的时候》、《欢乐歌》、《花纹歌》、《长江上》、《祝诗》、《长江边上“五七”路》、《万里长江横渡》、《登九山》、《痛悼敬爱的周总理》等等,甚至连表达夫妻之间送别之情的《赠友人》,也毫无动人之处可言;或是寻 常可见的生活工作场景、人物、事件的分行讲述,如《闷热的夜》、《三户贫农的决心 》、《爆竹两三声》、《婚期问题》、《胜利矿纪事》、《老矿工的爱情》、《木瓜树 的风波》、《秋日谈心》、《他们下山开会去了》、《墓志铭》、《雨大松青》等等。 这类在郭小川诗作中占了相当大比重的一批作品,读上去甚至远不如他早年写下的《晨 歌》、《疯妇人》、《给一个瞎子》等动人。当我们谈到诸如“但是,你必须承认:/ 你原来的猜想并不符合实情”,“你看那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时时都在刻苦地、谨慎地从事筹划,/以保证生产和线路畅通”。“然而也许正因为如此,/你所见的风光比刚才还要明媚,/你平素所熟知的那些数字,/此时更像大山一般地雄伟”(《鞍钢一瞥》)之类乏味至极的句子时,甚至会感到诗人实在是在浪费自己的才华,糟蹋自己的诗名。
从中不难看出,郭小川,这位本是才华横溢、亦写出了一些成功之作的诗人,创作心态是不稳定的,他并没有坚定地把握住自己的创作航向。由现已出版的郭小川的日记、书信及其它相关材料中,我们还可进一步发现,在建国后的生命历程中,郭小川的确并不像他在某些诗中表现得那样乐观,那样信心十足,而是随着时势及个人境遇的变化起伏不定的,甚至曾多次陷入绝望。他曾在1956年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对于文学,我好像完全丧失了兴趣。我简直不想在这样的气氛里生活,而且对于未来怀着很大的恐惧。这里的一切气氛是不正常的,工作的改善是辽远而且渺茫的。许多人都在反对教条主义,但,其中有些人不过顺流而下,蛆虫已在他们心中生了根。我们为如许的人效命 ,又会出现什么结果呢?12时睡下去,睡不着。近来,精神简直是分裂了,生活失去了 平衡。我倒异常想望着战争的过去的日子,那时候要愉快得多。”[9](P468)
至“文革”期间,他虽然坚持创作,且仍不乏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独立思考,但在实际的创作活动中,却不知如何是好。1971年初,他在给儿子郭小林的信中哀叹:他曾将“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视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最重要使命,但那个“无产阶级司令部”并不买账,反而予以唾骂和封杀,令他痛苦万分,感到“完全不会写了”、“不知怎样写了”(郭小林《1976:一个政治诗人的最后痛苦》)[6](P231—232)。1974年6月 ,他在致妻子的信中诉说:“原来,我对于创作是较有信心的,因为我搞过二十年左右 ,正反面经验都有了一些,又学习了样板戏;所以,在前年回北京没有分配工作的情况 下,仍想为党、为人民做出一点贡献。但毒草剧本发生后,我实在不知道怎样搞创作了 。”[7](P231—232)
久经磨难的郭小川,晚年的心理似已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病态。据当年一起劳动改造过的诗人牛汉回忆,在湖北咸宁干校期间的学习会上,郭小川虽然很爱发言,但往往不着边际,头脑不清,啰里啰嗦,甚至常常说些错话、梦话,以至有人常常拿他寻开心。有一次,他对牛汉说:“现在的政治我真不懂呵。”“我政治上很幼稚,不像你想像得那么正确。”(牛汉《我与郭小川在改造与被改造的日子里》)[6](P328)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郭小川如此的精神困境呢?郭小川的夫人杜惠及子女们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郭小川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遵命式的战士,同时也在企图以个性化的方式介入历史,我们从郭小川的某些诗作以及他从诗人立场出发进行的某些大胆思考中,即可以充分地感受到这种个性色彩。但在否定个性的时代里,这种介入的悲剧命运又几乎是必然的。
这是真正诗人的悲剧,也是郭小川独具个性的悲剧。从人生背景来看,延安时代,他与妻子杜惠和叶群曾是同窗好友;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期间,与担任电影处处长的江青也算得上同事关系。如果换一个人,郭小川也许会成为中国政坛上的另一类风云人物。但在他的内心深处,早从战争年代开始,就活跃着浪漫纯真的诗歌精灵,和平年代到来之后,这迷人的精灵进一步成为他生命的主宰,促使他及早产生了对官场权术,特别是他所熟悉的作协机关中勾心斗角的憎恨,而将更多精力投向了诗歌创作。于是,诗歌精灵成全了他,使他未能陷入别类的人生误区,而是成为中国当代诗坛上一颗耀眼的 明星,并以其刚正不屈的人格为后人追念不已。但同时,诗歌精灵也未能引他走进人生 的福地,而是令他饱经了炼狱的煎熬。
郭小川是在一个历史正在发生巨大转折的关头猝然去世的。1976年10月18日,住在河南安阳宾馆的郭小川,正为粉碎“四人帮”的喜讯激动不已,准备返回北京时,因夜间服用了安眠药,点烟入睡时,不幸引燃了床上的泡沫塑料垫窒息而死。而几乎是同时, 北京高层领导正拟召他速速回京。且据可靠消息,已内定他出任文化部长或副部长。从 他生前已开始的对毛泽东的某些做法的怀疑中,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诗人如果得以幸 存,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繁荣文艺创作及个人的诗歌创作方面,也许会写下独具魅力 的一笔。念及这些,我们不能不更为这位诗人的不幸早逝而叹息。
收稿日期:2002-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