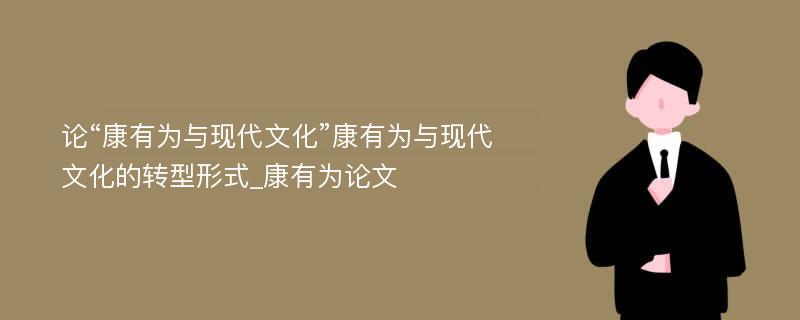
“康有为与近代文化”笔谈——康有为与近代文化过渡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康有为论文,笔谈论文,文化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过去强调康有为是近代中国的改革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是对的,但却忽视了他在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会通中西文化方面的历史地位。其实,他是一位学贯中西兼容古今的文化理论家、诗人和文章大家,是近代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继承者,更是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创造者。他为后世留下了近七百万字的文化遗产,代表着近代中国一个特定时段的文化理念和文化范式。用文化价值判断,康南海和章太炎、严复、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先哲,是中国近代文化的脊梁和文化英雄。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钱基博在评论近代中国新文学流派时说:“论今文学之流别:有开通俗之文言者,曰康有为、梁启超。有创逻辑之古文者,曰严复、章士钊。有倡白话之诗文者,曰胡适。五人之中,康有为辈最先,名亦极高;三十年来国内政治学术之剧变,罔不以有为为前驱。而文章之革新,亦自有为启其机括焉。”[1]可以说,康有为的文化语境,曾经是清末的主流文化,他创造了一个维新文化学派,开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河。
但钱氏的论断还停留在表象的认识层面,尚未触及这场文化变革的本质。我认为康有为发动的这场文化变革运动,不仅改变着中国人的文化传统、知识结构和感情形态,而且改造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其思想价值和文化影响,远远超过了其经济价值和政治影响。康有为开创的这种近代文化过渡形态,其内涵与特点是:兼容中华古今文化的优秀遗产,会通中西文化的陌生与隔膜,开掘近代新文化江河的源头,代表着中国文化冲出中世纪走向近代化的路向。
康有为从旧文化营垒中走来,以中华民族文化的承传者自命。他又生当大地交通开放,曾三周大地,游遍四洲,有机会吸取东西各国的先进文化。在这样的国际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康有为又具有追求真理醉心变革的文化品格,所以形成了贯通中西兼容古今的文化理念。他讴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但不泥古守旧,而是以发展的眼光批判的态度看待中国文化的前途。其文化表现形式为:在哲学上,向朱熹的理学挑战,批判程朱学派的“明天理,灭人欲”的封建文化理论,用西方天赋人权说反对蒙昧主义;在教育上,反对封建八股取仕制度,主张从封闭僵死的八股文风中解放出来;在文化上,突破了桐城派刻板的理论框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理论与文章风格,提倡文章以立言与立德并重,主张文从字顺,浅近直白,反对佶屈聱牙、艰涩难懂的文风。
在清末古文统治天下的局面下,康有为用半文半白的文字撰写奏章书稿、诗歌和文章,创造了一种从古到今、从西到东的文化过渡形态的政论文体,“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表现出自己的文化风骨。康有为述国政、陈风俗、兼容中西的文化过渡形态,是从他所处的时代潮流中催生出来的,其文激切而孤愤,其诗磊落而英多,发为中国近代新文体的滥觞。
戊戌变法失败以前,康有为了解和认识西方文化,以阅读中国人翻译的西书外国传教士办的中文报刊为主要渠道;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流亡异域,以直接的观察与调查研究为了解和认识西方文化的主要方法。他的文化体验是:“吾国人不可不读中国书,不可不游外国地,以互证而两较之,当不至为人所恐吓,而自退处于野蛮也。”[2]过去我们多侧重他热衷寻找君主立宪方案的研究,而轻视了他学习西方文化的努力。
首先,康有为创办了有别于官报的近代报刊《中外纪闻》和近代出版机构上海广智书局,可以说是中国人创办的民间最早的近代报刊出版机构之一,这种新式报刊的出现,使维新变法有可能形成一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化运动,通过这一新式文化传播媒体的文字宣传,使改革者比以前拥有了更广泛的读者;康有为创办了有别于秘密结社性质的近代学会不裹足会、强学会、保国会、圣学会等新式学会,把更广大的年轻志士包括有新思想的妇女组织起来,从事维新改革事业,甚至出现了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萌芽,使改革者比以前拥有了更广泛的听众。
其次,康有为创办了广州万木草堂、桂林广仁学堂、上海天游学院,亲编教材,亲自授课,把西方的学制与教学内容引入中国教育体制,开创了近代教育的新思维、新内容、新模式,引进了西方的进化论、民约论、科学论、社会学、国际法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内容,培养了一批文化精英。
第三,康有为逐渐放弃了传统注经式的文化思维传播方法,代之以近代科学逻辑思维的文化表述方式,撰写了一批面目全新文化作品。如果说康有为早期的文化学术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论语注》等书,仍然沿用旧的注经式的老套路,那么后期的《大同书》、《物质救国论》、《金主币救国议》等书,不仅更新了知识结构,而且吸取了近代章、节、目的综合网络著作方法,具有近代文化科学论证的特色。康有为在文化上表现出的一系列新问题、新理念、新关切,促使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将西学与中学割裂开来的文化隔阂得到一定程度的弥合,这是两种文化碰撞交流的必然结果。这些新问题、新理念、新关切,成为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的民族文化过渡形态的组成部分。
但是,康有为在学习西方文化时并未丧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他反对食洋不化和数典忘祖,表现出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自尊与自信。他既反对封闭固拒的文化守旧心态,也不赞成照抄照搬外国的一切文化观念,因为西方文化并非十全十美,不是一切都值得中国学习。他说:“吾久游欧美十余年,凡欧美之美善,有补于中国者,吾固最先提倡法之。然吾之采法,集思广义,去短取长,以补中国而已,非举中国数千年文物典章而尽去之也。”[3]
“五四”运动把科学与民主写在旗帜上,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争论,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之争。例如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无不带有这种反对封建文化的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科学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文化代表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
从戊戌年间到“五四”时代,康有为走的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思想路线,他主张废除八股建立学校,主张会通中西反对“中体西用”,主张科学救国反对泥古守旧。他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作斗争。他打着“尊孔”的旗号,以反传统的手法动摇传统的文化经典。他的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用考据的手法,判定二千年来文人学士信奉的儒家经典为刘歆篡改的“伪经”,又把孔子说成是一个为了“改制”可以任意“托古”的专家,给人以孔子创立的儒家元典中所提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可全信的疑问。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有为虽然从“尊孔”的原点出发,最后却走上了“损孔”和“贱孔”的悖论,从而拉开了“五四”以后否定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经典和疑古思潮的大幕。
据科学史家考证,康有为在中国文献中是第一个使用“科学”一词的近代学者。在海外流亡期间,康有为顶礼哥伦布,讴歌哥白尼,崇拜牛顿、伽利略、瓦特、达尔文、培根、卢梭、伏尔泰、约翰弥勒、笛卡儿等科学家。通过对这些科学家创造发明造福人类事迹的考察,他认识到西方社会是以智利为中心的理智型社会,中国社会是以仁义为中心的伦理社会。他从中西文化内在的结构上,揭示出欧美文化结构以智为中心,中国文化结构以仁为中心,并且意识到这种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关系国家民族的盛衰荣辱,指出西方国家大开民智而民富国强,中国统治者以礼义为干城而无以御侮。他认为“竞新之世,有物质学者生,无物质学者死。”[4](P7)而一切精妙物质皆出自科学发明创造,所以他主张中国应引进竞争机制,奖励科学发明,甚至疾呼:“科学实为救国之第一事,宁百事不办,此必不可缺者也。”[4](P90)在近代中国,康有为发出了“科学救国”论的第一声呐喊。
必须指出,把中国古代文化过渡到近代文化,是一个艰巨的文化使命,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康有为创造的近代理论体系和文化形态,必然打上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此种文化过渡形态自然是不完整、不健全、不完善、不成熟,甚至包含着封建毒素,这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在文化上的反映。但康有为辈是河上的桥,沧海的舟,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浪潮中,上下求索,笔耕不辍,推动着中国古代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过渡,像同时代其他先进文化人一样,从末代封建士大夫的僵蛹里终于幻化出近代文化最初的蛾蝶,昔日被封建古代文化视为“异端”的康有为近代文化清流,涓涓涌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的江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