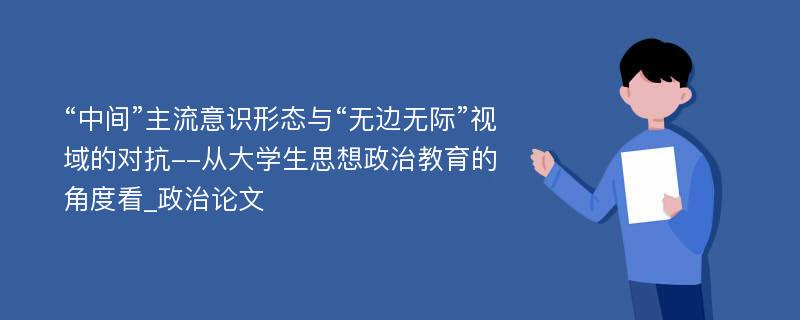
主流意识形态“在之中”与“无遮”视界的交锋——从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视角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视界论文,视角论文,主流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1)03-0124-05
学术研究崇尚百花齐放的氛围,强调平等的交流,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线的构筑不能简单等同于纯粹学理的探讨。一些学人强调学术“无遮”,此处可引为学界共襄学术盛举之谓,并无不妥。但如果将该概念直接引申到主流认知阵线的建设上,则会出现张冠李戴的乱象。我们研究的重点在于指出意识形态“无遮”的负面影响,分析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民众之中”建设的重要性。
一、“无遮”之惑:“大众文化”与“人性之爱”的稀释作用
“无遮”①本为佛教用语,寓意为没有遮拦,引申为不分贵贱、僧俗、智愚、善恶皆平等看待之谓。所谓意识形态“无遮”的侵蚀可区分为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为“外篇”,即西方意识形态身披着学术及流行文化的外衣对大众的侵蚀;其二为“内篇”,意谓面对西方文化的东渐,一些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自觉或不自觉地随着西方文化起舞。
在消费社会中,“大众”的概念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the masses”,而是指有消费能力的所谓精英阶层,即“时尚的、流行的、动态的、匿名的、非实指的、游牧的、年轻的、又带有某种不确定的具有主体意识的消费者”[1]。当下一部分高校大学生即属于西方消费理论中所谓的“大众”,对时代变化较为敏感是他们的特征,但他们对于西方文化毫无防备的爱慕也是令人担心的。西方意识形态进入国内主要是以大众文化的形式,它们利用我们一旦拒绝就等同于闭关锁国的途径进行传播,诸如影视作品、互联网络、奢侈商品等,大学生消费者已不单纯地把这些物件等同于某种使用价值,而是取飘浮于物之上的特定意义,正如鲍德里亚所指出的那样:
消费者与物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变化:他不再会从特别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等,除了各自作为器具之外,都含有另外一层意义。橱窗、广告、生产的商号和商标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并加强一种一致的集体观念,好似一条链子、一个几乎无法分离的整体,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因为它们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生产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2]
据统计,1994年至1998年,我国引进的外国有线节目共426部2533集,其中美国节目269部占全部外国节目的63.1%,1996年至1998年我国共进口外国电影片112部,其中美国片62部占55.3%[3]。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建立民用互联网开始,短短几年时间,就已普及到乡镇一级的地区,形成了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相连通的多媒体信息传递平台,上网计算机及网民人数逐年倍增,而且网民年龄结构总体上呈现出极强的年轻化特征。高校学子们在正式场所浸染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光辉中,在日常生活中则沐浴在西方文化的浴缸里,“回到马克思”与“奔向西方”的思想在大学生的脑海里一直相互撕扯着。
西学东渐在我国历史上有过数次大的浪潮,这里仅描述作为一个“失败者”的近代中国被迫接受西学的过程,因为该期西学的输入对于国人的政治观影响深远,由此而形成了由“君权”到“三权分立”再到“阶级理念”立国的思想转变过程。对于国人影响较大的当属西方基督教教义与儒学结合所产生的以人性之爱立国立人的学说,穿汉服宣传基督教义的利马窦的影像刻在了精英阶层的脑海里。基督教称其本质是“爱”的宗教,在其教义中宣扬上帝作为“一般”在创世之初将其本性传导到作为“个别”的人类身上,赋予人类爱与被爱的能力。耶稣说:“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②不仅要爱自己的亲人朋友,更要爱自己的敌人,“有人打你一边的脸,连另一边也让他打吧!有人拿走你的外衣,连内衣也让他拿走吧!谁对你有所要求,就给他;有人拿走你的东西,不要去要回来”③。此论与儒家所宣扬的“亲亲”、“尊尊”说颇为形似,既有悬置作为权威的“一般”,也强调“个别”的人伦之情。基督教所宣扬的“爱”可区分为两个层面的意义:一则爱上帝,这与儒家的“孝”道相似;二则爱世人,这与儒家的“仁”相似。“耶稣”身披着“孔子”的外衣取得了精英阶层的信任,精英阶层再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着西方的治世理论及为人之道。科技文明对于中国的实力提升是物理性的,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理念的冲击则试图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颠覆。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引进西学并高扬西学,同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自戮式的贬抑,一直是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基调。甚至是关于“什么是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都唯西方的标准马首是瞻,其结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西方话语霸权下的“失语症”状态。
当前的大众文化和“人性之爱”泛化都有稀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倾向,强调人伦之爱本无可厚非,但将国之基础建立在作为一种意识的“爱”之上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原则相悖。明显的事实是,我们在具体社会事务中一再呼吁民众要做一个源自儒家孔孟的仁爱、道家老子的慈爱、先秦墨子的兼爱精神基础上的“好人”,强调阶级分析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强调“仁者无敌”的民间意识形态由此而出现了理论的裂隙。一些学者强调泛“人性之爱”要提升为“彰显民族大团结,以民为本”[4]的大爱,这是一种试图将主流与民间意识形态合流的尝试,我们同样认为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一般”应显现于作为“个别”的民间意识形态层面之内。
二、“在之中”之盾:建制式灌输与内生性信仰的结合
“在之中”是海德格尔哲学中“此在”的先天机制,作为某种意识“在之中”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状态的对象是具有其特征的,它具有必须属于它(作为“它自身所是的存在之物”)的那些根本范畴的存在,以便它能够获得其他的、第二性的和相对的规定[5]。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民众之中”并非指一个现成之物在另一个现成之物“之中”的那种形成的“之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之中”不是因应外部存在引发出来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民众之中是已经澄明了的,“在之中”是一种存在者本身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6]。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民众之中可区分为两个层面分析,其一是由外及内的建制式的灌输,其二是由内及外的内生性的启蒙。
在第一个层面,我国学人对于意识形态理论及其防护之盾建设的理解,主要根源于列宁。“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在列宁那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意识形态”由贬义词变成了中性词,成了每个阶级用以武装自己的思想武器——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卑劣的谎言,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则是客观的真理。诚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列宁来说,意识形态涉及“不同阶级的利益和政府意识”,列宁特别强调“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峙”[7]。限于艰苦的斗争条件和险恶的学术环境,列宁生前没有机会读到《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使他无法全面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他只能把“意识形态”当成理论的标签和斗争的武器。这虽然在学理上存在缺陷,但它适应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需要”,因而其合理性的一面是“不容置疑的”[8]。但长期以来,“灌输”与“内生性信仰”被理解为两个现成东西的结果,出现了相互“之间”的破裂,民众自发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逐渐淡化。
可以对新中国的思想理论教育史作一个简要的回顾——此处专指学校教育,不旁涉社会运动对广大民众的专题教育——以检视我们主流意识形态灌输的重点在哪里。1949年12月召开的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明确提出,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是反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为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1950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强调,人民高等教育要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随后思想政治教育被正式列为高等学校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1951年9月,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华北地区各高等学校1951年度上学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论”等课教学工作的指示》,文中指出:消除政治课与业务课对立的错误做法,取消“政治课”的名称,各门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与其他课程一样列入整个教学计划,这可看作是纠正人为制造“科学中的科学”的一次尝试。之后的1956年,高等教育部将学生的考试考查作为评定学生成绩的唯一标准,排除了永无休止的社会运动对于学校教育的影响。1957年9月起,“红专”之辩在知识界广泛展开,形成了“红”在“专”前、无“红”必无“专”的教育基调。实际上,当时过多强调“红”,而忽视“专”,并以参加政治学习、政治活动的多少作为“红”的标准,甚至把“红”与“专”对立起来,认为非“红”即“白”。[9]1964年7月,全国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制定了“兴无灭资”作为政治课教育的基本指针。由此,意识之中的“阶级斗争”成为了现实中的“活物”,然后再以人造的“活物”制造更逼真的“倒影”。1978年中,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认为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程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区别于资本主义高等教育的重要标志之一,此后我国在科技文化、民主法制文化、市场经济文化、主体性文化观念诸多领域开放,大胆吸收经鉴别无阶级属性的西方世界的肯定性文明成果。
从以上追溯中可找到一条从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党根本指南到建国后30年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主线:救国图存的工具——巩固执政基础的工具——学术式的转向——红专之辩——兴无灭资——大胆开放,有甄别地吸收西方文明。虽然教育内容几经改革,教育方式也随政变迁,但其中一以贯之的红线从未更改:以阶级理念立党立国立人论,具体地说就是强调执政基础应建立在“阶级”之上,先进理论的阶级载体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区别是先进与落后,等等。这当然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基本纲领,但如何将其贯彻到终日为衣食住行忙碌的民众之中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第二个层面,所谓民众内生性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不仅包含着主流认知由外及内的影响力,也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传统文化对民众发生的潜移默化作用的因素。意识形态教化形式自古代开始就已存在:教育人民热爱自己的祖国、维护民族的传统价值观、维护统治阶级的威信,这些都属于意识形态机器的职能范畴。一句很普通的话,“我吃过了”,这不是意识形态式的辞令;“资产阶级的电影都不好”,这就有意识形态的意味。曼海姆认为,当意识形态这个术语表示“我们对由我们的对手所提出的各种观念和表象持怀疑态度的时候”,它所隐含的就是“有关意识形态的特定观念”[10]。一块丢弃在荒野的石头,我们可以任意处置它,但当它被用来雕刻成一位民族英雄的形象之后,我们就不能再任意对待这块同质但已变形的石头,这里就有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内。在中国史学典籍中言必称“英雄”是方便描述的需要,但目光“向下”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民众之中”的需要。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史来看,我们过于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非日常生活领域的理论传播,而面向普通大众的人伦日用层面的理论传播重视不足,其结果是自在的日常生活仍然处于自由放任状态,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意识形态的关系仿如油浮之于水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中生根开花,能够形成新的民族传统,不仅要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期待,而且要或多或少在民众文化中找到某种契合点。关于哲学与日常话语的交锋,马尔库塞有如下描述:
哲学中的精确性和明晰性不能在日常话语范围内达到。哲学概念以事实和意义的一种向度为目的,这种向度说明“外部”对于理解日常话语的根本意义,从而“从外部”来解释日常话语的原子化的词组或语词。或者说,如果日常话语领域本身变成哲学分析的对象,哲学话语就成了“元语言”。即使当它在不起眼的日常话语范围内运动时,它也仍然是对抗性的。[11]
马尔库塞给我们提了个醒,即如何协调元哲学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的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需要直面的一个论域。虽然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并不存在所谓“对抗性”一说,但仅靠灌输阶级理念极难使主流意识形态贯彻到民众生活的细微处,民众也落得一个乐逍遥——“国”与我何干?“家”才是唯一重要之物。可以考虑通过民众特有的“人伦”精神抓住民众心灵,这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实践发展的方向。
三、“无遮”与“在之中”的交锋:厘清界限与甄别处理的原则
所谓意识形态“无遮”实为以伦理名义侵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静悄悄的尝试。如果禁止“无遮”概念的泛化,我们可能将面对两种指责:第一个层面是违背人伦天性,强行对普通大众贴上“阶级”的标签;第二个层面是将学术与主流意识形态完全捆绑在一起,罔顾学术界对于“双百”美境的憧憬。
在第一个层面上,以人性之爱立国与我们的主流认知是相悖的,以“文化”解读人类社会历史同样与唯物史观基本点不容。我们一直认为,国不能建立在意识之上,上层建筑也不能以所谓的泛爱的名义刻意去淡化阶级界限。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可以找出很多的理论根据,例如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嘲讽,又如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再如列宁对第二国际的批判等。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说过:
按照费尔巴哈的看法,宗教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关系、心灵的关系,过去这种关系是在现实的虚幻映象中(借助于一个神或许多神这些人类特性的虚幻映象)寻找自己的真理,现在却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在我和你之间的爱中寻找自己的真理了。[12]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不赞同利用所谓的“爱”来构筑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那只能导致空想,对于既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如果意识形态也实行“无遮”,那么等同于自行解除武装。从马克思到列宁,从《资本论》到《伟大的创举》,革命导师们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制订了一些原则。澄清事实、重新擦亮这门学说的“门牌”,这是对模糊阶级界限的各种企图的最好回击。阶级学说对国人来说似乎是一个不太愿意提起的问题,记忆中的伤痛依然没有远去。但是,如果我们因噎废食,将造成更大的伤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这一现象,在那个除了反对统治阶级以外不需要维护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的阶级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灭的。[13]
从1917年“二月革命”到“七月革命”,这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政权并存于俄国大地上的历史阶段。在此期间,列宁关注的三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战争问题和国家制度问题。其实核心就是一个问题——如何在全俄国范围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没有执政权,其他两个问题都无法解决。这时候列宁对阶级理论的解读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在必然联系,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坚持,也是基于当时俄国现实斗争的需要。列宁指出:
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14]
从以上言论可以看到革命导师们对于划分阶级界限的重视程度。当然,没有人会否认人伦之爱的重要性,更不会有人想再回到“亲不亲,阶级分”的年代,回到没有电影与电视的“纯红”岁月。
第二个层面的问题颇为复杂难解,如何做到既保持学术研究的欣欣向荣、避免思想纪律化,又使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浩荡江河般涌进国民的脑海中,此题尚待具有大智慧的学人来解。1954年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1965年吴晗的《海瑞罢官》等历史事件均令人印象深刻。苏联哲学家奥伊则尔曼认为哲学的特点在于没有获得真理的一致声望,在于见解的分歧不断扩大,哲学是“唯一一个这样的知识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其优秀代表人物之间的相互一致与其说是常事,不如说是例外”[15]。与此相关的历史事实是,我们的学者相互间发生争论倒成了例外。类似于中国古史的撰写,我们的主流认知读本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层累”地叠加,启发民智的学术型哲学“层累”地消失。学术界一直深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如莫尔所描述的乌托邦社会那样,可以自由地讨论学术问题、任由思想翱翔在彼岸世界里[16]。
在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进程中,意识形态的斗争是必不可少的。众所周知,人们承认阶级斗争的三种形式——经济形式、政治形式和意识形态形式即理论形式。这三种斗争形式始终是有内在相互联系的,与经济竞赛和政治斗争一起,争取人的智慧和思想的斗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肩负着在思想上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重任,实践型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在“无遮”视界中,学术探讨无“正确的”提法,只有政治上有“正确的”意见,对于分辨能力尚待提高的高校学子,强调政治上“正确的”毫无疑义是正确的。
注释:
①参见《大佛顶首楞严经·卷一》,钦仰如来,开阐无遮,度诸疑谤。
②参见新约·约翰福音13:34.
③参见新约·路加福音6:2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