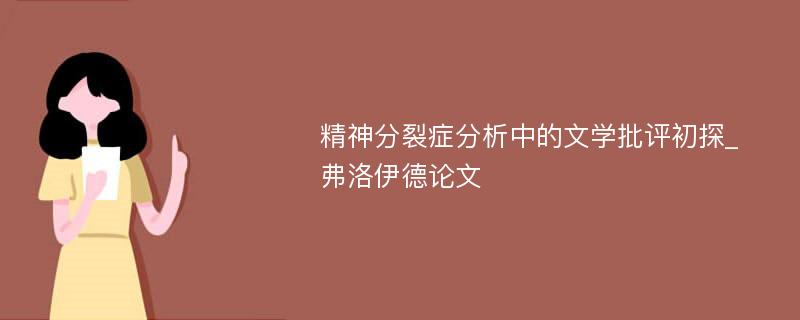
精神分裂分析文学批评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精神分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精神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是当代法国著名激进派理论家吉尔斯·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菲力克斯·瓜塔列(Felix Guattari)在70年代初中期提出的反弗洛伊德(及反拉康)精神分析的后现代批评话语,其理论阐述见之于两位合著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的第一卷《反俄狄浦斯》(L’AntiOedipe,1972),其实践运用见之于第二卷《千座高原》(Une MillePlateaux,1980)。德勒兹在五六十年代就曾以研究休谟、康德、尼采、柏格森、普罗斯特等哲学家蜚声法国文学与哲学界;瓜塔列也从50年代起从事弗洛伊德、特别是拉康的精神分析实践,两位都是激进的政治活动家,都参加过1968年5月的法国学生运动。通过社会实践和理论反思,他们发现了传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及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中俄狄浦斯化的“家庭中心主义”的局限性,主张把精神分析推向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生产层面,给我们提供了从发生于社会微观/宏观无意识中的“欲望”流动来透视社会机制与个体心理的新的透视法。这一方法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它孕育了一种新的“颠覆性的”创作和阅读理论,而且在拆除了西方话语传统关于世界表征的“超验能指”之后再次提出了文学应该扮演的角色问题,[①a]正如作者自己所言:
作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沿欲望流体而动,并促其流转。这一流体拆散作品里普遍的、暴君式的能指,必定在地平线上培育出革命的机器。[②a]
这一任务靠作家与读者的参与,需要一种新型的读者将文本变成欲望机器,最终变成他们所称的后现代的“革命机器”。本文试图对两位作者所阐述的精神分裂分析理论进行一些探讨,并以卡夫卡和劳伦斯的创作和解读为例将这一透视法引入文学阐释。
一、关于无意识和欲望的争议问题:反弗洛伊德、反拉康
如果说精神分析学说是“一门关于无意识的科学”的话,那么精神分析方法就是一种研究无意识活动的方法,无意识理论也就是精神分析文艺学方法的基础和核心。六七十年代以后,传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进入了一个后精神分析阶段,一些西方学者纷纷把弗洛伊德理论引入别的理论框架,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模式:如拉康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克莉斯蒂娃为代表的女权主义理论以及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理论等。德勒兹和瓜塔列的“精神分裂分析”也是这一后精神分析阶段的产物。
与精神分析一样,精神分裂分析关注的焦点也是无意识和欲望问题。传统的弗氏理论把无意识看成是混乱无序的、原生状态的、前语言的混沌体,属于个体心理的一块实体区域(弗氏经常把无意识称作das Es Unbewusste,德语的dasEs表示具有实体性的东西或区域),它的基本内容是源于“缺乏”的利比多(即性欲),寻找满足,在主体社会化过程中受到压抑。但弗洛伊德的理论存在一种逻辑性的矛盾,因为他把无意识和欲望既看成“缺乏生成”又看作“原始心理能量”;拉康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语境中重新阐释弗洛伊德理论时坚持了无意识和欲望源于“缺乏”的说法,但否定了弗氏关于无意识是“混乱无序、原生状态、前语言的混沌体”的观点,认为无意识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个体社会化(符号化)过程的产物。拉康说,“无意识的缺乏(gap)是先于存在的(pre-ontological)”,[①b]也就是说无意识和其基本内容(欲望)产生于“缺乏”,在前语言阶段并不存在。在他1936年的一篇讲演稿《心理分析实践中所揭示的主体功能形成的镜象阶段》(英译本1949)中,拉康证明了无意识只有被语言“格式化”才能产生的结论,从而纠正了弗氏把无意识欲望既看成“缺乏生成”又看作“原始心理能量”的这一逻辑性矛盾,坚持了唯心主义的一元论观点。拉康进而认为“它(无意识)既不是实体(being)也不是非实体(nonbeing)”,[②b]而是一种类似于语言的话语结构,正如拉康所言:“无意识既不是原生的也不是本能性的,它基本的成分仅仅是能指的成分。”[③b]德勒兹和瓜塔列反对西方传统自柏拉图到黑格尔、康德,特别是弗洛伊德和拉康关于“欲望源于缺乏”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和虚无主义的)观念”,追求他们所称的“唯物主义的精神分裂心理学”。[④b]两位认为,无意识既不限于个体心理的一块实体区域,也不是“类似于语言话语的符号结构”,而是一个微观与宏观的能动过程;其内容既不是弗氏所讲的具有生理本能性质的“欲望”,也不是拉康所讲的具有基于生理本能但又超越生理需要的“欲望”能指,而是一种具有积极创造性的、“完全唯物主义”的世界本源——“欲望”。由此看来,德勒兹与瓜塔列消解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个体无意识和社会的宏观无意识的差异,把二者视为一个能动生产过程,欲望就流动在这一过程之中。两位作者借用作家阿塔德(Antonin Artaud)“没有器官的身体”(The body without organs,即没有组织结构支配的身体)和“碎片客体”(Partial objects)来认识欲望的本质。正如他们所说:
它(欲望)无论何处都在起作用,无论何时都顺利地发挥功能,虽有时是一阵阵或不规则的。它呼吸、它发热、它吃饭、它通便、它乱动、它性交。[⑤b]
应该指出的是,欲望只是物质流动,它的唯一客观性就是“流动、冲撞”,就象江水一样在本质上既非是好的亦非是坏的,既可以使主体走向“解放”亦可以使主体走向“毁灭”。
德勒兹和瓜塔列这一关于“欲望”作为本体存在的观念来源于现代法国反唯理主义哲学大师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的“生命冲动”。柏格森把“生命冲动”既看成一种作为世界本质的生命之流(一种绵延的、运动的、流动的宇宙生命之流),又当作一种创造世界及历史万物的宇宙意志。这一“生命之流”在德勒兹和瓜塔列具体化为“欲望”,它才是世界的本质,是维系人类生命唯一积极的、创造性的冲创力量,它具有背离中心性、非整体性和能动性,“在其本质上具有颠覆性”;[①c]它并不源自于缺乏或某种失去的客体,它可以产生能量、推动物质和精神生产,是一种自由流动的“恒动机器”,而且又具有时刻冲击和颠覆社会表征的功能,总是处于某种“游动的和多元的”逃脱状态。因此,所谓文明的进步就是驯服和压抑欲望,就是把欲望“领土化”(reterritorialization)在某种封闭的结构里(从原始的乱伦禁忌到现代的婚姻制度),所以“给欲望编码(即封锁欲望)是社会的首要任务”。[②c]因此两位作者反对弗洛伊德和拉康心理学为欲望进行“家庭编码”的俄狄浦斯情结,因为俄狄浦斯情结承认社会抑制和心理压抑的合法性,承认文明的进步依赖于对欲望的封锁,正如弗洛伊德所说:
我们相信人类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之下,曾经竭力放弃原始冲动的满足,将文化创造起来,而文化之所以不断地改造,也由于历代加入社会生活的各个人,继续地为公共利益而牺牲其本能的享乐。而且所利用的本能的冲动,尤其性的本能最为重要。[③c]
在《反俄狄浦斯》第二章《心理分析与家庭中心主义:神圣的家庭》中,作者列举了心理分析方法论的五条谬误:1)欲望家庭化的主观推测性,因为俄狄浦斯情结武断地认为欲望只是利比多性欲,被认为存在于“父亲—母亲—儿子”的三角结构及关系中;2)俄狄浦斯情结对欲望双重束缚(double bind)的反人性,即俄狄浦斯情结通过社会抑制和心理压抑对欲望进行封锁从而阻碍了人类的创造性;3)心理分析实践中俄狄浦斯情节的“双重一元性”(biunivocality),即弗洛伊德把欲望既看作是“缺乏”的产物又看作“原始心理能量”的逻辑性矛盾;4)心理分析对欲望的改装和歪曲的非法性,即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本身扭曲了无意识的本质和能动的创造性;5)俄狄浦斯情结化是造成人类神经机能症和精神分裂的根源。作者在向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自我心理学宣战就是要颠覆西方哲学和心理学传统中的“自我”观念,并对传统的人性、超我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彻底清理人类心理中的“太多的人类因素”。[④c]至此,德勒兹与瓜塔列终于颠覆了心理分析理论的“自我”观念,使欲望从“家庭中心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流向社会。但两位作者并没有重新把欲望锁在“社会”这一宏观表征物上,而是进而分析了社会制度与话语权力对欲望的非法压抑本质。在第三章《野蛮人·原始人·文明人》中,作者通过对原始婚姻和生产方式的分析,发展了第一章“消解”自然与社会及自然与人界限的观点,把宇宙万物看作一个欲望流动的无序体。德勒兹与瓜塔列指出:在原始的社会形态中,婚姻首先是一种两个非血统族之间的欲望交换,“乱伦禁忌”之后这种交换通过“联盟式”(alliance)使得家庭直接来源于社会,又通过联姻繁殖(filiation)使家庭与社会形成一种复杂的、纵横交错的“联盟+繁殖”生产过程。所以家庭与社会的界限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传统弗洛伊德理论的“追根求源”(regression)实际上是“一个无限求源:父亲曾经是儿子,儿子将会是父亲”,所以“俄狄浦斯首先是成年人的妄想狂,然后才是儿童的神经机能症症状”。[⑤c]所以,并非压抑欲望生成了文明,而是欲望本身创造了所有的社会和历史现实,又是社会内在结构的组成部分。他们的这种“唯物主义”欲望理论把弗洛伊德心理学拉出了家庭中心主义的藩篱,并推进更广阔的社会环境。因此,他们把“宏观社会机器”的宏观分析与身体及它的“微观欲望机器”的微观分析结合起来。把欲望生产与社会机制结合起来,得出了文化、家庭、社会/个体、及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本身都根植于“欲望的物质性和创造性”的结论。
二、精神分裂分析文学阐释:以卡夫卡和劳伦斯为例
反俄狄浦斯就是反自我,精神分裂分析就是对精神分析的“反叛”,就是冲破社会与个体心理俄狄浦斯化的表征系统;分析对象不是对欲望的压抑,而是欲望的“逃脱”轨迹;不是俄狄浦斯化的三角关系无意识而是作为过程的能动无意识,正如两位作者所说:
精神分裂分析是一种先验分析和唯物分析,它的批判性的意义就在于对俄狄浦斯的批判,或使俄狄浦斯进入自我批判。它试图探索一种先验的无意识而不是形而上的无意识;物质性的无意识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无意识;分裂的无意识而不是俄狄浦斯化的自我无意识;非表征性的无意识而不是想象性的无意识;现实的无意识而不是象征性的无意识;机械性的无意识而不是结构性的无意识——最后,微观的、实体性的、解剖性的无意识而不是宏观的、群体性的无意识;生产性的无意识而不是表现性的无意识。[①d]
精神分裂分析的任务就是发现利比多在社会语境和个体心理的投资本质,“颠覆其表征系统,将其变为欲望生产。”[②d]
凭借这一分析方法,作者试图历史地分析不同的社会形态对欲望的疏导和控制方式:把这种驯服、疏导、控制、压抑欲望创造性的过程称作“欲望领土化”(territorialization,或欲望“编码”,即把欲望封闭或限制在某种社会单位内如家庭);而把欲望逃脱各种社会限制和封锁的过程称作“欲望非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或“欲望解码”)。作者的意图在于通过抑制性的社会符码(如国家、法律、道德)进行解码,使欲望能够超越限制性的心理和空间疆界,恢复它原有的创造性真面目。在他们的分析中,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并不是一种心理障碍,也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主体在社会中一种潜在的、革命性的心理状态,一种欲望冲创的产物。作为一种个体与社会心理的离心过程,主体总是试图逃脱社会的现实原则,挣脱社会符码资本主义压抑性的自我与超我的限制,逃脱俄狄浦斯化的陷阱。所以,关于欲望在社会宏观无意识和个体微观无意识中逃脱轨迹的分析方法就是两位作者所说的“精神分裂分析”,文学阐释活动也就是一种“欲望解码”活动。在德勒兹与瓜塔列自己的文学阐释中,他们引入了一些新词语:《反俄狄浦斯》中重复提到的“欲望非领土化运动”在《卡夫卡:走向少数人话语的文学》(1975)中变成了另外一个新词:“根状形态”(rhizome);《反俄狄浦斯》中“分裂分析理论”所设想的欲望存在的两极——分裂极(schizophrenia)和妄想极(paranoia)在《千座高原》中修正为欲望的三元轨迹:严格轨迹(rigid lines),可塑性轨迹(supple lines)及逃脱轨迹(lines of escape)。[③d]
“根状思维”(Rhizomatics)是精神分裂分析的核心概念。作者采用植物学的专门词语“地下根”一词作为隐喻来意指欲望的非中心化轨迹及多元性的表现形态。从植物学上看,rhizome一词意为“地下茎”、“根状茎”、“地下根”,与主根及胚根相对立和联系着,所以与树的结构不同,它具有一种随意性、纵横交错、紊乱无序的形态,这里作者暗指某种多元性的、非等级化的、非领土化的轨迹图式。这些轨迹图式与其它图式相连续形成了一种“通畅”的空间,使得作为生命本源的“欲望的自由流动”成为可能。这种“根状思维”在尼采的《快乐的知识》(1882,其中第五篇于1886年续写)和《反基督》(1888)等著作中就曾出现;两位作者的《反俄狄浦斯》与《千座高原》等著作当然也是“根状文本”。思维随欲望在无数的方向上自由流动,没有开始,也没结束,更没有中心,总暂时存在于一个能动的过程之中。在“根状思维”的精神分裂分析中,分析对象就象一面手掌,上面有许许多多纵横交错、粗细不匀的掌纹,其中有三条基本掌纹线:第一种被称作“严格性弧形纹线”(the rigid segementary line),它是一条粗线,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机制中通过二元对立构成某种稳定的、规范化的心理结构,个体也由二元对立的观念建构出来(如男人/女人、黑人/白人,奴隶主/奴隶、资本家/工人等);第二种被称作“可塑性弧形纹线”(the supple segementary line),它是一种背离“严格性弧形纹线”的欲望微观运动轨迹线,总是冲撞和干扰第一种线性结构和规范化图式。处于这一条线上的主体总是具有两种特征——双重逃脱现象,如弗洛伊德所分析的“狼人”总是试图逃脱,但同时又倾向于回到俄狄浦斯情结的三角关系图式中;在作者分析的卡夫卡的故事中总会遇到人试图变成动物、甲虫、猿人、老鼠,另一方面动物又总试图变成人;第三种被称作“逃脱线”(lines of escape),即欲望冲创宏观/微观符码的“非领土化运动轨迹线”。欲望主要占据这条纹线,它是一条积极的创造性的纹线,同时也是一条毁灭性的纹线,如劳伦斯的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主人公康妮在这里得到了“重生”;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在这里走向了死亡。
在现代欧洲文学中,卡夫卡的小说艺术始终充满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究其原因是卡夫卡的作品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根状结构”,作品的任何一部分都可以和其它部分连接,读者可以有许多方式进入卡夫卡的作品,而且这种“根状结构”在本质上是异质性的,能使作者和读者打破由传统的“超验能指”所建构的主体性,使欲望能够在个体与社会语境中自由流动,更有甚者,这一结构甚至可以颠覆文学的表征系统本身。卡夫卡生活在他自己所说的“孤独和友情的疆界”上,一方面作为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个犹太人处于“少数者、边缘人”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用主导语言(德语)创作,所以他总是试图逃脱欧洲文学传统和语言的桎梏来创造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而且又对文学本身充满怀疑,进而视文学为废物,因为他对天堂的理解就是“没有书的地方”。[①e]所以卡夫卡的艺术本身就是对任何抑制性的社会符码(文学的、社会的、语言的)的“非领土化”。这一点只要互读一下1890至1928年关于维也纳和布拉格的背景的文本就可得出:当时政治斗争异常激烈,有位市长就说大学是一个“充满颠覆性观点、革命、无神论、反民族主义的温床”;[②e]老一代人把年轻一代人视为“颓废、疯狂、病态”,年轻人很少正面还击,而是接受这一暗示,在他们的小说、戏剧、诗歌中把“颓废的人、疯狂的人、病态的人”表现为时代的英雄;当卡夫卡的父亲把卡夫卡称作“甲虫”时,卡夫卡没有正面反对,而是创作了《变形记》,描述了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一个“甲虫”。这一变形似乎不合时代、荒诞无稽,却是卡夫卡对传统符码的关注。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有一股力量(非经济的、非政治的、非意识形态的)使他们总是在逃脱所谓“合乎理性”的资本主义机器,变成在传统看来是“消极、悲观、焦虑、甚至丑陋”的精神分裂者,但对于卡夫卡来说,这才是真正的生命存在、真正的欲望生命体。1915年卡夫卡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要是我在1912年离开(布拉格)那会发生什么呢——会拥有我所有的力量,会带着清晰的头脑,不被压抑生命的力量吃掉。”[③e]
卡夫卡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畸形古怪、内心充满孤独、苦闷、恐惧的小人物形象,但这是外部表征,隐藏在这些小人物深层无意识中的那个俄狄浦斯化的社会机器造成了他们的荒诞、畸变、飘零,就是这些分裂的主体在“变成”和“转形”的过程中时刻清洗和冲撞人类内心世界那“太多的人类因素”,因此这些小人物的逃脱过程就是对俄狄浦斯的“非领土化”,就是在冲撞资本主义宏观社会符码的同时反对“自我本身”。“逃脱线”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具体表现为个体的心理和生理感觉,欲望生产从一极走向另外一极,虽然有时受阻,但总是在逃脱,逃脱过程形式多样——如变成动物、变成女人、变成儿童等。应该指出的是,卡夫卡的人物关系也是一张纵横交错、混乱无序的“根状结构”,如《判决》和《审判》中代表法律的符码——法院——充满各式各样的不同政见者,渴望法律时欲望被激起,在整个法律和政权圈里没有正义的“超验法律”,所存在的只有一个内在的“欲望场”,从而人物形成了一个永远不停地扩散的大序列。每一个人物实际上是功能性的“符码”:如在《城堡》中,每一个人物都与城堡有关,不仅有法官、律师、官员、警察、甚至被告,而且有女人、小女孩、画家、K自己;布劳克同时聘用6个律师,提特若里绘出一系列相同的画,K也遇到同样类型的怪诞的年轻的女人,……大系列生成次系列,每一个扩散都是一次“欲望的冲撞”。
在此同时,卡夫卡还嘲弄俄狄浦斯三角关系。卡夫卡的主要作品写作于弗洛伊德的高峰时期:《变形记》(1912)、《判决》(1912)、《美国》(1912)、《审判》(1914)、《城堡》(1922);弗洛伊德的主要著作是《梦的解析》(1900)、《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1901)、《玩笑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快乐原则之外》(1920)、《自我与伊德》(1923)。两位都生活于同样的维也纳和布拉格德意志的政治氛围中,弗洛伊德自称发现了“研究无意识的科学方法——俄狄浦斯情结”,而卡夫卡却发现了“欲望的逃脱”,他运用人物的系列扩散不断地消解俄狄浦斯的三角关系,消解两个官僚依附一个上级的三角关系,使整个权力的符码呈现一种错综复杂的“根状”关系网。所以卡夫卡的作品在每一点上都可以进行颠覆性的阅读,从而是“暴君能指”——法律、城堡、造船工业可以被粉碎,整个社会机器显露出恶毒虚假的本质。作为“后尼采主义”的典型作家,卡夫卡充满尼采的“疯人”思维模式和一股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情绪,在噩梦般的景象中,他解构了社会符码对生命的非法压抑和封锁,从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主体心灵深处俄狄浦斯殖民化对主体的扭曲和生存的恐惧。
上文提到的劳伦斯的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女主人公康妮对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和道德符码的“逃脱”也是德勒兹和瓜塔列“欲望非领土化”的典型例证。康妮生活于贵族之家,但俄狄浦斯化的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并没有封锁住她对真正生命的追求,她痛恨克里福德一类“干枯的”、“死鱼一般的绅士”,“他们的心就象赛璐珞一样冰冷无情”,从这种虽生犹死的生活中挣扎起来,在与梅勒的感情和肉体结合的热烈关系中重新感到了生机的恢复和生命的冲动,用康妮自己的话说,是“一个真正的生命,一个真正的女人”。[①f]这里,欲望对社会符码的冲创是巨大的,每当康妮迎着早春晚风穿过从寒冬季节苏醒过来的树林从男爵府邸走向梅勒的小屋,都感到这段路程是从死走向生命的旅程。
结束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何如?
德勒兹和瓜塔列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微观/宏观分析,通过透视发生于社会微观层面的欲望、无意识、身体的社会控制方式,发现了社会政治制度与利比多机制的微妙关系,这一方法把精神分析拓展到更广阔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生产层面,并沿着社会中的某些实体(如资本、劳动、权力)运行轨迹跟踪和解构欲望被“殖民化”的过程,展示了作者对主体分析和政治分析的真知灼见,在文学批评理论方面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但精神分裂分析无论作为一种作者自称的后现代主义的“革命”理论还是社会透视方法都显示出一些逻辑性矛盾:一方面作者反对任何“表征”,把他们自己的理论(作者自己反对这一词汇)称作“实验的政治学”,而不是“阐释的政治学”,但是他们的整个理论却是发现于文本的“表征系统”之中。《反俄狄浦斯》和《千座高原》大量堆积哲学、历史、心理学、文学微型文本,在文本的“拼贴”之中使之具有一种“精神分裂者话语”的性质,从而消解了他们所力图阐释的“实验的政治学”的透明度,以致福柯才在序言中说:
把《反俄狄浦斯》当作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来阅读是错误的……,我们决不要指望在这些格外离奇的新词语和令人震惊的概念中找到一种“哲学”……我认为《反俄狄浦斯》最好当作“艺术品”来读。[①g]
笔者认为,他们的“实验的政治学”也是一种文本拼帖,仅停留在文本的表征系统中,而没有任何的“实验意义”。究其原因还是作者对其解构理论的核心概念——“欲望”——的认识上,按照他们的论述,欲望似乎是一种“物质”,但却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物质概念,在本质上既非好的也非坏的,而是能动的和生产性的;欲望机器既可变成“革命性的”也可能变成“法西斯性的”;逃脱过程既可能变成解放过程也可能变成毁灭过程,然而这一观点就象“欲望源于缺乏”一样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作者似乎对“欲望妄想极”有一种“妄想恐惧症”(paranoid phobia),而对“欲望分裂极”有一种“分裂狂热症”(schizophrenoidmania)。再者,作者在使欲望本体化(欲望是客观实在)和历史化(欲望作为历史和社会的内在构成部分)的分析过程中也表现出一些逻辑性的混乱,不仅臆造了欲望的社会表征史,而且臆造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怪圈,一种当代西方知识分子特有的怪圈:一方面他们反对任何压抑性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反对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其结果还是坠入他们试图避免的无政府主义的窠臼。阅读《反俄狄浦斯》、《千座高原》等著作给笔者的感受就是这样,我们可以从任何一点进入他们的作品,从作品中可以读出一切,福柯把它看成是“非法西斯生活方式导论”,看成是“伦理著作”;詹明信把它看成是“政治学”;更多的人则把它看成是“一种新的精神分析方法”,于是精神分裂分析也只能是表征系统再分析,总是逃脱不了他们自己反对的“领土化”。更应该指出的是,作者追求的这种无序状、总是在流动中的“游民般的思维方式”在当代商品化和物质化的社会中总逃脱不出“生存”二字。
注释:
①a Elizabeth Wright," Another Look at Lacan and Criticism",inNew Literary History,1988(spring),P.622.
②a Gilles Deleuze & Felix Guattari,Anti-Oedipus,trans,RobertHurley,Mark Seem,and Helen R.Lane,(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133.
①b Jacques Lacan,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ed.Jacques-Allan Miller,trans.Alan Sheridan (New York:Norton,1977),p.29.
②b 同上,第30页。
③b Jacques Lacan,Ecrits:A Selection,trans.Alan Sheridan (NewYork:Norton,1977),p.147.
④b Deleuze & Guattari,Anti-Oedipus,p.25.
⑤b 同上,第1页。
①c Deleuze & Guattari,Anti-Oedipus,p.116.
②c 同上,第139页。
③c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中,本文转引自胡经之、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8页。
④c Deleuze & Guattari,Anti-Oedipus,p.xii.
⑤c 同上,p.274.
①d Deleuze & Guattari,Anti-Oedipus,第109—110。
②d 同上,第270页。
③d Giller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renia (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92),p.5—8.
①e Malcolm Bradbury and James Mcfarlane,eds.Modernism (Penguin Books Ltd.,1976),p.131.
②e 同上,第121页。
③e Bradbury and Mcfarlane,eds.Modernism,p.133.
①f D.H.Lawrence,Lady Chatterley’s Lover (Bantam Books,1968),p.187.
①g Deleuze & Guattari,Anti-Oedipus,p.xii.
标签:弗洛伊德论文; 精神分析论文; 文学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俄狄浦斯王论文; 生命本质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德勒兹论文; 社会论文; 无意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