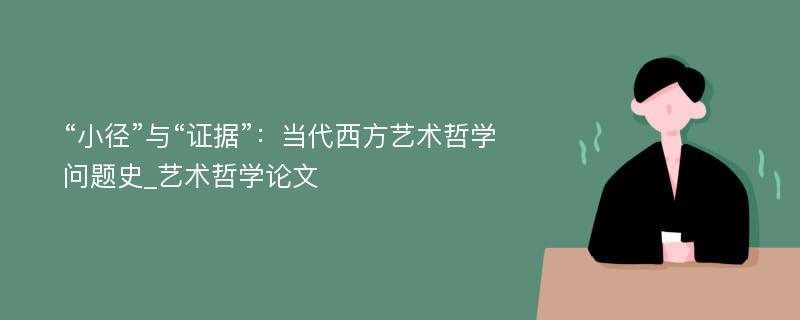
“踪迹”与“证据”:当代西方艺术哲学的一段问题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踪迹论文,证据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4-0059-09 当代英语学界的美学学者自称其当前的学术研究为“分析传统的美学”,相比欧陆学界,“分析传统的美学”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不再讨论美的本质,而是致力于艺术问题的研究。英国美学家乔治·卡瑞在其1999年发表的论文《视觉踪迹:纪录片与图片的内容》①中提出了“踪迹”和“证据”这一对概念以界定纪录片。卡瑞的论文在学界激起了较大的反响,西方学者纷纷参与讨论,形成了一段问题史,关于纪录片的界定和本质问题在这些讨论中越来越清晰。本文拟清理这一问题的源起和历史,以期推动中国学界对这一艺术哲学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卡瑞说,纪录片电影的记录方法可称为“踪迹(traces)”。踪迹负载着信息,但它不同于“证据(testimony)”负载信息的方法,其区别在认知方面。某个画家绘制一幅画,其细节生动,非常类似所再现的题材,以至于人们可以把它当做一幅照片。一张照片是其主体(subject)的踪迹,但一幅画是其证据。这一思想最初是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鲁·巴赞(Andre Bazin)在比较照片和足迹、死亡面具(death mask)、木乃伊的时候提出来的。那么足迹、死亡面具与照片的相似性何在呢?它们都是其主体留在世界上的踪迹。一幅画则不是踪迹,即便它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其主体的外表的信息,即便它告诉我们的东西是多么可靠。对主体详细和可靠的描写(description)也不是它的踪迹。各种踪迹,按照肯达尔·沃尔顿(Kendall Walton)的说法,是独立于信念的,这是绘画和描写所没有的。摄像机记录了它面前的东西,而非摄影者本人所想的在他面前的东西,但是画家可以描绘他所想的东西。某个有幻觉的画家可能绘制他认为他已经看到了的粉红色大象,某个有幻觉的日记作者也会描绘同样的东西,但某个有幻觉的摄影者在看到他的作品呈现的是空空如也的房间时会感到吃惊,因为他所想的东西并未出现在摄影图片中。这即是说,踪迹是客体决定性的,而绘画、日记等则是主体决定性的,是为意图所中介的。用卡瑞的话说,照片独立于信念,摄影者要记录的是在他面前的场景,而画家则描绘他所想的东西。绘画和素描与历史、新闻等,是为生产者的意图所中介的,这些可称为证据,其再现性的本质区别于踪迹。卡瑞指出,踪迹和证据的区别还在于其再现的范围。我们能够描绘和书写从来没有发生,或者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但只有真实的东西才能留下其踪迹,而且踪迹只能是属于过去的某种东西的,不是属于未来的某种东西的。但是,不能把这一点混淆于“照片从来不歪曲”这一错误的观点。 在区别了踪迹和证据之后,再看纪录片与踪迹的关系。纪录片使用摄影照片,高度依赖踪迹的生产方法。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理解图片和影片形象的再现方法,一个有用的办法是思考纪录片的歪曲(misrepresentation)。 纪录片可能歪曲,之所以如此要么是其作者对于其所记录的东西具有错误的信念,或者作者本身就是想要误导我们。比如,关于罗马帝国灭亡的纪录片,其制作者相信罗马公民生病是因为敌人投毒到饮用水里,他可能呈现给我们生病的人们,还评论说,这些人是这种毒害的牺牲品。但如果人们生病的真实原因是因为水管中有铅而非敌人投毒,那么这个纪录片就是误导了。这是因为图片是踪迹,而没有发生的事件,比如敌人投毒,是没有留下踪迹的。因此,如果作者认为某件事发生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纪录片就不能对之做出记录,虽然制作者能够以误导的方式记录,并将其呈现给我们。因此不能说,因为纪录片是踪迹,作为知识的来源,总是比证据比如历史更可靠。但如果纪录片有误导,它本质上不是误导性的:它的误导不是因为构成了纪录片的材料自身是对不存在或没有发生的事件的再现,而是因为我们从再现意指到其他的某种东西,这种意指是错误的,虽然我们是非常自然地做出这种意指,或者是作者想要我们这么意指。即是说,纪录片如果有误导,其缘由不在材料,而在叙事,在制作者的意图。但某部历史叙述可能本质上是误导性的,其再现、词汇和句子,能够是不存在、未曾发生的事件的再现,比如“野蛮人在供水设施中投毒”这样的句子就是如此,一幅描绘野蛮人正在向供水设施中投毒的绘画也是这样。 摄影图片,包括电影形象,能再现虚构性的东西吗?卡瑞的回答是肯定的,电影《卡萨布兰卡》中的形象再现了力克(Rick)和伊尔萨(Ilsa),就如再现了演员博加特和褒曼那样。但它再现虚构是第二位的,它是通过再现真实即再现博加特和鲍曼的一系列真实的活动而再现虚构的。这就是图片再现与绘画再现不对称之处:一幅画能够再现虚构的东西而无需再现现实。如果图片再现了虚构,它不是“属于(of)”虚构的东西的,比如一张电影《卡萨布兰卡》的剧照,它是属于真实的演员的,但它是“关于(about)”虚构性的剧本的。在图片,属于什么和关于什么存在差异。它属于某种东西,即是说,它是那个东西的踪迹(它是演员褒曼的踪迹),是我们借助因果关联可以辨识的。但如果图片是虚构的一部分,那么它也可能是关于某种虚构的东西的。 图片能成为信息的来源,这一点绘画难以做到。没有画家能够合理地希望,通过放大他的画作,能够找到在画作完成之时他不知道的东西的存在或发生的证据。但是,一张图片能提供某种东西的线索,这可能是其制作者在完成作品之时没有意识到的。图片和电影形象的差异是,电影形象能够表达更多的东西,因为电影形象记录了运动,而一张图片所记录的东西是静止的。某人可能通过创作一幅生动的卡通画去回忆一匹马的运动。如果他的记忆有误,是他的错误印象留在卡通画中。相反,摄影师的影像记录了运动是什么样的。通过对肯尼迪遇刺影像的画面的一点一点分析,我们希望获知事件的缘起和射击的次数,这是我们分析同样事件的戏剧性描绘(dramatic recreation)不能获知的。 在图片的认知性方面,有些哲学家走的更远。巴赞及其追随者罗杰·斯科鲁钝和沃尔顿认为,摄影图片和电影形象给予我们的与其说是再现的独特形式,毋宁说是,它们再生产了现实。这种观点认为,图片并非属于绘画和素描的亚范畴,因为图片根本不是再现,它们类似窗户、镜子和望远镜,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视觉能力,它们帮助我们去看我们以前不能看到的东西,我们因此能够看到已经不在世的人。如沃尔顿说,图片是透明的。卡瑞指出,我们能够与人和物发生认知关系,也能够与之发生情感关系。图片具有情感能力,这一点是手工做的绘画所缺乏的。在其他方面相等的情况下,相比一幅画,我们可能对一张讨厌的或让人不安的图片感到更为厌恶或不安。沃尔顿援引这一点以支持其透明论:我们更多地为图片和电影感到不安和被冒犯,是因为我们在看它们的时候,实际上是在看令人厌恶和不安的事件本身。相比绘画,图片和电影的影响力更大,但相比直接见证令人不安的事情,它们的影响力度就较小,这就表明图片是存在于现实和手工形象的中间。图片比手工绘画的影响力更大这一事实更好地解释了图片是踪迹。事物的踪迹负载着与那个事物的特殊的直接性的关系,拥有某人的一张图片、死亡面具或足迹,似乎把我们置入与那个人的特殊关系之中,这是手工形象不能做到的。 卡瑞强调,成为纪录片的必要条件是,其所再现的事物必须是踪迹。但所有的为摄影和类似的方法制作的电影都是踪迹,《卡萨布兰卡》是演员博加特和褒曼的行为留在世界上的踪迹,但不能说这部电影是纪录片,因此在界定纪录片时,踪迹是必要的但非充分的条件。在较弱的意义上《卡萨布兰卡》是纪录片,它记录了那些制作了《卡萨布兰卡》的人的行为,因此,必须承认每一部电影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纪录片。但纪录片的定义应该是较强的意义上的,要通过界定典型的纪录片而获得。卡瑞提出,一部影片要成为纪录片,其因果性地产生的形象,首先要具有再现的功能,它们要再现它们是其踪迹的事物和事件。这不是说,纪录片能够与叙事分离,相反,叙事是纪录片的组成元素,但其叙事要契合于电影形象是其所再现事物的图片性的踪迹。 我们已知,纪录片可能误导或歪曲。有些纪录片常常艺术性地暗示,某个事情发生了,但其实并没有发生,或者并没有如它所说的那种方式或基于那种原因而发生。当这么误导的时候,纪录片内部具有某种张力,这种张力是不可能发生在某个虚构或戏剧性的重构之中的,只要后者中的叙事是连贯性的。比如在《卡萨布兰卡》中,力克杀了梅杰·斯卡瑟(Major Srasser),电影形象中不可能有任何东西与这一事件相矛盾。如果戏剧性的重构,比如电影《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1976年,关于“水门事件”的电影)是为一群对于其试图重构的事件具有错误信念的人所制作,那么他们所生产的电影将契合于他们自己的错误的理解,就去再现实际上并没有存在和发生的事情。但是在纪录片里,那就是误导。在纪录片中,电影形象只是再现它们是其踪迹的东西,如果制作者相信或要我们相信的东西是矛盾于电影所记录的东西,张力就存在其中了,即是说,图片和叙事发生了矛盾。 说到叙事,卡瑞认为,除了感性的元素外,电影还有叙事。两部电影具有同样的感性元素,其叙事可能是不同的,如果在其语境中,感性元素带来的是不同的暗示的话。电影是在特殊的共同体层面的信念和期待的语境中获得叙事的,在某一语境中,某些元素可能被视为严肃的论断,但在另外的语境中则可能被视为讽刺。可见,卡瑞这里的叙事不仅仅指的是制作者的意图、画外音和解说,还包括更为广泛的文化性的语境。 在《艺术与心灵》这本书中,卡瑞进一步区分了踪迹内容(trace content)和叙事内容(narrative content)。前者是形象的内在的本质性的,而叙事内容依赖于围绕着形象的语境。踪迹内容是非概念性的,但叙事内容是概念性的,其差异类似语言的内涵和外延意义。某个摄影形象的踪迹内容独立于语境,无论你如何把它与其他的照片合并,无论你如何评论它,一张艾林阿姨的照片代表的就是她本人。实际上,其起源决定了踪迹的内容和图片的身份。这一点不同于摄影形象的叙事性内容。在电影《卡萨布兰卡》中,通过与电影叙事的联系,鲍曼和博加特的摄影形象代表的,是虚构人物伊尔萨和力克。但是,鲍曼和博加特的形象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能代表的是不同的叙事内容。②图片之所以无概念性的内容,是因为任何图片具有它自己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是摄影者没有意识到的。图片的内容完全决定于非理性的(非意图性的)缘由。如果说,图片或电影形象具有明确的叙事性的内容,那必定是因为在形象和叙事之间具有某种联系,那种联系必定是意图性的。③ 如果在其叙事性的和图片性的内容之间有张力,纯粹的纪录片可能是误导性的。相反,可靠的纪录片可能是非纯粹的,比如在一部关于迪斯尼的纪录片中,米老鼠扮演叙事者。我们看到米老鼠在屏幕上,带领我们走过拍摄地点。这里,米老鼠正在告诉我们各种事情,这是虚构的。但它告知我们的,是被制作者意图为一系列严肃的论断(assertion),我们视之为可靠的。特别是,制作者并没有意图误导我们,好像米老鼠是真实的,是在真正地说话。 纪录片误导的方式还包括采用虚假材料,比如巴泽尔·莱特(Basil Wright)1936年拍摄的《午夜邮差》(Night Mail),后来人们知道,火车车厢里面的邮差镜头实际上是演播室里的表演。在材料虚假的情况下,问题似乎不在形象自身,而在叙事所表明的有关形象的东西。比如,为了方便,在关于尼克松的纪录片中,有许多镜头用的是替身,在远距离和光线不好的情况下,他看起来像尼克松。那么这些镜头就不是记录性的。同样的,在《午夜邮差》中,演员在工作室里的镜头就不是这部纪录片的记录性部分。因此,我们称为纪录片的东西可能是记录性的和非记录性的混合物。有时候,影片不仅仅是伪造细节,它可能整体上都是虚构的。1972年的《没有谎言(No Lies)》声称记录了在强奸案中的女性受害者和男性攻击者之间的对话,他竭力表明她在攻击中是共谋者。演职人员在影片结尾表明整个事件其实都是演员耗时数周用手稿排练的结果。这部片子因此就不是纪录片,因为它的形象中没有一个通过其作为事物的踪迹的角色支撑了叙事:电影所记录的事件和叙事中所声称的事件完全不一致。 我们可以把镜头视为记录性的单元,但不能说,某个镜头,单独看,能够被视为记录性的或非记录性的。按照弗雷格的思路,我们可以说,只有在电影的语境中,镜头才能获得纪实性的身份。在前面提到的关于尼克松的电影中,替身我的哥哥的那些镜头不是记录性的,但它们在制作的关于他的性情和他的偏爱模仿尼克松的影片中则是记录性的。在电影《卡萨布兰卡》的语境中,那些有关褒曼的镜头是虚构的,但在关于褒曼的表演风格的纪录片中,它们是记录性的。这就有了一个解释学的循环:要名实相符,一部纪录片必须由大多数是记录性的镜头所组成,但镜头作为记录的身份取决于它所属其中的电影的记录性身份。这就是说,在宽泛的意义上,任何电影都是一部纪录片,就如任何镜头在单独看的时候那样:它之于它是其踪迹的那个事物是记录性的。但是在严格的意义上,不是每部电影都是纪录片。要成为纪录片,其影像须是事物的踪迹,而非具有其他的再现性功能,且这些影像支撑了论断性的叙事(asserted narrative)。 还有一种纪录片,这里没有拿破仑的影像踪迹(事实上不可得),也没有与拿破仑非常相关的东西的影像踪迹。相反,有很多拿破仑专家对拿破仑的描绘以及战场模型等,这样,影片的叙事是关于拿破仑和与拿破仑相关的事物和事件的,这就不是纪录片,因为影像部分作为其踪迹的东西与叙事焦点不一致:叙事焦点是拿破仑,但影像不是拿破仑的踪迹。我们能够辨识电影所呈现的某种亚叙事,它关系到研究拿破仑的专家、对拿破仑的描绘、战场模型等等,我们最多得出结论说,这是关于那些东西的纪录片,而非关于拿破仑的。严格说,这只能说是“与拿破仑相关的纪录片”,一种“想象性的纪录片(the imagined documentary)”,它提供的实际上是研究拿破仑的专家和其他事物的踪迹。 综上,卡瑞的结论是,“纪录片是影像性的叙事,其形象借助其图片性的再现支持了叙事;纪录片不是一个修辞性的、空洞的或混乱的范畴,虽然它本质上是一个模糊的范畴。” 卡瑞的文章引起了学界的争鸣,美国美学家诺埃尔·卡罗尔首先对卡瑞的观点提出了批评。④卡罗尔认为,卡瑞的纪录片概念,不是我们在实际中使用的,他的理论忽视了常规的用法,违反了日常的直觉。在卡瑞看来,纪录片是影像性的叙事。但卡罗尔指出,被称为纪录片的东西不总是叙事,它们有时是观点(arguments),有时只是图像的集合(catalogues of views),有时只有单个的镜头而无故事。即便我们保留卡瑞的理论,也应该明白,大多数被称为纪录片的不是卡瑞说的,其形象的主要组成部分行使的功能是踪迹。卡罗尔说,实际的情况是,许多纪录片自由地使用底片材料:在诺曼底入侵中使用的海军大炮被用于冲绳入侵的纪录片中,希特勒在一个场合演说的镜头被用于再现另外场合的演说。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直存在着的惯例。即是说,许多纪录片从档案馆中获得影片资料,后者并非这部纪录片中的事件的踪迹,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把它们称为纪录片。 还有许多关于未来的纪录片,比如迪斯尼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拍摄的关于太空旅行的影片,其主要的形象不是踪迹,而是动画,但我们仍然称之为纪录片。因此,卡瑞并没有提供给我们何为纪录片的必要条件,他也没有提供充分的条件,比如,许多电影的主要形象,其功能是再现了它们是其踪迹的那些东西,典型例子是历史上的先锋派电影。雷吉尔(Leger)的经典作品《机械芭蕾》(Ballet Mecanique)主要是由运动着的物体的踪迹性再现所组成,但它不是被分类为纪录片,而是一种电影诗(cine-poem)。再如,欧尼·格尔(Eernie Gehr)的《平静的速度》(Serene Velocity)的主要镜头是对公共机构中的走廊的踪迹性再现,这些形象按照不同的节奏被编辑在一起,不仅表达有趣的节奏,而且追寻对运动印象的感知性条件,其结果是对电影本质的反思性评论,而不是记录走廊中的画面,这部影片属于传统的元电影(metacinema),而非传统的纪录片。 卡罗尔设想另外一个例子以反驳卡瑞,比如有一部虚构性的影片叫做《我自己的越南》,影片中的每一个形象都是越南战争中的事件的踪迹性再现,但其中也有一个声音,是我自己扮演的一个虚构的步兵,他不仅描述呈现在屏幕上的战争场景,也说明他对所呈现的画面的心理反应。这里的每一形象都是踪迹性的再现,声音中的所有东西都契合那些事件的踪迹性再现,但这个虚构的评论员没有出现在所描述的事件之中,他只是观察他自己的情感反应。但这部影片不是一部纪录片,而是一部虚构性的影片。因此,卡瑞说的“主要是再现性的踪迹”并不能成就一部纪录片。 卡瑞可能说,这些相反的例子缺乏叙事,因此它们不是纪录片。但卡罗尔反驳,前面已经说明,不是所有的纪录片都是叙事的。把叙事视为纪录片的必要条件而排除这些例子是错误的。卡瑞说,踪迹不仅包括图片,还包括足迹和死亡面具,踪迹比手工图片在情感上更为有力,但卡罗尔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说,很多绘画相比摄影图片和相关事件的影像性踪迹更为激动人心,而足迹和死亡面具几乎不能激动人。 在卡罗尔的批评之后,卡瑞撰写文章予以回应,⑤在这篇文章中,卡瑞仍然维护自己的观点,即某种形式的踪迹内容是纪录片的本质性的组成部分。卡瑞首先澄清一系列误解。卡罗尔说,卡瑞的看法是,自动摄影机所获得的影像是“理想的纪录片”。卡瑞认为,这样的镜头没有负载作者控制的标记,摄像机只是简单地放在那儿去记录所发生的事情,这就不存在叙事。地震仪的记录不包含叙事,叙事是一种意图性的行为,因此,监控性的影像不是纪录片,更不是理想的纪录片。 卡瑞的观点是,纪录片中的影像应与叙事一致。但卡罗尔反对说,许多纪录片使用库存资料片(stock-footage),这并不一致于其叙事,因此一部战争纪录片可能呈现给我们一台谢尔曼(Sherman)坦克的形象,但不是这部纪录片所说的那场战争那个地点那个时间中的坦克,某些纪录片包含的大多数就是这样的库存资料片。卡瑞的解释是,某个既存的踪迹内容在某个描述层面上契合其叙事,但在另外的层面上并非契合其叙事。如果我们所有的是在德国的一台谢尔曼坦克的形象,在对“谢尔曼坦克”的描述的层面上,这就是一致的,但在描述“在诺曼底的谢尔曼坦克”这一层面,则是不一致的。后者强调的是在诺曼底使用过的坦克,这就必须是出现在法国国土上的谢尔曼坦克。 卡瑞也回应了卡罗尔的《我自己的越南》的思想实验。卡罗尔说,这部影片契合了卡瑞的核心条件,即电影中的形象的踪迹性内容和其叙事是一致的,但它不是纪录片。卡瑞说,这个说法有问题,并不能推翻他的观点。如果影片给予了事件的前景以大量的镜头,而相当少地关注老兵的虚构性反应,那么在卡瑞看来这部影片就包含了大量的纪实性内容,虽然人们可能不想称之为纯粹的纪录片。确实,这种情况类似卡瑞在论文中提到的米老鼠对迪斯尼的叙事,他归之为不纯粹的纪录片。如果影片主要关注叙事者的反应,以至于我们看到的是,影片告诉我们的是关于老兵的心灵情感的故事,那么,在卡瑞看来,这里踪迹内容和叙事的一致就没有达到有意义的程度,这个时候叙事就变成了叙事者对于事件的反应,这种情况就是卡瑞在论文中说的,有一种电影,其中虚构性的人物不显现出来,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是真实的地点和真实的人,这些前景只是作为所讲述的事件的背景,故事被一个声音所讲述出来,这种情况下它就是虚构性的了。 卡瑞主张,关于纪录片的界定必须考虑叙事和踪迹内容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必须要有踪迹性内容的形象呢?原因是,这样的形象具有明显的认知性力量。纪录片的形象要经得住质询(interrogation),这对于戏剧性的重构即对真实事件的虚构性构造的影像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卡瑞认为,卡罗尔的踪迹内容对于纪录片的界定来说是无关重要的观点是难以接受的。 以上三篇文章发表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的崔珍熙也参与了讨论。⑥卡瑞对纪录片的界定是诉诸视觉踪迹(visual trace):照相机面前的物体会在照片中留下踪迹,而不管照相者关于物体或事件的信念如何。即是说,照相机机械地记录了它面前的东西。卡瑞说,我们在追寻纪录片的本质的时候,要看其叙事是否主要由图片形象的踪迹性内容所构成。卡瑞试图开拓图片形象和影像形象的索引性和起源性,即相比其他艺术而言,纪录片对于世界具有索引性的关联(indexical bond)。在对卡瑞的批评中,卡罗尔列举了大量的反例,认为卡瑞的定义太过狭窄,还认为既非叙事也非叙事和图片形象的一致是定义纪录片的必要条件。在崔珍熙看来,卡罗尔和卡瑞的分歧在对术语“叙事”(narrative)界定的模糊。在他最初的文章中,卡瑞并没有明确地说何为叙事,仅仅只定义叙事为从形象、配音和画外音中提供的感知性线索推导而来的某种东西。在他的反驳卡罗尔的文章中加了另外的元素,即叙事是一个意图性的概念。因此,从监控摄像机中获得的形象,在卡瑞看来根本不是纪录片。但这里,卡瑞关于叙事的观点仍然是模糊的。 按照大卫·博德威尔(David Bordwell)和克里斯丁·汤普森(Kristin Thompson)的看法,叙事指的是某部影片中所描绘或暗示的事件的时空秩序(spatio-temporal)。只有观众把某部影片的线索连接为在特定时空中的一系列具有原因和后果的事件之时,叙事才被构造。在这种观点看来,因果关系、时间和空间是叙事的最小的单元。按照这个要求,卢米埃尔(Louis Lumière)的先锋派电影中有一些符合这个要求,比如卡瑞说的《工人从工厂走出》。工人从工厂走出,是因为他们完成了工作。但并非卢米埃尔的所有的《时事》影片包含叙事,比如《乔治城的环线》(1903年)就没有包含叙事,它只是呈现了有关移动的交通工具如船或火车的镜头。 卡瑞还要求,某部纪录片的形象应该契合其叙事,即是其形象的踪迹性内容与叙事所说明的相一致。但崔珍熙认为,卡瑞的这种观点是有瑕疵的。卡瑞的主要观点是,纪录片中,图片形象是“可靠的”,他试图以图片形象的索引性(indexicality)去维持纪录片的认知的优先性。但是,如卡罗尔指出的,大多数纪录片需要借用档案馆中的库存影像资料。这样,叙事和形象实际所是就不一致。但是,卡瑞说,只要形象在粗粒度(coarser-grained)的描述层面没有违背叙事的内容,它就是可以接受的。即是说,只要形象契合了“谢尔曼坦克”的描述,不管其地点如何,它就在一部关于谢尔曼坦克的纪录片中可用。但这种回应导致了卡瑞理论立场的不一致。卡瑞拒绝表演和再演(reenactments)作为纪录片的合适的部分,因为它们不是影片所关系到的人和事件的实际的踪迹。但是,崔珍熙反问道,如果使用库存影像资料是可行的,为什么我们不能使用再演呢?因为库存影像和再演都不是事件或物体的实际的踪迹。 但是卡瑞有解决的办法。他说,纪录片的影像的主体是实际的视觉踪迹。他把高度依赖于表演或再演的影片称为“B相关的纪录片(B-related documentary)”。也即是说,如果某人在约翰·肯尼迪飞机失事之后,制作了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其中主要是他的家人的访谈,没有使用任何实际的肯尼迪的影像资料,那么它就不是一部关于肯尼迪的纪录片,而仅仅是一部与肯尼迪相关的纪录片。但这样问题就来了。崔珍熙说,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借用比尔·尼古拉斯(Bill Nichols)的术语,兴起了“述行性的纪录片”(performative documentaries)。这些影片的内容主要是表演和再演,包括马龙·里格斯(Marlon Riggs)的电影如《饶舌》(Tongues Untied,1989年)和《黑色是,黑色不是》(Black Is,Black Ain't,1995年)、吉尔·古德汨罗(Jill Godmilow)的《远离波兰》(Far from Poland,1984年)、艾罗尔·莫里斯(Erroll Morris)的《细细的蓝线》(The Thin Blue Line,1987年)等。表演和再演按照卡瑞的看法不是实际事件的踪迹,它们是为摄影机而上演的。如果是这样,卡瑞的定义就排除了一个重要的纪录片运动。比如《远离波兰》主要是在美国拍摄,影片只有8分钟关于波兰的实际的影片资料。因为实际影像的不可得,古德汨罗使用了三段主要的再演,总共41分钟,即与安娜·瓦伦蒂纳文斯基(Anna Walentynowicz)的访谈、一个政府审查员的访谈和一个矿工的访谈(这些都是演员,而非团结工会的成员)。按照卡瑞的界定,《远离波兰》不是关于波兰团结工会的纪录片,而仅仅只是与波兰团结工会相关的纪录片。卡瑞可能说,这部影片只能被视为关于“表演”的影片,因为社会演员的表演超过了在波兰的实际的工人和团结工会成员的影像资料。但崔珍熙认为,卡瑞的这种看法不可信。 按照卡瑞的看法,在某部纪录片中,如果主要是表演或再演,那么它实际上是关于表演或再演的,而不是关于表演所再现的东西的。崔珍熙说,这是一种很奇怪的说法,这种分类违反了电影中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因为表演是从属于作为整体的电影的功能,而非相反。这个意义上,《远离波兰》可被视为对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解释,电影中的表演有助于实现这种功能,因此,与卡瑞的看法相反,崔珍熙认为这部电影不是关于表演的。通过插入实际的影像资料,不论是多么短的篇幅,导演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现实核查”(reality check)的东西,其目的是意指到现实,提醒观众注意作为整体的电影是关于何种东西的。 卡瑞认为考察某部影片是否是纪录片的方法,是要看每一单个的镜头和主要的镜头是否是可靠的,崔珍熙认为这种方法不切实际,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多数镜头在单独看的时候,其意指具有相当大的可塑性,是不确定的。按照卡罗尔的说法,某部电影中的单个镜头的意义应该在电影整体中去考察。卡瑞的主要问题,是他试图以“纪实性的部分”界定纪录片,但这反过来得依赖于电影的整体。卡瑞说,在严格的意义上决定某个镜头或某部影片是否是纪录片,我们要看的,不仅仅是其作为踪迹的身份,而且要看那些镜头或影片所支撑的意图性的生产的叙事和它们的构成性的断言(constituent assertions)。如果是这样的话,崔珍熙指出,纪实性部分的可靠性以及某部影片作为整体的纪实性身份应该取决于影片制作者所采取的指向影片内容的论断性立场,而非叙事和其构成性形象之间的一致。 卡瑞对崔珍熙的批评做了回应。⑦崔珍熙和卡瑞的分歧在于何为叙事,但是按照崔珍熙的观点,卡瑞说,他不明白为什么卢米埃尔的那些电影没有体现叙事。按照崔珍熙提供的定义,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是叙事包含的最小单元,但崔珍熙引证的电影是符合这个要求的,比如,如果我们从一艘移动的船上拍摄某栋建筑,我们看到它与船之间的变化着的时空关系及其存在的连续性,后者对于前者具有因果性的依赖关系。这里确实没有很多叙事,但不等于没有叙事。卡瑞表示,他和崔珍熙关于叙事的根本分歧在于,叙事的概念是否关系到意图性的代理人(intentional agency)这一概念,卡瑞相信是肯定的,而且这些电影里不缺乏这样的代理人。 关于再演的问题,崔珍熙批评卡瑞排除了一个重要的纪录片运动。卡瑞辩护说,他并没有粗暴对待历史,并没有否定这样的作品是独特的非虚构的电影类型。卡瑞说自己的思路,是在宽泛的非虚构电影的类型中,划分一个狭窄的可称为纯粹的纪录片的范畴,其图片内容和叙事之间是和谐一致的。卡瑞承认日常使用的纪录片这一术语很宽泛,泛指非虚构电影,但认为这种宽泛的范畴,虽然具有实用性,但当我们在思考纪录片的历史及其作为叙事和知识供给者的身份时,不能让我们深入考察概念上的相关问题。 卡瑞提出的踪迹和证据这一概念及其对纪录片的界定,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随着讨论的深入,关于纪录片定义的相关问题越来越清晰。美国密歇根州加尔文学院的卡尔·普纳迪加在研究纪录片时,从宏观语境中讨论了卡瑞的理论。⑧ 普纳迪加把传统纪录片分为两类,即索引性的记录(indexical record)和断言性的清单(assertion accounts)。前者主要是由运动着的图片性的形象所构成,这些形象是在影像之前的场景的索引性记录或踪迹。图片和声音的索引性最为制作者和理论家所关注。人们认为,图片是一系列摄像机的机械性操作的产物,这个过程遵循物理法则,而非人的意图,这就保证了图片的真实性。制作者必须选择拍摄什么和如何拍摄,图片当然牵涉到摄影师的意图和计划,即便如此,图片起源的机械性本质使得我们能够把证据性的身份(evidentiary status)归于图片,这是绘画所没有的。 索引性记录的定义重视图片记录世界的能力,低估影片制作的创造性和解释性。早期的实践者认为他们只是直接地记录和展示,把解释空间留给观众。后结构主义理论家认为没有纪录片能够完美地再现或再生产任何东西,他们认为先前的纪录片的观点是可疑的。问题当然不是在纪录片本身,而在关于纪录片的定义。普纳迪加认为,卡瑞的问题是,他有时说,纪录片运用图片去再现图片是其踪迹的东西,这样的形象是为了支持某个断言性的叙事(asserted narrative)。在其他的时候,卡瑞又说,纪录片自身是其所再现之物的踪迹。这就是说,关于纪录片卡瑞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把纪录片界定为视觉踪迹所支持的影像性叙事,这些踪迹再现了它们所属于的东西,一种是把纪录片自身界定为视觉性的踪迹。说纪录片是踪迹,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卡瑞的意思是,纪录片自身与个体性的图片,在同样意义的层面上,都是踪迹,那么卡瑞是想把同样的非信念依赖性(belief-independence)的特质归于纪录片,就如个体性的图片形象也具有这种特质那样。但普纳迪加认为这是有问题的,因为纪录片是被编辑过的,编辑总是进一步地解释事件,牵涉到制作者的意图,这是索引性的符号比如踪迹所缺乏的。当你添加音乐、标题或画外音给叙事的时候,就在纪录片和其主题之间做了某种调节。只有很少的情况下纪录片自身才可能是踪迹,监控性的影像可能是最佳的例子。 卡瑞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试图解决它,他说,大多数纪录片都包含非纪实性的部分。但这种解决办法,普纳迪加认为,不仅没有澄清问题,反而把卡瑞的错误推向了前台。像很多前人,卡瑞混淆了纪录片和文件(document)。一张图片式的文件是一份物质性的踪迹,纪录片常常运用这种踪迹,但只有非常少的纪录片被视为行使了踪迹的功能。在把纪录片界定为断言性的清单之时,断言与虚构相对,指的是对现实的指认,即作者说的是事实。当某个作者以断言性的立场指向他的作品的世界,他就希望观众明白,构成了其作品世界中的事情是真实地发生在现实之中,即是说,作者调动了观众的相关期待。相反的是,如果作者对其作品采取的是虚构的立场,意图其作品给我们提供审美享受和文化启迪,但不是要我们相信,艺术品中的事情是真实地发生在世界上,这种情况就不属于纪录片。这样,虚构的和非虚构电影的区别就奠定在言语行为理论之中了。 比尔·尼科尔斯(Bill Nichols)把纪录片分为六种模式,即诗性的、解释性的(expository)、观测性的、参与性的、反思性的和述行性的(performative)。在解释性的类型中,画外音叙事者提供了解释性的概念框架,形象和声音则给画外音叙事者提供解释或证据。这种类型的纪录片依赖撰写好的稿件,许多是对历史事件的特殊解释,很多电视新闻纪录片也属于此类。⑨就是这类纪录片,索引性的定义无法面对,特别是对于摄影机被发明之前的历史题材纪录片,因为在摄影机被发明前,关于这些题材的图片性踪迹是无法获得的。卡瑞承认,他的索引性记录的定义排除了关于拿破仑的纪录片。这种定义也无法解释最早的纪录片。初期的纪录片作者主要使用娱乐(recreations)和对事件的表演,这样的镜头很显然不是再现性图片所属的东西。这种定义只能阐释1960年代以后的现场拍摄电影(direct cinema)和真实电影(cinema verite)运动。 但在普纳迪加看来,这种定义最大的问题是不能抓住解释性纪录片的最重要的特质。卡瑞说,在他的纪录片定义中,意义从形象走向叙事,而在非纪实性的影片中,意义是以其他的方式生产的。卡瑞的意思应该是,纪录片的意义起源于图片性的踪迹,而非来自某种先在的观点,即先前研究所得的关于历史的观点、政治分析和科学解释等。但卡瑞的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著名的纪录片,诸如《后勤女工》《细细的蓝线》《大亨与我》等都是围绕着某个观念所组织的精心制作,其形象支撑了某种稿件性的观点或叙事,其意义并非必然来自使用过的形象。因此,说这些纪录片的本质是把运动性的图片使用为踪迹是不准确的,在这些纪录片中,摄影的使用是服务于制作者的论证性策略的。普纳迪加的结论是,索引性的定义太过狭窄,不仅排除了许多典范性的纪录片,而且不能说明解释性的纪录片这一纪录片的核心模式。 纪录片的研究关涉到很多问题,诸如其审美特质,其政治效果,其客观性和科学性叙述等,但讨论这些问题只有在厘定纪录片的定义之后才是可能的。卡瑞所提出的命题及其所产生的效应,对于纪录片的研究具有开局性的意义。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对卡瑞命题及其效果史梳理的学术意义在于:一是,看到分析美学的理论主旨,即是具体研究当代的艺术问题;二是,从中看出西方学界对纪录片这一影片类型的界定及其问题的复杂性,得出对纪录片的清晰认识;三是,关于每一问题,学者从多方面多视角提出观点,反复辩论,推动了这一问题的发展和深入,这是学术争鸣和学术生产的理想模式,值得中国学界借鉴。目前,中国电影研究和艺术哲学领域对纪录片的界定基本停留在泛泛而论的教科书阶段,没有深入到纪录片的时空、叙事和影像等特质方面,卡瑞的理论命题及其效应对于中国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卡瑞及西方学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做了如下的初步思考。 典型的纪录片要运用真实的所再现之物的踪迹的图片,但叙事是不可或缺的,叙事要服务于图片,而且,这里的叙事应是论断性的而非虚构性的。即是说,踪迹性的图片和论断性的叙事,这是典范纪录片的两个元素。但在实际的操作中,这两个元素的不同组合会出现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图片是真实的,但叙事是虚构的,这就是虚构电影,如卡罗尔设想的越南战争的例子。第二,图片是虚假的,叙事是论断性的,这是很多纪录片的情形,比如《欧洲自然写真》等BBC制作的很多纪录片,是常规的纪录片,但不是典范性的。第三,典型的纪录片:图片是踪迹性的,叙事是论断性的。比如BBC制作的系列自然片。制作者意图我们认为它是论断性的、真实的,我们也确实认为它是真实的。第四,只有无间断的影像而无叙事,即自动摄影机所拍摄的,比如动物夜间行为的纪录片,放置在运动场记录运动员动作的纪录片,用于司法机关以防止刑讯逼供所用的不间断的审问嫌疑犯的影片。这些影片没有解说和画外音,也没有编辑的意图,但考虑到纪录片提供信息和知识的功能,这也应视为纪录片。第五,只有踪迹性的图片的重新剪辑,常常有配乐,但没有画外音和解释,比如许多电视台制作的世界各地自然风光的影片。这些图片的剪辑是意图性的行为,这也就有了叙事,包含了制作者的意图,也应视为纪录片。但只有踪迹性的图片的重新剪辑,也可能是虚构影片。比如在人群密集的城市广场中拍摄人物和建筑的图片予以重新剪辑,其中可能包含制作者的逻辑连贯的意图,具有故事性,这种情况就是虚构影片了,但这里的意图是否能呈现,取决于观影者的观看。在看不出意图的观影者眼中,它是风景或时事纪录片,反之,则视之为虚构电影。这种情况典型地表现出纪录片边界的模糊性。第六,一种极端的情况是,画面上无任何踪迹性的图片,只有科学性的解说,这就不能是纪录片,因为没有图片,只能视为科学性的讲座。第七,图片的主要功能服务于虚构性的叙事,这就是典型的虚构电影。 纪录片中的图片意指到图片之外的现实,而虚构电影中的摄影图片只指向虚构世界,即便运用了真实的图片,比如《罗马假日》中罗马的镜头,也是服务于故事情节,不是致力于呈现罗马实景。此外,纪录片需要解释性的叙事。叙事不是如卡瑞说的,是从踪迹性的图片中自然生成的,因为图片自身不说话,图片到底意味着什么样的知识和信息需要解释说明,但纪录片中的解释是论断性的,它意指到外部世界。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纪录片是一个边界模糊的范畴,其容量很大,外延很广,但其知识性和科学性这一核心功能要求其图片是踪迹性的,叙事是论断性的,两者均指向外部世界,这一点显著地区别于虚构电影,在后者,图片和叙事指向作品的内部世界。 注释: ①Gregory Currie,"Visible Traces:Documentary and the Contents of Photographs,"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vol.57,no.3,1999,pp.285~297.除非特殊说明,本文以下关于卡瑞的观点均出自这篇论文。 ②③Gregory Currie,Art and Mind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76、78. ④Noel Carroll,"Photographic Traces and Documentary Films:Comments for Gregory Currie,"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vol.58,no.3,2000,pp.303~306. ⑤Gregory Currie,"Preserving the Traces:An Answer to Noel Carroll,"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vol.58,no.3,2000,pp.306~308. ⑥Jinhee Choi,"A Reply to Gregory Currie on Documentaries,"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vol.59,no.3,2001,pp.317~319. ⑦Gregory Currie,"Response to Jinhee Choi,"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vol.59,no.3,2001,pp.319~320. ⑧Carl Plantinga,"What a Documentary Is,After All,"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vol.63,no.2,2005,pp.105~117. ⑨See Carl Plantinga,"What a Docmnentary Is,After All,"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vol.63,no.2,2005,pp.105~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