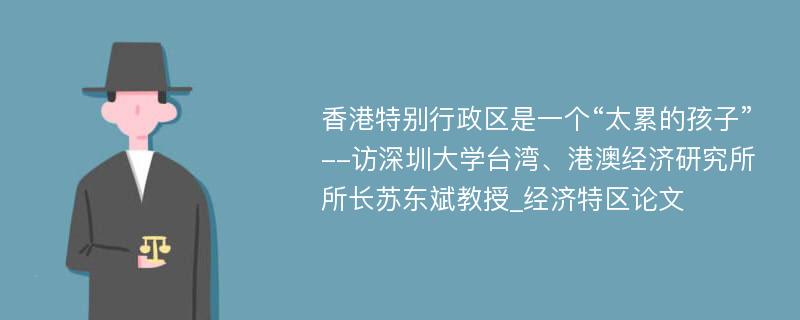
特区是个“太累的孩子”——访深圳大学特区台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苏东斌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港澳论文,特区论文,是个论文,所长论文,太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特区可能面临有史以来最为艰难的处境:一方面是众多的期望和种种的猜疑,另一方面则是多项优惠政策逐渐将被取消的现实,在这种形势下,特区还能不能做好“第二次创业”这篇大文章,这是所有关注特区前途和命运的人们所担忧的。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特区问题专家、深圳大学的特区台港澳经研所所长苏东斌教授,请他就某些问题谈了些看法。
记者:从前一段时间的争论来看,人们对经济特区在认识上还有误区,这对特区的进一步发展或多或少将产生不利的影响,苏教授,您能否从理论上对特区作个界定?
苏:我想,人们之所以对经济特区还存在各种各样错误的认识,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在概念上明确我国的经济特区与世界上一般经济特区的区别。
大家都知道,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设有经济特区,发达国家的特区甚至达数百个。普遍而言,这些经济特区侧重于自由贸易港、经济贸易区、开发区的形式。因而,相对于这些国家的其他地区来说,它们的经济特区是特殊功能的经济区,决不是其他地区学习的榜样。我国的经济特区自建立始就被赋予了不一般的历史使命,特别是在今年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被明确了6个字:示范、辐射、带动。
特区的示范作用,就是要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上作好排头兵,为全国开路。这不单意味着国家要在特区搞很多试点,比如现在深圳搞的口岸管理体制试点,特区自身也要在诸多领域主动地往前闯,如深圳进行的一系列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就充分地表明特区的示范作用正在发挥。在我看来,示范作用就是我国特区的主要作用,而且正是这一点,使得我国的经济特区有别于世界的一般经济特区。
辐射作用是由于特区的特殊地理位置造成的,这一点是国内其他城市所无法取代的。比如深圳,面临港澳,只要中国想实行“一国两制”,想保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就必须发挥它的辐射作用。试想如果深圳仍是改革前宝安县城那种贫困落后的情况,大量农民逃亡过去,香港还能谈得上稳定吗?更何来社会主义优越性?
带动作用,从本质上说,我认为是转移支付而不是扶贫。现在深圳动不动就拿出多少钱给老区、革命根据地办学,当然,这不是不好,但我认为主要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应多创造本身财富,给省、中央多交税,然后由中央转移支付。中国的经济制度已经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了,那么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政府应该有两大政策:第一条是根据经济的发展非均衡原理,实施邓小平讲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唯一途径。讲到共同富裕,毛泽东时代的这个愿望更强烈,但是为什么实现不了,就是因为大家平着往前走,都没有了积极性,最后导致了普遍贫穷。这是历史的局限,我们千万不能再回到这条老路上去。第二条政策是政府在救济贫困地区、缩小贫富差距的同时,一定要有个前提——发展经济。如果忽略发展,就会回到原来的体制上去,这是当前要注意的一个很容易形成偏差的问题。投资讲回报,沿海地区条件好,回报率高,资金自然就集聚过去了。如果你硬要把资金投到某些条件差的地区,回报率低,总的财富也增加不了。事实上,只有在普遍发展以后,差距才会自然缩小。
记者:谈到地区贫富差距,这正是目前颇为令人瞩目的一个问题,尤其是特区的高工资高收入和内地某些省市的贫困落后所形成的巨大落差,已经在不同层次上引起了争论。那么您又是怎样看这种不平衡的呢?
苏: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原理有个背景一定不能忽略,那就是要分清财富创造和财富转移。15年的事实表明,特区的发展是财富创造而非转移的结果。也就是说,它的财富不是从其他地方转移过来的,更不是剥削抢来的。如果不创建不发展特区,那么这笔财富现在就是零。特区非均衡发展的理论深度就在于:特区的资源条件、地理条件及其他经济因素,使该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力价值的实现程度高出了其他地区。商品经济不讲究劳动投入多少,而是看劳动力价值能实现多少,实现程度越高,表现的富裕程度也就更高。一般人对特区的高工资有误解,认为仅仅是政策的产物,但事实上,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多发钱,并不是从中央政府拨款来的,而是高劳动生产率带来的良性循环,是地方自己创造的。而且特区虽然是税收优惠,但是绝对值不少,国家全部拿去了;内地税收比例大,但事实上成了一纸空文,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国家不仅收不到,还要补贴,这笔帐也要算,这就是说特区的15%甚至大于内地的33%。因此,缩小差距,只能靠发展,提高本地的劳动生产率,实现共同富裕。
记者:确实,15年的高速发展造就了特区的今天,但不能否认优惠政策对特区的重要性。而且现在不容乐观的是,我们看到,在特区拉开“第二次创业”序幕的同时,一些优惠政策正在或即将丧失,比如说,明年的关税调整对特区而言,就将形成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冲击。在这种现实面前,您认为,特区应该怎么做?
苏:特区当然是政策的产物,它本来就是中央建立的。政策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如果全部优惠政策拿去了,特区就消亡了。当然,不一定因为有了中央政策,你就能干得起来,自然还要苦练内功。就象一个企业,有再好的政策,如果管得一蹋糊涂也好不了。但管理不能代替改革,苦练内功不能代替中央大政策。这里需要一提的是,今年在体制改革上有种错误的说法,企图以管理来代替或部分代替改革,这是很可怕的,导致了体制改革的停滞。中国的体制为什么要改革,不就是原来那一套不行吗?让大批企业苦练内功,向管理要效益不是不好,但原来的框架不打破,怎么努力都证明是不行的,事实上,改革就是对秩序的破坏,是制度的创新,中国的改革不是小修小补,而是第二次革命。
1996年的降低关税,是从全国的意义上来考虑的。只有走向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相通了,才能建立商品经济的正常市场秩序。这是一个趋势。如果这方面的优惠没有了,特区不妨从别的方面比如说加强辐射、扩大开放度上多下功夫。而且我认为,深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上仍大有文章可作。
首先在企业制度的改革上,显然深圳能继续走在前面,并且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说“三级授权经营”模式虽然已经得到了全面的推广,但直至目前,依然留有相当多的问题,如对国有企业怎么管理?路子到底怎么走?这都需要进一步研究。而且,我对这个新型的“委托—代理”制度本身也存在着疑问:经营者能不能尽职尽责地维护国有资产或者说所有者的代理人能不能有效地监督经营者?在西方的私有制经济中,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机制非常明确,而在我国公有制条件下,“合谋机制”则很可能取代“监督约束机制”,发生代理人与委托人相互勾结的集体寻租活动,从而联手算计国有资产。所以这样模式的“委托—代理”制能不能适应公有制还是个问题。
其次是市场要素的完善。虽然深圳的市场化走在了全国的前面,但从总体上而言,现在还谈不上已经完全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如在资本市场上,国有股还不能流通,法人股也比较麻烦,光靠个人股流通,市场怎么能活起来;再如劳动力市场,深圳的聘任制比内地要好一些,但公务员制度还是没有建立,市场双向选择机制也没有完全形成等等。当然,这些方面的滞后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步伐这两年有所放慢有关,但在有限范围内,特区还是能做不少事。
总的来说,深圳的条件,不管以后怎么艰难,在我看,还是全国经济发展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历史包袱少,人口总体素质不错,只要市委市政府能抓住发挥特区关键作用的东西,抓好企业体制改革、市场的完善、宏观的调控这三条,特区还是大有可为的。
记者:这么看来,特区肩上的担子还很重,任务还相当艰巨。但是面对众多的历史使命和发展目标,特区的脚步却似乎没有了前15年的潇洒,故而这一次创业能不能重现辉煌,还是颇令人担忧的。请谈谈您的看法。
苏:特区超常发展也好,正常运作也好,我们不能给特区太多的压力。我在文章中也讲过,深圳不可能是“终身先行者”,也不可能永远当“经验批发商”,它仅仅是一个新型城市,一个在中国最贫困的小渔村建立起来的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如果能在这基础上做更多的工作,那样最好,但指望它怎么更辉煌,我认为有些不现实。“第二次创业”不是单纯的一个具体指标,这不象石油开采,第一个15年创多少,第二个15年可能再创多少。从荒原上建起一个城市和发展一个城市是两回事,不要给它太多的要求,定位也不要过高,别的城市都没什么要求,偏偏对深圳又是要追赶“四小龙”,又是成为精神文明样板,如果象过去那样走树典型的弯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不但不会推进城市的发展,反而会毁了它。深圳仅仅诞生了15年,他还是一个孩子。“示范、辐射、带动”等功能的赋予已经使他很累了,如果不切实际地要求他再增加若干功能,就恐怕是太累了,是强人所难。当然,即使做个“太累的孩子”,也是一种光荣。
不过,同时也要看到,现在困难是不少,但以后的机会还是有的。对深圳来说,最近最大的一次机会就是’97香港回归。深圳曾提出成为香港和广州之间的一个国际性大都市,我看作为香港的沿伸,发展为一个国际化现代化的中等城市可能更切实可行些。这没什么不好的,事实上历史也证明,没有香港就没有深圳。香港的回归,对深圳也是精神上的一种寄靠。所以目前深圳要做的,就是加快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调整产业结构,客观上发展金融商贸,尽快实行国际惯例,充分发挥桥梁作用,争取在相同的秩序上为香港提供更加广阔的服务,增强大陆对香港的吸引力。
“第二次创业”成功与否,我认为关键在于两条:一是中央必须坚定把经济特区办下去的决心。希望优惠政策能真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起码到本世纪末才取消。不过还好,中央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要办好经济特区,就在前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还要求特区更好地发挥几大作用,这说明特区在长时期内还是存在的。二是特区必须提高自身的素质。目前,尤其是工作人员的素质令人担忧,以致于在某些情况下,官僚主义远甚于内地,这将成为特区内在的一个致命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