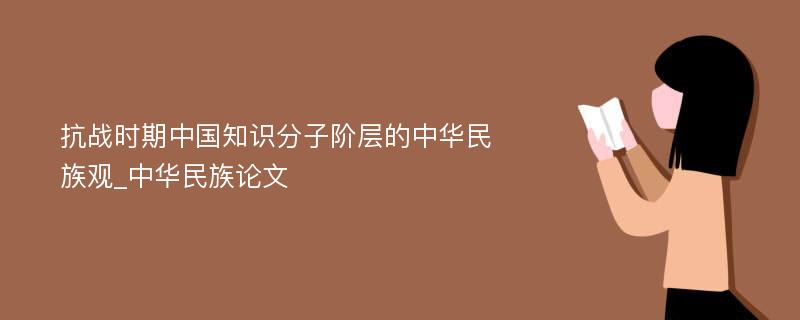
抗战时期中国知识阶层的中华民族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中国论文,中华民族论文,阶层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08)03-0087-06
中华民族经历了数千年的自在发展,到近代以后,才逐渐开始出现自觉发展。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自觉意识发展的重要阶段。自九一八事变后,侵略中国的日本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构成极大威胁,中华民族成员在与“民族之敌”的殊死较量中,对民族共同体共同的命运有了深切的体验、对共同体的民族文化有了明确的认同。而知识阶层则开始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范畴、共同体的一体性与本质、共同体结构的体认与自觉,促进中华民族自觉意识发展到更高的层次。
一、知识阶层对“中华民族”概念和中华民族范畴的探讨
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中华民族成员现代民族意识的自觉。知识阶层是中华民族现代民族意识自觉的先驱者和传播者。尽管知识阶层的中华民族自觉过程一度受传统的种族意识和西方单一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但是,自清末民初以来,他们通过对历史上中国民族发展史的研究和对现实民族危机、民族命运的急迫关注,中华民族范畴意识、界限意识、一体意识开始自觉,“中华民族”一词也越来越频繁地被使用,并逐渐成为民族共同体共享的称谓。当然这一过程并不是单线发展,而是充满争论与歧义。争论不仅源于“民族”定义本身存在歧义,而且因为中华民族意识正处于形成之中。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知识阶层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范畴意识和一体意识逐渐清晰,其科学地、理性地审视中华民族和阐释中华民族概念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1934年,吕思勉的经典著作《中国民族史》出版,这部书探讨历史上中国民族的相互关系和中国民族形成发展过程。吕思勉在书中经常使用“中国民族”一词,也使用过“中华民族”概念。他指出:“汉族,……或称中华民族;词既累重,而与合中华民国而称为一民族者,仍复相淆。”[1]9 吕思勉的意思是指,从历史的演变来看,中华民族指称汉族,现在中华民族是中华民国内的所有民族的统称,这二者存在混淆。其实早在清末,梁启超就曾经对中华民族与汉族的关系做了澄清,并“悍然下一断案曰: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2]4 而吕思勉为避免混淆,以“中国民族”来代替“中华民族”,即中华民国内所有民族的统称。1935年,赖希如在《中华民族论》一文中给“中华民族”一词下过完整的定义,把吕思勉的意思进一步明确:“我们现在称‘中华民族’,就狭义说,当然指的是中国境内民族的主体汉族。汉族古称夏族,然夏和汉皆为朝代之名,非民族之本称,今民国已确定以‘中华’为族国之全称,故用今名。复就广义说,中华民族是统指中国境内诸种族的全体而言,今日中国境内分别为六种种族即汉、满、蒙、回、藏及未开化之苗族、瑶族及其他各族,就人类学上和民族学上,当然有显著的分别。惟汉族和其他各族经数千年长期间的接触,辗转东亚大陆,互相交杂,在血统上实已混乱。若细加分析,汉族的血统中实包含有其他五族的若干成分,如满族之东胡、鲜卑、契丹、女真;蒙族之匈奴;回族之突厥、回纥;藏族之羌。元、清两代,蒙族和满族之同化汉族,则尤为显著。至苗族如今云南之一部分进化的土司,亦渐已同化于汉族。此种同化一方面是血统上的混合和生活上的同化,另方面是精神上接受汉族的文化,很自然地铸成了新中华民族固结的基础。故汉族其实为中华民族的母体,自然应代表中华民族之全称。”[3] 赖希如明确地将中华民族一词赋予了两种含义:即狭义上只包含汉族;广义上包括中国境内全体民族,汉族是核心,是中华民族的母体。随着中华民族范畴意识的逐渐形成,“中华民族”狭义上的意义渐渐失落,广义上的意义流行开来。
1935年林语堂在美国出版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中文译名为《中国人》或《吾国与吾民》。林语堂在考究中华民族的概念与特性时认为:“中华民族种族构成的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作为一个人种实体,中华民族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是古老民族的特点呢?还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还年轻,在种族上远未成熟的那样一个民族的特点?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区别:中国人在文化上是古老的,在种族上是年轻的,这是一个当代许多人类学家都主张的观点。”[4]52-53 他还说,“中国过去是一种文明,不仅仅是一个民族。”[4]341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华民族举国投入卫国战争中,知识阶层对中华民族含义作了包含国家的意义、人民的意义、民族构成的解释。学者芮逸夫指出,中华民族“由国家的意义说,它现在拥有1100万余公里的国土,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由民族的意义说,它现在包含华夏、通古斯、蒙古、突厥、土伯特、倮倮、么些、佧侵、摆夷、撞、仲、黎、苗、瑶等族”[5]。还有的学者对中华民族概念做出进一步解释:“中华民族者,非吾族以往历史上之名词,乃中华民国以内之数个民族,结合而成为一个民族之总名词。”[6]21-22。罗香林提出,中华民族“是构成中国这个国家的主体,他是中国所有人民的总称,所以凡住在中国领土以内而取得中国国籍的人民,都是中华民族的细胞,他们的综合就是中华民族的内蕴。这是中华民族的第一定义。……就广义的观点来说,凡是与中国人民同一种属源流的,都是中华民族,这是中华民族的第二定义。”[7]
由此可见,知识阶层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了理论上的审视,概念上的探讨,虽然并未取得一致,但是中华民族一词正在成为中国各民族统称的称谓,学者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范畴的认同是一致的,即包括中华民国境内的全体民族,或者包括全体中国人。而存在的歧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特性到底是什么?是种族共同体?还是文明共同体?还是文化共同体?因为这涉及到共同体的认同依据。
赖希如认为中华民族既有“血统上的混合和生活上的同化”的特性,又有“精神上接受汉族的文化,很自然地铸成了新中华民族固结的基础”的特性[8]。林语堂则认为,“从‘民族’这个词语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只有中国才可以称作一个民族,一个受过单一文化熏陶的同族人的政治集团,他们具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学和某些共同的道德价值上的准则”,而在血统上是一个正在形成的种族。他指出,格里菲思·泰勒根据移民区模式,把中国人划分在人类进化中最年轻的一层。
实际上,他们都混淆了民族与种族的概念。如果将种族的融合作为中华民族认同依据的话,那么中华民族实体就成为“将来时”而非“完成时”。这样说来,中华民族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这是一个极大的悖论。
当时中国民族主义文学派作家陆震遐也认为共同的种族是中华民族的特性。他的长诗《黄人之血》就以元朝蒙古人为代表的黄种人远征俄罗斯的“英雄业绩”来唤起黄种人对于同一段历史的自豪感,这原本是为了通过对民族历史的叙述,以人种来认同包括蒙古在内的中华民族。但是,从民族角度来说,当时各族群对蒙古的西征有着不同的记忆,蒙古人的辉煌与汉族的反抗曾同时存在。中华各民族有“共同的历史回忆”,也有“不同的历史回忆”。以蒙古人远征俄罗斯作为“共同历史”来构筑中华民族认同,恰恰是民族主义者的悲哀。《黄人之血》明显地受到了近代以来一度盛行的“种战”论述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认同依据的混乱。
有学者认为,“民族的真正本质是无法陈述的,所以,民族的均质化、实体化最后只有通过对‘民族之敌’的论述性构建才能得以实现。‘民族之敌’当然是想象性的,他们同时存在于民族内外。对民族之敌的想象性构建,能够增进共同体成员对于作为想象共同体的民族的集体认同”[9]92-194。“民族之敌”的存在的确有利于民族整体意识的自觉,但是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的民族之敌不是想象的,也不是与“黄种人”对立的“白种”,《黄人之血》所针对的“民族之敌”——白种是“种战”论的余绪,是一种过时的“敌情判断”。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华民族之敌不是某一种族,而是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包括在黄种内的日本人。针对“民族之敌”,“谁是我们”不能靠种族来认同,而是靠“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利益”来认同。齐思和等学者反对以种族作为民族认同的标准,指出“种族”在西方是一个正在衰落的观念。他认为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民族形成的重要因素,而这种意识来自共同的历史背景、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荣辱记忆,甚至认为外国势力的存在对民族意识的形成是不可欠缺的。[10] 因此有当代学者认为:“正是由于关系民族利益的民族意识的历史累积,才衍生出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11]170-171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利益使中华民族成员产生一体意识。而知识精英的中华民族观正在进一步深化,它既包括国土范畴,也包括人民的范畴和民族构成,既具有政治含义,又具有民族含义。虽然也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并不包括政治含义,只是民族学含义,但是从认同趋势来看,种族的认同逐渐淡出,中华民族成员对国家的认同、对各民族一体性认同意识普遍增强,这些认同正在变成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意识。
二、知识阶层的中华民族一体观
虽然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民族之敌”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但是中国民族危机都是以中华民族整体形式出现的,知识阶层从理性层次上认识到中华民族有共同的国防、共同的边疆,中华民族在地理上是一体的。九一八事变以后,这种中华民族整体性、唇亡齿寒的关系被知识精英表述为:“东北亡,热河丧,新疆变,西藏乱,这一套亡、丧、变、乱的痛史,才引起了国人注意边疆之诚心。”[12] 边疆研究专家指出: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中国全部边疆进入多事之秋,绥远问题、满洲事变,“还有不少的澜涛翻覆汹涌,甚至卷上这个‘中国’号的船面,冲破船腹。怎样渡过这个惊涛险浪,实是这个有覆舟的险的‘中国’号的全体船员之责呵!”[13]2 七七事变以后,中华民族对日本这个“民族之敌”的仇恨普遍增长,对中华民族的共同命运有了深切感受。以“中华民族”相号召的“焦土抗日”融进了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阶级的思想和悲壮命运之中。林语堂指出:“是日本的武装侵略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使得中国团结得像一个现代化国家应该团结的那样众志成城。在现代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团结一致地行动起来,像一个现代民族那样同仇敌忾,奋起抵抗。于是,在这种血与火的洗礼中,一个现代中国诞生了。”[4]343 霍布斯鲍姆也曾经提出,民族产生的要件之一便是武力征服。“说来令人难堪,就像李斯特早已指出的那样,似乎只有在优势民族挟其强权进行兼并的威胁下,才会让被侵略的人群生出休戚与共的民族情愫,一致对外。”[14]39
中国知识阶层从中华各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实际出发,理性地思考中华民族一体性,承认、了解、研究中国多民族的存在与统一问题成为他们的共同特征,他们走的是一条从“识异”到“求同”的路。一些关于边疆问题、边疆研究、民族问题的书籍和文章纷纷问世,这些著述历数民族多元的存在,民族问题的发展与现状和当代边疆问题的成因①,探讨解决边疆民族问题,以共同御外的办法。
顾颉刚指出:“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受够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份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归我们的。……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政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叫起来,这不是我们的耻辱?”[15] 他认为地理与民族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主张从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的角度研究中华民国领土范围和民族。顾颉刚号召“以前与汉族没有关系的许多种族之民,在今日‘团结为一个国族’的目标下,一齐努力向前迈进……这是我国家复兴的原动力”[10]。杨青田著文说:“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中心(满回两族也多与汉族杂居),满蒙回藏及西南夷各族则围绕在东北、北方、西方,西北及西南边地,成为一大半圆周形。而边疆的纠纷事件,也就不断地发生在这个半圆周形的地带以内。”[16] 一些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系五大民族合组之国,必使五大民族联合而成一中华大民族”[17]12。大中华民族或者中华大民族的提法说明了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知识阶层中华民族意识的模式,即在各民族平等的前提下认同中华民族,也在这一前提下思考中华民国的民族政策以及中华各民族的关系。他们认为“总理遗训在合各民族以造成一强固之中华民族,揆此意也,即各民族之特性似未许其永远存留,致为合作之梗,而同时总理则又主张扶持弱小,俾各族有充分自治之表明,是各族之特性,固又未许其泯灭也,然则总理之意究何居乎,夫强邻环伺,非团结无以共存,故凡为共存之梗者,必须铲除净尽,以谋意志之统一,此前意也,习惯风俗、宗教信仰、因地制宜,无关宏旨,应许存在,各遂其生,此后意也,二意已明,斯知并存而不相害,并行而不悖矣”[18]21。
学者的努力集中在“树立国内各民族同属于中华民族的意识与国家观念,灌输民族思想,使其明了整个中华民族之意义”上面。在这个目的下,应采取的手段是:“尊重各民族之固有特性,并益发扬之”,“尊重各民族之文字,并利用其文字,以灌输各科知识”,编撰有利于培养中华民族意识的教材[18]41;尊重信仰自由,“改革宗教,为民族上进之先声”[19];重视边疆,开发边疆,开发西北,以民族平等的精神,让西北各民族享有民权。“凡许多民族同在一个政治及经济组织下生活,如果没有维持着一种合理的相互关系,那么纠纷是一定不可免的。因为一个民族,必有其自己的特殊的体格,语言,风俗,历史和文化”,“而一个民族复杂的国家,倘若内部没有调整的关系,无论它土地大小如何,人口多寡如何。对内总受不了纠纷,而对外也总是没有力量的”[16]。1937年,《禹贡》出刊三周年《纪念辞》中指出:“在这样严重的时势之下谁不感受到窒息的痛苦,只要是有血气的人谁的心里不曾沸腾着热血,于是嚷着救国。可是救国固仗着热烈的感情,但尤其仗着冷静的理智;救国不是一个空谈的问题,乃是许多有效的实际规划与行动的总和。……我们要鼓励远游的兴趣,改变昔日怕出门的习惯,使得荒塞的边疆日益受本国人的认识与开发,杜绝了野心国的觊觎。我们要把我国祖先努力开发的土地算一个总帐,合法地承受这份我们国民所应享有的遗产,永远不忘记在邻邦暴力压迫或欺骗分化下所被夺的是自己的家业。我们要把我们祖先冒着千辛万苦而结合成的中华民族的经过探索出来,使得国内各个种族领会得大家可合而不可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使命,彼此休戚相关、交互尊重,共同提携,团结为一个最坚强的民族。”[10]
三、知识阶层的中华民族结构观
知识阶层的中华民族一体观的形成不仅来源于“民族之敌”的威胁,来源于对中华民族共同命运的切身感受,也来源于对中华民族多样性的理性认识和对多样性的中华民族一体融合的历史发展道路的认识。中华民族一体发展的趋势和现实与中华民族多样存在的历史相纠缠,引发了知识阶层对中华民族结构的自觉与争论。
民族学家江应樑指出:“今日之中华民族,绝对不是以一般所谓之汉民族可以概括一切的,也不是如一般所谓之汉满蒙回藏五族可以概括一切的,把汉族看作主人翁来代表中华民族是绝大的错误,把中华民族分为汉满蒙回藏五族更是绝大的荒唐;……今日之中华民族,实是整个的,同一的,而无所谓分歧的。能对于中国领土中全部民族的各个分子均有一个彻底的明了认识,方能说得到了解我们自己,方能说复兴中华民族之道。”[20] 中国民族学家不像外国民族学人类学家那样,一味地对各民族进行“识异”,而是在此基础上“求同”,在对各民族的比较研究中,肯定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同一的”。
顾颉刚针对日本利用“民族自决”的口号在中国西南掸族、东北内蒙古地区进行分裂中国的阴谋,写下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呼吁“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能再析出什么民族”,“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应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称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致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词之下,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明确提出“我们所以要抗战为的是要建国,而团结国内各种各族,使他们贯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实为建国的先决条件”[21]。他认为,中华民族在血统上、文化上都经过了长期融合,没有什么汉人文化,只有中华民族的文化,“五大民族”的说法是不科学的。[22]
在顾颉刚鲜明地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命题时,引来一片赞同之声和一些反对意见。张维华赞同这一看法,认为“一是从政治的联系上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关系上说,非成为一个不可。……换句话说,这个‘一个’的意义,是合则共存,离则俱亡”,“第二方面是从血统上或是文化上,说明国内各民族是混一的,不是单独分立的,因为是混一的,所以成为一个”[23]。他要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加强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并认为“这正是解救时弊的一付良药”。黄举安《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指出,“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虽然有过各种民族名词的记载,可是是否都能当得起民族的称号,实在大有讨论的余地”。他甚至主张“现在一般人称的汉、满、蒙、回、藏、苗、夷等名词,同样没有存在的价值”。如果说顾颉刚让“大家留神使用‘民族’二字”的话,那么黄举安干脆提出“滥用名词(指用民族一词),恰好给野心者一个侵略机会,像泰国也在高唱滇桂是他们故居的谬论,这责任不能不归之于乱喊‘民族’的人们来负担”[24]。
费孝通、翦伯赞等学者不赞同“中华民族是一个”。费孝通撰写了《关于民族问题讨论》,认为中华民族应团结一体进行抗日,但是从民族研究学理角度也应该承认中国是一个拥有众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事实应当受到尊重。抗日并不一定要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存在。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人群发生共同的利害,有对内稳定、对外安全的需要,自然有可能结成一个政治团体。因此实现政治上的平等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谋求政治上的统一,不是要消除各民族及经济集团之间的界限,而是要消除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25] 翦伯赞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命题“包含着否定国内少数民族之存在的意义,然而这与客观的事实是相背离的”,他指出,主观意愿不能改变客观事实,国家确实需要国内各民族的团结统一,但“团结”不是“消灭”,“团结”不但不应否定其他民族之存在,并且应扶助他们的独立自由之发展,把中国国内的一切不同语言、文化与体质的少数民族,消解于一个抽象的“团结的情绪”的概念之下,而概念地造成一个中华民族,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中华民族也只是一种观念的中华民族。只有承认各民族之生存乃至独立与自由发展的权利,在民族与民族间建立经济的政治的乃至文化的平等关系,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26]
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者其实无法回避中华民族多样性的历史与现实,他们往往把多样的中华民族归结为“同源异流”或者“异源同流”。当时有学者这样归纳:“中华民族内之若干支,自古实同一祖先;经过五千年之流转迁徙,种种演变,固曾分为若干不同之名称,迄今尚有一部分各异之痕迹,但追溯有史以来之血统,仍为一元的。”“另一派主张,则谓今日之中华民族,系由有史以来若干不同之民族互相接触之结果,逐渐循着自然之趋势,陶熔结合而成为今日之一个庞大民族。在过去中国历史上之若干民族中,当然以华夏系(即后之汉族)之文化为最高,故同化工作上,亦以华夏系为主干,逐渐将华夏之文化,向东西南北发展,最后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生活血统各方面,将四围之外族,同化吸收,使之加入华夏系之中,而消弭民族之界限差别于无形。”[6]21-22
黄举安根据历史记载和田野调查,证明“满人早就同中华民族凝成一体,无分彼此了”,“蒙古是匈奴人后裔”,“匈奴出于淳维,淳维出于夏后氏”,“是黄帝的子孙”。他还引用《山海经》、《后汉书》,证明藏族、西南的苗夷与汉族都是“同源”的。[24]
芮逸夫主张“同流说”:“我中华民族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多元的:领土兼具多种地形,人种混凝多种族类,语言包括多种支派,文化融合多种特质。然此种种,早已混合同化,而归于一。秦汉的统一,是我国族的初步形成;西晋时五胡的乱华,而突厥人种同化于我,然终被华化;而各个成为今日中华国族的重要分子。正如江汉的不辞细流,所以能成中华国族之大。”[15]
持“同源说”的学者受历史文献记载和传统民族意识的影响,但这并不是中国民族历史的全部真相,很多学者“不敢苟同”,认为“汉苗风习不同,语言迥异,数千年来彼此争战,虽一胜一败,而今犹未被同化,焉得谓无族可分?”[27] 少数民族亦不承认同源说;持“同流说”的学者虽然具有“多元”与“一体”视角,但其一体观大都以文化的融合角度或种族融合的角度立论。说中华民族已经融合为一体,“无分彼此”,这也不是民族历史的真相。而按芮逸夫的说法,“我国人向来有句谚语,叫做‘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但那是指细节而言,若就大体上说,都是大同小异的,只有蒙古、西藏、新疆,差异稍大,然其化而为大同小异,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5]
可见,知识阶层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范畴和共同体的一体性取得一致认同的前提下,对于中华民族到底是单一民族,还是多个民族的集合体的问题产生分歧。这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内部结构认识的分歧,争论的双方对中华民族结构的认识都具有合理的一面,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既是多元的,又是一体的,只是由于中华民族这种独特的结构,无法套用一般的民族概念来解释,再加上这种争论发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知识阶层对中华民族结构的认识深受民族战争的现实影响,辨清二者孰是孰非的学术条件和现实条件尚不具备。
庞中英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存在着‘竞争性认同’(competing identities),就是说,中华认同与国内各族群认同可能陷于冲突”[28]106-107。中华民族的独特结构使这种冲突在抗日战争时期显现出来。当时一部分学者强调两种认同的冲突性,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一部分学者看到了两种认同的共存性,提出“民族团结不应否定其他民族的存在”。这一争论实际上是丰富中华民族含义的过程,中华民族的主权意识、疆域意识、民族一体意识在争论中得到传播,中华民族的传统意识与现代意识产生互动,中华民族概念的政治性和民族性不断浸润。以《益世报》为阵地的争论暂告一段落后,芮逸夫对中华民族概念总结道:“我尝以为,中华国族、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三个称谓,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由社会及文化的观点来说,应称中华民族;由政治及法律的观点来说,应称中华国家,而中华国族,则兼具社会、文化及政治、法律的种种观念成称说的名词。”[5]
尽管中华民族的概念没有形成共识,但是抗战时期知识阶层的中华民族观由此得到深化,推动着民族大众中华民族意识的形成,也为当今的中华民族自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收稿日期]2007-07-26
注释:
① 当时重要的边疆民族问题的书籍如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凌纯声等:《中国今日之边疆问题》,南京:正中书局1934年版;马鹤天:《内外蒙考察记》,上海:新亚细亚学会1932年版;华企云:《中国边疆》,上海:新亚细亚学会1932年版;方秋苇:《中国边疆问题十讲》,上海:引掣出版社1937年版;黄慕松:《我国边政问题》,南京:西北导报社1936年版,等等。
标签:中华民族论文; 民族论文; 汉族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边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