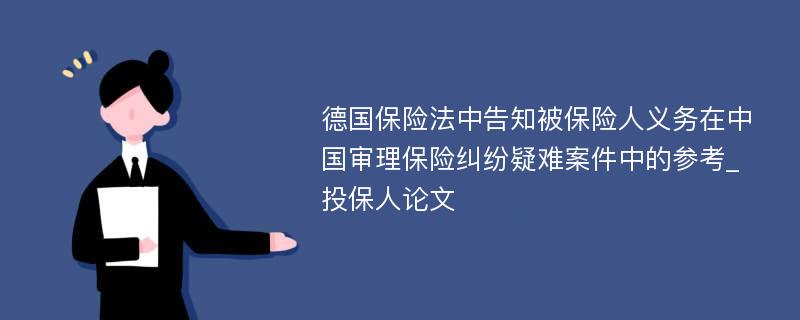
德国保险法的投保人告知义务规定对我国审理保险纠纷疑难案件的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险法论文,投保人论文,德国论文,疑难论文,案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并规定了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但是,该条规定在保险审判实务适用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争议。德国保险合同法制定于1908年,被称为德国旧保险合同法。该法于2007年11月23日又被重新制定,称为德国新保险合同法。德国新保险合同法对德国旧保险合同法以及保险法实践中的投保人告知义务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加以完善,笔者认为这对我国审理有关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案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文以通过介绍德国法的相关规定为出发点,对我国审判实践中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若干疑难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审判实践或者制定保险法司法解释提供参考。
一、关于如实告知义务人的问题
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该条款明确了承担如实告知义务的是投保人,但被保险人是否负有如实告知义务,在审判实务中不无争议。
对于被保险人是否负有如实告知义务,我国学者多认为,无论在损害保险还是定额保险,被保险人如果知道危险状况,而投保人并不知道,那么被保险人亦负有如实告知义务。①主张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义务的观点认为,“对于损害保险来说,被保险人是保险标的的所有人或者保险利益的归属者;对于定额保险来说,被保险人是保险事故发生的对象,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及其他危险状况则最熟悉,因此赋予被保险人此项如实告知义务才能达到保险人评估与控制危险的立法目的。”②但笔者认为这样的论证在逻辑上并不成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
首先,这样的观点让并非合同当事人的被保险人承担保险合同上的义务,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同一人的情况下不成问题,但是在纯粹为被保险人利益的利他合同中则存在问题。因为这违反了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如,在雇佣关系中,作为被保险人的员工同作为雇主的投保人约定,由投保人为员工投保员工第三者责任险,一般情况下保险人只是将询问表格交给雇主,由雇主去询问员工。如果雇主没有询问员工,则被保险人由于违反了法律义务而无从获得保护。若法律赋予被保险人告知义务,那么由于被保险人违反法定的告知义务,其亦不得基于雇主违约而请求雇主赔偿,这显然对于被保险人不利。因此,对于被保险人来说,其并非保险合同的主体,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理,不能要求并非合同主体的被保险人来负担义务。其次,如果赋予被保险人如实告知义务,那么在被保险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时,法律后果却是等同于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的法律后果。这样的逻辑等于让投保人为第三人的义务承担责任,显然与对自己的自由意思负责的民法基本原理相违背。再次,对于被保险人知悉的危险情况,被保险人不负告知义务并非就没有其他好的风险控制方法。
针对被保险人知悉的危险情况的告知义务问题,德国新保险合同法第47条第1款第1项规定:“如果投保人的知悉和行为具有法律意义,那么在为他人计算的保险合同中,亦需要考虑被保险人的知悉和行为。”这样规定的结果显然将投保人的知悉和被保险人的知悉等同起来,但是仍然将如实告知义务的主体限制为投保人,将即使是为他人利益订立的合同也保持在合同相对性的框架之内,而不是赋予被保险人如实告知义务。因此,对于被保险人所知悉的危险情况,投保人负有告知义务,如果投保人对于被保险人所知悉的危险情况没有告知,就视为其自己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我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告知义务的主体是投保人。基于上述理由,这样的规定是正确的。但是,保险法的规定并没有涉及到被保险人所知悉情况的告知义务问题。对此笔者认为,我国的立法或者司法解释应该一方面否定被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另一方面,为了保持保险法上的利益平衡,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可以借鉴德国法的规定,在未来通过修改保险法或者制定司法解释时作出规定:“如果投保人负有如实告知义务,那么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知悉亦需要负担如实告知义务。”③
当然,鉴于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之一是投保人,因此,在具体的保险实务操作上,推定投保人知悉并且需要告知被保险人知悉的危险情况,在被保险人欺诈或者故意隐瞒导致投保人并不知悉从而未如实告知的情况下,投保人也不能提出其不知悉及不能知悉的抗辩。如,在学校为全体学生投保意外伤害保险签订的保险合同中,保险人明确说明了一系列疾病不保的范围,学校将投保申请材料发到每个学生手中,由学生自行填写,某学生故意隐瞒了其患有不在承保范围的某种疾病,后该学生由于该种疾病的原因而发生医疗费用,保险公司得主张投保人的未如实告知责任,投保人则不能以学生欺诈或者故意隐瞒患病情况而导致其不知作为抗辩。
二、关于如实告知义务受领人的问题
我国保险法并未规定如实告知义务的受领人。保险人当然具有受领权,但是,保险代理人是否具有告知受领权存在争议。
德国旧保险合同法第43条第1项规定:“保险代理人具有受领关于订立、延长或变更保险合同的申请及撤回此申请的请求”。但是,德国旧保险合同法第44条又规定:“依照本法规定须保险人知悉才适当的情况,受委托招揽保险的代理人的知悉,不相当于保险人的知悉”。因此,在适用德国旧保险合同法的实践中经常发生保险人一方面赋予保险代理人承揽业务、收取费用、扩充业绩的权利,另一方面却又有保险代理人被告知的信息不能对保险人发生作用的限制,这显然对投保人不利。为了克服投保人的这种不利地位,德国法院判决发展出来保险代理人是保险人的“耳目”理论,即保险代理人所知悉的情况亦是保险人所知悉的情况。进一步,法院又基于保险代理人的“耳目”地位针对德国旧保险合同法第43条第1项确定了一个法定的基本思想,即不允许通过一般条款改变保险代理人的“耳目”地位。④在德国新保险合同法制定过程中,保险代理人的这种“耳目”地位被写入到该法第69条和第71条中。而为了确保这种“耳目”地位不得被更改,德国新保险合同法第72条明确规定:“对保险代理人根据第69条和第71条规定享有的代理权进行限制的一般条款,对于投保人和第三人是无效的”。因此,保险代理人有接受告知的权利,并且这种接受告知的权利不允许通过一般条款被更改。
我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保险代理人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佣金,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机构或者个人”。对于保险代理人是否享有告知受领权的问题,存有很多争议。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财产保险的保险代理人的告知受领权争议较少。但在寿险部分,往往少数代理人为赚取佣金而存在故意诱导投保人不实告知或者向保险公司隐瞒告知的事实,因此有的保险公司采取了否认保险代理人具有受领告知的权限。
笔者认为,德国法的立场值得借鉴。首先,代理的法律本质在于将代理人的行为后果归属于被代理人。如果一方面允许保险代理人从事招揽业务的行为,另一方面却又限制其被告知事项的效果不能直接归属于保险人,显然违反保险代理人作为保险人的“耳目”地位的本质。其次,对保险代理人的业务行为的控制风险应该归属于保险人,而非投保人,否则由投保人承担保险人所委托的代理人的行为后果,没有法律依据和法理依据,不符合公平原则。再次,对投保人和保险代理人串通损害保险人利益的情况,可以通过其他法律救济途径来解决。⑤
综上,鉴于我国并无保险代理人告知受领权的规定,在未来应该在立法或者司法解释中规定保险代理人的受领告知权,并禁止对这种受领告知权进行限制。具体来说,可以规定:“投保人对保险人的询问亦可向保险代理人告知。对保险代理人受领告知的权利进行限制的一般条款对投保人及第三人无效。”
三、关于投保人如实告知的义务范围问题
对于投保人如实告知的义务范围,在比较法上有不同的模式,主要有无限告知义务模式和询问回答义务模式。
无限告知义务模式。在保险发展初期,由于保险技术尚不发达,保险经验比较缺乏,因此对于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要求非常高,需要投保人对于所知晓事项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客观地进行无限告知。德国旧保险合同法第16条第1款规定:“投保人知悉且对于危险承担重要的情况,应于订立合同同时告知保险人。”就是采取的无限告知义务模式。但是,随着现代保险技术的发展,无限告知义务模式已经不被当代保险立法所采纳。而德国保险法实践也已经否定了这种无限告知义务模式。询问回答义务模式。根据此种模式,投保人应告知的事项以保险人所询问的事项为限。此种模式不但符合现代保险发展进步的趋势,而且对于欠缺保险知识的投保人也有很好的保护作用。⑥因此,目前很多国家的保险立法均采取此种模式,德国新保险合同法第19条第1款规定:“保险人于要约前应将其所知悉的对于保险人基于书面形式所询问的关于决定保险合同内容具有重要性的情况告知保险人。”我国保险法也采取的是询问回答义务模式。
对于询问回答义务模式的询问回答目前又有两种立法例。第一,自由询问模式,即保险人的询问可以采取口头、书面或者其他的形式。第二,书面询问模式。指投保人所应告知的事项,以保险人的书面询问为限,对于未以书面询问的重要事项,投保人不负告知义务。奥地利、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采取此种模式。
我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因此,我国保险法规定的是询问回答义务模式。但保险法并没有规定保险人的询问方式,而根据文义解释,应该理解为自由询问模式。在我国的保险实践中,保险人往往为了揽客需要,仅仅进行口头询问,并且通过格式合同的方式要求投保人在保险合同上划勾,而投保人往往不会详细阅读保险合同的内容,甚至还存在保险人诱导情况下的故意隐瞒。在发生争议时,往往涉及对于保险人询问内容的确定问题。由于保险人往往通过格式合同的方式向投保人询问,投保人则很难证明其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反之,对于保险人来说,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却比较容易证明,这不利于对投保人利益的保护。因此,笔者建议,在将来修订保险法时应明确采取书面询问模式。通过书面询问的模式,投保人可以对于其所回答的问题进行充分的准备,并且对于其回答的后果予以充分的权衡。而在发生争议时,应该将已经询问及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举证义务赋予保险人。另外需注意的是,如果保险人采取格式条款的方式对投保人进行询问,那么保险人需要证明其明确询问,否则这种询问对于投保人并不发生效力,而投保人不需要承担告知义务。⑦
四、关于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时间问题
合同经要约——承诺而成立,投保人要在发出要约之前(或要约时)将其所知道的对于承保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以及保险人所不知道的情况完整以及正确地告知保险人,投保人的此种义务是缔约前的义务。而保险人则可以根据投保人提供的事实作为计算保险费的基础,以便控制风险以及估计保险费,进而做出承诺。但是,在投保人提出投保申请后、保险人承诺前,保险标的物的危险状况发生变动的,应如何处理?
1.德国法上投保人嗣后登记义务的变迁。
关于这个问题,事实上涉及投保人在发出要约申请之后的嗣后登记问题,即投保人对于其发出要约之后、保险人承诺之前所出现的新的危险状况是否负有嗣后登记义务。对此,德国旧保险合同法第16条规定投保人对于其知悉的重要情况应于订立保险合同时告知保险人。从文义上理解,投保人负有要约发出后、承诺之前的重要危险情况的嗣后登记义务。但是,这种规定在德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遭到了很多批评。在新保险合同法制定之前,德国学术界的通说认为,根据德国旧保险合同法第16条第1款的规定,投保人对于在要约之后承诺之前所发生的危险状况不予告知是无可归责的,否则投保人要一直担心其要约被拒绝。⑧多年以来,德国的司法实践也否定了投保人的嗣后登记义务。德国新保险合同法则明确放弃了德国旧保险合同法所规定的嗣后登记义务,该法第19条第1款句2明确规定:“保险人在要约之后、但是在承诺之前所发生的重要的危险状况,只有在保险人对此提出询问时才具有告知义务。”根据德国学术界和判例的主流观点,这样的规定更符合立法一贯的倾向于保护投保人的宗旨,即基于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属于询问告知的告知模式,对于要约之后才知道的情况,只有保险人就此提出询问的,投保人才有告知义务。如果保险人并未询问,则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⑨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的问题,德国法规定,保险人也可以根据危险增加的规定终止或者变更保险合同。
2.完善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
我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该条规定的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是否包含投保人对于要约之后、保险人承诺之前所发生的新的危险状况?笔者认为,德国法的立法规定对于我国保险法的理论建构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我国保险法规定的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是有限的询问告知模式,因此,鉴于投保人对于保险人在要约之前的询问已经如实告知,其对于发出要约之后始知悉的情况基于有限告知模式,不负有告知义务。其次,更有利于对投保人的保护。如果投保人一直担心其要约是否被承诺,则其对于保险保护的担心是持续的,这不利于投保人利益的保护。⑩再次,在我国保险法实践中不承认投保人的嗣后登记义务,但可以通过投保人的危险增加的告知义务来弥补这个漏洞,而保险人也可以基于我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状况增加的通知义务来获得保险利益上的平衡,所以,将来在修订保险法是可以规定:“投保人对于要约之后、承诺之前发生的危险状况应负担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
3.适用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的配套法律规定的协调。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国保险法关于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规定的是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并没有涵盖要约与承诺之间危险增加的情形。从逻辑上说,保险人承诺之前,合同并未成立,谈不上合同有效期间。因此,将来可以增加规定:“投保人发出要约之后保险人承诺之前发生的危险情况,投保人亦负担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投保人未通知的,准用本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其次,尽管可以准用保险法规定的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违反危险增加的告知义务上并没有区分过错程度,不考虑主观过错的立法模式是不妥当的。但是,从目前的体系协调角度看,还应该采取准用当前规定的形式。再次,我国保险法在危险增加的告知义务规定上,没有区分保险人可以变更保险合同或者解除保险合同的具体条件,因此在适用上带来的困难更多。(11)对此,需要进一步通过司法解释来解决。最后,保险法规定的是被保险人的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这种规定并不妥当,应该赋予投保人的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因为被保险人虽然知道危险状况,但是被保险人并非投保人,非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而让并非合同当事人的第三人来承担合同上的义务,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适当的作法是如同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知悉的情况的告知义务的规定一样,规定投保人对被保险人所知悉的危险增加的情况亦应该及时通知保险人。
4.合同欺诈的协调问题。
尽管投保人的嗣后登记义务并不存在,但是,保险人是否可以适用欺诈的法律规定来行使合同撤销权?我国保险法并未规定投保人基于欺诈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对此,德国新保险合同法规定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并不排除欺诈的适用。笔者认为,应该肯定欺诈情况下的保险人撤销保险合同的适用。相较于对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的规定,欺诈是更严重的恶意,在欺诈法律效果上,应该可以准用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效果,并且欺诈也不需要存在因果关系。
如果肯定欺诈在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上的适用,并且如果确定了不存在投保人嗣后登记义务的基本原则,那么只有在保险人通过嗣后询问的方式才能够使投保人具有嗣后登记义务;如果保险人没有提出询问,那么投保人就可以认为其在发出要约之后不需要再负任何说明义务。这样的解释应该排除投保人未嗣后登记情况下基于欺诈的合同撤销权。(12)如,在人身保险中,投保人要约订立重大疾病保险,投保人对于保险人提问的以往疾病问题亦如实告知。但是,在保险人向投保人开出保险单之前,投保人获知其患上了不予承保的心脏病。基于投保人不具有嗣后登记义务,那么,在保险人对投保人没有嗣后询问的话,投保人就不用主动去联系保险人告知其患心脏病的情况。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考虑到基于欺诈的抗辩而使保险人享有根据合同法的撤销权,就使得嗣后登记的义务从窗户偷偷地爬了进来,(13)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排除欺诈亦适用于追溯保险。对于追溯保险,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三款前半段规定:“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此,对于保险合同是否可以约定自保险合同成立之前的某个时点生效的追溯保险问题,根据立法的表述是持反对观点的。但是在我国的保险法实践中,尤其是在海事保险实践中,经常对于航行中的船只投保,因此保险合同经常约定追溯到航行之前的船只,这是典型的追溯保险。(14)鉴于我国保险实务中所存在的大量的追溯保险问题,笔者在此着重探讨追溯保险中的嗣后登记义务情形的排除欺诈问题。对此,可以通过比较承认嗣后登记义务和不承认嗣后登记义务的法律后果来加以说明。如果承认投保人的嗣后登记义务,并且约定的是追溯保险,因为违反嗣后登记义务与要约前已经发生的保险事故并不存在因果关系,(15)因此在结果上保险人根据存在嗣后登记义务的法律地位享有解约权,但是其对于已经发生的保险事故要承担保险责任。如果法律不承认嗣后登记义务,并且如果法律承认保险人可以适用欺诈撤销权的话,那么由于投保人实施了欺诈,保险人就不仅仅享有合同撤销权,而且其不承担责任,因为在欺诈的情况下不需要因果关系。因此,在不承认嗣后登记的情况下,如果承认欺诈的法律后果,显然对于投保人的保护不利,不符合立法的精神。
五、关于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方式问题
我国保险法并未规定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必须采取何种方式,有观点认为,基于保险合同的最低限度内容的保障功能,应认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除以书面方式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外,亦允许以口头方式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但是这样在是否告知的举证责任方面容易产生争议。
德国新保险合同法在投保人的告知形式上采取的形式比较自由,投保人可以采取口头、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告知。但同时赋予保险人更大的义务,保险人一方面需要负担所有合同订立过程以及变更合同的记录义务,另一方面保险人需要将这种记录的文本连同保险单一起邮寄给投保人。这实质上从另一个角度赋予保险人对于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举证责任。笔者认为,德国新保险合同法的规定对于减少投保人如实告知的争议具有很好的作用,值得借鉴。具体来说,这种保险人的记录义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投保人可以采取口头、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以及其他方式予以告知,但是保险人对投保人的告知内容负担记录义务。其次,保险人在签发保险单的同时,必须将此书面记录内容同时邮寄给投保人。再次,在举证责任上,保险人要承担记录的举证责任,否则保险人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进一步而言,保险人要证明其明确询问以及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实。
鉴于通过司法解释是不能规定保险人的记录义务的。而在我国保险法修订之前,针对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的解释适用,应该由保险人对于投保人未如实告知承担举证责任。因为,只要保险合同订立,那么就可以推定投保人已经如实告知,否则保险人就不会订立保险合同。
注释:
①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至第165页。施文森:《保险法总论》,三民书局1995年版,第115页。梁宇贤:《保险法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周玉华:《最新保险法释义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②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③这实际上涉及民法上为第三人的行为归责的制度问题,保险法上不仅仅包括投保人需要为被保险人的隐瞒或者欺诈负责,而且需要为其履行辅助人或者代表人、知识代理人、意思表示代理人等的行为负责。对此的论述,参见Manfred Wandt,Versicherungsrecht,边码第629页。Looschelder,VersR 1999,666。
④Peter Schimikoski,Versicherungsvertragsrecht,慕尼黑,2008年第四版,边码第110页。
⑤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第252页;亦参见同一作者:《保险法论文集》,第三卷,第183页。
⑥张国键:《商事法论》,三民书局1985年9月版,第108页。
⑦Peter Schimikoski,Versicherungsvertragsrecht,边码第124页。
⑧参见Roemer教授在Roemer/Langheid,Kommentar zum VVG中的论述,2003年第二版,边码第8页。
⑨Manfred Wandt,Versichrungsrecht,边码第630页。
⑩参见Roemer教授在Roemer/Langheid,Komrnentar zum VVG中的论述,边码第8页。
(11)我国保险法的此缺失在德国保险法是予以明确规定的。参见Manfred Wandt,Versicherungsrecht,边码第630以下的论述。
(12)Peter Schimikowski,Versicherungsvertragsrecht,边码128页。
(13)15Marlow/Spuhl,Das neue VVG kompakt,2008年,第三版,第46页以下的论述。
(14)追溯保险属于保险分支的一种重要类型,我国大陆学者很少有相关论述,对此的论述可参见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第二卷,第271页。
(15)参见Baumann在Berliner Kommentar VVG中的论述,1999年,第二章,边码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