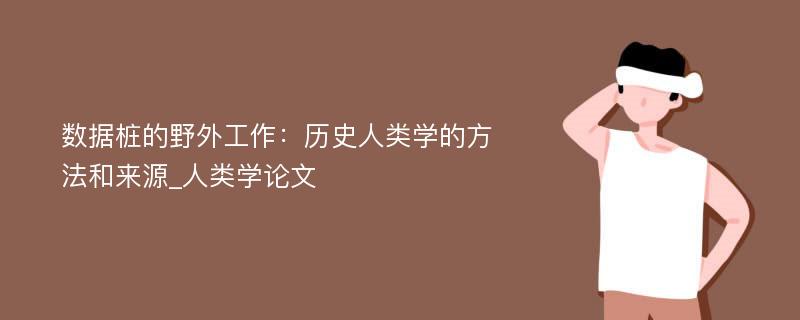
资料堆中的田野工作——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与资料来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田野工作论文,资料论文,人类学论文,堆中论文,来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1)03-0008-012
引论
1899年,福莱德利克·梅特兰写下了经常被后人引用的宣言:“不远的将来,人类学将选 择 要不然成为历史,要不然什么也不是”(1978:295)。尽管人们不同意他的观点,梅特兰的 断言给十九世纪的进化派学者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方法。进化派学者认为,跨文化结构变迁 的阶段是广泛的和一致的,形成了普同的历史。梅特兰曾在人类学家中间引起了一场争论并 延续至今,每当学科范式更换的时候,它就表现为一种新的形式。二十世纪早期,博厄斯的 历史特殊论(强调社会是由历史环境造成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梅特兰挑战直接的回应。
与之相对照的是,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占统治地位的功能主义范式是与历史无关的。譬 如,拉德克利夫·布朗争辩说,“无文字记载历史”的社会通常是人类学调查和历史研究的 对 象,在这种社会里只有猜测和怀疑。功能主义立场的含义是很清楚的。正如博克(1992:13) 所说,“很难说是田野工作的扩展导致了功能主义的兴起还是相反。人们要是滑向功能 主义的习惯用语,他们会说新的解释和新的研究方法相互很合适。不幸的是,他们支持社会 理论家把过去忘记。”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常把“无历史民族”置于固定的、静态的分析框 架中的实在论。
E.E.伊文思·普利查德在一篇关于人类学和历史的论述中评论了结构功能主义的非历史主 义,他的这篇评论或许至今与梅特兰的宣言同样有名。伊文思·普利查德争辩说,人类学是 “一种特别的编史工作”,只此“才是经验主义的,真实地讲,才是科学的”(1962:26)。 他问到人类学家习惯于研究的小型社会隔离性的问题:“尽管这些社区的结构依然相当简单 ,但它们组成了大的历史社会之一部分……人类学家不能再忽视历史……要么明确地拒绝它 ,要么承认它的关联”(P21)。
尽管有些英国社会人类学撰写了历史框架的民族志(塞泊罗Schapera1962,刘易斯lewis196 8),但是,本学科作为一个整体从功能主义范式中解放出来还是花费了时日。甚至那些在世 界上有丰富文字历史记载的地方开始工作的人类学家倾向于在表面上处理这些文字记载,或 者根本不予理睬。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s1984:xiii)描述了他到西班牙那瓦赫( Navarra)省伊卡拉(Echalar)市立档案馆时引起的震惊。“馆长办公室的墙边堆满了乱七八 糟的纸张,有些是十五、十六世纪的遗物。我做出了一个任意的决定,即使用最早的人口调 查资料(19世纪中期),在此基础线上,我可以忽略所有更早的文件。“当人类学家考虑历史 资料的时候,他们主要把这些资料当作当前民族志的背景,而不是当作人类学分析不可或缺 的部分”(西尔维曼Silver-man1979:413)。
当然,那些自称为民族志史学家的人类学家是例外,他们主要研究土著美洲人的过去。对 于很多人来说,民族志史是重建一个地区和一个无文字记载历史的民族之历史。对于另一些 人来说,它是局内人眼中的历史(格沃兹Gewertz、西夫林Schieffelin1985)。最近,有人定 义民族志史为历史意识的研究(戴宁Denning1991)。仍然有人强调应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于 历史,可以使民族志史接近历史人类学。勿容置疑,民族志史学家富有成效的工作向历时过 程分析模式的转化提供了基础。奥特纳(1984)曾在《六十年代以来的人类学理论》(Theory in Anthropololgy Since the 1960s)一书中描述了这种模式。在证明上述转换的人类学主 要著作中,有《无历史的欧洲和民族》(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r History)(沃尔夫 1982),《历史的岛屿》(lslands of History)(萨林斯1985),《甜蜜与权利》(Sweetness and Power)(珉兹Mintz 1985),《瑟琵柯河的社会:阐伯里人和邻居们的历史民族志》(Sep ik River Societies:A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the Chambri and the Neighbors)(格 沃兹1983),《大宗教:社帕佛教的文化与政治史》(High Religion:A Cultural and Polit icaal History of Sherpa Buddhism)(奥特纳1989),《西西里西部的文化与政治经济》(Cu lture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Western Sicily)(史奈德和史奈德1976),《移民一个意 大利南方城市:一段人类学历史》(Emigration in aa South Italian Town:An Anthropolo gical History(道格拉斯 198),和《权利的实体,反抗的精神:一个南非民族的文化与历 史》(Body of Power,Spirit of Resistance:Th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a South Afri c an People)(康莫罗夫Comaroff 1985)。五十年前,我们不能要求我们今天所能要求的—— 历史在民族志的视野里,在人类学的方法中找到了一个新的、严肃的,最有可能的是永久的 位 置。
在历史人类学中,是什么促进了与历史的友好关系呢?对于奥努基·铁内(Ohnuki-Tieney)( 1990a:1)来说,原因有二:(1)人们认识到“从没有无历史的文化”;(2)越来越多的人类学 家从事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所谓更复杂社会的研究。强思(Chance)(1996:392)有意回避了 如下事实,即古人实际上对某种实践和信仰起了更大的作用,这种认识在我们的分析中发生 了变化而没有持续下来。我们还应对文化概念的局限性提出挑战,这要求我们探索和理解个 人、家庭和社区的生活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并且怎样不但被地方势力而且被全球势力所 改变的。
有人说道,历史通过增加研究的案例——在时间上而不是空间上——给人类学家提供了扩 展比较研究的机会。西尔维曼(1986:125)表明,在布满灰尘的意大利省级资料馆中与历史 学家一道工作的人类学家可能在研究相同的文件,但是他或她却与“新几内亚的民族志学家 ,研究玛亚征服之前的考古学家,观察黑猩猩社会行为的研究家,以及在当代曼哈顿研究韩 国人杂货店的都市人类学家”有着类似的目的和问题。历史人类学家趋向于在地方性区域提 出大问题,并在跨文化比较的框架下研究该问题。因此,珍和皮特·史奈德(1996:3)在西 西里开始研究出生率下降和阶级意识形态问题,他们如是说:“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人口 历史上出现的戏剧性事件和灾难,以及后人如何评说,乃本研究最广义之旨趣。西西里一社 区于1860至1980年间人口之消长,乃本研究最狭义之关注。” 虽然,关于人类学与历史的密切关系已有众多著述(孔Cohn 1962,1980,1981;戴维斯Davis 1981;亚当斯Aderns 1982;萨林斯1983;克兹奈特Kertznet 1986;麦笛克Medick 1987; 彼尔思科Biersack 1989,1991;罗瑟柏雷Rokseberry 1989;凯劳格Kellogg 1991;考码罗 夫和考码罗夫Comaroff 1992;西尔维曼和格利夫Gulliver 1992;德克斯Dirks 1996),但 历 史人类学的方法很少谈及。有一种含糊其词的说法想当然地认为,历史人类学就是通过文字 资料重建一个社会的过去。但这些资料是些什么?怎样评估和使用它们?那些自称历史人类学 家的人做的事与历史学家有所不同吗?或者与那些自称为民族志学家的人也有所不同吗?如何 在资料馆里做田野工作呢?
当然,历史田野的方法是由询问特殊问题来塑造的。雷那多·罗塞尔多(1980)主要依靠口 头历史,来探索菲律宾卢桑北部伊隆哥特猎头们战争文化的建构。布莱特(Brettell)(1986) 和奈廷(Netting)(1981)使用了残缺不全的记载,分别调查了一个葡萄牙村庄和一个瑞士山 区社区两、三个世纪的人口统计模式和亲属关系。科兹(Kertzer)(1984)使用了同样的方法 研究了过去整整三十年间意大利中部的家庭结构。萨林斯(1981,1985)把神话的分析和历史 资料的分析相并置,探讨对库克船长之死(于1779年被夏威夷土人杀害)所做的主客位解释之 区别。孔博纳(Bernard Cohn,1987,1996)在资料馆里做了毕生的田野工作,接触了大量的资 料来源(各种法规法典,统计明细表格,官方调查,其他已发表的报告,游记,报纸,管理 档案,以及博物馆展览细目等),这些文本可被解构以反映印度殖民社会的本质。最后,马 勒·帕沃斯(Marla Powers,1986)使用了传记的方法和生活史来记载奥格拉拉·萧克思(Ogla la Sioux)女人的生活变迁。
在本章的最后,我将进一步讨论这些不同的历史方法。我开始讲资料来源,以及人类学家 怎 样使用资料来研究家族史,人口统计史和政治经济史。我特别注重应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 注重宏观和微观的历史方法之区别。随后,我讨论生活史和口头史。然后,我将简要谈及可 被用于历史人类学的其他来源和方法,特别是物质文化和影视表现。结尾时我将考虑民族志 田野工作与资料研究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把过去与现在联系在一起。这次讨论有两件事 十分明确:(1)来源,方法,分析模式,理论最终是不可分的;(2)只有通过考察历史人类学 家的作品才得以学习其研究策略与方法。查尔斯·笛利(Charles Tilly,1981)和泰德·斯高 泊(Theda Skocpol,1984:361)对于历史社会学所做的宣言也同样适用于历史人类学:世上没 有一成不变的方法。
资料性证据:评估的来源
在民族志史研究的早期,像布鲁思·特利格(Bruce Trigger)一样的人类学家严厉地批评了 在 使用资料性证据时缺乏严谨的态度。“他们孤立地看待资料,全然不顾当时的场景,也不去 判断记录者的偏见和能力。其结果导致了资料使用过程中的傲慢与无知,职业历史学家对此 不屑一顾(1976:12)
那么,怎样才能具有批评眼光地评估资料来源呢?皮特(Pitt)写过《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对于 历史资料来源的使用》(1972)一书,内容简明扼要,对于使用资料的介绍十分有用,尽管有 点陈旧。他猎涉了大量的资料——来自公众和官方的、宗教的、社会机构的,商业和公司的 来源,私人信件和数据银行——也猎涉了批评分析的方法。当人类学家涉险进入资料时,他 们必须了解和应用历史学家应用的同一评估标准来确认资料性证据的可靠性。该标准包括评 估观察者的社会地位、智力和语言能力;可能影响观察的态度;所有列入的和省略的内容; 针 对的读者、撰写的动机以及叙述的风格。
然而,历史人类学家对于使用资料还有额外的问题。存在这些问题通常是因为他们了解当 代民族志、民族中心主义、殖民境遇中的权利政治、以及局外人理解他文化之困难。大多数 历史人类学家在他们为之撰写历史的民族中间做过田野工作,他们的认识是来自于这种民族 志的知识,并以此来评价观察者(留下文字记载者)获得的某种文化理解。斯德特温特(Sturt evant)(1968:158)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位历史学家在1944年写了关于森密诺尔(Semin ole)领导人寇库齐(Coacoochee)(野猫)于1837年穿过狭小的监狱窗户从奥古斯丁堡逃跑的事 件,他怀疑野猫用“药草根”减轻他的重量才从缝隙中挤出去的说法。斯德特温特认为,巫 术的知识和现代森密诺尔人的信仰使得人类学家会“接受这个细节为可靠的说法。”这里的 问 题不是关于药草根是否有上述的效力,而是关于一个特别的主位解释,对森密诺尔人来说是 正当的,因而亦是一种清楚的历史事实,可以作出不同的学术判断。
民族志知识也可有助于评估可列举的资料来源。舒麦克(Shoemaker)(1992)提到了家庭历史 学 家面临的方法论问题,他们用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美洲土著的家庭结构。她还特别试图把土 著美洲人放入欧洲美洲人的模式,使用可列举的数据检验政府关于再安置和再组织政策是否 成功。翻译问题也是具有意义的,尤其是在处理关系的问题上。她争辩说,人口普查的数据 对于切诺基(Cherokee)可能比对于那瓦尤(Navajo)具有更高的质量,因为他们的英语程度更 好,更容易与欧洲式美洲文化相融合。
对于文化模式的广泛理解亦能有助于资料来源的评估。这样,一个传教士讲述的关于南佛 罗里达卡鲁萨印第安人一个高级头领娶了他亲妹妹为妻的事情就是合理的,这对于全世界其 他分阶层的社会中的乱伦禁忌是个例外(斯德特温特,1968:458)。同样地,有关美洲土著 人(譬如伊罗各瓦斯)更丰富的民族志史的资料可以谨慎地用来贯穿另一个族群(譬如虎琅)不 太充分的数据(特利格1976)。
最后,对于文化接触、文化征服和殖民主义作为历史过程之影响的充分理解才能够阻止误 解 释。奥贝塞克(1992:9)把斯里兰卡国康提市一个名叫沃尔夫的英国公务员的待遇(1907年英 国人充当地方首脑的角色之后)与英国1796年驻康提独立王国大使罗伯特·安朱的待遇相比 较,并通过比较做了一番描述。在第一个例子中,斯里兰卡人拜倒在沃尔夫的脚下;在第二 个例子中,安朱被要求下跪,他的随从人员都必须拜倒在国王的脚下。这种区别反映了历史 条件和权利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了仪式生活和外来者的待遇。
奥贝塞克从该问题转向分析如下问题:他认为人们不加鉴别地阅读了有关1779年夏威夷岛 上吉姆斯·库克船长之死的文本,那就是土著人思想的误解释。他从马歇尔·萨林斯的书《 历史隐喻》中摘了几个例子。荫林斯(1995)提供了一种令人信服的严谨的回应。在他的《土 著人如何思考》一书的几篇附录中,他特别提到了他曾被指责忽视或误读了的特定来源。因 此,他就使用历史证据的问题提出了令人感兴趣的方法论问题。根据一位书评人的观点,该 书的历史证据“使其成为历史人类学方法论高级课程的上佳选择”(弗里德曼1997:262;保 罗夫斯非1997)。尽管他们的意见相左,但我认为,萨林斯和奥贝塞克在一般性的问题上会 达成一致,如果不是在具体问题上。(1)应该在关注社会、政治和文化场景(历史资料产生于 其中)的情况下阅读历史资料。(2)我们必须不但要认定一个文本作者的民族中心主义,而且 要认定作为该文本的评判者我们自己的民族中心主义。
家族史和历史人口统计学
在家族史和历史人口统计学的领域,已经发展了一类数据采集和分析的定量方法。人类学 家已经成功地应用了很多这种方法,特别是在欧洲工作的人类学家,以及那些在更传统的人 类学田野工作地点如非洲和东亚从事研究的人类学家(施坚雅Skinner 1957;沃尔夫Wolf和 黄 Huang 1980;翰雷Hanley和沃尔夫1985;戴维司Davis和海罗尔Harrell 1993;海罗尔1995))
。在论述定量方法应用于历史数据综合性著作的作者中,有哈金斯(Hakins)和捷夫雷(Jeffr ey)(1991),杰罗斯和哈代(Hardy)(1991)。格罗斯泊特(Grossbart)(1992)制作的文献目录 也是同等重要的。然而,最好的历史人口统计学来源与方法综合性著作是维利根(Willigan) 和林匙(Linch)写的(1982)。他们不但评述了来源的种类——教区的民事记事录、明细表和 人口统计表、家谱和人口记事录、组织和机构的档案——并且也从事人口重建与分析的特别 方法的细节讨论,包括记名记载和家庭重组、计算机模拟、回归、时间系列、线性记录模型 和要素分析。
记名记载涉及了在来自不同来源的众多的资料中寻找同一个人的过程。家庭重组是这些个 人组织为一个家庭单位的过程。尽管来源不全、准确认同、名称变迁和人口流动诸问题都适 用于这些方法,但这些方法对于重建“普通”人过去的日常生活是一种最有效的途径(12)。
温切斯特(Winchester)(1992)关于上述方法发展与应用20年的概述是一佳作,它还写到这 些方法发展与应用亦适应了当今计算机的世界。应用记载和家庭重组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实例 是科兹(Kertzer)(1984)和科兹与郝根(Hogan)(1989)对于19世纪晚期意大利中部凯斯莱箫(C a sellechio)人口的研究;布莱特(1986)对于葡萄牙北部1700年至今的移民、婚姻、繁殖和犯 罪的研究;博德维尔·费森特(Birdwell-Pheasant)(1993)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爱尔兰 主干家庭的重新思考;史奈德(1996)对于1860至1980年西西里岛繁殖衰退的研究;沃尔夫和 黄(198 0)对于1845至1945年台湾的婚姻和寄养问题的研究;奈廷(1989)对于1700至1980年瑞士一个 山区社区生态变化的研究。
在奈廷的案例中,这种方法非常奏效,因为他是研究一个封闭的社区,其历史的变动很小 。90%以上的家庭都已经全部或部分地重组,在公开的家谱、人口统计资料和税单中得到的 补充数据使精确的核查成为可能。科兹更多关注的是家庭的组成和共居的模式,而不是人口 统计的比率。科兹和他的同事使用了意大利人口记事录(另一类历史资料来源)和尤金·汉摩 尔(Eugene Hammel)发展的家庭类型学(汉摩尔和莱斯利特Laslett 1970),得以重建19世纪 晚期和20世纪早期意大利中部复杂的佃农家庭的生活(13)。
科兹和郝根最具创新的工作是使用了生活轨迹的方法。历史学家塔玛罗(Tamara Hareven(1 982)在研究新英格兰的产业工人时使用过这种方法,历史学家乔治·奥特George Alter)(19 88)在研究19世纪中期比利时维尔威斯(Verviers)妇女时也用过这种方法。该方法使个人成 为研究的中心,并关注个人的生活是怎样被历史的变迁所影响。该方法对于更规范的和更固 定的家庭或发展循环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这在社会学家戈兰·艾德(Glen Elder)的 很多著作中完全是线性的描述(1975,1977,1987;海罗温Hareven1978;科兹和希尔费诺Sc hiaffino 1983)。
罗塞尔多(1980)在对伊琅哥特做的历史研究中使用的群体研究的方法略有不同。罗塞尔多 认为,“群体研究是针对不同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群体再造了他们自己,他们永久生 存下去,他们修正或突然改变其社会结构”(p12)。与生活轨迹方法一样,群体研究是来自 于社会学(莱德1965),但已在历史研究中应用,旨在对个人的群体之共同目的做纵向分析(麦森以及其他等1973;维利根和林匙1982)。
在人类学中,家谱方法对于历史重建已被广泛接受,并在工作于非洲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 中具有悠久的传统(博汉男1952;路易斯1962)。人口统计学史的家谱分析方法最全面的讨论 是班奈特·戴克和华伦·莫利编辑的《家谱人口统计学》(1980)。在引论中,编辑者评价了 家谱的民族志和资料的方法,表明在“报导人”的清单与“记载”中的清单核对时有多少内 容被遗漏了。维利根和林匙(1982)的著作具有同等的价值,他们概述了家谱的种类,家谱来 源的问题以及用于从家谱数据中抽出婚姻与繁殖比率的方法。
在弗里曼(1979)对于西班牙北部派西哥人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应用这种方法的好例子。通 过与报导人的会谈,弗里曼建构了派西哥人的家谱,并将此与人口统计资料相联系。在一篇 解释该方法的未发表的论文中,弗里曼(1981)说道,在收集家谱的过程中,会有其他的数据 被传达——婚姻的政治学,财产传递问题,组合家庭的动力,迁移,人与人之间、社区与社 区之间的关系,谣传和丑闻。她争辩说,这些家谱可以衬托对于文字来源(譬如教堂和民事 档案、纳税记录和地籍图)的解释(1981)。尤其是,它们可以帮助展示某些记录的惯例,这 些惯例会把领养这样特别的行为实践弄的难以理解。文字记录可被用来反向延伸家谱,评估 民族志的描述。人类学家若看到一个较短历史的家系,就会不同意“我们一直住在这里”这 样的说法,而去更多地考虑这种说法的真实和象征的意义(1981;10)。
其他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特别是那些研究欧洲、亚洲和美洲家族史的人们,转向了已发 表的家谱,而不是通过交谈以建构之(麦斯科Meskill 1970;塞宾Sabean 1970;艾恩Ahern 1 976;亚当斯和凯斯科夫Kasakoff 1980;奈廷1981;翰雷和沃尔夫1985;克那戴尔Knodel 1 988;奥特那Ortner 1989)。这些家谱通常可用定量方法进行分析,该方法亦用于分析重建 于生命记载的众多家族。
从家族史到地方社会、经济和政治史
历史人类学家通常超越了建立在生命文献、人口普查资料、人口记录、以及口头或文字家 谱的数据上的家族重建和人口统计史,以探索其他定性的历史来源,它们有助于理解过去的 社会和经济生活,以及地方人们生活中特殊事件的意义。
高尔特(Galt)(1986,1991)把家庭人口普查数据与纳税记录、公证的交易数据、公安与司 法记录相联系,以重建18世纪至20世纪在意大利南部艾普林镇的居住模式和社会阶层之面貌 。通过分析记忆的和记载的历史,他能够展示当今经济和社会全景的特别要素的历史深度。 在 讨论各种证据时,他提到很多人类学家是在那些他们曾作过民族志的地方开始攻击历史的, 这样他们就必须与历史文件的局限性打交道(1991:67)。
罗森泊格(1988)在一个更具叙事风格的版本中使用了很多历史资料,以追溯瑞士艾尔畔社 区在国家和资本主义扩张影响下的变迁。罗森泊格使用了一种处理模式,重点分析生计方式 、 市场条件和阶级组成,以此方式她探索了农人怎样处理对他们社区外来的日益变化的要求。 她主要的来源是财产和纳税记录以及遗嘱,这些资料提供了关于财产关系的很有价值的情况 ——土地交易以及阶级组成和不平等的长期趋势。(15)其他一些人类学家和民族志史学家使 用遗嘱、公证记录和其他法律文件来重建居住模式、家庭关系和价值观以及对于死亡和宗教 的不同态度(奥贝塞克1967;戴维司1973;顾笛Goody等1976;阿利斯Aries 1981;白赫Beha r 1986;克兰Cline 1986;布莱特1991)。他们也分析大量法院的卷宗,以理解印度和非洲 这样的地方殖民主义的结构和意义(曼恩Mann和罗伯特Robert 1991;孔1996)。
麦德克斯(1993)写的一个西班牙南部城镇(17-20世纪)地方社会政治关系的变迁史比高尔特 和罗森泊格的地方史有更大的手笔。该书分三部分。麦德克斯谈到了宗教、荣誉和赞助的主 题 ,以及它们在旧秩序的传统氛围中怎样塑造了地方社会的精神气质。地方历史攻击了前章所 述的国家历史,强使进贡和外部权威。这个传统和统治的阶段结束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 随之,土地资本主义的势力蔓延,乡村贵族之间和基督教会之间发生了危机。最后阶段是“ 自由主义传统”阶段,西班牙内战之后,阶级社会被改良。麦德克斯在方法论上与众不同的 是,他文笔流畅,每每引用重要的历史、文学或宗教文本,为他论述阿拉西那镇历史上不同 阶段的话语形式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铺平道路。
长期以来,或许近来在历史人类学中地方研究最棒的范例是格利弗和西尔维曼(1995)关于1 7世纪中期至今爱尔兰东南部汤姆斯商城的店主和商人的分析。他们设计的时间框架要求他 们处理不同的数据,在一个阶段和另一个阶段之间进行富有创造性的连接。“当我们走进现 代的时候,当档案资料的状况大为改善的时候,当田野数据与资料数据相互交叉的时候,我 们 在描写民族志细节方面或在分析深度方面都有长进吗?”(p9)他们对此做了历史的研究。纳 税记录、土地测量报告、人口普查资料有助于理解克劳姆威尔统治时期的地方性经验,以及 人口是怎样根据种族和阶层进行划分的。教区记事录记载了人口增减的情况,地方业绩数据 展示了经济条件之变化及地方企业之发展。
格利弗和西尔维曼的叙述的事情发生在19世纪,商业名录、城镇计划、商店往来帐户、卫 报理事会和乡村地区议事会的小册子、县报都被用来描述建立在零售业上繁荣的地方经济。 在叙述汤姆斯城1840-1991年政治经济一章谈到了诸如核心边缘和控制地域等分析模式,并 对其提出了挑战。该讨论在这一章中达到了高潮。之后,他们谈到了家族企业、亲属关系及 继承权诸方面的问题。三个家族企业的个案史以记录相连和重建的方法为基础,重建于多种 资料来源、口头家族史和报导人叙述之上。它们提供了更深入、更广泛的统计分析。格利弗 和西尔维曼作出如下结论:汤姆斯城在空间上位于欧洲的边缘,因而占据了“在一个特别的 水平上发展统治等级制”的中心位置(1995:339)。根据他们的观点,汤姆斯城并不典型也 不 奇特。它的历史比另一个民族志个案要长久。它对理论的建立作出了贡献:“我们对于达到 富有意义的理解具有特别的看法——不是通过宏观研究、定量分析和模型,而是在跨文化方 法的场景中进行仔细的、有控制的比较,这种跨文化的方法使用了对于代理人、网络、资源 和利益的经验主义个案研究(314)。
小地方的大问题:政治经济史中的全球性视野
上述地方性历史说明了孔(1980:220)指出的历史与人类学历史之间的一项主要区别。“人 类学历史的研究单位应是文化的和从文化中衍生出来的:权利、权威、交换、互惠、行为准 则 、社会分层体系、时空之重建、仪式。一个人在一个特别的地方跨时间地研究这些内容,但 是,该研究是关于文化类别之建构,而不是关于时间和空间。”尽管有人会对孔的论述颇有 微词,但是,那些采用宏观和全球性历史视野的研究或许是最好的例证。
无数历史人类学家以这种视野进行工作。因此,弗里德利奇(Friedrich)(1977:ix)对于墨 西哥那兰佳(Naranja)社区的研究真正是“关于土地改革和土地政治的起源与发展,关于农 民观念和农民反抗技术的形成。”为从事该项研究,他通过民族志的方法(与本地老人交谈 ,对社区的现代生活做内部分析,与其他塔罗斯甘村庄进行比较)重建了19世纪晚期的历史 ,并研究了政府和土地档案。该书富有意义的部分主要叙述了革命领导人普利姆·塔佩的传 记史。弗里德利奇(1986)在后一本书更充分地叙述了他的“人类学方法”。这是关于连接地 方、地区和国家历史话语,也是关于民族志“碎片”一般性解释的最饶有兴趣的论述。绝大 多数谈论小地方中大问题的历史人类学家在关注文化接触、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国家渗透 (沃勒斯Wallace 1972,1981;史奈德和史奈德1976,1996;考码罗夫1985;德克斯1987; 盖雷Gailey 1987;西维布拉特Silverblatt 1987;汉森Hansen 1989;林肯Linnekin 1991 ;凯恩Kahn 1993)。此类著作最好的例证之一是罗斯伯雷(Roseberry)(1983)对于拥有财产 和制造商品的委内瑞拉农人之形成和转变所做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他有兴趣把地方性事实提 升到世界历史事实的水平,并欣然撰史,以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主义不平衡发 展加深理解(p.202)。罗斯伯雷引用了20世纪记载土地使用和土地权的地方资料、地方咖啡 合作社的文件、地方报纸、市纳税记录、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大量第二来源的资料,撰写这 本包罗万象的变迁史。以他的观点,第二资料来源对于历史人类学家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必 须处理国家历史和地方历史之间的紧张关系。罗斯伯雷描述了他的如下方法:“应用理论框 架于一特定情景:当我采集的数据表示差异,即修正该框架;当理论修正引出新的问题,即 寻找新的数据”(p.212)
理查德·福克斯(Richard Fox)(1985)采用了略有不同的方法,分析了人类种族分离的观念 怎样影响了英国人对20世纪早期旁遮普(Punjab)的锡克教徒(Sikhs)的态度,允许把僧伽罗 人(Singhs)(狮子)当作异类,认为殖民压迫理所当然并热衷于此,引发了僧伽罗·撒哈(Sin gh Sabha)的抗议运动。福克斯主要依据第二资料来源,分析“建构20世纪早期旁遮普(政治 经济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意义之间特定的历史关联”(1985:10)。然而,他最后撰写了一本关 于在文化接触的场景中建构认同的历史,一地区有文化接触者,即融于世界经济也。福克斯 论道,被统治阶级的成员盗用统治阶级的霸权模式,并在他们的反抗中加以修改和应用。他 对本身就总在变化之中的文化概念进行概念“再置”(re-situation)。他认定了一个“卷入 了统治体系之各种事项及其相关文化代码”的历史,其目的是“解释在社会行为中跨时间运 行和发展的真实社会过程和实践”(p.206)。
奥特那(1989)也把政治经济和文化于一体的视野融入民族志史,该民族志史不仅叙述了国 家的影响,殖民主义或资本主义,而且叙述了这种影响最终是被怎样解释的。(17)她论述道 ,人类学家“必须把地方社会的文化框架和结构矛盾当做一面可以看到更大体系里实践和政 治的镜子,因为正是这种文化框架和结构矛盾传递了上述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势力的意义和影 响”(p.83)。
民族志分析方法在历史中的应用
有些人类学家通过采用以事件为中心(event-centered)的分析方法攻击历史(派尔特和派尔 特Pelto 1978:200-208;傅格森Fogelson 1989)。他们研究的焦点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及 其对地方社区和人们所产生的持久影响。资料来源以依赖于该事件的历史深度,它们有口头 的、有文字的,或二者兼而有之。马歇尔·萨林斯(1981)对于库克船长之死的探索就是用该 方法进行研究的佳作,他最近对1843-1855年间斐济战争的分析也很出色(萨林斯1991),但 还有其他好的例子。温森特(Vincent)(1992)依靠文字资料来源——已发表和未发表的地方 和 国家某些专门事务委员会的报告,重建的家谱和家族史,以及物质文化的调查——以探索卷 入了爱尼斯克林(Enniskllen)济贫法联盟拥护者集会(对一个爱尔兰郡的饥饿问题的反响)的 单一事件所产生的影响。科利尔(Collier)(1987)广泛引用口头历史(档案资料来源作补充))
,以记录针对西班牙南部劳斯·奥利夫斯(Los Olivos)社区社会主义建立的一系列政治暗杀 的影响。
当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1957,1974)关于社会戏剧的概念和他扩大的个案研 究的方法与以事件为中心的分析方法十分相同。泰勒(1983)引用特纳的方法,对新英格兰的 荷兰移民区做了民族志史的分析。他的民族志史主要研究两个长期的争端,每一个争端都有 戏剧性的冲突,都有主要演员、临时演员和客串角色。在谈到他的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的优 越性时,他说“有机会探索(1)可引发公开冲突的潜在冲突;(2)个人操纵行为准则以谋求私 利的方式;(3)针对生活无序而共同和象征性维护的道德秩序”(1983:185)。(18)
特纳在象征人类学的发展中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象征分析的方法构想宏大,已被有 些人类学家成功地用于历史研究。最好的例子是奥奴齐·提内(Ohnuki-Tierney)(1987,199 0 b)探索18世纪至今在日本文化中猴子作为自我的隐喻其意义的变迁。文字记载的资料,包括 古代文本和民间传说,显示了譬如在中世纪,猴子主要作为媒介;在现代早期,猴子变成了 替罪羊;到现代时期,又出现了另一种意义,即猴子变成了小丑。奥奴齐·提内认为,这些 转变与日本历史上的主要变化是巧合的。
13世纪中期和14世纪,日本政治一片混乱,史无前例地动荡不安、反复无常和崇洋媚外。 然而到现代早期,形势趋于稳定,产生了一个高度等级的社会,对外封闭,对内缺乏活力。 直到19世纪晚期,日本才又重新对外开放,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赫尔维兹引用民族科学方法论,发现了“19世纪社区社会关系的文化场景”(1978:27)。 他的方法是以语意分析为基础核查原始资料来源,记录参照事项和地址以及它们被应用于其 中的场景。后来他发展了一系列领域,或陈述类型的分类学,此种学科通过社会成分之分析 ,引出了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
在另一个层面上,话语也是泰勒(1992)和考码罗夫和考码罗夫(1992)的历史研究之焦点。 考码罗夫分析了南非非国教教会的编年史,并进一步分析了其他文字资料来源,包括报纸、 官方出版物、小说、流行歌曲、绘画及儿童游戏。通过话语分析,他们可以追朔一个文本的 转变过程,一个单一的、一致的和连贯的观念是从互不相关的声音和表达方式中衍生出来的 。 泰勒应用了这种方法来分析19世纪岛那格尔(Donegal)的宗教记事(民间故事、杂志文章和赎 罪词),以更全面地理解对立的文化和社会事实及政体。
最后,应当提到被民族志史学家成功运用的比较方法,他们以相同条件下有关文化和社会 规则的某种假设为基础,进行跨时间比较(强思1996)。在历史人类学家中间,埃里克·沃尔 夫在他的整个生涯中运用该方法于微观的(1957;库勒Cole和沃尔夫1974)和宏观的研究(198 2)。古迪(Goody)也运用该方法,对欧洲家庭和婚姻做了全面的研究。然而,克拉克(Clark) 应用的范围更为广泛,汉森(1989)提出(而不是刻意追求)一种思想:她对赞比亚家政服务的 研究有助于批判地理解美国的类似问题,最终有助于我们理解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 有偿家政工作的地位。 生活史
人类学历史方法的任何讨论都必须提到生活史。尽管生活史是一种口头的历史数据,但它 清楚而又广泛地记载了“一个人的生活,被人记录并相传,被人编辑并撰写,像是写一本他 的自传”(兰格尼斯1965:4-5)
生活史方法源于对美洲土著历史回忆的研究,盛行于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并在一次 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关于个人资料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的讨论会上达到了顶峰(高兹壳克等1 947)。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生活史曾引起争议,主要是因为生活史是否具有可靠性、有效性 和代表性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导致了生活史的方法之运用在战后有所消减。(20)然而近年 来,生活史又重视,很大程度上与反思人类学和女性人类学不无关系。尽管关注特定民族志 的应用可以间接地研究这种方法(克莱潘宰诺Crapanzano 1980;萧斯泰克Shostak 1981;布 莱克曼Blackman 1982;弗里德利奇1986;坎戴尔Kendall 1988;戈麦尔齐Gmelch 1991;拜 赫1993;布莱特1995),但仍然有些出版物更为直接地探讨之(兰格尼斯1965;博德思Bertau x 1981;博德思和高利Kohli 1984;克莱潘宰诺 1984;华生Watson和华生·弗兰克Watson- F ranke 1985;拜赫1990;罗森华尔德Rosewald和奥克柏格Ochberg 1992;林德Lined 1993))
。尤其,兰格尼斯和弗兰克(1981)对如何处理可靠性的问题,如何用其他数据补充生活史数 据以求更全面的理解,提出了很多见解。当然多是关于参与观察更一般的问题——关联、语 言能力、交谈技巧、道德标准——它们对于生活史的收集是同等重要的。
尽管生活史被用来研究人性,探索个人与他或她的社会或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主观经 验的现象学”(华生和华生·弗兰克Watson-Franke 1985),但在本文中,我们要询问生活史 作为历史方法的特性。皮考克(Peacock)和赫兰德(Holland)(1993)关于概念性差别的阐述颇 为有用。他们比较了聚焦生活(life-focused)和聚焦故事(story-focused)的方法。有人把 生 活叙述当作历史和民族志事实的客观经验之窗口,有人或关注叙述者的主观经验。在第一种 情况下,有效被列入日程,但是重点主要是记载社会变迁对个人生活的影响。第二种观点与 历史分析也是相关联的。确实,历史学家已借用了生活史的方法,深入探究北非、西非和中 非妇女的奴隶制问题(艾尔珀斯Alpers 1983;司旧拜尔Strobel 1983;莱特Wright 1993), 北非的殖民主义问题(勒文LeVine 1979),中非的等级制与种族问题(考德Codere 1973),中 国妇女的劳动问题(谢立丹Sheridan和萨拉夫Salaff 1987),或者欧洲战时的移民问题(博德 思·维埃姆Bertaux-Wiame 1982)。
人类学家在田野中与报导人进行互动和对话撰写的生活史,类似于历史学家使用的一些其 他个人或主观的资料——信件、日记、自传、口头叙事——人类学家据此以揭示参与者对于 他或她所卷入的经历的看法(严思·迈克拉夫林Yans McLaughlin 1990;梅因斯Maynes 1992 ;崴斯特West 1992)。最近,戈拉夫(Graff)(1994)编辑了一本有用的文献目录,收入了应 用此种资料来源的著作。阅读其中一些书,对于那些有意将生活史素材与文字记载的生活故 事融为一体的人类学家来说,或许是受益匪浅的。
口头历史
生活史是一种记载口头历史数据的形式,但口头历史本身的应用范围更为广泛。在“无历 史民族”中运用口头历史的先驱当属让·万思那(Jan Vansina)。万思那在非洲工作,他曾 论道,口头传统是同其他资料来源一样可靠的历史来源,特别是在与文字记录、考古证据及 语言学模式的比较中对其进行评估的时候(1970,1985)。万思那概述了一些口头传统:口 号和惯用语句、地方名称、官方和私人诗歌、故事、法律或其他评述。
在万思那之后,众多历史学家运用口头历史的方法撰写了很多著作(格雷里Grele 1975;胡 珀斯Hoopes 1979;海那志Henige 1982;汤姆森Thompson 1988;当纳维Dunaway和宝姆Baum 1996)。这些著作论述了历史与口头历史的关系、讲故事人的权威、交谈过程、平衡的主观 与客观、以及编辑和偏见的问题。口头历史的方法被应用于经济史、劳工史、科学史、社会 史、家族史和妇女史。历史学家一般运用正式的交谈方法使人讲出真实的历史。很多人类学 家也这样做,但有一些人类学家是从非叙事口头传统(非正规讨论、随意的评论及日常交谈) 中编制口头历史(泰勒1983;拜思特曼Besteman 1993)。(32)
细查一下引用口头历史的历史民族志诸多作品,就会发现一条共同的线索,那就是重视采 集于口头历史的数据和文献资料的数据二者之间的对话,以使“一组数据的意义仅在另一组 数据的参照下得到满意的解释”(罗杰斯Rogers 1992:25)。因而,对话方式的目的就是更全 面地记录一次事件或历史结构。斯岛克德(Astockard)(1989)与150位老妇女交谈(她称之为 回忆式交谈),得出了非正统婚姻习俗(即推迟新娘过门的婚姻)的口头历史,广州三角洲一 带的人在传统上时兴这种婚姻,而它的产生与蚕丝生产相关联。事实上,一位报导人的随便 一 说会把一项原先计划研究现在的项目转向研究过去。为证实口头历史中的叙述,斯岛克德开 始探察其他文字记载——地名索引、教会叙事、历史、游记——以寻求对于口头叙述的“确 认”。
口头历史与文字记载的对话式并置是为了聆听同一历史经验之不同声音和不同解释。该方 法应用的实例不计其数(斯道尔克Stolcke 1988;珀易Poyer 1994)。例如,郝伊勒·伐特恩 (Hoehler Fatton)(1996)通过(或如她所说的“特权”)口头传统,认识了在殖民时期肯尼亚 西部逻族人中,妇女对于神圣的基督教运动之兴起所做的贡献。“尽管殖民地和教会的报告 或许更加可靠(涉及基本年表时),但它们无一例外地突出了男性领导人的活动。当这些文本 中提到女人的时候,通常是用集体(排除性)名词。正如我们所见,女人一直都是这个大众宗 教的骨干。对她们的活动保持沉默的历史将是严重扭曲的历史”(郝伊勒·伐特恩1996:8)
哲罗姆·铭兹(Jerome Mintz)(1982)对20世纪早期西班牙凯萨斯·威亚斯(Casas Viejas) 地区无政府暴动的研究焦点,是不同阶级背景的历史记述。铭兹把口头传统与无政府主义者 的文件和地方报纸、国会辩论和报告、信件和杂志、教会和法院记录相比较。文字记载包含 上 层社会的记述,而口头传说则属于农民。一种记述把凯萨斯·威亚斯的卡姆利特(Carmelite )寺院的僧人描绘成精神支柱;另一种则把他们描绘成压迫者。同样,一种记述把地方寺院 的衰落归咎于19世纪早期法国人的侵入,另一种则认为是由于僧侣本身的贪欲和竞争。(p.7 7)
在对克隆笛科(Klindike)淘金热的研究中,克鲁伊柯珊科(Cruikshank)(1992)把西方关于 扩张、个人主义和霸权的故事与当地人恢复和维护主权记述相比。在评价与文字记载相对的 口头记述时,她提到,“这种做法不是简单地整理一些事实,而是去认识该认知模式怎样产 生了不同的社会分析,并因此对一特定事件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蕴涵于官方的历史 中,另一种则淹没在集体的记忆里”。(p.22)
奥特那(1989)撰写了尼泊尔佘琶(Sherpas)族人的大宗教民族志史,描述了关于历史多音道 的不同经验,该经验来自于口头传统与文字记载的并置。她从可以谈论寺院和庙宇(历史的 一部分)的个人那里收集故事和个人记忆。在此过程中,她发掘了权威知识的主位观点—— 尽管她想获得多种观点,但她还是不停地走访“具有真知”的喇嘛。对于她的报导人来说, 她的历史作品比她早期的民族志作品更有意义,因此情况也就更容易收集。更具挑战性的是 在证据的碎片中建构可叙述的历史。
或许这种对话式的经典之作当属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里程碑式的著作《第一时 间》(Frist-Time)和《阿拉比的世界》(Alabi's world)。“第一时间”是苏里南的撒拉玛 卡(Saramaka)人形成时期的神圣历史。普莱斯在田野工作的起初,他并没有想到要做这个课 题。他在田野中做了几年之后,方才能够提出这个题目与那些老者交谈,并且向他们诉说了 他在荷兰的资料堆中找到的对于历史的感觉。他从一群老者的口中探求到“第一时间”的口 头历史,条件是他们在讲述不愿对外人讲述的故事时不会感到尴尬。
普莱斯(1983)的方法集中焦点于事件。“从不同的人那里获得不同的片段(经常只有一个句 子 ),进行比较,进行探讨,进行反证,最终与当代文字记载进行对照,我试图描绘一个画面 :最博学的撒拉玛卡人知道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为什么要保留在记忆中。”(p.25)他对 残缺不全的文字记载也使用同样的方法,认真考虑“一大堆复杂的证据,经常包含着明显矛 盾的事实……我对资料来源慎之又慎,终能去伪存真”(p.40)。
在与文字证据进行比较时,他一直都知晓建立撒拉玛卡历史规范和权威的版本存在危险。 他的解决方法是在书里使用不同的字样,以使两个(同样支离破碎的)历史得以区分。他的第 二本书《阿拉比的世界》主要研究了1762年以前的时期,并引用了一部分早期无法得到的新 的文字资料。在该书中,他继续应用声音并置的方法——撒拉玛卡人的声音、摩拉维亚传教 士的声音、荷兰殖民地官员的声音、民族志历史学家的声音——这就是历史。普莱斯说,民 族志史学家的目标就当是“透过不同于他的存在之存在而现其本质;我们须沟通文化和语意 的隔膜,从而沟通人类学家与历史表演者和观察者之间的联系。二者本身就创造了文化的来 源,这来源又拥有和呈现了复杂的早期历史”(普莱斯1990:xix)。
物质文化与影象
一些历史人类学家或许受其学科的考古学分支所鼓舞,他们把物质文化当作撰写历史的重 要资料来源。对该方法同等重要的激励来自于法国社会历史学家马克·布劳科的著作,他的 《法国农村史的原始性》于1931年在巴黎出版,后来译成英文,取名为《法国农村史》(布 劳科 1965)。布劳科研究系列地图上的每一件器具以撰写法国农村史。人类学最早应用物质 文化撰写历史的例子是克罗伯和里查森(1940),他们仔细研究了欧洲300年间妇女穿着风格 的循环变化。他们把这些变化与紧张与危机时期相联系。
最近,孔(1996)探索了19世纪印度布匹、衣服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24)铭兹(1985)把 烹饪指南作为窥视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口味的窗户。傅莱克曼和劳夫格林(1987)在其他场景 中选择了家庭空间,研究1880-1910年间瑞典资产阶级的文化。费尔南兹(1990)和拜赫(1986 )也“解读”了家庭空间来研究过去。麦克唐纳(1986)仔细分析了戏院和墓地,研究19世纪 巴塞罗那上流社会的城市生活。古迪(1993)以更全球化的规模考查了墓地,以及其他古代碑 林和艺术品,对鲜花象征性和交易性用途做了大规模跨时空的研究。甚至奥奴齐·提内(199 0)在漆器的箱子上发现了一些猴子象征主义的表述。史奈德和史奈德(1996:94)实际上谈了 物质文化的综述。“我们询问不同阶级背景老人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是如何生活的,并在他 们的叙述中插入过去的人工制品、家庭、衣柜和居住情况”。
影象(绘画、照片、雕塑)也是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是撰写历史有价值的资料来源(斯哉 伯1994)。珀尔玛特(1994)说道,影象历史学家能够探询对影象的起源、制造、传播、作用 、观念和存留产生影响的社会和历史力量,并探询这些影象是怎样影响并塑造了思维和事件 。他列举了一系列可在影象的分析中进行探索的意义,包括意义的产生和内容的认同,是功 能的、表现的、比喻的、修辞的、道德教育的、社会的或特定历史时期的,还是比较的。
历史学家应用影象已有多时,而只有为数不多的历史民族志学家走出了文字资料来源。约 翰和珍·考码罗夫发现这是通往无声之声的必由之路。在方法论上,占主导地位的叙事作品 ,使他们“超越思想的声音和制度的形态,进入无言的形的领域,如物体,如建筑,如巫术 ,如商品,一窥殖民之做派。这又把我们带回到资料堆中——信函、名录、插图、照片—— 尺管作为世间的地图,它们所表现的要多于它们想表现的”(考码罗夫和考码罗夫1992:36)
。 考码罗夫们号召历史民族志学家建立他们的自己的资料库。“作为人类学家,对官方记录我 们须用之又弃之,全在保留和超越我们研究的社会之记忆”(p.34)。
结论:连结过去与现在 连结历史与民族志
在凯伦·汉森(Karen Hansen)(1989:xiii)对赞比亚家政服务员研究的前言中,她描述了从 历史资料向现时观察的跳跃,从赞比亚首都到美国大都市的跳跃。这跳跃是她特意安排的。 她说,历史学家是不会这样跳跃的,也不会为了理论而牺牲细节。然而人类学家经常进行这 样的跳跃,他们从民族志的后门钻进资料堆中。历史人类学与历史的区别之一就是人类学把 过 去和现在相连结。
在早期作品中(布莱特尔 1992),我探索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过程中一些重要问题。我注意 到参与观察的方法可以对历史研究导致相关的问题,人类学家在此基础上看到的社会关系模 式对我们做出过去社会互动的假说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我还注意到,历史研究可使我们对理 想和现实的关系有更清楚的认识,对理想化的过去有更清楚的认识。(25)在此基础上,格利 弗(1989:32)加入报导人的资料,以使一项政府报告、一个法律契约或一篇报纸文章的事实 都更加有血有肉,或者加入历史资料以唤起报导人的记忆,要么作为交谈或讨论的基础。史 奈德和史奈德(1996)使用了同样的方法解释生命记录和家庭文件,以充分理解过去交媾中断 的实践。
作为民族志学家,我们带了很多方法到田野中。我们也可以在资料库中使用相同的方法。 确实,有人曾说历史研究之目的就是写出好的民族志。“这意味着我们要寻找在特定事件的 证据中发现其规律性的途径,寻找把个人生活资料与社会过程相连结的途径,个人资料正是 存留于社会过程之中的”(西尔维曼 1986:125)。
总之,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方向像是二者必具其一,每个方向都提倡独特的研究方法,二者 并不相互排斥。对一些人来说,历史民族志学家就是要通过他人的眼睛解释历史事件。德麦 利(De-Mailillie)论道,民族志历史的方法在于以它自己的方式理解过去,在于以如下的方 式解读过去的记录:尽可能充分和尽可能逼真地表述表演者所理解的事件,然后运用这种知 识 撰写以文化为根基的历史及历史民族志“(1993:553)。对另一些人来说,历史人类学主要 是对过去和现在影响了人类行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过程做出跨文化和比较性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