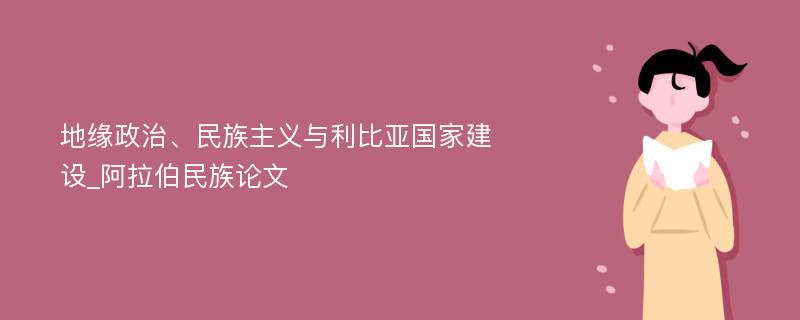
地缘政治、民族主义与利比亚国家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比亚论文,地缘论文,民族主义论文,政治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2011年以来,阿拉伯国家经历了几十年未有之大变局,维系这些国家多年的统治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出逃沙特阿拉伯,其政权轰然崩溃。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民众抗议声中黯然离职。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在北约和国内政治反对派的内外夹击下倒台,卡扎菲本人死于非命。也门总统萨利赫被迫辞职,避难他国。复兴党统治下的叙利亚仍然如履薄冰,前途未卜。本次阿拉伯大变局是继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主义浪潮、20世纪80年代的伊斯兰复兴主义浪潮以来,阿拉伯世界遭遇的第三次政治体制变革浪潮。由于其冲击力之强,引起变化之大,影响范围之广,堪称苏东剧变以来又一次世界政治大变革。苏东剧变最终导致了冷战结束,而此次变革则引起阿拉伯强权体制国家的“连锁崩溃”,阿拉伯国家陷入剧烈动荡之中。阿拉伯大变局引发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学者们从各个视角深刻反思这场政治变局发生的原委,大都认为,阿拉伯大变局的发生是内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内因是这些国家政治发展的衰朽(特别是威权主义、家族政治以及老人政治),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以及网络新媒体的传导等,外因则是欧美国家的干预与美国“大中东民主化”的余波,甚至考虑到气候变迁的影响等。①应当说学者们的上述探讨至少在表象上揭示了这场大变局的某些原因,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内外学术界忽视了引发大变局的一个深层次原因,那就是困扰阿拉伯国家至今的国家构建问题。 从近现代历史进程来看,现代国家构建主要是民族国家构建。但国家构建与民族构建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人为构建一个具体、真实的政治共同体,存在大国和联合国等外力干预,而后者是构建一个具有相似历史记忆与文化符号的想象的共同体,尽管是建构的但外力很难干预。②在哈贝马斯看来,国家构建是指由公民组成的民族,民族构建指的是由人民组成的民族。③二者重合则是理想的民族国家构建,二者疏离则会造成公民身份与民族身份的紧张。除了民族国家构建的一般性问题外,国家构建还包括具体政治议程的推进。从国家构建的实践来看,尼尔·罗宾逊认为,国家构建不仅仅是控制一块领土,更重要的是构建某种政治权威,完成市场经济与民主制度建设等议题。④在此意义上,国内有学者认为:“国家构建是指,国家政治结构、制度、法律的建设,包括行政资源的整合和集中,使国家能够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实施统一的行政控制。”⑤综合而言,国家构建主要是指政治共同体建立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建设。 在民族国家框架内,政治共同体如何建立,是由外部力量主导还是由内部力量主导,亦或由内外部力量共同推动,将型塑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的后发展国家的国家构建类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亚非拉国家中,涌现了一波去殖民化与国家构建的浪潮。大多数亚非拉国家的国家构建都是内部民族主义力量推动完成的,但在阿拉伯国家构建中,尽管民族主义精英也在起着重要作用,大国的外在影响更为明显。而利比亚的国家构建则更为曲折,它是大国博弈过程中最后由联合国“制造出来”的国家。这一颇具特色的国家构建方式,尽显利比亚民族主义力量与地缘政治在该国政治共同体建立过程中的复杂角色与作用。 国外学者已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⑥他们虽然指出了大国博弈对利比亚国家构建的积极作用,但却忽视了其消极影响。大国博弈和联合国推动下的国家构建,只是在形式上或某些内容方面使利比亚成为现代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许多实质性问题并没有因为建国而得到根本解决,分裂的地缘政治、部族社会等历史性难题也没有得到有效化解。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些因素与大国博弈在利比亚国家构建之路上一再重演。2011年,以美国和法国为首的北约,配合利比亚政治反对派推翻卡扎菲政权,其根源仍可以追溯到联合国推动下利比亚国家构建的先天不足以及近代以来利比亚不成熟国家形态发展自身。因此,在利比亚国家构建的问题上,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利比亚的国家构建是如何进行的?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作为地缘政治的集中体现——大国博弈的深入开展,大国为何将其交给联合国?这一国家构建方式对利比亚政治产生了何种影响? 二、多文明竞逐的地缘政治:利比亚国家构建初起 利比亚地处阿拉伯半岛、非洲与地中海的边缘区域。东部为昔兰尼加,西部是的黎波里塔尼亚,西南部是费赞。但三者之间有沙漠阻隔、交往不便,而且各自分立,历史上从未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三个地区的交往对象也不一样:昔兰尼加同马什里克国家(Mashriq,包括埃及与中东其他国家)交往甚密,而的黎波里塔尼亚则认同马格里布国家(包括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⑦由于利比亚南部延伸到撒哈拉沙漠深处,费赞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频繁接触。可以说,利比亚一直处于被马格里布国家和马什里克国家利益伸张的离心结构中。⑧正因如此,阿里森·帕格特指出,利比亚成为一个国家纯属偶然,利比亚的历史就是各地区历史的简单相加。⑨独立前的“利比亚”仅是地理学上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利比亚人更喜欢被称为的黎波里塔尼亚人、昔兰尼加人和费赞人。⑩作为行政、经济与政治浑然一体的、现代国家意义上的利比亚,从1951年大国博弈下联合国大会推动建国算起,其历史仅有60多年。(11) 地处欧亚非三洲边陲地区以及分裂的地缘结构,使利比亚国家构建极易遭受外来文明的干涉。在外来文明角逐的历史进程中,利比亚形成了复合型的政治文化。利比亚的统一,不仅面临整合分立的地缘政治,而且还需整合这些复合文明因素,即非洲地缘特征、阿拉伯民族特性以及伊斯兰宗教特质。 利比亚的原住民柏柏尔人没有自己的书写语言。至于柏柏尔人什么时候来到了利比亚,至今仍是历史之谜。腓尼基人(Phoenician),或者叫布匿人(Punics)是北非地区最早的外来居民。公元前1000年,腓尼基人占领的黎波里塔尼亚,成为迦太基的一部分。布匿文明对本土柏柏尔人的影响较大,后者将布匿崇拜仪式融入了他们的民间宗教。公元前218—前202年,迦太基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被击败,的黎波里塔尼亚被罗马帝国征服。公元1世纪,罗马人击败托勒密王朝,占领昔兰尼加,这里的居民说希腊语。而的黎波里塔尼亚属于布匿人统治区,说拉丁语。(12)从地理特征来说,昔兰尼加更具欧洲风格,而的黎波里塔尼亚具有非洲风情。(13)因此,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政治与文化背景截然不同。 4世纪,罗马帝国分裂后,利比亚的东西部又分别纳入拜占庭帝国和西罗马帝国领土范围。而费赞地区除与利比亚西部存在一定的贸易联系之外,保持着独立状态。632年,阿拉伯军队进入北非地区。644年,阿拉伯人占领昔兰尼加。646年,阿拉伯人进入的黎波里塔尼亚。663年,阿拉伯人进入费赞。阿拉伯人的到来给利比亚地区带来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它对现代利比亚社会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地区迅速完成了“阿拉伯化”或“伊斯兰化”。柏柏尔人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内陆地区对阿拉伯人进行了顽强抵抗。摩洛哥历史学家阿卜杜拉·拉洛伊指出:“阿拉伯化经历了多个世纪,伊斯兰化是柏柏尔人自己完成的。他们模棱两可地承认了阿拉伯人的统治,民众更认同地方首领的权威。”(14)甚至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利比亚的阿拉伯化仍在进行,但伊斯兰化则早已完成。阿拉伯语成为社会交往的主要语言。不过,的黎波里塔尼亚和费赞的阿拉伯人的语言带有马格里布方言,而昔兰尼加的阿拉伯人方言与阿拉伯半岛地区相似。许多柏柏尔人将阿拉伯语作为第二语言。(15) 11世纪,处于法蒂玛哈里发统治下的利比亚受到来自阿拉伯半岛内志的希拉尔和萨利姆部族的入侵,这是阿拉伯人的第二波入侵,它对利比亚部族社会结构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历史和分布地区来看,利比亚的诸多部族与希拉利亚人的希拉尔部族和萨利姆部族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利比亚成了一个典型的部族国家。(16)部族既是利比亚强大的社会组织,也是模糊的政治单元以及政治合法性的来源。(17)部族国家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是以种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在共同的族群或族裔祖先神话与历史记忆的基础之上,政治权利甚至特权只授予那些领主部族成员,即处于统治地位的政治精英和与此相联系的统治阶级。(18)利比亚的国家权力往往由一个领主部族掌握,其他部族则处于附庸地位。利比亚部族形态的本质更多地体现为社会学而非意识形态上的联系与结合,部族的凝聚力和相互救济依关系亲疏而定。部族成员往往将政治认同与种族起源、身份联系起来,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所以有学者将利比亚的这种文化单元称为部族民族(tribe-nation)。(19)部族民族和部族国家在一致的情况下,就是民族国家,但二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一致,血缘、传统和部族纽带是排他性的,部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经常背道而驰,其结果就是部族社会与国家的频繁冲突。 16世纪,奥斯曼帝国征服利比亚,并未对其实现直接统治,地方和部族势力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从16世纪中期至1911年奥斯曼帝国在当地统治的垮台,利比亚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面临欧洲新兴列强对亚非拉殖民的威胁。在英、法、意等国的侵略面前,奥斯曼帝国自身难保。被奥斯曼帝国“虚领”的利比亚更是首当其冲。随着欧洲国家同非洲地区多层次交往欲念的日益强烈,利比亚的地缘战略魅力更加鲜明地显现出来。这里一方面是贯通地中海与南部非洲的交通要冲,的黎波里地区是通向中南非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这里也是欧洲同非洲经济交往的贸易中心和中转站,贸易范围包括羽毛、象牙、黄金和奴隶。到19世纪中期,非洲奴隶贸易的1/2都经由利比亚三个地区过境。(20) 为了延续自己的统治且缓解帝国本土的压力,奥斯曼帝国支持当时兴起的宗教民族主义力量抵抗欧洲国家的入侵。(21)赛努西教团得以崛起。该教团活动是以复兴伊斯兰教为目标的泛伊斯兰主义政治运动,保留了传统苏菲派的神秘教义和礼仪,严厉谴责带有泛神论倾向的观点,其教义与瓦哈比派一脉相承。(22)赛努西教团始建于1837年,活动场所被称为扎维亚。1843年后,扎维亚遍布昔兰尼加、费赞及其周围地区。(23)赛努西教团和奥斯曼帝国苏丹都支持泛伊斯兰主义。1886年,苏丹哈米德二世成为赛努西教团正式成员,不久被拥戴为哈里发,并在伊斯坦布尔设立赛努西教团的常驻机构。赛努西宗教民族主义的斗争目标直指法国等殖民者,在某种程度上与奥斯曼帝国利益有契合之处。该教团不拒绝世俗政治,与奥斯曼帝国的世俗主义并不矛盾,因而得到奥斯曼帝国的支持,成为一支积极的政治力量。帝国苏丹对赛努西运动的支持态度培养了一股宗教民族主义力量,并在意大利入侵利比亚后发展起来。昔兰尼加赛努西教团以“圣战”名义发起了规模较大的抵抗运动。(24) 早在19世纪70年代,意大利就为入侵利比亚而积极准备。1896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失败后,决心将利比亚打造成为地中海的“第四海岸”。意大利作为欧洲国家的后起之秀,尽管刚刚实现统一,经济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但一直有谋求大国地位的雄心。而占领北非则是其谋求大国地位的第一步。许多意大利人相信,将意大利主权行使到曾经被罗马帝国统治的区域是历史赋予的权力与义务。(25)此外,人口稀疏的利比亚紧靠意大利,意大利的统治者希望本国农民通过到“第四海岸”的利比亚殖民定居,减缓本国的人口压力。1911年9月29日,意大利在向奥斯曼帝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的三天之后,便公开宣战。1911年10月5日,意大利舰队占领利比亚。意大利和奥斯曼帝国的“三日战争”最终以后者的失败而告终。11月5日,意大利政府宣布吞并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 意大利入侵激起了抵抗组织的出现,但分散各地,而且各自所秉持的政治理念还不一致。志在复兴伊斯兰教的赛努西教团在昔兰尼加直接抵抗意大利的入侵,奥斯曼帝国一直为他们供应武器装备。奥斯曼帝国灭亡后,1913年,赛义德·艾哈迈德成立赛努西国家并对意大利入侵者采取“吉哈德”(jihad)圣战,通过开展游击战与意大利周旋。而以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为使命反对泛伊斯兰主义的世俗民族主义力量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组织的早期抵抗运动并不成功,苏莱曼·巴鲁尼(Sulayman al-Baruni)组织柏柏尔人进行抵抗,以失败而告终。在与意大利的斗争过程中,这两股力量都在不断发展并创建了各自意义上的国家与政府组织。 1915年4月,欧洲国家签署《伦敦条约》,许诺意大利占有利比亚。但意大利因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混乱不堪,并不想在利比亚过多耗费精力。1920年10月,昔兰尼加和意大利谈判,达成《拉加玛(Rajma)协定》,赛努西教团领导者伊德里斯被授予昔兰尼加埃米尔(阿拉伯语音译,即国王)头衔,管理库法拉(kufra)绿洲等地。伊德里斯从意大利政府按月领取薪金和生活补贴,意大利提供警察和行政人员,赛努西教团负责解散昔兰尼加的部族武装。(26) 意大利法西斯统治期间,伊德里斯领导下的昔兰尼加民众发动反法西斯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本人避难埃及,但其助手赛义德·奥马尔·穆赫塔尔领导下的抵抗运动通过与昔兰尼加部族合作,获得政治合法性,成为利比亚国家构建进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赛努西宗教民族主义运动植根于现实社会的政治斗争,采取了宗教形式,实质上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和伊斯兰教相互渗透、相互借重的产物,是追求阿拉伯民族独立、反对西方国家殖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1912年,苏莱曼·巴鲁尼在的黎波里塔尼亚西部成立地方政府。1915年,拉马丹·苏韦赫利在密苏拉塔(Misurate)和的黎波里塔尼亚东部成立地方政府。1916—1926年,哈里法·扎维(Khalifa al-Zawi)在费赞成立地方政府。尽管这些地方政府持续时间较短,但为的黎波里共和国的成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政治资源。1918年秋,的黎波里共和国成立,它是阿拉伯世界创建的第一个共和国政府。(27)的黎波里共和国想在巴黎和会寻求大国承认,但没有得到支持。1919年10月,意大利与的黎波里共和国代表签署协议,颁布了《基本法》,实施范围延伸到昔兰尼加。《基本法》承认各省拥有自己的议会和治理委员会。利比亚人被授予利比亚一意大利双重公民身份,所有居民在地方议会选举中有投票表决权,免服兵役,其税收权归属地方选举的议会。意大利总督可以在十人委员会提名的基础上任命地方行政职位,但十人委员会中有八人是议会选举的利比亚人。实际上,《基本法》给利比亚民众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空间。尽管《基本法》得到的黎波里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导人巴鲁尼和昔兰尼加赛努西宗教民族主义领导人伊德里斯的欢迎,但从未被付诸实践。昔兰尼加议会从成立到1923年被废除,期间召开五次会议,参加者几乎都是部族谢赫(长老),很少有城市市民阶层的代表参加。 由于政治精英陷入内斗,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政府没有举行过议会选举。的黎波里塔尼亚贵族与酋长之间派系对立严重,到1912年年中,领导人之间甚至相互倾轧,自相残杀。直到伊德里斯被任命为昔兰尼加埃米尔后,的黎波里塔尼亚的精英才意识到内战已经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错过了自治的最佳时机。1922年10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上台执政。1923年,意大利法西斯分子进驻利比亚,的黎波里共和国因缺乏强有力的领导集团、内部派别林立而被迫解散。 的黎波里塔尼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属于北非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部分,它与西亚阿拉伯民族主义一样以复兴阿拉伯民族为使命,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阿拉伯民族国家,反对泛伊斯兰主义。但二者在如何处理与西方国家关系上存在不同主张:西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为了实现阿拉伯民族统一,同意与西方国家合作,而北非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宗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称当时欧洲入侵是“基督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28) 可以说,分裂的地缘政治格局,复杂的部族社会结构,柏柏尔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和意大利人等多种文明在三个地区的角逐成为利比亚历史的主题,是利比亚国家形态的底色。近代以来,在各种外来力量角逐的情势下也催生了本土的赛努西宗教民族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二者在各自的政治理念下纷纷谋求独立与建国尝试,尽管失败了,但在利比亚国家构建的进程中仍然是重要的本土政治资源。 三、大国博弈及处理利比亚问题的方案 德意轴心力量在二战后期遭遇重创,北非反法西斯战线逐渐转入意大利本土。随着意大利人的离开,英法美盟国力量开始主导利比亚的政治局势。1943年1月,驻乍得的法国军队占领费赞。同年5月,轴心国在突尼斯投降,英国政府成立军事行政当局管理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 战后,利比亚的地缘政治博弈更为激烈。昔兰尼加、的黎波里塔尼亚和费赞的形势也因此各不相同。伊德里斯因温和的政治立场赢得了英国的支持。英国早在1942年的艾登声明中就向伊德里斯保证,不会让昔兰尼加再次落入意大利人之手。(29)1918年的黎波里塔尼亚共和国创建失败后,这里的政治活动暂时平静下来,但在1944年再次兴起,其原因在于英国保留了意大利的行政制度,法院的法官竟是意大利人。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政党要求成立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利比亚,但其内部由于争夺领导权而难以形成合力,在是否接受伊德里斯的领导地位方面也存在不同意见。由于利益冲突以及泛伊斯兰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理想诉求的差异,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政治精英在关于利比亚的未来走向的谈判中破裂了。1946年年末,法国占领下的费赞成立秘密社团,呼吁与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合并,但被法国政府镇压下去。 上述情况表明,由于利比亚三个地区政治精英力量弱小且分歧严重,再加上英法等国的外来干预,因此在国家构建问题上,外部力量就更容易介入。意大利虽是战败国,仍拥有利比亚殖民地的法理主权,且意大利新政府将战争的责任都推给了墨索里尼。如果大国妥协,利比亚仍可以归还给意大利。不过,这仅是意大利政府的一厢情愿,大国并没有这样想。按照它们的逻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利比亚应该从意大利转到另一主人之手。(30)美英法苏等大国都认为自己有资格成为利比亚的主人。对英国来说,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这里既是英国从直布罗陀到新加坡海上通道的重要一环,也是英国到东非、印度洋和远东的中转站。(31)在英国被赶出埃及和巴勒斯坦后,昔兰尼加还是英国在中东军事基地的一个超级替补。(32)法国人认为,费赞地区与利比亚没有任何关系。1943年,当法国占领费赞后,这里的居民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十人有九人患有沙眼,1/4人口患有疟疾。(33)法国人在费赞开展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重建工作,例如提高工人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开办学校,治愈民众疟疾,沙眼患者也治愈了一半。法国在费赞苦心孤诣的经营,表明其独占该地区的决心。 因此,利比亚国家构建不只是受到某一殖民地宗主国的牵制,而是处于几个大国利益博弈与权力制衡的状态。他们对利比亚的前途提出种种建议,表明了利比亚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东西方阵营之间、甚至西方国家内部的紧张关系。英美法苏等国在处理利比亚问题上经历了不同的方案,反映了它们的地缘政治诉求。 波茨坦会议期间的大国瓜分方案与集体托管方案。1945年7月18日,杜鲁门总统建议将意大利殖民地问题(利比亚问题为其一)交给由美苏英法中五国外长组成的外长委员会。苏联想以托管方式从意大利殖民地分一杯羹,建议大国瓜分利比亚。美国国务卿伯恩斯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反对苏联计划,建议利比亚殖民地问题暂且搁置。(34)波茨坦会议末期,大国在利比亚问题上的立场逐渐靠近,即集体托管。英国赞同将利比亚主权和领土置于四大国控制之下。苏联赞同三国管理利比亚。(35)实际上,英国并不想管理整个利比亚,仅对昔兰尼加感兴趣。当看到苏联想把的黎波里塔尼亚作为其称雄地中海的战略要点时,英国遂改变想法。每一方都提及集体托管方式,但几乎都是大国委任统治的老套。 伦敦会议期间的集体托管方案与联合国托管方案。1945年9月11日,英美法苏四国外长召开伦敦会议。当时,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民众情绪高涨,极力反对大国干预利比亚的未来。英国外交部的胡德(Hood)勋爵提出警告,北非局势已经很危险,我们如果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情况会越来越糟。(36)美国代表提出了集体托管模式并提交大会讨论。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抨击美国的建议是不切实际的,建议苏联管理的黎波里塔尼亚。(37)莫洛托夫还保证,的黎波里塔尼亚将在十年内独立,苏联不会将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给利比亚人,除非后者乐意接受。苏联之所以对的黎波里塔尼亚感兴趣,目的是在地中海构建自己的出海口。法国反对美国的说法,戴高乐公开声明,集体托管是不切实际的。他不反对意大利管理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英国外长贝文对美国的建议反应冷淡,同时断然拒绝了苏联的计划。(38)9月14日,美国国务卿伯恩斯提出联合国托管利比亚,联合国托管理事会将成立7人顾问委员会,行使管理权,十年后实现独立。在伦敦会议上,外长委员会关于利比亚问题陷入僵局,大国立场相去甚远。但解决利比亚的方案日渐明晰,即集体托管方案和联合国托管模式的选择。 巴黎会议期间的联合国托管方案与利比亚独立方案。1946年4月,外长委员会在巴黎召开会议,史称巴黎会议。英国外长贝文重提联合国托管意大利殖民地问题,而法国提出将意大利殖民地主权交与联合国,而由意大利代管。苏联建议邀请意大利参与利比亚的托管,成立由英法苏美四国组成的顾问委员会,意大利充当副手,苏联管理的黎波里塔尼亚。十年后,这些殖民地实现独立。英国外长贝文随即又提出反驳意见,建议利比亚成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39)英国计划宣布后,立刻得到利比亚国内民众的支持。伊德里斯电文赞赏贝文的立场。(40)法国反对英国的设想,支持苏联的建议,其原因有二:一是担心英国控制利比亚;二是认为利比亚经济发展落后,还不具备独立的条件。(41)1946年7月15日,美国在第二次巴黎会议上提出,处理意大利殖民地问题的时间延长一年;如果各大国在一年内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就将利比亚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大会;并派遣调查委员会考察利比亚民众的真实想法等。尽管巴黎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会议提出的成立调查委员会考察利比亚民众的想法,也反映了大国在博弈困境情势下寻求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明确了联合国大会处理利比亚问题的基本原则。 1947年2月,意大利签署《和平协定》,取消意大利与利比亚的殖民关系,规定利比亚的归属由美英苏法共同决定,并考虑利比亚民众的意向。四国必须在协定生效的一年内提出利比亚问题的解决方案。(42)国家构建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民众意识形态层面的认同以及通过政治动员而塑造的社会认同,因此,了解利比亚三个地区民众的政治取向显得尤为重要。1948年11月8日,外长委员会派遣调查组前往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调查民众对利比亚建国的态度。经过几个月的调查,调查委员会认为昔兰尼加需要外国援助,而英国则是最好的援助国。虽然赛努西社会结构提供了利比亚独立的理想基础,但还没有发展到独立的程度。(43)调查委员会得出如下结论:利比亚民众想摆脱外国人统治,更没有回归意大利怀抱的热情,由于缺乏管理国家的能力,并不准备独立。这一说法引起利比亚民众的愤慨。(44)1948年8月,调查委员会将调查报告交给外长委员会。苏联赞同意大利托管利比亚。英美赞同将昔兰尼加置于英国的委任统治之下,的黎波里塔尼亚和费赞的归属问题暂且搁置。一年后再做决定。1948年9月13日,在苏联的建议下,外长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巴黎会议,苏联看到自己的想法难以实现,突然放弃意大利托管的立场,要求联合国直接管理利比亚。 总之,英美法苏等国在如何处理利比亚问题上经历了大国瓜分、集体托管、联合国托管与利比亚独立等方案的博弈,反映了大国在利比亚问题上的不同利益诉求。英国的目标是占领昔兰尼加;法国的目标是控制费赞;苏联旨在管理的黎波里塔尼亚;美国并没有自己的固定目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防止任何一个大国控制利比亚,使利比亚问题国际化。可以说,大国博弈使利比亚国家构建陷入二元悖论:即一方面,各大国寻求利益平衡为联合国大会接手利比亚问题铺平了道路,使利比亚国家构建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大国在处理利比亚问题上的重重矛盾又使得利比亚国家构建充满阻力。 四、联合国与利比亚联合王国的建立 近代国家构建的历史逻辑是,民族主义力量在与旧政权或外来侵略者的抗争中以政治动员为手段推进社会革命并创建统一、独立的国家。但问题是,利比亚内部民族主义者不团结且缺乏自组织能力,又往往被大国分化控制,故很难自发地展开集体行动,难以实现政治动员和社会革命,而大国在此问题上也相互拆台、各怀心腹之事,因此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其国家构建的外部力量。在此情况下,将利比亚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反而迎来了转机。1948年9月15日,英美法苏四大国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备忘录,放弃在利比亚问题上扮演主要角色,要求联合国大会决定利比亚的命运。(45)而联合国接手利比亚问题对其国家构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刚刚诞生的联合国,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引起利比亚民众的好奇,更为重要的是,诸多亚非拉国家的成立使利比亚民众对联合国充满期待和信任。其次,联合国成为利比亚民众政治动员的有效工具。最后,联合国大会处理事情不像安理会那样实行五大国一票否决制,大会成员国在平等基础上对重大问题都可以投票,2/3成员国表决通过即可生效。 1949年4月,联合国大会召开利比亚问题第一次会议,会议成立由比利时、埃及、法国、海地、印度、新西兰、挪威、爱尔兰、苏联、英国和美国组成的联合国利比亚问题委员会。(46)委员会经过多次到利比亚实地调查后,向大会提交了四份报告,介绍了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地区政党组织的基本观点。昔兰尼加地区的利比亚解放国民大会呼吁利比亚独立,接受伊德里斯的领导。(47)他们反对大国(特别是意大利)托管,甚至以发动暴力袭击相要挟。(48)利比亚军人退役协会以及利比亚和东非难民社团属于亲意大利派,声称自己代表大多数利比亚人的利益,要求意大利托管利比亚,(49)指责伊德里斯的统治“臭名昭著、腐朽落后且反对民主”。(50)的黎波里塔尼亚的犹太社区并不在乎利比亚的分裂与统一,更在乎犹太社区的利益是否得到保证。(51)经过一个月的讨论,联合国大会关于利比亚问题第一次会议陷入僵局。在大国博弈之外,新增了其他非关联国家的建议,体现了联合国大会集体干预模式的特点。 1.英国的建议。1949年5月3日,英国提出自己的决议草案。内容包括:自决议履行之日起,十年后只要联合国大会认为利比亚具备条件就可以独立;昔兰尼加并入利比亚,但在过渡期间由英国托管;埃及、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将根据利比亚独立期限和条件以及托管理事会的建议,将利比亚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52)很明显,英国人支持伊德里斯,确保昔兰尼加不落入意大利的控制,保护英国利益。英国的建议受到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指责,拉美和阿拉伯国家也反对英国决议,前者是因为英国排斥意大利参与利比亚问题,后者是因为英国剥夺了利比亚独立的权利。(53) 2.苏联的建议。1949年5月16日,苏联提出自己的决议草案。利比亚将在5年后独立。在此期间,联合国托管理事会将按照相关协议任命咨询委员会管理利比亚。咨询委员会由9人组成,英、苏、法、意、美、埃和其他欧洲国家各出一人,利比亚本国出两人。(54)苏联的战略目的是阻止英国控制利比亚,挫败欧洲国家主导利比亚问题的图谋。 3.印度的建议。印度主张利比亚置于国际托管之下,由联合国行使管理权。10—20年的托管期结束后,在托管理事会的建议下,由联合国大会同意后举行全民公决,决定利比亚的未来:各地区是统一在一起,还是并入邻国。(55) 4.拉美国家的建议。拉美国家极力争取意大利托管利比亚,赞扬意大利对西方文明及其所在殖民地的贡献,认为墨索里尼时代只不过是意大利的一场悲剧,意大利托管利比亚有着宗教、文化以及种族的意义。正如秘鲁代表所说:“拉丁人最擅长协调正义,意大利凭什么被剥夺了捍卫自己利益的权利,罗马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56)印度强烈反对拉美国家的建议,认为将殖民地管理权委托给某一大国,后者会对殖民地施加影响,甚至将殖民地吞并。(57)印度的提议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拉美国家看到自己的想法难以实现,又提交了一份决议,要求将利比亚问题交给联合国大会。 5.伊拉克的建议。(58)1949年5月6日,伊拉克向联合国提交决议草案,建议利比亚立即独立。这代表了阿拉伯国家和利比亚民众的想法。利比亚民众反对意大利托管,要求立即独立,并得到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支持。 就在大会僵持不下之际,美国代表杜勒斯(Dulles)建议联合国成立利比亚问题委员会分委员会,协调相关各方的立场,并在1949年5月12日前提交一份能让大多数国家都接受的报告。(59)分委员会成员为巴西、智利、丹麦、埃及、埃塞俄比亚、法国、印度、伊拉克、墨西哥、南非联盟、苏联、英国和美国。在苏联的极力争取下,波兰加入分委员会。 与此同时,大国在联合国框架外解决利比亚问题的行动并没有停止。由于拉美国家在联合国大会占据席位优势,因此只要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任何决议都难以通过。贝文—斯福札计划(Bevin-Sforza Plan)即在这种背景下出台。该计划由英国外长贝文和意大利外长斯福札提出,建议自1951年起意大利托管的黎波里塔尼亚,英国托管昔兰尼加,法国托管费赞,10年期限结束后,利比亚在联合国大会认可的情况下实现独立。法国、英国与美国都支持贝文—斯福札计划,但遭到利比亚境内民众、阿拉伯国家以及苏联的反对。1949年5月,贝文—斯福札计划被联合国大会否决。小国可以通过投票否决大国的决议,这一前所未有的举措表明了联合国大会捍卫宪章的决心。 利比亚问题在联合国第四次大会上取得了突破。大会成员国经过投票表决,一致同意利比亚独立。美英代表团知道利比亚独立已经大势所趋,决定放弃所有托管计划,赞同利比亚独立,但又要求预留3—5年的准备期。苏联要求利比亚立即独立,外国军队撤出军事基地。苏联的主张得到阿拉伯国家的支持。(60)拉美国家看到自己的想法难以实现,向阿拉伯国家妥协,放弃意大利托管计划,支持利比亚独立。1949年10月11日到12月1日,利比亚问题委员会按照印度、伊拉克、巴基斯坦和美国代表团的建议,草拟了一项决议。1949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任命联合国副秘书长艾德里安·佩尔特为联合国处理利比亚事务特派专员,帮助利比亚草拟宪法,创建国家。 1949年12月21日,经过激烈讨论,联合国大会以48票赞成,1票否决(埃塞俄比亚),9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利比亚问题的289号决议。该决议内容如下:利比亚的领土范围包括昔兰尼加、的黎波里塔尼亚和费赞;利比亚不迟于1952年1月1日前成立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昔兰尼加、的黎波里塔尼亚和费赞代表组成的国民大会决定利比亚宪法的内容;联合国大会成立10人顾问委员会,成员来自埃及、法国、意大利、巴基斯坦、英国与美国,并包括经联合国处理利比亚问题专员艾德里安·佩尔特任命的4位利比亚领导人。英法等国将权力交给利比亚政府;利比亚独立后加入联合国。(61)卫拉德认为,该决议的通过体现了英美苏法和阿拉伯国家在利比亚问题上的博弈:阿拉伯国家欢迎阿拉伯兄弟国家的诞生;社会主义苏联反对一切殖民统治;英国想从繁重的行政治理中解放出来;美国一直以支持自由与民主国家独立为标榜;尽管法国不乐意看到利比亚独立,但也无能为力。(62) 利比亚政治精英在政府组成方面存在两种观点:即联邦制和集权制。昔兰尼加赛努西教团与民众担心人口占多数的的黎波里塔尼亚垄断权力,主张成立一个地方政府拥有较大自治权的联邦制政府,而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民族主义者则害怕中央政府缺乏权威,赞同成立一个中央集权制政府。1949年12月2日,双方达成妥协,同意成立一个联邦制的民主政府。(63)1949年12月,佩尔特到达利比亚。在国民大会中,佩尔特试图平衡3个地区的利益。但各方都想在宪法中寻求地位平等,这种平等试图掩盖各省之间人口素质、部族传统和资源禀赋的客观差异。1950年7月,佩尔特要求昔兰尼加、费赞与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各自派出7名代表,组成21人委员会。随后经委员会讨论决定,提出国民大会成员的产生方式,即由3个省长各指派20名成员。1951年3月,利比亚临时政府成立。10月,国民大会批准了佩尔特和占领当局共同拟定的宪法草案。宪法宣布利比亚联合王国是一个世袭的君主制政权,联邦制的政治架构最终敲定。1951年12月15日,英法按照联合国大会的安排将除国防、外交以外的所有权力交给利比亚临时政府。12月24日,利比亚联合王国建立,伊德里斯为国王。利比亚联合王国的成立标志着利比亚国家构建的初步完成。 利比亚问题移交给联合国大会对利比亚的未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就实际情况而言,当时的利比亚还没有任何一种民族主义力量能够凭借自己的权威,建立一个让民众信服的、具有政治合法性的政府。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地缘政治主导者和民族主义力量在政治共同体的建立上破天荒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使利比亚结束了分立的局面,具有了统一立国的基础,但民族构建与国家构建的深层次矛盾仍深植在这一新生的政治共同体之中。 在国家领导人的确立方面,面对大国博弈的复杂局面,伊德里斯赢得了三个地区民族主义力量和部族的支持。1944年7月,流亡22年的伊德里斯回到昔兰尼加,受到各部族的热情拥戴。(64)1945年6月,在外长委员会开始认真讨论利比亚问题以前,伊德里斯的支持者给开罗的英国国务大臣递交信件,阐述了昔兰尼加独立,支持伊德里斯为国王的构想。1946年7月,昔兰尼加的部族首领发表声明,要求英国承认伊德里斯为赛努西埃米尔,并在昔兰尼加地区成立宪政政府。1949年7月,伊德里斯在马纳尔王宫宣布昔兰尼加独立,并担任埃米尔。昔兰尼加在英国的支持下实现独立,但英国人仍保留了立法和外交权。的黎波里塔尼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也认同伊德里斯国王。到1947年,的黎波里塔尼亚领导人由于没有得到英国人让他们独立的保证,并担心重新被意大利殖民,呼吁与昔兰尼加统一。昔兰尼加宣布独立后,的黎波里塔尼亚民众承认伊德里斯的领导地位,认为后者是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统一的不二人选。(65)费赞地区人口稀少,民众缺乏政治意识,但也要求利比亚统一,接受伊德里斯的统治。(66)昔兰尼加和费赞在人口上不敌的黎波里塔尼亚,但伊德里斯国王的领袖地位抵消了上述劣势。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一个由伊德里斯为国王,包括昔兰尼加、的黎波里塔尼亚与费赞,实行联邦制的利比亚,符合民众的利益和需要。 在一个以部族结构为主体的社会里构建政治共同体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因为部族社会的政治忠诚多以地方和部族认同为主,很难上升到民族国家构建理论所要求达到的国家认同高度。昔兰尼加的部族首领明确支持联邦制,其目的在于最大程度地保持自治地位。(67)因此,部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内在矛盾仍然保留下来。 利比亚联邦政府面临中央、地方和国际三方面力量的现实博弈,这里面既有原来部族、超越部族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赛努西宗教民族主义以及殖民地时期宗主国因素的传承,也有在创建联合政府时期所产生的现实问题。正如佩尔特指出,利比亚联邦制的现代化模式代表各地方力量在制度层面的折衷调和,联邦政府现在还没有能力将松散的国家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68)具体而言,政府方面的博弈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中央和地方之间权力制衡,互相约束。利比亚宪法第36—39条清晰阐明了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联邦政府在某些领域拥有立法和行政执行权,但是在银行、进出口贸易、税收、地下矿藏等重要领域仅有立法权和监督权,行政权归属地方政府。第二,地方政府权力坐大,联邦政府权力弱小。但的黎波里、班加西和塞布哈(sebha)的省级立法会和行政会拥有较大权力。第三,各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首脑、议会和内阁等立法行政机构。第四,由于难以确定班加西与的黎波里哪一个为国家首都,最后只好认定二者均为首都。这一安排弊端明显:行政费用昂贵,办事效率低下。随后,利比亚政府又将班加西与的黎波里轮流设立为首都。一开始是一年轮换一次,后来改为两年一换。 由于联邦政府软弱,赛努西君主制政权面临着一系列国家构建难题。利比亚联合王国的成立使利比亚达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整个国家仍然是一个松散的“大拼盘”。三大省份之间难以形成一种政治共识:在多种矛盾对立面之间构建一种国家认同。利比亚联邦制只是不同地区之间妥协的一种政治制度,为长期分立的利比亚三个地区披上了“国家”的外衣。从根本上讲,利比亚国家构建的独特性源于其产生的特殊方式,利比亚既不是从西方式的绝对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发展而来,也不是如其他中东国家那样源于民族独立运动,而是大国博弈和联合国推动的产物,这便造成了利比亚缺乏整合国家行政资源和社会动员的能力,从而只能实现形式上的统一。 五、未完成的叙说:民族主义、地缘政治与国家认同 利比亚政治共同体建立之后,家族和部族认同仍然是社会同化与阶层融合的阻力,致使民众的国家认同观念淡漠。因此,对于利比亚来说,国家认同的构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利比亚当时存在两种实现国家认同整合的政治文化资源:昔兰尼加的赛努西宗教民族主义和的黎波里塔尼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69)伊德里斯王朝时期,前者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然而,宗教民族主义在利比亚国家认同的构建中存在严重缺陷。赛努西宗教民族主义的影响力仅限于利比亚的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只承认伊德里斯国王是利比亚的政治领导人,而非宗教领袖。(70)与此同时,宗教民族主义与利比亚的家族和部族认同相互影响,并不是一种打破狭隘认同观的革命性力量。因此,利比亚的宗教民族主义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社会动员,构建有效的国家认同。就利比亚统治者而言,国王尚缺乏国家认同构建的自觉性。国家认同构建本身是一种有意识的政治行为,执政者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伊德里斯国王仅认同狭隘的部族和宗教共同体,对国家构建缺乏真情实感,而传统的伊斯兰文化中并不具备产生国家认同的充分条件。这也是利比亚国家认同构建的制约因素。 20世纪50年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利比亚的一些学生和军官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利比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深受埃及的影响。当时埃及对利比亚的影响仅次于英国,埃及在昔兰尼加地区的影响甚至强于英国。埃及和利比亚地缘上接近,利比亚新政府雇佣了大量埃及行政官员,学校中的许多教师都来自埃及。(71)这些人将埃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传播到利比亚。利比亚民族主义者倡导阿拉伯统一和社会公平,希望强化国家认同,反对帝国主义等。(72)这些政治和社会主张与伊德里斯王朝所奉行的亲西方和反对阿拉伯统一的政策相悖。伊德里斯王朝最终为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这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所取代。卡扎菲执政后,在国家认同构建理念上一直徘徊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利比亚国家主义”之间。在理论上,卡扎菲的“革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试图把“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结合在一起。但在现实操作中,由于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超国家特点,二者往往存在着现实的矛盾,这也是卡扎菲推进泛阿拉伯主义联合行动多次失败的根本原因。每当利比亚与其他国家进行联合时,包括利比亚在内的每个阿拉伯国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现实的、具体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历史上阿拉伯大帝国的昔日辉煌。卡扎菲的激进做法,如鼓吹推翻阿拉伯君主制,支持摩洛哥军官推翻国王,在阿拉伯峰会上用手枪逼迫约旦国王侯赛因退位以及与沙特国王阿卜杜拉恶言相向等,均使其所谓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流于形式。同时,卡扎菲依靠自己的卡达法等亲属部族来统治国家,打击其他部族,造成任人唯亲和裙带资本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变得面目全非。卡扎菲求助于部族主义、依靠强力来维持自我统治的做法也使其政治体系具有部族政治的某些特征,这对于构建现代国家来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独立后的利比亚君主制政权仍然没有摆脱大国的控制与影响。大国之所以将利比亚问题交与联合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缓和大国矛盾,确保自己在利比亚的利益得以保全。利比亚的财政援助资金和专家都来自西方,君主制政权允许美英分别租借惠勒斯(Wheelus)、阿丹姆(al-Adem)等军事基地,其原因有二:一是伊德里斯出租军事基地换取欧美国家的援助资金以渡过财政难关。1959年末,美国援助利比亚达1亿美元,利比亚成为美国无偿军事援助数额最大的国家之一。(73)从1964年美国国务院与利比亚驻美大使阿比迪亚(Abdia)的电报往来可以看出,利比亚石油收入还不足以支撑国家发展计划,利比亚迫切需要美国的技术、经济和军事援助。而美国则需要利比亚的惠勒斯军事基地。(74)二是大国仍在利比亚进行暗中博弈,赛努西君主制政权很难摆脱西方的影响。1953年7月29日,利比亚和英国签署友好条约,以加强二者两个世纪以来的友谊。(75)1954年,法国和利比亚签署友好条约,以确保法国在费赞地区的影响。(76) 而赛努西君主制政权向西方国家出租军事基地等亲西方行为,引起了国内民众对大国干预利比亚内政的抗议,削弱了前者的政治合法性。伊德里斯国王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1964年3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总统特别助理的备忘录中可以看出,伊德里斯国王再三要求美国废除惠勒斯基地租让协议,以便制止风起云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挽救风雨飘摇的赛努西君主制政权,(77)甚至以退位相威胁。(78)而事实上,美国和英国已经同意在基地协议上做出让步。(79)但还没等美英做出反应,赛努西君主制政权已经在1969年被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利比亚联合王国难以在东西方之间找到最佳契合点,亲西方的赛努西君主制政权在民众中威信扫地。卡扎菲统治时期,利比亚亲苏仇美,支持中东的极端组织和输出革命,干涉非洲国家内政,与西方国家交恶不断,并招致国际社会的孤立。进入21世纪,利比亚通过交出“洛克比空难”嫌疑人、赔偿遇难者家属、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也放弃革命民族主义,试图实现超越民族主义的现代化转型,与西方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80)由于利比亚在非洲的地位突出,欧美国家一直对利比亚石油产业参与较深,特别是法国。法国之所以在推翻卡扎菲政权的利比亚政治变局中充当急先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关心本国企业在利比亚的石油利益。2011年,以美国和法国为首的北约,配合利比亚政治反对派对卡扎菲政权的袭击,则是大国干预利比亚的历史重演。 1969年,赛努西君主制政权被推翻,标志着利比亚国家认同构建的第一次失败。2011年,卡扎菲政权倒台,标志着利比亚国家认同构建的第二次失败。如今的利比亚国家构建正处于解构与建构之间,政治重建前景渺茫。利比亚国家构建的艰难历程说明,与地缘政治、大国干预以及相伴生的部族社会、地方政治等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宗教与世俗民族主义力量,要想在国家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需要正视其自身存在的问题。因为利比亚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在与地缘政治乃至大国博弈下谋求国家构建的,宗教与世俗民族主义力量最清楚利比亚是在何种历史境遇下建立政治共同体然后才致力于建立公共行政机构,建设共同的教育体系、法律制度、语言及国家象征体系,弥合各族群的矛盾,从而推进民众的国家认同的。利比亚国家构建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能否克服地缘政治对其内政的播弄,并建构一种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政治制度,切实完成国家建设的诸多命题。 注释: ①相关成果请参见 Michele Penner Angrist,"Morning in Tunisia:The Frustrations of the Arab World Boil Over," Foreign Affair.corn,January 16,2011; Richard N.Haass,"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Egypt," Project Syndicate,February 13,2011; Dina Shehata,"The Fall of the Pharaoh:How Hosni Mubarak's Reign Came to an End," Foreign Affair,May/June 2011; Geneive Abdo,"Green Movement 2.0? How U.S.Support Could Lead the Opposition to Victory," Foreign Affairs.corn,February 18,2011; Gideon Rose,"In Libya,How Obama Can End a Mission that Started Badly," Washington Post,March 25,2011; Micah Zenko,"The Mythrology of Intervention:Debating the Lessons of History in Libya," Foreign Affair.com,March 28,2011,i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Foreign Affairs,eds.,The New Arab Revolt,2011,http://www.google.com.tw/books?id=GMYgzhm2KAcC&printsec=frontcover&hl=zh-CN&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epage&q&f=false,pp.75,115,137,163,279,284.Habibul Haque Khondker,"Role of the New Media in the Arab Spring," Globalizations,vol.8,no.5 (October 2011),pp.675-679; Sarah Johnstone and Jeffrey Mazo,"Global Warming and the Arab Spring," Survival: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vol.53,no.2(April-May 2011),pp.11-17.国内学者对中东大变局的分析,参见黄民兴:《世纪震荡:阿拉伯世界政治动荡的原因和前景》,《回族研究》2011年第3期;刘中民:《关于中东变局的若干基本问题》,《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2期;田文林:《对当前阿拉伯变局的深度解读》,《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3期;王锁劳:《有关北非中东剧变的几个问题》,《外交评论》2011年第2期等。 ②Patrick Sutter,"State-Building or the Dilemma of Intervention:An Introduction," in Julia Raue and Patrick Sutter,eds.,Facets and Practices of State-building,Bost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09,pp.7-9. ③尤尔根·哈贝马斯:《欧洲民族国家——关于主权和公民资格的过去与未来》,《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5页。 ④Neil Robinson,"State Building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The Emergence of a 'New' Problem and Agenda," in Aidan Hehir and Neil Robinson,eds.,State-building: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Routledge,2007,p.13. ⑤王建娥:《族际政治:20世纪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9页。 ⑥与主题直接相关的研究为:Adrian Pelt,Libyan Independence and the United Nations:A Case of Planned Decolonization,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70; Hisham Sabki,International Author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Libya,Indiana University,Doctor Degree Dissertation,1967; Anna Baldinetti,The Origins of the Libyan Nation:Colonial Legacy,Exil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Nation-state,London:Routledge,2010; etc..提及利比亚去殖民化的成果有:Ronald Bruce St.John,Libya:From Colony to Independence,Oxford:One World,2008; Majid Khadduri,Modern Libya: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63; Scott L.Bills,The Libyan Arena:The United States,Britain,and the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1945-1948,Kent: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5. ⑦Ronald Bruce St.John,Libya:From Colony to Independence,p.2. ⑧Janice Monti-Belkaoui and Ahmed Riahi-Belkaoui,Qaddafi:The Man and His Policies,London:Avebury,1996,p.vi. ⑨Alison Pargeter,Libya:The Rise and Fall of Qaddafi,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12. ⑩Majid Khadduri,Modern Libya: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p.v. (11)利比亚数易国名:1951—1963年为“利比亚联合王国”;1963—1969年为“利比亚王国”;1969—1973年为“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1973—1986年为“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1986—2011年为“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2011年9月16日,利比亚国名更改为“利比亚”。 (12)Abdulhafid Fadil Elmayer,Tripolitania and the Roman Empire,Markovz Jihad al-Libya Studies Center,1997,Deposition Number 1996/1915/Dar.Kotob.P.O.Box:5070/Tripoli,p.56. (13)Henry Serrano Villard,Libya:The New Arab Kingdom of North Afri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6,p.12. (14)Abdallah Laroui,The History of the Maghrib:An Interpretive Essay,trans.Ralph Manhei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87. (15)Louis Dupree,"The Arabs of Modern Libya," The Muslim World,vol.48,no.2,1958,pp.113-124. (16)截至2011年,利比亚有140多个部族,其中影响较大的有30多个。 (17)Areal Obeidi,Political Culture in Libya,Richmond,Surrey:Curzon Press,2001,p.131. (18)菲利克斯·格罗斯:《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王建娥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36页。 (19)菲利克斯·格罗斯:《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第178页。 (20)A.A.Boahen,British,the Sahara and the Western Sudan,1788-1861,London:Clarendon Press,1964,p.128. (21)民族主义运动是指那些在现实政治中的民族国家为建立独立国家或维护本民族国家利益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因而世俗性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典型特征。20世纪后期,一些民族国家在斗争目标和旗号中却包含着某些宗教因素。宗教因素与民族主义运动融合,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纯粹的宗教运动,也不同于世俗民族主义运动的新现象,即宗教民族主义运动。(钱雪梅:《宗教民族主义探析》,《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第17页) (22)Ali Abdullatif Ahmida,The Making of Modern Libya:State Formation,Colonization,and Resistance 1830-1932,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p.86. (23)E.E.Evans-Pritchard,The Sanusi of Cyrenaic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9,pp.24-25. (24)Lisa S.Anderson,The Stat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unisia and Libya,1830-198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118. (25)Ronald Bruce St John,Libya:From Colony to Independence,pp.57-58. (26)Dirk Vandewalle,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28. (27)Lisa S.Anderson,"The Tripoli Republic,1918-1922," in E.G.H.Joffe and K.S.Mclachlan,eds.,Social &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ibya,Wisbech:Middle East & North African Studies Press,1982,pp.43-65. (28)Majid Khadduri,Modern Libya: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pp.9-10. (29)Scott L.Bills,The Libyan Arena:The United States,Britain,and the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1945-1948,p.22. (30)Majid Khadduri,Modern Libya: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p.v. (31)Mary Jane Deeb,Libyan's Foreign Policy in North Africa,Boulder,San Francisco,London:Westview Press,1991,p.23. (32)Anna Baldinetti,The Origins of the Libyan Nation:Colonial Legacy,Exil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Nation-state,p.111. (33)约翰·赖特:《利比亚》(下),陆茵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40页。 (34)Scott L.Bills,The Libyan Arena:The United States,Britain,and the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1945-1948,p.38. (35)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利比亚史》,韩志斌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第79—80页。 (36)Scott L.Bills,The Libyan Arena:The United States,Britain,and the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1945-1948,p.37. (37)C.Grove Haines,"The Problem of the Italian Colonies," Middle East Journal,vol.1,no.4(October 1947),p.422. (38)Hisham Sabki,International Author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Libya,pp.41-42. (39)C.Grove Haines,"The Problem of the Italian Colonies,"Middle East Journal,vol.1,no.4(October 1947),p.425. (40)Scott L.Bills,The Libyan Arena:The United States,Britain,and the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1945-1948,p.56. (41)Hisham Sabki,International Author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Libya,p.46. (42)Document,A/895 (以下只标注文件序号),United Nations,Official Records of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以下简称ORTSGA),Part I,Plenary Meeting,Annexes,1949,p.104. (43)F.E.Stafford,"The Ex-Italian Colonies," International Affair,vol.25,no.1(January 1952),p.55. (44)Majid Khadduri,Modern Libya: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p.124. (45)Document A/875,United Nations,ORTSGA,Part I,Plenary Meeting,Annexes,September 15,1948 p.105. (46)Document A/873,United Nations,ORTSGA,Part II,Plenary Meeting,Annexes,1949,p.91. (47)United Nations,ORTSGA,First Committee,Summary Records of Meeting,April 5 May 13,1949.p.139. (48)Document A/873,United Nations,ORTSGA,Part II,Plenary Meeting,Annexes,1949,p.132-133. (49)Document A/873,United Nations,ORTSGA,Part II,Plenary Meeting,Annexes,1949,p.146. (50)Document A/873,United Nations,ORTSGA,Part II,Plenary Meeting,Annexes,1949,p.147. (51)Document A/873,United Nations,ORTSGA,Part II,Plenary Meeting,Annexes,1949,p.144. (52)Document A/C.1/446,United Nations,ORTSGA,Part II,Annexes,1949,pp.19-20. (53)United Nations,ORTSGA,First Committee Summary Records of Meeting,April 5-May 13,1949,pp.161-165. (54)Document A/881,United Nations,ORTSGA,Part II,Plenary Meeting,Annexes,1949,p.100. (55)Document A/C.1/448,Adrian Pelt,Libyan Independence and The United Nations:A Case of Planned Decolonization,p.77. (56)United Nations,ORTSGA,First Committee Summary Records of Meeting,April 5 May 13,1949,pp.108-109. (57)United Nations,ORTSGA,First Committee Summary Records of Meeting,April 5-May 13,1949,p.64. (58)Hisham Sabki,International Author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Libya,p.92. (59)Document A/C.1/453,United Nations,ORTSGA,Part II,Plenary Meeting,Annexes,1948,p.94. (60)Majid Khadduri,Modern Libya: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pp.133-154. (61)Document A/RES/338(IV)-A/RES/288(IV),United Nations,Official Records of the Fourth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1949,pp.10-13. (62)Henry Serrano Villard,Libya:The New Arab Kingdom of North Africa,p.33. (63)Confidential,No.13,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eds.,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简称 BDFA),Part V,From 1951 through 1956,Series G,Africa 1951,edited by Peter Woodward,vol.1,LexisNexis,2005,p.324. (64)Scott L.Bills,The Libyan Arena:The United States,Britain,and the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1945-1948,p.21. (65)Majid Khadduri,Modern Libya: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p.82. (66)Majid Khadduri,Modern Libya: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pp.122-123. (67)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eds.,BDFA,Part V,From 1951 through 1956,Series G,Africa 1951,vol.1,LexisNexis,2005,p.324. (68)Dirk Vandewalle,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p.46. (69)Jacques Roumani,"From Republic to Jamahiriya:Libya's Search for Political Community," The Middle East Journal,vol.37,no.2,1983,pp.159-163. (70)Marius K.Deeb and Mary Jane Deeb,Libya since the Revolution,Santa Barbara:Praeger Publishers,1982,p.96. (71)JT10316/1,No.4,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eds.,BDFA,Part V,From 1951 through 1956,Series G,Africa 1954,vol.III,LexisNexis,2008,p.112. (72)Majid Khadduri,Modern Libya: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pp.330-333. (73)Dirk Vandewalle,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p.45. (74)Nina Davis Howland and David S.Patterson ed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简称 FRUS)1964-1968,vol.XXIV,Afric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9,p.69. (75)JT1052/23,No.6,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eds.,BDFA,Part V,From 1951 through 1956,Series G,Africa 1953,vol.III,LexisNexis,2007,p.368. (76)JT10317/12,No.2,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 General eds.,BDFA, Part V,From 1951 through 1956,Series G,Africa 1954,vol.III,LexisNexis,2008,p.109. (77)H/63-6/64,Secret,Nina Davis Howland and David S.Patterson,eds.,FRUS,1964-1968,vol.XXIV,Afric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9,p.72. (78)7/64-12/68,Confidential,Nina Davis Howland and David S.Patterson,eds.,FRUS,1964-1968,vol.XXIV,Afric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9,p.76. (79)H/63-6/64,Secret,Nina Davis Howland and David S.Patterson,eds.,FRUS,1964-1968,vol.XXIV,Afric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9,p.73. (80)韩志斌:《从革命民族主义到超越民族主义——利比亚现代化的跃迁》,《西亚非洲》2009年第12期,第45—51页。 责任编审:姚玉民标签:阿拉伯民族论文; 政治论文; 利比亚战争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意大利战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民族独立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