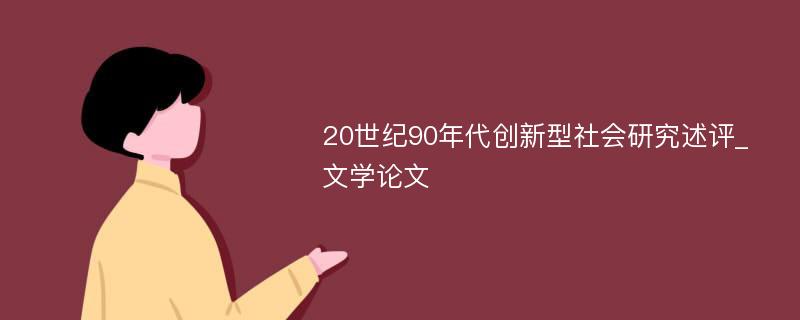
20世纪90年代创造社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25(2004)02-0076-05
20世纪的最后10年,是创造社研究成果最多、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10年。认真总结 这10年创造社研究的学术成绩及其学术经验,考察其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研究中的学 术遗漏和学术分歧,对于深化创造社研究乃至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是有意义的。
几个重要课题的突破
1.创造社的青春文化品格
从青春文学或青年文学的角度,探讨创造社的文化特征,这一时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王富仁在《创造社与中国现代社会的青年文化》[1]一文中,率先提出以“青年文化 ”这一概念去综括创造社的文化特征,让人耳目一新。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体现着 “老年文化”的特征,《新青年》及其倡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中年文化” 的独立身姿,创造社则是中国现代社会“青年文化”的代表。创造社作家与五四倡导者 的重要区别在于,他们还保留着对现实社会文化环境的“界外感觉”,高扬着自由意志 与自由精神,传达着人类初生时期最单纯最原始的啼哭,同时将爱情的描写推向了高峰 ,并表现出很强的瞬时情感形式,所有这些都是青年文化的集中体现。在他的观察中, 创造社后来转向了中年文化。文章的分析精细、透辟,使得创造社独有的文化特征从五 四新文化的文化时尚中鲜明地凸现出来。围绕这一观点,魏建的论文从青年学的角度观 测了创造社这支“异军”之“异”的一些本质所在,并通过“年龄文化”的细致分析对 作为青年文化的“创造社现象”做了深入的阐释。[2]周海波的《前期创造社与五四青 春人格创造》[3]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作者认为创造社独有的创造精神是直接继承和 发扬五四青春精神的结果,是五四青春人格,青春民族形象的突出体现,这种青春人格 又集中体现在“征服精神”和“性爱意识”之中。
2.前期创造社与五四文学革命
创造社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影响最大的纯文学社团之一,它与五四文学革命之间的 关系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朱成甲的《创造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1]从新文 化运动的历史演变过程出发,对创造社与这场运动的关系做了重新评价。文章指出,创 造社诞生于新文化运动的低潮,却以卓越的创作实绩,弥补了新文化运动中文学创作落 后的缺憾,并以大胆的创新和自我否定精神推动着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发展。有趣的是, 与朱成甲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台湾学者周锦的文章《创造社给予中国新文学发展 的冲击》。[1]与朱文从历史发展变化中把握问题的论述方式不同,周锦以一种近于事 实推理的归纳法切入作品,直接从创造社成员当年的言论出发,总结出这个社团在中国 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对新文学发展的巨大冲击。他还从正反两方面看待创造社 的影响力,既肯定了创造社以其独特的个性及创作改变了文坛风气,导正了中同新文学 的发展方向;又指出其失控后带来的负面影响。魏建和张全之则主要从另一角度剖析了 创造社五四新文学之间的非同步性。魏建在《创造社的价值:为“五四文学革命”补课 》[4]中明确指出,诞生于异域的创造社“异军”从一开始就不是与五四新文学革命先 驱及其继承者文学研究会并肩前进的,而是将纠正和补充“五四文学革命”的缺失确定 为自己文学事业的“起点”。创造社前期为新文学建设做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从道德叛 逆、个性解放、“拿来主义”以及对五四新文学非艺术化倾向的纠正四个方面为“五四 文学革命”补课。张全之的文章《五四文学的“二次革命”——重评前期创造社在五四 文坛上的地位》[5]和《论创造社向“五四”文学的两次挑战——创造社与“五四”关 系新论》[6]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在前文中主要考察了创造社成员早期在日本的文 学活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国内文坛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是在各自独立的情况下并行 发展的,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创造社的意义在于把文学的审美特征与个体生命的情感 相结合,感同身受地展示了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标志着文学意识的再一次觉醒,是五四 文坛上的“二次革命”。另一篇文章则以创造社20世纪20年代挑起的两次大规模论战为 研究对象,分析了创造社与五四的关系。这三篇文章都着力于同中求异,打破陈规,强 调创造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独立性,具有一定的开创价值。宋益乔的《一代青年代言 者的心声——论前期创造社对批判封建道德斗争的特殊贡献》[7]则推陈出新,仍从反 封建伦理道德的立场出发,揭示出前期创造社的存在对五四文学的意义与价值。总之, 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语境中重新审视和把握创造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是 必要的,也促进了创造社研究往纵深方面的开掘与拓展。
3.创造社与中外文化
研究视野的拓展与研究领域的扩大还体现在研究者对创造社与传统文化以及外来文化 关系的探索与考察。由于创造社在五四文坛是反封建、反传统最决绝的一个社团,因此 ,长期以来大多数研究者都忽略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90年代这一问题取得了明 显进展。如魏建在《创造与选择——论前期创造社的文化艺术精神》一书中通过还原传 统,开掘出了创造社作家诗歌和戏剧中强烈的功利倾向的由来;在对创造社与传统文化 艺术关系的梳理中,发现了一个为中国文学史研究长期忽略的传统文学母题——“倡优 士子”模式。
创造社与外来文化艺术渊源的问题本身就是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存在争议、分歧最多 的是“浪漫主义”问题。90年代,一些研究者注重分析创造社对外来文化吸收的复杂性 。朱寿桐在这方面用力最勤、成就最大。他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如《评创造社研究 的浪漫主义体系》[8]《论创造社对东西方文化的选择》[9]和《创造社对浪漫主义:挑 剔的选择》,[10]对这一问题做了集中的探讨。他认为,创造社本质上并不是浪漫主义 或别的什么主义,而是超越于各种主义规范之上的“情绪表现”。他认为创造社文学与 浪漫主义固然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用浪漫主义美学方法研究创造社文学也确实取得了 一些成就,但这并不能说明创造社对浪漫主义美学在事实上倾心接受了。因为创造社对 浪漫主义观念及作品向来是十分挑剔的,有时还进行严厉的批判和诋毁。他们的创作倾 向、艺术风格是复杂综合的,只有那些符合情绪表现要求的美学才会被他们选择接受。 即使那种情绪表现的文学倾向基本上也不是浪漫主义影响的结果,而是与创造社作家的 中西文化、文学素养有着内在的联系。魏建的《论创造社式的“拿来主义”》[11]也认 为前期创造社与外来文化艺术的关系并不是用某一种主义或什么是主导能说清楚的,其 外来艺术渊源实际上是一个多元的外国文艺复合体。其“拿来主义”的方式独具特色。 以古化洋,取皮去核,消化变形是其吸收和借用外来艺术的主要形式。陈旋波的论文借 助于音乐性这一独特视角对创造社诗学理论、诗歌和抒情小说创作的浪漫主义特质进行 了考察,[12]读来耳目一新。
此外,唐世春的《论创造社与表现主义》、[13]黄川的《创造社与西方现代主义》、[ 1]陈遐的《心灵的契合——屠格涅夫对创造社前期主要作家的影响》[14]以及李风的《 难以应答的神性呼唤——创造社对基督教的误读》[15]等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 创造社与其他外来文化的异同以及创造社受外国思潮影响的情况。
4.创造社的文艺批评观
鉴于创造社文学批评理论在五四文坛地位的举足轻重,近年来也吸引了不少学者对其 文学批评观的关注。谢昭新的文章《论前期创造社文学批评观》[16]主要论述了前期创 造社文学批评观的内容及特点。他认为,前期创造社的文学批评观以“自我表现”为核 心,并以开放式的态度接受了西方文学艺术及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极影响,由此,其批评 观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与变动性。与这篇文章同一思路的,还有《论创造社前期的文艺 批评理论及其实践》[1]一文。李怡、段从学的论文《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倡导者的“创 造社”批评群体》,[17]把这一批评群体置于马克思主义批评线索上来论述。他们认为 ,与前期创造社特有的青年文化气质不同,后期创造社批评群体更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 和作家的无产阶级意识。
5.创造社作家的文化心态
对创造社作家文化心态的研究,是90年代创造社研究的一个全新课题。黄侯兴的《论 创造社作家的文化心态》[18]将人们业已观测到的创造社作家的“自我表现”,鼓吹破 坏并倡导创造的精神特征提炼到一种文化心态层面加以把握,在学术思维的方法论上表 现出鲜明的开拓性。蔡震的《历史抉择与创造精神——创造社文化心态审视》[1]从创 造社主要作家前后期社会思想、文学主张和审美趋向的转变或者不变的种种复杂现象着 眼,揭示其在急剧动荡的中国现代社会思潮裹挟下执着追求并努力实行创造精神的文化 心态,将黄侯兴宏观地提出的问题通过更集中更鲜明的方式阐述出来。这两篇文章不约 而同地都将研究视线从外在显性因素的考察转移到了作家内在心理因素的探讨,推动了 研究的深化。
学术争鸣
1.创造社的“转向”
后期创造社的方向转换,一直以来被研究者们视为“谜”一样的文化现象。创造社转 向与当时社会政治革命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但关于创造社方向转 换的本质原因,学者们却见仁见智,人言言殊。蔡震的《论创造社的方向转换》[19]一 文,在承认客观外界条件的前提下,认为创造社方向转换的内在主观动因是他们一贯奉 行的浪漫式的理想主义。他力倡要把创造社方向转换看作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指出前 期创造社的唯美倾向与转向时激进的功利主义追求之间源于同一种思维逻辑。他们始终 坚持用审美的方式思考一切,在为艺术与为革命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他还在另一篇文章 [20]中从创造社文化心态内在转化的必然性,论述了后期创造社成员转向的必然性。而 刘玉山《浪漫主义向革命文学的过渡——论创造社的转向》[21]一文,通过分析创造社 浪漫主义的发展,认为时代对于创造社作家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因素,时代才是造就创 造社作家转向的根本动力。
2.创造社的纷争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1922年至1924年的那场论争,也是研究者兴趣浓厚的研究话题之 一,90年代亦然。刘炎生的文章《不同文艺观和“行帮意识”的表现——文学研究会与 创造社论争评述》,[22]通过具体的材料分析,认为在这场论争中,文学研究会作家的 观点基本正确,而创造社作家的观点基本上是错误的。论争的原因不过过是“旧式的文 人相轻”与“行帮意识”。但张全之在《五四文学的“二次革命”——重评前期创造社 在五四文坛上的地位》一文中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不应该把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之 间的矛盾简单地理解为宗派主义情绪与相互之间的误解,而主要源于他们对文学本质的 不同见解以及对西方文学吸收借鉴的不同价值选择。另外,这时期创造社与其它社团的 比较研究也开始出现。赵小琪的《倾斜的象牙之塔——前期创造社、前期新月派文艺思 想的悖论》[23]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主要论述了二者前期文艺思想的相似点 及各自的复杂性,二者丰富了五四文学的审美形态。
存在的问题
1.被冷落的“后期”
就目前创造社研究状况来看,主要成果大都集中在前期,后期近乎空门。一般看来存 在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创造社的核心力量、影响较大的作家作品大都集中在前期。像 郭沫若的诗歌,郁达夫的小说,田汉的戏剧等。而到了后期,他们的创作均明显减少。 其次,后期创造社的突然“转向”,是研究的难题。再次,后期创造社与写作的非文学 化,难以引起研究者的兴趣。90年代,吴禹星的《创造社第三期成员与<文化批判>》[2 4]是为数不多的研究文章之一,作者借助《文化批判》及其成员对后期创造社的活动进 行了简单的评析。实际上,作为创造社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发展阶段,后期创造社是非常 重要和不可或缺的。
2.文体研究冷热不均
这10年来创造社小说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多,而其他文体,尤其是散文、戏剧的研究远 远不够。90年代创造社诗歌研究的重要成果是柯文博的《论创造社诗歌》[25]和龙泉明 的《对于一种社会成规的革命——创造社诗歌综论》[26]两篇文章。柯文扩大了研究视 野,对创造社的诗歌作品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探讨。龙泉明从整体上探讨了浪漫主义思 潮与创造社诗歌之间的联系,特别指出创造社诗人群不同于五四其他一些诗派的关键之 处在于他们“破坏”与“创造”的时代精神。戏剧研究成果更少。90年代除了刘珏的一 篇《浪漫主义对“五四”戏剧的审美影响》[1]外,鲜有问津。尽管创造社不乏郁达夫 、郭沫若这样的散文大家,创作数量颇丰,上乘之作也不少,但还是被研究者们忽视了 。作为创造社文学创作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散文和戏剧的研究是当前亟待开拓的领域 。
收稿日期:2004-04-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