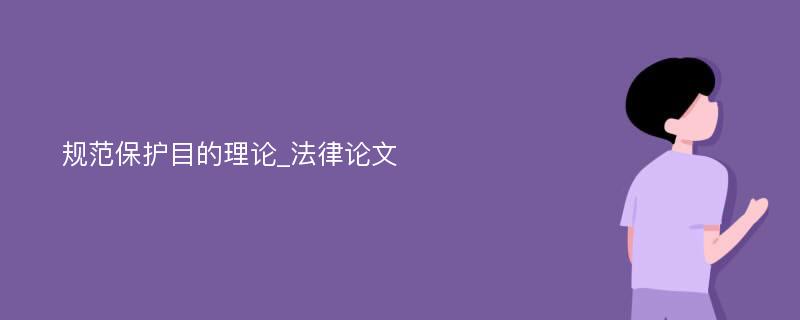
规范保护目的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的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规范保护目的理论,是指损害结果发生在规范保护目的之外的,应排除归责。亦即,“规范并不防护所有的在个案情况中超越了规范规定范围的危害,而是只应当防护不遭受那些危害后果,对这些后果规范一般适合于对它们的避免,同时这些规范也是为避免这些后果而制定。”①在规范制定过程中,立法者设定人们的行为模式和注意义务时通常都具有一定的目的;相应地,在规范适用过程中,法官在确定个案事实与具体规范的连接时就需要上述目的的指引。法益理论能确定法条的保护法益,却无法确定某一损害结果是否属于本法条所防范的类型,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则能弥补这一缺陷。“任何行为规范之目的均在于保护某些人在某些情况下,免于某种危险,而非保护任何被害人免于任何发生在他身上之危险。”②以故意杀人罪为例,法益理论只能确定故意杀人罪的保护法益是人的生命权,却不能确定某种生命权灭失的具体情形是否为该条规范所禁止。例如,一名警察在开车时将自己上膛了的职务手枪放在汽车仪表盘上,他的情人用这把手枪自杀了。被告知道被害人常常抑郁、忧伤并有自杀的倾向,将上膛的枪放在她跟前是危险的。③不过,即便被告的行为引起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该结果也不在故意杀人罪的保护范围之内。因为被告所违背的注意义务并不是故意杀人罪所要求的,此时对行为人进行归责以确证刑罚的效力是无意义的。“注意义务不是为了避免某个结果的发生,而是为了避免某种特定类型的结果发生”。④根据规范保护目的,可以判定侵害某种法益的行为与结果,是否某一注意义务所力图防止的对象。“任何完整的法律规范都是以实现特定的价值观为目的,并评价特定的法益和行为方式”,⑤由此确定:行为是否制造了法不容许的风险,结果是否法不容许风险的实现。 规范保护目的理论起初主要用于交通过失犯的归责问题,现在则作为客观归责的下位规则之一,服务于结果犯的刑事归责。在德国,围绕规范保护目的理论所展开的激烈争论从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潮,并一直蔓延到现在。我国学者对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研究则始于21世纪初,到现在只有十多年的时间。较早的研究往往是客观归责研究的副产品,范围和深度都有不足。近年来,随着客观归责理论研究的深入,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也引起了诸多学者的重视。总体来看,我国学者研究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主要有两种进路:理论研究与适用研究。⑥前者主要在过失不法与结果归责的框架下进行,例如倪培兴博士的《论作为归责理论的犯罪构成理论》(2004),周光权教授的《结果回避义务研究:兼论过失犯的客观归责问题》(2010),笔者的《刑法中注意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研究》(2013),陈璇博士的《论过失犯中注意义务的规范保护目的》(2014)等等。后者则将规范保护目的与分则具体罪名或案例结合起来,将规范保护目的作为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例如劳东燕教授的《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与结果加重犯的界定》(2008),刘艳红教授的《注意规范保护目的与交通过失犯的成立》(2010),梁根林教授的《“醉驾”入刑后的定罪困扰与省思》(2013)等等。在理论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对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研究多数是在客观归责理论的框架下进行的,只有少数是在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前者例如笔者的《刑法中注意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研究》,后者如刘艳红教授的《注意规范保护目的与交通过失犯的成立》。在适用研究方面,与德国相仿,我国学者对规范保护目的研究也集中在过失犯,尤其是交通过失犯上。 规范保护目的理论是客观归责的核心规则,它与客观归责的其他下位规则也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加强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研究,可以深化客观归责研究的深度。进言之,在司法适用研究的同时,需要加强关于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基础的研究。理论研究对适用研究具有指引作用,如果理论研究跟不上适用研究的步伐,适用研究就只能是经验上的积累,无法获得理论上的自觉。当然,理论研究也需要从案例中获得灵感和资料,在这方面,适用研究对理论研究也具有促进作用。规范保护目的理论是从德国刑法学中引入的知识,我们在奉行“拿来主义”的同时,也要对其有所反思,这样才能够促进外来知识的本土化。只运用而不思考,并不是法学移植妥当的态度。因此,本文侧重对规范保护目的理论进行基础研究,尤其以历史、思想和方法基础为论述重点。 一、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历史与现状 (一)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之起源 1.大陆法系 在大陆法系,在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产生的时间上,刑法学者认识并不一致。一种观点认为,规范保护目的理论首先出现在民法中侵权责任领域,后来才被引起到刑法学之中。20世纪30年代中叶,德国比较法学者拉贝尔(Ernst Rabel)于统一买卖法草案相关研究中提出规范保护目的理论,本意为“合理预见说”提供一个替代标准,却为因果关系的归责转型提供了契机。1956年,拉贝尔的学生Von Caemmerer在弗赖堡校长演讲中发表《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之基础》一文。此后,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在德国民法学上被采为通说,后来又被刑法学者运用到刑事归责上。⑦ 另一种观点认为,规范保护目的理论首先产生于刑法学中。早在20世纪初,德国学者马克斯·路德维希·米勒(Max Ludwig Müller)就提出了自己的规范归责构想,这一构想被认为是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先导。⑧日本学者山中敬一指出,米勒在1912年《刑法及损害赔偿法中因果关系的意义》一书中所展开的理论也是将“答责性的限定问题”置于“违反法规范”,即违法性问题中。米勒的考察很显然将“风险化的程度”(制造风险)与“规范目的与结果的有责的惹起”(实现风险)问题进行区分。⑨ 上述两种观点都只有部分的道理。其一,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确产生在刑法学中,只是在当时被忽视了。当时的刑法学正处于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迷雾”之中,当然容不下这种规范性的思考。其二,刑法中的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真正引起广泛的重视,并奠定客观归责的基础,是在民法中客观归责理论发展起来之后。可见,“刑法中的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不是一种战后时期的成绩,尤其不是民法保护目的理论的一种后续繁荣,而是至少在一百年前就已经开始的一部历史。……但是,民法的规范保护目的原理对其刑法分支的产生和现今面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⑩ 2.普通法系 在普通法系,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出现得更早,有史料可查的最早案例是19世纪70年代的Gorris v.Scott一案。在该案中,原告委托被告将他的羊群从德国运送到英国,不料在海运途中遭遇暴风雨,羊群因而死伤大半。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赔偿损失,理由是根据英国法律,自外国运送牛羊到英国的船只必须将牛羊分区、设置围栏并铺设地板,被告却没这么做。法院判决认为,本案中所涉及的英国法令并非旨在防范海上灾难可能导致的损失,而是为了防止动物过于拥挤、传染疾病并将疾病带入英国。暴风雨来袭所导致的羊群死伤之损害结果,并不在上述法令所欲防范的损失范围之内,因此被告不负损害赔偿责任。(11)显然,这里体现了规范保护目的的思想。 在美国,Joseph W.Bingham在1909年发表的论文中就已经相当熟练地运用“义务的目的”、“义务的保护范围”或“法律的目的”等概念。他指出,“法定义务总是基于某种法定目的而被赋予,法律因果关系就是确定具体义务的具体目的问题。在每一个研究的判例中,所关心的问题是某错误行为或疏忽对于损害结果而言是不是‘法律上可责难的’。对这一问题,都是通过澄清被违反的义务的目的解决的。只有错误行为同时也处于法律设定义务的目的范围之内,才有可能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反之,该行为也就不是结果的法律原因。”(12)美国也有运用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判例。在1938年Draxton v.Katzmarek一案中,一开始被告确实是在超速驾驶,但在公路某处他减速到合理限度之内,恰好在这时一个小孩突然跑到车前并被撞伤。法官认为,不应该去询问在速度和事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而应基于以下理由作出裁决,即法规意图遏制的在速度上冒险,指的是类如失去控制这样的情况,而本案明显不在这类情况之列。(13) 在英美法中,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已成为刑法和侵权法通用的归责原理,虽然在细节上不完全相同,但都发挥着重要的归责指引功能。正如哈特和奥诺尔所指出的那样,“损害是否是这个不当行为的‘结果’或‘后果’,或者由这个不当行为而‘造成’;或者这种结果是否‘过于间接’或者‘不足以最接近’;或者是否有其他第三者的行为或者一些特别的自然事件成为‘替代原因’。这些问题看上去好像是一些事实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根本就不是事实问题。它们的答案不在于查明某一特定案件的事实是否归属于某一因果联系的一般概念所涵盖的范围,而在于询问特定案件所适用具体法律规则的‘适用范围’、‘目的’、‘政策’对责任所加的限制是什么。”(14) (二)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之前史 1.米勒(Müller)(15) 在《刑法和损害赔偿法中因果关系的意义》一书中,马克斯·路德维希·米勒指出,不是每一个通过有责任的行为引起的结果都有罪责。例如,当一个人站在射击靶前,其已经遵守了一般的注意规则,但未经允许使用了他人的子弹,而于同时一名射击场管理员突然出现在射击线范围内并被射死,那么射手的行为只能被认定为应当负责的财产损害行为。虽然死者的死亡是因射手的有责行为(损害财产行为)引起,但射手并不因此承担责任。因为对死者的责任应当负责的行为应当是由违法的侵犯生命权的行为,而不是被禁止的损害他人的所有权(未经允许使用的子弹的所有权)的行为。在另一个案例中,当一个人将一个花盆放在了一扇朝着闹市街道的窗台上,而未将其放稳,以至于花盆很可能会掉下窗台,考虑到以保护生命权和身体健康权为目的的法律规范,这样的行为是违法的。如果花盆从窗台掉下去,刚好有一名行人路过并因躲避被花盆砸中而快速的逃到街道的另一侧,但在街道的另一侧时被掉落的屋瓦所砸死,那么其死亡结果可归结为由禁止伤害的违法行为(摆花盆的行为)所导致。基于上述两个案例,米勒认为,如果损害结果是由于有责行为引起而且实现了该行为的危险性,那么损害结果可认定为由该行为所导致,并且该行为是有责的行为。 2.恩吉斯(Engisch) 大约二十年后,米勒的规范归责思想被恩吉斯所采纳。为了更形象地予以说明,在其相当性原理中,恩吉斯将结果相当性与特殊形式的因果流程区别开来。第一次相当性判断以构成要件规范为标准判断行为的危险性,即判断是否存在一个构成要件结果(行为危险论);第二次相当性判断则以“基于因果进程的特殊方式的相当性”说明具体结果与规范违反之间的联系(危险实现论)。(16)山中敬一指出,恩吉斯的理论构建已经突破了相当因果关系说,实际上具有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萌芽。“恩吉斯的危险实现论是以事后判断的立场为基础,因此不再是本来的相当说,事前违反规范(违反注意义务)的危险,在事后,如果不在目的的射程范围内,则该危险并未实现结果,在这一点上,显然是保护目的论的思考方法。”(17)在另一个判例中,行为人通过一个有责的威胁生命的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了严重烧伤,但是被害人并非直接死于烧伤,而是在后续的健康恢复中,亦即在为了皮肤移植而进行的手术中,因不能承受麻醉剂而死亡。恩吉斯认为,因为不存在违法性关联而不能认定该行为应承担刑法责任。尽管行为人的行为因可能造成死亡危险而应当被禁止,但是所发生的结果不是与违法行为相联系的结果,因此,其不属于基于其发生可能性而对举止加以禁止的结果。(18) 3.阿明·考夫曼(Armin Kaufmann) 阿明·考夫曼在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上有一个态度转变的过程。起初,他肯定了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功能。在下述案例中,他适用了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并得出恰当的结论。一个司机首先闯了一个红灯,但此时并未发生交通事故,而是在之后的路程中,以正确的行车方式撞死了一名路人。与恩吉斯一样,阿明·考夫曼也认为,这里缺少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的先行为与之后结果发生之间的违法性联系。之所以不存在违法性关联,是因为被违反的注意义务规范只是为了保护十字路口的交通安全,而不是为了避免之后的死亡结果。而人们把与违反注意义务无关的结果归结为可被处罚的基础性意义,而这是与罪责原则相违背的。(19)后来阿明·考夫曼却认为,客观归责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而是一种种类集合,尤其是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实际上无法作为一种在内容上指示如何适用法律的工具。这一观点后来得到了福利许(Frisch)的支持。(20) 4.耶塞克(Jescheck) 在《德国刑法教科书》中,耶塞克指出,“刑法首先追求的是法益保护。因此,就法目的问题而言,对被保护的法益及刑法规定的保护范围的认识就显得非常重要。”(21)根据何种标准确定刑法规定的保护范围呢?耶塞克认为,自然科学的因果关系只能提供问题解决的外部框架,结论则必须按照“特殊的规范标准”才能得到。这种“特殊的规范标准”不是相当性判断,而是规范保护目的判断。“相当理论作为界定责任的原则对于民法来讲,网眼太宽了。……如今在民法中责任界限问题主要是通过顾及说明责任的规范的意义和承受力来解决,而不是通过不准确的盖然性判断来解决。换句话说,这取决于被违反了的规范的保护目的,这一思想也在刑法中形成了过失犯罪范围内客观归责的标准。”(22)在下列案例中,耶塞克运用了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司机的驾照过期了或者司机喝了酒,但却没有过错地撞了人,那么结果就不在各个规范的保护目的范围之内。在帝国法院判决的著名的摩托车事故案中,两名摩托车司机在黑夜、没有照明的情况下一前一后、歪歪扭扭地行驶着,而在下一个岔路口处,其中一名司机与另一名也没有打开照明灯的摩托车司机相撞,两人都死了。在这个案例中,耶塞克认为在后面的行驶的摩托车司机没有参与到撞车中,他对此不承担责任,因为法律要求的照明义务不是为了让其他的车辆注意自己,或者通过这种方式避免他人的相撞。(23) (三)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之现状 规范保护保护目的理论在德国的争论现状可以描述为三种立场:一种是“积极支持”的观点,一种是“谨慎支持”的观点,还有一种是“消极反对”的观点。 1.“积极支持”观点 这种观点倾向于认为:(1)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对于结果犯的限制归责具有重要功能。例如,许乃曼认为,当结果不在注意规范保护目的之内,处罚行为人无法达到一般预防的效力;再如,鲁道菲也认为,当结果不在注意规范保护目的之内,行为人没有避免结果发生的法义务。(2)这种观点认为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可以作为指导法律适用的工具。例如许乃曼曾指出,在个案的适用上,客观归责始终取决于具体相关的行为规范和这些规范的目的构造。要确定特定结果是否处于所侵害的行为规范的保护范围之内,行为规范是否对防止结果发生有意义,必须对所涉及的规范做目的论的解释。(24)(3)一般来说,这种观点所界定的规范保护目的理论较为宽泛。例如,罗克辛不但认为规范保护目的包括构成要件保护目的与注意规范的保护目的,还认为规范的保护目的不仅具有排除和限制归责的功能,还有归责的积极认定功能。再如,鲁道菲甚至认为合法替代行为的结果避免可能性也属于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范围。(25) 2.“谨慎支持”观点 这种观点倾向于认为:(1)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与相当性理论具有同样的缺陷。例如,拉伦茨认为法规目的说的意义被其支持者过高估计了。实际上,法规目的说提出的标准与相当性标准同样过于宽泛。(26)普铂(Puppe)甚至认为,注意规范保护目的其实就是相当理论的化身。(27)(2)这种观点倾向于确定和限缩规范保护目的理论所适用的案例类型。例如,沃尔特就区分了“真正”的保护目的问题和“不真正”的保护目的问题,借此划定了保护目的理论的核心区域,即除了震惊损害案例和持续伤害的后遗症案例之外,还包括了典型的禁止追溯情形和第三人帮助的自我危险情形。(28)(3)“谨慎支持”观点批评了下述现象,亦即“法规目的之确定经常系法官自行判断之结果,法官无形中扮演着立法者的角色”,(29)要求合法、客观、合理地确定规范保护目的,避免过分主观随意。 3.“消极反对”观点 这种观点起初倾向于认为:(1)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实际上无法作为一种内容上指示如何适用法律的工具。(30)阿明·考夫曼、福利许等学者认为规范保护目的或范围非常模糊,不明确的场合很多,而一种自身即不明确的理论,显然无法发挥指导法律适用的功能。(2)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不仅不能限制归责,还有可能扩张归责的范围。不过,现在持“消极反对”观点的人越来越少,主要集中在反对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过分滥用,即反对一种“规范保护目的万能论”上。这种“万能论”认为,所有归责问题的解决最终都要落到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上。(31)正如布劳洛克教授指出的那样,反对保护目的理论者于论理上之见解较少提出基本性之反对,警告过度使用保护目的理论之声音几乎总是涉及一些特定之适用范围。(32)因此,这种观点逐渐流向“谨慎支持”观点,即框定其主要适用的案例类型。现在主流意见认为,注意规范保护目的只能适用于典型案件,在非典型案件中,无论遵守注意规范与否都有可能制造法不容许的风险。(33) 二、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思想基础 德国学者德根纳(Wilhelm Degener)指出,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基础思想包括两点:其首先伴随着反抗“自陷禁区原则”(Versari in re illicita)而成长,随后受到来自于利益法学的“立法目的原则”(ratio-legis-Maxime)推动。(34)在结果归责问题上,自陷禁区原则和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代表了两个极端。自陷禁区原则是最早限制结果归责的标准,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则是最新限制结果归责的标准。由于自陷禁区原则划定的归责范围过宽,现在成了恶名昭著的“结果归罪”的典型代表。对自陷禁区原则的反抗一直持续到现在,尤其是体现在结果加重犯问题上。“立法目的原则”是指,法律解释应探究立法者历史上的意思,也就是坚持“对制定法忠诚”。由此形成的“历史的法律解释”和“法官受制定法拘束”两项原则,构成了利益法学的基点。(35) (一)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与“自陷禁区原则” 1.“自陷禁区原则”及其问题 根据宾丁(Binding)的见解,加重结果犯的起源可追溯至罗马法或日耳曼部落法,不过,持相同意见的极少。一般认为,加重结果犯起源于教会法上的自陷禁区原则(versari in re illicita),且已成定论。此一原则的意思是指,“从事不正行为之人,对因此而生之一切结果必须负责”(versanti in re illicita omnia imputantur quae sequuntur ex delicto)。(36)在盛行客观归罪和主观归罪的早期人类社会生活中,追究个体责任的由往往只需要单纯的犯意或者损害结果即可。这样的归责标准无疑给人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极度限缩了生活的范围和个体的自由。自陷禁区原则之所以被引入世俗刑法中,本意是为了限制结果归罪的泛滥,因此具有“正义的核心”。它用以限制归责的标准是“是否从事了不正行为”。亦即,如果从事了不正行为,就要为该行为所导致的所有结果负责;如果没有从事不正行为,即使发生了损害结果也不可归责于他。所谓“不正行为”,并不等于“合法行为”,而是在合法行为的同时也要保持“相当之注意”。例如,即使是基于博爱的精神而为手术时,如果怠于为必要之注意,亦被认为是不正行为。(37)根据现代观点,自陷禁区原则在结果的界定上可以超出行为人的预见,这种纯粹客观的界定表达了结果责任、间接处罚的意思,因此遭到了当今刑法理论的强烈批判。 迄今为止,自陷禁区原则在刑法中并没有被清除干净。作为自陷禁区原则的残余,很多国家(包括我国)刑法中都仍然规定着结果加重犯。结果加重犯,又称加重结果犯,是指行为人在实施基本罪之行为时发生了超出基本罪构成范围的重结果,因而导致刑罚加重的犯罪形态。(38)在结构上,结果加重犯包括基本结果的故意犯和加重结果的过失犯两部分,但其刑罚却比二者刑罚之和重得多。因此,结果加重犯的正当性问题一直是学者争议的焦点。例如,黄荣坚教授认为,从宪法上的公平原则来看,除非另有特别的不法要素存在,否则把刑法当中某些原本应该用想象竞合处理的情形另外做大幅度的加重刑罚的规定,显然违宪。(39)蔡蕙芳教授则认为,想象竞合犯与加重结果犯虽然在以行为数罪名这一点上相同,但是在结构上仍有重大不同:在想象竞合的情形下,两项罪名同时出现只是偶然,而在结果加重犯的情形下,基本犯罪与加重结果罪名间则是必然关联。(40)许玉秀教授从想象竞合犯的不足入手,认为结果加重犯相较于想象竞合犯,不会有过度评价而违反平等原则的问题,相反,想象竞合犯较之于结果加重犯而言,却有不完全评价(或者过低评价)的问题。(41)通说认为,结果加重犯与想象竞合犯确有不同,有必要作为独立的犯罪类型。在结果加重犯的基本行为中蕴涵着加重结果的危险,“具有一定倾向在经验上内含着发生加重结果的类型的、高度的危险性的故意犯,作为其倾向的现实化而造成了加重结果,就是结果加重犯的加重根据。”(42) 2.从“自陷禁区原则”到“规范保护目的” 鉴于结果加重犯的法定刑比较重,通说要求严格限制结果加重犯的范围。在因果关系方面,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的“直接关联性”。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不仅要满足条件因果关系,而且还要求加重结果必须是基本行为的“特有危险”或“固有的内在危险”的实现。以伤害致死罪为例,福利许明确主张,加重结果之产生必须来自故意的伤害结果中蕴涵的风险实现,或者故意实施的伤害结果具有足以产生死亡结果的倾向。雅科布斯(Jakobs)也认为,结果加重犯的加重根据是行为人对基本犯产生的危险的量的制御不能。(43)加重结果的产生必须来自行为人因实施基本犯罪行为所制造的风险,这就是所谓的“风险同一性”。如果加重结果之产生是来自与基本犯罪行为实施无关的风险,则不能构成结果加重犯。(44)由此可见,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是否具有直接关联性的判断,仍然主要是从事实层面或者说是从社会经验上进行的,这里并没有认识到“法律所指责的风险能够与禁止性规范的意义相适应”。(45) 与福利许、雅科布斯等学者不同,罗克辛则从结果加重犯的规范保护目的出发,认为“只有在从基本犯罪的典型危险中产生结果时,才适用这种行为构成,这是符合立法目的的。只有这种结果才能为结果加重犯罪的保护目的所包括”。(46)亦即,加重结果必须是罪刑规范所防范的结果才行。“结果加重犯由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罪刑规范阻止加重结果;如果某种结果既不为行为触犯的罪刑规范所阻止,也不为其他罪刑规范所阻止,那么,这种结果不应当被认定为加重结果。”(47)虽然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所具备的风险实现上的直接性,可以间接体现二者之间的保护目的关系。但是,这种“保护目的关系并不总是以始终不变的方式通过直接性来表示的,而只能从各种行为构成的分析中得到具体的结论。结果加重的影响范围必须‘对各种应当考虑的行为构成——以不同的评价’加以确定。”(48)这样,客观归责理论的“规范保护目的”标准逐渐取代了“直接关联性”标准,成为结果加重犯的主要判断标准。 (二)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与“立法目的原则” “立法目的原则”是指,在法律的解释和适用过程中,需要法律的目的作为指引。正如普铂所言,在具体案件审理中,法官为了明确法规范的含义通常需要对法规范做出一定的说明或补充。因为法规范本身并不是清楚单义的,法律适用者在证立这类的补充时,就只能上溯到规范的意义和目的。只不过,其所涉及的并不是任何一个人任何的目的与利益,而是涉及那些依法应被追求之目的,这些目的的实现对于特定社会中的人类生活而言,是正义的、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49) 1.“立法目的原则”的精神实质 “立法目的原则”首先体现了一种目的论解释的思想。“目的论”一词源于希腊语telos(目的)和logos(理性),即按照某种目的或结果来解释事物的学说。目的论解释是一种从某种目的出发解释世界万物的方法,它的存在源于人类对自身及其存在的时空、意义等终极关怀的偏好。在法律上,目的解释的兴起是从利益法学批评概念法学开始的。利益法学指出,“概念法学的决定性错误就是,判断法条不是根据它们的目的和功能,而只是它们在概念金字塔上的层级。”(50)概念法学过分强调逻辑和演绎,强调封闭的规范体系对于立法者权威的尊重。由此所形成的形式主义进路,就将政治、社会、道德等价值判断排除到体系之外,教义学就成为一种价值中立的学科。问题是,逻辑并不能为法教义学提供知识增量,因此,概念法学的做法容易引起法教义学疏远社会现实的后果。随着类型概念和规范的构成要件的发现,价值评价重新融入教义学中。想要借规范来规整特定生活领域的立法者,他通常受规整的企图、正义或合目的性考量的指引,它们最终又以评价为基础,要“理解”规范就必须发掘其中所包含的评价及该评价的作用范围。(51)在法律中,最主要的价值评价莫过于立法目的。如耶林所言,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事实上的动机。(52)因此,在理解法律条文的时候不可以忽视法律的目的设定。 其次,“立法目的原则”体现了“历史的法律解释”和“法官受制定法拘束”的观点。在刑法教义学上,历史的法律解释(主观解释)认为,解释法条需要从立法者的目的开始;目的论解释(客观解释)则认为,解释法条需要从法条本身的内容和功能去理解。主观解释严格遵循立法者的目的,体现了制定法对法官的约束,有利于实现法的权威和安定性。客观解释不以立法者的目的为终点,而是在立法者的目的随着时代变迁变得不合理时,继续根据法条的功能确定规范目的,有利于实现法的正确性和实质理性。“立法目的原则”原出于利益法学,利益法学的主要代表学者如耶林、海克等人,都主张规范的解释需从立法目的开始。耶林之前的法律人当然也意识到法律是用来实现某种目的与价值的手段,但那被认为只是立法者的任务,司法者则只要严格运用三段论逻辑,便能自动实现立法者所设定的目的。(53)例如,萨维尼起初就没有采用目的论解释,他认为立法者的目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立法者实际上规定在法条中的内容。后来,萨维尼却转变了态度,主张“在法律使用的表述不确定的情况下,应该像援引法律的特定目的(只要它是可以证明的)一样多地援引‘立法的内在关联’。如果不能证明特定目的,允许追溯到‘更普遍的理由’”。(54)现在,站在法官立场上、主张司法能动主义的客观解释稍占优势。但是,鉴于两种解释各有其优势和缺陷,折中论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亦即:“尝试将法律中所明确表述的历史上的立法者的意志——即使是提示性的(提示理论)——作为标准的意思内容而加以尊重和忠实,只要公正性上的迫切理由、社会关系的发展或时代精神,不将过去的价值判断视为过时。”(55) 2.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与“目的理性” 在刑法教义学中,规范的保护目的理论主要放在客观归责体系中探讨,但它显然不只是客观归责理论的附属品,而与一种“目的理性的刑法体系”相呼应。(56)众所周知,在刑法教义学上,刑法体系的建构经历了从古典到新古典、再从新古典到目的论、最后又从目的论到目的理性的过程。从哲学基础上看,这是一个从存在论到规范论的过程。古典犯罪论体系具有鲜明的存在论色彩,对法益、行为、责任等概念的理解都显示出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特点。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虽然也以物本逻辑为基础,但在罪责部分增加了许多价值因素。反对目的论刑法体系的学者以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为知识背景建立起目的理性刑法体系,其出发点在于,“刑法的体系性形成不是与本体的预先规定性(行为、因果关系、物本逻辑结构等等)相联系的,而只允许从刑法的目的设定性中引导出来的”。(57)即便是以物本逻辑为基础建构犯罪论体系的许乃曼,也坦承:“对于一般法学的体系思考而言,根据我的确信,这是一个无论如何再也无法隐瞒的进步,这种体系思考无法就这样局限于纯粹地说明自然的既存事物及其关系,也无法仅以此种讨论为起点;相反的是,由于这种思考与一种规范性的秩序(也就是与法秩序)有关,所以在形成概念的时候,必须从其目的(功能)出发。”(58) 从法哲学上看,刑法体系转型的过程也体现了法律思维的转变,即从“体系内的解决”到“体系外的解决”,在“体系外解决”问题上,又经历了从探求“事物本质”到追寻“规范目的”的过程。除了主张严格解释和封闭体系的概念法学之外,无论是利益法学还是评价法学,都主张对法律漏洞进行有限制的弥补。“事物本质”和“规范目的”都是法条之外的存在,它们对于法条漏洞的弥补非常重要。生活关系本身即提供了自身的标准和秩序,即便其发展程度不一,人们把此种事物内在的秩序称为事物本质。当找不到实证法规范,或实证法规范不完整或不明确时,有思考能力的法学家必须回到事物本质。(59)除非在现实状态之外寻找规范效力的基础,可以笼统地认为探求事物本质的思想体现了一种自然法的思维。物本逻辑的主张者认为,在法律不明确时“有必要返回‘存在’本身,从存在中导出秩序”,“它先于法而存在,法也无法改变它,因此,应该为立法者所重视”。(60)与存在论相反,规范论则认为价值无法从存在中导出,存在和价值是相互对立的,在法条不明确的时候只能求助于规范目的。因为规范是立法者制定的,从规范意旨出发划定归责范围可以满足立法者的要求,从更深层来看也反映了立法者背后全体公民的意志,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归责更为积极妥当。 三、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方法基础 (一)从“自然·物理”思维到“规范·政策”思维 作为客观归责理论的下位规则之一,规范保护目的对于结果犯的刑事归责具有重要指导功能。结果犯归责标准的发展体现了刑法思考方法的变迁。详言之,从单纯要求条件因果关系到相当因果关系(条件说+相当性判断),再到客观归责理论(条件说+相当性判断+规范判断),体现了从“自然·物理”思维到“社会·经验”思维再到“规范·政策”思维的过程。因果关系理论是只问有无“物理上因果关系”,而相当性因果关系理论,则是在确定了具有“物理上因果关系”后,进一步追问具有这个“物理上因果关系”是否具有“相当性”;在此同时,客观归责理论则是对一个具有“相当性”的“物理上因果关系”再进一步追问其是否具有“引起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性”。(61) 1.自然·物理思维 “以精确的自然科学为蓝本,根据因果性的和心理性的因素来建造”(62)的古典刑法体系,以条件说作为客观归责的全部标准,根据已成为常识的因果法则判定因果关系。因为在李斯特、贝林所处的时代,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突飞猛进,人们相信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反映在法学上,则正是实证主义占据统治地位,刑法教义学进行体系建设的黄金时期。为坚守来之不易的罪刑法定原则,学者主张客观、价值中立的构成要件,排斥一切主观和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例如,李斯特对“意志”的定义,就停留在心理学层面上。他指出:“表明意思活动特征并进而表明行为特征的‘意欲’,在这里仅意味着意志冲动(Willensimpuls)。可将其规定为心理学上的神经支配(Innervation),可将其理解为心理学上的‘确定其原因的意思过程’。”(63)在因果关系问题上,李斯特则将其定位在物理学的层面上。他认为,“因果关系涉及一个思维方式问题,借助这个思维方式我们将实际存在的情况联系在一起,而不对导致事件过程的力量作出任何评价。”(64)之所以不对物理学的因果关系进行评价,是因为在构成要件符合性这个阶段,“借助于因果关系范畴,我们只是为刑法研究寻找材料或对象。”(65) 2.社会·经验思维 相当因果关系说在条件说划定的因果关系范围基础上再进行相当性判断,通过引入社会经验性的价值判断淘汰那些偶然发生的、在刑法上不具有重要意义的条件。其所利用的价值判断标准,包括行为的可预见性、可控制性,损害结果发生的概率等等。虽然这些判断标准不是规范性的,却是价值性的,因而与追求价值中立的古典刑法截然有别。比如说,A未保持安全距离超车,被超车的B受到惊吓,突发心脏病而死。对此,条件说只问“未保持车距超车”和“死亡”间有无因果关系,相当说则还要问“未保持车距超车,引起被害人心脏病突发而死,一般人是否会觉得奇怪”。社会学思维源自刑法本来也是社会控制的工具之一,“对犯罪的科学的研究,一方面应从一般的法学理论和法哲学的角度进行,另一方面应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66)在刑法教义学中,社会学思维往往是在自然的事实界定基础上,根据社会控制的需要作出评价。例如,李斯特提出“实质违法性”,就是对具有形式违法性的行为进行再评价。具有实质违法性的行为,即“危害社会的行为”,其判断标准是是否侵害了被上升为“法益”的生活利益。实质违法性概念有利于在违法性阶段合理出罪。此前,形式违法性框架下的合法化事由是从成文法中找出来的,内容和功能都有限;实质违法性框架下的合法化事由则是从成文法之外找出来的,不仅内容丰富,同时具有更合理的出罪功能。 3.规范·政策思维 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已经证明,条件说对于归责是不够的,“与哲学层面或科学层面因果关系查明不同,法律层面查明因果关系不是要揭示物质世界的本质或其运行的某种基本的或经验的真相。法律层面因果关系查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公正的根据。据此,一个人可以对所发生的社会危害事实负责。”(67)不过,相当因果关系所借助的“非规范价值标准只可能在前实定法的意义上排除那些与‘刑法无关’的行为类型,而根本不是用来判定某个结果是否为某个行为的‘作品’(Werk)的合适工具。”(68)可见,相当性评价也不能穷尽归责的全部标准,在相当性之外还要对事实因果关系进行规范上的评价。规范评价切入归责问题始于梅茨格尔,他所提出的重要性理论区分了结果的造成与结果的客观归责。前者适用条件说,后者则“注重因果关系发生中的在刑法角度上的重要性,只认可因果经过范围内的构成要件相当性条件为构成责任成立,注意到规范的保护目的和各犯罪构成要件的特别性”。(69)重要性理论在理念上与罗克辛提出的客观归责理论如出一辙,只是后者更具系统性。客观归责理论“可以说是意图在体系性、政策性的指导观念之下,从各种案例类型中将具体的下位标准体系化,从目的理性的观点出发,并按照规范的、事实的观点来组织归责标准的方法论”。(70)不过,在不同的案件中,规范·政策思维发挥作用的成分侧重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在常规案件中可能规范判断的成分较大;而在疑难案件中则经常在规范判断的掩盖下,通过后果考察诉诸于刑事政策。正如托尼·奥诺尔所言,“在边缘案件中,法规目的说判断之标准,经常系基于诉讼经济、迅速、社会财富及允许损害赔偿之社会效果等因素考量之结果;亦即基于一般社会与经济政策,被害人之损害移转由加害人负担是否合理,为判断标准。”(71) (二)规范保护目的与“跨越李斯特鸿沟” 1.“跨越李斯特鸿沟”命题的提出 在《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一文中,罗克辛提出“跨越李斯特鸿沟”的命题。所谓“李斯特鸿沟”,是指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相互分离的二元结构,这种分离模式被认为可能引起判决结论的教义学方案与刑事政策方案的冲突。“从体系中得出的正确结论虽然是明确和稳定的,但是却无法保证合乎事实的结果。这些具有充分的明确性和稳定性的法律问题,却是在刑事政策上有所欠缺的。”(72)为了对教义学上概念性方案进行纠正,罗克辛认为有必要将刑事政策的价值选择融入到刑法体系中去。在融入渠道上,他借鉴了新康德主义学者里克特的做法,因为目的理性刑法体系也建立在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基础之上。里克特为价值的概念创造了进入精神科学方法论的入口,他证明了这个概念是精神科学认知论上的先验条件。(73)这一入口就是目的论的概念建构。相应地,“评价性目的”成为将刑事政策的价值选择融入刑法体系的“通道”。“当正确的体系性解决方案作为一种事先评价的结果表现出来时,体系性结论及其希望达到的事实上的正确性(Sachrichtigkeit)之间的一致性,从一开始就可以得到保障。”(74) “评价性目的”对刑法体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并非我们先阅读了法规,再了解了它的目的。相反,我们是先知道了目的,然后法规才变得可以理解”。(75)但是,恰恰在“评价性目的”的理解上,学界并没有一致的认识。如方泉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既可以理解为“实心的”,即以新康德主义价值学说为基础,在犯罪论体系中以刑法特有的判准——刑法(罚)的目的——将新康德派的文化价值具体化;又可以理解为“空心的”,即泛指一切以“刑法目的”为指引建立的、功能主义的犯罪论体系。(76)当然了,即使是前一种理解,也是将“评价性目的”交给具体的刑事政策制定,交给政治、立法者去决定。为了避免纳粹刑法再度出现,作为“评价性目的”内容的规范保护目的、刑罚目的以及法益等等,都要从人权保障和社会控制的平衡上着手,做到真正的“目的理性”,而不是形式的“目的理性”,实质的“工具理性”。 2.规范的“一般目的”与“特殊目的” 就客观归责而言,损害结果发生在规范保护目的的保护范围内,造成或引起该损害结果的行为才能取得规范上的重要性,违反此种规范的行为人也将因为其行为具备了构成要件该当性而受到形式违法的评价,这显然也是一种目的论的思考方式。在此,还可将规范保护目的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规范保护目的就是规范在整体上的目的,每一部法律都有自己作为整体的目标设定;狭义的规范保护目的则是指具体规范的保护目的,所防范的是特种类型的法益损害。以往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主要是从宏观上研究规范目的,即着眼于刑法目的或刑罚目的。但是,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意义主要不是从广义上而是从狭义上获得的,即从具体的条文分析保护目的所导出的注意义务指向何种个体,何种时空条件下可以对他这样要求,以及可以要求到何种限度等。在这个层面上研究规范保护目的,实际上就在教义学中将它的功能具体化了。换言之,虽然广义的规范保护目的和分则各章规定的保护目的都有限制和帮助理解具体规范保护目的的功能,但是,相比于具体法条的特殊目的,刑法在整体上的目的和各章规定的保护目的只是法条的一般目的,功能有限。实际上,在法条不明确的地方,应该先按照有利于实现本条的“特殊目的”的方向来解释,如果这样做还不能明确法条的真实含义,再依据有利于本条的“一般目的”的方向来解释,才能合理确定法条的保护范围。 3.规范保护目的与不法的确定 不法和罪责受不同的“评价性目的”指导。罗克辛指出,“人们应当把‘罪责’这个范畴扩展到‘责任’的一种理论上去,并且,这应当是从有待施加的刑罚的目的——而不是像不法那样,从刑法的目的中——派生出来的。”(77)可见,规范保护目的主要服务于不法的确定,刑罚目的则主要服务于罪责的确定;或者说,规范保护目的主要服务于可罚性的判断,而刑罚目的则主要服务于需罚性的判断。正如德根纳所言:“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捍卫者被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这样做的必要性何在?换言之,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思想究竟产生了哪些成果?答案是:它将呈现一个方法性的原理,按照这种方法性原理……不法将被准确表达。”(78)结果犯的不法既包括结果不法,也包括行为不法。结果不法是指实际受损的法益属于行为规范的保护对象,而行为不法则是指行为模式和注意义务属于行为规范所禁止的类型。根据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通常表述,即“结果发生在规范保护范围之外的,应排除归责”,容易将规范保护目的与结果不法直接连在一起,而忽视其对行为不法的确定功能。实际上,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又分为注意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和构成要件保护目的理论,前者属于风险制造阶层,后者属于风险实现阶层。注意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主要服务于行为不法的确定,即通过抽象性的结果是否发生在注意规范保护目的之内,判断行为是否具有危险性,属于事前判断;而构成要件保护目的则主要服务于结果不法的确定,即实际发生的损害结果是否发生在构成要件保护目的之内,判断实际损害结果在刑法规范上的重要性,属于事后判断。 4.规范保护目的与利益衡量 目的往往与利益紧密相连,规范保护目的也不例外。劳东燕教授曾指出,由于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深受事前的与风险分配相关的规范的影响,而规范已经变得日益复杂,并对刑法归责的认定产生重要的影响。(79)规范通过规定或轻或重、或宽或窄的注意义务,在行为人与被害人中间分配风险,而这自然与他们的利益紧密相关。判断结果是否发生在规范保护目的之内,其实就是判断利益的归属。美国学者Wex S.Malone一针见血地指出,因果关系是一种理论上的概念,具有政策决定的特性,法官经常运用因果关系,以达成其欲促成的社会政策。(80)刑法领域也是如此。在客观归责理论体系中,与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紧密相连的“容许风险理论”将风险划分为容许风险和法不容许的风险,就与行为人的利益和自由边界有关。行为人制造容许风险所产生的结果,不会将他陷入刑事责任之中。相反,行为人制造法不容许的风险,即便没有产生实际的法益损害结果,行为人也要负未遂之刑责。 需要指出的是,规范保护目的与法益并不相同。首先,霍尼希(Honig)的“方法论的法益”或“目的论的法益”,将规范保护目的与法益相等同,不仅使法益丧失了体系批判功能,也使得规范保护目的自身的功能长期遮掩在法益理论之下,因此是两败俱伤。其次,法益和规范保护目的显然是密切联系的。行为规范所保护的根本目的实际上就是法益,因此,可以认为二者是形式与实质的关系。再次,目的理性刑法体系将刑法目的设定为“辅助性法益保护”,因此,并非所有的法益都由刑法保护。不同的部门法既可能保护不同种的法益,也可能保护同一种法益。但是由于规范保护目的不同,在法益的保护范围和力度等方面可能都有区别。最后,正如沃勒(Wohler)、施特拉滕韦特(Stratenwerth)等学者所指出的,“法益是一种独立的东西——不同于保护目的,而是存在于保护目的背后的‘东西’。”(81)安德鲁·冯·赫尔希进而指出,处于利益背后的这种资源要被定义为一种手段或者一种能力,这种手段或者能力在通常情况下对于人类的生活质量来说,理应具有某种价值。(82)可见,法益比较倾向于物质性和实体性,而规范保护目的更倾向于价值性和相对性,二者共同规定了法益侵害结果的可罚性。 四、结语 在德国,对于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探索远未到终点。即便是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所反对的也无非是将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作为归责的“万能公式”。对于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意义,主流意见是持肯定态度的。而在我国,对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探索才刚刚开始。随着刑法知识转型的起步,刑法教义学已经走到兼收并蓄、百家争鸣的时代。在这种形势下,讨论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基础的意义就更为重大。规范保护目的是与“目的理性”相通的概念,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也是客观归责理论最重要的下位规则,而后者又是体现目的理性刑法体系的关键。如此看来,规范保护目的正是理解目的理性刑法体系的一枚钥匙。在它的帮助下,不仅有利于解决有关的实际问题,在此基础上还有利于理解目的理性刑法体系的构成原理、目标追求以及前途走向。 在因果关系问题上,我国传统的主流观点——必然和偶然因果关系说——也没有停留在事实因果关系层面,而是也认识到需要一定的标准对事实因果关系再次限缩。虽然该学说在表述上采取了“必然”和“偶然”这种具有哲学色彩的语词,但在实际判断上则与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相仿,也采用了社会经验型的判断标准。只是这种学说不如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成熟,由于缺乏具体的下位规则,很多判断难免流于主观化。即便如此,该学说中仍然蕴涵着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萌芽。例如,有学者指出,“在研究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时,需要抽出来进行研究的因果环节,不但要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一定量的规定性,并不是漫无边际,随心所欲的。所谓质的规定性,就是在由一系列因果环节所组成的因果链条上,取哪些环节才具有刑法上的意义。根据刑法学研究的对象和目的,这些环节只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和危害社会的结果。所谓量的规定性,就是在一系列危害社会与危害结果中取出几个环节才不失去刑法上的意义,这要根据刑法学研究的目的,从具体案件出发,视行为的危害程度而定。”(83)根据上述论者的观点,传统学说在众多因果链条中抽取“具有刑法意义的”因果关系,也必须考虑刑法学研究的目的。笔者认为,虽然刑法学研究的目的并不等同于规范保护目的,但在其中难免也体现了刑事政策和刑法目的。由此可见,目的论思维贯穿了因果关系判断的全过程,不仅在质的规定性上,而且在量的规定性上,致力于因果关系的“筛选”。这些论者还认为,探讨因果关系问题的目的是为了筛选出“具有刑法意义的”因果关系,这种意识无疑也突破了必然与偶然因果关系的巢臼。因为众所周知,德国学者梅茨格尔首倡“重要性理论”,其核心思想就是提出了“具有刑法上意义的因果关系”观念。客观归责理论无非是借助众多下位规则,将重要性理论予以系统化了。 在本土化知识基础上,引入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但在功能塑造上,仍然需要把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作为限制结果归责的一种标准,将其作为出罪而非入罪的一种根据。因为,规范保护目的理论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规范保护“目的”本身的界定,只有将其作为出罪根据,方可避免对人权的侵犯可能。这样,规范保护目的作为一个堵截因素,在第一层次上将发生在注意规范保护目的之外的结果排除到归责范围之外,对那些发生在注意规范保护目的之内的结果才认为具有法益侵害或威胁存在;在第二层次上,如果这些损害结果或威胁发生在构成要件保护目的之外,则证明侵害或威胁没有达到需要刑法管辖的层次,也不予归责。通过上述双层次的规范保护目的审查,使得最终受到惩罚的行为实际上都是其他法律无法管辖,而必须由刑法予以规制的部分,这也是符合刑法“辅助性法益保护”的机能设定的。 注释: ①[德]约翰内斯·韦塞尔斯著:《德国刑法总论》,李昌珂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页。 ②陈聪富著:《因果关系与损害赔偿》,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37-138页。 ③[德]克劳斯·罗克辛著:《德国最高法院判例选辑·刑法总论》,何庆仁、蔡桂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④[德]Wilhelm Degener,“Die Lehre vom Schutzzweck der Norm”und die steafgesetzlichen Erfolgsdeliket,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Baden-Baden 2001,p.18. ⑤[德]魏德士著:《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⑥倪培兴:“论作为归责理论的犯罪构成理论”,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周光权:“结果回避义务研究:兼论过失犯的客观归责问题”,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6期;李波:“刑法中注意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3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页;陈璇:“论过失犯中注意义务的规范保护目的”,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1期;劳东燕:“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与结果加重犯的界定”,载陈泽宪主编:《刑事法前沿》(第4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页;刘艳红:“注意规范保护目的与交通过失犯的成立”,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4期;梁根林:“‘醉驾’入刑后的定罪困扰与省思”,载《法学》2013年第3期。 ⑦拉伦茨的学生王泽鉴指出:“法规目的说是由Rabel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50年代再经Caemmerer加以阐述发挥,而成为德国通说”。参见王泽鉴著:《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Caemmerer的学生曾世雄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曾世雄著:《损害赔偿原理》,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9年第3版,第79页。德国学者乌韦·布劳洛克也认为,Rabel提出了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他所引用的Rabel的著作出版年份是1936年。参见[德]乌韦·布劳洛克著:《法规保护目的理论》,姚志明译,载萧文生主编:《中正大学法学集刊》(第3期),台湾中正大学法律学系2000年版,第241页以下。笔者原来也持这种观点。参见李波:“刑法中注意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3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页。 ⑧吴玉梅著:《德国刑法中的客观归责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⑨张亚军著:《刑法中的客观归属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版,第62页。 ⑩[德]Wilhelm Degener,“Die Lehre vom Schutzzweck der Norm”und die steafgesetzlichen Erfolgsdeliket,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Baden-Baden 2001,p.11. (11)[1874]9,L.R.(Exch.)125.See Henderson et al.,TORTS,supra note 260,at 357-358; Grady,TORTS,supra note 200,at 727-728.转引自陈聪富著:《因果关系与损害赔偿》,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44页。 (12)韩强著:《法律因果关系理论研究——以学说史为素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页。 (13)[美]H.L.A.哈特、托尼·奥诺尔著:《法律中的因果关系》,张绍谦、孙战国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14)同注(13),第5页。 (15)[德]Wilhelm Degener,“Die Lehre vom Schutzzweck der Norm”und die steafgesetzlichen Erfolgsdeliket,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Baden-Baden 2001,p.15. (16)吴玉梅著:《德国刑法中的客观归责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以下。 (17)[日]山中敬一著:《刑法中的客观归属论》,成文堂1997年版,第311页。转引自张亚军著:《刑法中的客观归属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18)[德]Wilhelm Degener,“Die Lehre vom Schutzzweck der Norm”und die steafgesetzlichen Erfolgsdeliket,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Baden-Baden 2001,p.16. (19)[德] Wilhelm Degener,“Die Lehre vom Schutzzweck der Norm”und die steafgesetzlichen Erfolgsdeliket,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Baden-Baden 2001,p.16. (20)[德]许乃曼:“关于客观归责”,载许玉秀、陈志辉主编:《不移不惑献身法与正义:许乃曼教授刑事法论文选辑》,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558页。 (21)[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德]托马斯·魏根特著:《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22)同注(21),第349页。 (23)同注(19),p.18。 (24)[德]许乃曼:“关于客观归责”,载许玉秀、陈志辉主编:《不移不惑献身法与正义:许乃曼教授刑事法论文选辑》,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558页。 (25)[德]Wilhelm Degener,“Die Lehre vom Schutzzweck der Norm”und die steafgesetzlichen Erfolgsdeliket,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Baden-Baden 2001,p.22. (26)叶金强:“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展开”,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 (27)张姿倩:“注意规范保护目的在刑法客观归责理论上的功用——重新检验德国文献上的实例”,台湾政治大学法律学研究所2005年硕士论文,第37页。 (28)同注(25),p.31。 (29)陈聪富著:《因果关系与损害赔偿》,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74页。 (30)同注(24)。 (31)同注(25),p.52。 (32)[德]乌韦·布劳洛克:“法规保护目的理论”,姚志明译,载萧文生主编:《中正大学法学集刊》(第3期),台湾中正大学法律学系2000年版,第244页。 (33)例如,Jakobs、Schünemann、Samson、Liefrung、Wellels、Cramer、Frisch、Lenckner等学者都认为注意规范保护目的仅适用于典型案件中。参见张姿倩:“注意规范保护目的在刑法客观归责理论上的功用——重新检验德国文献上的实例”,台湾政治大学法律学研究所2005年硕士论文,第63页。 (34)[德]Wilhelm Degener,“Die Lehre vom Schutzzweck der Norm”und die steafgesetzlichen Erfolgsdeliket,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Baden-Baden 2001,p.14. (35)顾祝轩著:《制造“拉伦茨神话”——德国法学方法论史》,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 (36)[日]丸山雅夫著:《结果的加重犯论》,成文堂1990年版,第182-183页。转引自林怡秋:“加重结果犯中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间关系之研究”,台湾成功大学法律学研究所2008年硕士论文,第4页。 (37)同注(36)。 (38)卢宇蓉著:《加重结果犯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 (39)黄荣坚著:《刑法问题与利益思考》,元照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504页。 (40)蔡蕙芳:“德国法上结果加重犯归责理论之研究——以伤害致死罪为例”,载《刑事法学新趋势——Lothar Philipps七秩祝寿论文集》,神州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96页。 (41)许玉秀著:《主观与客观之间——主观理论与客观归责》,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25页。 (42)张明楷:“严格限制结果加重犯的范围与刑罚”,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 (43)同注(42)。 (44)同注(40),第285页。 (45)[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德]托马斯·魏根特著:《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48页。 (46)[德]克劳斯·罗克辛著:《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 (47)张明楷:“严格限制结果加重犯的范围与刑罚”,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 (48)[德]克劳斯·罗克辛著:《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 (49)[德]英格博格·普铂著:《法学思维小学堂:法律人的6堂思维训练课》,蔡圣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5-66页。 (50)张青波著:《理性实践法律——当代德国的法之适用理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51)[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4页。 (52)Jhering Der Zweck im Recht(1893),S.435ff.转引自吴从周著:《概念法学、利益法学与价值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页下注[293]。 (53)劳东燕:“刑法中目的解释的方法论反思”,载《政法论坛》2014年第3期。 (54)张青波著:《理性实践法律——当代德国的法之适用理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55)[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德]托马斯·魏根特著:《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 (56)劳东燕:“规范保护目的与结果加重犯的界定”,载陈泽宪著:《刑事法前沿》(第4卷),第134页。 (57)[德]克劳斯·罗克辛著:《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58)[德]许乃曼:“区分不法与罪责的功能”,载许玉秀、陈志辉主编:《不移不惑献身法与正义:许乃曼刑事法论文选辑》,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417页。 (59)[德]莱茵荷德·齐佩利乌斯著:《法哲学》,金振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页。 (60)蔡桂生:“韦尔策尔犯罪阶层体系研究”,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1期。 (61)郑逸哲著:《构成要件理论与构成要件适用》,作者自版2004年版,第285页。 (62)[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犯罪原理的发展与现代趋势”,载梁根林主编:《犯罪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63)[德]弗兰茨·冯·李斯特著:《德国刑法教科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 (64)同注(63),第185页。 (65)同注(63),第185页。 (66)同注(63),第6页。 (67)[英]威廉姆·威尔逊著:《刑法理论的核心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5页。 (68)熊琦:“论客观归责理论的规范维度——兼析本体论、价值论因果关联与客观归责的本质区别”,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58页。 (69)[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著:《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 (70)[日]铃木茂嗣著:《刑法总论(犯罪论)》,成文堂2001年版,第87页。 (71)Honore,supra note 6,at 62.转引自陈聪富著:《因果关系与损害赔偿》,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48页。 (72)[德]克劳斯·罗克辛著:《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73)张青波著:《理性实践法律——当代德国的法之适用理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页。 (74)[德]克劳斯·罗克辛著:《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75)Stanley Fish,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280(1980).转引自[美]丹尼斯·M.帕特森著:《法律与真理》,陈锐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页。 (76)方泉著:《犯罪论体系的演变——自“科学技术世纪”至“风险技术社会”的一种叙述和解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5页。 (77)[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犯罪原理的发展与现代趋势”,载梁根林主编:《犯罪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78)[德]Wilhelm Degener,“Die Lehre vom Schutzzweck der Norm”und die steafgesetzlichen Erfolgsdeliket,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Baden-Baden 2001,p.52. (79)劳东燕:“风险分配与刑法归责:因果关系理论的反思”,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6期。 (80)Malone,Ruminations on Cause-in-Fact,9 Stan.L.Rev.60-62(1956).转引自陈聪富著:《因果关系与损害赔偿》,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9页。 (81)[英]安德鲁·冯·赫尔希:“法益概念与‘损害原则’”,樊文译,载《刑事法评论》(第2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 (82)同注(81)。 (83)李光灿、张文、龚明礼著:《刑法因果关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