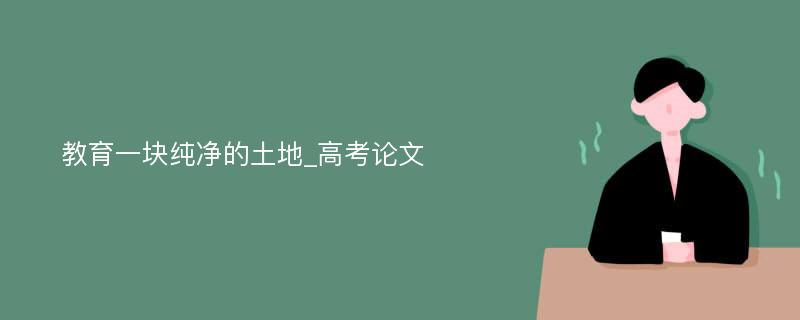
还教育一片净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净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最令人关注的教育问题,是在当年的高考中出现了罕见的大面积舞弊;同时,高校收费继续大幅度上涨,引起强烈社会反响。这一切,使中国教育大发展过程中的教育公平问题突显。如果不能保证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公平、公正,就将损害没有权势的大多数人的教育权利,这不仅会损害教育自身的发展,并且会严重地危及社会公正。
高考舞弊大曝光
2000年被媒体曝光的高考舞弊案,主要有三起:湖南嘉禾县一中考点发生大面积的、严重的高考舞弊事件,考场秩序混乱,答卷大面积雷同,其涉及面之广、影响之坏,是湖南省恢复高考以来所未有的;广东电白县的高考舞弊案,系电讯器材店出售或出租BP机用以作弊,将答案传到考生的BP机上,有33个考生的答案雷同;湖南省隆回一中选送的14名保送生,13名系作假,其中两人分别是隆回一中正副校长的儿子,另外11名均为县及县属单位的干部子弟。
综合各方面的消息,类似湖南嘉禾一中、广东电白县、湖南隆回一中的高考舞弊案并非个别和孤立的事件,被媒体揭露的只是冰山一角。它引起举国上下的震惊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尽管有种种弊病,但正由于它最重要、最本质的优点——公平和公正,而被人们普遍接受。“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提供了社会公正的基本防线以及人才标准的公信度。这一被视为最公正的高考制度正在受到腐败风气的严重侵袭。一方面,教育规模的扩大、考生和高校招生数的逐年增加的确加大了考试组织、监考的难度;同时,不少地方由于片面追求升学率,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考试舞弊已经呈现出“集团化、规模化”特征。它对当前的教育公正和教育改革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高校收费大幅提高激起强烈反响
虽然随着高等学校扩招,更多的青年走进大学,然而,持续增长的高校收费,又一次敲响了教育公平的警钟。据统计,全国各大学对2000年大学本科生学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提涨,由1999年大致3000元左右,涨到4500元的水平,平均涨幅在1500元左右。2000年北京地区高校学费上调了20%。按照一般院校与重点院校以及专业的差别,学费标准分为6个档次,其高限从4200~6000元不等。上海高校的学费则从5000~6500元不等。广东省普通高校文史类专业学费平均上调26%,理工类平均上调43%,进入“211工程”的高校,学费可上浮20%。2000年,许多师范院校对师范生也开始收缴学费。华东师范大学2000年将师范生与非师范生的收费标准拉平,都是5000元左右。这样的涨价幅度是否有理论和政策的依据,是否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国情?一些调查显示,大多数家长表示对这一价格难以接受。据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的数据,京津广的1000位学生家长中,38%的被调查者可以接受的大学收费标准为每年学费2000元以下,46%的被调查者可以接受的大学收费标准为2001~4000元。也就是说,高达84%的学生家长无法接受2000年4500元的大学学费水平。调查表明,家庭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的被调查者中有25%的人可以接受每年4001~6000元的大学学费,这个收入水平在城市中属中等,而在小城镇和农村中,恐怕已经是相当高的水平了。
广州社情民意的调查显示,对于2000年各地高校普遍每年4000元以上的学费标准,近七成的家长认为偏高,另有三成家长认为一般。表示“完全能承担得了”的家长则不到一成,其余的家长大多只能“勉强承受得了”,极少家长表示“承受不了”。调查表明,家长可以接受的大学的年收费标准平均为3400元。
以2000年学费的最低标准4200元计,按照1999年我国人均收入统计数据,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5854元)的72%,农村居民人均收入(2210元)的190%。如果加上住宿费、书本费、伙食费等实际支出,则将超过一个城镇居民或两个农村居民一年的总收入。如此昂贵的学费,不仅让贫困家庭的子女对上大学望而生畏,即使对普通的家庭而言,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与此同时,不少高校“扩招”低于录取分数线的“议价”学生,每个学生收取数万元费用;许多学校学生转系或转专业也明码标价,收取数万元。这种不规范的行为无疑助长了教育腐败。
教育制度和政策的不公
除了高考舞弊事件之外,人们对现行的高考制度和教育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和探讨,以追求更为公平、公正的教育制度。
倾斜的高考录取线。我国现行的统一高考制度,具备了形式上的公平——分数面前的人人平等。但由于实际录取学生采取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各省市区的录取定额并不是按照考生数量平均分布的,而是按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优先照顾城市考生的准则,因此出现同一份考卷,各地录取分数线的极大差异,从而加剧了原本已经存在的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公平等。例如,1999年湖北、湖南的重点理科院校的录取分数线比北京分别高106分和77分,重点文科录取线比北京分别高78分和90分。
保送生制度和三好生、特长生问题。湖南隆回一中保送生舞弊案被揭露,引发了关于保送生、特长生制度的反思。原本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或优异生开辟的升学通道,在当前严重的社会腐败的环境中,正在成为一些有权势者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的捷径。尽管对保送生增加了综合能力测试,似乎并未能有效地遏制这一势头。许多学者、家长、学生呼吁教育部取消保送生制度,黑龙江省已首先取消了这一制度。类似的是目前实行的对省市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文体特长生等高考加分的制度。事实上,保送生的舞弊通常是在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方面作假。教育腐败的现实与实行这些办法以因材施教、防止“一考定终身”,以及扩大学校招生自主权的初衷产生严重的背离。它使我们认识到当前中国道德失范的严重性,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教育改革的特殊性和必要的限制。
小学升初中电脑派位制度。为了推进素质教育,减轻升学竞争和学生负担,我国大中城市均已取消小学升初中的入学考试,重点中学不再举办初中。北京、上海等城市实行电脑派位(抽签),确定学生进入哪所中学。这一政策的初衷无疑是好的,希望以此逐渐减小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的差距,保持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平。但目前的现实,由于学校之间客观存在的差距依然很大,为了享受更好的教育,以避免被随意“派”到差校的命运,在取消了分数的竞争后,出现了家长之间权力、社会背景和金钱的竞争。那些质量稍好的学校,以共建、赞助等名义收取高额费用。据家长透露,北京市一类学校的赞助费5万元,二类学校为4万元,个别3万元;“公办民助”学校收费更高。这意味着上一所好中学,费用甚至超过上大学。当我们严格地限制民办学校发展,强调“不能以营利为目的”时,那些享有优越资源的公立学校却几乎公开地大举营利,成为创收的高手,办学行为发生明显扭曲。对公平、公正的教育理想而言,这都是令人感到悲哀的。
假文凭现象日趋严重
当前教育和学术领域比较突出的现象,一是日渐猖獗的弄虚作假,二是官本位对教育、学术领域的腐蚀、渗透。假文凭泛滥,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有报道称,目前在职人员中持假文凭的有五六十万之多。在今年西安市报名参加民办教师班招生考试的345名教师中,就发现有138人的大专毕业证书是伪造的,假文凭比例高达40%!除了公开买卖的假文凭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各种舞弊行为。例如,不久前,蒲富恪等5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4位博士生导师联名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揭发,广州师范学院(现已与广州大学合并,以下简称广师)物理系凝聚态物理硕士点2000年毕业生陈某的毕业论文严重剽窃他人成果,并且在事先有人指出的情况下,仍然被强行通过。他们对此深表痛心和愤慨,呼吁有关部门尽快查处这种违反科学道德的劣迹,维护我国学位制度的尊严。
当前比较严重的,是权与学、钱与学越来越紧密的结合与交换,所谓“仕而优则学”,“富而优则学”。目前,无需进行入学考试的研究生课程班“遍地开花”,仅北京大学一家,2000年8~9月开学的课程班就有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心理系)、区域经济学专业(城市与环境学系)、企业管理专业(经济学院)等十多个。同时,北大还设有近20个短期的研究生课程研修班。此外,北京大学还在重庆、太原、广州等地设有研究生课程班。这种研究生班造成“公款上学”的空前繁荣,有的单位甚至规定,处级干部可以上研究生课程班,一般干部只能“专升本”。许多单位还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如提供学习时间、报销全部或部分学费等。已有专家对这种培训方式提出质疑,认为仅仅凭较短时间的面授,而没有付出比全日制研究生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时间和精力,就认为已达到研究生同等学历,是不太可能的。这种方式就好像是对不合格产品的精美包装,实际上也是一种舞弊或变相舞弊行为。一些官员几乎不需要怎么上学,请人AI写作论文而获得学位。与已经成为社会公害的假文凭泛滥相比,这种真文凭中的虚假成分更不易辨识,比街头小贩兜售的假文凭的危害更大。它势必导致文凭和学历贬值、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准降低,教风学分的溃散,教育的公信度下降,从而不仅损害教育和学术,并且危及社会的健康发展。
在2000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王守昌委员痛陈学术腐败的种种表现:无论博士、硕士还是博士后点的建点或导师的遴选,评估尚未开始,背后的非学术活动便早已半公开地展开,或登门馈送,或美其名曰请专家讲学,往往不惜花费;有职有权者可以用公款出书,从而获奖、评职称、当博导,甚至获得各种荣誉称号;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卖”作品、论文的情况,以供评职称、学位用。由于权力可以随意跨越、干预学术活动,有权者就有学术地位、有经费、有成果,势必导致大家都往‘官场’上挤,导致我国的学术水平大滑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