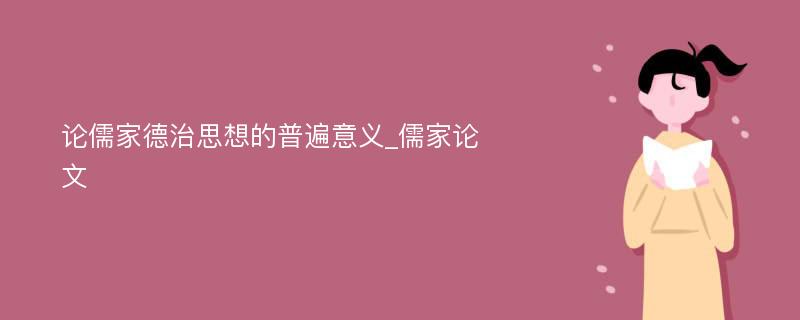
略论儒家德治思想的普世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德治论文,意义论文,思想论文,普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治思想是儒家留给我们的一份优秀文化遗产。它凝聚着先人从治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的管理经验和政治智慧,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认真研究德治思想的合理内核,结合当今时代的精神需求加以发展,对于当今社会的政治实践乃至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人们常常把“德治”与“法治”联称并举,其实,“德治”观念要比“法治”观念久远得多。“法治”是有了阶级、有了国家之后出现的,并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渐形成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德治”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有人之初,追溯到阶级、国家出现之前。在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原始社会里,部落或氏族的首领的德行乃是群体凝聚力的核心。他以自己高尚的德行影响、感召群众,管理群体的公共事务。首领本人必须是道德的楷模,否则他便没有资格担当首领。我们从远古的传说中,可以很容易找到首领德治实践的例证。神农尝百草的献身精神,尧主动让位给舜、舜主动让位给禹的禅让精神,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感人之举,都是首领德治实践的生动体现。他们或许没有明确地提出德治主张,然而在他们的不言之教中无疑体现出德治精神。因此,儒家在阐发“以德治国”思想的时候,把尧、舜、禹描绘为“圣王”,视为躬行德治的楷模。由此来看,德治实践由来已久。正是在德治实践的基础上,才逐渐产生出德治观念、德治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德治”可以说是纵贯古今的普遍观念,它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同步的。
据一些著名学者的研究,早在西周初年,就已出现德治思想的萌芽。据侯外庐先生考察,在周天子的王号中就包含着道德的意义(如文王之“文”)。郭沫若先生也指出,“德”在西周是一个新字,是周人的新思想。他在《青铜器时代·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中指出,这种“敬德”的思想在周初的几篇文章中就像同一个母题的和奏曲一样,翻来覆去地重复着。这的确是周人所独有的思想。周人是在推翻商纣王的暴政后建立新王朝的。他们总结商纣覆灭的历史教训,提出“以德配天”说。《周书》写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人在传统的天命观中添加了新内容:上天保佑君主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看君主是否有高尚的德性。基于这种新观念,周人又提出“敬天保民”说。“敬天”就是君主以自己的德性感动上天,以获得上天的保佑;“保民”就是君主以自己的德性赢得民意,确保统治的有效性。周人以“德”论证周取代商的合理性,寻求长治久安的道德依据,在中国政治文化史上首开“以德治国”的先河。不过,周人的德治观念还是比较笼统的,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德治思想的萌芽不仅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史上可以找到,在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中也可以找到。例如,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让哲学家做王”的主张中,就包含着德治的意思。亚里士多德强调,人自身的善是伦理学和政治学共同的研究对象。他说:“政治学让其余的科学为自己服务。它还立法规定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它自身的目的含蕴着其他科学的目的。所以,人自身的善也就是政治科学的目的。一种善即或对于个人和对于城邦来说,都是同一的,然而获得和保持城邦的善显然更为重要,更为完满。一个人获得善值得嘉奖,一个城邦获得善却更加荣耀。”[1]他把伦理学与政治学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包含着德治的意思。基督教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后,政权与教权分开,“归还凯撒的东西给凯撒,归还上帝的东西给上帝”。从表面上看,宗教既不管现世的事,也不管现世的问题,而事实上仍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即便在当今时代,法治也不是西方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的惟一手段,宗教的教化功能仍然是法治所无法代替的。政府的首脑们十分清楚这一点,他们也千方百计地利用宗教维护自己的统治。对于这种情形,贺麟在《基督教与政治》一文中以事实为依据作了以下充分的说明:
裨斯麦说,“基督教是普鲁士的坚实基础,没有建筑在别的基础上的国家,可以永久存在。”至于德国旧教的牧师,当其就职时,必须作下列的宣誓:“我誓以至诚服从并效忠于普鲁士国王。我将努力养成人民忠爱祖国,服从法律,尊敬国王的忱悃。凡于公共治安有害的结社,我绝不参加,凡有危害国家的密谋,我若有所知,必首先报告国王。”德皇阅兵演说曾有这样的话:“大家须仅记日耳曼人是上帝的选民。我,德国的皇帝,是直接承受上帝的精神。我是上帝的降衷。我是上帝的宝剑,上帝的武器,上帝的战将。凡不服从、不信仰而怯懦的人,必受灾殃与死亡的惩罚”。(注:参见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141页。)
由于受到宗教与政治分开原则的限制,尽管西方基督教没有明确提出德治主张,但实际上却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德治的功能。可见,德治不仅是纵贯古今的普遍观念,同时也是横盖中外的普遍观念。
二
德治观念具有普世性,在中外的政治实践中都可以找到实行德治的例证,在中外政治思想中也可以找到德治思想的萌芽,然而,提出“以德治国”的系统理论,则是儒家独到的理论贡献。
在春秋时期,孔子通过反思周人的政治文化传统,明确地提出德治理论。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执政者必须具有高尚的品德,才算称职;对于民众来说,称职的执政者有如夜空中的北斗星。民众如同众多的星星一样围绕着北斗星,衷心地拥戴着执政者:这才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局面。孔子特别重视执政者的道德素质,认为道德素质与行政效率之间有直接的关系,紧紧地把伦理与政治结合在一起。孔子对德治和法治加以比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理,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如果仅仅采用行政手段和惩罚手段治理民众,只能受民众避免犯罪,但不能培养他们的廉耻之心;德治比法治高出一筹,只有实行德治,以礼教化民众,才能帮助民众养成廉耻之心,使他们发自内心地服膺执政者。在这里,孔子并没有把德治与法治对立起来,没有否定法治、片面突显德治的意思,只是如实地指出法治的局限,并把德治看成弥补法治局限性不可或缺的手段。
孔子的德治学说有两个理论支点,一个是“仁”,另一个是“礼”。“仁”是德治理论在观念层面的支撑,表明德治的可能性,从人性角度说明德治可能的前提。孔子认为,“仁”乃是一种普遍的德性,“仁远乎?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尽管孔子尚未明确地提出性善论,但实际上已预设“仁是人性中固有的”的前提。由于执政者具有仁德,所以他们才可能选择德治;由于民众具有仁德,所以他们才可能接受德治;因为双方都具有仁德,德治才可能得以实施:“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子张》)“礼”是德治理论在制度层面的支撑,表示实施德治的途径。礼治是商周政治文化的主流,人们以礼为准则,确定自己的社会等级身份,明确自己的社会待遇,规定交往方式、礼仪制度,协调人际关系,维持社会秩序。可是,到周王朝的末年,礼治已流于形式,礼变成了礼仪条文的总汇,变成了一套死板僵化的规定。孔子对这种情况十分不满,提出严厉的批评。他质问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论语·阳货》)当然不是。那么礼的深刻内涵是什么呢?在孔子看来,就是“仁”。他把仁理解为礼的实质,把复礼看成行仁的手段,得出的结论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子路》)“天下归仁”,也就是实现了“以德治国”。就这样,孔子突破了传统礼治的形式主义的局限,赋予礼以仁德的内容,把礼治改造为德治。德治通过礼治得以实施,并没有另外的途径。德治的制度化就是礼治。在孔子以后,儒家对德治与礼治一般不再加以区分,当做同等程度的观念来使用。
尽管在孔子的仁学中包含着人性善的意思,但毕竟明确地提出性善论;孟子在战国中期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提出人性善作为德治内在的理论根据。同孔子一样,孟子也主张从道德教化入手解决治理国家、统一天下等政治问题,贯彻伦理政治合一的思想路线。他采用王道与霸道两相比较的方法论述他的仁政主张;霸道的特点是“以力服人”,而王道的特点是“以德服人”。两种不同的政治策略会产生不同的统治效果:“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急功近利的霸道虽然可以一时奏效,可是不能长久,因为这样做违反人性;只有采取王道,实行德治仁政,才能贯彻“以人为本”的人性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护,并且实现长治久安。
孟子把德治仁政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他在说明仁政的可行性时指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孟子·公孙丑下》)“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善心、良心。“不忍人之心”不仅先王有,而且每个人都有,这就自然引出关于普遍人性的探讨。孟子得出的结论是:人性本善。人生来就具有向善的能力,他称之为“良能”;生来就具有道德意识,他称之为“良知”。“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学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良知良能是万善之源,由此而形成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等四端;由四端而形成仁、义、礼、智等四个基本的道德观念。他强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他从人性论方面为儒家德治主张找到了内在的根据,确立了儒家基本的价值取向。
孟子认为,人性善正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这里强调的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而不是“人异于禽兽者”。“人异于禽兽者”属于现象层面的差异,是很容易发现的;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属于本质层面的差异,就不那么容易发现了。孟子认为,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有求善的意识,而禽兽没有。正是因为人性善,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但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事实上并非如此。造成人格差别的原因在于每个人保留善性的程度不一样,有“去之”与“存之”之别。基此,孟子强调心性修养的必要性和对“庶民”进行德治教化的必要性,帮助他们寻求已经失掉的善性,“求其放心”。孟子一方面运用性善论说明德治仁政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又用性善论说明了实施德治仁政的必要性。
孟子立足于仁学,过分强调王道而排斥霸道,对儒家德治理论的阐发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缺乏制度化的设计,难免有“迂远而阔于事情”之嫌。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在战国末期弥补了孟子的不足,进一步发展孔子的礼学思想,协调礼法关系和王霸关系,提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主张,使儒家的德治主张在政治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
孔子已经对周礼作了损益,荀子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反思和理解礼乐文化,试图揭示它的起源。他分析说,人的气力不如牛大,奔跑不如马快,但人为什么能够驾驭牛马呢?其原因就在于人能够结成社会群体。人之所以能够结成社会群体,是因为人类创造了一套用来协调人与人相互关系的礼义制度。“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正是因为人类创造了礼义制度,所以才取得了“最为天下贵”的地位。荀子指出,礼义的作用在于“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即协调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他给“礼”下的定义是:“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贵贱皆有称也。”(《荀子·富国》)荀子剔除传统礼治观念中世卿世禄的陈腐内容,把“礼”界定为君臣父子各守其位的封建等级制度。他强调,每个人的社会身分不是一成不变的,“虽王公大夫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把荀子的这一主张变成了现实。从荀子对礼义的新解释中反映出,他已把礼义视为组织社会群体必不可少的准则。经过这样的解释,孔子提出的“约之以礼”的命题获得丰富而具体的内涵。
荀子对儒家德治理论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重新解释礼法关系或王霸关系,使之不至于流于空疏,而获得可操作性的现实品格。在荀子看来,礼既然是一套等级制度,那么,便与同是等级制度的法互不冲突。他认为礼与法不是互不相容的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礼者,法制大分也,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礼作为道德规范,其本身也具有强制性的约束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礼与法没有原则区别,礼就是广义的法,甚至可以称为法的总纲。孔子已把伦理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荀子进一步把伦理与法治紧密结合在一起。经过荀子的解释,礼与法、王与霸具有了相通性,不再是孟子眼中的那种对立关系。荀子强调,礼与法、王与霸都是维系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强制性手段。他否定了孟子尊王贱霸的观点,主张王霸杂用、礼法双行。“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荀子·强国》)荀子作为儒学大师,当然不会把礼法并列起来、等量齐观,而是以王道为“粹”,以霸道为“驳”,以王道为主,以霸道为辅。他的这一主张实际上为封建帝王采纳。汉宣帝直言不讳地宣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用之。”(《汉书·元帝纪》)经过荀子阐发,儒家的德治主张终于从理想层面落实到现实层面,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影响。
经过孔子和孟子的努力,到荀子这里,儒家的德治理论框架基本上已经成形了。后来的儒家对它进一步加以补充论证,使之更加完善。《中庸》和《易传》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入手,试图把德治提到哲学的高度,借以强化德治的理论基础,提高德治的权威性。《易传》提出“天人合德”的理论,《中庸》提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仁之道也”的理论。直到宋明理学,才比较圆满地完成了这一理论任务,理学家或以“天理”、或以“本心”论证德治的普遍有效性,形成儒家的“道德形上学”,用以支撑儒家的德治理论。
三
儒家德治思想作为古代的理论成果,不可能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它的合理性,否认它的普世意义和现实意义。儒家的德治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相信人性中具有美好的一面,要求相信他人、尊重他人,承认人与人之间有相互沟通的共同基础,主张通过人格自我提升的途径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社会习俗,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完善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承认儒家德治思想具有普世意义和现实意义,并不意味着可以把它直接运用于当今的政治实践。对于当今时代来说,儒家的德治思想只是一种文化资源,我们应当根据现实社会的需要,对它加以改铸发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政治文化。
第一,儒家所说的“德”,固然包含有“普遍德性”的意思,但主要还是指封建主义的道德观念。封建主义的道德观念维护等级制度,维护强者的利益,损害弱者的利益,片面地强调强者的权利,片面地强调弱者的义务,宣扬什么“天下无不是的君父”,“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这样的道德观念,显然不能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以德治国”中的“德”。我们所讲的“以德治国”中的“德”,应该是新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它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倡导奉献精神和对社会、对祖国负责的精神,其中包含着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而及人之老,幼吾幼而及人之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道热肠,又比儒家的道德观念深刻得多。儒家所讲的“德”虽然包含着“公德”的意思,但侧重于“私德”,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们所讲的“以德治国”中的“德”,主要不是指“独善其身”的私德,而是指公德。“以德治国”中的“德”,包括公民道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等内容,比儒家的道德观念意义广泛得多。
第二,儒家所说的“治”,包含着关心国事民瘼的民本意识,但毕竟以民众为统治对象,通常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说话的。在当今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以德治国”中的“治”,不可能再是这种意思,而是治理国家、综合整治、维持社会秩序、形成良好社会风尚、建设精神文明、提高综合国力、发展先进文化等意思的总和。我们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讲“以德治国”的,应当以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宗旨。我们一方面应当发扬儒家关心国事民瘼、尊重民意的入世精神,另一方面应当突破民本主义的局限,把“民本”提升到社会主义民主的高度。
第三,儒家所说的德治,着眼于社会稳定,而不着眼于社会的发展,具有过度的非功利主义倾向,无意也无法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儒家在处理义利关系的时候,往往强调义而忽视利,宣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样的义利观已不能适应现时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有必要实行现代转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家需要稳定,更需要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提高综合国力应当是“以德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提倡“以德治国”,应当突破儒家思想的局限,处理好义与利的辩证关系,不能再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当然,这里所说的“利”是指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个人的私利。不过,也应当看到,尽管儒家比较重视道德价值,不甚看重功利价值,但并不意味着儒学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毫无用武之地。市场经济也是诚信经济,儒家的诚信观念经过现代转换以后,可以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有助于经济秩序的合理化。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人们往往会感受到意义的失落、价值失衡的困惑;极端的功利主义诉求会造成人们道德水准的滑坡。对此,儒学将发挥制衡作用,有助于精神文明的建设。
第四,儒家所说的德治仅以人性善为前提,其理论基础比较薄弱。人性中固然有善的一面,否认这一点将导致非道德主义;然而把人性完全归结为善,理论上也难以站得住脚。从人性善出发,儒家对理想人格只提出道德方面的要求,而没有提出能力、才干等方面的要求。例如,王阳明以金子喻做人,认为金子的珍贵体现在成色上,而不是分量上;人的价值体现在道德品格上,而不是才干上。儒家这样诠释理想人格,无疑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我们今天所说的“以德治国”,显然不能再局限于人性善的理念,而应当以全人类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为理论依据。现时代所要求的理想人格,应当是德才兼备的人才。他既具有高尚的人品,也具有报效祖国、服务社会的本领。
第五,儒家所说的“德治”,把伦理与法治紧紧地结合在一起,限制了法制独立发展的空间,以至于影响法制的健全。由于儒家常常把伦理准则同法律条文混在一起,结果既影响了伦理准则的感召力,又影响了法律条文的明晰性。这大概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法制不够健全的文化原因之一。我们实施“以德治国”,决不能沿袭儒家的老路,必须把划清伦理准则与法律条文之间的界限,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贯彻“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辩证统一的原则。在当今社会的政治生活中,“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并不矛盾,完全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兼容,并行不悖。法治有制度化的优势,但只能使人消极地不为焉,却不能激励人积极地为善。德治弥补了法治的不足。德治虽然不能像法治那样制度化,却有法治所不具备的感召力,能在健全人格、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如果离开德治片面地强调法治,将导致极端的惩罚主义;如果离开法治片面地强调德治,将流为不切实际的说教。“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有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二者相互配合,共同促成人类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
标签:儒家论文; 孔子论文; 国学论文; 荀子论文; 以德治国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孟子·尽心上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孟子论文; 人性论文; 法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