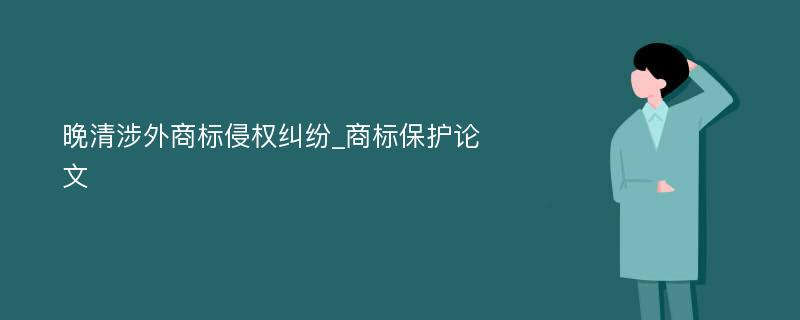
晚清时期的涉外商标侵权纠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纠纷论文,时期论文,商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随着西方学者所谓的“条约制度”(treaty system)的逐步形成,中国大量的经济贸易主权渐为外人所攘夺。与之同时,大批洋商亦携各色洋货而入各通商大埠。甲午战争之后,洋商又恃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在华设厂制造之特权,在华外商企业由是日增,加之当时晚清政府也推行了自开商埠、鼓励工商、允许商民自行设厂等方面的经济措举,沿海各埠商务渐盛,而华人和洋商在经济和贸易领域的纠纷无疑也变得益加繁杂。迨至清末,涉外商标纠纷问题逐渐成为华洋交涉的焦点之一。关于此问题,以往学界着墨极少,下面笔者拟就此略陈管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
所谓商标,“谓营业者表彰系自己制造商品及自己贩卖商品所用之文字、图书或记号也”。[1] (P160)作为知识产权载体的现代意义上之商标,其观念传入中国约在清末,但在传统工商业领域,中国很早就有保护商标意识的萌芽。按早期中国商业惯例,商标亦即牌号,所谓冒牌纠葛与现代意义上之商标侵权略似。最迟在明末清初时期,中国许多行业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在生产和销售商品过程中,为使自己的产品与其他行号示以区别,即出现使用牌号的现象,而彼此间混冒牌号之事也时有发生。对于冒牌纠纷,有时地方官府偶也发布禁止冒牌的禁令或通告,或对冒牌者提讯究办。顺治元年,苏松府就牙商沈青臣“勾同别商,射利假冒布商三阳号”,及“虎牙恣伪乱真等事”,勒石为碑,发布晓谕:“为照众商各立号记”,“取信远商,历年已久,向有定例,不容混冒”,对于“觊觎字号,串同客贾,复行假冒”者,“许即指名报官府,以凭立拿究解抚院,立法施行,决不轻贷”。[2] (P84-85)但工商业者之间的冒牌纠纷,主要由当时传统工商行会组织如商帮、同业公会等进行理处。如上海绮藻堂布业公所,在1825年就开始对本行业牌号进行登记,严禁已在公所登记的牌号有重复名称出现,并对销售他人冒牌土布者,进行严厉惩处。该公所还制定《牌律》,其“冒牌罚则”规定:“同号如有顶冒他号已经注册之同路同货牌号,经本所查明或被本牌呈报确有实据者,将冒牌之货,尽数充公。如有掮客经手,必须追查姓名,由公所通告各号,以后永远不许该掮客再掮布货。”[3] (P49)由此可见,保护商标问题并非西商东渐才开始有之,但传统中国政府对于商标的管理和保护,在制度层面基本上处于一种缺失状态。
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很早就开始在商品上使用各种商标,并通过国家立法加以保护。逊清之际,由于西力东侵,洋货充斥中国市场,许多舶来洋货和中国本土制造的洋货上均附有商标。而中国民间销售、仿造洋货及创办民族企业的活动也日盛一日,故尔华洋商人之间也就滋生出无数商标纠葛。概而言之,当时的涉外商标纠纷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因所生产商品使用商标相似而产生的纠纷。如:1909年左右,日商钟渊纺织公司以华商又新纺织厂冒用其蓝鱼商标为由,禀请日本领事函致上海道,再转至上海商务总会,要求予以饬禁。后上海商务总会询据又新公司,查复谓钟渊商标与又新商标系两式,一系二鱼,一系三鱼,鱼数不同,何谓冒牌,表示坚不允改。但最后在各方压力之下又新纺织厂仍不得不将其商标酌加改换。[4]
(二)摹造他人商标使用于同种产品加以贩卖所肇之纠纷。如:1909年2月,英商祥茂洋行主投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禀控华商宏源洋货店私卖伪牌肥皂,公廨谳员张柄枢将宏源执事人张云山等拘获到案,会同西官开堂研讯,祥茂主人声称,本行出售肥皂分为头二等,均有定价,今宏源将次等货私印头等牌号混售于人,于生意有碍,请即严惩,中西官会商之下,判宏源洋货店罚洋钱200元充公。[5]
(三)因转售他人冒牌商品而误侵他人商标权产生的纠纷。如:1882年6月,有上海顺全隆洋行洋人,到法租界会审公堂呈控盈泰丰洋货店冒牌销售其制造的双斗鸡牌自来火,虽然该华人店主则声称伪货从日本三菱公司买来,共五箱,每箱14两,当时只为贪图便宜,并不知其为冒牌之货,但经中西官会审,仍判将货主交保候审,余货一箱缴案。[6]
(四)将自制产品装入他人有注册商标之容器而导致的商标纠纷。如:1909年7月,有华商协源祥号邵而康以新油装入老牌火油箱,冒充美孚牌号,冒戤美商美孚商标,被美孚洋行所控,并由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传案讯究,后判邵具结悔过,声明以后不准再冒,且罚洋一百元充作同仁医院经费。[7]
总之,当时的涉外商标侵权纠纷主要发生在生产和销售两个领域。就生产领域来看,商标纠纷多是因产品商标有所相似所致。清末随着国内民族企业的纷纷兴办,一些华商逐渐在自制产品上贴附商标,而晚清对商标的注册管理及判定冒牌等自始至终在律令依据上存在诸多制度上的纰漏,一旦洋商觉得自己的产品在中国市场受到华商产品的竞争,或因债务等其他原因与华商发生纠葛,即多有藉商标问题禀控华商者,1907年10月间,曾有上海英美烟公司,不满华商三星纸烟公司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蓄意兼并之,所谋不售,竟对三星纸烟公司提起注册商标遭侵害之诉讼。[8] (P235-237)
就销售领域来看,发生商标纠纷的商品多集中在火油、火柴、肥皂、香烟等日用小商品上。启讼原因虽不乏部分不法华商,以劣质假冒之商品,影戤洋商商标,冒牌射利。如1909年8月,上海英租界之中国勒威药房,收买瓶上印孖梨烟林文字样之花露水空瓶,实以自制之花露水冒牌混售,以致被上海老晋隆洋行经理人麦格赖所禀控。[7] 但因华商昧于商标常识,贪图便宜收售伪货,以致误冒洋商商标,甚或被洋商以商标为由无端欺凌之事也不胜枚举。1903年9月间,福州美国面粉公司代理人裕昌洋行向华商公记号购买面粉,当公记前往催收货款时,裕昌洋行竟禀控公记所售卖熊标洋粉,属假冒商标,要求酌议示罚。公记诘问洋商为何初买时并不声称假冒商标,迨至收取货款时竟藉商标肇讼,但在福防同知的谕令下,仍被迫缴洋300元转送美领事,“情愿吃亏省事,以免缠讼受累”。[9] (P14480-14481)
二
晚清时期,涉外商标纠纷中以华商侵冒洋商牌号者居多。而华洋商标纠纷的大量涌现,又滋生出复杂多绪的华洋诉讼和华洋交涉问题。
清季由于列强在中国据有领事裁判权,如有洋人起诉华人,除上海租界等少数几地由会审公堂受理外,其他则依“被告国籍主义”,由领事把禀状呈由中国地方官厅理处。到清末司法改良,随着各地审判厅的建立,亦有洋人迳赴司法衙门具诉者。不论其诉讼程序如何,在关乎商标之诉讼中,多以洋商胜诉而告结,地方官府和司法衙门,在商标诉讼和交涉中,或因无章可循,或因惧于交涉,多责令被控华商将争议商标酌订,或对冒牌华商处之罚款,没收货物等惩戒。1908年,华商何瑞霖开创芝兰香牙粉公司,并曾在天津商务总会和工艺总局挂号注册在案。1909年4月,芝兰香粉公司被大阪日商呈控假冒商标,后来将该公司商标与该日商两家货样“呈堂比较,并不相同,绝非假冒”。但受理案件之中方官员仍“谕以商标略似,饬商更改以避嫌疑”,“后又纯用野蛮手段,屡次更改呈验,终未洽意”,最后“断令将一切装璜花样删去,仅准商用带字白签书明中国造白粉字样”。[10] (P1785)中国官府在处理纠纷时抑已尊人之举如是无忌,使得华商一旦与华洋因商标涉讼,大多受亏累累,莫可申辩。
不仅如此,地方官厅为防范于未然,还屡屡准领事或洋商所请,在华民中发布禁止冒用洋商商标的示谕,1907年4月,九江德化县“据上海英美烟公司禀请”,“查得九江一埠近有渔利之徒,明用该公司纸皮包面,暗则假烟冒充”,“即照该商所禀,刷告示千张发交该商自行张贴而杜弊混”,“自示之后,倘有仍前不知自爱,希图渔利冒牌混售,一经查觉或被函告,定即拘案究办,决不姑宽。”[11] (P663)1907年北华捷报也报道,上海道瑞澂即应英国总领事的要求发布禁止中国人侵犯英国商标的公告,而且瑞道台“满足英国总领事的愿望已不是第一次了”。[11] (P665)更有甚者,洋货甫经运抵中国口岸,西商即托请本国领事,吁请中国地方官府备案,严禁华商仿冒。1900年9月,驻沪日本领事小田切君万寿之助,应日商所请,“解送本国村井纸烟公司所制新式纸烟一箱到道,请余晋珊观察存案,俟有人假冒此牌者,即请查究”。[12] 华官此举,当时朝野多有訾议,宣统元年十一月,盛宣怀致书度支部尚书载泽等,“查英美烟公司历年要求领事照会各地方官出示保护,并查拿冒牌,我国官吏有求必应”,“不知商标注册尚未开办,彼此保护牌号仅有空约,洋商既未缴注册之费,我国断无保护其商标之义。何况普通形似,一经出示,致使华商所造之烟稍有纸料色泽一处普通与伊同,即指名控罚,受害之家不少”。[13] (P198-220)不惟纸烟如是,其他商品,无端被洋商以侵冒商标而被诬控者也不一而足。
为了有利于洋货在中国倾销并长期有效地占领中国市场,在频频出现的商标纠纷中,列强也逐渐注意到利用商标专用权推广其在华商务的重要性。他们不满足于仅和地方官府交涉,希望通过与清政府签订条约,以条约的形式把国外商品的商标权予以固定下来。1902年,英国在《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始创此议,该约第7款规定:“英国本有保护华商贸易牌号,以防英国人民违犯,迹近假冒之弊,中国现亦应允保护英商贸易牌号,以防中国人民违犯。”[14] (P103)这是晚清政府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互相保护并防止假冒贸易牌号的条文。此后1903年的《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及1904年11月《中葡通商条约》亦有大抵如是的规定。此款一开,对中国殊为不利,当时一些清方大吏对此深有洞鉴,中美商约签订之后,张之洞就在致参与签约的吕海寰、盛宣怀等函中指出:第10款保护专利牌号一条,“其首起数语,美国允许中国人将其创制之物在美国领取专利牌照云云。此时中国人岂有能创制新机在美国设厂者,不过藉此饵我允保护美人专利耳,真愚我也。所谓保护者,即禁我仿效之谓也,……此款一经允许,各国无不援照,此约一经批准之后,各国洋人纷纷赴南北洋挂号,我不能拒,则不独中国将来不能仿效新机新法,永远不能振兴制造,中国受害实非浅鲜。”[15] (P32)而晚清政府对中美商约中保护商标的条款也心存不安,曾嘱吕海寰、盛宣怀等与美使商改,无奈美使坚不允删,且提出中国保护美国商标详指以下三类:“一系指立约后有在美国已准保护独用之商标,一系指立约后有在中国行用之商标皆可请注册保护,一系指立约后新拟商标请先注册保护然后行用者”。[16] (P4)无论各界反应如何,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被迫仓促上马,着手商标法规的制定。
三
商标是工商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20世纪初,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商品生产尚为薄弱,而此时方面清政府的商标立法和商标管理在制度安排上尽付阙如,另一方面华商的商标利用和商标保护之观念也极为淡薄。由于洋商对保护商标的不断要求和有约各国驻华使领的屡次催促,晚清政府被迫启动商标立法程序,而经由华洋商人之间商标侵权诉讼和纠纷处理的刺激,部分华商开始认识到商标在生产和销售产品过程中的重要性,商标意识亦得以逐步培塑和增强。
(一)近代商标法律制度的建立。前已述及,清政府在与列强所签订的一系列商约中始创保护商标的条文,而中国近代商标法规的制定,主要是源于这些不平等条约,其初衷出于保护洋商产品的商标专用权;当然,由于清末涉外商标纠纷日益增多,预防和解决华洋商标纠纷也对商标法规的制定提出了制度需求,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晚清商标立法活动似乎带有鲜明的工具性色彩。
1904年初,清政府商部向朝廷上奏,要求从速颁布商标法规:“中国自开埠通商垂数十年,而于商人牌号,向无保护章程。此商牌号有为彼商冒者,真货牌号有为伪货攙杂者,流弊滋多,遂不免隐受亏损……保护商标一事,自应参考东西各国成例,明定章程,俾资遵守”,以后“无论华洋商人,既经照照章注册,自应一体保护,以示公允”。[17] (P19)
1904年4月,《商牌挂号章程》出台,此为中国商标史上起草的第一个商标法规。该章程由英人裴式楷拟定,但其内容偏护洋商歧视华商之意极为明显,故一出台马上引起国人强烈反对,“上海外贸商人向驻北京的英国大使提出申述,要求英国大使转总税务司进行修改”。[3] (P29)之后,商部又参照英国驻华大使代拟的条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代拟的草案及其他各个国家的商标法规等资料,又重新拟订《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并于1904年8月正式对外公布。该章程共28条,细目23条,明令“商部设立注册局一所,专办注册事务,津沪两关作为商标挂号分局以便挂号者就近呈请”,此外章程对商标注册的资格和程序、商标侵权的种类和惩戒措施等,也作了详尽备至的规定。[17] (P20-22)章程对外颁布之后,洋商呈请商标注册者颇为踊跃,仅至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就“陆续收到洋商呈请之商标计七百余件之多”。[18] 但当清政府将商标章程咨行有约各国时,不料除“日本公使略改数条,首先承认外,余国以窒碍多端,或驳或改都未承认”。[19] “英使照复外务部,仍有异词”,德使也“嘱旅沪德公商公所开会集议”,且照会外务部声称:“保护商标一节,所有通商各国,应视同一律。”并要求我国拟订章程时,“先应听取各洋商所陈述的意见,其他各国也相率提出同样要求。[20] (P5)清政府不得已遂于光绪三十二年、三十三年又对该章程两次加以酌改,但皆未洽意。及至民初,虽然也数次有过重新修改商标的活动,然因政局动荡,大多中缀未果。直到1923年5月,方在列强的再次敦促下颁布《商标法》44条及实施细则37条,并在农商部下设立商标局,此为真正付诸实施的我国第一部商标法。
(二)近代华商商标意识的培塑。由于商标问题与华商的生产和营业极为攸关,在华洋商标纠纷的产生和处理过程中,又逐渐使现代商标意识在部分华商中得以培塑,使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1903年8月,上海英美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发生一起涉外商标侵权纠纷案,原告为日商祥茂洋行,被告为华商徐某。徐设肥皂厂于沪,“时皂牌群推祥茂为巨擘,长江上下游岁销达数百万,徐命名祥芪,货亦不弱,而定价远逊。商贩逐十一之利,咸舍彼就此,祥茂大受刺激,控于公堂,指为象形影射”,会讯时“原告诘徐既为华人,不应用西文商标。徐谓祥茂既为洋商,亦不应于皂上刊印‘祥茂洋行’汉文之字。辩难移时,徐袖出《康熙字典》,检草部内芪字,谓此并非杜撰,华人用华文,有自由择定之权,初不知某字为冒、某字非冒。原告语塞,乃判祥茂败诉也。”[21] (P224-22)
1902年,天津商人张咀英筹资1万元设立松盛大麦啤酒厂,该厂曾经天津商务总会备案并报农工商部批准注册,然因当时商标局并未成立,以致不能如愿。1907年,美商永康洋行(德国酒厂“站人”牌啤酒在中国的包销商)向天津商务总会呈控松盛酒厂侵犯其“站人牌”商标权,请求“严加查禁”。张咀英据理申辩,两者“商标逐加比较,实非酷似,不同之处甚多,德法文不同,出产公司不同,牌号不同,国旗不同,美女人名不同,人手持物不同,颜色浓淡不同,制造及发售处不同,封皮及瓶又不同”。天津总商会也认为“既非酷似,即不足侵夺利权,无可科罚”,拒绝了德国人的请求。但后来天津地方审判厅恐酿交涉,判定张咀英将商标稍为酌改。不意永康洋行却不甘就此罢休,又在《大公报》上刊登告白,诋毁松盛酒厂,称“今有假站人牌啤酒出现,右手执杯,左手执瓶,与本号不同,饮之大碍卫生”等词。张咀英对永康洋行诋毁商誉、侵夺商利的行为,极为愤慨,要求商会从速立案,以维护松盛酒厂的商标权,并请其照会德领事“责令作速为收拾赔补”。[10] (P1794-1797)此案后来虽不了了之,但华商维护自身权益之商标意识亦可概见。
20世纪初年,伴随着涉外商标纠纷的大量出现,商标的重要性逐步为越来越多的华商所认识。一个明显的例子,当时的刊发的许多报纸中,突出自身商标,提醒消费者认真区分商品商标,严禁其他生产者伪冒牌号的商业广告触目皆是。此外,为寻求国家法律制度的保障,在清末华商中就有不少向津沪海关呈请注册商标者,民国时期,此风更盛,自1928年北洋政府开办商标局起,迄至1934年底,注册之商标“统计有24747件,内中国注册商标数计7778,占31.45%,外国注册商标数16969件,占68.75%,单计上海一隅,华商在该期间注册商标数字,计达5259件”。[20] (P10-11)
四
综上所述,晚清时期的涉外商标纠纷问题,是在中国外交失败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华洋交涉的一个历史断面。透视这些纠纷的产生与解决,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晚清时期的涉外商标侵权纠纷,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当时中国政府的商标立法和商标保护在制度层面的缺失和民间商贸系统商标观念之淡漠,但在深层次却是当时西方商人冀图藉商标问题压迫中国民族企业和垄断中国市场的一种表征。2.华洋商标纠纷的产生与解决,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早期的商标立法活动,并对近代中国民间确立商标法制观念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