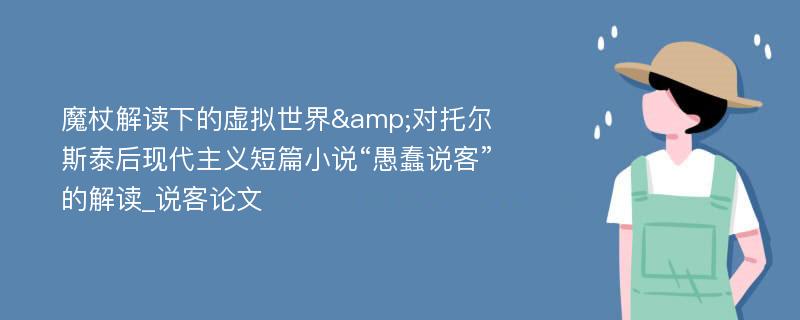
“童话魔棒”演绎下的虚拟世界——托尔斯塔雅后现代主义短篇小说《痴愚说客》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说客论文,后现代主义论文,短篇小说论文,斯塔论文,托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托尔斯塔雅的短篇小说充满了各种美妙的或不美妙的幻想与童话,有评论家把她的短篇小说比作“一根能将生活变成童话的魔棒”。(注:Βайлъ П.,Генис А.Городок в табакереке,“Звезда”,1990,No.8,c148,转摘自Нина ЕФимома(США),Мотив игры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Л.Петрушевской и Т.Татьяной,“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сер.9,филология 1998 No3,c60.)用童话式的虚拟世界描摹本真的世界特征与人生图景,是这位特立独行的俄国后现代主义女作家理解与把握生活的一种不同寻常的美学感知方式。
《痴愚说客》就是这样一篇十分典型的作品。它是托尔斯塔雅2001年短篇小说精品集《黑夜》中的一篇,被文学史家和评论家视作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美学纲领”性文本。(注:Н.Л.Лейдерман и М.Н.Липовецкий,《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в трех книгах,3-якнига,УРСС,М.2001,с.43.)在这篇小说中读者看不到具有完整叙事特征的可以理解的现实世界,推动叙事发展的也不是情节的有序进展,而是一个虚拟人物——“痴愚说客”费林“说痴”性的片断性叙说,是他幻想出的一个又一个“童话”。托尔斯塔雅表达了一种与任何形式的现代人文主义相脱离的意图,依照一种心理学、地理学的方法,向我们展开着关于历史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叙说。
关于“痴愚说客”费林的“童话”
费林是贯穿小说全文的中心人物,是“童话世界”的制作者,是作家用戏仿的后现代笔法塑造的一个当代俄罗斯文化“圣愚”。(注:圣愚:俄罗斯东正教中的清教徒,专以痴癫形象示人,云游四方,批判不公,弘扬正义且具有预言功能。)“费林”一词在俄文中作“专门在夜间出没的、类似猫头鹰的猛禽”解。在小说中他专门在晚间邀请朋友来下榻之处做客,向他们叙说他所杜撰的“童话”故事。小说的原文标题——“法基尔”有两个意思:一是指无家可归、四处云游、清心寡欲、穷困潦倒的僧人;二是指教堂里以苦行示人,但精神坚毅且具有预言未来本领的圣徒。“痴愚说客”的费林寄人篱下,沉湎于幻想,执着痴愚于自己创造的“童话”,时又侃侃而谈,竭尽迷醉、蛊惑、警示他人之能事。
费林有着一个令人“赏心悦目”,却不无滑稽的长相:乌黑亮丽的“阿纳托利式的美目”,靡非斯特式的眼神,色泽银白的大胡子,如同刚刚嚼了块煤炭的有点发黑的嘴……。他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有着常人难能企及的“思维潜能”,他的心灵中有一座美丽而丰饶的“大花园”。他会营造一个温暖、光明、温馨的家庭氛围,让来到这里的客人感到亲切美好而留连忘返,他收藏着让人羡慕不已的古董,他会讲谁也不知道的美妙故事。在他的“童话”世界里,一切都是稀世珍宝,甚至连小狗也能开门、做饭、热汤,切好面包,放好刀叉,等候主人的到来。总之,他是一个“一抬手,一蹙眉就能将世界变得无法辨认的无所不能的先生”。
费林的言语、行动、思索和隐私常常会被世俗生活所鄙弃,所忽略。人们常常数落他和他家中的一切。他的功利而又势利的情人阿丽莎,一度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嘉丽雅,最后都对他彻底失望,弃他而去,但他却始终没有放弃善的努力,这种努力是发自内心的,全然没有高尚者们装腔作势的伪善表演。所以,在他的身上似乎崇高的追求与不无卑劣的苟且兼有,也许这正是抵抗异化的最好方式。费林并不与主流与世俗同谋,他对现实的阻斥、抗拒与遏制是有限的,对现实绝望之后的热情把他引向了另外的精神出路。
当他绘声绘色地讲述那些荒谬故事的时候,历史与现实的荒唐与丑陋会时有所现:将在商店买的肉馅充作罕见的美味是独特时代的社会性疾患——自欺欺人;强行追索秘密的食谱配方,点心师的精神分裂——极权政治的产物;种种来历不凡的荒唐珍藏,人们物质生活的窘迫,历史学家窘迫的生活与受到的精神压制——一个并不发达与民主的社会;5 百万宝石回归人民——人民当家作主的荒唐……但费林并非社会主流意识的异见者,更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斗士。作为一个标准的后现代主义叙事者,他不断地在用一种天马行空、游戏式的思维方式,借助充满假定性的想象,把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当作一个无穷尽的虚拟的文化系列,演绎着他的童话故事。费林解读世界的方式不是政治学的,也不是道德学的,而是心灵学的,人类学的。一切社会的矛盾冲突,政治歧见都变得很淡很淡了,重要的是能讲述出来以求得心灵的解脱与今人的价值重估。
关于费林“宫殿”的“童话”
费林所居住的“宫殿”是由费林和他的客人嘉丽雅等凡俗之人臆造的。那是一个十分浪漫而又宏伟的世界:浆洗过的洁白的桌布,明晃晃的灯火,暖融融的温度,特制的美味馅饼,英国的红茶,从天花板传出的优美动听的音乐,令人心醉的谈话,蓝色的帷幔,玻璃橱柜里的各种珍藏,墙上挂满的各式珠串,来自“天上的”魏式瓷器……“宫殿”矗立于“玫瑰山顶”,山被装点得奇异多彩——建筑式样不同,装饰风格各异,创作构思多样。
由这座美丽而富饶的“宫殿”衍生的现实既是人们的孩子,也是人们的玩具。他们玩的是一种心灵的轻松,他们从不为自己确定目标,也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这个幻想世界之所以很值得客人们把玩,因为这里毕竟温馨:有美味可尝,有香茗可品,有珍藏可赏,有迷人的音乐和醉人的故事可听,还有美人相伴……在繁忙的都市节奏压榨下的郁闷不堪的人群通过在这里聚合与聊天,可以远离现实,可以逃避混乱无序,享受安宁与悄然的惬意,从而求得一种心灵的释放。更难能可贵的是,由这种释放带来的心灵惬意能够一再重复——人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费林的邀请,在这里欢度心灵的节日。所有“俗人”都把这座宫殿当作理想的去处和可以完全放心的地方,与这个“宫殿”和它的“主人”费林相比,包括尤拉与嘉丽雅夫妇在内的所有客人永远都是愚钝的“阿乡”,谁也无法阻止他们向“宫殿”长久地跋涉。宫殿的意念尽管是虚幻的,但人们的努力却是真诚的。直面虚无的“宫殿”的主人费林总是极力把对现实的绝望和美妙的幻想推到极致,以此来提高理想之光的价值。
然而,费林的“宫殿”是柔软和脆弱的。“宫殿”式寓所其实不过是位于莫斯科胜利广场上的一栋普通的居民塔楼,费林也不是它的真正主人,那是他向一位极地考察人员租用的。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在嘉丽雅为代表的费林忠实的听众和好友们的心目中,费林美好的童话很快化作了“黑夜里的焰火,色彩斑斓却瞬间即逝的风儿,黑暗中火红玫瑰在我们头顶上空的歇斯底里的发作”,“那株结满金色果实的树已经枯萎”。随着宫殿童话的破灭,人们都离散而去。“我们的上帝已经死了,他的庙宇已经空无一人。永别了!”这是嘉丽雅,也是女作家对苏维埃神话模式彻底失败做出的深刻的感喟。众人向往、憧憬的这座“宫殿”是物质极大丰富的乌托邦王国,是个虚构的天堂,是20世纪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神话”的幻影。而与这种“童话”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饱经沧桑的历史学家的生活。老人马特维·马特维依奇如今依然家徒四壁,喝的是已经泡得没有味道的茶,吃的是自制的不得不加上糖的果酱,至今仍然穿着一条已经洗得发白的运动裤,留在他记忆中的是革命后强行的分地,大官僚,阴谋家,一个名叫库津的庸才对他的迫害。在作家看来,费林的“宫殿”世界与现实的凡俗世界是难能和谐的,或者说幻想世界和现实世界是根本无法沟通的,这就是当今世界的真实状态。兴许,通过费林的提醒,正在变得庸常的现实人也可以在这里享受幻想,重新在色彩迷乱的都市下做梦,即使那梦最终会醒,那也是“美妙”的。
小说结尾,在臆想的童话破灭之后(阿丽莎最终识破“宫殿”连同其中的一切都不是费林的),情人阿丽莎离费林而去,嘉丽雅也来找他“算账”。但费林似乎毫不在乎,对嘉丽雅的指责也毫不生气,依然像往常一样,听音乐、吃鳕鱼,甚至津津乐道地把鳕鱼当鲈鱼来吃,继续讲他的关于极地人员和歌德的“童话故事”。其实他自己并没有生活在“宫殿”的童话中。费林已经没有了听众,失去了朋友,尽管他的住房是借的,生活是拮据的,他仍然活得如鱼得水,为能给他人带来短暂的生命的美好而开心。形单影只的他坚守为别人制造“童话”的个性,坚持他的文化战略,以有限而不变的活法应对着无限而万变的生活。
关于俄罗斯文化的“童话”
小说由费林讲述的故事中充满了包括俄国与苏联时期在内的俄罗斯历史中大众文化的内容,比如,历史古玩的收藏,美味佳肴的食谱,甜点师的信教,苏维埃新政权建立初期人们的迁居海外,往艺术家住宅中安插无房的穷人,芭蕾舞演员的命名,“瓦西里·焦尔金”式的游击队员的功勋,苏维埃弹唱诗人弗拉索夫的说唱,被人们推崇备至的“特异功能”者……
由费林信口说出的荒唐故事显然无力承担政治与历史的重负,它们只不过是一些文化戏言。但咂摸下去,里面深藏着叙说者对俄罗斯经典文化蓄意的嘲弄,长期以来始终被人们视作极权统治的血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史实,可歌可泣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英雄壮举,苏维埃艺术家为了人民与艺术献出一切等等壮伟的业绩,严肃庄重的历史记述统统被消解了。在费林的一切都“付笑谈中”的展示与赏玩中似乎蕴蓄着一种内在朴实的道理:人类你死我活的生存状态其实不过是历史的一种叙说方式而已,对早已凝结成历史过去时的人类自身的黑暗,后人未必始终要给自己的心灵留下永远作痛的疮疤而耿耿于怀。
与此同时,费林讲述的历史“童话”故事还充分展示出文化等级性差异的可笑性:普希金之死与甜点师库兹马的狂饮导致诗人未能吃到所喜爱的甜点联系了起来,忠诚于祖国与人民的游击队员不仅能用手枪击落德国飞机,而且还因此获得了一套货真价实的英国瓷器,贫穷的农夫用古老的“真正的魏氏瓷器”作餐具端来了牛奶,“法力无边”的芭蕾舞女演员居然用一条训练有素的腿阻止了轮船启航,芭蕾舞大师由索巴金娜而科什金娜而梅思金娜的姓名的变更(由狗而猫而鼠的)演绎成了一种渐次屈尊的人生游戏,人们会像在苏联时期的商店里售货员对待顾客那样把追逐女性的人类文化的奥林波斯神——歌德臭骂一顿。这是把包括苏维埃文化在内的俄罗斯文化世俗化了,具有高度人格尊严与傲慢精神的文化精英们其实也都难逃庸常生活的卑俗,有着再日常不过的,与凡人毫无二致的好食、好色之性。
托尔斯塔雅所能让人悟出的经典文化,的确有着似曾相识的历史依托,包含着苏联社会令人心碎的梦魇和伤痛的悲歌,比如,社会革命党人,革命胜利后一切归苏维埃,游击队员,反法西斯战争,具有特异功能的人等。更为荒唐的是,小说以高度隐喻性的手法,讲述了尤拉、嘉丽雅夫妇策划的换房故事,他们与15家要求换房的家庭进行了联系,却最终以一户的反悔而功败垂成。“15户人家叫啊、吼啊,闹了个天翻地覆,连地球轴心都错了位,火山爆发岩浆奔涌,名为‘安娜’的飓风将一个年轻的、欠发达的国家刮走了,喜玛拉雅山变得更高了,马里亚纳沟谷更深了”。嘉丽雅一家“改换门庭”的这一叙说显然隐喻着苏联的解体与15个加盟共和国的独立。但所有这些绝不是有关社会历史的具体叙说,因为所有碎片式的记忆都没有任何的因果链接。
小说中提到的现象都是对20世纪苏联历史的涉及,但小说既无对历史史实的具体纠缠,也无特定时空的铺叙,这种超然的态度表明,作者是在对历史沉渣、时代污渍和罪恶因子的具体内涵剔除洗涤之后的思考。这样小说便避免了任何意义上的时代、社会分析,女作家不避讳俄罗斯人的苦难历程和崎岖命运,却既没打算揭露、批判或抗争,也无意进行道德重估;小说是有关存在、生命、历史的书,却不是耽于存在、生命、历史的终极思考。
就文学的文化传承而言,无论在普希金的还是托尔斯泰的创作中,无论在拉斯普京还是索尔仁尼琴的创作中,我们都很难发现有类似托尔斯塔雅小说的先例,无法找到后者与俄罗斯文学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我们又很难否认小说中俄罗斯文化的特性与气质。这是一种与历史文化相连,却未受经典文学传统熏染而又不乏创造精神的崭新的文学混合体。
关于都市文明与郊野文明的“童话”
小说《痴愚说客》的主体不是人,不是人的命运, 而是现代人的叙说与现代人的感受。如果说费林的动情叙说展开的是“客观的”虚拟世界,那末小说中女市民嘉丽雅的心灵感应便是对虚拟世界的主体感受。正是由于嘉丽雅的存在,费林的“虚拟妄说”才具有了广阔的精神版图的意义,才被附加了精神与情感沟通的内容。身居郊野的嘉丽雅对都市文明与郊野文明的思考使得小说成为一篇反映中心与边缘冲突的现代“童话”。作家在小说中并没有揭示现代都市文明的真相,她大概也没有想这么做。女作家只是通过嘉丽雅心目中两种不同文明的对立与碰撞,表达了她对现代两种不同文明的思考。
费林连同他的“童话世界”是嘉丽雅崇尚追随的目标。都市、中心始终在嘉丽雅的视野中,成为她梦牵魂绕的对象。而她身居其中的郊野如同“极地般黑暗”,“充满着野性,昭示着苦难”。离开都市走向郊野的漆黑、泥泞的道路是“世界尽头”原型的延伸。郊野“三流的生活”充满了屈辱与“戳心窝子”的事情。她在大雨与泥泞中艰难跋涉到大剧院看芭蕾舞的故事正是她企图走出蛮荒融进都市文明的一次徒劳的尝试。观看“天鹅湖”芭蕾舞演出与眼泪、屈辱相伴,舞台上的“小天鹅”最后化作了“黄脸的”“工会会员”,高雅失落,激情索然。与嘉丽雅为伍的“苦命的狼”更是小说中荒芜、野蛮的叙事点,忽远忽近出现在荒郊山林中的一个生命,它们始终蛰伏在嘉丽雅心中,是不断回到她现实意念中蛮荒的图腾。这是嘉丽雅演绎的人类生存图景的一个“童话”模式。嘉丽雅对远郊生活与大自然中蒙昧、野蛮的各种回忆,对都市文明与郊野文明的比较,是生活在中心与边缘的人们相互之间不可能理解的一个明证。
郊野是一种具有隐喻性的缩微景致,是远离中心文明的人类中不得意者的集聚地,是远离现代都市文明的生命存在方式。然而,与都市文明一样,郊野也是一种否泰并存,祸福相依的宿命。嘉丽雅渐渐意识到,都市文明不仅仅“活力四射”,同时还是一种浊世文明、日益物化的文明。费林的“童话”破灭了,自诩为国王、苏丹、魔术师的费林不过是个“会伪装,善于装腔作势”、自欺欺人的“可鄙的小矮子,穿上君王睡衣的小丑而已”;“绝顶美妙的尤物”阿丽莎也不过是个“长着小胡子”、“穿着菜绿色连衣裙”的俗物,她嫌弃费林没有自己的住房而离开了她;著名弹唱诗人在朋友聚会上的演唱也只是为了赚取一个卢布。嘉丽雅最终没能在费林身上和他的“宫殿”里找到她追求的美丽。而郊野不仅仅是“生活最后的脆弱地带”,是泥泞的“前寒武纪”,还是一个“空气出奇地清新……尤其是对孩子好,别墅都用不着”的地方。居住在那里的人有着都市人所没有的“诚实”,是她消除恐惧、摆脱紧张、远离现代世俗的一种方式,是心灵之家。小说结尾,“郊区边缘时空”的贫瘠与野性被诗意化了,衍生出一种富于韵律的宁静、温柔、敦厚的诗意化的美:“现在——该回家了,尽管路不近。未来——是新的冬天,新的希望,新的歌谣。是呀,我们讴歌乡郊,雨水,泛出灰白色的楼房,黑暗来临前漫长的黄昏。我们讴歌旷野,褐色的青草,小心翼翼的脚下那冰凉的粘土层,我们讴歌姗姗来迟的秋日的朝霞……”两种文明互为映衬,互为表里,互为补充,构成当代文明难以或缺的整体。
关于爱情的“童话”
小说中的爱情处理是相当低调黯淡的。作品中没有任何浪漫情爱的情节构置,当然也更没有深深的情爱悲怆,书中有的是后现代社会的爱情本质:功利与非浪漫。在后现代社会里,连人本身都是脆弱的,何况比人更脆弱的爱情。如果说,现代爱情童话带给人们的是爱情的理想画图,那末现代文明的后现代情爱模式是一副提供给现实中爱情男女的清醒剂。从这个意义上说,《痴愚说客》还是一本写给女人看的书。
费林喜欢的女人如同他叙说的故事、邀请的客人和收藏一样,奇特、罕见。她们或是杂技演员,或是白皙得耀眼,以至于客人不得不戴上墨镜以免造成“雪盲”。与费林相伴的阿丽莎,是个看起来魅力四射的年轻女子,这种魅力主要来自她与众女人的不同:从她的女人通常没有的小胡子,少见的鹰钩鼻子,到奇怪的腌渍黄瓜色的裙子。更要命的是,俗不可耐的阿丽莎尤其喜欢出风头。费林之所以容纳这样的女人不是为了爱,而是担心自己的灵魂在混乱无序的现实中变得形单影只,害怕对周围一切冷漠疏远后的孑然独立,于是渴求一个新奇独特、可爱可触的异姓。这是他惟一可以抓得住的一个美好的世界,是一个似乎可以拒绝污秽肮脏的方式。但是费林爱的方式是荒诞的,因此爱的努力也是徒劳的,最终他仍然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回归“孤独”。
嘉丽雅是一个很“土”的女人。她所生活的都市远郊,粗糙、肮脏、野蛮,那儿只有生活的庸常,那是一个磨损感情、消蚀浪漫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她与尤拉的家庭生活便成了一种负担,成了不知所终的期待,无法抵御的无边的空虚,甚至带上了发霉的味道。一边是风光无限,另一边是阴霾重重。陷入无望的她心生厌意,想换换环境,换换爱情。在费林的身上她看到了未构设过的爱情理想,在他的身上种下了种种浪漫的期望,费林是以一种幻象的形式出现在她的爱情憧憬中的。心智与情感结构还发育得不甚健全的嘉丽雅错把幻想当现实,她一度钟情的男人只是她自己幻想的一厢情愿的爱的投射。一旦看到了费林那座宫殿的虚妄,他言说的虚妄,思想的虚妄,行为的虚妄,她便懂得了自己的爱的迷误,似乎也就学会了理解她所处的这个世界,包括她的家庭与她自己。于是她看到了自己和尤拉要“比他诚实一千倍”,又从骨子里想回家,因为爱情走到最后怎么说起来都是老婆老公孩子,柴米油盐,虽然细微琐碎,却也实在具体,让人心里踏实。
托尔斯塔雅1991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就天性而言,我只是个旁观者。一边观察一边思索:‘天啊,多么奇妙的荒诞的舞台,荒唐的舞台,愚蠢的舞台……为什么我们所有的成年人要参与这种游戏呢?’”(注:阿·尼托奇金娜:《塔·托尔斯塔雅:我没加入布尔什维克……》,载《首都》,1991年No 33,第12页俄文)。)女作家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用种种“童话”展示了虚拟世界和在这一世界中现代人生存的荒唐“个案”,同时又在不断地将其演化为稳定与恒久的人生图景:生活的庸常,现实的无序,生命间的龃龉,爱情的虚妄,心灵之家的寻觅。作家质疑生活,挑战现实,表达了意欲摆脱乌托邦式的神话思维,解决生存危机的一种非理性的努力。小说大大强化了这样一种不无偏执的理念,即社会秩序、人类关系普遍受到了一种莫明其妙的,日益非理性化的威胁。小说是人间美好失落后的畅想,灵魂遭遇后的迷茫,是怀疑者的怀疑,寻觅者的寻觅,是在对无序、混乱的现实否定后的一种新的世界结构的期待。
作为一种艺术的开放式的遐想与神游,《痴愚说客》没有传统小说所遵循的“方向与线路”,甚至连一条贯穿始终的情节主线都没有。文中没有任何足以称得上是理性的思索与判断,与道德伦理也几乎无涉。作者逼近生活、思索的原质地,仅仅从生活、文学本身的视角出发,对流行的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作了极力的疏离与背弃,回到了文学写作的本体。
小说所提供的新的时空体验,沿用后现代的话语,可以叫做后地理、后历史的体验。即作者跳过地域空间的物理和社会维度,穿越历史,将活着的与死去的、过去的和现在的串联在了一起。托尔斯塔雅笔下的小说是对时间空间的重新设置,对人生经验的重新组合。就小说所反映的事件整体和部分细节而言,它们是虚拟的。而按照历史的逻辑它们又是一种潜在的和可能的,故而又是可以理解的。这种虚拟世界具有现实世界的效果性,这是一种具有真实性的虚拟。这种真实性体现在它们反映了现实世界的本质性特症:荒唐性、非逻辑性和混乱性。
女作家后现代主义创作实践的用心在于反思20世纪现当代俄罗斯文明的困境,并建构了一种新的“二元对立语境”:原始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对立。它为人们认识俄罗斯人精神生命的存在与发生、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可供阐释的文化语境:精神生命的苦难与现代文明的关系,这是一种新的忧患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著名学者本杰明说,小说的结尾应当“把读者带到对生活意义的某种预感式的意识”,(注:转引自王鲁湘等编译《西方学者眼中的西方现代美学》(北大出版社,1987),第227页。)托尔斯塔雅似乎做到了,她确实把有关时间、空间、生存、生命的“预感式的意识”传达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