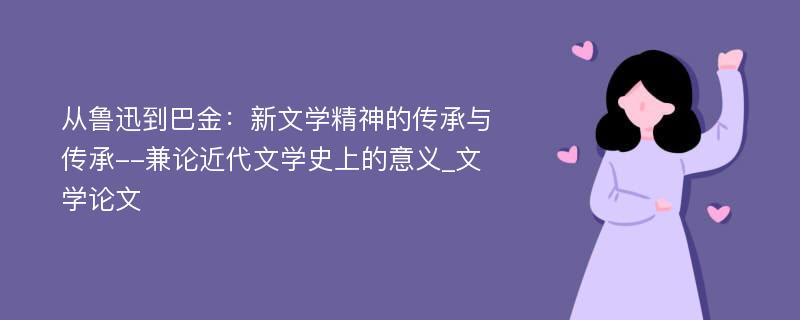
从鲁迅到巴金:新文学精神的接力与传承——试论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金论文,鲁迅论文,新文学论文,史上论文,现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几年前,我曾应一家杂志之约写过一篇《巴金的意义》,试图从中国知识分子的角度来探讨巴金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本文将换一个角度,从文学史的范围来继续探讨这一问题。但这是一个比较难以把握的问题,因为巴金先生从未以一个作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相反,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以社会革命家的事迹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直到耄耋之年,依然认为自己的所有文学创作只是一种与读者、与世界进行交流的特殊方法,文学并不是他的主要的职业。他自称是个“业余”作家,希望自己能在文学以外对社会多作贡献。那么,巴金在文学史上究竟有没有意义呢?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认识巴金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是有所争论的。我注意到,随着巴金先生以百岁高龄辞世,很多媒体对此作采访时,仍然是以“巴金先生的文学史地位”为主要话题,仿佛这一话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本文从鲁迅与巴金的精神传承关系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这仅仅是讨论巴金先生与现代文学史的意义的一个侧面,因此并不是全部,而且也不涉及巴金先生的文学创作在美学上的贡献。我希望通过我的理解和表达,引起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我曾经在《人格的发展——巴金传》里说过,巴金先生从1929年发表《灭亡》起走上文坛,很快就成为一个深受读者喜爱的畅销作家,但是他并没有以此为幸,反而深以为痛苦,时时有生命浪费之感。从1929年起的五六年时间,既是他的创作高潮期,同时又是他的精神危机期。这期间他几乎居无定所,四处漂泊,流浪在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之间,直到1935年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他的朋友们邀他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他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民间知识分子岗位,也找到了自己在文坛上所建立的积极的价值取向。因此,我们说巴金先生主要贡献于文学的,除了他的几百万字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外,还有他所确立的文学岗位,他曾经作为一位卓越的文学编辑,团结和凝聚了一大批青年作家,把他们的作品推荐给读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于巴金人生道路的意义,还不仅仅是让他发现了适合于自己的工作岗位,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他与鲁迅发生了联系,成为鲁迅旗帜下的文学新生代中的一员。我经常读到有关鲁迅的晚年处境孤立的说法,为了突出鲁迅晚年的悲壮,许多学者把鲁迅描写成一个四处树敌、心境凄凉的孤独老人。其实这是错看了鲁迅,也不理解鲁迅所具有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素质。鲁迅从来就不是一个习惯于孤军奋战的独行侠,他在反抗黑暗环境的一生中,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同盟军。他的一生是寻找结盟的一生:早年投身于辛亥革命,中年加盟于《新青年》,后来又南下广州参加国民革命,最后又担当起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责任,成为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帜。鲁迅总是寻找到社会上最有活力、最有革命性的力量,尽管他本人的思想之前卫可能已经超越了那些思潮,但他仍然愿意与它们建立统一战线,结为盟友,共同担负起战斗的责任。但是在鲁迅的生命的最后一年多时间里,就是在他与周扬等人发生了激烈冲突,左联也濒于解散(不久真的解散了)之际,也就是在他为了对付同一阵营里的冷箭决定“横站”的时候,他发现了身边活跃着一批值得信任的文学青年。这批青年中有胡风、聂绀弩、萧军、萧红、叶紫等左翼青年作家,有来自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和吴朗西,有帮助他编辑《译文》的黄源,有先编《自由谈》后编《中流》的黎烈文,有主持良友图书公司的文学出版的赵家璧,有编辑《作家》杂志的孟十还,等等。而在这批青年中间,最有活动能量并能够团结人的是胡风和巴金,当时因为巴金的关系使一批自由主义作家如章靳以(主编《文季月刊》)、萧乾(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等也间接地围绕在鲁迅的周围。我把这批青年作家和青年编辑称为当时的“文学新生代”。他们年纪相仿,都充满了热情和理想,他们的政治态度也相仿,对当时的黑暗环境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他们中少数是左联成员,更多的是站在比较激进的自由主义立场上,也有的是被左联关门主义的错误路线排挤在外,更有像萧红那样没有参加左联,但自觉追随鲁迅的青年,他们几乎都是从各地流浪到上海,聚集在一起,从事喜欢的文学事业。他们身上并没有一般流浪知识分子常见的毛病,如浪漫成性、偏激好斗、狂妄自大、不负责任、喜欢窝里斗等等,而是对文学充满信心,认真向上,真诚待人,对鲁迅先生都满怀着自觉的敬意,愿为先生做任何事情。一般学者对此的解释,常常是偏重鲁迅对青年人的呵护和支持的一面,这当然是不错的,但似乎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任何关系的合作都是双向的,当鲁迅对那些青年人满腔热情地给以支持时,他也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左联“元帅”们所不具备的信任感和希望所在。所以当时有个日本人问鲁迅为什么要与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巴金合作时,鲁迅用很赞扬的口气说,巴金做事认真。鲁迅识人是从其具体的行为着眼的。
巴金就这样成为鲁迅旗帜下的文学新生代的一员。从文学史的角度似乎还很难为这个既非社团又非组织的作家编辑群体命名,但这批青年是当时上海文坛上最活跃的力量,又掌握着各种生机勃勃的现代传播媒体——刊物和出版社(所以当时鲁迅的声音可以在几家刊物上同时发出,足以振聋发聩),正能够发挥积极而健康的作用。鲁迅把他们团结在身边,支持他们的各种文学出版活动,也获得了青年们的尊敬。就这样,在克服党派与宗派的争斗,超越流派与社团的局限,独立于官方和左翼宗派势力之外,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新的力量。这是鲁迅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又一次展示出极有光彩的一页。如果鲁迅不是因为肺结核过早去世的话,以他为旗帜的这股新生力量在未来文坛上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这一点,作为当时地下党的负责人冯雪峰已经意识到了。当左联解散、鲁迅拒绝参加周扬搞的中国文艺家协会时,这批文学新生代也都拒绝参加,而且还特意发表了一个《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双方对阵的架势也已经摆开了,冯雪峰立刻嘱咐茅盾两边的活动都要参加,这显然是有着明确的统战观念在里面。但由于鲁迅突然去世,这一文学新生代的积极能量并没有完全爆发出来。他们最后一次集中的能量爆发是在鲁迅的追悼活动中,真是有声有色,负责护送灵柩的正是这批倾心于先生的青年人。这以后,抗战的炮声催促他们各奔东西,各自经历了命运的考验。但鲁迅的精神传统也在他们这一代人的文学活动中继续体现出来——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仍然是胡风和巴金,一个创办《七月》、《希望》,于特立独行中团结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青年作家和诗人,而另一个则以文化生活出版社为岗位,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学新人。所以他们两人在上世纪40年代以后的文学领域所发挥的作用,显然都超过了他们个人的创作的意义,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即是文学团队的领军人物。
如果我们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孤立地比较鲁迅与巴金两人的言论及其表述方式,那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很容易淹没一切本来更加值得注意的相似性。但如果深入到两者关系的发生及演变的全过程去看,他们之间的继承和联系则是相当深刻的。巴金对鲁迅的认识有过一个质的变化。在1935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创办以前,巴金与鲁迅没有实质性的接触,他虽然早在20年代就读过鲁迅的书,虽然后来他们同样生活在上海这个城市里,但由于生活圈子的不同,好像彼此之间没有什么来往的机会。巴金的《家》可以说是对旧式家庭“礼教吃人”的生动演绎,但在作为首创这个观念的《狂人日记》里,鲁迅所要表达的人的自我批判的彻底性及其对自身的忏悔的深刻度,在十多年以后才产生的《家》里并没有得到全面体现,如果说《家》是《狂人日记》的精神血脉的继承者,它也只是继承了其揭露家庭制度弊病的部分。30年代前期,巴金是一个站在无政府主义立场上的激进的反抗者,基本上与文坛主流不直接发生关系,那时他与鲁迅的精神传统,从理性到方式上都还有很大距离。但是在巴金亲炙于晚年鲁迅的人格精神、并具体地在鲁迅身边工作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巴金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他与文坛的疏离感很快消失,而且渐渐卷入了文坛的冲突和社会的运动。鲁迅晚年与周扬的两次大冲突,一次是“两个口号”之争,引起争议的是胡风的一篇文章(当然背后还有冯雪峰和鲁迅);还有一次是《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的发布,而起草者正是巴金和黎烈文。这是巴金主动请缨捉笔的结果。所以徐懋庸写给鲁迅的那封雄赳赳的信里把胡风、巴金、黄源三人列入主要攻击对手不是无的放矢。鲁迅撒手西去,配合鲁迅编辑《译文丛书》的黄源不久也离开上海去了苏北战区,而巴金则坚持编辑出版《译文丛书》,推出了50多种世界名著,把鲁迅生前规划的工作计划一直坚持到50年代初。抗战爆发后,《文学》、《译文》、《中流》、《文丛》四家杂志联合组成战时刊物《呐喊》(后更名《烽火》)宣传抗战,之所以取名《呐喊》也是有继承鲁迅的意思,这家刊物列名主编为茅盾和巴金,但自始至终的编辑工作都是巴金一人在承担。在这个民间的工作岗位上,巴金一直默默承担了文学薪传的工作,他所发挥的作用是相当全面的,不仅仅以创作传播自己的影响,而且通过编辑出版工作、培养新人、团结作家、翻译大量进步的思想读物等来传播和普及他的理想。许多文学青年都是在他的推荐下走上文坛,从而坚定了一生的文学道路。
我过去读过一份萧乾在“文革”中的检讨交代,这样介绍当时活跃在上海的文学编辑圈的情况:“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底子比不上开明,但能拥有新作家特别多,这样使巴金在文艺界形成一个可观的力量,实际上抗战前巴金、靳以及我(指萧乾本人——引者)三个人是形成一个小圈子。”这一说法至少反映了当时以这批年轻编辑为中心的新的文坛生力军的产生,这是结合了京派和海派的文学中间力量而形成的一支新的文学青年队伍。说他们的核心在抗战前就是巴、靳、萧三人未免有些夸大,但在抗战以后的文学活动中,巴金在编辑工作中建立起来的威望是肯定的。5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对巴金和老舍两位非左翼作家的推崇,显然不完全出自文学上的评价。在抗战前,巴金和老舍与一般的非左翼作家没有很大的区别,但在抗战的文学实践中就不一样了:老舍整个地主持了文艺家抗敌协会的日常工作,是抗战文学的一面旗帜;而巴金依然通过他的民间出版工作,把一大群青年作家团结在周围,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抗战改变了文学史的原有格局,巴金从一个边缘的自由撰稿人,通过民间出版工作的实践,终于成为一个众望所归的文学领军人物。
当然,巴金与他前辈之间的精神继承关系,最重要的标记还是体现在他的创作。巴金在抗战以后的创作从风格到内涵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抗战以后的巴金在创作里再也没有空洞地呼喊反抗和控诉黑暗,早期英雄主义风格和“眼泪文学”的煽情手法都消失了,弥漫于文字间的不仅是对小人物的深刻同情与关怀,也体现了他对人的复杂性的理解,人性的力量也增强了。以《憩园》为例,他本来要写的主人公,是《激流三部曲》里的高克定之流,但他放弃了高家的故事改写杨家的故事,在描写放荡地主杨梦痴的败家故事时也饱含了对人物悲剧命运的挖掘,作家把批判的锋芒不再简单地集中在个别“坏人”身上,而是在所有的人物(包括憩园的新主人姚家,也包括作家自己)身上都挖掘出人性的缺陷,使批判的深度推进了。这是典型的鲁迅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特点。如果说《家》所描写的“礼教吃人”,还仅仅是巴金对鲁迅创作的稚嫩的回应,那么在他后期创作的《寒夜》里,他把鲁迅在《伤逝》里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思考更加推进了一步。他把人性的善良和失败、自私与怯懦完整地糅为一体,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在“五四”新文学的鼓舞下走上理想主义道路的,这正是巴金所描写的高觉慧、高淑英们让人羡慕不已的反叛道路,但是这些反叛英雄们出走以后怎样呢?作家再也不把杜大心一类的英雄作为他们的榜样了,而是让严酷的生活现实把他们困在贫穷和疾病中无以自拔,一步步地被逼向精神的崩溃和无谓的死亡。这里作家并没有一味谴责主人公的自私和软弱,却是相濡以沫地把一点微弱同情和温暖洒在他们寒冷的身上,显现出人性的真正博大。我想,人是需要有温暖来支撑其精神的,人不能完全沉浸在怨毒与黑暗之中,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也是一个作家所应该给予这个社会和挣扎在这个社会中的读者的。
纵观巴金的文学创作道路,其前后期的美学风格和创作精神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而后期的几部中长篇小说则真正代表了他的创作高峰。巴金最为成熟的风格和最有深度的创作,应推《憩园》和《寒夜》。这些作品是整个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中能够承传鲁迅精神的少数佳作之一。由于40年代文学的黄金时代非常短暂,以后迅速发展的中国政治局势又是朝着另外一条道路在催迫文学的进步,所以这批光亮辉煌的创作一直没有被人充分关注,这与鲁迅的精神传统面临重新阐释的政治大趋势有关,决非巴金本人的能力所能挽回。但只有充分认识了巴金在抗战后期的创作与鲁迅精神的关系,我以为,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和评价巴金的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活动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