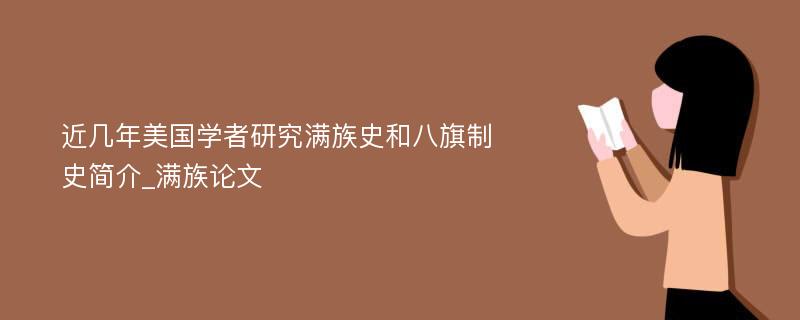
美国学者近年来对满族史与八旗制度史的研究简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满族论文,美国论文,学者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65X(2002)01-0060-04
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发生了迅速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新的研究领域迅速拓展,旧的观念被颠覆。这些变化也反映在汉学研究中。虽然对于美国学界来说,清代的满族与八旗制度是一个离他们的主流相距甚远的课题,加上语言等障碍,研究者不能不限于一个极小的圈子之内,但自1980年以来,这一课题却受到新一代学者的重视与重新审视,接连出版四、五部大部头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专著,足堪令人瞩目。这与近几年国内满族史学界的相对沉寂,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几年前全美亚洲学会会长伊芙林·罗斯基(EvelynS.Rawski)与老一辈著名汉学家何炳棣的一场论争,更增加了美国汉学界对这一题目的关注程度。由于见闻有限,这里只介绍本人较为熟悉的几个问题,挂一漏万之处尚请谅解。(注:此文系笔者参加2001年9月沈阳故宫博物院纪念八旗制度建立350年学术讨论会时提交的论文,因专题是八旗制度,所以八旗制度研究情况的介绍尤详而其它较略,如有轻重不当之处请谅解。)
一、“汉化”之争
1996年,伊芙林·罗斯基在全美亚洲年会上以前任会长的身份发表一篇演讲,名为《再现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后来发表在当年10月的《亚洲研究学刊》上,针对何炳棣1967年所写《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所说清朝统治者的“汉化”问题提出异议。罗斯基反对将“清”与中国完全看作是一回事,她强调满族中心观,认为这对评价清帝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她认为,清朝能够在中国成功地维持了近300年的统治,主要原因并不是汉化,而是有效地利用了与内陆亚洲诸非汉民族的文化联系,从这点上说来,满族统治者是以中亚诸民族的大汗而并非中国传统王朝的皇帝身份出现的。她认为满族只是利用了儒家的很多东西而本身还是保留了诸多自己的特点。罗斯基的说法在美国汉学界反响强烈,颇得好评。接到挑战后,何炳棣用近两年时间撰写了《我对汉化问题的再思考:对罗斯基“再观清代”一文的答复)(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一文,对罗斯基予以驳斥。指出罗斯基的许多观点都是似是而非的,并举出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都要争“正统”的大量事实,说明少数民族的“汉化”乃是大势所趋。他认为,以清朝来说,汉化的标志就是“儒化”,所以也不妨以“儒化”代替之,而儒化与中国化就是一回事。何还强调说,少数民族当然可能保持自己的某些特点,但保留这些特点并不说明就没有中国化,中国化了照样可以有自己的特点。何的文章观点犀利鲜明,史料确凿充分,说理透彻精辟,行文准确精美,堪称是阐述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儒化”过程的典范性文章,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重视。
不过,罗斯基并未因此而被打倒,她的观点在年轻一代的学者与学生之中颇有市场。1998年,她出版了《最后的皇朝:清皇家机构的社会史》一书(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Institution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加州大学出版社,1998),将自己关于满族并非未汉化而只是“利用”儒学的观点,再次作了充分的发挥。这部长达400页的著作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清朝的物质文化;第二部分论述清朝的社会组织,谈到皇族的世系、清廷对皇族的政策、皇家妇女与奴仆等诸多内容;第三部分谈清宫的祭祀与崇拜,如满族早期的萨满教和后来的藏传佛教等。作者再次强调,她的主旨是从满洲统治的角度来剖析清朝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强调清朝作为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政权,所具有的与以往汉族传统封建王朝不同的某些特点,描述了在中央统治机构中保留的满族特色,同时突出论述了清皇室是如何利用宗教(如佛教以及满族固有的萨满教)来进行统治的。美国汉学界的部分学者对罗斯基一书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说她注意到了以往学者很少留意的民族问题,并且对此有比较完整具体的阐述。认为它所采取的角度,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的读者,都会感觉到某种新意。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最令人感兴趣之处,也许不是作者对于满族统治者的儒化与中国化问题的阐释。
不过,这部书也存在诸多问题。虽然作者企图从满族统治的角度来剖析有清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但从全书的构架和布局看,对满族诸项制度的叙述并不全面,对于清朝统治起到过重要作用的军事、法律和财政政策,很少或几乎全无涉及,似有畸轻畸重之嫌。满洲这一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以及民族意识等问题,是作者在本书中的重头戏,但脉络交待得并不十分清楚。此外,本书中还有些常识性的错误。再者,作者虽然自称此书是在掌握了大量清代满汉文档案,并在汲取了大量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写成的,但事实上对于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动态却相当生疏。例如对清代中央统治机构中的满族特色问题,我国老一辈清史学家早有论及,王钟翰先生谈明清官制异同的文章中,就明确论述过清制中那些明代所无的机构如理藩院等,作者对此却全未提及。她虽也引用了一些我国史学家的论著,却往往并非该人的代表作。对我国史学研究成果持这种隔膜甚至漠视态度,在美国汉学界至今仍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表明两国学者要达到充分交流和了解的程度,还有很大的路要走。(注:参见拙作:《对美国学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回顾》,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9期。)
二、满族的族群问题
美国学者所说的Manchu与我们今天常用的“满族”并不完全是同一个概念。为叙述方便起见,本文还是用“满族”来指称这个人们共同体。满族作为一个民族,对它的族群意识与认同等问题的研究,并不自罗斯基始。事实上,满族研究之所以成为热点和争论的中心,是与族群(ethnicity)理论在学界的兴起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关于族群理论的探讨,首先受到民族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关注,其内容非常丰富,在很大方面都对我们传统的民族史研究构成挑战,这里对此不拟多谈。我们要谈的是,有关满族的族群认同问题,就是由此而引起学者关注的,新一代学者提出要以新的观念和新的叙述(New Narrativcs)来重新审视满族的形成与认同。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柯娇燕(Pamela Kvle Crossley)的两部书,一是1990年出版的Qrphan Warriors(汉译作《孤军》,本书有两个引人注目的论点,一是认为“满族”是乾隆时期被统治者人为建构的,二是与皇室贵族不同,满族下层内的族群意识与认同是在清末才产生的。1999年,她又出版了《透明之镜:清朝皇族的观念》(A TranshucentMirror:Qing Imperal Ideology,Bcrkeley and Los Angeles:加州大学出版社,1999)一书,受到清史与满族史学界的广泛注意。
埃德伍德·路斯(Edward J.M.Rhoads)的近著:《满与汉:晚清到民国时期的民族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Manchus&.Han: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China,1861-1928,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0)。从满汉民族关系的视角讨论辛亥革命后满人从特权阶层(即旗人)沦为截然不同的边缘人群的变革过程。并详细叙述了清朝宫廷与汉族革命者之间的对话与相互影响。由于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美国等处,历史学家对于满族的主要兴趣,都集中于满族兴起直到入关(1644)这一阶段,对清入关之后的研究成果则相对较少,至于从清末到民国这一时期满族的兴衰,也许由于多年来一直是敏感话题甚至已部分地成为禁区,至少在国内,更几乎是一片空白。该书便成为迄今为止有关乎此的惟一一部史学专著了。(注:该书共六章,目录为1,种族隔离与不平等;2,慈禧与特权制度;3,载沣与“优遇满洲”;4,1911年的革命;5,1911年以后的皇族和满洲;6,结论。)
三、满族与八旗制度
欧立德(Mark C Elliott)的《满洲之道:清朝的八旗制度与民族认同》(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主旨也是讨论满族族群形成的问题,但该书最精彩的部分,是对八旗制度与满族关系的阐述,不仅论述系统详细,而且多发人所未发,即使我们国内各种著作的论述也尚未有如此深入的。此书甫一出版就受到美国汉学界重视,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有关中国人与满洲人生活的一部最有趣的历史,是十年来清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本书研究的出发点,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满族这样一个刚刚走出山林的少数民族是凭借什么来驾驭一个具有高度发达文化且人口远较满族众多的以汉人为主的国家并维持它的权力达近300年之久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在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令学者迷惑,但直到如今还没有哪个人试图从满族的视角来走进它。
作者继续了罗斯基的满族中心观并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满族征服者虽然作为全中国的统治者,不得不遵奉儒家君主的行为规范,但作为一个非汉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权力不仅来自汉族传统的官僚阶层的支持,同时还来自不同人种、不同文化、不同层面的少数民族的一致承认。满洲贵族的内亚、中亚众多民族的共同君主,它的统治具有双重性,对汉族地区和其它地区,也采用了双重的统治模式。有清一代的满族尽管与汉族在某种程度上有所融合,但作为一个群体,在清代却从未被吸收进汉族社会之中,也就是说,即使他们采纳了汉族文化的诸多因素,却从未将自己等同于汉人。同样地,汉人也从未将自己与满洲人等同。作者因此而提出一个“族群宗主权”的概念,并在全书开篇时对他的这个概念做了详细介绍。
作者将清朝朝廷对“满洲”(Manchu)的定义与人们实际生活中对满洲的概念以及满洲与旗人这两个名词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群中的不同内涵作了详细的考辨。他认为满族的精英集团能够成功地维持本民族的一致性和民族意识,靠的就是八旗这个严密的、独特的组织。他指出,正是因为朝廷察觉到了满洲认同的危机,才导致了雍正时期对八旗制度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与调整。从此八旗制度成为满洲认同的根基,它为被它囊括于其中的成员建立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书中用大量篇幅描绘了旗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和特权,指出正是这一切使清代的旗人男女与汉族男女构成了明显的区别。
本书的另一可贵之处,在于使用的几乎完全是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处爬梳搜剔的满文档案史料。作者认为,要想对所研究的对象有真切和全面的理解,研究他们如何用自己的文字来描写他们自己是至关重要的。除此之外,他还广泛地利用了中文史料以及中国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这种熟练掌握和运用多种语言的功力,殊非一般学者所能及。(注:该书共分三部分:介绍:满洲之谜。第一部分 八旗的社会结构:(1)满洲与八旗的起源;(2)驻防之城:下山之虎;(3)皇帝之子。第二部分 旗人的生活方式:(1)铁轩庄稼:旗人的特权;(2)在“尼堪”中间;(3)特殊居民。第三部分 十八世纪的危机:(1)哪一条是满洲之道;(2)对八旗制度的挽救。结语:满族族群形成的实践。)
美国近几年对满族史、八旗制度史的研究硕果累累,这也对我们提出了要求与挑战。传统史学发展到此,许多观念与方法乃至史料的运用,都亟待发展与更新,祈盼诸位同行、前辈对此予以更多的兴趣与兴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