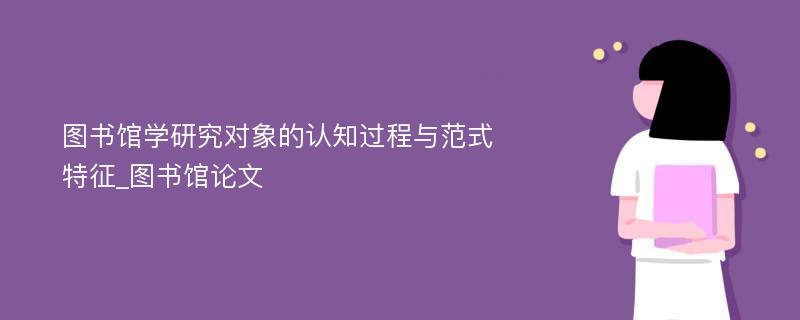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过程及范式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范式论文,研究对象论文,特征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在图书馆学中,研究对象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元问题,它规定着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规定着图书馆学的科学性质。科学地确定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既给图书馆学提供了赖以建立的基石,也为图书馆学提供了与其他科学知识相区别的理论根据。
1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过程
在图书馆学发展的两百年历史之中,世界各国有关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表述有数百种。虽然这些认识受不同时代的文化影响,有着不同时代的文化烙印,但它们都含有科学探索精神,就像不同时间里撒下的理性种子,每一粒都蕴含着宝贵的思想价值。从历史发展轨迹看,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1 整理总和说
图书馆职业是世界最古老的行业之一,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藏书事业及其藏书活动史。图书馆学正是在以往人们丰富的藏书实践活动中逐步发展成熟的。1922年蔡元培曾说:“一种事业发达到一定的程度,便会产生一种有系统的理论。有了系统的理论,那种事业的发达,才有迅速的进步。这是各种事业的通例,图书馆也就不在例外。”[1]1931年,英国克罗伊登公共图书馆馆长、 伦敦大学图书馆学院讲师贝里克·塞耶斯(W.C.Berwick Sayers)也认为:“只有从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中,才能渐渐地推演出一种理论,并加以表述。”[2]
图书馆学(Bibliothekswissenschaft )这一名称是德国图书馆学家施雷廷格(M.W.Schrettinger,1772~1851)在1807年最早提出的。此后,施雷廷格在慕尼黑皇家图书馆任职期间,又出版了两卷本的《图书馆学综合性试用教科书》(1808~1929)。在该书中,施氏将图书馆学研究内容确定为“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3]施氏认为图书馆工作的核心是目录的编制, 他不仅编制出12个大类、200个小类的分类表,而且编制过字顺目录、主题目录。他在此书中第一次全面叙述了图书馆目录的编制原理,并将其视为图书馆学的重要知识体系。施氏尝言:“图书馆应当尽快地找到必要的书籍,以满足任何文献工作的需要。”[4 ]与施氏同时代的另一位德国图书馆学者艾伯特(Friedrish Adolf Ebert,1791~1834),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德累斯顿王立图书馆等处工作二十多年,他在名为《关于公开图书馆》(1810年)的小册子中认为,把图书馆学局限于图书整理范畴过于狭窄了,指出“图书馆学是图书馆员执行图书馆工作任务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技巧的总和”。[5]1820年, 艾伯特又出版《图书馆员的教育》,强调图书馆员所需要的是综合性的知识,即应掌握外语、历史、文学史、目录学、古籍、百科词典等众多知识。[6 ]艾氏的观点得到丹麦学者莫尔贝希(C.Molbech,1783~1857)的支持,后者在1829年出版的《论公共图书馆》一书中,进一步阐发艾氏观点并系统化,后人称之为“艾伯特—莫尔贝希体系”。
历史表明,早期一些图书馆学家都是在图书馆整理活动中取得巨大成就而闻名于世的。如德国的莱布尼兹(G.W.Leibniz,1646~1716)在1666年写过一篇论文《组合技术论——使全部知识转换为具有可计算性的方法》,他计划将所有知识纳入一个具有逻辑概括性的人类知识一览表,借以向读者提供检索与自学的方便。而担任过大英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帕尼齐(A.Panizzi,1797~1879)于1841年编制出版了以著者为主要款目的《91条著录规则》,后被世界许多国家图书馆所接受。他们均系以非凡的学术思想与方法而享誉图书馆学界的。因此,将图书馆学研究内容归纳为整理文献所需要的一切知识与技术的总和,这种观点对后世影响极大。如20世纪前期,美国图书馆协会(ALA )在给图书馆学下定义时说:“图书馆学就是发现、搜集、组织及运用印刷或书写的记录之知识与技能。”[7 ]日本图书馆学家推名六郎早年也认为:“图书馆学是将图书馆的一切知识与技术,作有组织的研究的学问。”[8]
“整理总和说”的提出,反映出西方近代图书馆工作已趋于复杂化、精细化、系统化,图书整理中的知识、技术含量愈来愈高,不设专门学问便无从下手。“整理总和说”最早为图书馆学设定了明确的研究对象,它为图书馆学的建立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它强调图书馆学既有知识,又有技术,将图书馆学内容表述成“知识、技术的总和”,形成了后世图书馆学研究理论与应用并重范式的先声。“整理总和说”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界说,源于图书整理实践活动,属经验的总结,尚处于现象描述的认识阶段。
1.2 图书馆管理说
19世纪中叶以前的各国图书馆,或为王侯贵族所建,或为修道院所设,或为大学附属,或为新兴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私立,几乎不向社会公众开放。当时有一种面向读者的“会员图书馆”一度流行于英美,但其服务对象仍以学者、有产阶级中层人物为主,并且还要事先入会。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工业革命加速了城市的成长、产业大军的壮大,同时工业生产又对劳动者知识技能素质有不断提高的要求,因此,各国公共图书馆应运而生。185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第一部公共图书馆法。该法要求人口在一万人以上的各英格兰城市,都有权建立公共图书馆。从此,英美各国掀起了一场公共图书馆运动。这些新建公共图书馆有三个特征:(1)向所有居民免费开放;(2)经费来源于地方政府税收;(3)图书馆的设立与经营有法可依。[9]
公共图书馆的蓬勃发展,使图书馆学研究开始发生转变。图书馆学的研究客体从以往侧重于图书资料,逐步转向整个图书馆,研究内容也从以图书整理为中心渐渐转向以图书馆经营管理为中心。1821年,德国图书馆学者F·A·艾伯特首次提出“图书馆管理学”(library economy)一词。1839年,法国学者L·A·C·海塞出版了《图书馆管理学》,他认为图书馆学的宗旨是解决如何最有效地管理图书馆。1859年,英国的爱德华兹(E.Edwards,1812~1886)出版《图书馆纪要》两册,其第二册即为《图书馆管理》,对17~19世纪的图书馆管理经验进行全面总结。1887年,美国图书馆学家M·杜威创办的图书馆学校, 全称即为哥伦比亚学院图书馆管理学院(School of Library Economy at Columbia College)。杜威图书馆学思想的核心是如何提高图书馆管理的时间和成本效益,办学目的就是培养专业的图书馆管理人才,故其课程偏重于图书馆经营之实际。同年,圣路易斯公共图书馆馆长F·M·克伦登著文提出,应运用企业管理方法管理图书馆。此后有关图书馆管理的论著日益增多。[10]
受美欧图书馆学影响,我国早期图书馆论著论及图书馆学研究内容时,也多将研究客体指向“图书馆”。如李小缘在其《图书馆学》(1927年讲义初稿)中指出,就图书馆的“各方面研究之,是为图书馆学”。[11]1934年,刘国钧《图书馆学要旨》一书出版,该书在讲到图书馆学的意义时说:“什么是图书馆学?图书馆学便是研究图书馆的组织法、管理法和使用法的学科。”[12]1935年,李景新在一篇论文中也明确表述:“图书馆学就是以科学方法研究关于图书馆的一切事项的学问。”[13]
“图书馆管理说”扩大了以往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它要求图书馆学研究不仅要关注图书整理,也要关注图书馆的经营与管理,这无疑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图书馆管理说”将研究重心从图书整理转向图书馆管理,实现了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第一次转变。这种转变对于世界各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发展以及对于图书馆工作的职业化,都起到了直接的推进作用。
1.3 图书馆事业说
20世纪前期,世界各国的图书馆事业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一方面各类型、各级别的图书馆纷纷涌现,另一方面图书馆员的职业化又促进了图书馆协会的繁荣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图书馆事业,已成为该国家或地区的重要文化设施和事业。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学也遇到了一些新的研究命题,如图书馆的馆际互借、图书馆法规的制定、图书馆员队伍的建设、图书馆藏书的协调、图书馆网的布局等等。因此,众多的图书馆学研究者开始调整自己的研究视角,逐渐将研究视野提升到宏观层面上来。在他们看来,不仅微观图书馆的研究很有价值,宏观的图书馆事业也同样具有研究的价值和必要。
1957年,我国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发表《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文章指出:“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图书馆事业及其各个组成要素。图书馆是客观存在着的一种事业,是人类社会生活现象之一。这种现象,这种事业,深刻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学习生活、文化生活、科学研究生活。既然如此,难道不应该弄明白它的性质、它的发展规律、它的各个组成要素及其规律吗?”[14]刘国钧说,图书馆事业有五项组成要素:图书、读者、领导和干部、建筑与设备、工作方法,欲掌握图书馆事业的规律,必须分别深入研究这五项要素。后来,人们在谈到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时,一般将刘国钧的观点概括成“要素说”。其实,刘国钧所言研究对象是明确指称“图书馆事业”,而不是什么图书馆要素,所以是典型的“图书馆事业说”。
1963年,武汉大学黄宗忠先生根据毛泽东《矛盾论》的论述,提出了图书馆事业中藏与用这对特有的矛盾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15]这一观点亦曾被人称为“矛盾说”。1981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教材《图书馆学基础》出版,该书称:“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生发展、组织形式以及它的工作规律的一门科学。”[16]此说被人简称为“规律说”。1984年底,黄宗忠先生又对自己提出的“矛盾说”进行了修正,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这里的图书馆不是具体的,而是经过抽象的“一种科学概念的图书馆”。[17]1985年初,沈继武先生又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活动”,[18]人们简称之为“活动说”。这些研究对象的新解各有独到之处,在我国图书馆学界广泛传播。不过,它们的出发点均已不再局限于微观的图书馆,而是扩延到了宏观的图书馆,不再仅以图书馆的内部因素为根据。因此,这些观点可以看作是“图书馆事业说”的发展与延伸。当然,“图书馆事业说”不仅在中国流行一时,国外图书馆学界亦有持此说者,如苏联图书馆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讨论图书馆学研究客体与研究对象的区别时,一种主导观点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客体是图书馆事业,研究对象是图书馆的规律、组织、发展、职能等。图书馆学不仅要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内部关系,也要研究其外部关系,包括图书馆事业外在的广泛社会系统的联系。[19]
在20世纪后半叶,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阐释,“图书馆事业说”在我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至今尚为一种主流意识。“图书馆事业说”不但拓展出图书馆学研究的宏观领域,而且也因其开始关注图书馆事业与社会的各种复杂联系,为图书馆学研究增加了深度与广度。“图书馆事业说”包容了“矛盾说”、“规律说”、“活动说”等等诸多观点,这些观点都具有“本土”特色,它们表现出中国图书馆学者的创新意识与开拓精神。
1.4 知识交流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高峰期。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学技术的分工越来越细,专业越来越多;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横断学科纷纷问世;文献量也急剧增长,呈现出数量膨胀、内容交叉、文种多样、类型复杂、分布分散、失效加快等特征。人们曾用“知识爆炸”来形容文献的迅速扩张。由于电子计算机、缩微复制等技术的应用,图书馆工作也出现了从手工方式向自动化方式转移的趋向。此外,情报学此时已从图书馆学母体中剥离出来,成为一门充满活力的新兴学科。一些图书馆学者意识到,图书馆学、情报学自身的任务就是促进社会知识信息的有效交流,以满足人们快速、准确获取有用知识信息的需求。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亦应向这个方向进行转移。
40~70年代,国外一些图书馆学者对图书馆的知识、信息、情报的交流问题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如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在《图书馆学教育基础》(1972年)一书中提出,“交流是社会结构的胶粘剂”,“图书馆是社会交流链中的一环”,“图书馆具有教育作用和传递情报的作用。它是人们与文字记录知识之间的中介,是促使记录知识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利用的交流系统”。[20]日本图书馆学家推名六郎称:“情报理论和图书馆学都是以人类社会的情报交流为对象的科学。两者都立足于情报交流现象的同一基础上。”[21]苏联图书馆学家丘巴梁谈及苏联图书馆学时说,它是“一门把图书馆过程作为群众性地交流社会思想的一种形式的社会科学”。[22]
从80年代开始,我国图书馆学者也开始提出自己的知识、情报交流的理论与观点,如北京大学周文骏先生在《概论图书馆学》(1983年)一文中阐述了他的“情报交流”观点,认为文献是情报交流的工具,图书馆是情报交流工作的机构,图书馆学理论是一种用文献进行情报交流工作的经验结晶。[23]1984年11月,华东师范大学的宓浩先生向在杭州召开的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讨论会提交论文《知识交流和交流的科学——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建设》。文章对以往图书馆学仅停留于对图书馆工作表象研究的状况提出了批评,认为应当发掘隐藏在表象下面的内在机制,从表象描述上升到本质揭示。宓浩指出,图书馆收集、存贮、整理、组织、传递和利用知识信息的活动本质是人类知识交流。图书馆实质上是社会知识交流的工具,图书馆学应分三个层次研究知识交流:(1)知识交流的基本原理(研究知识、知识载体、知识交流三者关系);(2)知识交流与交流实体(如图书馆)之间的关系;(3)图书馆知识交流的内在机制。[24]该文发表后,在图书馆学界影响甚广。
“知识交流说”在理论形态上自称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它是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一种新解。“知识交流说”摆脱了从图书馆实体出发确定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方式,致力于抽象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这对打破传统图书馆学研究封闭的思维模式,推动本学科科学化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知识交流说”的不足之处在于,理论层次较高,它能涵盖图书、情报、档案等多门学科,但最后如何返回图书馆及图书馆学中,用于揭示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机理,却显得较为乏力。
1.5 信息资源说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可依劳动工具的演变划分为手工工具时代、蒸汽机时代、电脑时代。第一个时代的经济形态是以土地和人力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第二个时代的经济形态是以机器和资本为基础的工业经济;从20世纪晚期开始,人类经济形态正在向以知识信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过渡与转变。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导致社会信息的激增、信息技术的普及与知识经济的崛起。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从80年代起,欧美国家兴起了一个新的专业概念“信息资源管理”(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简称IRM),IRM理论认为信息是可共享的资源、财富,任何组织机构都应对它进行高效管理(与设备、资金、技术、人员及信息系统形成整体化管理),充分发挥其作用,以提高组织机构的效率和竞争力。
IRM理论形成后不久就渗入了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如美国80 年代图书馆情报学教育陷入困境之后,众多图书情报学院倒闭,但也有一些学校成功地引入IRM理论改进教学从而获得了生机。80年代末,IRM理论传入中国。进入90年代,国内一些高校图书情报学系纷纷更改为信息管理系或相关系名,并在教学中加大了信息资源管理的课程比重。1996年9月,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主办“96 信息资源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来自二十多个国家或地区的约五百篇论文,使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界对信息资源理论的研究达到了高潮。
美国图书馆学家切尼克(Barbara E.Chernik)在其《图书馆服务导论》(1982年)一书中曾说,图书馆“是为利用而组织起来的信息集合”,[25]并用了将近一章的篇幅来谈图书馆资源(Library Resources)问题。1999年2月,徐引篪、霍国庆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一书出版,该书明确表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动态的信息资源体系”。其基本观点是:(1)图书馆的实质是一种动态信息资源体系。无论是文献信息资源、口语信息资源、实物信息资源或多媒体信息资源,根据社会需要图书馆都可以收集起来,使之形成一个信息资源体系为用户使用;(2)信息资源体系是一个发展的有机体,它是动态的,有形成、维护、发展、开发四个主要阶段;(3)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图书馆,而图书馆的实质是信息资源体系,故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动态的信息资源体系。[26]
“信息资源说”将图书馆视为动态的、有机的信息资源体系,合理地继承了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提出的“图书馆是一个发展着的有机体”的观点。“信息资源说”力图揭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本质,这对我们认识图书馆以及发展图书馆学都有重要意义。“信息资源说”融合了系统论的思想,将图书馆学内容拓展到一个开放的社会信息资源领域,反映出更加宽广的学术视野。但是,“信息资源说”挟西风而传布,在很短的时间里几乎不可能经过“本土化”过程。
1.6 知识组织说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技术、多媒体技术、光纤与卫星通讯技术不仅将人们带入了网络时代,使社会知识信息的总量得以飞速增长,同时也使传播速度加快。随着高新技术、软件开发、管理策划、咨询服务、教育培训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知识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知识社会与网络时代,如何有效地组织、控制与传递知识信息,克服知识的无序状态,提高知识信息的利用率,增强组织与个人的核心竞争力,这已成为人们极为关注与急待解决的问题。
知识组织(Knowledge Organization)的概念产生得较早,1929年英国分类学家布利斯(H.E.Bliss,1870~1955 )便出版过《知识组织和科学系统》和《图书馆的知识组织》两部著作。1989年,国际知识组织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nowledge Organization,简称ISKO)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学会将创刊于1974年的《国际分类法》杂志作为自己的会刊,并在1993年将其更名为《知识组织》。该学会的宗旨是,联合国际力量,促进知识组织方法的研究、应用与发展,为献身于知识组织工具的开发、创新的学者提供交往与合作机会。除文献分类领域外,情报学界也对知识组织十分关注。如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B.C.Brookes)指出,图书馆中的文献分类是文献组织而非知识组织,知识组织是对文献中所包含的知识内容进行分析,找到相互影响及联系的结点,像地图一样把它们标出来,展示知识的有机结构和内在联系,为人们直接提供所需知识服务。知识组织可通过建立“认知地图”得以实现。而印度情报学家塞恩(S.K.Sen)根据英国学者道金斯(Dowkins.R.)“思想基因”的观点,提出知识组织可依“思想基因进化图谱”进行,即从文献中找出“思想基因串”,编制出新的概念索引供人利用。[27]1996年,美国情报学家德本斯(A.Debons)说:“知识组织将是下一个世纪人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我们这里所谈及的知识组织概念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分类技术,而是指更高水平上的知识组织。”[28]
我国有关知识组织的学术讨论始于80年代末期。如1989年至1990年马费成、胡昌平、刘植惠等撰文探讨了知识组织、知识揭示与知识基因的方法,丰成君则称知识组织是图书情报工作所面临的主要问题。[29]90年代初,青年学者刘洪波针对“知识交流说”的不足指出,知识交流理论对图书馆活动的外部关系给予了有力说明,但未能揭示出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本质和机理,图书馆内部活动的实质是知识组织。知识组织理论是知识交流理论的补充。[30]90年代末期,有关知识组织的文章再度多了起来。王知津撰文说,如何将无序的知识组织起来供人们使用,这是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31]知识组织不仅是对文献的组织,也包括对文献中“知识”的组织,即将客观知识世界中的最小知识单元、知识因子如何组织成一个有序的体系。知识组织的任务不仅要应付大量的知识,还要控制知识的增长。[32]而蒋永福则撰文称,图书馆是对客观知识进行专门组织和控制的社会组织,我们应从知识组织的角度理解图书馆学。[33]
“知识组织说”的提出,顺应了网络时代知识管理的需求。它成长于以往图书情报理论之中,文献分类理论、情报组织理论、知识交流理论是其三大来源。“知识组织说”从宏观上揭示出图书馆活动的本质,准确说明了图书馆的社会作用,成为转移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重要推力。“知识组织说”在肯定传统图书馆学以文献单元为基础的知识组织方法的同时,还探讨了以知识内容为基础进行逻辑分析的知识组织方法(如“认知地图”的建立),为图书馆学提供了纵深发展的广阔空间。当然,“知识组织说”目前在研究上还缺乏系统性,尚待进一步地整合与深化。
2 以往研究对象认识的范式特征
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从其研究客体的活动中概括抽象出来的。虽然对人们生活有影响的一切客观实在,哪怕轻微的影响、微细的事物,如一条蚯蚓、一片树叶都可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但科学却不能停留在对客体的表象描述上。图书馆学也是如此,它应从一堆事实、现象、技术、方法中,抽象、概括出研究客体的本质和规律,以此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科学研究活动就是科学工作者与科学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明确了科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就能准确地规范出本学科的研究内容,提炼出本学科的科学定义。
恩格斯说过:“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34]从总的发展进程看,以往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经历了从局部到整体、从经验直觉到理论抽象、从封闭研究到开放考察这样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2.1 整理总和说的范式特征
“整理总和说”流行于19世纪上半叶,它是以图书为研究客体而建立起来的学问(The Science of Books),虽然“整理总和说”首次提出了“图书馆学”的概念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但它与当时西方的著述史(Literary history,英语)、目录学(Bibliographi,拉丁词)、书志学(Bücherkunde,德语)等研究内容并无多大差别。“整理总和说”试图对著述史、目录学、书志学等进行整合,形成“图书馆学”(Bibliothekswissenschaft,德语),不过从其研究范式上看, 它依然是有关“图书整理”的,我们可以简称为“书皮图书馆学”。因为在“整理总和说”的影响下,图书馆工作对图书形式特征的重视往往高于对图书内容特征的重视,许多图书馆员为自己具有丰富的图书知识而自豪。1914年,美国图书馆学家毕晓普(W.W.Bishop,1871~1955)在一所图书馆学校发表讲话时,以生动的实例阐明图书馆员熟记图书的重要性,他对约翰·克里纳图书馆助理馆员霍普金斯能记住馆藏首批60万册书的每个书名而赞不绝口。后来毕晓普出版他的短论集时,就名之为《书皮学》(The Backs of books)。[35]
2.2 图书馆管理说的范式特征
“图书馆管理说”将图书馆学的研究重心从图书整理转移到了图书馆管理,这是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一次重要转换,顺应了各国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趋势。但在这种新的学术范式影响下,图书馆学把大量低层次的内容揽了进来,如打字法、书写法、印刷术、装订术、修补法、登记法、陈列法、出纳法、统计法、参观法等。许多图书馆学管理类、通论类教材或著作,甚至对书袋卡的制作、书目卡片与目录柜的大小、书架的高低、阅览桌椅的尺寸和布置等均一一叙及,配图说明,力图使学习者在最短的时间里全面掌握图书馆管理的一般方法,规范从事。因此,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我们可简称之为“尺寸图书馆学”。当然,图书馆学中原有知识含量较为专深的分支,如目录学、分类学等,随着研究的深入也越来越精密、复杂,但它们亦侧身于上述方法之中,使图书馆学内容一时良莠混杂。人们对图书馆学是否为一门科学的质疑,与此种范式的存在与扩张有着直接的联系。
2.3 图书馆事业说的范式特征
“图书馆事业说”将图书馆置身于社会环境中,更多地关注图书馆事业的宏观发展、图书馆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它阐明了社会需求是图书馆发展动力这一命题。但它却把图书馆学限定在“图书馆”这一客体上,如图书馆的性质、图书馆的职能、图书馆类型、图书馆网络、图书馆藏书、图书馆目录、图书馆读者服务、图书馆管理、图书馆现代技术、图书馆的未来等等,举凡有关“图书馆的……”才能构成图书馆学的内容。甚至隶属于图书馆学的众多分支学科也必须是“图书馆的……”,如图书馆管理学、图书馆统计学、图书馆建筑学、图书馆美学等等。此种思维范式,不但没能解决本学科学术层次过低的问题,同时还忽视了文献、知识、信息、情报、阅读等涉及图书馆命脉的一些基本命题。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我们可简称之为“机构图书馆学”。
2.4 知识交流说等的范式特征
从“整理总和说”到“图书馆事业说”,有关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们未能揭示出图书馆的实质。犹如各种各样的灯,虽然可以用一个抽象词汇“灯”来涵盖,但它并未揭示出灯的本质。灯的本质是“照明工具”。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知识交流说”、“信息资源说”和“知识组织说”克服了以往研究对象的认识局限,从不同角度努力探究图书馆的本质,因此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我们可简称之为“本质图书馆学”。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正是经过这些观念的突进与洗礼,才进入了与世界图书馆学同步发展的水平。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从“知识交流说”到“知识组织说”,它们均存在着认识上的不足。如“信息资源说”将图书馆看成是“动态的信息资源体系”,并以此为研究对象,它的不足表现在“信息资源”这一概念太泛,且有以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取代图书馆学或消解其个性的倾向。“知识交流说”虽然揭示了图书馆与社会的本质联系,却未能很好地解释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根本机制。“知识组织说”作为“知识交流说”的补充,无疑克服了上述缺陷,但所刻画的是图书馆内部活动过程的本质,忽略了知识受众,其哲学特征属“方法”而非“本体”层次,不是以某种“社会现象”当成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而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往往是由一种有“本体”意义的“社会现象”来充任的。[36-37]总之,科学研究是一个不断探索而逐步接近真理的过程,对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同样需要我们图书馆人发扬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的精神,才能逐渐逼近真理之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