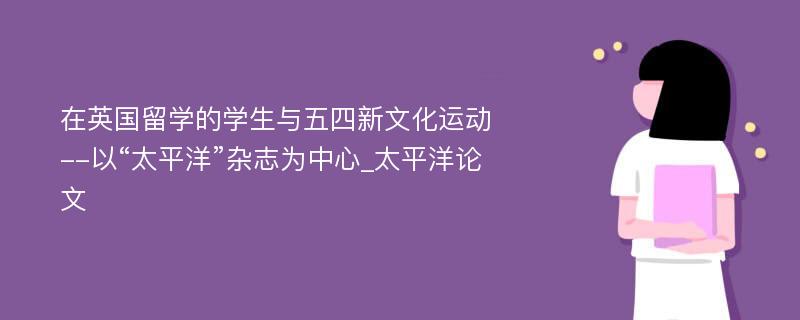
留英学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太平洋》杂志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洋论文,生与论文,杂志论文,文化论文,四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04X(2006) 02—0045—07
近代中国的改革运动由于各种因素而激发,在人事和思想方面,留学生及其所传播的域外思想对于清季民初改革运动的影响,至深且巨。但由于留学运动自身的复杂性,亦使得这种影响发生很大的分歧,不同东道国家给中国的改革运动烙下各自不同的文化模式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因子。周策纵先生在其经典之作《五四运动史》第二章分析“促成五四运动的力量”时,对日本、美国以及法国的中国留学生的思想活动及他们对于国内的影响,分别做了细致地分析和讨论,可惜于英国留学生的革新思想和文化主张未置一词①。显然,周先生忽视了英国思想对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的持续性影响,而晚近众多五四运动史的著作也未见对此的讨论。
事实上,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所谓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其实就是以大英帝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做榜样的,而在其中穿针引线的,非留英学生莫属。严复是梁启超所称赞的晚清思想界的一个“重镇”②,几乎所有严译名著都取自英国的资料;而辛亥之后,能够称得上舆论“重镇”的,亦是从英国学成归来的留学生章士钊,经他参与或主持的《民立报》、《独立周报》、《甲寅》杂志,遂成为民初影响巨大的政论刊物。但亦不必讳言,五四时代的留英学生,对于国内思想运动的影响力的确大大下降了,且参与程度似也不高,所以研究者的忽略也在情理之中。本文的目的不在于为留英学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而辩解,而是通过对留英学生于1917年3月创刊于上海的《太平洋》杂志中部分内容的讨论,来理解他们在五四时期的活动方式和文化主张,以此为五四思想文化运动提供一些新的面貌③。
一
民国初年留英学生的来源大概有以下三种:一是中央各部选派的官费留英学生,据1913年调查的“留学欧洲各国官费学生姓名表”,由稽勋局、交通部和海军部选派出的留英生有25人以上,以学习理工科为主,其中包括李四光、王世杰等人。二是各省陆续派出官费留英学生又有近百名,湖南省的名额共有20人,其中就包括了李剑农、杨端六、任凯南、向绍轩、皮宗石等人④。以上两部分人应占留英生总数中的大部分。三是在华英国基督教各教会创办的学校中所选派出的留英学生。据《曾宝荪回忆录》所记,当时在英国的中国基督教学生亦有自发的教会组织,并有刊物East in the West,主持人是巢坤霖、胡伟德,男生有梁宝畅、梁宝鉴、吴天保、傅铜等十多人,而女生则有胡素珍、何兴等7人⑤。可见教会学校的留英生亦不在少数。此外还有一些不易统计的私费留学生。
由于1912年底开始的反袁斗争的激化,大批新知识分子被迫流亡海外。这些海外活动者以政治边缘的方式参加反袁斗争,其中一大部分集中在日本活动,但又分化成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和黄兴的“欧事研究会”两个阵营,二者反袁的目标一致,但手段却有激进与温和之别。前者以《民国》为机关刊物,后者以《甲寅》为宣传其政治主张的主要阵地。而在法国的那批流亡者,如蔡元培、张继、汪精卫、吴稚晖等人,则是“欧事研究会”的成员,也为《甲寅》作文。但还有一批流落到英国的人员,就是上述李剑农、杨端六、皮皓白、周鲠生等人的活动,则鲜见人提及。
李剑农、杨端六等人均是湖南人,少年时即是湖南省立第一小学(即第一师范前身)的同窗好友⑥,然后一同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后即返回国内,在汉口创办《民国日报》;嗣因宣传反袁斗争,报馆被查封,他们几人亦为法国巡捕房所监禁,幸未被引渡给袁政府;获救之后,因得到黄兴的支持和协助,获得湖南省官费于1913年初始赴英伦留学,分别进入英格兰的伦敦大学和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留学生涯⑦。留学时间最长的如杨端六和周鲠生,直到1920年、1921年才回国,留英最短的李剑农则于1916年夏回国。留学期间,他们就是章士钊的《甲寅》杂志的成员,并且是《甲寅》后五期“论说”部分最重要的作者群。而《甲寅》停刊之后,即1916年间,李剑农、杨端六等人又在张东荪的《中华杂志》和政学会谷钟秀、杨永泰的《中华新报》上继续他们的报章活动。直到1917年3月1日,以李剑农为国内联络人,这批留英学生终于在上海组织了自己的刊物《太平洋》。他们发布刊物宗旨说:“本志主旨,在考证学理,斟酌国情,以求真是真非;于财政经济各问题,尤多论列;不为何种政团张其党势,亦不自立门户,别成一新政团之机关。”⑧
杂志的英文名是The Pacific Ocean,到1925年6月终刊时,共出版4卷42号。杂志采取当时流行的同人刊物的运作方式,在上海英租界白克路10号成立“太平洋社”,自行组稿和编辑,发行则归泰东图书局,在第五号,太平洋社宣布将编辑事务所迁至法租界恺自迩路长安里口261号。但从第二卷第一号起(1919年11月)改由商务印书馆发行。从第四卷第五号起(1924年3月),编辑所又迁往北京大学的社员住处——东吉祥胡同3号。《太平洋》前、后期的栏目设置有很大的变化。第一卷栏目最丰富,设有论说、海外大事评林、译述、通讯、文苑、小说、国内大事记等栏目,“外论坛、附录二目,随时增损”。但是不知何故,从第一卷第十二号起,《太平洋》不再保持以上栏目,只是形成以政论文、译述和小说为次序的编排。第四卷时,增加了“内外书籍绍介批评”栏目。
鉴于他们曾为《甲寅》主要成员,而且《太平洋》的办刊宗旨亦与其一致,所以当时就有人认为,《太平洋》杂志是《甲寅》的一个分支(另一分支是《新青年》),吴稚晖在为《太平洋》创刊而写的贺信中称:“盖《太平洋》之记者,皆即《甲寅》一部有名之记者。虽其离《甲寅》而独立,止以《甲寅》继续有待。”⑨ 报学专家戈公振亦云:《太平洋》“为《甲寅》分出之英法派人所编辑。”⑩
杂志的主编最初是由李剑农担任,大概第二卷第七期以后改由杨端六编辑,第四卷以后又由周鲠生及其北京大学的同事主持(11)。从《太平洋》的人员来看,它聚集了许多留英学生。除了李剑农、杨端六、周鲠生和皮皓白这4位核心社员以外,其他的留英学生,包括沧海、钱天任、周春岳、向复庵、吴稚晖、介石、陶孟和、朱东润、之奇、S.R.生、李寅恭、李张绍南、刘半农、邓大任、刘秉麟、宁协万、李敬思、梁龙、袁昌英、陈源、程振钧、刘光一等,均是这份杂志比较固定的作者。不宁惟是,当时一些官派留英学习科学的学生,如王世杰、石瑛、丁西林、李四光、王星拱等人,后来也在《太平洋》上发表文章。我们统计《太平洋》共发表“正式论文”402篇(12),以上留英学生31人,就发表了277篇,占总数的68.9%。其中周鲠生和杨端六的贡献最大,二氏共发表论文148篇,占总数的36.8%。由此可见《太平洋》的确是留英学生主导的一个刊物。
进而可知,留英学生以外,其他作者在《太平洋》上发表正式论文125篇,占论文总数的31.1%,甚至低于周鲠生和杨端六的文章数总和。但这部分的作者人数并不少,总计72人,可见不少作者仅发表1篇论文。其中比较重要的作者有; 李大钊、高一涵、彭一湖、汪精卫、胡适、郁嶷、刘半农、李凤亭、刘彦、曾仲鸣、杨少荻、阎一士、张务源、杨润余、胡庶华、王祉伟、杨树达、张效敏、燕树棠、江绍源,等等。
试分析《太平洋》作者群体的几个特点:第一,《太平洋》在创办初期是以英国留学生为主,中后期以后,尤其是五四以后,各社员陆续回国,他们亦成为当时新知识界中的成员,并联络海内外“学有根底”的学人为《太平洋》投稿和讨论议题,因此自第二卷以后,作者范围显著扩大,原来留英学生同人杂志的性质日益冲淡,变成“东西各国勤学之士暨国内名贤”同人杂志。第二,从人物谱系上看,《太平洋》和《新青年》分别是《甲寅》的支脉,二者既有分化之处,但作为五四时期新知识分子的共性亦很明显。他们基本上是19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代,有着“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历史记忆,在教育背景上,传统与近代新式教育参半,并大约同时从海外学成归来。故而《太平洋》亦属于五四时期新知识分子的一股倡导力量。第三,《太平洋》第四卷之后,社员与作者多为北京大学各个系科的教师。因其中一些人曾在吉祥大院共同租住一所民房,在学生中流传着“吉祥八君子”的说法(13),而鲁迅后来攻击的所谓“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也与此有密切关系(14)。
1924年12月,以“东吉祥派”为中心的太平洋社与创造社骨干之一郁达夫合作,成立了新杂志《现代评论》。随着大部分成员加入新份新刊物,《太平洋》亦决定解除与上海方面的出版关系,改由北京大学同人完全接手,并整顿编辑、出版等事宜。1925年6月,《太平洋》出完第四卷第十号,便告终刊,它的成员大多数作为《现代评论》的主要成员。关于两社的合作过程,郭沫若对此有过一段回忆:
太平洋社和创造社的合伙在当时的情势上是有充分可能的。太平洋社本来有《太平洋》月刊在商务出版,他们的构成分子大都还是有点相当学识的自由主义者,所发表的政论,公平地说,也还算比较开明。……我对他们虽然没有什么接触,但其中的主要角色多是湖南人,与仿吾有同乡之谊,而与仿吾的长兄劭吾又多是日本留学时代的同学。仿吾随着他的长兄留学日本时,是和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同居过的。其在达夫,则因为多是北大的同事,过从当然更加亲密。有这种种关系,加上我们自己本已有趋向政治的要求,两社的合伙,除掉我自己的一点点洁癖和矜持之外,几乎可以说是等于自然之数(15)。
二
《太平洋》属综合性的杂志,政论为主,文艺为辅。它对于五四时期的政治、法律、经济等问题的评论有其独特之处,而且从思想资源和政治主张上看,它延续了严复、章士钊等留英学生努力倡导的用英国社会政治模式改造中国的思想脉络,因此,它对于五四前后政治运动的影响,不容忽视。但这个主题当另文论述,本文试图从另一方面,即从《太平洋》正处于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当中作为视点,检讨它与这场运动有何关联。以下即以《太平洋》(尤其是第一、二卷同人留英时期)的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思想主张为中心,分析留英学生的活动方式及其与国内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如前所述,《太平洋》社员在英国几所著名大学学习政治、法律和经济等专业,并在若干年后取得了相关学科的硕、博士学位。但他们在留学期间与留美学生就有着共同的思想倾向,对教育和文化问题特别关注。他们首先现身说法,向国内青年传授自己的留学经验和体会。李剑农曾在《太平洋》上发表了他们社员之间的几封通信,以此向国人说明留英学生“苦学中之快乐”的情形。因为《太平洋》社员均是欧战发生前后到达英伦留学,但紧接着战事愈来愈紧张,加上1917年以后德国潜艇封锁英伦三岛,生活异常困顿。其中一位社员写信告诉李剑农说:欧战持久以来,“英国食物日缺,物价日涨,生活费大增”,房租、伙食费等比以前“多三分之一”,已无多余钱购买书籍,“衣服则除购冬衣一套外,皆破敝仍旧。三年前在伦敦所购之唯一外套,冬夏皆服之,今已破孔累累,犹日被以俯仰自雄于壹丁堡(即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之自由天地也。”而更糟的是,“公费恢复之杳无消息如故”,其中一人“久已一钱莫名矣”。但他的学习却不因此落下,反而于高等经济学一科,在去年年终试验中“倖列第一”,力压前年的冠军亚历山大女士,自称是“老夫战胜女将军”(16)。
李剑农之所以将他们的私函揭示于《太平洋》,“一欲示国内学生以青年奋斗之范,二欲使政府改良教育行政之方针”。所以他在该信后作按语说:某君“癸丑由某省政府咨送英伦,嗣因某省都督易人,将前督之案,全体推翻,不分良莠,一律裁撤,某君誓非学成不归,即以撤学之川资与同社某君同佃一小舍,节用苦学,后闻苏格兰居食较廉,始迁往壹丁堡,入该处大学,极为该校教授所奖许,稍暇则作文寄售各杂志一为生,今已三年又半矣。去冬闻某省有恢复留欧未归学生公费之议,并闻已由该省政务会议议决,自今岁正月起寄费往欧,不知何故忽来变议,延搁至今,闻系格于中央新定之补费章程。”各省留欧学生的费用竟受中央的无端干预,这令本就对于中央集权主义持反对意见的李剑农更加愤慨,他接着说:
按某省旅欧学生共仅数人,皆系青年奋斗、前途多望之士,恢复原有省公费,本属省政府已成之事实,与中央无干,何须彼此互为轇輵,延误青年。按今日当局心理,事事梦想中央集权,事事欲干涉,其极也。一事不能办,彼此相干涉,彼此以虚文程式相拑制,彼此不负责任,延误要政,不知凡几,学生补费一事,犹其小焉者也。夫教育行政,实无中央集权之必要,非徒无必要,且为有害,征诸学术发达之英美,未有不取地方自由主义者也。今日各省之骄兵悍将冗滥糜费,一任各督军之自为编制,语对外则不克自由调遣,供国防之急需,语对内则徒有扰骇愚民之害中央竟无如何,独于遣送学生一事,则惟恐各省之稍有滥费,当集权者不能集,不当集者则百计集之。愚窃为当局不取也。今因某君函,附言于此,顾世之留心教育者,一垂察焉(17)。
这是从政治的角度对于教育问题的一个反思,但在更多情况下,《太平洋》是从社会的角度,发出他们对于教育问题的倡议的,其热衷程度,非当时正将绝大部分精力注入反传统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新青年》所能企及。他们所讨论的问题包括小学义务教育、大学学制、女子地位及其教育问题,以及科学教育、实业教育等问题,除了第一个问题是来自一位留日学生的议论,其余问题均是留英学生自发倡议的。不宁惟是,他们尤以世界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教育改革问题,并结合欧战后的新教育趋势来为中国教育改革指导方向。
已有七、八年在英伦学习经历的李寅恭、张绍南夫妇,对于欧洲新教育的趋势深有体会,遂借《太平洋》向国人作了有力的发言。在《论今日教育之趋势》中,李寅恭指出,欧洲各国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即重视“使国中男女青年,于智育上切实发展,而国势乃有恢复之望”,德国更是喊出“救亡惟教育之语”,故各国对于教育问题即屡有改革方案的引入。而欧战以还,英、美、德虽陷于战争环境,但对于教育的重视丝毫不松懈,并着手制定教育改革计划。这让李氏深切感到战后“世界教育大革命,已毕呈于吾前”。他接着指出,虽然战争使宗教教育的观念在下一代人的信仰中一落千丈,亦为欧美社会教育的一大损失,但它们早已崇尚“实学”的风气,则造就了大量科学发明家,并取得了巨大的科学进步。具体地说,欧美社会已意识到,仅仅普通教育已属不足,而应引入科学教育于普及教育之中(18)。
本着这个观念,李寅恭对于国内新成立的科学社及其刊行的《科学》杂志,以及提倡新文学的《新青年》杂志,表示了期望和赞同的态度。因为他相信这二者的结合,使国内少年“既能为清白文字,则从事科学,不虑不解译名,亦不难学制译名,而我之文学亦日富矣。”但他对部分人固守“闭户造车,出门合辙”的传统教育,则持强烈批评态度。因此,他提倡的是一种新教育,要求国人拥有“教育为人类进化之原理”的信念,并能够深刻理解欧美列国“日日所竞争之科学教育”的趋势,“自是以往,如欲追随世人,出我不开化之阶级,则科学为唯一之事业,有待于我,亦时事之所需求也。”(19)
于政治经济学研读颇深的杨端六,则发表《实业前途之曙光》一文,提议真正振兴实业,重视发展实业教育,以为实业长远发展提供技术骨干和熟练工人。他指出,现今世界各国除了极不开化者外,莫不为长足进步,“乃还顾吾人,犹内斗未已也,实业迟迟不进,政府焉能辞其咎?”但是杨氏深明当下无论如何指责政府,也仍然不可恃,因此提议离开政治问题不论,由有力之实业家负起社会责任,“挟不屈不挠之毅力以打破政治上之障碍”。不倚靠政府而独立发展中国实业,成效如何,自有后来事实证明(20),但杨端六确实相信当时中国实业家能够担当此任。他指出,实业家的自觉行动不仅是于资本、原料、劳力等实业发展的必须要素上考求,更应该着眼于为实业界造就“特出之人物”。特别人才从何而得?“是不外乎教育与经验”。依据英国和德国实业教育的经验,杨端六向中国实业界提出了他久已拟就的实业教育方案:
吾尝有一未曾发表之议案,欲国内大实业家提倡之(前汪精卫先生过英时,曾与言及,颇以为然)。即于每年赢利之内,提出若干,作为养育人材费。其办法或在本地设立工商学校,或选送东西洋留学生,或独立行之,或联合同类之公司行之,均听各公司之便。开办之初,股东或少受红利之分配,然“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公司之发展,正惟此项新进人材是赖,目前之小小损失,毫不足计。英美实业教育之发达,不仅政府提倡之力,工商业者亦与有劳焉。常有大公司寄赠款项若干与某某大学作为奖金。无论何学生或已卒业学生;苟有应选从事一特定科目之研究者,则以奖金给之。奖金之名额,或一名或数名,奖金之继续,或一年或数年,均酌量情形定之。吾国大公司可仿此办法,更加以扩充,则公司事业不蒸蒸日上者,吾不信也(21)。
再以女子教育问题为例。《太平洋》团结了数名留英女生,张绍南、袁昌英即为其中的佼佼者。正是基于对自身经历的深刻体会以及当时欧洲社会思潮的刺激,她们在《太平洋》上呼吁女子社会地位平等,女子与男子同样出洋留学,以及国内开放女子大学或实行男女同校等要求。张绍南在《英国女子教育及其生活》中指出,英国的平民女子“特具一种独立之精神”,为老大中国人所不能想象。她说:在英国“有进取心之女子,尽出贫家,及敏而勤学者,亦多来自贫家,……欧战以还,贫女生活,途径愈辟,国中凡百职务,悉仰藉女子承乏。”(22) 用英国女子自立、自主的新形象昭示中国女子的努力方向。
一位未具名字的英国留学生指出,今日世界大势所趋,是女子的社会地位蒸蒸向上,到处与男子享有同等权利、均等机会,“所谓男女平权,在欧美文明国家,已成事实。”但中国女子问题却因传统社会习惯的桎梏而踯躅不前,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女子自身对于打破现状、超脱社会专制,跻身与男子同等地位的问题尚未有思想上的觉悟。袁昌英亦同意,中国女子欲在政治上、法律上及社会上,实际争得男女平权,“则非首从教育平等之问题争起不可”。但她还指出,从教育上争取男女平权,不仅须普及初浅及中等女子教育,而“高等女子教育,万不可忽视”。因之,她主张在国内现有条件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男子大学中开放女禁,实行大学男女同校制度(23)。袁昌英还强调女子不仅有权利接受现代教育,亦可与男子有同等权利出洋留学。她说,女子到文明国家读书可以培养出一种活泼精神,“一种合法合理的自由和独立精神”。她说:
中国的女学生对于自由、平等、独立等字样,是很熟悉的。但是怎样叫做自由、平等、独立,其中所含蓄的精神,确未必有十分的研究。这种精神到底如何,这篇文字上是不能讨论的。但是这样的精神是很要紧的。并且非亲眼观察,是难得其真象的。数千年间,中国女子关在闺房之内,不准出门,现在忽然开放,行为自然难得其中。大半都是对两头走:有的说,我们现在是自由,有什么事不可做?所以他们万事都要来试一试,到了末了,或不能收拾,以至于身败名裂;有的还把旧日做小姐的习惯拿起来,万事都不敢做,万事非依赖他人不可。这样过于激烈、不正当的自由和这样腐败不堪的守旧,都是我们新中国所不要的状态。我们所要的是一班稳健的女子去改造女子社会,这样合中的德行,这样健康的活动,非到这个文明的境地亲身考察是很难得到的(24)。
《太平洋》对于教育问题的批评和倡议既述之如上,可知他们所提倡的新教育与五四新文化潮流是并行不悖的,可以说对新思潮具有推动和指导作用。他们对于教育问题的有些批评甚至能够直接推动国内有力人士的反思,如周春岳以投函的形式发表了《大学改制之商榷》一文,对于1917年9月27日颁布、由蔡元培等人参与修订的“大学改制方案”表示不同意见,即很快得到蔡元培的答辩书(25)。因此,《太平洋》的教育观点在国内亦已形成一定的影响力,而五四之后,《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则又在美国人杜威、孟禄等影响下,真正开始阐述他们的新教育方针和改革目标。教育改革运动亦由此而兴起,内容包括教育基金独立、职业主义教育、平民主义教育、男女同校教育,等等(26)。尽管这些均是仿效美国模式的教育改革主张,但亦与前述《太平洋》所阐述的教育观点相一致。
下面再述《太平洋》的文化观。
相对说来,在《太平洋》早期,除李剑农以外,其他社员均在海外,对于国内思潮的感受尚有些隔膜,他们所提出的革新观点,很多情况下是由于外国新思潮的牵引以及他们自己的学术研究视线所引发的思考。但在《新青年》所领导的反孔运动、文学革命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背景下,《太平洋》明显有同样的趋向。如它是五四之前最早一批宣布使用白话文与新式标点符号的刊物,同时它亦是反孔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但比较《新青年》激烈反孔的态度,《太平洋》对于孔子的批评却是相当地温和,李剑农的话可以代表《太平洋》的非孔态度:
仆窃以为孔子非惟未尝集学说之大成,并未尝集道德之大成;非惟孔子未尝集道德之大成,即世界之群圣,未有集道德之大成者;非惟世界已往之群圣,未有集道德之大成者,即将来能否有集道德之大成者,出现于世,亦属疑问。何也?道德之为物,乃变易不可名状,此邦以为道德,彼邦乃以为不道德,先世以为道德,今世乃以为不道德。今世以为道德,将来又将以为不道德(27)。
这种态度的背后是一种与胡适的思想方法相差不远的“经验主义”,是对任何一种先验的或超越的知识的高度警惕。
论者指出《新青年》的言论态度可用八个字归纳:“议论激昂,态度刚愎”。这确实言之有据,如他们在反传统时喊出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打倒孔家店”等;又如陈独秀在确立文学革命方向时声称:“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28) 相比之下,《太平洋》温和、持重的言论态度在当时言论界颇为少见,所以上海的读者有这样的评价:“贵杂志产生,与《甲寅》取同一之态度,注重通讯一门,无愧为全国舆论代表,而所持论,尤极纯正。”(29) 但不可否认,如另一位论者指出,若不是《新青年》诸人用宗教家的态度来武断地宣传新思想,则新思想能否一出就震惊世俗,引起绝大的反响尚未可知(30)。惟其如是,武断的《新青年》与严守论理的《太平洋》,这一北一南的同人刊物,一个冲锋,一个维持阵地,可见物各有其短,贵用得其当罢了。
实际上,《太平洋》的文化观是一种英国式的调和主义,其思想资源主要来自英国思想家斯宾塞、莫烈等人的调和思想,依据斯、莫二氏的理论,李剑农指出“调和”是社会进化的一种现象,“故调和精要之所在,特为新者不可以锐进过猛之势,使若枘凿不相容,决非使新者自毁其新机,削其方枘,以入于圆凿也。”(31) 英国文化的发展方式,以和缓、平稳、渐进为其主要特色,这亦渗透到了留英学子的思想底蕴里。以下再通过两个具体例子,来了解《太平洋》以“进化”和“新机”为方向的调和主义文化观。
留英期间,李寅恭、皮皓白、陈源和杨端六4人曾造访英国著名的汉学家解尔斯先生(晚清时曾任英国驻华领事),他们了解到解氏所在的剑桥大学图书馆里收藏的中国典籍至为丰富,而他有意将这些典籍陆续整理出版,并翻译成英文,无奈个人资金有限,无法独立承担,希望中国政府能提供资金方面的帮助。李寅恭等人认为这的确是传播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机会,“欲传播我国之文化,我国民责无旁贷,进行之道,不外二种:一使外人传习我语言文字,二将我典籍译成西文。二者异曲而同工,理宜兼程而并进,然事体重大,非一二人所能举,宜合中外有志之士,协力图之。”于是他们联名通过《太平洋》向国内发出一份通告函,希望获得国内资金以资助解尔斯出版中国典籍的计划(32)。此事后来的成效如何,并不可知,但由此反映出《太平洋》人依然认可中国文化学术上、思想上的价值,并不是如激进主义者所主张的极端的反传统主义。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们仍有信心,而对于新文化人的现代学术成果,他们亦取认同和支持的态度。当胡适发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墨家哲学》两篇学术论文后,李剑农即征得他的同意,在《太平洋》第1卷上先后转载。 而那本奠立胡适学术地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甫一出版,李剑农立刻就去买来,“费了一天两晚的工夫,把他翻过一遍”。本来《太平洋》第1卷是没有“介绍书报”栏目的,但他读了这本书之后,“忍不住就要提起笔来写几句话,把这本书介绍到各位,使各位不曾在北京大学听过讲的,也来赏识一番。”李氏的评论有三点:
(一)我觉得这本书,确实是胡先生费了很精密的心思去研究才著成的,并不是书贾作投机生意,请人抄袭的,也不是失业的文人,因为没有钱用,东涂西抹,拿日本人的“唾余”作他们的赚饭品的。(二)近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人虽然多,从没有哪个指示我们一个门径、一个研究方法。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诸子学,算是有大发挥的,但是我们看了他的书仍旧“不得其门而入”,虽然说是我们的资性太蠢,又没有学问,但是那‘先觉’要来‘觉后觉’,也要有个‘觉’的方法。看了胡先生这本书,就觉得我们有个‘觉’的方法。(三)胡先生提倡白话文学,我也是赞成的,……但是那反对白话的人,总不相信。现在胡先生这本书,就是用白话著的,中国古代哲学,算是最高深的学理了,胡先生竟用白话把他说出来使我们懂了。觉得从前反对白话的人,失了一个证据(33)。
由于有胡适的这个学术“典范”,新文化运动算是真正有实绩的运动,而对于反击国粹派或保守派的攻击也更具说服力。李剑农亦以此反击守旧派对于胡适的攻击:“还有一层,自从胡先生提倡白话文,在《新青年》做了几篇指导青年、不合‘国粹派’的胃口的文章,那‘国粹派’的人就视他为外道邪教,甚至于想用不正当的方法,来摧残北京大学的生机,现在我要请‘国粹派’的先生也平心静气,把胡先生这本书过细一读,看胡先生到底是外道邪教么?”(34)
以上可见,《太平洋》与《新青年》对传统文化的革新思想取向上具一致性,但前者的态度稍持调和主义,注意处理好传统与变革的关系,但又不“抱残守缺”。在五四时期激进主义思潮的背景下实属少见。
综合以上的讨论,可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太平洋》作为留英学界的一股知识力量,同样对这场运动予以积极的推动和引导,其背景及所提供的新思想,与以《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指导力量并无二致。换言之,《太平洋》亦介入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新思想运动,并且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一点或为论者忽视,但通过对《太平洋》与新文化运动之间联系的讨论,却能使我们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新面貌。
注释:
① (美)周策纵著、陈永明等译:《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8月版,第29—55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③ 就研究状况来看,目前只见到《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三联书店1979年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上各有一篇介绍《太平洋》的文章。两文均以摘述原文的方式,大体介绍了《太平洋》的“调和”精神、改革政治的具体主张、重视国际形势和中外关系、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态度等内容。但两者对于《太平洋》杂志的创办、发行、运作及同人群体均语焉不详,对于它的思想的评论也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另外,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本论述近代中国留英教育的专著——刘晓琴著《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已经注意到《太平洋》杂志为留英学生所创办的刊物,但著者未对其做进一步的研究,仍然依靠上述两篇介绍性文章来了解这份杂志。见该书第280—281页。
④ 刘晓琴:《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第239—240页;元青:《民国时期的留英学生与中英科技交流》,《历史教学》1997年第8期,第13页。
⑤ 《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9—60页。
⑥ 参见周如松:《周鲠生先生传略》,收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5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页。
⑦ 参见杨静远:《我的父亲杨端六》,《万象》第6卷第7期,2004年7月,第125页。
⑧ 《本志宣言》,《太平洋》第1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
⑨ 吴稚晖:《通讯·杂志界之希望》,《太平洋》第1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第2页。
⑩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页。
(11) 由于《太平洋》没有标明主编名字,具体分工不易了解,但杨端六发布的一则启示却能提供部分信息,他的启示如下:“鄙人自民国九年回国以来即在上海办事,当时留欧同学多未言(归),旋以事务之便宜,嘱鄙人担任《太平洋》杂志编辑事,阅时三载,虽未能增进本杂志之精神而勉强支持,得留其驱壳者,仍赖乎海内外同志之襄助。近以同学多归,亟思整顿。第一,扩充内容;第二,按期出版。本杂志前途实有无穷希望,惟是鄙人学力既形竭蹶,他务亦日见彷徨,深恐有碍本杂志之进行。特此宣告,自第四卷起,所有本志编辑责任均归北京同人负之。鄙人仅为普通献稿者之一人,嗣后,凡关于投稿通讯等事均请直接寄交北京后门内东吉祥胡同三号《太平洋》杂志编辑所可也。谨启。”见《太平洋》第4卷第5号,“封二”。
(12) 仅包括论说文、评林、译述三种文类,不计通讯、书评和小说类文章。
(13) 参见王书庄:《怀念丁西林老师》,收入孙庆升编:《丁西林研究资料》,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第48页。据李书华回忆,1920年代初住在北京后门内东吉祥胡同里的北大教师包括他自己、王世杰、周览、李鳞玉、李四光、丁燮林、皮宗石、陈源、石瑛等人。参见李书华:《七年北大》,收入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3页。
(14)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太平洋”,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33页。关于“东吉祥派”的描述,亦可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第145、146回,“女师大与东吉祥”(一)、(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0—507页。
(15)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篇》,收入《郭沫若全集》第12卷,“文学编”,第211—212页。
(16) 本社某君:《通讯·苦学中之快乐》,《太平洋》第1卷第2号,1917年4月1日,第20页。
(17) 李剑农按本社某君:《通讯·苦学中之快乐》,《太平洋》第1卷第2号,1917年4月1日,第20—21页。
(18)(19) 李寅恭:《论今日教育之趋势》,《太平洋》第1卷第5号,1917年7月15日,第1—2、3—4页。
(20) 在1920—1923年间,在缺乏强有力国家政权干预的情况下,中国实业家和商人们幻想通过自治运动,摆脱官僚的束缚,获得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的自由发展。上海商界甚至尝试创立一个“商人政府”以代替虚弱的国家政权,但这些自由主义运动都不可避免的失败了。平心而论,这股思潮与上述杨端六的观点不谋而合,但我们亦不必就此认为杨端六已自觉地成为中国实业阶级的利益代言人了。关于中国商人的自治运动,参见(法)白吉尔著,张富强、许世芬译:《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9—245页。
(21) 端六:《实业前途之曙光》,《太平洋》第1卷第11号,1919年4月15日,第2—7页。
(22) 李寅恭:《通讯·英国女子教育及其生活》,《太平洋》第1卷第8号,1917年11月15日,第11页。文中附张绍南回复家乡某女子询问英国女子教育及贫女生活书。
(23) 袁昌英:《通讯·大学男女同校说》,《太平洋》第2卷第5号,1920年6月5日,第1—2页。
(24) 袁昌英:《论女子留学的必要》,《太平洋》第2卷第8号,1920年12月5日,第4—5页。
(25) 周春岳:《通讯·大学改制之商榷》,《太平洋》第1卷第9号,1918年1月15日;蔡元培:《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太平洋》第1卷第10号,1918年7月15日,蔡文系李剑农转录自《北京大学日刊》。
(26)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375—376页。
(27) 记者(李剑农):《通讯·答徐天授》,《太平洋》第1卷第2号,1917年4月1日,第14页。
(28) 参见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32—533页。
(29) 徐天授:《通讯·孔道》,《太平洋》第1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30) 常乃惪:《中国思想小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
(31) 剑农:《调和之本义》,《太平洋》第1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第2页。
(32) 李寅恭、皮宗石、陈源、杨冕:《通讯·剑桥大学图书馆》,《太平洋》第1卷第7号,1917年10月15日,第14—15页。
(33)(34) 李剑农:《介绍〈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太平洋》第1卷第11号,1919年4月15日,第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