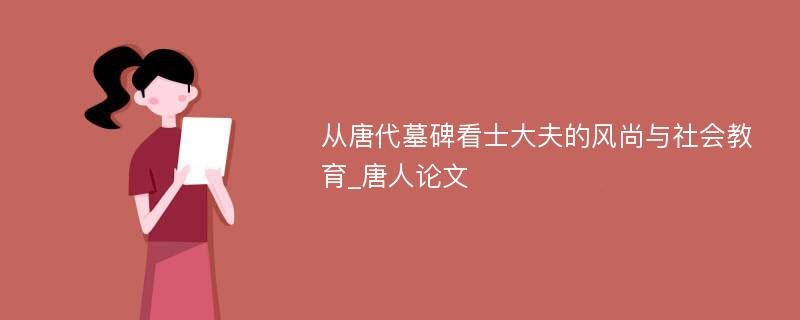
从唐人墓碑文看士女风尚及社会教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女论文,唐人论文,墓碑论文,风尚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7)04-0070-05
墓碑文是适应古代殡葬制度而产生的应用文,这里包括墓志铭和墓表文。《文心雕龙·诔碑篇》追溯其产生过程曰:“碑者,埤也。上古帝王,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可见,墓碑的来历原是宫室、宗庙前立的石柱,本是用来拴牲畜的,后来发展到在石上刻字记事,进而产生了碑文。刘勰对墓碑文体的写作标准也作了规范:“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1](卷三)墓碑文属记事文体,主要记述死者生前事迹,这就要求作者具有史才:因为是悼念死者的,又免不了要抒发称颂之情。
自汉代起,墓碑文逐渐多了起来,如蔡邕、孔融等人都是当时的著名写手。但汉代的墓碑文尚能“叙事也该而要”,“缀采也雅而泽”[1](卷三)。到东晋孙绰的碑志文,则开始变得“辞多枝杂”。《晋书·孙楚传附子绰传》载:“绰少以文才垂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足见孙绰为当时的不少名士写了“辞多枝杂”的墓碑文。由于民间殡葬时树碑立传风气的渐趋盛行,各朝的统治者曾不断地发布一些禁令来制止这种风气,如《宋书·礼志二》记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武帝这一诏令显然是倡导丧葬尚简的。到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2](卷十五《礼志二》)这次晋武帝的诏令里就明显包含着对碑文的褒美虚伪趋尚的反感。但是,诏令往往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失去其原有的威严和作用,所以即使在实行禁令的晋代,“大臣长吏,人皆私立”碑文的现象依然存在。到南北朝时期,由于骈体文的盛行,墓碑文的写作也免不了受到这种注重辞采、讲究声韵的文体的影响,极尽颂扬浮华之能事,以至于遭到时人的批评。如《洛阳伽蓝记》卷二九记载了隐士赵逸对当时墓碑文的不满:“‘人皆贵远贱近,以为信然。当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问其故。逸曰:‘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联系前文晋武帝对碑志文的禁诏,我们不难想见当时流行的墓碑文夸大谀美的风气,所以赵逸的批评也并非言过其实。尽管墓碑文经常会遭到人们的诟病甚至朝廷的禁止,但这一文体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反而越来越兴盛。到唐代,更是蔚然成风。
唐代的墓碑文不再像前朝那样是达官贵人才能享有的专利,而是几乎普及到了市井百姓,因此,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前朝,并且在内容上也出现了许多新变化。
首先是墓主生前自撰墓碑文的现象十分普遍。唐前,自撰墓志铭见于记载的很少,据《魏书》卷十五记载,北魏宗室元景临刑前曾自作墓志铭,但只是寥寥几语:“洛阳男子,姓元名景,有道无时,其年不永。”[3](卷十五《常山王遵传附忠子寿兴传》)而唐代自撰墓志铭的著名士人就有王绩、傅奕、严挺之、白居易、颜真卿、杜牧等,这些墓志不仅记载他们各自的身世事迹和著述,而且能总结其性情品格,为后人了解墓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最直接、最真切的资料。如王绩的《自撰墓志铭》这样写道:“王绩者,有父母,无朋友,自为之字曰无功焉。人或问之,箕踞不对。盖以有道于己,无功于时也。不读书,自达理,不知荣辱,不计利害,起家以禄位,历数职而进一阶,才高位下,免责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于是退归,以酒德游于乡里,往往卖卜,时时著书,行若无所之,坐若无所据。乡人未有达其意也。尝耕东皋,号东皋子,身死之日,自为铭焉。曰:有唐逸人,太原王绩。若顽若愚,似矫似激。院止三径,堂唯四壁。不知节制,焉有亲戚?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无思无虑,何去何从?垅头刻石,马鬣裁封。哀哀孝子,空对长松。”[4](卷一百三十二)王绩在墓志中把自己放达自适、简傲嗜酒的个性完全凸显了出来,其口吻虽有些自我解嘲之意,但他不适于时、不达于意的牢骚和不遇,表述的还是很明显。又如白居易自撰的《醉吟先生墓志铭并序》,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是“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4](卷六百七十九),将自己外儒内释的复杂思想如实托出,这种自我评价及自我绘像的效果,可能比让他人事后对墓主进行隔靴搔痒的盖馆定论要真实得多。
其次,小人物和女性墓碑文增多。虽然唐代立碑刻文也有一定的制度限定,如元稹在为南阳王张奉国所撰写的《南阳郡王赠某官碑文铭》中,就记载当时制度说:“唐制三品以上,殁既葬,碑于墓以文其行。”[4](卷六百五十四)但人们并不受其约束。一些坎壈小吏或没有社会地位的妇女也都可以树碑立传。在《全唐文》中,这样的墓碑文占很大的比重,如杨炯的《从弟去溢墓志铭》、《从弟去盈墓志铭》、《从甥梁墓志铭》,韩愈的《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处士卢君墓志铭》,柳宗元的《筝郭师墓志》,李翱的《故处士侯君墓志》等。给女子立碑刻铭的也很多,如张说的《司属主簿博陵崔讷妻刘氏墓志铭》、《荥阳夫人郑氏墓志铭》,柳宗元的《朗州员外司户薛君妻崔氏墓志》、《太府李卿外妇马淑志》等。唐人甚至可以因为一个梦而为相隔几代的前朝女子撰写墓志,如褚遂良的《故汉太史司马公侍妾随清娱墓志铭》就是为汉代司马迁的侍妾所写,文中说到:“永徽二年九月,余判同州,夜静坐于西厅。若有若无,犹梦犹醒,见一女子,高髻盛妆,泣谓余曰:‘妾汉太史司马迁之侍妾也。赵之平原人,姓随名清娱。年十七事迁,因迁周游名山,携妾于此。会迁有事去京,妾侨居于同。后迁故,妾亦忧伤寻故,瘗于长乐亭之西。天帝闵妾未尽天年,遂司此土。代异时移,谁为我知血食何所?君亦将主其地,不揣人神之隔,乞一言铭墓,以垂不朽。’余感寤铭之。”[4](卷一百四十九)可见,褚遂良就因为司马迁的侍妾托梦而为之撰写了这篇墓碑,这种奇特的写作缘起,使这篇墓志铭不免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再次,文学色彩增加。墓碑文的写作体制有一定的模式,刘勰认为要“资乎史才”。然而,虽然墓碑文记载的是人物事迹,但它与史传中的人物传记还略有不同。岑仲勉先生的《贞石证史》就区分二者说:“夫碑志与列传,志趣有异。前者为私门撰述,胪举仕履,人必不责其过繁;后者乃举国官书,满纸升除,群将诋为朝报。”可见,在墓碑文中“胪举仕履”、“满纸升除”是被人们认可的。因此,长期以来这类文体就形成了“铺排郡望,藻饰官阶”的创作套路。但是唐人的墓碑文能变化出新,不仅遵循史家实录的原则,还能润以文学之笔,刻画人物的音容笑貌,神情个性。唐代以碑志文而名家的如张说、李邕、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都属这方面的能手。如张说的《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渲染墓主王方翼热海之战的英勇:“热海之役,流矢贯臂,阵血染袖,事等殷轮,帝顾而问之,视疮欷歔曰:‘为国致身,乃吾亲也。’”[4](卷二百二十八)李邕的《左羽林大将军臧公神道碑》描绘墓主臧怀亮的倜傥英姿:“公濬发卓荦,雄举倜傥,风雨之气,凛凛出徒;金玉之声,锵锵激物。”[4](卷二百六十五)白居易的《安定皇甫公墓志铭》赞颂皇甫镛的气宇轩昂:“公为人器宇甚宏,衣冠甚伟,寡言正色,人望而敬之,至於燕游觞咏之间,则其貌温然如春,其心油然如云也。”[4](卷六百七十九)他又在元稹的墓志中渲染其为同州刺史时,如何关心民生疾苦,离任时百姓的恋恋不舍:“始至,急吏缓民,省事节用,岁收羡财千万,以补亡户逋租。其馀因弊制事,赡上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将去同,同之耆幼鳏独,泣恋如别慈父母,遮道不可通,诏使导呵挥鞭,有见血者,路辟而后得行。”[5](卷七十《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元公墓志铭》)其中,在墓志文中描绘人物最生动奇特的要推韩愈。他的碑志文虽然也有被人讥为溢美隐恶的“谀墓”之作,但不少作品能注意剪裁,在精辟的议论、真挚的抒情中巧于描摹,善于刻画人物,突出个性,使其成为“一人一样”的生动传记文。如常被学者们举为范文的《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中的王适,韩愈通过对其骗婚娶妻过程的白描,形象地勾勒出了一位“怀奇负气,不肯随人后”的奇男子形象。其《幽州节度判官赠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篇幅虽短,但突出墓主张彻死前的骂词以刻画其“义士”的个性:“君出门,骂众曰:‘汝何敢反!前日吴元济斩东市,昨日李师道斩于军中,同恶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鸱鸦。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骂。众畏恶其言,不忍闻,且虞生变,即击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绝骂,众皆曰:‘义士义士!’或收瘗之以俟。”[4](卷五百六十四)此外,韩愈被人称道的《柳子厚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等,也都能“行文叙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袭”。总之,唐代墓碑文对人物的文学性描绘的逐渐增多,既提高了这类应用文的审美价值,也成为许多学者将其列为文学作品的重要依据。
唐代墓碑文如此繁盛,作者如此之多,墓主对象如此之普及,其中对人物品行、道德风范的描述自然就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特征,我们不妨从这些墓碑文中看看当时社会的这些时尚:
(一)男子的典范。其一,崇尚性情温良。在唐代墓碑文中,对墓主温和性格的肯定十分普遍,如张九龄《故瀛州司户参军李府君碑铭》称赞墓主李元祐:“公懿列无忝,雅有风度,体和而韵,缗之以丝;性婉而文,受之以采。故好学不倦,而坟典必精;虑善以动,而规矩皆中。悉心存乎道义,余力文章,人以美谈。”[4](卷二百九十二)靳翰的《大唐故朝散大夫护军行黄州司马陆府君墓志铭》赞美墓主陆元感:“君生而敏慧,长而温良,识清朗而惟深,体矜重而不野,宗族爱而加敬,乡党狎而愈恭。”[4](卷二百七十九)许鼎的《通和先生祖君墓志铭》对其墓主也有类似的描绘:“先生讳贯,字子元,范阳人。先生性宽平,家人州里,莫得见其喜怒长短。”[4](卷八百四十二)诸如此类,都是对于风雅温婉的男性品格的赞美。其二,崇尚宽以待人。如元稹的《唐故中大夫尚书刑部侍郎赠工部尚书李公墓志铭》记述墓主李建:“于朋友间好尽言,然而未尝以胜负形喜愠。进退之际,几微不苟,受官法与操行牢不夺,亦未尝皎皎自辨。性洁廉,而沓贪有才者皆进之,考行取友甚峻,能铢两人伦,而滔滔者莫见其厚薄,终肯延荐人,常为讳避其短。”[4](卷六百五十五)杜牧《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赞颂牛僧孺:“公始自河南荐乡贡士为郎官,考吏部科目选,三开幕府,中丞宰相外,凡取六十余人,上至宰相,次布台阁,皆当时名士。每暇日燕语寮吏,必言古人修身行事,旁诱曲指,微警教之,不以己所长人所不及裁量高下,以生重轻。”[4](卷七百五十五)这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品德在唐代墓碑文中也是屡屡被称道弘扬的。
如果说上述男子的性情特点是对儒家君子风范传统美德的承继,那么,唐代开放的社会环境造就的士人张扬个性、简傲狂放的时尚也体现在墓志文中。如张九龄《故辰州泸溪令赵公碣铭》称赵公“刚洁不群,精明独断,非义所在,不以利污名;非礼所安,不以迹伤教;
有立卓尔,童丱而然”[4](卷二百九十二)。韩昶《自为墓志铭》评价自己“好直言,一日上疏,或过二三,文字之体与同官异。文宗皇帝大用其言。不通人事,气直,不乐者或终年不与之语,因与俗乖,不得官”[4](卷七百四十一)。李翱《故处士侯君墓志》记侯高“性刚劲,怀救物之略,自侪周昌、王陵,所如固不合,视贵善宦者如粪溲”[4](卷六百三十九)。这样直率不群的性情,看似与温良谦让对立,但都统一在才气的盛名之下,唐代人更加崇尚心雄万夫、怀抱利器、饱读诗书的才子。如韩愈称许樊绍述的著述:“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必出入仁义,其富若生蓄,万物毕具,海含地负,放恣横从,无所统纪。”[6](卷三十四《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白居易赞叹元稹:“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又观其述作编纂之旨,岂止于文章刀笔哉?实有心在于安人治国,致君尧舜,致身伊皋耳。”[5](卷七十《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元公墓志铭》)而皇甫湜更是赞颂韩愈的文章:“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适,精能之至,入神出天。”[4](卷六百八十七《韩文公墓志铭》)雄心和才气是傲气的资本,也助长了傲气的张扬。唐代社会中所形成的对傲诞狂放才子的崇尚在这些墓志文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二)女子的典范。唐人为女子所作的墓碑文中,除了称道女子们相夫宜家的恭敬、敦睦、和惠、孝悌等妇德外,一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更加倡导女子的才学。如张说为司属主簿博陵崔讷妻刘氏所作墓志铭中赞美刘氏:“夫人璇室载兰,蕙林曾秀,喈喈黄鸟,艳艳清明。闻诗闻礼,窃比诸生;茂行渊心,实称士女。”[4](卷二百三十一《司属主簿博陵崔讷妻刘氏墓志铭》)穆员《崔少尹夫人卢氏墓志铭》中颂扬河南少尹清河崔徵的夫人卢氏:“县君泉源发清,峻极凭厚,孕和缊粹,吐芳如春。其在弱笄,雅有君子之度。”这位卢氏女子不仅孝舅姑,睦娣姒,“和琴瑟之乐,以谐所从”,而且“阅《诗》《易》之义,以修所职。妇仪母训,垂五十年,不一日违仁,不须臾忘礼。温颜和气,物莫之侵;朗识清机,道与之接。雅好黄老,且精禅慧。尝谓要本无二,教焉有三,吾将贯之以一,守之以一。”[4](卷七百八十五)此外,柳宗元的《朗州员外司户薛君妻崔氏墓志》也称道了一位崔氏女子的才华,她“三岁知让,五岁知戒,七岁能女事。善笔札,读书通古今,其暇则鸣弦桐讽诗骚以为娱。始简以文雅清秀重于当世”[4 ](《全唐文》卷五百八十九)。而柳宗元的母亲也是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才女,柳宗元在《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中回忆母亲说:“尝逮事伯舅,闻其称太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知之,七岁通《毛诗》及刘氏《列女传》,斟酌而行,不坠其旨。汝宗大家也,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闻。岁恶少食,不自足而饱孤幼,是良难也。’又尝侍先君,有闻如舅氏之谓,且曰:‘吾所读旧史及诸子书,夫人闻而尽知之无遗者。’某始四岁,居京城西田庐中,先君在吴,家无书,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以诗礼图史及剪制缕结授诸女,及长,皆为名妇。”[4](卷五百九十)这些秀外慧中、满腹经纶的女子,可以与男子一样,在墓碑文中被称道赞美,足见唐人对于女子典范的评价标准已悄然发生了变化,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唐人在男女平等意识上,相对前朝有了很大的进步。
唐代墓碑文中记载和颂誉的这些士女的优良品行和过人才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群体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对于当时社会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引领高尚的士女道德风尚,起到了很好的促动和教育作用。墓志文的兴盛,是一种非制度文化现象,而其中所形成的对于道德品行的崇尚,是对社会主流教育的一种补充方式。它从侧面对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起着规范和宣导的作用,引人向善向上。这样的事例是见之于文献的。《晋书·羊祜传》曾记载:“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羊祜是一位立身清俭,颇有政绩的人物,他死后,为了纪念他,“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羊祜因为生前政绩显著,人品高尚,人们看了其碑文事迹无不感动得流泪,并且这种感染力不会随时代的推移而消减,直到唐代,孟浩然与朋友一行登岘山游玩,读到羊祜碑文时仍为之感动流泪。他在《与诸子登岘山》中写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可见,一篇好的碑文,一个高尚的灵魂是可以不断地对后人的心灵产生冲击感化作用的。
唐代大量的碑志文中对其墓主的“推美实行”,让后代的人“崇识素心”,对道德风尚的引导,也符合了儒家传统的要求。儒家经典《礼记》第二十五《祭统》对铭文就有如此规定:“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铭者,论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顺也,明示后世,教也。夫铭者,一称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观于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为之者,明足以见之,仁足以与之,知足以利之,可谓贤矣。贤而勿伐,可谓恭矣。”在铭文中,对祖先“称美而不称恶”,一方面是为了显示子孙的孝顺之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明示后代,对其进行教育和感化。
一个好的社会风尚的形成,除了社会机构制度化的教育培养外,还要靠非制度文化的化育和熏陶。唐代的官学教育体制承继着隋代的基础,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六学。其中前三学属于普通学校,学习儒家经典。后三学属于专科学校。此外,还设有崇文馆、弘文馆和医学。这“二馆”为收藏书籍、校理书籍和研究教授儒家经典三位一体的场所。同时在地方上,各府、州、县还分别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地方学校主要学习儒家经典。这种看似遍及全国上下的教育网络,并不能满足对社会成员普及教育的要求。实际上,靠官学接受教育的范围是很小的部分,因为这些教育机构的入学条件很高,如“二馆”的学生限于皇亲贵戚和高官功臣的子弟,太学的学生限于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等。因此作为对官学的一种补充,私学,包括乡闾私塾、族学与家教等,就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支撑社会教化的力量。从唐代墓碑文中对女子才学的称颂中不难看出,唐代私学中母仪母教是很被重视的。从一个人的成长过程看,母亲是人生的第一位老师,她的品德教养、言行举止对孩子的熏陶化育影响最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母亲所具备的良好品格与学养,是承绪家学,光大门楣的重要条件。如盛唐时薛播的伯母林氏,训导家族子弟成才,晚辈中有七人举进士,中科名。又如上述柳宗元母亲对他的教育等事例都是力证。虽然重视女子才学的培养不唯唐代所有,南北朝时期也不乏妇女博学有才识的个例,如《晋书》卷九十六《列女传》载韦逞母宋氏学习儒家典籍的事迹:“韦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学称。宋氏幼丧母,其父躬自养之。及长,授以《周官》音义。”但像唐人这样在大量的女子墓志文中张扬她们才华,赞美她们的才德,尚属空前。
要之,唐代大量产生的墓碑文,不仅在史学上为后代提供了许多可资查证的史料,在文学上丰富了传记文学的领域,还让我们从中看到了唐代社会士女道德品行的崇尚。同时,作为官方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唐代墓碑文中所倡导赞扬的人品道德和文章,也对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起着宣导和化育的重要作用,成为导引社会群体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不可或缺的一个非制度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