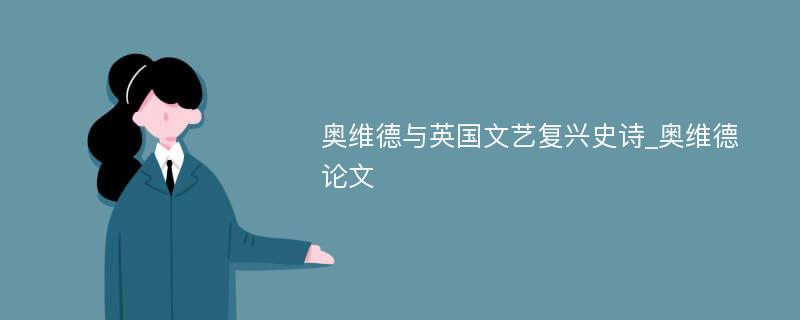
奥维德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小史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史诗论文,文艺复兴时期论文,维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产生过巨大影响,当时的文坛巨匠如马洛(Marlowe)和莎士比亚都曾借用奥维德《变形记》中的故事框架作为诗歌再创作的母题,并且使得一种新的诗歌文类“艳情小史诗”(epyllion)在16世纪末的英国诗坛上风靡一时,成为世纪末的一个奇特文学现象。
从词源学上来看,“小史诗”(epyllion)一词来自希腊文,只是在19世纪才首次出现,意指“以神话浪漫故事为主题的短篇叙事史诗”,其主要代表作包括古罗马时期奥维德的《变形记》、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托马斯·洛奇的《希拉的变形》、马洛的《希洛与李安达》(以下简称《希》)、莎士比亚的《维纳斯与阿都尼》(以下简称《维》)以及后来约翰·马斯顿(John Marston)的《皮格米翁雕像的变形》。
本文拟探讨奥维德在英国的本土化过程,以及他如何影响了英国小史诗的形成与发展。笔者将着重分析马洛和莎士比亚的两部长篇小史诗中的世俗化爱欲诉求、这两首诗中对彼特拉克诗歌常规的颠覆和戏仿,以及小史诗的一些共同特征。
奥维德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诗坛
奥维德在西方文学史上的名声一直是毁誉参半,难以定论。即使当他在世之时,他也遭遇了人生的坎坷,曾被奥古斯都大帝以“有伤风化”的罪名流放到荒芜的黑海之滨托弥,并老死在那里。奥维德被称作“跨越两个时代的人”:他处身于古希腊璀璨的文学遗产和即将到来的拉丁文学“黄金时代”之间,是古希腊神话的集大成者,随后自己也成了后继者摹仿的典范。
早在14世纪时,乔叟(Chaucer)和高尔(Gower)就曾直接搬用奥维德作品的片段融合进他们的诗歌中去,但奥维德真正全面地进入英国文坛,则是从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于1483年翻译出版的《变形记》开始的,随后他的作品被陆续翻译成英文,包括华尔德(Wynkyn de Worde)所译的《爱的艺术》(1513)和图尔博维尔(Turbervile)所译的《女英雄家书集》(1567)。最著名的则是戈尔丁(Arthur Golding)所译的《变形记》(1565-1567)。到了17世纪则有桑迪斯(George Sandys)的《变形记》译本(1621-1626),1717年出版了加尔登组织翻译的《变形记》译本,译者中甚至包括了大诗人德莱顿(Dryden)。从上述翻译出版史来看,奥维德的作品在英国一直畅销不衰,深得读者喜爱。①
奥维德的《变形记》可以看作是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的对应物。颂扬的是勇士的冒险和尚武精神,因此是阳刚之气的象征,而《变形记》则歌颂人类欲望的阴柔一面,这两部诗作构成了人类生活的两个不同方面。奥维德自认写不了战争的宏大题材,坦白道:“温柔的爱神粉碎我描绘重大主题的努力。”② 但与此同时,他声称爱情是另一类战争,故此写出了“凡情人都是战士”的名句。③
熟悉英国文学史的读者都知道,英国文艺复兴要比欧洲大陆晚一两个世纪,直到都铎王朝时期才开始,到伊丽莎白时期达到鼎盛,以莎士比亚的诗歌和戏剧作为其登峰造极的象征。古希腊罗马文学经典为英国本土作家和艺术家提供了母题和范本,成为他们创作灵感的来源。自人文主义在英国兴盛以来,古希腊罗马神话一直作为古典价值观的载体在人文主义教育中被介绍给受教育者。在当时的文法学校中,拉丁文是必修课,而以奥维德为代表的古典作家在学校课程中占有中心地位。英国16世纪大主教、亨利八世的权臣沃尔西(Cardinal Tbomas Wolsey,1473-1530)批准把《变形记》放进文法学校课程里,让学生以此为楷模学习用拉丁文作诗。莫斯(Ann Moss)对这种态势作了精辟的概述:“在整个16世纪里,拉丁文学(在更小的程度上也包括希腊文学)提供了文化的、道德的和知识的标准,而且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提供了一种语言学模式。”④ 换言之,人文主义教育就是拉丁文教育,而且还是最典雅的古拉丁文教育。但这种教育也带来了一个宗教文化上的问题:古拉丁作家均为异教徒,他们作品中的异教思想如何与基督教教义共存呢?此外,希腊神话中诸神的道德行为实在难以跟清教徒的道德原则协调起来。这一窘境可从以下例子看出:拜伦在《唐璜》中讥讽少年唐璜的母亲控制他的教育,禁止他读未经删节的古典作品,唯恐他的心灵受到污染。⑤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唐璜的初次风流韵事不是因为阅读奥维德引起的,而是因为唐璜母亲闺中密友的引诱。
当时的教育者所采取的一种措施,就是对奥维德的神话故事(fables)加以基督教的道德阐释,即所谓的“道德化的奥维德”(Ovide Moralizé)。奥维德在欧洲中世纪最早的批评者把他视为诲淫诲盗的祖师,他的《变形记》应该付之一炬。12世纪的法国女诗人玛丽·德·法朗士(Marie de France)在其叙事小诗《桂日马尔》(“Guigemar”)中描述了一幅壁画,画中的维纳斯把奥维德的《情伤良方》投入烈焰中。奥维德自己在听到流放的判决之后,也是一气之下把《变形记》的手稿焚烧成灰。(幸好其手抄本早已流传甚广。)另外一些注释家则扭曲奥维德的故事的寓意,使之增添了基督教教会的说教色彩。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注释家们把阿都尼的生母弥尔拉(Myrrha)对她的国王父亲的乱伦畸恋加以如此荒谬的阐释:即她是贞女玛丽亚的预表(type)。⑥
在英国本土,对奥维德的道德化、寓言化阐释也很早就开始了。最早的奥维德译介者卡克斯顿其实译的不是奥维德的原著,而是法文中所谓“道德化”了的奥维德阐释版本。后来的译者戈尔丁也竭力使奥维德的故事为基督教的道德观服务。他对《变形记》的道德化阐释就是,“变形是对违背自然的性行为的惩罚”。⑦ 戈尔丁对《变形记》中神话故事的寓言化和道德化阐释的一个例子,就是把阿波罗追达芙妮的神话解读为要保持处女的贞操。⑧ 然而,在16世纪90年代,英国诗坛风向突转,偏向了来自意大利的一股潮流,诗人们纷纷把《变形记》中的故事改编为颂扬艳情和人神之恋的小史诗。“这类诗作中毫无枯燥的道德教诲,反而求助于机智诙谐的诗句,高深的幽默感使得爱情—神话诗歌从苍白无力的道德寓言阐释中解放出来,焕发出想象丰富的瑰丽色彩。”⑨ 控制意识形态的政府和教会权威当然不会对这股世俗化的情爱文学潮流坐视不管,因此企图禁止奥维德在英国的传播。早在1582年,枢密院就颁布了一道禁令,不许在学校里教授奥维德的诗歌。禁令中写道:“为了年轻人的利益,应将文法学校中通常诵读的淫秽诗人作品撤掉……其中包括奥维德的《爱的艺术》和《哀怨集》等。”⑩ 坎特伯雷大主教和伦敦主教于1599年6月1日颁布禁令,禁止艳情和嘲讽作品的出版,并召回了已经发行的这类书籍,并让刽子手付之一炬,上演了英国版的“焚书”。在被焚书籍中,就包括马洛翻译的奥维德《恋情集》。(11)
神圣之爱与世俗之爱
英美小史诗表现了从神圣之爱到世俗之爱的趋势,这是西方文化世俗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世纪基督徒那里,爱欲这种人类自然的感情被认为是一种邪恶,要在苦修与禁欲中被涤除,并升华到唯一可接受的对上帝之爱。对一个文士的诘难“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曾如此回答:“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12) 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如此表达他对上帝之爱:“那么,不爱你,这是否仅是轻微的哀伤呢?在我看来不是的。”(13) 在基督教的某些神秘主义流派中,上帝与基督和信徒的关系被描绘成新郎与新娘的关系。正如荣格在《女性面面观》中所论述的那样:“然而,神秘主义的阐释总是喜欢把新娘设想为以色列,而把新郎设想为耶和华。这种阐释被一种健全的本能所推动,甚至把色欲情感都转化为上帝与选民的关系。基督教为了同样的原因也把《雅歌》借用过来,把新郎解释为基督,把新娘解释成教会。”(14) 更有甚者,人类灵魂被视为阴性,她在人世间的驻留被比喻为流放,远离了自己的初始家园天堂,并渴望与自己的新郎基督结为一体。十字架圣约翰(St.John of the Cross)把信徒对上帝之爱描写得十分诚挚:“爱情之伤没有解药,除非是那施加创伤给我们的人。所以受伤的灵魂被爱情之伤的灼热之痛所驱使,紧迫着所爱的人,呼叫他解救痛苦。”圣约翰指出了这种追求上帝的爱情的两种特征,其一是摆脱对凡世造物的留恋,其二是灵魂忘却自我,脱离躯壳去追随上帝。(15) 这种对上帝之爱构成了虔诚的信徒生活中唯一的欢乐,正如托马斯·阿·坎比斯所说:“我的上帝和我的一切……有你在,我就感到一切尽都甘甜,没有你在,我就感到一切都令人讨厌。”(16)
基督徒这种对上帝的爱就意味着放弃凡间之爱。费尔巴哈如此声称:“在天国里,两性之爱之原则被当作属地的、属世界的原则而被弃绝了。”(17) 台多立安在《勉纯洁》第13章中断言:“想进天国者,就得放弃天国里所没有的东西。”大马士革的约翰则宣称:“独身生活乃是学天使的样。”(18)
英国宗教诗人但恩在其神圣十四行诗第14首中曾写出如下对上帝表示热恋的诗行:“然而,我深深爱恋您,也乐于为您所爱,/可是,却偏偏被许配给了您的寇仇死敌;/……/我将永远不会获得自由,除非您奴役我,/我也从来不曾保守贞洁,除非您强奸我。”(19)
随着世俗化进程的展开,人们日益把对虚无飘渺的上帝之爱转化为对有血有肉的人之世俗之爱。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就是,在倡导苦修主义的中世纪鼎盛时期(12世纪),奥维德的《变形记》却成了最畅销的书。个中奥秘,也许可用被压抑的性能量对苦修主义的反动来解释。世俗之爱的源头也许可以追溯到12世纪法国普罗旺斯行吟诗人的情歌,以及随后衍生的“典雅之爱”(courtly love)。
墨西哥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塔维欧·帕兹(Octavio Paz)在其论述爱情的名著《双重火焰》中,曾对典雅之爱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追根溯源的探索,得出了独到的见解。帕兹断言:“文学的功能之一就是再现激情,以爱的激情为主题的文学数量极多就能说明这一点,爱情是西方男女主要的激情。”(20) 帕兹把典雅之爱也称作骑士之爱,论述了它之所以兴起的社会、历史原因。他认为骑士之爱是一种产生于贵族阶层的高尚情操,是“高贵宫廷的特质”。(21) 这种“纯净优雅之爱”高扬了女性的地位,把单纯动物性的欲求升华为一种精神上的互相吸引,使得人类爱欲审美化了。帕兹因此得出了著名的论断:“爱欲是肉体的诗歌,而诗则是语言的爱欲。它们既对立又互补。”(22) 20世纪英国批评家C.S.刘易斯在其力作《爱的寓言》(The Allegory of Love)中也对典雅之爱做过精辟的论述。刘易斯概括了典雅之爱的四个特点:谦卑、殷勤、私通、爱的宗教。“谦卑”就意味着男女地位的颠倒,骑士对他所爱恋的贵妇自称是奴隶,愿为她赴汤蹈火。“殷勤”则表现在骑士对女士彬彬有礼,举止文雅。至于“私通”,刘易斯指出了其历史和社会根源:中世纪的婚姻不是奠基于爱情之上,而是建立在家族的门当户对和政治、经济利益的联姻之上的。刘易斯声称:“在一个婚姻纯粹是实用主义的社会里,任何对性爱的美化都必须以对私通的美化开始。”(23) 所谓爱的宗教就是对爱神(Amor)的崇拜。这种宗教是作为真正宗教的对手或戏仿形式而兴起的。它深受奥维德《爱的艺术》之影响,以其诙谐、调皮和轻率无礼为特征。作为例子,刘易斯引证了12世纪法国的一首打趣诗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一所女修道院的修女们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讨论爱情的恰当对象是什么。除了几位“诚实的男修士”,所有男性均不得列席。会议开始时宣读的是“奥维德博士”的爱情法规而不是福音书。随后一位女主教宣布了她到访的使命——爱神派遣她来了解修女们偏好哪种情人。修女们分为两派,一派选择男修士作情人,一派偏爱骑士。女主教随即宣布,修女们唯一合法的情人只能是男修士。偏爱骑士的那一派被宣布为异端,被责令立即悔改。(24)
刘易斯对11世纪末法国诗人发起的这场爱的革命评价如此之高,令人不禁拍案叫绝:“法国诗人在11世纪发现或曰发明了那种浪漫激情,英国诗人到了19世纪仍在描写那种激情……跟这场革命相比,文艺复兴只不过是文学表层的一个涟漪。”(25) 作为对以上引言的一个注脚,我们可以回想起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诗人马修·阿诺德所写的爱情小诗《多佛海滩》,在诗中,他对如海潮般退却的基督教信仰发出哀叹,只能求助于爱情来帮他度过漫长的黑夜。
英国小史诗的嬗变
所谓小史诗也被称作奥维德体诗歌(Ovidian poetry)。根据乔治亚·布朗(Georgia Brown)的定义,“小史诗是机智、艳情、温文尔雅的诗歌,它特别强调诗风与创意,要展示出超群绝伦的诗歌技巧。”(26) 西方学者们公认小史诗滥觞于托马斯·洛奇(Thomas Lodge)的《格劳库斯与希拉》(Glaucus and Scilla),其另一名称是《希拉的变形》(Scilla’s Metamorphosis)。这部作品于1589年问世,但这一诗体并未流行开来,要等到莎士比亚的《维纳斯与阿都尼》于1593年出版才成为诗坛时尚。(虽然马洛的《希洛与李安达》的现存最早版本是1598年的,但该诗早在1593年9月就在伦敦书商公会注册簿上登记了。(27))此外,《希》在正式出版前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上层社会读者中广为流传,对莎士比亚的《维》也产生过影响。小史诗的流行标志着年轻一代作者登上文坛,他们对文学的“教诲”(didactic)功能不感兴趣、而是对这一新兴文类(genre)的唯美情趣,猎艳心态和华丽词句情有独钟。对这一文类的共同爱好塑造了他们的群体身份,使他们成为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边缘群体和世纪末的文学先锋派。小史诗也有其特定的读者群,他们是以骚桑普顿侯爵为代表的年轻宫廷贵族,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偏爱新的艺术潮流,以显示自己标新立异,离经叛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小史诗既是对典雅之爱的传承,又是对它的颠覆。作为从意大利传进英国的一种新诗体,典雅之爱的具体代表就是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这种诗体较之本土原有的爱情诗在文辞上更为精雅,在情感描述上更迂回曲折,而且相对于当时存在的本土诗歌,其诗歌意象也更为多样和新颖。十四行诗在英国的早期模仿者如老怀亚特爵士、萨利侯爵等多拘泥于彼特拉克诗中的常规,比如把诗歌中的求爱者(一般是骑士)描写成甘心做美女谦卑的奴隶的人,他内心的情感折磨往往被用一系列的悖论意象来表征:情人与冤家、寒冷与炎热、希望与绝望并存。在彼特拉克体的十四行诗中,爱情还是占据着高贵的地位,而且从没有对肉欲的渲染。诗人所爱恋的美女被理想化到接近女神的程度,颇有“美人如花隔云端”之感。对于日益变得僵化和程式化的彼特拉克诗体,英国诗人中很早就有人起而反叛。例如,锡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在他的一首十四行诗中就抱怨平庸的诗人只会机械照搬用滥了的希腊神话典故,而缺乏诗歌最基本的实质——真情实感。他借用缪斯女神之口给诗人们提出写作的忠告:“探视你的内心,然后再命笔。”(28)
英国最早出现的小史诗《格劳库斯与希拉》取材于《变形记》第13章,讲述的是海神格劳库斯对仙女希拉的单相思,以及希拉的变形。这首诗在很多方面还脱不了对彼特拉克诗风的模仿,主要的形式是失恋的抱怨。(29) 这首诗的总体格调哀怨有余,也利用了一些“情感谬误”(pathetic fallacy)手法来衬托失恋的格劳库斯的悲伤,可是太拘泥于常规化的诗歌手段,缺乏后来马洛与莎士比亚的灵动文采和机智诙谐调子,也没有把爱欲渲染到几乎有伤风化(risqué)的地步。作为一种新型文类的小史诗,要在马洛和莎士比亚的笔下才焕发出异彩,并在世纪末的英国诗坛蔚然成风。有评论家认为,莎士比亚写《维》借鉴了很多《希》中的手法,但笔者以为,这两首诗之间存在的与其说是借鉴,不如说是一种互文性,两位大师争奇斗艳,都在这一新文类上展示自己的诗歌才华。莎士比亚把《维》题献给骚桑普顿侯爵,(30) 借此敲开了精英诗人俱乐部的大门。《维》这首诗一经出版,就获得了读者的欢心,在短短数十年里一共印刷了16版,并且在当时的一出剧本中,一个剧中人物声称要用莎士比亚的诗句去向他的情人求爱,而且每夜都把《维》放在枕头下,可见此诗多么深入人心。(31)
西方评论家的一致看法是,马洛的《希》直接取材于公元5世纪亚历山大里亚诗人缪塞乌斯(Musaeus)的原诗,也参照了奥维德的《女英雄家书集》(Heroides)中的原始叙述。但是,美国学者布彻(Warren Bloutcher)于2000年发表的文章考证出了《希》的另一个来源,就是西班牙诗人胡安·博斯坎(Juan Boscán)的《李安达》。(32) 布彻认为,影响了小史诗的不仅是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而且文艺复兴时期的本国语人文主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莎士比亚的《维》的直接来源就是戈尔丁的《变形记》译本,同时他也参照了奥维德的拉丁文原作。在诗歌形式上,马洛的《希》是用英雄双行体写的,而莎士比亚则沿袭了戈尔丁的六行体(Sixain)。马洛的《希》在思想结构上分为三部分,由希洛与李安达在阿都尼节上的初会、赫尔墨斯神与一个凡间牧羊女的恋情和希洛与李安达在城堡里的幽会构成。由于马洛的版本在出版时结尾处写了一句拉丁文“有缺漏”,所以西方评论家多认为这首诗是残篇,因为作者只写到这对恋人终成眷属就匆匆结束,并未叙述李安达后来渡海淹死和希洛投海自尽的情节。后来贾普曼(Chapman)的续写本在情节和氛围上都与马洛的版本不称,颇有续貂之嫌。
小史诗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厄洛斯(Eros)的绚丽渲染和铺陈,给人类这一独有的内心情感特征以突出的地位。根据荣格的看法,“女性心理是建立在厄洛斯原则之上的……而自远古以来,归属于男性的主宰原则就是逻各斯。”(33) 荣格对这两大原则的定义分别是:厄洛斯属于精神联系(psychic relatedness),而逻各斯则是“客观利益”(objective interest)。但是,在《维》中,代表厄洛斯的女爱神维纳斯颠覆了传统女性的“软弱、无助、温驯”的形象,大胆地向阿都尼求爱,演了一出“凰求凤”的喜剧,突破了世人对男女性别角色的思维定势。而在《希》中,希洛则以更委婉和女性化的方式表达了她的欲望。与维纳斯的勇敢表白相反,女性的典型特征羞赧(coyness)在马洛的《希》中成为作者嘲讽女性欲望的突出手段。布朗把羞赧看成是“产生羞耻感的那些婉转、悖论和自我边缘化的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34) 例如,希洛对李安达一见钟情,却又受到社会常规的束缚,要保持淑女的矜持和羞赧。
笔者以为,在《维》中,作者所描述的是欲望受挫的过程,把维纳斯与欲望对象近在咫尺却似乎远隔天涯的窘境比作坦塔罗斯(Tantalus)的困境。这两首诗中的主要角色为了达到自己的欲望,都充分运用了修辞术来企图说服自己的所爱。这也反映出当时人文主义教育对修辞术的重视。(35) 我们若是看看这首诗中主动求爱者的吐诉,就能发现,爱神维纳斯运用了赞扬对方美貌、自夸和谴责等手法。维纳斯在诗的开头用夸张手法盛赞阿都尼的容貌,她先夸他美,说:“你比我还美好几倍。”
地上百卉你为魁,芬芳清逸绝无对。
仙子比你失颜色,壮男比你空雄伟。
你洁白胜过白鸽子,娇红胜过红玫瑰。
造化生你,自斗智慧,使你一身,俊秀荟萃。
她说,“你若一旦休,便天地同尽,万物共毁。”
(第7-12行)(36)
在这节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逆转,即维纳斯用了赞美女性的词藻来夸阿都尼,把他比作百花之魁:“洁白胜过白鸽子,娇红胜过红玫瑰”(鸽子是爱神的专属禽鸟,而玫瑰则是爱情的象征)。在随后的几个诗节中,红与白的意象反复出现:“只见他又红脸,又撅嘴,老那么心硬,”“她脸又红,心又热,似一团炭火,熊熊融融,/他脸也红,心却冷,只羞似霞烘,严如霜凝。”维纳斯的脸红是她炽热情欲的外现,而阿都尼的脸红则是他羞涩的表征。维纳斯诱惑阿都尼的另一个手段就是自夸,这与要求女性谦卑驯服的传统也是不符的。这位女爱神如此自夸:“我的眼水汪汪碧波欲流,转盼多风韵。/我的美丽像春日,年年不老,岁岁更新。”“我也会学精灵,在绿莎上细步轻踏;我也会学水中仙子,飘飘披着长发,/用平沙作舞茵,却不见有脚踪留下。”笔者以为,诗人在此化用了柏拉图《会饮篇》中的一个典故。柏拉图借用阿伽通之口,论证爱神的娇嫩:“因为他不在地上走,也不在脑壳上走……而是在世上最柔软的东西上走,也就在那上面住。他所奠居的地方是人和神的心灵。”(37) 维纳斯这番劝说最具挑逗之处,就是那高度性暗示的一节:
那我就是你的苑囿,你就是我的幼麑。
那里有山有溪,可供你随意食宿游息。
先到双唇咀嚼吮吸,如果那儿水枯山瘠,
再往下面游去,那儿有清泉涓涓草萋萋。
(第23-4行)
帕特里奇(Eric Partridge)在其专著《莎士比亚的低俗》(Shakespeare’s Bawdy)中,曾专门探讨了《维》中的情色意象。他指出,“苑囿”(park)是西方文学中专指女体的常规比喻。与之相关联的词就是“庭园”(garden)。我们甚至可以从《圣经》中找出其源头。在《雅歌》中,有新郎如此赞美新娘的诗行:“我妹子,我新妇,乃是关闭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38) 弗莱(Northrop Frye)对《雅歌》的情爱性质评价十分正确:“无论注经家怎么解释,《雅歌》仍然是被性爱所激发的诗歌之丰碑。在《雅歌》中,新娘被描述为‘一个关闭的庭园,一座封闭的喷泉’。”(39) 而“幼麑”(deer)在英语中是双关语,与“亲爱的” (dear)谐音。在《雅歌》2:9中,我们也可读到“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的诗句。至于“山丘”(mountain)和“溪谷”(dale)的含义,读者自可发挥想象。(40)
正如有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莎士比亚蓄意运用性别角色逆转来达到喜剧效应,因为阿都尼不像常规爱情诗中的骑士那样夸饰他情人的美貌,维纳斯只好自夸了。(41) 另外,莎翁还用猛禽的意象来比喻欲火中烧的维纳斯,而把阿都尼比作一只关在笼中的小鸟,完全颠倒了征服与被征服者的地位。马洛在《希》中也运用了同样的逆转手法来描述李安达的阴柔之美,使得他和希洛都成了人们欲望的对象。格林布拉特对这一现象的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逆转,他认为文艺复兴时期作家把性别差异看作流动和不确切的现象:“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故事中,性别被证明是不稳定的,在其起源上是人为的。”(41)
结语
小史诗是对宗教正统和对清教苦修主义的一种挑战和颠覆,是回复人性本能和恢复文学娱乐功能的趋势。小史诗的喜剧效应就在于它对世俗爱情观的逆转,就在于它捕捉住了故事主人公性格和言行中的自相矛盾之处,并加以夸张和戏仿,从而使读者忍俊不禁,露出会心一笑。小史诗的渲染艳情是对读者的一种色诱,邀请读者参与偷窥叙事角色的情爱活动,并从中得到替代的愉悦。
与史诗的宏大叙事使命相反,小史诗则偏重于所谓的边缘化题材,尤其是离奇的爱恋和变形。毋庸讳言,小史诗描写爱欲,并且把处理艳情跟文学创新联系起来。因此,其主要特征就是侵越性和标新立异。另外,小史诗还有一个偏离正题的叙事插曲。作者往往在叙述主要神话情节中插入一个次要情节,如《希》中马洛自己原创的墨丘利神(42) 与村姑之爱和《维》中阿都尼的坐骑去追捷尼母马的插曲。这种离题叙述通常要么是解释原因的(etiological),如墨丘利的神话是要解释天下学者为什么都是清贫的,要么是为主要情节铺垫和衬托的,如马的插曲被维纳斯用来为她的求爱话语做活例子,要阿都尼放弃自己的拘谨和守贞。此外,作者对马的求爱的拟人化诙谐描绘也是对所谓典雅之爱的戏仿。
诸多英美评家都把《维》定性为一出悲喜剧,但他们的根据都是建立在阿都尼的惨死上的。这只是比较低级的一种解读。笔者以为,莎翁之意在于展示出维纳斯求爱不得、欲望受挫的悲剧,这是被人们所忽略的一个方面。由于生理结构的先决条件,没有阿都尼的同意,作为女性的维纳斯注定要遭受欲望诉求的失败,并在诗的结尾咏叹出“此恨绵绵无尽期”的悲曲,而且对人世未来的爱情加以诅咒。维纳斯的形象在这首诗中也经历了一个截然相反的转变:从一个纠缠不休的轻狂女子到一个伤心欲绝的母亲。有评家甚至把维纳斯在诗篇结尾的形象比作《圣母怜子图》中的玛丽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维》也是莎翁对淫欲的讥讽和嘲弄,是对但丁、彼特拉克等鼓吹新柏拉图主义之爱的诗人的“恶搞”。
马洛的原版《希》,若不考虑到贾普曼的后续版本,则只能是一出喜剧,因为诗中的两个主要角色最后都进入了爱欲的乐园,就像赫丘利(Hercules)进入了极乐岛上的金苹果园一样。但这出喜剧中的两个角色都被置放在一个如梦幻般的仙境中,而且诗人善意地讥讽他们对爱欲的无知和他们言行不一、自相矛盾的荒谬状态。
文艺复兴小史诗是奥维德的诗歌艺术在英国的再生,它代表了一种时代精神,张扬人类自然情感,纵情于文字游戏和艳丽雕饰,与欧洲大陆的人文主义互为呼应,构成了世纪末英国文坛的一道亮丽风景。但是,小史诗只兴盛了十多年就让位于嘲讽诗了,这一转折背后的社会文化原因,则是另一次探索的话题。
注释:
① Philip Hardie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Ovi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249-250.
② 奥维德:《罗马爱经》,黄建华、黄迅余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51页。
③ 奥维德:《恋情集》,第9首。
④ Glyn P.Norton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Vol.3,p.145.
⑤ 拜伦:《唐璜》(上),查良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⑥ 弥尔拉的故事出自《变形记》第10章,其名字在英语中意为“没药”,即这种植物流出的汁液是弥尔拉悔恨的泪水。阿都尼是接生女神从没药树中取出的。
⑦ Jonathan Bate,Shakespeare and Ovid(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53.
⑧ Murray Roston,Sixteenth-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Macmillan,1982),p.93.
⑨ 蒋显璟:《英国人文主义的两朵奇葩》,载《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9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90页。
⑩ Dympna Callaghan,“Comedy and Epyllion in Post-Reformation England”,Shakespeare Survey online,Vol.56(CUP,2007),p.31.
(11)(26)(34) Georgia Brown,Redefining Elizabethan Literature(Cambridge:CUP,2004),p.105,p.103,p.158.Cf.Shakespeare Survey online.
(12) 《马可福音》12:30。
(13) Augustine,Confessions,Chapter V。
(14)(33) C.G.Jung,Aspects of the Feminin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 Kegan Paul,2003),p.16,p.74.
(15) “St.John of the Cross:A SPIRITUAL CANTICLE OF THE SOUL”,http://www.ccel.org/ccel/john_cross/canticle.txt(accessed 2009-05-01).
(16) 托马斯·阿-坎比斯:《效仿基督》,第3卷第34章。
(17)(18)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223,224页。
(19) 约翰·但恩:《英国玄学派诗鼻祖约翰·但恩诗集》,傅浩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244页。
(20)(21)(22) 奥克塔欧·帕兹:《双重火焰——爱情与爱欲的几何学》,蒋显璟、真漫亚译,台湾边城出版社2004年版,118,93,22页。
(23)(24)(25) C.S.Lewis,The Allegory of Love:A Study in Medieval Tradition(Oxford:OUP,1938),p.I3,pp.18-20,p.4.
(27) 伦敦书商公会注册簿(the Stationer’s Register)是伦敦出版业的行会,该注册簿是早期的版权形式,公布某出版商拥有出版某部作品的权利,他人不得侵权。
(28) Philip Sidney,Astrophil and Stella,Sonnet 1.
(29) 乔治亚·布朗列举了16世纪90年代英国诗坛最风行的三种书写文类:哀怨诗、英国历史的叙事和书信体。
(30) 骚桑普顿侯爵属于反叛保守权贵的年轻贵族,生活作风奢侈放荡,最终因卷入埃塞克斯叛国阴谋而被因。
(31) 转引自Georgia Brown,Redefining Elizabethan Literature,103页。把《维》放在枕头下的典故是借用了亚历山大大帝每夜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放置在枕头底下的轶事。参见Plutarch,Greek and Roman Lives。
(32) Warren Boutcher,“‘Who Taught Thee Rhetoricke to Deceive a Maid?’:Christopher Marlowe’s Hero and Leander,Juan Boscán’s Leandro,and Renaissance Vernacular Humanism”,Comparative Literature(Winter,2000),pp.11-52.
(35) 文艺复兴时期文法学校中的“三学科”(Trivium)包括语法、逻辑和修辞。
(36)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1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9页。本文中《维纳斯与阿都尼》的引文均出自此。本文中《希洛与李安达》的引文为笔者自译。
(37)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247页。
(38) 《圣经·雅歌》4:12-15。
(39) Northrop Frye,Myth and Metaphor(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90),p.48.
(40) Katherine Eisaman Maus,“Venus and Adonis”,The Norton Shakespeare,ed.Greenblatt,1997,p.603.
(41) 转引自Robin Headlam Wells,Shakespeare’s Humanism(Cambridge:CUP,2005),35页。
(42) 墨丘利(Mercury)是罗马神话中的一位神仙的名称,其在希腊神话中的名称为赫尔墨斯(Hermes),其职能之一就是当信使,为诸神传递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