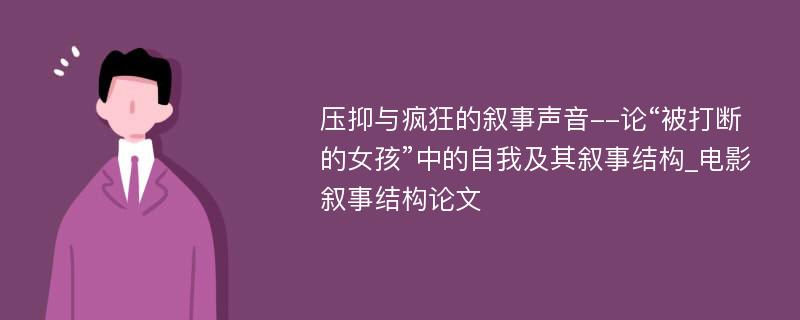
抑郁而疯癫的叙事声音——论《被中断的女孩》中的“自我”及其叙事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抑郁论文,声音论文,自我论文,女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1)04-0077-07
《被中断的女孩》(Girl,Interrupted)也译为《丢魂女孩》、《断线女孩》,是美国作家苏珊娜·凯森(Susanna Kaysen)1993年发表的一部自传,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生命书写”(life writing)大潮的产物,也是这个大潮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品。自传出版后即成为当年“最畅销回忆录”之一,1998年被拍为同名电影,安吉丽娜·朱莉凭借在该电影中的出色表演赢得了2000年奥斯卡最佳女配角。
自传讲述了十七岁的凯森于1967至1968年间在著名精神病院麦克林医院(McLean Hospital)里十八个月的经历,主要包括她如何与心理医生见面并被诊断为边缘性人格分裂症(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随后被送入精神病院,在医院里她接触了其他病人、医生和护理人员,以及出院后的情形。通过自我叙事,凯森对抑郁症、疯癫以及自我、身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本文重点考察曾经是精神病人的凯森,如何在这部自传中讲述自己过去的经历,以及如何在讲述中建构“自我”。上世纪90年代以后,“疾病叙事”(illness narrative)这一叙事文类已经受到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笔者希望借本文的个案研究,引起国内学界对“疾病叙事”、尤其是“疾病自传”(autopathography)的关注。
“自我”问题的提出
《被中断的女孩》书名取自荷兰绘画大师维梅尔(Vermeer)的一幅绘画作品《在音乐中被中断的女孩》(“Girl Interrupted at her Music”)。画中,一名贵族装扮的男人试图给一名女子讲音乐,但该女子却扭过头,看着观众,似乎有什么人正进入画面打断了她的音乐课。维梅尔的原意是使本来静止的画面动起来,interrupted一词也取其字面意思,即“被中断”,但凯森显然给此画赋予了新的含义。在自传《被中断的女孩》的末尾,凯森这样阅读维梅尔的绘画:
这一次,我读了这幅画的标题《在音乐中被中断的女孩》。
在音乐中被中断:我的生命中断在十七岁的音乐中,和我一样,她的生命也被中断,给取出来固定在画面上:生命被凝固成一个时刻,这个时刻代表其他所有时刻,不管过去和未来。还有什么生命能从这样的画面里回来?
我现在有些事情想告诉她。“我理解你,”我说。
我男朋友发现我在走廊哭泣。
“你怎么啦?”他问。
“难道你不明白,她想走出来?”我用手指着她。
他看了看那幅画,又看看我,说:“你想的永远都是你自己。你根本不懂艺术。”他走开,看伦勃朗的画去了。(Kaysen:167)①
音乐中的女孩周围是另外一种光,微暗而躁动的生命之光,借了此光,我们能够偶尔隐约地瞥见自己和他人。(168)
原画旨在说明,女孩似乎被外来的什么事物所打断,而凯森却从中读出了一个被禁锢的鲜活生命,并将自己等同于画中女孩,认为自己在麦克林精神病院的经历“凝固”了自己的整个人生。正如画中女孩想走出画框以寻找生命的“其他时刻”,凯森也希望从那段经历中走出来,寻找生命的其他意义。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甚至可以说只是问题的表象。我们都知道,自传叙述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事后叙述”,即回顾性叙述,凯森写作此书时已经四十多岁,距离她在精神病院的经历已超过三十年。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凯森现在才来讲述许久前的一段经历?如果仅仅为了走出那段经历,我们无法理解凯森为什么要等待三十年之久。换句话说,如果凯森真的想忘记这段经历,她早就应该把它讲述出来。将人生的一段经历深埋心中三十余年,不外乎两个原因:其一,由于某种社会的压制不能讲述;其二,由于这段经历隐含了自己的真实“自我”,因此不愿意讲述。通过把自己比成画中女孩,凯森表达了想逃离那段经历的愿望,也就是逃离抑郁症和疯癫,成为“正常人”,这给了她的讲述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同时这也是读者和社会希望看到的理由。然而透过凯森叙述的间隙,我们聆听到的却是一个远非“正常”的凯森,她对三十年前那段经历流露出的深深留念甚至让读者觉得,抑郁症和疯癫正是凯森内心有意或无意地希望表达的真实自我。她的讲述不是为了逃离,而是想重新“表演”(perform)那一段经历,以再次体验成为真实自我带来的激动。《被中断的女孩》正像维梅尔画中女孩周围的那道微暗而躁动的光,让读者得以瞥见凯森的内心真实自我。
评论的三个典型观点
对《被中断的女孩》的评论很多,大体可归纳为三类:第一,认为凯森讲述的是她从“疯癫”回归“正常”的历程;第二,认为凯森的讲述表明她没有真正回归“正常”;第三,认为凯森的讲述表明,她无法确信自己现在是否仍有“精神病”,更无法确信三十年前的“精神病”诊断。这三类观点恰恰对应了三类典型的疾病叙事,或疾病叙事的写作/阅读策略,即关于康复过程以及重建正常身份的疾病叙事、关于病人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行叙事治疗的疾病叙事,和关于病人与医生、医疗机构及社会常规之间发生冲突的疾病叙事,这也是疾病叙事领域内三部有影响力的专著各自重点探讨的主题。这三部专著是霍金斯(Anne Hawkins)的《重构疾病:疾病叙事研究》(1993)、弗兰克(Arthur Frank)的《受伤的讲故事人:身体、疾病与伦理》(1995)和库瑟(Thomas Couser)的《康复的身体:疾病、伤残与生命写作》(1997)。当然,这三类典型的疾病叙事之间并无明显的界限,多数疾病叙事的主题是混合的,既讲述重建身份的过程,也对自己的疾病身份进行反思,并相对于医疗机构及社会对疾病的建构形成“反故事”(counter-story)。尽管如此,不同疾病叙事的进程会揭示不同的主题倾向。
安德利亚(Andrea)代表了第一种阅读策略:“在回归正常之旅中,她[凯森]不得不找回自我,重新组装破裂的自我碎片,这样才能为真实世界所接纳。”②“回归正常之旅”表明,《被中断的女孩》讲述的是一个从不正常状态到正常状态的回归。而“重新组装……自我”表明,凯森在进入精神病院之前有一个完整的、正常的“自我”;由于某种原因,这个“自我”遭到了破坏,凯森在精神病院的经历帮助她找回了这个“自我”。但这种阅读没有考虑到《被中断的女孩》的实际叙述情景,因而或许完全是误读。
第二种阅读策略的代表是柯尔尼希(Jennifer Cornish),她这样评论:“凯森讲道多数病友最终都出了院,她还讲述了自己和她们中一两个后来见面的情形。这里,凯森的讲述相当以自我为中心,令人读起来感到不安,让读者依稀回忆起她进入精神病院前的那些行为。”③柯尔尼希的阅读明显注意到了凯森的叙述方式,即“以自我为中心”,这令柯尔尼希深感不安,因为正是这种自我中心才导致凯森进入精神病院的。如果凯森在自传的最后仍然表示出强烈的自我中心,无异于说她在精神病院的经历并未让她“回归正常”;如果考虑到这是三十年后的自传,那种“自我中心”式的叙述是否表明,三十年后的凯森仍然在遭受精神病余波的折磨?笔者完全同意柯尔尼希对凯森的叙述方式、对凯森写作自传时的精神状态的判断,但并不为此“感到不安”。柯尔尼希感到不安是因为,她认为“疯癫”状态对凯森不是一件好事,而笔者则恰恰相反,认为不仅仅在结尾,凯森传记的叙事整体上都是“疯癫”叙述;凯森写作这部传记时的内心自我一如她三十年前的自我,依然是抑郁而疯癫的;凯森能发现并通过讲述在身体上体验、即使是短暂地体验这个真实自我,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代表第三种阅读策略的是克莱蒙斯(Nadine Clemens),他在2002年度《美国研究——文学卷》中这样评论《被中断的女孩》:“这是苏珊娜的故事,是她走出麦克林医院三十年后讲述的,因此,这是一位现在已是成年女性的反思之作,她不能确信自己是否仍然疯癫。她甚至说,她以前是否疯癫过她也不能确信。”(354)在《被中断的女孩》中,凯森就她及病友的“精神病”与医生、护士们发生了多次冲突,但这些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病人和医疗机构在如何认识精神病以及如何处理精神病人方面存在差异。具体地说,凯森虽然承认自己的行为与常人不同,但她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没有逻辑,相反,她认为自己生活在拥有不同逻辑的“另一个宇宙”中。因此她否认“疯癫”这一标签,对医疗机构乃至整个社会不公正地对待所谓“疯癫病人”抱有怨恨和恐惧之心。严格地说,克莱蒙斯的评论并不准确,因为凯森十分确信,她的世界与常人世界不同;同时她也十分确信,如果这就是疯癫,她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的内心一直都是疯癫的,改变的只是她的外在行为和公众身份:由于社会压力,她不得不当“正常人”;但只要给她机会,比如阅读维梅尔的绘画,乃至写作《被中断的女孩》,她就会显示出内心的真实自我。
抑郁而疯癫的叙事声音
在自传中,叙事结构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更是一个意义问题。采取何种叙事形式,决定了传主为自己过去的经历赋予何种意义,或者建构何种自我。正如布鲁斯(Elizabeth W.Bruss)所说,“自传通常会让读者关注其叙述手段,关注其故事展开的过程,关注其是否成功抓住并表达出了其主体的特征。”(164—65)在讨论身份的建构性质时,弗莱曼(Mark Freeman)认为,“自我书写就是为过去之我寻找一个阐释框架,然后往其中添加相关信息”;“记忆不仅仅是重叙过去,而且是理解过去。”(29—30)在另一些批评家看来,人生经历与人生故事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但是人生故事不仅可以“表达”,还可以“改变”人生经历的意义。(Josselson:6—9)
三十年前,凯森在精神病院的真实情形如何,读者永远无法追溯,我们面对的只有她的自传文本。阅读这个文本,我们与其说获知了凯森过去的真实经历,还不如说了解了凯森写作自传时的心理状态,因为自传不仅仅关乎过去,更关乎当下。而深入凯森当下心理真实的唯一途径,就是去探索她组织文本的方式。《被中断的女孩》的最大结构特征是其片段性(episodic),全书由34个片段构成,每个片段讲述凯森的一段经历或一个思考。埃根(Susanna Egan)曾归纳出自传中的四大“经验模式”(patterns of experience):孩童模式(从无知到经验)、青年模式(英雄或艺术之旅)、成熟模式(心灵升华或落入不复)、忏悔模式(英雄讲述自己的故事)。然而,这些模式均不符合《被中断的女孩》,因为这部自传的各个片段之间没有起承转合的关联,因此无法串成一个连贯的、有某种意义的“人生故事”(life story)。以安德利亚为代表的“回归正常”阅读模式不适合《被中断的女孩》,因为这部自传根本就没有叙事结构来支撑这样的阅读。如果我们借用托多罗夫的归纳,“回归正常”故事的结构序列应该是:“正常——外力1——不正常——外力2——正常”。(Selden:60—61)但是,我们无法在《被中断的女孩》的34个片段中识别出这些叙事结构成分,相反,该自传的多数片段都处于平行状态,它们似乎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读者读到的只是凯森进入精神病院的前前后后,却无法从中捕捉到这段经历的意义所在。缺乏装载“意义”的结构,读者很难解释这部传记中的事件因何而来,又因何而去,只能将其理解为“疯癫叙述”。这显然是凯森有意为之:她讲述这段往事,并不是为了简单告诉读者她从这段经历中获得了某种顿悟、经验或新生,而是有其他更深层的意图。
如果《被中断的女孩》没有那种层层推进以昭示意义的叙事结构,甚至也没有按照某种时间结构来叙述,那么它的叙述到底遵从了什么逻辑顺序呢?仔细考察书中的34个事件片段,笔者发现,这些片段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后一片段往往因受到前一片段结尾的某个词或某个意义的触动而开始。凯森是在律师的帮助下进入精神病院看到她当年的病历,并开始写作她的回忆录的。在书的开端,她就原封不动地把病历的第一页直接呈现给读者,其中最重要的是医院的诊断结论“心理神经性抑郁症”,由此引发了她对“精神病”的思考,以及自己如何进入精神病院的回忆,这构成了回忆录的第一和第二片段;第二片段的结尾是“踏上一条他/她也许永无归路的险途”;第三片段讲述的则是精神病院一位女孩自焚的经历,结尾是“我们也许终究能走出来,而她却永远被锁在自己的身体里”;接下来的第四片段标题就是“自由”,讲述的是另一位女孩丽莎(Lisa)如何欺骗精神病院工作人员而获得了三天“自由”,最后一句话是“丽莎给我们讲了很多她在那自由的三天内经历的故事”;而第五片段的标题正是“生活的秘密”,但这里的秘密与丽莎的故事完全没有关联。布鲁斯认为,“自传主组织文本的方式体现了他的认识水平和个人才能。”(13)同样,自传的叙述方式还体现了作者的记忆方式。很显然,《被中断的女孩》中的记忆没有遵循事件的逻辑联系,而是一种连环式的记忆。为讨论方便,我借用中国传统的修辞手法“顶针”,将这种记忆方式暂命名为“顶针记忆”,其特点是不拘泥于某个特殊事件及其意义,而是在受到某种激发后,立即转向另一个事件。这种记忆方式恰恰是精神病人的特点之一。在“速度与黏性”这个片段中,凯森详细描述了这种记忆方式,并将其定义为“疯癫”的两个基本类型之一:
疯癫有两个基本类型:太慢和太快。……“太慢”这一形式的主要特征是黏性(viscosity)强。时间缓慢流动,就像水滴慢慢渗过被阻塞的厚厚的感知过滤器……黏性导致细胞麻木,与此相反,速度(velocity)给全身每块肌肉都赋予思维能力,使它们足以了解并评价自己的行为。感知太多,而且除了无数的感知外,还有无数对感知的思考,对有感知这一事实的思考……(75)
如此看来,“顶针记忆”就是一种“太快”类型的疯癫,因为在“顶针记忆”中,后一片段往往就是对前一片段的思考。记忆者还没叙述完或还未理解前一片段,即快速转入本质上并不相关的另一个记忆片段,其效果就是各种记忆和感知混杂在一起,让读者无法看清时间先后关系和主题意义。
如果说通过没有意义的结构和“顶针记忆”方式,凯森已经为读者建构出了一个仍然抑郁而疯癫的自我,那么在书中倒数第二片段中,当凯森叙述她和病友丽莎出院多年后见面的情景时,则几乎明确地表达了她对精神病院生活的强烈留恋:
[丽莎和她儿子]就要乘地铁回布鲁克林了。在地铁入口级梯,丽莎再一次朝我转过身来。
“你可想念那些日子,在那里面的日子?”她问我。
“嗯,”我答道,“我的确想念。”
“我也想念。”她摇摇头。“噢,呵呵,”她说,看起来相当快乐。然后,她们俩走下级梯,消失在地下。(164)
怀旧气息相当浓厚,凯森对精神病院生活的留恋溢于言表,这也正是引起柯尔尼希“感到不安”的原因所在:凯森仍然沉迷在“疯癫”的心理状态中,她仍然有再一次变成疯子的潜势。但柯尔尼希没有注意到的是,凯森这里除了表达一种留恋之情外,字里行间还传达出了深深的无奈。当丽莎意味深长地说出“我也想念”后,她们立刻“走下级梯”,“消失在地下”。这个细节实际上完全可以做隐喻式阅读:丽莎和凯森,乃至和她们经历相同的所有所谓精神病人,虽然可以怀念过去的经历,但在现实生活中她们只能将那段经历埋在心底,正如“消失在地下”一样。如果这个阅读是正确的,那么凯森将不会再一次变成疯子,她能做的只是在内心保持一份对“疯癫”的留恋。
寻找“自我”与叙事治疗
如果我们接受布鲁斯的观点,将自传写作看成“交流的行为”,(166—70)那么,凯森写作《被中断的女孩》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如前所述,凯森颇具“疯癫”特征的叙述方式无法让读者对该自传作出类似卢梭《忏悔录》那样的阐释。凯森并未在叙述中暗示过去的经历为她提供了“成长”或者“反思”的契机,相反,她的叙述让读者觉得她仍然沉浸在、甚至想重新回到那段抑郁而疯癫的经历中。让我们再次思考这一事实,即凯森是在三十年后才来叙述那段经历,此时她早已被医疗机构鉴定为“正常人”了,连她自己也已相信自己从那个“疯癫”的世界中跨回来了。然而,一个“正常”了近三十年的凯森为什么要选择使用如此“疯癫”的方式来讲述她过去那段“疯癫”的历史,而且流露出恋恋不舍的情绪呢?如果回到维梅尔的绘画,我们还会追问:为什么凯森要对这幅画做出与众不同的解读?为什么她希望画中女孩逃出来,并为这一想法泪流满面?很显然,凯森将自己等同于画中女孩,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她也是被禁锢的:将近两年的精神病院的经历让她学会了“正常人”这一身份的意义,在此后的三十年中,她一直被囚禁在“正常人”这一画框中,生活毫无生机,这一点在书中最后两个片断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内心深处属于自己的“疯癫”世界而不能见容于“这个世界”,只能被压抑而“消失在地下”。维梅尔的绘画唤醒了凯森心中的真实自我,让她在瞬间瞥见了自己的人生。正如画中女孩无法逃出画框,凯森知道她也无法逃出精神病院的经历给她设定的画框,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她为何泪流满面了。
在凯森眼里,维梅尔画中围绕在女孩身边那道“微暗而躁动的光”照亮了女孩的人生,同理,我们也可以将《被中断的女孩》及其写作看作一道光,给凯森提供了一个寻找自我,甚至体验自我的契机。在“正常人”这一身份标志下,凯森失去了自由和生命力,三十年生活在与“正常人”的矛盾较量中,读者可以想象凯森的痛苦和无奈。而书中字里行间充斥的那份“疯癫”、那份留恋,至少可以让凯森暂时忘却现实世界,走进属于她的自我世界;在那里,她可以按照自己的逻辑自由地呼吸,嘲笑甚至嘲弄精神病院里的心理医生、护士乃至整个医疗机构。因此,写作《被中断的女孩》对于凯森而言,无疑是一次精神恢复之旅。很明显,旅途归来凯森还是要回到现实生活中,但踏上这个旅途本身就具有足够的疗伤功用。在这个意义上,《被中断的女孩》也可以说是近年来西方学界兴起的“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④的一个标本。
在身体/灵魂这一两分法中,灵魂一直处于核心地位,身体常常被视为灵魂的反映。因此“疾病的身体”常常用患者的性格、爱好、生活环境、社会关系等加以解释,很少有人关注“疾病的身体”本身。(Couser:3—5)研究表明,有些疾病,比如抑郁症或疯癫症,其病因并非来自社会或家庭,而是因为患者体内缺乏某种化学元素所致。(Cheever:346—68)对这类天然的疾病,我们不应对其做出负面的隐喻式解读。桑塔格在《作为隐喻的疾病》(1978)一书中,从历时的角度讨论并批判了对疾病的隐喻式解读。弗兰克(Arthur Frank)则认为,“[疾病的]身体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2)国内学者近年来也开始关注“身体叙事”这一范畴,认为“真实作者身体的健康与否,或正在写作时身体所处的状态(兴奋、癫狂、烦躁等等)都会对其写作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作家本身所罹患的身体疾病也会影响该作家所采取的叙述方式”。(许德金等:28—34)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推论,患者发出的“声音”或者“叙述方式”,可以出反映他/她的身体状态。凯森在《被中断的女孩》中写道,抑郁症和疯癫症可以通过服用“苯丙胺”(amphetamines)加以控制。(95)这说明她的抑郁症和疯癫症更多的是一种身体状态,并不反映“灵魂”的某种性质;同时,凯森的叙述也没有将其病症归因于社会或家庭等外在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被中断的女孩》是凯森用疾病身体书写出来的真实故事,在她疯癫而迷恋的叙述中,我们读到的是她大脑中“神经生物节奏”(neurobiological rhythms)⑤的律动,而不是疾病叙事的隐喻含义。这也许就是我们在面对身体叙事、尤其是疾病身体叙事时,应该采取的阅读立场。
注释:
①文内《被中断的女孩》一书的引文,除非特别注明,均为作者自译。为免繁琐,以下只视需要出注。
②See Andrea,
③See Jennifer Cornish,
④按照查荣(R.Charon)等人的观点,医疗从业者应该具备足够的“叙事能力”(narrative competence)来聆听病人的自我故事,并通过这些故事找到病因和治疗方式。病人的讲述不仅可以透露出与其疾病相关的信息,讲述本身也具有疗伤之功用。参见参考文献所列Charon、Langellier and Peterson、Rudnytsky各条。
⑤自传叙事反映的是自传主大脑中的“神经生物节奏”这一观点,来自美国传记研究专家依金(Paul John Eakin)。(Eakin:121—32)同时参见唐伟胜主编《叙事》(中国版)第3辑(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