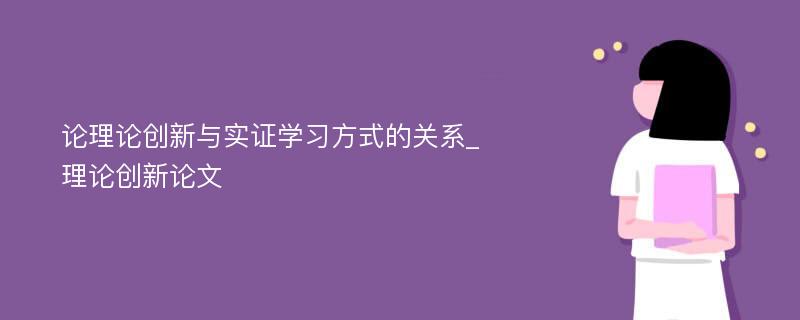
略谈理论创新与实证学风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风之论文,理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所经历的重大转型,我国学术文化也正经历着渐进式的却极为重大的历史性转型,人们的学术观念正在悄悄发生着重要的变化。《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及时组织“学风·文风·世风”问题的讨论,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对学术文化这种重要转型的反思与内应。
学术创新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有密切关系,已成学界共识。本人曾就文艺学、美学如何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寻求突破之途发表过意见。这里想换一个角度,就学术理论创新与实证精神、学风的关系作一思考。
我觉得理论创新与实证精神之关系,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关于理论探索和考据实证两种学问何者更有价值,或价值孰高孰低的问题;二是关于理论创新探索与考据实证在学术研究(治学)中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学界目前存在不同看法。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在批评浮华空泛的不良学风的同时,在部分学者中滋长了重实证考据,轻理论探索的风气。其中不无合理之处,却也明显存在片面性。在此,我想首先郑重推荐一篇好文章——傅杰先生不久前发表的《“抬轿人”和“坐轿人”如何对话——20世纪的义理与考据之争》(载《文汇报》2003年3月30日“学林”版)。该文借清代思想家戴震的一个比喻(将考据与义理分别比作“轿夫”与“轿中人”)为题,对清代以来,主要是20世纪学界关于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的争论作了深入的历史回顾,并提出义理考据不可偏废、是为学术发展之双翼的辨证看法。文章写得十分精彩,论据翔实,论证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我这里只想接着傅文补充几句。
我们说的理论创新与实证精神之关系,同传统义理与考据之学的关系虽不完全相同,却有相当大的一致与重合。其中强调理论探讨、创新与注重实证、考据这两种不同的治学侧重点,在不同学者的学术观念和追求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有的学者认为搞理论研究是“空对空”,是“从理论到理论”,是“哗众取宠”,学风浮而不实,“没有学术价值”等等;而唯有考据、实证才是“实事求是”,体现“扎实学风”,“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个个具体学术问题”。这实际上对以上这两种学问作出了价值的区分与评价。对此,我有一些不同看法。
我认为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同义理与考据两种传统学问在研究的具体内容上虽不完全相同,但从学术分类看基本一致。这两种学问究竟何者学术价值更高?恐怕不可笼统回答,而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论题以及对学术发展的推动、影响的大小等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一般说来,理论与考据两种学问在研究目的、对象、重点、方法等方面存在重要差别,判断它们在学术上的成就、价值有各自不同的尺度、标准,因此,我们不应对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学问作抽象、笼统的价值评判。换句话说,我觉得理论与考据这两类学问在现代学术中仍然各有其存在价值和重要地位,缺一不可,笼统地说哪一种学问更有价值或价值更高,均不妥当。看轻考据而单纯推重理论固然不对,但夸大考据作用而贬低理论的指导意义同样片面。
这两种片面性在整个20世纪曾一再重演,傅杰先生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仅就70年代以来,义理与考据之争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延伸的情况稍作补充。“文革”之后,随着现代迷信的打破,80年代的学术界也呈现出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百花齐放、学术繁荣的大好局面。西学的大量涌进,学术视野的极大拓展,世界性、跨文化比较眼光被广泛接受,研究方法的日趋多样,学科之间交叉互补和新学科的形成、建设,都为我国理论研究和创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契机,事实上,整个80年代学术发展中理论研究的成就在数量、质量上可能更为突出一些;与此同时,传统的考据之学在新观念、新方法、新手段的冲击下也获得了新的拓展和活力,也有长足的进步。但是毋庸讳言,在理论学术追求突破、创新的大气候、大氛围下,某些浮夸的不良的学风亦有所抬头:理论探索中重宏观概括、轻微观研究;重新学说、新观念的提出和新理论新体系框架的建构,而轻新学说、新理论具体依据的深入阐述和缜密论证;好移植、“创造”、玩弄、炫耀新概念、新命题、新名词、新术语,而不重视对这些新东西的深入研讨和扎实应用……其结果,滋长了某些浮华不实的学风,在一部分学者中实际上对实证考据之学有所看轻、贬低和压抑。
上世纪90年代之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一方面,学界对上述浮华现象的逐渐觉察和日益厌倦,促使理论研究中空疏、浮夸之风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另一方面,出于对西方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警惕和抵制,学界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呼声日益高涨,一度出现了“国学热”,传统的考据之学重新受到重视和推崇,实证的学风也得到极大的张扬,其中一个突出的标志便是陈寅恪先生实证考据方面的学术成就(他在史学理论方面的贡献同样巨大)从学术版图的边缘移到中心位置。相对而言,理论研究和创新在一部分学者心目中受到冷落和看轻。
从80年代到90年代,理论研究与实证之学在我国学术文化中的地位出现上述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我以为虽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追根究底,恐怕与我们学界、与我们部分学者对两种学问所持看法存在某些片面性不无关系。
所谓合理性,一是指80年代理论探讨、创新对我国整个学术文化的建设和推进功不可没,这种建设在性质上是突破性的,是对“文革”乃至建国以来中国学术受“左”的路线的压制造成的僵化、狭隘、沉闷局面的猛烈冲击和根本突破;在范围上则是全局性的,是对人文社会科学所有学科的全面推进,其中也包括对实证考据学问的推进;二是指90年代以来实证学问地位的提升和理论研究地位的相对降低,对于那些迷恋于空疏庞大的宏观理论体系而无视微观实证依据的学者无疑是一付有效的清醒剂,对于80年代以来学界滋长的华而不实的浮夸学风也是有力的冲击和反拨,同时对于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夯实学术文化建设的根基也有好处。
所谓片面性,则是指80年代理论学术空前发展的大潮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吸收西学的过程中出现良莠不分、生搬硬套、简单移植的现象,追求理论创新时满足于新观点、新学说的提出,而疏忽于对这些新说作细致的考据和缜密的实证,导致其根基不牢,易成过眼云烟,尤其在客观上助长了一部分学者浮华不实、投机取巧的不良学风,这也正是后来遭致实证学问批评的主要原因;90年代以来,实证学问的倡导对学界的浮躁风气不啻是一付良药,但过分走极端却也会对理论探讨和创新造成一定程度的看轻甚至压抑,这种现象的存在已是不争之实了。
我觉得,造成以上两种治学的片面性的根由,还是在对两种学问各自价值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上存在误区。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从傅杰先生文中转引一下尊重义理与考据两种学问的思想家戴震的看法。戴震面对当时代表学术主流的考据派人士朱筠只承认他的考据成就而批评他“空说义理”,是“将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时,叹曰:“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可尽我,是犹误轿夫为轿中人也。”其意如傅文所说:“思想家是坐轿子的,考据家是抬轿子的,只重视我的考据而忽略我的思想,那是只把我当作轿夫了。”戴震用轿夫与坐轿人比喻这两种学问,我以为并不一定十分准确,却也道出两者的基本关系:首先,两种学问缺一不可,坐轿的整个行为(学术行为)必须有轿夫与坐轿人共同组成,缺少任何一方,这一行为就不能成立;其次,考据之学是学术的基础,无此依据,任何思想、义理都立不起来,恰如若无轿夫,坐轿人寸步难行;再次,义理、思想是学术研究的追求和目的,只为考据而考据,不作义理阐发和思想提升,整个学术文化建设就得不到真正的推进和发展。这也如同轿夫是为坐轿人而抬轿子的,而决不会满足于抬不载人的空轿子一样。戴震既是考据大家,又是思想大家,他的考据显然不是为考而考的,相反,他的考据最终服务于其义理的阐发和思想的提出。他毕生从事考据,决不会像今天某些理论工作者那样因不懂考据而轻视考据;但他也决不满足于仅仅做个考据家,他也有理论追求,还是个大思想家,他痛苦的是,人们对他后一方面的追求和成就视若罔闻,甚至指责、贬抑。
戴震的学术生涯对我们当前的学术、学风建设极有启示,它告诉我们:理论与实证两种学问其实是密切相关、互补互动、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任何抬高一个、贬低另一个的做法都是片面的,不足取的,都会阻碍学术的健康发展。而若能自觉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则恰为鸟之两翼,协同展动,对学术发展极为有利。
具体来说,在当前的学术建设中,一方面,理论创新需要以实证、考据为基础和支撑,否则会成空中楼阁,易于倾塌;另一方面,实证、考据需要理论指导和提升,才有可能从实证、考据成果中提取出“微言大义”,更充分地发挥其为理论创新服务的功能。在当代学术中,无论中西,都有大量例证可以说明这个道理。比如80年代以来陈尚君先生在唐诗考据方面作了出色的工作,他的《全唐诗补编》从大量非唐诗中发现和考订了《全唐诗》未收的唐诗达5000余首,相当于《全唐诗》的十分之一强。这项考据成就对拓展、推动唐诗研究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如将这项考据成果束之高阁而不作为唐诗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实证基础,它的学术意义就会大打折扣。又如王振复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一书,我以为成功地体现了理论创新与实证考据的互补互动,该书第二章三、六两节分别对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抄本和儒家《性自命出》篇作了考证与理论有机结合的全新阐述,提出了一些前人未发的新观点,并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这里,理论对考据的指导、对所考据对象的深层意义的发现和开掘,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同时,考据、实证对理论创新强有力的支持也一目了然,限于篇幅,这里不作具体介绍了。
其实,在西方这一学术法则也不例外。海德格尔在对基础存在论论证时,曾引过老子的“道”的概念,并从中西方语义学、语源学角度作过详细考证;德里达提出解构理论也是从对“文字学”及文字、言语、逻各斯等西方基础学术范畴的哲学、语义学、词汇学的考据切入的。当然,其考证的目的十分清楚,是为其理论、学说的建构服务的。
顺便提一下胡适“五四”时期在西方实证主义思想影响下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理念,其实这也是一种注重理论创新与实证考据相结合的治学方法,至今我们仍然认为是具有一定合理性和价值的。
总之,在当前,我们应当把90年代开启的重实证的治学精神继续发扬,但不应加以绝对化,更不应走向轻视理论创新的极端,而应努力把追求理论创新与倡导实证学风有机结合起来。这是走向学术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
写于7月梅雨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