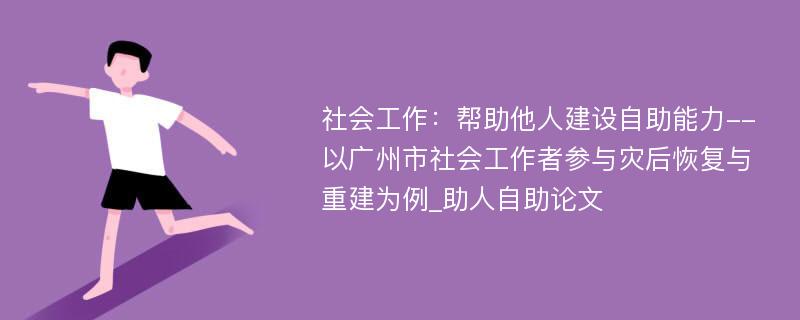
社会工作:通向能力建设的助人自助——以广州社工参与灾后恢复重建的行动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工论文,社会工作论文,为例论文,广州论文,能力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0)03-0141-08
从2008年6月24日至今广州社工参与灾后恢复重建的行动历时一年①。期间广州社工扮演了资源链接者的角色。中大—香港理大映秀社工站将来自国内外慈善组织近150万元的救灾物资链接到汶川县映秀镇、绵篪镇、草坡乡最偏僻的5个行政村,在灾难救助中既发挥了拾遗补缺的作用,也维护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与此同时,广州社工还扮演了“映秀母亲”同行者的角色。从“5·12”震后50天起,十多位失去孩子的母亲、失去至亲的女儿、失去家园的妇女们,在广州社工的陪伴支持下,重新拿起针线,制作羌藏绣品,或绣自己创新的儿童画,寄托哀思,持重前行。至今,“映秀母亲”已凝聚了三个乡镇五个行政村近100名妇女,制作出400余幅羌藏儿童画绣品,他们绣花疗伤的同时,正在走出一条可持续生计发展之路。本文通过广州社工链接资源和“映秀母亲”刺绣小组的行动案例,试图说明在“5·12”灾后恢复重建的独特社会文化环境中,社工之所以同时扮演资源链接者和社区民众同行者的角色,这与社工“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公平正义”的价值观紧密相关。社工在面对灾区民众一无所有以及救灾物资分配不公平的现状时,必须扮演资源链接者的角色,尽力将最宝贵的资源链接到最需要的人群中,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是社工最基本的救济式助人行动。但另一方面,从社工自助的理念出发,我认为单纯从受助(prosumer)②的角度从事社会工作,只会强化灾区民众的依赖性,弱化受助者的能力,增强社工的无力感。而完整的社工助人自助③更应该从自助能力建设(self-help capacity building)的视角深刻地理解社会工作的本质。本文先从理论上澄清助人自助与能力建设的关系,然后运用具体的行动案例详细阐述广州社工如何通过与社区民众同行逐步通向自助能力建设。
一、助人自助与能力建设
(一)专业语境下的助人自助
西方及中国港台主流的社工教材(Johnson,Louise C.,1998;周永新,1994;林万亿,2002)一般都将社会工作定位于一种助人的专业(解决问题)。深受西方和中国港台专业社工的影响,中国大陆社工专业的统编教科书从专业化的角度将社工定义为:“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服务活动。这一定义指出社会工作的本质是一种助人活动,其特征是提供服务。更确切一点说,社会工作是一种科学的助人服务活动,它不同于一般的行善活动。”(王思斌,2006:12)由此可见,国内外社工专家大都侧重于从助人的角度理解社会工作。
受上述专业社工定义的影响,中国官方基本上接受了社工专业的助人本质。例如,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要“建立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按照中共中央《决定》的精神,国家有关部门将社会工作定义为:“社会工作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体现社会工作核心价值理念,遵循专业伦理规范,坚持‘助人自助’宗旨,在社会服务、社会管理领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帮助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群体、组织和社区,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促进社会和谐的职业活动。”(王思斌,2007:4-5)
综上所述,尽管学术界的定义注重社工助人的科学性,而官方的解释更加强调社工在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方面的作用,但就社工的助人性质而言,双方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在当前社工发展的现实语境中,中国学术界和官方既从学理层面(研究)不断澄清社工的“助人”性质,更致力于从实践的层面(实务)对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群体和社区提供服务,实施帮助。从救助的理念出发,社工扮演救济者或扶助者的角色,直接帮助服务对象解决问题④。相比之下,学术界和官方无论是对“自助”的学理阐释,还是从实践层面使工作者和社区民众在互动中实现自立自强都还不尽如人意。正如香港资深社工区结莲所说:“虽然概念上我知道‘助人’和‘人自助’之间存在着一种延伸的关系:即由‘助人’开始以达致对方‘自助’。但在实践当中,我们往往只聚焦于助人,而忘却令对方自助的方面。”(区结莲,2009:5)
笔者近十年的专业实践经验表明⑤,单纯从受助者(prosumer)的角度从事社会工作,只会强化社区民众的依赖性,弱化受助者的能力,增强社工的无力感。而完整的助人自助更加强调从“自助”的角度深刻地理解社会工作的本质。“自助”最起码应该包含两方面的涵义:一是对工作者而言,社会工作作为一项职业并不是单方面的助人活动(救助式的)。稍有实践感的工作者都会明白,真正的助人自助是工作者与社区民众在同行中的共同成长和改变,在助人的关系中生命之间是互换和增值的。因此,自助首先体现在帮助服务对象的同时,社工的自我成长(生命影响生命)。正如佩恩(Payne,1995)所说:“社会工作是一种互相作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案主改变了工作者及社会工作的本质,也因此改变了社会工作的理论。此一论述的目的在于反驳社会工作只是一种催化过程且案主是由不受改变的社会工作者及机构所改变的概念,相反的,上述论述指出案主也会改变社会工作者和机构。”自助的另外一层含义是社工必须致力于激活⑥社区民众自力更生的能力。毕仁(Butrym,Z.T,1976)在《社会工作的本质》一书中指出,社会工作的哲学思想主要源自三个假设:第一是对人的尊重;第二是相信人有独特的个性;第三是坚守人有自我改变、成长和不断进步的能力。依据毕仁的思想,周永新(1994:10)将社会工作的基本假设归纳为:尊重他人、人是独特的个体、人有改进的能力。因此,从人本的意义而言,社会工作的根本宗旨就是相信人的独特潜能,激活人的自助能力。从自助的理念出发,通过社工与社区民众同行者的角色定位,激活个人、群体和社区自我改变、成长和不断进步的能力。受研究主题的限制,在与社区民众同行过程中如何激活社工的自助能力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值得另文探讨。本文仅以“自助”的第二层含义探讨迈向能力建设的助人自助。
(二)能力建设中的自助能力(self-help capacity)
之所以选择能力建设作为助人自助的形容词,不仅因为激活人的自助能力与能力建设的目标相契合,而且能力建设是近年社区发展中一个广为使用的说法,它经常被拿来与“赋权(empowerment)”、“参与”等饶富批判意味的实践概念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透过社区民众能力建设以促进社区转化(Moyer,et al.,1999; Li,et al.,2001,转引自刘晓春等,2007),或是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方法的指称(Eade,1999)。至于能力建设中能力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大部分文献并没有明确指出。刘晓春和古学斌(2007)说:“我们提出,在社区发展实践里,民众的能力除了一般认为的外在支持和技术能力外,更重要的是自我意识和知觉能力。”古学斌(2008)还梳理了能力建设的几个假设:
每个人都有实践能力,虽然这些能力不一定为人所知,甚至有时连自我也未能意识到;一切抑制主体实践,或剥夺主体实践权力的力量,是造成人民贫困和苦难的症结。从社区发展的意义上看,能力建设要孕育和恢复的是当地民众的能动性,促使当地民众觉知自己的主体价值,并实践自己的道路。
根据上述学者的论述,结合映秀社工站参与灾后恢复重建近一年的实践经验,我将自助能力概括为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一是指主体的觉醒能力,即主体觉醒到自身的困境并有强烈的改变愿望;二是指主体的实践能力,尤其是主体的组织与合作能力;三是主体的改变(成长)能力。以上三方面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主体意识觉醒—积极付诸实践—实现自我改变(自助)的循环往复。
本文借助上述助人、自助、自助能力建设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视角,以广州社工参与灾后恢复重建的具体行动案例,再现(representation)广州社工由助人开始试图达致对方自助的艰难历程(自助能力建设),从而反省社工的助人自助。
二、从救助到自助能力建设
2008年6月至2009年3月间广州社工之所以积极链接资源、提供救助,是因为震后映秀民众一无所有,与此同时,大量的救灾物资又难以分配到边缘人群手中⑦。于是,广州社工秉持弱势优先的价值观,在灾难救援中扮演了资源链接者的角色,将最宝贵的资源链接到最需要的人群中(这是社工最基本的救济式助人行动),以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据不完全统计,广州社工站挂牌成立近一年来,社工共链接到价值150万元的物资发放给汶川最困难的群众。广州社工链接资源的基本做法是:第一步由前线工作员通过走村串户评估边缘人群(妇女、孩子、老人、边远村寨的村民等)的需求,撰写需求评估报告;第二步将需求报告透过关键人物(广州社工行动中社会关系广泛的有心人)传递给广东民间公益机构(如广东狮子会等)或将需求信息放在网站上;第三步当得到国内外热心人士的支持后,广州社工一般会协助资助机构的代表采购救灾物质并动员当地妇女小组(社工发育出来的组织)的骨干一起将物资送往目标人群。
广州社工的实践证明链接资源的做法(救助)像一把双刃剑。剑的一刃是共赢的:社工及时有效地满足民众最紧迫需求(发放床铺和越冬棉衣等)的同时,也赢得了扎根映秀的合法性。当老百姓和地方官员看到社工总是去最边远的村寨,总是进最破烂的人家,总是将资源给予妇女和鳏寡孤独时,他们认定社工是好人。2008年6月当社工冒着生命危险进入映秀镇最偏僻的黄村家访时⑧,有村民热泪盈眶地说:“你们是党中央派来的,共产党好啊!要像33年那次地震,我们早就死光了。”2009年3月当社工爬上草坡乡碧塔村海拔最高的山寨访问一户老人时,老人家以为是红军来了(这里是当年红军走过的地方)。很明显,许多民众眼中的社工形象就是党的形象。所以,熟知社工的政府官员常说广州社工在灾难救援过程中发挥了拾遗补缺的作用,社工行动提升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但剑的另一刃具有明显的破坏作用:从可持续性来看,社工的救助行为强化了灾区民众的依赖性,弱化了受助者的能力,增强了社工的无力感。从2008年底开始,广州社工的救助行为首先被一些妇女质疑:“你们就是一小点一小点的帮,像撒胡椒面一样,也解决不了我们啥子问题(建房子等),你们要是帮我们找到活路(生计),我们就可以自己解决问题了。”与此同时,有些社工帮助过的村民要么守在板房等待救济,要么时常登门索取救灾物资;有些社工不断照顾过的孩子开始对廉价物品和小组活动不屑一顾,他们甚至进入社工站小偷小摸。
毫无疑问,广州社工必须摆脱受助(prosumer)的困扰,才能使社工站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当时社工站从两个方面寻找转机:一是利用最新链接的广东金秋慈善基金会一笔善款启动“编织毛衣、助人自助、社区互助”的送温暖计划,以改变社工单方面的救助模式,实现社区互助。与以往的救助不同,这次广州社工不是直接向社区民众发放御寒毛衣,而是将社区妇女组织起来,动员大家为自己织一件毛衣的同时,必须为身边的“三孤”人员(孤老、孤寡、孤儿)织一件毛衣,这是她们领到毛线的先决条件。没想到有60多位板房区妇女参与了这一社区互助计划。她们领到毛线后,有的妇女为有家遇难的邻居织毛衣、有的妇女为外出复课的地震孤儿织毛衣、有的妇女为孤寡老人织毛衣。毛衣织好后广州社工以村为单位举行了现场赠送毛衣活动。当妇女们将自己亲手编织的毛衣给孤寡老人和地震孤儿穿上时,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有的老人含泪说:“我的女子(女儿)都没给我打过毛衣啥。”这次行动使社工意识到只要稍微转换一下自己的角色就能够使社区民众逐步摆脱“等”、“靠”、“要”等负面的“灾民”形象,从而实现社区互助与自助。
广州社工摆脱受助困境的另一个尝试是推动“映秀母亲”羌藏刺绣小组逐步迈向能力建设的助人自助。广州社工一进入映秀,就竖起了“助人自助、点燃希望”的旗帜,社工努力从绝望中看到希望,从废墟中看到民众自力更生的能力。社工组织起100位“映秀母亲”(尤其是丧亲母亲)寄托哀思,生产自救。至今“映秀母亲”已经成为汶川妇女自力更生、重拾信心的品牌。从“映秀母亲”羌藏刺绣小组的成长经历既可以清晰地看到“映秀母亲”的觉醒能力、实践能力和自我改变的能力,也可以从社工与“映秀母亲”同行的过程觉察到社工作为协助者(facilitator)和中介者(mediator)的角色定位。下面先完整地呈现“映秀母亲”刺绣小组曲折的成长过程,然后在第三部分总结和反思激活自助能力的过程。
小组缘起⑨
震后第43天,广州社工来到被称为“震中的震中”的陈坪村。住在帐篷区的妇女和社工没说几句话,就直接把话题切入到孩子。董四妹,两个女儿都在映秀小学遇难,她从胸前挂着的包包里,拿出女儿的照片给社工看,大女儿小字生前爱画画,董四妹把女儿的画扫描了和照片一起存在U盘里,随身携带。蔡英,女儿上四年级,儿子上学前班,双双遇难,她的手机里还有孩子生前可爱的笑脸。除了她们,围坐在社工身旁的几个妇女,每家都有亲人遇难。她们讲着讲着,好像是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时低下头去,深深地叹一大口气。
第三次到陈坪村帐篷区的时候,社工发现了余二妹的一幅十字绣画稿,才知道这里的妇女有刺绣的传统,羌藏妇女一般都会做传统的羌绣、藏绣,汉族妇女也会纳鞋垫、做十字绣。董四妹这些天正在做十字绣“福”字,她说这个字最简单,先做着玩玩。董说:“住在帐篷里,板房还没分,不知道将来干啥子,一个人离了婚,孩子又没得了,天天吃了睡、睡了玩,一到晚上心里就发慌,不如做点手工,啥子都不想。”
正是董四妹的这些话启发了社工。社工开始设想,能不能利用当地妇女的特长,发育妇女刺绣小组,既为妇女们创造团体疗伤的机会(大家聚会谈心里话),也有可能将刺绣发展成为生计项目。
小组发育
当社工第四次来到陈坪村帐篷区的时候,余二妹已经带着几个姐妹坐在危楼前边做绣活边等社工。余二妹是羌族,做一手好绣活。社工上次带走了她的几双鞋垫给其他同事看,有人提议寻找慈善团体收购这些精美的绣品,使妇女们获得劳动报酬,从而转变她们被救助的灾民形象。
至于收购绣品的用途当时有两个方案:一是把绣品赠送给映秀的丧亲家庭,也算是对丧亲者的小小安抚;另一个方案是把妇女的绣品带到广州,以“映秀母亲”为主题举办一次展览拍卖会,将拍卖所得全部返还“映秀母亲”,作为妇女小组下一步生计发展的创业基金。社工此行的目的是征询妇女们对这两个方案的意见。
余二妹和姐妹们都比较倾向第二个方案。余说:“地震发生后国家和很多志愿者都来帮我们,让我们很感动。但是将来的生活还是要靠自己。我们要照顾家庭和小孩,很多人没办法外出打工。如果在家绣花能带来收入,哪怕只有一点点,我们也很乐意去做。”董四妹说:“如果要买绣品送丧亲家庭,我们就不要钱,因为社工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应该送社工绣品才对啊。”最后大家决定一起努力筹备广州拍卖会,将刺绣发展成为可持续的生计项目。
这次讨论非常热烈,妇女们甚至商量好要合绣一副主题画,画面要绣上“广州”、“汶川”、“映秀”、“512”、“母亲”、“娃儿”等字样。董四妹的心愿是把女儿的遗画全部绣出来。当时社工建议多绣一些传统的民族图案,这才具有文化价值。尽管妇女们将信将疑,但她们很快地付诸了行动。
社工立刻将上述想法写成项目建议书提交成都基督教女青年会,没想到仅过了10天,青年会就批准了这项计划。社工获得6万元基金用于收购妇女的刺绣作品。与此同时,董四妹搭乘社工的便车到成都买线买布,余二妹拿出从废墟里掏出来的针线布分给组员,大家一边研究绣法,一边在板房和小树林里开始刺绣。就这样陈坪村的妇女刺绣小组发育起来。
小组矛盾
董四妹第一次从成都买线和布回来后,就有妇女向社工告状:“董四妹不懂刺绣,买回来的线颜色不鲜艳,绣出的花不好看。”社工反问道:“不是你们集体决定让董四妹去买的吗?”后来妇女们知道告状没有用,便开始疏远董四妹,亲近余二妹,因为余二妹懂刺绣,又愿意把自己家的线分给大家使用。当召集妇女开会时,董四妹喊不来人,社工只有请余二妹出面。社工建议董四妹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只要涉及集体利益,都要商量决定,这样才能责任共担。
这段时间董四妹也有很大的变化,她将孩子的遗画绣成了半成品。社工鼓励她将作品拿出来跟姐妹们分享。没想到这件未完成的作品得到大家啧啧称赞,有的妇女还向她请教儿童画绣法。得到赞同的董四妹脸上露出了笑容,她重新在小组活跃起来。为了配合妇女们刺绣儿童画的愿望,社工将幸存的孩子们组织起来,让儿童通过绘画释放心情、畅想未来。后来孩子们充满想象力的画作成为“映秀母亲”创作的源泉,一幅幅精美的儿童画在母亲们手中得到升华。
小组成长
为了让更多的妇女受益,社工还深入映秀镇的其他两个村发育妇女小组。没想到新建小组的过程不仅壮大了“映秀母亲”,而且促进了陈坪村妇女小组精诚团结。
陈坪村妇女小组建立一个多月妇女们就绣出一批传统的羌绣和儿童画作品。社工与成都青年会积极筹备第一次收购会,希望借此机会鼓舞妇女们的土气。那么,如何确定每一幅绣品的收购价呢?社工借鉴云南等地小组定价的经验,确定了三项定价原则:一是劳动价值;二是艺术价值(包括精美程度及“5·12”价值等);三是文化价值(要挖掘古老的羌绣图案等)。
原则好定,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有的妇女定价太高,有的妇女定价过低。最后一个折中方案是大家把相同类别的绣品排列起来,评选出一幅最好的作品。这幅作品的实际价格是按每天8小时折合的天数乘以每天20元的价值。在最好作品的基础上,其他绣品依次降低。大家还规定,为了鼓励制作精品和初学者,最好的作品和新绣品都加价50元收购。就这样,社工与妇女们一起讨论出了每幅作品的价格。
2008年8月24日,在陈坪村一间尚未正式启用的板房厨房里,妇女们将自己震后绣制的第一批作品漂漂亮亮地挂出来迎接收购。会前她们还兴高采烈地跳起了舞蹈,这是震后妇女们第一次开心地跳舞。在这次收购会上妇女们第一次拿到了不是救济款的劳动报酬。拿到钱后她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归还社工当初借支给她们的启动资金103元。
第一次收购会激活了汶川妇女自力更生的能力。除了陈坪村的妇女之外,远在汶川县草坡乡和绵篪镇最偏僻3个村庄的妇女也找到社工希望通过刺绣生产自救。很快地社工又在金碧、沙坪、小河3个行政村发育了3个羌藏妇女刺绣小组。到2009年1月2日,社工举办第五次绣品收购会的时候,妇女小组已经从1个扩展到5个,成员由10人发展到100余人,至少有100个汶川家庭通过刺绣项目受益。
小组转型
从开始发育妇女刺绣小组社工就强调将“5.12”作为卖点不具备生计的可持续性,准备借助“5·12”一周年纪念活动推动妇女小组转型。为此,社工除了鼓励妇女们制作民族艺术品,走公平贸易的道路外,还积极筹备“5.12‘映秀母亲’羌藏绣品慈善拍卖会”,期望为“映秀母亲”筹集一笔创业基金,由此推动刺绣小组可持续发展。经过一年的紧张筹备,2009年5月12日下午两点拍卖会在广州市越秀区文化艺术中心如期举行。出席会议的嘉宾除了7名“映秀母亲”的代表外,广东狮子会的全体理事、广东省金秋慈善会的顾问等200余人参与了竞拍活动。最后有156幅精美的绣品被拍出,共筹集善款20余万元。
拍卖会的第一件绣品是董四妹孩子的遗画“小熊猫”,起拍价为1,000元,最后以20,000元成交。董四妹激动地对媒体说:“我感到我女儿已经是一个画家了。”余二妹临摹的祖传绣品“婚丧图”也以11,000元的高价拍出。创造现场单幅拍卖最高纪录的绣品是余二妹、杨二妹等四人合绣的“广州汶川心手相连”的主题画作,狮子会会长以40,000元拍得并赠送给拍卖会的主办单位。
总之,经过一年的努力,“映秀母亲”已经成为一个汶川母亲们自力更生、重拾信心的品牌,以“映秀母亲”命名的绣坊、食堂、金碧生态游等灾后重建的可持续生计计划有的已经启动,有的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社工坚信在这次义卖所得“创业基金”的支持下,在广州社工3年的陪伴下,象征自强不息和自力更生的“映秀母亲”一定会在四川汶川开花结果。
三、结论
上述“映秀母亲”自助能力建设的经验表明“社会工作是工作者与案主互相作用的过程”(佩恩Payne,1995)。正是社工与“映秀母亲”的同行和妇女小组自力更生的实践,激活了社区民众的自助能力。下面从社工的角色定位和社区民众的实践能力两个方面总结自助能力建设。
(一)同行中的协助者(facilitator)和中介者(mediator)
一般的社工教科书都会提及社工作为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或使能者(enabler)⑩的角色定位(Jonhnaon,1998;林万亿,2002),这是典型的单方面助人的思维习惯。受到问题解决模式的影响,在最初几个月广州社工不断向映秀民众提供救助,其结果基本上是好心办坏事。
“映秀母亲”的案例表明,要从救助达致自助能力建设,社工必须摆脱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和救助者的角色定位。在刺绣小组的成长中,社工扮演了社区民众同行者的角色,从开始酝酿小组到小组转型,社工始终与“映秀母亲”一路同行。刚接触到陈坪村妇女时社工不是从江河破碎和丧亲剧痛等现实问题出发,而是从妇女们刺绣的传统优势开始,不断深入废墟和帐篷与妇女们平等对话,共同发育了刺绣小组,逐步激活“映秀母亲”自力更生的能力。
仔细回顾小组的成长过程,我们发现社工与“映秀母亲”一路同行中除了相互支持、陪伴和彼此倾诉外,同行中社工还扮演了协助者和中介者的具体角色。首先,通过社工的具体协助和中介,“映秀母亲”链接到必备的绣品收购资金和持续发展的创业基金。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成都青年会和香港泽善基金会启动资金的支持,小组不可能发育起来。同样,正是依靠社工的中介作用,广州市慈善会、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中大—香港理大映秀社工站合作搭建起“映秀母亲”羌藏绣品义卖会的平台,借助这个平台,广东狮子会和金秋慈善基金会等才得以慷慨解囊。其次,在社工的协助和中介下,刺绣小组与海内外许多机构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透过与这些组织的具体合作,“映秀母亲”逐步自立自强。例如,社工将云南和贵州少数民族刺绣小组负责人请进映秀,让她们向刺绣小组现身说法。此外,社工组织刺绣小组的代表赴贵州和广东交流学习,以此激活妇女们的精品意识与合作能力。通过“5·12”广州拍卖会,映秀妇女还与香港等境外公平贸易组织建立了销售关系。总之,社工在同行中协助者和中介者的角色定位,是激活社区民众的能动性和主人翁意识的前提条件。
(二)在实践中觉醒与改变
“映秀母亲”的故事告诉我们,人在危难时刻绝不会坐以待毙,相反这时主体的实践、觉醒和改变能力会立刻激活。首先是“映秀母亲”的实践能力“逼迫”社工在工作上不敢有丝毫懈怠。当第一次到陈坪村时,正是董四妹等丧亲母亲在废墟旁的刺绣举动激励社工将妇女们组织起来。后来当社工提供两套方案供妇女们选择时,她们毫不犹豫地走上了生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仅如此,妇女们设计、生产绣品的能力超出社工的想象力。例如,当社工第五次收购绣品时,妇女们竟然制作出价值5万元(我们预计只有2万元的产品)的绣品,而且许多绣活的精美程度令人称奇。从某种意义上说,“映秀母亲”是先行者,她们的创举不断推着社工往前走。
其次,社工之所以能够坚守映秀,是被“映秀母亲”在实践中的觉醒和改变所感染。区结莲(2009:5)反省道:“我开始觉醒到,若要让对方变得有能力自助,应该从对方自己的觉醒开始:觉醒自己身处的困境,觉醒自己在生命中有选择的可能,觉醒自己想要些什么、不想要些什么。”当社工在同行中扮演好协助者(配角)和中介者(搭建合作的平台)的角色时,“映秀母亲”就会推己及人。例如,2008年底,暴雨将几百辆汽车阻挡在映秀板房区3天3夜,许多人乘机向司机高价出售盒饭。余二妹和杨二妹便发动刺绣小组成员连续3天免费为司机送饭。她们说:“原来都是别人帮助我们,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帮助别人了。”董四妹和杨二妹是陈坪村妇女刺绣小组的领头人,但她们常说:“‘映秀母亲’项目不是我们陈坪一个村的,也不是我们映秀一个镇的,它是我们整个汶川母亲的……我们应该帮助更多的母亲们。”她们说到做到,与社工一起将妇女小组扩展到汶川的其他乡镇,惠及了更多的汶川母亲。
(三)自助能力建设的两难困境
其实“映秀母亲”自助能力建设并不是那么理想,现实状况是社工和“映秀母亲”的自助能力提升经常处于两难的困境中。对社工而言,同行是非常艰难的。首先,深受问题解决思维模式的限制,社工经常不自觉地扮演专业救助者的角色,致使工作者与“映秀母亲”的同行地位是不平等的(专业的主客体助人关系),其结果时常背离社工能力建设的初衷。其次,无论社工以多么平等的姿态与刺绣小组同行,在“映秀母亲”的心目中社工是资源和知识的拥有者,她们必须以“服从”、“等待”、“迁就”,甚至“讨好”等方式与社工同行,这显然不利于自助能力建设(11)。最后,人的意识觉醒和改变不是线性上升的,当环境发生改变时工作者和“映秀母亲”都会出现倒退。例如,当在贵州和广州同行时,工作员和“映秀母亲”都表现出积极的思维和行为,但当重返各自的生活环境时,工作员和“映秀母亲”又回复到惯常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中。
收稿日期:2009-11-25
注释:
①中大—香港理大映秀社工站(原名广州社工站)是在广州市民政局鼎力支持下于2008年6月24日正式在四川汶川县映秀镇板房区建立。广州社工秉承助人自助、点燃希望的价值观,在社区—学校心理支持、妇女生计能力建设、资源链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得到当地民众、政府、援建方、驻军等广泛认可。为了将广州社工界关注民生、服务民众的社工精神发扬光大,与灾区民众共同走过灾后恢复重建的三年历程,从2008年9月开始中山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将广州社工站改名为中大—香港理大映秀社工站。关心映秀社工站的同仁请登录:http://www.yingxiu512.org(建设中)。
②这个英文单词是“专业型消费者”(即professional和consumer的合成词)的意思。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http://www.chinavalue.net/Media/Article.aspx?Articleld=39007。笔者用这个英文单词指称受助者是指在专业关系中案主(受助者)成为社工的专业消费者。
③我认为自助有两重含义:其一是主体之自力自强,其二是主体间互助。
④除了大专院校社工系师生或者用科研项目的方式(如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等)或者向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如中山大学、深圳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直接提供社会服务外,政府部门(如民政、工青妇等)也积极与大专院校社工系合作,直接向市民提供社工服务。这些实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工专业化发展。
⑤从1999年至今我和同事一直深入社会最“底层”广泛接触少数族群、普通农民、性工作者、吸毒者等社会边缘弱势群体,运用社工专业方法介入他们的日常生活,期望帮助受助者摆脱困境(助人)。但我们经常遭遇事与愿违的境况:即受助者的依赖性增强,能力被弱化,而我们社工越来越感到无能为力。这是我们最大的专业困扰。本文既是对专业实践的反省,也是对专业新尝试(自助)的总结和反思。
⑥之所以使用“激活”而非“提升”、“促进”等,正如区结莲(2009:5)所说:“‘提升’往往意味着一种‘高’、‘低’的二元对立关系,仿佛是高的一方做了什么令低的一方提升了起来,当中假设了能力和权力上的不对等,同时亦隐含着一种‘主位’(当然是‘助人’的社工)和‘客位’的关系。这个‘提升’的过程,也许是‘助人’了,但究竟是否能达致‘人自助’的效果,对于这个问题,我愈来愈质疑了。”因此,我使用“激活”意味着通过社工同行者的角色定位,为社区民众搭建起一个改变的媒介或平台,利用此平台激活工作者与社区民众的主体性和自助能力。
⑦2008年七八月间广州社工通过入户访谈评估到映秀民众有七个方面的应急之需,但这些需求从主流的救灾渠道基本上得不到满足。详细情况见张和清、裴谕新(2009)。
⑧基于研究伦理,本文涉及到的人名和村庄地名均为化名。
⑨有关“映秀母亲”成长过程的叙述有些直接引用裴谕新(2009),张和清、裴谕新、阎红红、刘念、杨明宇、苏巧平、卓彩琴(2009),阎红红(2009)等文章,有些是笔者对2009年一系列“映秀母亲”后续行动的呈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上述文章。
⑩我认为与“提升”、“促进”等词汇一样,“使能者”也预设了工作者与服务对象“高”、“低”的二元对立关系,仿佛社工做了什么令服务对象能力提升起来,当中假设了能力和权力上的不对等,同时亦隐含着一种“主位”(能力提升的社工)和“客位”(能力被提升的服务对象)的关系。因此,我使用同行者的角色定位,期望社工与社区民众在同行中激活主体性和自助能力。
(11)可喜的是妇女们也会通过集体投诉的策略挑战工作员。
标签:助人自助论文; 社工论文; 社会工作专业论文; 社区功能论文;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