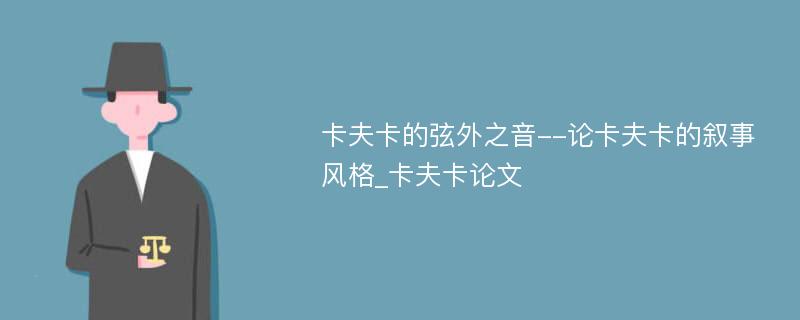
卡夫卡的弦外之音——论卡夫卡的叙事风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卡夫卡论文,弦外之音论文,风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若要开启门户紧闭的卡夫卡作品,到底需要一把钥匙还是一串钥匙?那钥匙是丢了,还是压根儿就不存在?〔1〕我们则认为, 卡夫卡的神秘首先来自其独特的写作方式。他的神秘在于他那清晰、平静而单调的叙述总是夹带一种惊心动魄却又妙不可言的弦外之音,所谓弦外之音,就是指不明说、不直说的艺术,如象征、反讽。本文拟就卡夫卡的弦外之音作一番探讨,说具体点,我们所要研究的,是将写作变成自我投影的卡夫卡,是从痛苦看出滑稽、以滑稽衬托痛苦的卡夫卡。
投影式的写作
1917年卡夫卡写了一则故事,1931年才由遗作保管人布洛德冠名为《平常的困惑》发表。故事全文如下:
平常的事件造成了平常的困惑。〔2 〕甲要和丙地的乙做一桩大生意。他去丙地预谈,来回各用了10分钟,还对家人夸耀自己的神速。次日他又去丙地,这是正式谈判。预计要谈好几个钟头,所以甲一大早就出了门。可是,尽管——至少甲是这么认为的——所有情况都和头天完全一样,这回他却走了10个小时才到丙地。晚上他精疲力竭地赶到那里,人们却说乙因为甲迟迟不到而大为恼怒,半个小时前去了甲的村子,他们在路上本该碰上的。人们劝甲等一等。甲又担心生意受影响,所以赶紧动身往家里走。
这回一转眼就走完这段路,他自己倒没太注意。他在家里听说乙大清早就来了——当时甲刚刚走;他在门口还碰到甲,还提到他们的生意,甲却说自己没空,要赶紧上路。
虽然甲的行为不可思议,但乙还是留下来等甲。他尽管多次问甲是否已经回来,但他还在楼上甲的房间里呆着。甲很高兴还能跟乙说话,向他解释这一切,于是就顺着楼梯往上跑。快到上面的时候,他摔了一跤,肌腱拉伤,他痛得差点晕了过去,他甚至喊不出声来,只能在黑暗中泣不成声,就在这时,他听见——不清楚离他远还是近——乙怒气冲冲地从楼梯下来,终于离去。〔3〕
这是一个离奇而悲哀的故事。说离奇,是因为它与我们的经验和理性相抵触,恐怕连相对论的鼻祖爱因斯坦也无法解释比如说同一个人在同样的状态下走同一段路为什么会有10分钟和10小时的差别;说悲哀,是因为甲来回奔波寻找乙,却总是鬼使神差,未能遂愿。这也是一篇非常典型的卡夫卡小说,讲述的是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势力对人的压迫与捉弄,使之最终陷入悲惨和绝望的境地。由于叙述者与主人公的感觉和思维保持一致,对重要细节语焉不详(“至少甲是这么认为的”,“不清楚离他远还是近”等等),所以这篇小说给读者留下了诸多困惑。人们不禁要问:卡夫卡究竟想说什么?据说卡夫卡是有记录或者说描写梦境的嗜好的,把这个故事看成一场梦也未尝不可,但多数研究者还是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比如奥地利卡夫卡专家索克尔就根据卡夫卡日记中的一句话——“因为急躁,人类被撵出伊甸园,因为急躁,人类又无法返回伊甸园”——推断,卡夫卡在讲述欲速则不达的道理,〔4 〕我国的谢莹莹教授则认为这说明人的相互交往十分困难,事态又是那样变幻无常。〔5〕这些见解很有启发,不过我们想换一个角度, 用深层心理学的眼光来透视这个故事。
若论深层心理学对文学批评的意义,我们自然要想到弗洛伊德对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所作的阐释。《俄狄浦斯王》是一部戏剧反讽的经典。戏剧反讽是一种特殊的反讽形态,它专门揭示意图与效果的对立,表现事与愿违或者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类可笑亦可悲的现象:俄狄浦斯为了避免得尔斐神庙预告的杀父娶母的命运,匆匆逃离科林斯。走到道利亚路口,他杀死一个跋扈的老人——他的生父拉伊俄斯。到了忒拜城,他因解破司芬克斯之迷而加冕为王,娶了王后伊俄卡斯忒——他的生母。由于瘟疫流行,他下令辑拿并严惩凶手——他自己!从古至今,戏剧反讽始终受到作家和读者的青睐,但是,在现代文学中,戏剧反讽已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反讽眼光“内转”,就是说,从前人们仰望上苍,在《俄狄浦斯王》中看到的是自由意志和冥冥天意的冲突,是渺小的个人对命运的无可奈何,现代人则反观内心,看出了别的东西。这种变化的根源与其说在于弗洛伊德,倒不如说在于德国浪漫派——尤其是浪漫哲学家叔本华。叔本华的惊人之举在于宣布意志第一性、认识第二性,并且使西方传统哲学概念——意志——发生了位移,将意志从头部移到下身,使之从理性的、精神的象征变为非理性的、欲望的载体。他说:“在旧说,人是要他所认识的东西,依我说人是认识他所需要的东西”,〔6 〕由此他把理智看作为欲望遮羞掩丑、涂脂抹粉的奴仆。叔本华对传统哲学所作的颠覆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判断人的行为时不再轻信意图与表白。由此,从叔本华到弗洛伊德就只有一步之遥:前者所说的意志和理智与后者所说的潜意识和意识相对应,而且两者都认为肉体和精神、潜意识和意识之间存在着的欺骗与被欺骗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现代人便说俄狄浦斯乃至索福克勒斯都不了解自己,俄狄浦斯那杀父娶母之举看似偶然,违背他本人的意志,实际上是必然的、受其下意识支配的。简言之,深层心理学重内因,轻外因,时刻准备从偶然之中挖掘必然,警惕意图与结果、思想与行动之间可能出现的裂缝,并把这条裂缝视为寻找下意识的突破口。
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深层心理学并非什么灵丹妙药,但它的确可以给文学世界中的某些幽暗角落带来光明,可以同时将作品的“心迹”和“叙事轨迹”展现在人们眼前。卡夫卡的世界同样需要深层心理学的烛照。若用深层心理学的眼光来透视《寻常的困惑》,我们就不难发现甲在下意识里是不想见乙的。如果不想见又不得不见,如果不想见又不想承认,大概就只有寄希望于偶然失误甚至奇迹降临,比如匆忙之中擦肩而过,比如道路突然变长,比如因摔伤而痛苦失声。有了这三种情况,甲就见不着乙,不管后者在丙地等他,还是找上门来或是途中相遇。这种心理、这种思路都极为寻常,而且合乎人之常情,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有类似体验。但是,卡夫卡没有交待他的主人公有这些念头,也没让主人公意识到自己有这些念头,读者也没有看到一个正躺在床上或者坐在凳上的甲。相反地,卡夫卡却真让他的主人公走拢见不着人,真让他跟对方路上错过,而对方也真的等不耐烦走了。而且他并不就这一系列奇怪的事件向读者作出合理的解释,反倒把一些偶然的、似是而非的甚至不可理喻的事情——甲对乙视而不见,道路变长,甲摔跤——摆在读者面前,结果搞出这么一个宛若梦境的故事。简而言之,甲并非“鬼使神差”,而是“心中有鬼”,这个“见不着”的故事底下其实潜藏着一个“不想见”的故事,甲这一连串扑朔迷离的外在经历则不过是他的一番朦胧飘忽的深层心理活动。这种打破内心与外界、想象与现实的做法是极富现代性的。自卡夫卡之后,这种手法几乎成为现代派艺术家的家常便饭。更有甚者,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表演这种穿梭游戏,比如在意大利电影《八部半》中,一位导演伙同两个人绞死了他所痛恨的批评家,可是镜头一转,批评家又唠唠叨叨地坐在导演身旁:批评家没有死,前面的一幕不过是把导演心里对批评家的咒骂——“我绞死你”——化为幻觉,化为艺术现实。〔7〕
如是观之,我们仿佛只有借助深层心理学、只有在头足倒立或者说颠倒黑白的情况下才能看得清、看得懂现代文学画卷,仿佛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现卡夫卡的微言大义,才能从他那些离奇古怪、匪夷所思的描写中找出理性的蛛丝马迹。比如,推销员格利戈尔·萨姆沙(《变形记》)一觉醒来变成一只巨型甲虫,这是否反映出他下意识地厌恶自身,或是下意识地逃避他那艰难职业?乡村医生(《乡村医生》)一脚踹开自家猪圈,里面却跑出两匹马和一个兽性大发的陌生马夫,这是否反映了他的深层欲望?约瑟夫·K(《审判》)躺在床上摇铃催早餐, 却招来一伙逮捕和审讯他的人,这个招之即来的法庭是否是一场内心审判?〔8〕还有,为什么到处都有人好奇地、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 据雅努施记载,卡夫卡跟他初次见面就称自己“是个被审判者,是观众”,〔9 〕这句耐人寻味的话与其说概括了卡夫卡热衷于自我分析自我作贱的性格,毋宁说点破了他的叙事技巧。就是说他在作品中把自己、把自己的内心世界“一分为二”,而且分为一个个完整的、鲜活的实体。具体就《审判》而言,约瑟夫·K是被处决的卡夫卡, 其他人——法庭看守、窗子对面的老头老太太、银行同事、他的叔叔、甚至包括画家提托雷利阁楼里那些小女孩——则是旁观的卡夫卡。难怪画家要说“这些小女孩也属于法庭”,〔10〕难怪他要提醒K “几乎每个屋顶上都有法庭”,〔11〕其实他把小说中最大的秘密泄露给了读者:人最大的恐惧是内心恐惧,世上最严厉最无法逃脱的法庭是内心法庭。只有当内在法庭运作起来,才谈得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有这一切是否都在证明整部小说就是一场情节化、场景化的内心审判?综上所述,卡夫卡是一个写自我、写内心的作家,他写作的奥秘就是不加声明、不露声色地把内心世界投射到外部世界,使虚幻蒙胧的下意识形象化、客体化,由此打破了心灵与外界、幻觉与真实的界限。可以说,卡夫卡创造了一个象征的、二元的、辩证的叙事世界,它是虚与实、动与静、具象与抽象、现象与本体的对立统一体。
悲喜式的写作
卡夫卡的另一叙事特征体现在他那耐人寻味的两面相:一方面他描绘出黯淡、残酷、荒诞的世界景观,辐射出惶恐、焦虑、绝望的情绪。另一方面他的字里行间又流露出冷嘲和怪诞幽默。确切地讲,我们所要探讨的是他那别具一格的反讽艺术和滑稽艺术。反讽和滑稽是两个难以界定的概念,放在一起考察更是难上加难,因为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反讽和滑稽都旨在揭示反常现象,揭示现象与本质、意图与结果的错位,而且都会引人发笑。但是,反讽更多地诉诸智性,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思维活动,它表现为意味深长的“微笑”,所以比较“阳春白雪”,滑稽则更多地诉诸于感性,是一种比较直接的精神——生理反应,它引起的是沁人心脾的“大笑”,所以比较“雅俗共赏”。尽管对反讽和滑稽作出了一番自以为是的界定,但在具体的文学描写中,二者的界限常常是模糊的、变动的,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我们还是从《变形记》谈起。毫无疑问,《变形记》讲述的是一场悲剧,然而,小说里面自始至终都存在一种冷嘲,存在许多似乎与悲剧基调不协调、不相容的描写。看看小说的开头,我们就会明白一大半:
一天早晨,格利戈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躺着,背部硬如铠甲,稍一抬头便看见他那棕色的、穹顶式的、被分割成一条条弧形硬块的肚子,肚尖上的被子难以停驻,整个就要滑下来。相比之下,他那不计其数的腿脚倒是细得可怜,全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晃动着。〔12〕
小说用若无其事的口吻交待了一个奇特而恐怖的事件,同时让格利戈尔显得十分滑稽。令人不解的是,他不去思索,也没有意识到他的虫身即将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所以他还想着自己的工作和职业,一心要起床出门赶火车。随着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他的境况已引起外界关注,家人和上司已站在门外催促、威胁、哭泣,格利戈尔则苦苦挣扎、忧心如焚。可就在这紧锣密鼓、令人窒息的紧要关头,小说却大段大段地、仔仔细细地、从容不迫地描写格利戈尔的“虫性”,写他如何拖着虫身下床翻身开门,如何思索和克服由此必然产生的技术性问题。比如,为了过第一道关,他“开始均匀地晃动整个身体,想把自己摇出床外。让自己这么掉下去,估计伤不着脑袋,因为他想在下落时高高地抬起头。他的背部似乎很硬,落到地上也不要紧。他最担心的是触地时无法避免的一声巨响,那将在几扇门外都可能引起焦虑,即使不是恐惧。可他还是得冒这个险”。〔13〕在第二和第三章中,小说也不厌其烦地描写甲虫格利戈尔的饮食习惯,写他鼓着肚皮藏在沙发底下多么难受,写他如何在墙上爬上爬下、在天花板上晃来晃去,自寻快乐,甚至没忘记交待甲虫爬行过后留下多少脏兮兮的粘液。人们不禁要问,卡夫卡怎么有这等闲心、怎么如此执着或者说迂阔,竟然在一个令人压抑而悲凉透顶的故事中把玩有趣的或者说无谓的细节?这种强烈的反差、这种极端的不和谐是反讽笔法,而且是典型的卡夫卡式的、现代派式的反讽。这种反讽与其叙事方式密切相关。我们知道,作为现代小说鼻祖的卡夫卡放弃了传统小说里面惯用的全知和旁知视角,基本采用人物视角或说内视角。就是说,叙述者和主人公共用一双眼睛、一个大脑,叙述者见主人公所见、想主人公所想,他不再居高临下、无所不知,反倒与那些在思维和感觉方面都不同寻常的主人公平起平坐甚至融为一体。比如在《变形记》中,叙述者与格利戈尔认同,而且既认同其人性又认同其虫性。格利戈尔一方面要甲虫生活,要具备甲虫的习性,另一方面又跟人一样思维,但他对自己变成虫这一事实不从根本上加以反思。他只知道虫身在当下时刻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从不思考变形对其未来及整个生存的含义。这种分裂的意识导致了分裂的文字,所以小说中出现了虫性与人性、大祸临头与拘泥小节的强烈反差。卡夫卡这种叙事风格在《审判》中更是明显。约瑟夫·K目光如豆,既不瞻前顾后也不左顾右盼, 经常冷不丁地撞上神秘人物,同时他的思维缺乏连续性,不能吃一堑长一智,所以要接二连三地陷入意外和惊骇,正因如此,小说中弥漫着恐怖和压抑的气氛。应该说,卡夫卡创造了一种十分高明的叙事手法:叙述者与主人公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读者的视野和思维,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读者与主人公认同、迫使他与之同甘共苦。然而,读者毕竟是旁观者,毕竟有自己的感官和思维,他能够看到和想到主人公所看不到、所想不到的事情。《变形记》的读者一眼就看出家里人的态度,能够预感到格利戈尔的最终结局,《审判》的读者在惊骇两回之后,必然要步步提防、疑神疑鬼,至少在读至《大教堂》一章时,他对神父的出现与背景不可能没有一点心理准备。由此看来,叙事家卡夫卡装愣作傻,目的在于刁难读者、刺激读者,在于制造一种巨大的心理落差:主人公越是心不在焉、稀里糊涂,读者就越是感到恐怖和滑稽,越感到困惑和震惊。这就是典型的卡夫卡式的弦外之音。
如果说卡夫卡的反讽艺术能够制造出上述心理落差,那么他的滑稽艺术又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在卡夫卡笔下,滑稽人物、滑稽场面比比皆是。短篇小说《初次烦恼》的主人公是一位表演高空飞人的杂技艺术家,他“起先是为了追求完美,后来也由于一种无法摆脱的习惯”,〔14〕竟在高高的吊架上度过日日夜夜,生活必需品则靠一个特制的滑轮装置传送。这种悬浮生活对他已是不可或缺,连乘火车上外地演出时也必须睡在行李架上。当饥饿艺术家(《饥饿艺术家》)看出值夜班的看守坐到远处打牌,是为了给他进食机会时,他感到无比屈辱,只好凭借最后的一点力气引吭高歌,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可这纯属多此一举,因为看守们又认为他有边唱歌边进食的本领。粗俗的女仆(《变形记》)为了证明格利戈尔死了,不惜用扫帚将格利戈尔的尸体推出一尺远。在《审判》中,法庭是不容辩驳的绝对权威,辩护律师无足轻重,被告更是轻如鸿毛,所以律师办公室的窗户又高又小,要看窗外就必须踩到同事的肩膀上,所以被告布洛克对律师胡尔德卑躬屈膝,竟然对着黑洞洞的通风口捧读后者随手扔给他的书。《城堡》讲述的是一个人尽管百般努力也还是被城堡机构拒之门外的故事,主人公K是一个找不到自我、 找不到安身之处的人,初次见到信使巴纳巴斯,K 就以为可以跟着他进入城堡,所以他竟然死皮赖脸吊在巴纳巴斯的膀子上跟着他回家;为了尽快见克拉姆,K 竟在黑咕隆咚、寒风凛冽的马路上让一个助手打着灯笼,同时又在另一个助手的背上为巴纳巴斯书写口信内容;失去栖身之地的K冻得瑟瑟发抖,只好用手交叉捶背以获取热量。K的两个助手举止神态似顽童似小丑似宠物,他们专事盯梢纠缠骚扰K, 但方法十分奇特,比如用两只手装作望远镜或者比谁的胡子长谁的胡子密,比如被撵出门后又从窗户爬进来,硬要和K 和弗莉达呆在一起。施瓦泽热恋女教师莉萨,莉萨上课,他就坐在一群小学生中间或者干脆坐到她的脚跟面前;莉萨改作业,他就帮忙,以求“耳鬓厮磨”。城堡的官员们也是些不可思议的人物:神秘莫测的克拉姆“到村子里来是一个样,离开村子又是一个样,喝了啤酒和没喝啤酒不一样,醒着和睡着不一样,而且——这点最令人费解——他在城堡里几乎又是一模样”;〔15〕官员们并排站在斜面桌子旁边读书,换着看时他们不是相互换书,而是相互换位,由于地方窄,换位时免不了你推我挤;他们深更半夜到村子里盘问当事人,是因为对他们而言,当事人的嘴脸在青天白日之下不堪入目,灯光底下还稍微好点,而且可以通过随之而来的睡眠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城堡秘书毕格尔入睡时最好有人陪说话。此外,城堡机构之庞杂,文件之多,也到了滑稽的地步:电话打进去,所有办公室的电话机都有反应,但电话铃声是关掉的,偶尔会有一个疲劳过度、想寻开心的官员打开电话铃,给人答复,但这答复无非是个玩笑;村长家的文件柜塞得满满当当,要想关上就得放倒在地,再让两个人坐上去慢慢把门压上。单独看来,这些描写无甚特别之处,它们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位幽默作家的笔下。可是,一旦有痛苦、焦虑、死亡作背景,这些文字就不免令人诧异。卡夫卡的幽默是一种怪诞的幽默,他的特色和魅力正在于他使痛苦和滑稽、悲剧和喜剧水乳交融的本领。
众所周知,卡夫卡所塑造的都是些异化的人,他以巨大的艺术表现力,全面地、深刻地揭示了他所体验的异化现实,写出了他的恐惧和悲哀。问题在于,恐惧和幽默,悲剧和滑稽本是相互排斥的,为什么卡夫卡又能使两者相得益彰呢?为此,我们可以求助于亨利·柏格森对滑稽艺术所作的经典性论述。在《笑——论滑稽的意义》一书中,柏格森从他的生命哲学出发,把滑稽看成一种偏离和损害生命本质的现象。他认为生命的特征就在于“形体的不断变化,现象的不可逆性,每一系列事件的充分个性”,而滑稽就是“人和物相似那一面,是人的行动以特殊的僵硬性模仿简单而纯粹的机械活动,模仿自动机械动作,模仿无生命的运动那一面”。〔16〕换言之,每当以灵活性、独特性、丰富性为特征的生命变得僵硬、重复、片面的时候,滑稽意味便油然而生。就人而言,滑稽表现为意识——人之为人的特征——的僵硬,因此,无论见到一个踩着西瓜皮的冒失鬼还是一个边啃鸡腿儿边谈禁欲哲学的哲学家,我们都不免噗哧一笑。柏格森的理论具有重大意义。他不仅为五花八门的滑稽现象归纳出一条本质特征,而且无形之中也点破了异化现象的滑稽特性。狭义的异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劳动异己化;广义的异化,是指特定的现实造成的人性畸变。尽管柏格森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提到异化概念,尽管他所探讨的滑稽现象并不具有可怕的、悲剧性的特征,他的阐述却使我们看出滑稽和异化有着天然的姻缘:如果说滑稽是对灵活、独特、丰富的生命的偏离,那么异化便是对自由、健康、全面发展的人的否定。异化,也就是人的机械化、畸形化、孤立化。
必须指出,一般的、包括柏格森所理解的滑稽都旨在通过笑声来消除紧张、化解矛盾,而卡夫卡塑造的滑稽人物却使人大笑之后变得茫然怅然,对嘲笑对象久久不能忘怀。卡夫卡为什么能够创造出这种滑稽到怪诞的艺术?为什么在他眼里不存在纯粹的悲剧和纯粹的喜剧,而只有悲喜剧?我们可以说,柏格森没有意识到、没有说穿的,卡夫卡却意识到了,而且化为了艺术现实;我们还可以说,物极必反,量变必然引起质变,换言之,卡夫卡式的怪诞滑稽效果正是得益于极度的夸张和极度的变形。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往往是滑稽得使人感到悲惨,在悲惨中又显出滑稽。然而,我们并不满足于这类解释,因为这有点浮面化、有点技巧化。我们认为,卡夫卡的悲喜剧有着深刻的世界观根源。鲁迅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17〕就是说,不论悲剧或者喜剧,都要以明确的价值判断为前提。可是,人的体验是复杂的,“悲”与“喜”的界限是相对的、游移的,鲁迅自己创作的《阿Q正传》(比如阿Q死到临头还立志把花押画圆,这是“悲”还是“喜”?)证明了这点,中外文学史上的许多杰作也证明了这点。如果说悲喜剧在以往的戏剧和小说创作中多半属于偶然,属于天才妙笔,那么,就生活在20世纪初的欧洲人卡夫卡而言,选择悲喜剧似乎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随着上帝的死亡,欧洲人失去了信仰的根基,不再有统一的、恒定的、和谐的世界景观,他们是在价值混乱、价值颠倒、价值毁灭的氛围中进入20世纪的。生活在这种氛围中的卡夫卡,用怀疑的、嘲弄的目光观察世界人生,他所看到的,只是痛苦和滑稽,只是无价值无意义,于是,荒诞成为其世界观,悲喜剧成为其审美原则。随着荒诞意识的蔓延,在20世纪西方文学中,泾渭分明的悲剧和喜剧日趋减少,悲喜剧则日益增多,大有成为主流文学的势头。如是观之,卡夫卡的创作具有天才性的超前性。卡夫卡是一位叙而不议、观而不语的小说家,也是一位用形象思维的哲学家,他从不采用理论的、逻辑的表达方式,所以他的思想总给人云山雾罩、难以捉摸之感。不过我们相信,现代荒诞派大师、和卡夫卡一脉相承的尤内斯库说出了卡夫卡的心里话:“在我看来,喜剧的东西就是悲剧的东西,而人的悲剧都是带有嘲弄性的。对于近代批评思想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能够完全加以认真对待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能够完全加以轻松对待的。”〔18〕
注释:
〔1〕研究卡夫卡的人都喜欢谈论“钥匙”,参见Franz Kafka,Text+ Kritik,Sonderband (Hrsg.:Heinz Ludwig Arnold),edit.text+kritik,1994,S.39,S.7.
〔2〕新近的手稿研究表明, 布洛德将“平常的英雄”误抄成“平常的困惑”。布洛德的失误冲淡了作品的反讽意味,但并不影响我们对作品的基本理解。参见上书第12页。
〔3〕 〔12〕〔13 〕〔 14 〕Franz Kafka, Samtliche Erzahlungen,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6,S.303—304,S.56,S.60,S.155.
〔4〕Walter H.Sokel,Franz Kafka, Tragik und Ironie —Zur Struktur seiner Kunst,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3,S.15.
〔5〕《外国文学》,1996年第1期,第46页。
〔6〕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402页。
〔7〕扎东斯基《卡夫卡和现代主义》,外国文学出版社, 1991年,第164页。
〔8〕Benno von Wiese (Hrsg) ;
Der deutsche Roman-Von Realismus bis zur Gegenwart,August Bagel Verlag Dusseldorf .1963,S.246.
〔9〕古斯塔夫·雅努施《卡夫卡对我说》, 时代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6页。
〔10〕 〔 11 〕 Franz Kafka, Der Prozeβ ,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95,S.158,S.173.
〔15〕Franz Kafka,Das Schloβ ,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95,S.215—216.
〔16〕亨利·柏格森《笑——论滑稽的意义》,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第54页。
〔17〕 《鲁迅选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59页。
〔18〕《荒诞派戏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