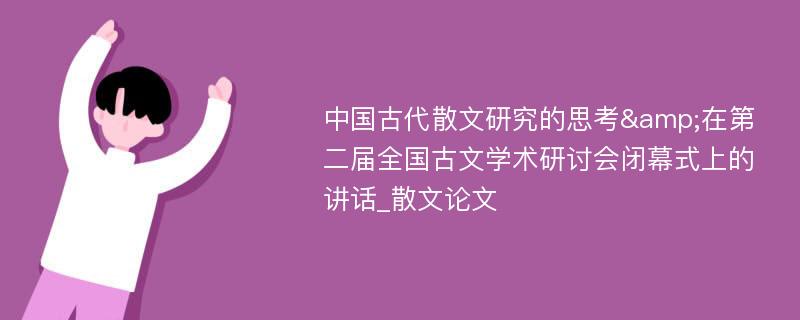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断想——在全国第二届中国古代散文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断想论文,闭幕式论文,中国古代论文,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62/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码:1005—1287(1999)04—0086—03
感谢东道主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换学术意见。我觉得这样的机会不容易得,能够在学术上做交流,在中国自古以来机会就不是很多。有时候我想,咱们国家这么大,如果有机会跟大家见面,能够相互认识,能够以文会友,的确很不容易,所以遇到这样的机会,我很珍惜,也很高兴。当然,要我作“学术总结”,也有些紧张,大家知道学术总结可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因为学术问题有时经过很长时间观点也不可能统一,现在总结怎么总结得了。我只能就自己这几天听到的大家的发言里对我启发大的一些观点稍作补充。当然,不见得能把大家说的所有的精华都概括到,我也不可能做很重要的补充,我这里谈的只能起个“狗尾续貂”的作用。
这次散文研讨会真正达到了学术会议的目的,讨论学术问题,大家都很认真。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虽然不能说面面俱到,但古典散文研究的几个重要的方面,从治学路子、研究方法到文章的风格流派,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等,都讲到了,而且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我很受启发。这里择要作一点补充,附带谈点自己的看法。
关于古代散文的研究方法,是孙昌武先生最先提出的问题。他认为研究古代散文,应该深入地研究古代历史。这个观点我很赞同。鲁迅先生就非常重视历史研究,他曾经说过:“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都应该先看一部简明而可靠的历史书。”但是读历史有不同的读法,孙先生是研究唐代的专家,对唐代文学研究应该怎样与历史结合起来有切身的体会,他以韩愈反佛为例作了具体的说明,谈得深入细微。我觉得很好。唐代对佛教、道教都比较推崇,唐宪宗更是迷信佛教,为了福寿,而迎佛骨。韩愈认为,迎佛骨没有好处,他在《论佛骨表》说:自古以来,没有奉佛的时候,皇帝活的岁数都很大,奉佛以后,却活不长,梁武帝等人就是例子,言下之意说唐宪宗迎接佛骨未必能长寿。韩愈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之下能写《论佛骨表》,很需要勇气,这种文章也很有价值和意义。我们讲古代散文,如能把当时的社会状况、风气与文章结合起来,文章的深度、高度就不同了,理解也就可以更深入。由此我还联想到柳宗元的不迷信仙道。唐代是崇尚道教的,因为崇尚道教,从皇帝到一般大臣,甚至一般的人,都吃些仙药企求长寿。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有人劝柳宗元从养生、长寿的目的出发吃点丹药。柳宗元写信回答说,我吃这个药,即使长寿,对“生人”也没有好处。他的人生理想是活着就要做点事情,要对生人有用处,否则活得再长也没有意义。这样的文章逆潮流而作,不仅在当时有现实作用,对后代也很难得。我们若能联系当时的社会状态和社会风气研读这些文章,就能更准确地把握柳宗元的思想。宋代的欧阳修也反佛,而且反道。他说有的皇帝崇尚佛教或道教,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什么都有了,所缺的只有寿命,寿命不是想要就有的,所以崇尚道教,其目的是为了长生,信仰佛教则是怕死。信道,信佛,一个贪生,一个怕死,他的分析是深刻的。我想:要是有人能写一篇论述中国历代反佛情况的文章,一定很有意义,不一定从韩愈写起,韩愈之前早已有人反佛,包括范缜的《神灭论》在内。韩愈之后有欧阳修,还有曾巩。曾巩分析佛教盛行的原因,在反佛的同时又批评儒家自身。再往后到明朝的陈继儒,对于佛的看法就和韩愈等人不同了。他有篇文章讲到佛教时,说佛家的寺庙对社会有好处,其作用类似“养济院”,那些穷得结不了婚的人可以去当和尚,给养起来,这样一来社会就安定了,因而他说佛教是对国家政治的重要补充。论佛者从范缜到韩愈、欧阳修,再到陈继儒,代有其人,可以专门研究。
韩愈的文章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特别注意人才问题。他主张人才要选拔,选用人才要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进学解》、《原毁》、《毛颖传》等都是谈人才问题,这些作品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的特点。《毛颖传》类似游戏文章,当时就有人不赞成,认为是“以文为戏”。当时最理解韩愈的是柳宗元。柳给人写信称赞韩愈的这篇文章写得好,但他也只是认为文章好,没有看到韩愈的文中所说人才应尽其用的问题。毛颖为秦朝立了那么多的功,起了那么大的作用,最后却因老渐疏,遭到遗弃,批评秦朝太寡恩,对人才太不尽其用。从汉代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到隋末王绩、初唐四杰,都讲怀才不遇,唐代论及怀才不遇的文章特别多,这种情况到宋代却发生了变化。宋代感叹怀才不遇的文章非常少,其原因是宋代文人的待遇比较优厚,科举制度放宽了。宋太祖这个人从孤儿寡妇手里夺取天下,不少讲历史的人都骂他,但他有一个优点,就是对文臣比较宽大,他曾经立了一个戒碑:不杀文臣。这很难得,在宋代树立一个很好的传统。宋初很多人的文章是比较敢于讲话的,因为言事讲话不会被杀。唐代初年,唐太宗虽然也比较开放,也曾有一批人敢于讲话,如魏征等,但到后来就不行了。宋代对文人的待遇则一直比较好。举个例子,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当政的时候待遇很好,换了皇帝,待遇仍然好。自己组织班子,朝廷提供写作条件,供给纸墨、酒果等。经历了几个皇帝,待遇始终没有变,著书立说有这么好的条件,很难得,我觉得在宋代这是很典型的。当然也有个别的问题,比如诗人杨亿曾说他得到的薪水不够维持生活,想到外地做官。但是从总体上看,宋代文人的待遇是比较高的,言论也比较开放,这跟宋代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讲到政治,大家都不怎么说了。有人觉得从政治方面研讨文学,是庸俗社会学。实际上,历代文人写文章都不离开当时的社会条件,敢不敢写也离不开政治条件,文学能不能发展,与政治的关系很大。战国时代,为士者可以周游列国,觉得这个国家不行,可以到别个国家去,不一定要守在一个地方,所谓“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到汉代以后,政治情况就不一样了,东方朔说现在不像过去,我不能到别处去做官,扬雄也这样讲。韩愈上宰相书,有人很讨厌,认为是不知耻。宋代儒者就是这么看的。其实是不理解韩愈的苦衷。韩愈在文章中说,现在不像战国,在这个国家不能做事,还可以到别国去;现在不行,向宰相上书是谋得做事的机会。不能否认韩愈上书时没有解决生活问题的考虑,但那个时候,他是不能不考虑政治方面的问题的。所以,我觉得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分析其思想内容,考察其发展变化,不能不联系当时的历史实际,讲清政治环境、社会风气与文学发展变化的关系。
政治之外,还有经济,对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研究散文不能不加以注意。现在讲古代散文,好像一讲经济就是机械唯物论。但是经济要不要讲呢?过去咱们写文学史,先讲某个时候的经济怎么样,政治怎么样,接着才讲文学怎么样,分成两大块,这当然不好。但是,在文学研究中注意分析经济因素的影响,我觉得有必要,也很重要,关键是要讲得深入细致,讲得具体,不能太空洞。比如我读夏咸淳先生的书,他论晚明散文,援引了许多笔记野史中的材料,讲了很多经济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写得好。鲁迅先生主张读书不仅要读正史,还要读杂史、野史。明代很多经济方面的问题在野史笔记中都有记述,就做官而言,有的杂史记载,在某个年代做官的人,做的官很大,不做官回家时,家里的家底跟做秀才时差不多,没有什么变化;但另一个年代情况就不同了,有些人做官后家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钱了,阔多了;有的书中说某个年代请客吃饭,桌上没有几样菜,很简单的;但是几年后,一请客吃饭,山珍海味,各种新奇东西都有了,人们的穿戴、衣饰,妇女的打扮也和以前不同。如此叙述经济生活,就把时代、历史的面貌具体地展现出来了,读者一看就知晚明文章的变化与社会生活习尚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如果不把社会经济生活情况分析清楚,要论定明代某些文章的好坏就比较困难。刚才刘衍先生提出对明人和明代文章应有一个新的评价,夏先生则谈了谈清代人的看法,我觉得也是可以从这方面入手的。我们现在谈散文,不能孤立地谈,还应该与其他文体联系起来考察。就明代而言,此时出现的小说跟过去也不一样,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金瓶梅》。《金瓶梅》里面讲到“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等谚语,就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生活和社会习尚,这样的经济生活和社会习尚,对于散文的发展变化也有影响。
关于历代作家的研究,大家认为应该力求全面地研究一个作家,深入考察他所处的历史环境,生活状态和创作背景,努力写出一个“全人”来。所谓“全人”,我想,从横的方面讲,他有几个侧面,有的人各方面有不同的表现。从纵的方面讲,一个人生活几十年,也有变化,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表现。拿我自己来说,小时候很幼稚,年轻时候很骄傲,中年以后很糊涂。今人几十年来变化这样大,那么,古代作家在他的一生中就没有变化?肯定有。我们可以拿古代证明现代,也可以拿现代证明古代,拿今人证明古人。我觉得古人不都是圣人,孔夫子也是有变化的,我们不能把人看成一个僵死的、没有变化的东西。既然如此,一个人的文章从内容到风格,从小到大,也是会发生变化的。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许多作家流传下来的文章不全,甚至全集亦不全,比如欧阳修,他的集子是自己选的,不是全集。还有些文集经过朝廷或某个朝代的审查、筛选,更不见得全。例如《四库全书》里面的文集,有些被抽掉了,有些被篡改了,也不全。根据这些文章论述古人当然也就很难见出一个全人,我们只能尽量求其全,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有的学者评论古代诗文,往往根据一点材料就总结出一种观点,比如朱光潜讲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认为这是诗的一种境界,一种静穆的境界,是诗歌达到炉火纯青时的境界。但鲁迅则认为古往今来的诗不见得都是这种境界,而且这“江上数峰青”之前还有“悲风过洞庭”的句子,“悲风过洞庭”就是很萧瑟的景象,其境界跟“江上数峰青”不一样。所以论一个人,仅凭一首诗,一篇文章不够,应该论他所有的诗,所有的文章,分析一定要具体、深入、细致。鲁迅论陶渊明、袁中郎,就是这样做的,他说陶渊明不仅写过“悠然见南山”的诗句,也有《咏荆轲》这样金刚怒目式的篇章。
至于具体作品的读解也很重要,文章读不懂,怎么去分析?古代的东西不容易读,王国维给朋友写信,就说过他读《尚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诗经》不能解者也有“十之一二”。他说不仅他不全懂,汉、魏以来的大师也非全懂。后代的文章也有难于读懂的。我自己对此亦有体会。有的老师提出这个问题,希望青年注意。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基本功问题。
最后谈谈艺术性特征的问题。前些年分析文章,大多从思想性与艺术性两方面着手,这是向苏联学习的结果。以前讲得并不多,有些同志提出讲古代散文还是应该运用我们自己的传统方法。我们有分析散文的传统,比如评点的方法。但当时就有人反对,茅坤评点古文,就有人非议。古代散文的基本特征有哪些?某个时代、某位作家的艺术特点又该怎么讲?这些问题我过去谈过一些看法,我觉得汉语文章的特征与汉语、汉字有关,要说清楚也不容易。具体到某一篇文章,又有其自身的特点。所以,归根到底,我觉得要分析好一篇文章的艺术性,还是要联系作者的“全人”和他所处的整个时代来讲,否则,就事论事,是讲不清楚的。
收稿日期:1999—0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