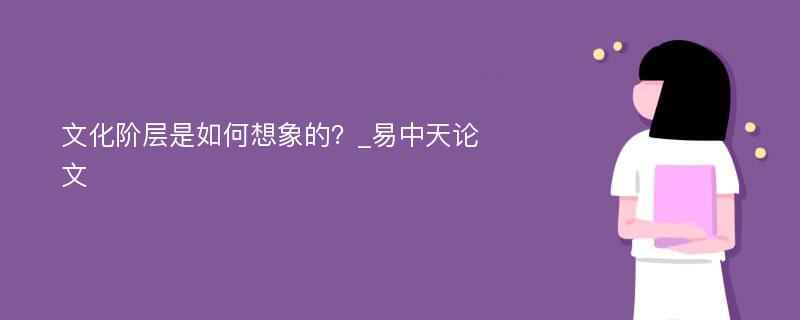
文化阶层是如何被想象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层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文化的意义来说,“文化阶层”横跨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种种可能。大众文化在外在表现形式上往往与精英文化意识疏离、割裂甚至悖立,但就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功能而言,二者也存在着文化秩序和审美趣味有机整合、精神意蕴殊途同归的契机①。在“金字塔”式的社会架构中,大众文化很大程度上是服务精英文化的,而非对于后者的反叛。在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中,大众文化被认为是那种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普及社会大众之中的通俗文化,有明显的商业性质,是一种纯粹的消费品,是一种被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产品”,仅仅满足着人的低层次的精神需求。在功能上,这种文化的本身是服务于精英阶层的,实际上维系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一种天然的鸿沟,使得阶级双方的沟通无法继续,仅仅通过文化售卖的形式来达到精英阶层对于大众在文化上的掌控,大众文化从而起到了一种“社会水泥”的功能价值。
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之下,口语中的“文化名人”一词似乎应该是“知识精英”的代名词之一,但社会心理现实的确如此吗?在大众文化的环境中,无论“文化名人”以平民代言人出现还是以精英教化者的形态出现,他们都可以是文化的创造者与主导者,通过大众传媒,实现着对于文化的控制与社会秩序的维持。换言之,文化名人的文化传播现象研究,对于理解知识分子的社会化作用,具有强烈的示范性。
一、“文化名人”:记忆与认同的差别
为了探究以上假设的合理性,本研究设计了一个有关“文化名人”的公众印象的比较分析,试图研究文化阶层中的“名人”在普通公众心目中的记忆、认同程度及其差别,从而试图更好地理解知识阶层的社会传播过程及效应。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如下:
问题一:公众是如何建构与理解“文化名人”类型之间的内在差异与维度的?
问题二:“文化名人”的公众知名度是通过何种途径建构的?
问题三:公众是如何理解、想象“文化名人”的群体身份与社会价值的?
在建构分析的变量时,本文确定了两个测量指标:1)公众对“文化名人”的记忆程度;2)公众对于“文化名人”的认同程度。通过对于这两指标的定性分析,本研究试图促进对于“文化名人”的公众知名程度的反思与思考,通过自我报告的形式反思记忆与认同这两者之间差异产生的原因。至于知名度的传播途径,访谈者基于传播学的基本经验,将其预设为三种类型:公众的个人体验,主要指自身与知名文化阶层或其作品的交往;人际传播,主要指通过与同侪或其他公众的日常交往间接获得有关文化阶层的相关信息;大众传播,即指公众通过大众传媒(包括网络媒体)间接获得文化名人的相关信息。
本研究是一个探索性的研究,主要采用质化的深度访谈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在研究的推断过程中使用了有限的定量内容分析)。调查对象与访员均为大学的在校学生,调查对象的选择采用便利抽样的方式。深度访谈的好处在于可以很快地获得大量并且广泛的信息,且因该方法可以让访员在被访者表达不清、语焉不详的情况时连续追问或要求其举例,所以比较容易达到资料的澄清。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探索式研究具备创新讨论的价值,但本文的结论不可能具有实证性的推论意义;此外,深度访谈仍有局限性,因为访谈是一种人际间的互动,所以极为需要被访者的配合,而有些被访者可能会不想与访员分享他心中的一些想法,或者对相关的问题感到不舒服;有时,或者由于访员本身的问题,甚至会影响到整个系统信息的收集与分析②。
访问形式分为两种:
1)访员本身的自我采访,即自我报告过程。访员在对他人进行采访之前被要求先对“文化名人”的概念进行思考,并形成自我报告,随后进行自我采访,分别列出“记忆中的文化名人”(不多于10个)及“认同的文化名人”(不多于10个),并给出相关的理由。
2)对于大学生同龄人的访问,采用深度访谈的形式。要求同龄人分别列出“记忆中的文化名人”(不多于10个)及“认同的文化名人”(不多于10个),并给出相关的理由。
3)对于两种报告作综合研究——包括话语分析、内容分析。另外要提及的是,访谈的对话包括了面谈、电话方法,也包括了网络即时聊天、邮件等自我书写的方法。这样的方法设计能够有助于研究对象对“记忆—认同”的指标结果的反馈及其之间差异的比较;能够有助于个体在对文化名人知名度概念思考的过程中做到“感性—理性”的递进;能够有助于访员在访问报告中做到“自我—他者”的比较;有助于本研究对于“个人反思—集体反思”的分析与讨论。
选择在大学生人群中开展的原因主要为:
1)大学为社会中知识人群分布最为密集的机构,但大学生群体不属于文化精英或者知识分子的范畴,因此,一方面,大学生对于文化阶层的接触可能较为密切,另一方面,大学生对于文化阶层的概念属于建构而非被建构的范畴,这样有助于通过大学生这一群体的样本研究能够有效地推及其他公众群体对于文化阶层的记忆、认同与想象的研究。
2)相比较于社会中的其他人群,大学生在文化程度、理解能力、信息接受的广度与深度上都具有相当的优势,即他们在“文化阶层知名度的传播途径”之一变量测量的过程中具有天然的优势,由于他们对于多种信息来源最广泛的利用,致使研究能够最为有效地测试文化阶层知名度在各种传播途径传播过程中的效果。
3)本研究为初探性研究,研究的性质决定了该研究对象选择的面不宜过广,个案的研究有助于最迅速地了解该研究课题的价值,有助于日后进一步的深入与细化的研究。
这部分研究完成于2008年2月至2009年10月期间,共有87名学生担任访员工作,收回访员的自我采访报告87份。这些访员共访问了197名同侪,收回完整的采访报告共183份。
1.记忆的“文化名人”
我们先要求被访者列出他们所能够马上记得并说得出名字的“文化名人”,并给出相关的理由。通过对183份访谈报告的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大学生对于“文化名人”这一知识分子阶层的概念定义极为多元化。
大学生一般会将“文化名人”的定义限定在与文化、文艺有关的专业领域,然而仍有相当比例的大学生将这一概念进行泛化,使得这一概念包含了众多与传统定义中文化不符的相关领域,如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还有一些大学生也将众多“网络红人”、“媒体热点关注现象”涉及的相关人士作为该定义中的范畴。
在“文化名人”定义多元化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学生对于“文化人”、“名人”等概念的多元化或者相互混淆了若干概念后造成的。他们对于“文化人”的定义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专业领域,他们在对概念定义的时候将概念进行了泛化,几乎所有“有知识的”阶层都可或多或少地被调查对象定义为“文化人”。
在本研究的深入阶段,研究者要求被访者列出记忆深刻的文化名人,并且说出相关的理由。在访员自我采访与对同侪的深度访谈中,相当多的个体在回忆的过程中出现了相关的困难。一些被访者由于自我对“文化名人”定义不清等原因,一时无法回忆出相关人名或者在列名单的时候出现了犹豫与反复。大多数被访者由于知识背景和兴趣爱好等个人特质的关系,他们罗列的“文化名人”名单与他们的个人特质有强烈的相关性。在访问报告中显示出大多数被访者在罗列时大多表示会优先考虑他们熟悉的专业、与爱好相关的文化人士。
访谈还表明:被调查者在选择“记忆中的文化名人”时主要参考了这类人士在媒体中的曝光度,这与他们接触媒体的习惯、爱好有关。然而媒体对于这类人士的评价与价值判断却对于被调查者的选择影响较小。被调查者往往对“文化名人”有着自我相对独立的价值判断,然而这类的个人的价值判断却不会影响被调查者在这一问题上的选择,即被调查者坦诚他们在做这部分访谈时主要衡量这些人士的“知名度”而非“贡献度”或者“社会规范”。如众多被访者不认同于丹的国学水平与李宇春的知识素养,但是他们在接受这一部分的访谈时坦诚:他们脑中最先反应的却恰恰是这部分人的姓名,这与这类“名人”媒体极高的曝光度有强烈的相关。
另外,我们可以发现,在选择“记忆中的文化名人”时,众多个体与被选择对象之间没有任何的个体体验的经历,很多情况下没有接触过被选择人的作品或者都不知道被选择人的长相,如很多人没有读过金庸的书,仅仅看过改编自金庸小说的电视剧或电影,没有读过赵丽华的诗、也不清楚王朔的作品,然而他们却将这些人罗列进自己“记忆中的文化名人”的名录。在这一过程中,媒体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些“文化名人”在被媒体传播的同时,被赋予了某种符号的意义,个体所接受的仅仅是这些单独而强烈的符号,而不关心或者不在乎符号的背后。
2.认同的“文化名人”
然后,研究者要求被访者列出他们认同的或称为始终承认的文化名人的名录,并说出相关的理由。在访问的过程中发现,被访者在回答该问题上的难度较大,往往无法说全10个人名。由于知识背景的原因,众多被访者选择了与自己领域相近或者与爱好相近的领域中的知名人士。并且在采访的过程中,被访者坦言在列名单时名次的排序意识要强于列“记忆中的文化名人”。
研究者对所有采访报告中的“认同的文化名人”列表中随机抽取了35份进行量化的统计分析,对所列的“文化名人职业分布”和“首选者(排名第一)身份职业分布”进行了频数分析。所列的“文化名人”中娱乐、文艺界人士(包括作家)占了47%的比例,学者(包括自然科学领域)占了43%的比例,体育、商业、政治领域人士占了9%的比例,其他领域(如芙蓉姐姐等难以归类的人士)占了1%。对该名单中的“首选者(排名第一者)”的职业身份进行频数统计,发现娱乐、文艺界人士(包括作家),占了36%的比例,学者(包括自然科学领域)占了41%的比例,体育、商业、政治领域人士占了23%的比例,其他领域(如芙蓉姐姐等难以归类的人士)则不占比例。
研究发现,被选择的知名人士“历时性”较强,很多并不是近期媒介所热捧的媒介人士,而是逐渐被受众形成刻板印象、内化在意识形态中的人物形象。在对被调查者的陈述理由部分进行质化分析之后,研究得出以下的初探认识:爱国主义、民族情结成为被访者选择的重要理由;学术精英成为选择的重点,学科相近的小群体性成为选择的理由;大众媒介发挥着潜在的影响作用。
3.二者的比较分析
接下来,研究者要求被访者自我解释“记忆中的文化名人”与“认同的文化名人”之间差异的原因,当对这些原因进行归纳分析时,我们可以发现有以下两个较为突出的原因。
(1)两种不同的评判标准的存在。
众多被访者坦言,在罗列两份名单时采用了不同的选择标准。一般而言,在回忆“记忆中的文化名人”时多依据名人的知名度与其在大脑中瞬间的反应结果;然而在罗列“认同的文化名人”时主要参照主流的价值评判标准,以及意识形态、刻板印象、专业背景等综合因素。
(2)大众媒体对于个体判断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研究中可以发现,大众媒体对于被访者确定“记忆中的文化名人”的影响作用要远远大于他们对被访者罗列“认同的文化名人”的影响作用。由于大学生群体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媒介素养和文化批判能力,他们对于大众媒体中所传播的信息能够有着较佳的独立思考能力,这种能力有助于大学生理性思维的重塑,从而产生两份名单中的巨大差异。
二、个案分析:《百家讲坛》与“网络红人”
前述研究显示,有大量的被访者选择了以于丹、易中天、阎崇年为代表的中央电视台摄制的《百家讲坛》节目中的出镜学者作为他们“记忆中的文化名人”或者“认同的文化名人”。现在,我们基于访谈的经验性材料,对这一典型对象作一个分析。
在《百家讲坛》的舞台上,易中天与于丹的媒体曝光度最高,并且在我们的研究中也屡次被被访者提及。从易中天和于丹的专业背景而言,前者并不忝列从事历史研究的重要专家,后者甚至不是专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当他们以一种知识精英的身份在电视这种大众文化为主导的媒介中,以一种卡拉OK的形式普及文化的时候,自于其身份与行为的多重矛盾导致了来自社会各方的追捧与质疑③,无疑反映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在当今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中无法避免的冲突。李泽厚认为:“大众文化不考虑文化批判,唱卡拉OK的人根本不去考虑要改变什么东西,但这种态度却反而能改变一些东西,这就是……对正统体制、对政教合一的中心体制的有效的侵蚀与解构”④。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建构中,精英与草根文化保持着天然的壁垒。尽管在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确立了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发展总方针,精英文化无疑受到了来自商业利润要求的冲击与来自技术对于文化传播手段的瓦解。流行文化,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
面对已经被大众文化浸染的社会,中国的知识分子选择了“自我净化”、“自我隔离”的防范措施,他们普遍的拒绝承担“社会良心”的角色⑤,倡导坚守学术岗位,严正学术规范。199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这种职业化的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不再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态,并且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⑥。而媒体亦对此做出了呼应,在它们的呈现中,知识分子大都是技术专家面目。
然而,于丹、易中天带头打破了这种传统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主动迎合大众文化的口味,因此也获得了来自大众的欢迎。精英阶层指责这类“学术明星”放弃了知识分子理应具有的“启蒙”责任,将知识当作一种可以量化的商品进行贩卖。显而易见的是,于丹与易中天为代表的“媒体明星”已经不可避免地与“学术精英”们形成了某种对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中间层。
其实在知识分子中,持世俗立场的论者早已有之,只不过于丹与易中天成为了坚定的践行者而已。通常,持世俗立场的论者在质疑过度的精英意识的同时,还主张知识分子不应当通过与世俗社会、大众文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对立来确立自己的立场与认同,他/她可以引导、批评它们,但是不应当全盘拒斥它们⑦。李泽厚认为:“当前知识分子要与大众文化相联系,因为大众文化具有雄厚的基础,从‘策略’讲,也应该从这方面入手。而知识分子文化和大众文化之所以可能构成联盟,在于它们都是在新的经济基础之上提出的要求,只是层次不同而已……大众文化一般是盲目的,自发的,跟随着大众消费趋势走。知识分子文化与之联系,将可以引导大众文化,也可以塑造大众文化。所以,它们的联盟有两个作用:一是消解正统意识形态,二是引导大众文化走向一个健康的方向。”⑧无疑,《百家讲坛》中的“学术明星”们仍然属于文化意义上的核心层,只不过他们放弃了传统知识分子阶层所特有的话语体系与思维方式,主动地迎合了大众文化与商业的要求。因此,即使是主动呈现自我的媒体知识分子,那些缺少精神认同者,也一样会随波逐流,沦为媒体或其他什么主宰力量的工具,这里,则出现了一个新的变体:他们没有沉沦,但是变异为了媒体通俗文化的代言人。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这两位学者“认同的文化名人”入选比例要远远低于“记忆中的文化名人”比例。在知识分子分层中,在校大学生属于“外围层”的准知识分子,他们有一定的文化批判能力,在大学的环境中虽然不属于精英阶层,然而却了解理想主义的精英立场。因此,他们在对待像于丹和易中天这样的“学术明星”时,态度会有着相当的分歧。部分被访者承认于丹、易中天是他们第一反应中的“文化名人”,然而在罗列“认同的文化名人”时却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删去。
于丹与易中天这类“学术明星”在通过媒体的包装之后,在某种意味上已经成为了公众潜意识中的“文化名人”,尽管学术精英阶层对于这类的“学术明星”的不屑经常见诸报端,然而学术精英的批判力却无法抵抗住“学术明星”提供给公众的实用的审美趣味与娱乐手段。即使部分公众认同学术精英所做出的犀利的批判,也并不妨碍公众对于这种快餐式的电视文化的消费与满足。
在某种意义上,于丹与易中天身上的“明星”气息已经超越了他们的“学术”身份。此外,在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公众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在“接受”文化,而是在“消费”精英阶层视之为思想的核心知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众多的被访者也毫不掩饰他们对于于丹和易中天的认同与尊敬。
今天,商业化的趋势使得我国的大众媒体已经由精英阶层单头统领的局面过渡到市场、主流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统治的时代⑨。市场的力量主导着我国非政治类媒体节目,使其尽量地满足受众多方的需要。《百家讲坛》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之下,促成了精英的学术知识通过大众文化的包装向普通公众售卖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样促成了一批原先的知识精英将封闭的学术经典话语体系向大众文化的开放。这不仅是文化立场的转化,也是语言体系转化的过程,于丹与易中天为代表的阶层与媒体合谋,完成了这样的工作。
这样的一批善于利用大众传媒作为手段的知识阶层受到了社会的关注,然而在身份上却受到各方的质疑,这种质疑并非由于阶层本身的原因,更多地在于精英阶层与大众的冲突与不协调。
这种不协调,将会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与阶层话语体系的不断融合得到最终的消解吗?这将会是一个新的问题。
说明这个问题的一个最新的文化范本,是与数字化生存成为社会主流以来的所谓“网络红人”现象。我以为,从文化分析的视角来说,草根中心化的“网络红人”现象,正与精英世俗化的“百家讲坛”现象相映成趣。
今天,“网络红人”早已被高高地贴上了“草根文化”的文化标签。草根文化指的是进入互联网时代的一种平民文化的代称,作为一个混杂体系,大型电视选秀节目《超级女声》中的李宇春等人,“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后现代、反权威、反传统的语言的“网络写手”今何在等人……甚至夸张而拙劣地展示自我的芙蓉姐姐及其不遗余力喝彩的拥趸,都可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这个体系中,更多的特征来自于互联网上层出不穷的网络红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网络红人与草根文化的兴盛是密切相关的。
在互联网时代之前,由于传播技术的限制,信息传播的主导权掌控在精英阶层的手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随着电视商业化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赋予了普通民众更多的接收、传播和共享信息的权力。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出现了一个被命名为“后偶像时代”⑩的时期,在我国,这个命名与传统的政治偶像、传统的文化偶像及商业偶像时代相对应。
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在社会文化方面,原有的“金字塔”结构已经逐渐被平权化的传播技术所削弱,在社会的底层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个“网络型”的文化共享平台。草根文化借助着先进的传播技术,迎合着商业化盈利的需求,逐渐朝向“精英文化”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有力的反扑。
方兴东在《大教堂里的章子怡和大集市中的芙蓉姐姐》一文中指出,“互联网的力量已经超越社会精英的把握,义无反顾地走向大众主导阶段,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也不管我们喜不喜欢”。(11)戴维·申克认为:“在今日的注意力匮乏社会,人们却发现,举止粗野是通向知名度、金钱和权力的捷径。这么多极富天赋的煽情主义的杂耍不表演,使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着一个被传播学学者凯瑟琳·霍尔·贾米森称作‘夸张的寻常化’的过程。……为了捕获注意力,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不但被容忍,甚至被景仰。骇人听闻的举止,获得了财富和权力的回报。”“未来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已经形成,它的颜色是刺目的氖气灯放射的光芒,它的音响特征是叫嚣、唾骂和爆炸,它的文化商标则是极尽粗暴之能事的公共关系噱头。”(12)方兴东认为精英体制下的文化“大教堂”模式受到了来自文化“大集市时代”的全新压力。(13)这种压力来自掌握了传媒技术与资源的草根阶层,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原有的文化生产机制与传统的文化审美趣味,超越了精英阶层可控范围,成为一种独特的、相对独立、富有生命力的全新文化阶层。
在社会阶层属性上,这批“草根文化名人”大多属于社会中产或者中产以下的阶层,尽管在经济上或许无虑生计,但是在社会话语权上却存在一定的缺失,也正是这种话语权的缺失使得这批人使用一种另类的、非主流的反文化或者娱乐的方式赢得主流社会的关注;与此同时,文化精英和主流媒体的批判,也用另一种方式成就了草根文化的定型。
如果对本研究所有采访报告中的“记忆的文化名人”与“认同的文化名人”列表作分析,统计“草根文化名人(例如李宇春、芙蓉姐姐、胡戈、今何在、郭德纲等)”出现在两份名单中的比例,那么将很容易发现:文化名人虽然大量地被公众所记忆、认知,然而在公众心目中的认同度则较低,无法受到被访者的尊敬。大多数的被访者虽然乐于接受这类草根文化,并且在媒介接触中也会主动地搜索这类文化,然而在理性上却表达了对这类文化的反对与不屑。
三、进一步的讨论
在上述讨论中,我们首先能够看到的是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与文化生态的尴尬。尽管知识分子在中国仍然以知识精英的形态生存在社会中,然而从整体来看,中国至今为止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群体。安琪认为:“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越来越背离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意识,特别是共产党执政以后,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高压,一部分知识分子与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合流,将另一部分知识分子挤压为这一专制机器的祭品。”在各种惊心动魄的政治运动与阶级斗争下,更多的知识分子丧失了思维能力,甚至不自觉或者自觉地放弃了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14)
尽管在1978年之后,中国政治环境得到了改善,原有的政治高压已经逐渐缓解,然而商业力量对于学术界的冲击,再一次使得知识分子回到了文化理念上的迷茫,与此同时,意识形态的管制和媒体势力的强盛又再一次剥夺了文化的独立精神。
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只能在官方意识形态允许的架构之下生存,并且紧紧地依附于中国现有的政治生态环境。这种依附的现象同样存在于大众文化的领域。然而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更多的受到商业力量控制的大众文化,却在文化抵抗方式上与中国的精英阶层有着不一样的处理方式。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政治结构的转型与经济的迅猛发展,公众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信息,并且能够享有更多的信息共享、发布的权力。然而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之下,这种权力仅仅局限于不对政治体系造成冲击的前提之下,而普通的公众在中国现有的离散的社会结构之下不具有冲击政治权威的可能与条件,这样,他们只能以一种另类的、消极的方式无视或者“恶搞”主流文化以达到发泄的目的。主流文化被一种极端的另类的“草根文化”所解构,在本质上而言,这种文化与激进的西方摇滚文化并无二致,只是——中国的草根文化更为消极。
在本研究中,被访者对待通俗化的精英文化与草根化的通俗文化的态度,竟有相当的相似之处,即:大众对他们,愿意付出关注,但却不愿付出尊重。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1.文化从对象化到自我化的转变
对于网络红人和草根文化人物的记忆与认同的矛盾说明了:一方面,公众对于草根文化的热忱引发了媒体的包装宣传,媒体的反复宣讲则助长了草根文化在公众记忆中的扎根。另一方面,公众并非是把这些文化对象视同于文化本身——因为他们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文化参照物:他们自身。
文化名人的概念,在被调查者那里为什么会呈现为所谓的网络红人、草根文化名人?一个表面的理由无疑会是:它们代表了另外一种文化。但是追根究底,这种文化却是由其拥趸建构的——这些观众就是俗语所称的“粉丝”(fans,“迷”)。从媒介批评和公众生活的角度看,当下的中国社会传播宛如一个旋转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主演的,是“非著名演员”(如郭德纲)的火热表演,和一些类似“超女”、“梦想中国”的媒介狂欢。2005年,大约可以称为“超女”年,2006年,“梦想中国”使出浑身解数向着全中国观众邀好,2007年以后,则是“快乐男声”、“名师高徒”等一大批选秀节目的同存共荣。如果我们在这个时代左顾右看,媒体喜剧还有“天仙妹妹”、胡戈及其无数化身,而“反偶像”式的媒体闹剧还有木子美、芙蓉姐姐、凤姐……这些光怪陆离的媒体事件中唯一的共同点是:草根偶像成为焦点。进一步观看:那些草根偶像的光环背后,那只看得见的手,是“粉丝”。
为了缔造自己的偶像,也为了让自己的偶像成为更多人的偶像,粉丝们不畏辛劳地奔忙呐喊,利用手中的网络、短信和现场资源,粉丝们参与了一个个造星神话。粉丝造星现象的集中出现,一个最为可能的解释是:在一个注意力高于一切的媒介时代,粉丝意味着一切:收视率,广告,收入。在草根偶像和粉丝秀的背后,“超女”上演了一场财富传奇:1400万的节目冠名收入、7场总决选2000万的广告收入、3000万元的短信收入;湖南电广传媒股价上涨1.24亿元、赞助商蒙牛实现2.5亿元纯利。在这样的榜样的力量下,无论是在尊贵如“中国中央电视台”还是贫贱如“非著名演员”郭德纲那里,草根偶像和粉丝的秀还会继续下去,而且愈演愈烈。
我因此而以为,内外因素的多重作用,导致了今天的粉丝和从前的拥趸有了很大区别——他们作为一个社群正在日渐崛起,而且日益主动参与着当代中国文化的转型;与此同时,也导致了粉丝作为下种文化信号正在被整个社会逐步放大。“粉丝”社群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具有了社会动力学意义上的群体功能。而我们真正要重视的是粉丝势力背后所蕴含的那种文化觉醒力量。
自然,以此为信号,文化觉醒或文化叛逆的理念进而有可能向社会、经济等领域逐渐渗透。粉丝的成长,带来身在其中的紧张;粉丝的渗透,带来旁观者的畏惧。这些紧张和畏惧,都无一例外的源自文化反抗的力量。近世以来,无论什么明星,大都是由权力部门、资源部门打造的,粉丝似乎只有“追”的份;但是现在,草根也可以作为主体参与造星了。这样的现象来自一个广义的社会文化的冲击。隐藏在背后的,我想应该是更广大的大众对那种已经日渐守旧、假模假式的文化规则的否定和反抗。
说得清楚一点,也许很多民众并没有从文化高度来认识个人的态度和行为,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们现在所坚持的、所追捧的是草根文化,其对手正是不入大众之眼的庙堂文化。当庙堂文化已经形成了绝对主流,仪式化、符号化、规范化的国家文化、媒体文化,不知不觉中已经和民众产生了很大的距离的时候,必然会激起某种集体意识的反弹。
简而言之:人们会用自娱自乐来消解那些他们不喜欢的文化所带来的压迫。在这个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春晚。当试图给全国民众带来民俗与欢乐的春晚也成为庙堂时,必然会激起某种反动,这种反动未必只存在于春晚的收视率的持续走低上,更可以反映在一系列的文艺事件中,比如“超女”、郭德纲、“馒头血案”。因此,“粉丝”现象绝不仅仅是“粉丝”,它代表着一种反抗的力量,代表着对体制内文化的集体不认同。
推论是:这种反抗和不认同,体现了文化解构的力量,却并非是一种成形的文化建构。于是,当公众付出关注时,他们选择草根;而当自省认同时,他们却可能不会选择草根。
2.文化传播的“网络化”转型与大众对文化精英想象的重构
文化传播的“网络化”具有以下三种内涵:其一是社会文化的多元化,不同文化的交织构成了一种类似于网络形态的多向度交流与回馈;其二是在强势传媒时代的基于各种传播力量的复杂竞争,所形成的传播主体的多极化;其三,在互联网传播的概念和体系下,传播的信源与信宿的界限日益模糊,传播的对象日渐主体化,导致了“泛传播”形态的发展。
我曾对“泛传播”形态的传播学意义作过如下总结:“我们把这种影响定义为泛化影响,而定义这种泛化影响,则基于对传统传播时代向新传播时代变动所做的全景化判断:
(1)由静态的化为动态的;
(2)由确定的化为不确定的;
(3)由狭义的化为广义的;
(4)由单向、双向的化为双向和多向的;
(5)由集中的化为分散的;
(6)由控制的化为自由的;
(7)由稀有的化为普及的;
(8)由对立的化为融合的;
(9)由相对孤立的化为普遍联系的;
(10)由物理的化为人本的。”(15)其结果则是“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式的传播大行其是,传播的“网络化”开始具有后现代意义的分散性。
方兴东曾经如此评价过当代的传播技术对于文化传统传播体系的冲击:
“他们(芙蓉姐姐、木子美、流氓燕等)源自于草根,不来自于主流,更不来自于精英可控制和可预测的传统流程,而作为社会深层变化的表征。主流机制依然会强有力地运作,但是走向金字塔顶尖(影响力和资源汇聚的顶尖)新的通道已经打开,而且面向所有大众成为可能。精英体制的大教堂模式将受到全新的压力。新的‘大集市时代’在徐徐拉开帷幕。大集市模式不是简单颠覆或者替代大教堂模式,而是一个全新的补充,更可能推动大教堂模式的变革。两种模式将共同丰富人类社会文化。”(16)
传统的文化传播的“金字塔”结构拥有严格的等级壁垒,知识的传播必然由文化的精英向大众以普及的方式作直线灌输,大众对待文化自然秉持着虔诚的态度,以一种仰望的姿态被动地接受来自精英指定的文化。然而传播技术的发展将精英的特权无情的解除,蓬勃兴起的商业的力量也瓦解、稀释了原有的话语体系与传播方式。现今的知识分子只能平等与大众分享知识,在一个网络化的结构中互相争夺受众的眼球。这背后的力量自然是来自商业的驱使,这种力量使得曾经贵族化的文化可以被普遍地消费。
在文化向着“网络”形态的转型中,也许最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个结果:大众对文化的想象发生了偏移,与此同时,对文化的代表者——文化阶层(尤其是作为其精英成分的文化名人)的想象也产生了重构。
“文化名人”是一种社会标杆的象征,尤其在大学生群体,文化偶像更是被年轻人想象为一种非世俗的精神,其中寄托了他们的冲动与激情,更寄托了一种对于理想的执著。但是现在,一切都面临着瓦解的可能。
文化名人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偶像的范畴,公众对于偶像的崇拜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于自我身份的想象,对于梦想的一种“代入”性的实现。尽管不能将文化名人严格地等同于偶像,然而文化名人对于公众的作用是一种深刻的认同——部分来源于公众对于其身份、气质、理想与价值的向往与想象。
可是,当知识成为方便共享之物时,公众对于其有形的价值的认同被消解了;当文化觉醒首先表现为文化反抗时,公众对于其无形的价值的认同被消解了;当知识分子在强大的权力和主流文化势力面前畏缩时,公众对于其身份符号的认同也被消解了。最后,强大的媒体势力出场了:它们负责迎合并助长这些消解——因为这种迎合和助长是其实现市场价值的唯一通道;它们负责经由反复灌输和宣传,将新的文化记忆植根于公众的大脑——自然,它们也就带来了“文化名人”概念与指标的混乱。
这种对文化精英的想象的重构,无疑有其积极的一面:使得文化系统逐渐因为异质化而产生进化的推动力,但是其代价则是文化舆论、文化价值观、文化认同的模糊。
唯一值得庆幸的,也许是这样的一个事实:这种对于文化舆论、文化价值观、文化认同的模糊,尚未达到根本颠覆的程度。调查中我们看到的“被记忆的”与“被认同的”名单的反差,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明证。换言之,不管文化的革命、媒体的冲击有多强烈,文化价值观的基石仍然健在——它们所呈现的,恰恰是那些经久不息的、普世的文化认同。
于是,文化作为传播的记忆和认同就带来了双重挑战:通俗化的文化力量挟媒体之威向固守象牙塔的知识分子炫耀他们在市场上的成功;草根化的文化力量向代表着权威的知识精英宣告他们对传统的反叛。知识分子对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可能不发出回应,这种回应的唯一路径,或许正是其一贯的文化品质和批判精神。
我们所观察到的对文化名人的记忆与认同之间的分裂,来自于当下社会的文化价值观的含混与多元,尽管传统的普世的文化价值观仍然在发挥影响力,但是市场力量的绝对主导和意识形态的全面挤压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世俗文化力量的挑战,与此同时,草根文化对庙堂文化的反动,以及知识分子公共性的普遍退缩,促使了新的一代在文化观念上的反叛。这样,双重力量的破坏导致了文化记忆的重构——不仅在文化、文化人的概念上,今天与以往相距甚远,而且在文化行动的规则上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所有这些冲击,唯一可以辨识的来源是:大众传播。具体而言,近世以来的文化传播的“网络化”,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尽管作用巨大而空前,但是这种来自传媒的文化刻写也有自己的盲区,实证表明,世俗文化力量的挑战以及文化观念上的反叛,并未完全破坏漫长历史所建构的文化认同,迄今为止,公众内心深处的文化标准,是与其口中所谈的文化标准有所区别的。反映在现实中,他们所乐于记忆的文化,未必就是他们乐于认同的文化;他们所乐于记忆的文化名人,未必就是他们乐于认同的文化名人。
有线索表明,这种对于文化传统的反动或扰动,仍然是处在集聚实力的时期;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所反映出来的并非确定的意见,而是文化的时代情绪。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推论:有可能被历史认同的知识阶层未必是当世所欢迎的;当世所欢迎的则未必是会被历史认同的。另外一个颇为吊诡的推论则是:有可能被公众认同的知识阶层未必是公众所欢迎的;而公众所欢迎的却又有可能是他们内心所排斥的。
从受众研究的视角看,社会公众的对文化名人的记忆与认同的分裂,一方面与媒体的精神导向、专业水平有关,另一方面也无疑与公众自身的媒介素养水平有关。如果论及这个时代文化结构与文化精神认同的缺陷,那么我们可以说,整个社会的媒介素养的低下,甚至缺失,受众面对媒介宣传缺少认知、批判的能力,既无力于鉴别,也无能于竞争,这是当下社会文化价值观变异的主因。
而站在文化核心阶层——知识分子的立场上看,这种来自社会公众的变异的认同,无疑也造成了中国文化阶层自我想象的混乱与悖论。更进一步说,这种变异,或许正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日益混沌、矛盾、暧昧、复杂的根源。
注释:
①吕广利.大众化文化思潮与精英意识的悖立、整合与共生.广西社会科学,2005,(9).
②Marshall,C.& Rossman,B.G.(1999).Designing Qualitative Research,3rd edition.London:Sage Publication.
③例如,2007年中国高校十大博士联名抵制于丹现象,复旦历史学教授朱维铮的论文亦对于丹现象持严肃的批评立场。
④李泽厚等.关于文化现状与道德重建的对话(上).东方,1994,(5).
⑤⑥⑦佚名.圣人立场与贫民立场.http://www.paper800.com/N122/4D9D62F1/
⑧李泽厚等.关于文化现状与道德重建的对话(上):东方,1994,(5).
⑨Zhao,Yuezhi (2003).The state,the market,and media control in China.in Pradip Thomas and Zahoram Nain (eds.),Who Owns the Media:Global Trends and Local Resistance (Penang,Malaysia:Southbound Press and London:Zed Books,2004,179-212)
⑩从芙蓉姐姐现象论后偶像时代的来临.http://ent.sina.com.cn/r/i/2005-07-05/1726771275.html
(11)方兴东.大教堂里的章子怡和大集市中的芙蓉姐姐.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78896.html
(12)戴维·申克.信息烟尘——在信息爆炸中求生存.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13)方兴东.大教堂里的章子怡和大集市中的芙蓉姐姐.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78896.html
(14)安琪.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忏悔.http://publishblog.blogchina.com/blog/tb.b?diaryID=5218630
(15)杜骏飞.弥漫的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3.
(16)方兴东.大教堂里的章子怡和大集市中的芙蓉姐姐.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78896.html。
标签:易中天论文; 大众文化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精英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于丹现象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知识精英论文; 百家讲坛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自我认同论文;
